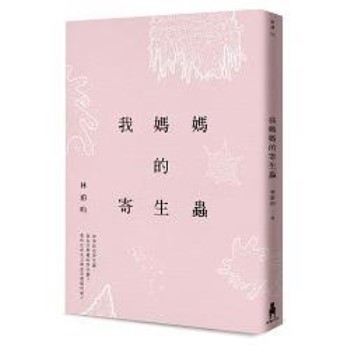絛蟲
我小時候經常和朋友一起去河邊釣魚,那些魚都有絛蟲,我們把蟲從魚肚子裡扯出來,把它們埋在土裡(因為怕狗去挖),然後把魚烤來吃。有一次,在我們埋完蟲後,有一個小孩跑來附近玩。他在地上東挖西挖,也不知道在挖什麼。後來他的爸媽來找他,他驕傲地轉向他們,手裡拿著我們的絛蟲,大喊:「哈哈哈!你們看我找到什麼?鞋帶!」──我的波蘭朋友E和我說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童年回憶之一,是一隻在東京「目黑寄生蟲館」看到的絛蟲。
那是人的絛蟲。牠到底有多大我已經忘了,只記得很大很大,像輓聯或那種用來上吊的白布條一樣掛在牆上,比當時的我高出好幾倍,而且還繞了好幾圈。想來應該有十公尺吧。也許,牠並沒有這麼大,只是在我孩童的眼光看來,牠簡直大到不可思議。
我會看到這隻絛蟲,是因為我媽媽。她當時在台灣知名學府T大的寄生蟲學科工作,是那裡的副教授。當別人問起她的職業,她總是曖昧地笑著說:「我在教寄生蟲。」言下之意,學生也是寄生蟲。所以那些學寄生蟲的研究生為了避嫌,都說他們是「微研所」的學生,而非「寄生蟲學組」學生。
從我有記憶開始,寄生蟲就存在於我生命中,和我常相左右,像是童年最好的玩伴或最棒的玩具(雖然,牠不能陪我玩也不能讓我拿來玩),或甚至,一個隱形的手足。
在我開始學英文,認識ABC並且會說第一句英語「How are you?」之前,我就記住了一個非常難並且拗口的英文單字──Parasitology(寄生蟲學)。我媽媽指著電梯前的樓層標示向我解釋這個字,當時小小年紀的我發下宏願,要把旁邊其他的英文單字如Anatomy(解剖學)、Pharmacology(藥理學)、Biochemistry(生物化學)、Public Health(公共衛生)……都背下來。
我有沒有想過要和爸媽一樣,成為一個具有博士頭銜的生物學家?答案是有,也沒有。我小時候第一個志願是當動物園園長(因為父母都是學生物的),後來是當發明家(這是因為看了小叮噹),之後是當小學老師(我父母、我外婆和我曾外祖父都是老師),十二歲的時候我立志當作家(這是因為看了張系國的小說《棋王》),然後念國中時我突然說,我要去研究水母(因為在帛琉看到的水母很漂亮,而且我想試試看被水母螫到是什麼滋味)。
爸媽對我宣布要去研究水母的事沒有多作評論,爸爸只說:「如果妳要念水母,妳就要去法國,那裡的水母研究是全世界最好的。」我至今不知道他們對此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是開心「女兒終於走上正途了」,還是憂慮「唉她的興趣又變了」或是恐懼「天啊她也要變成一個博士嗎?這一定是我們家逃不掉的命運」。說到命運,也許「當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真的是我們家的命運兼詛咒。我媽媽的外公是前清秀才,我外婆的姊姊是女子學校校長,我媽媽和我兩個舅舅都是美國博士,而我爸爸是他家唯一的博士,因為我外婆在我爸爸第一次來我媽媽家吃飯兼面試的時候,把他叫進房間恐嚇他:「我女兒可是要出國念博士的哦,如果你要娶她,就要和她一起去念。」
生在這麼一個博士過剩的家庭,從小又被一堆博士、博士後、助教、副教授、教授、系主任、院長……包圍(是的,那些在我小時候陪我玩的青蛙姊姊、大魚姊姊、蚯蚓哥哥……在我長大後都變成各大院校的菁英),任何人照常理判斷,我爸媽應該會希望我拿到一個博士學位(白金會員卡),加入他們的學術圈(博士俱樂部)才對。
然而,從我有記憶以來,爸媽就不斷對我耳提面命:「不要當博士,不要爭第一名。」(這句話就和我媽媽的寄生蟲一樣,一直和我長相左右)他們的說法是,他們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看到太多可悲的案例,太多人為了爭第一、進好院校、念博士而搞得遍體鱗傷,不知道人生除了博士之外還有什麼目的。然後有一天,當他們考到人生第一個九十九分,他們就崩潰了,得憂鬱症或自殺。
「得了博士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我爸總是這樣語重心長地作出結論:「現在博士太多了。而且,就算妳當上教授,也要像我們一樣每年被學校和學生評比,太沒有尊嚴了。妳看我做PowerPoint這麼認真,一堂課花了幾百個小時,我的學生還是不領情,說我尸位素餐,真是太沒有良心。」說完這句話,他又回去繼續弄他的PowerPoint。
然而,我爸媽沒有料到的是,他們的寶貝獨生女沒有念博士、沒有從事生物學研究,人生之路卻還是一樣走得不太順遂。
這些年來,我歷經休學、憂鬱症發作、自殺未遂、強制入院……現在雖然情況比較穩定了,也在專業領域有一番成就,但在金錢和情感方面,我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著父母,就像是一條寄生蟲。
如果我是寄生蟲,我會是什麼樣的寄生蟲?我的生活史又會是怎麼樣的呢?
跳蚤
被跳蚤叮咬有別於被蚊蟲叮咬,當跳蚤叮咬人時,會分泌一種出血唾液,破壞人體皮膚之表皮組織,使得被叮咬部位除痛癢外,並出血;所以皮膚上留有紅點;而且跳蚤叮咬時不僅只叮咬一處。被跳蚤叮咬另有一特徵,即被叮咬的部位多在膝蓋以下之小腿;此乃因跳蚤擅跳,一躍可達二、三十公分(所以才叫做「跳蚤」);又跳蚤的成、幼蟲多棲息於地板的塵芥內,羽化的成蟲自地面跳上來咬人,所以被叮咬的部位多在膝蓋以下之小腿。(⋯⋯)有些人或動物對蚤叮咬特別敏感,奇癢難忍,呈過敏現象,有的人則不痛不癢,毫無感覺。──台灣環境有害生物管理協會網站
被跳蚤咬應該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悲慘、最荒謬可笑的經驗之一。被咬之後,我無時無刻不在抓癢,上課抓,吃飯抓,睡覺抓,而且越抓越癢(撇開整件事的悲劇性,這個動作其實是深具喜感的,就像那個「香港腳,香港腳,癢又癢」的廣告。)我全身沒有一處完好的皮膚,精神更是瀕臨崩潰邊緣,每分每秒都覺得煩躁、不安、不知所措──這是在我還不知道被跳蚤咬了之前。當我確認自己被咬,我的情緒還加上深深的憤怒、無力和絕望,因為當時的我無法做任何事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是在倫敦上語言學校時,在寄宿家庭被咬的。那年,因為憂鬱症而高中休學了兩年、不想再回到台灣教育體制、又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出路的我,在倉皇之中決定到英國遊學三個月。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想要在當地找學校,第二是試水溫,看看自己是否能適應國外的生活。第三個原因說起來有點無聊,但卻是促使我在十七歲離家的主要動力──我想證明給大家看,像我這樣的溫室花朵,也是有能力獨立生活的。
身為獨生女,我從小就被家庭保護得很好(我連短暫離家出走到金石堂都會被我爸跟蹤,自己卻渾然不覺),也處處依賴父母的幫助。
念國中時,因為無法早起趕公車,所以每天我爸爸都開車或坐計程車帶我上學。選高中時,我想要脫離家庭獨立,於是選了離家很遠的景美女中。但是直到甄試錄取,我才晴天霹靂地發現:原來只有外縣市的學生才能住校。打錯如意算盤的我,只好天天通勤,又因為爬不起來,再次讓我爸爸坐計程車帶我上學。
在別人眼中,我確實是個依賴、缺乏生活能力的小孩。許多事我只要表示擔憂,甚至不用開口要求,父母就會自動自發替我著想,幫我處理好。比如,十七歲時第一次當導演做小劇場(我去投一個藝術節的公開徵件計劃,結果被選上了),不知道上哪裡找排練場地,爸爸就把他學校的辦公室借給我用。後來要公演了,劇場卻在滴水,爸媽也到場幫忙拖地板,讓主辦單位嘖嘖稱奇:「別人來搞劇場,父母都威脅要打斷孩子的腿,從來沒見過這麼相挺的。」
我一方面享受父母照顧帶來的方便,另一方面深深引以為恥。當別人對我說:「哎喲,妳就是一個千金大小姐嘛。」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覺得別人只看到我的先天優勢,卻看不到我的後天努力。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父母的庇蔭和高成就成了我身上一個帶來恥辱的印記。我曾經這麼希望:要是我父母很貧窮、很普通就好了,這樣別人就會把我的成就視為是我自己努力得來的,而不是把它當成理所當然的、我父母的一部分或延伸。
十七歲的我很不獨立,又渴望獨立──或者該說,渴望證明自己的獨立。因為這樣,我鼓起勇氣開始第一趟「自助旅行」:我立志環島一周,到朋友家去住,用攝影機去拍他們的生活。這個計畫一開始聽起來很棒,執行起來卻十分困難。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在外旅行過,也缺乏和他人相處的經驗。結果只出去三天,我就夾著尾巴回台北了。這次的失敗讓我感到更加屈辱,於是我痛下決心:下一次,我要去一個更遠的地方,不那麼容易回來的。
我選了英國。為什麼選擇去英國,而不是我父母曾經留學過、較為熟悉的美國?一方面是因為我很喜歡英國導演Danny Boyle拍的《猜火車》,覺得它是關於尋找人生意義的另類經典。
(雖然內容是在講一群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不是在吸食海洛因就是在上床,或是把自己的人生搞砸。)另一方面,我那時極度需要離開父母的保護,當然不能選一個他們熟悉的環境。如我所料,我爸媽對英國很陌生,在那裡也沒什麼熟人。他們本來反對我去,但在我堅持下還是勉強答應了。後來,他們發現我的表哥在倫敦工作,這讓他們放心不少。
我在父母陪伴之下來到了倫敦,開始在滑鐵盧附近的語言學校上課,他們則在英國停留了三個禮拜,帶著我的履歷到各大學去拜訪,幫我詢問申請學校的事。我覺得他們多管閒事,但也沒有拒絕他們的幫助。等到他們飛回台灣,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興奮刺激(我終於可以證明我的獨立了,而且是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大都市!),伴隨著恐懼不安(我真的有辦法證明自己嗎?)。
最初的那段日子處處充滿挑戰。因為英文還不是說得很流利,加上個性退縮,我在與人溝通上遇到許多困難。許多事我不敢問,不敢尋求別人的幫助,不敢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事,甚至不敢開口和別人聊天,也就很難交到朋友。我在倫敦的第一個寄宿家庭住得不是很舒服,卻沒有勇氣和學校說,於是打公共電話向媽媽求救。媽媽幫我打電話和學校反映,學校於是給我換了一個寄宿家庭。我很感激媽媽出手救我,但同時也感到非常丟臉,覺得我真是遜斃了。我不是要離家證明自己獨立嗎?怎麼現在卻像個在外頭被欺負,哭哭啼啼回家要媽媽安慰的小孩呢?
在第二個寄宿家庭我打定主意所有事情自己解決。我積極和室友社交、和寄宿家庭的女主人聊天,讓別人喜歡我。我給人如此好的印象,後來媽媽來倫敦看我一個禮拜,寄宿家庭的女主人還邀請媽媽來她家吃晚餐。有一個在英國住了很久的朋友後來對我說:「這表示她很喜歡妳,英國人不常請陌生人到家裡吃飯的。」
也許就是基於這種好感,以及害怕打破這種好感的顧慮──當我知道寄宿家庭的貓身上有貓蚤,而且我還被牠們咬了的時候,我不敢採取任何行動。
我的德國室友就不一樣。她不喜歡女主人,女主人也不喜歡她。所以當她被貓蚤咬,就義無反顧地搬了出去
(不過,她事後才告訴我關於貓蚤的事,那時我已經被咬得慘兮兮了。旁邊的西班牙同學還開玩笑地指著滿臉血痕的我和已經康復的她對大家說:「你們看,這就是『整形前』和『整形後』的差別喔!」)。我一方面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被咬,另一方面不想破壞和女主人的關係,所以只暗示性地對她提到:我「可能」有被跳蚤咬,「也許」是來自她的貓。
女主人的反應比我預期的激烈,她用比平常高八度的聲音說:「這是不可能的!傑克是一隻好貓!妳大概是過敏吧!」
在語言學校的心目中,她是個優秀的寄宿家庭主人。如果他們知道她家有貓蚤,可能就不會再送學生到這裡來了。我和媽媽訴苦,但是同時央求她嚴守秘密,不要和任何人說這件事,免得破壞我和女主人的關係。「反正再沒多久就要回台灣了,現在搬家很麻煩,而且我和女主人約好要把一部分行李寄放在她家,之後回英國可以直接帶到大學宿舍(是的,感謝父母的奔走,我申請到了愛丁堡一所學院的大學預科課程),現在我們就不要撕破臉吧。」我對媽媽說。
「也許妳可以抓一隻跳蚤給她看,這樣她就沒話說了呀。」媽媽建議。
我本來嗤之以鼻地想「跳蚤哪有那麼容易抓啊」、「牠還真的那麼笨,會跳出來給我看喔?」然而,命運似乎是想給我一個機會/考驗。於是有一天,我真的在房間地板上看到那黑褐色的扁平生物。
看到跳蚤的時候,我整個人愣在原地,不知道如何反應。要把牠抓起來當成物證拿去給女主人看嗎?「妳看妳看,妳的貓真的有跳蚤!」接下來要怎麼處理?去和學校反映?搬家的話要搬到哪裡?行李要怎麼寄放?還是再忍耐一下就過去了(反正都忍那麼久了)?
我的天人交戰還沒有結束,跳蚤就已經跳走了。不像我,它沒有時間考慮這些,它的生命只有「存活」和「死亡」這兩件事,容不下「關係」、「面子」、「身段」這一類的問題。我有點遺憾,但是沒有很後悔。我想就算我抓到跳蚤,大概也不會有任何作為。因為那時候的我就是如此懦弱,寧可自己受苦(那是我定義中的「獨立」),也不願找人幫忙,或和人起衝突。
我像是一隻大型跳蚤,從台灣跳到英國,想要過獨立的生活,但我缺乏獨立生活的勇氣和決心,於是只能縮在自己的角落,像一隻躲在地板縫隙的跳蚤忍受飢餓痛苦,只為了找到下一個可以照顧我的人,下一個可以讓我吸他/她的血,好讓我活下去的宿主。
我小時候經常和朋友一起去河邊釣魚,那些魚都有絛蟲,我們把蟲從魚肚子裡扯出來,把它們埋在土裡(因為怕狗去挖),然後把魚烤來吃。有一次,在我們埋完蟲後,有一個小孩跑來附近玩。他在地上東挖西挖,也不知道在挖什麼。後來他的爸媽來找他,他驕傲地轉向他們,手裡拿著我們的絛蟲,大喊:「哈哈哈!你們看我找到什麼?鞋帶!」──我的波蘭朋友E和我說的故事
我印象最深刻的童年回憶之一,是一隻在東京「目黑寄生蟲館」看到的絛蟲。
那是人的絛蟲。牠到底有多大我已經忘了,只記得很大很大,像輓聯或那種用來上吊的白布條一樣掛在牆上,比當時的我高出好幾倍,而且還繞了好幾圈。想來應該有十公尺吧。也許,牠並沒有這麼大,只是在我孩童的眼光看來,牠簡直大到不可思議。
我會看到這隻絛蟲,是因為我媽媽。她當時在台灣知名學府T大的寄生蟲學科工作,是那裡的副教授。當別人問起她的職業,她總是曖昧地笑著說:「我在教寄生蟲。」言下之意,學生也是寄生蟲。所以那些學寄生蟲的研究生為了避嫌,都說他們是「微研所」的學生,而非「寄生蟲學組」學生。
從我有記憶開始,寄生蟲就存在於我生命中,和我常相左右,像是童年最好的玩伴或最棒的玩具(雖然,牠不能陪我玩也不能讓我拿來玩),或甚至,一個隱形的手足。
在我開始學英文,認識ABC並且會說第一句英語「How are you?」之前,我就記住了一個非常難並且拗口的英文單字──Parasitology(寄生蟲學)。我媽媽指著電梯前的樓層標示向我解釋這個字,當時小小年紀的我發下宏願,要把旁邊其他的英文單字如Anatomy(解剖學)、Pharmacology(藥理學)、Biochemistry(生物化學)、Public Health(公共衛生)……都背下來。
我有沒有想過要和爸媽一樣,成為一個具有博士頭銜的生物學家?答案是有,也沒有。我小時候第一個志願是當動物園園長(因為父母都是學生物的),後來是當發明家(這是因為看了小叮噹),之後是當小學老師(我父母、我外婆和我曾外祖父都是老師),十二歲的時候我立志當作家(這是因為看了張系國的小說《棋王》),然後念國中時我突然說,我要去研究水母(因為在帛琉看到的水母很漂亮,而且我想試試看被水母螫到是什麼滋味)。
爸媽對我宣布要去研究水母的事沒有多作評論,爸爸只說:「如果妳要念水母,妳就要去法國,那裡的水母研究是全世界最好的。」我至今不知道他們對此是高興還是不高興?是開心「女兒終於走上正途了」,還是憂慮「唉她的興趣又變了」或是恐懼「天啊她也要變成一個博士嗎?這一定是我們家逃不掉的命運」。說到命運,也許「當一個高級知識份子」真的是我們家的命運兼詛咒。我媽媽的外公是前清秀才,我外婆的姊姊是女子學校校長,我媽媽和我兩個舅舅都是美國博士,而我爸爸是他家唯一的博士,因為我外婆在我爸爸第一次來我媽媽家吃飯兼面試的時候,把他叫進房間恐嚇他:「我女兒可是要出國念博士的哦,如果你要娶她,就要和她一起去念。」
生在這麼一個博士過剩的家庭,從小又被一堆博士、博士後、助教、副教授、教授、系主任、院長……包圍(是的,那些在我小時候陪我玩的青蛙姊姊、大魚姊姊、蚯蚓哥哥……在我長大後都變成各大院校的菁英),任何人照常理判斷,我爸媽應該會希望我拿到一個博士學位(白金會員卡),加入他們的學術圈(博士俱樂部)才對。
然而,從我有記憶以來,爸媽就不斷對我耳提面命:「不要當博士,不要爭第一名。」(這句話就和我媽媽的寄生蟲一樣,一直和我長相左右)他們的說法是,他們在自己的職業生涯中看到太多可悲的案例,太多人為了爭第一、進好院校、念博士而搞得遍體鱗傷,不知道人生除了博士之外還有什麼目的。然後有一天,當他們考到人生第一個九十九分,他們就崩潰了,得憂鬱症或自殺。
「得了博士也不一定找得到工作。」我爸總是這樣語重心長地作出結論:「現在博士太多了。而且,就算妳當上教授,也要像我們一樣每年被學校和學生評比,太沒有尊嚴了。妳看我做PowerPoint這麼認真,一堂課花了幾百個小時,我的學生還是不領情,說我尸位素餐,真是太沒有良心。」說完這句話,他又回去繼續弄他的PowerPoint。
然而,我爸媽沒有料到的是,他們的寶貝獨生女沒有念博士、沒有從事生物學研究,人生之路卻還是一樣走得不太順遂。
這些年來,我歷經休學、憂鬱症發作、自殺未遂、強制入院……現在雖然情況比較穩定了,也在專業領域有一番成就,但在金錢和情感方面,我依然在某種程度上依賴著父母,就像是一條寄生蟲。
如果我是寄生蟲,我會是什麼樣的寄生蟲?我的生活史又會是怎麼樣的呢?
跳蚤
被跳蚤叮咬有別於被蚊蟲叮咬,當跳蚤叮咬人時,會分泌一種出血唾液,破壞人體皮膚之表皮組織,使得被叮咬部位除痛癢外,並出血;所以皮膚上留有紅點;而且跳蚤叮咬時不僅只叮咬一處。被跳蚤叮咬另有一特徵,即被叮咬的部位多在膝蓋以下之小腿;此乃因跳蚤擅跳,一躍可達二、三十公分(所以才叫做「跳蚤」);又跳蚤的成、幼蟲多棲息於地板的塵芥內,羽化的成蟲自地面跳上來咬人,所以被叮咬的部位多在膝蓋以下之小腿。(⋯⋯)有些人或動物對蚤叮咬特別敏感,奇癢難忍,呈過敏現象,有的人則不痛不癢,毫無感覺。──台灣環境有害生物管理協會網站
被跳蚤咬應該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悲慘、最荒謬可笑的經驗之一。被咬之後,我無時無刻不在抓癢,上課抓,吃飯抓,睡覺抓,而且越抓越癢(撇開整件事的悲劇性,這個動作其實是深具喜感的,就像那個「香港腳,香港腳,癢又癢」的廣告。)我全身沒有一處完好的皮膚,精神更是瀕臨崩潰邊緣,每分每秒都覺得煩躁、不安、不知所措──這是在我還不知道被跳蚤咬了之前。當我確認自己被咬,我的情緒還加上深深的憤怒、無力和絕望,因為當時的我無法做任何事去解決這個問題。
我是在倫敦上語言學校時,在寄宿家庭被咬的。那年,因為憂鬱症而高中休學了兩年、不想再回到台灣教育體制、又不知道自己有什麼出路的我,在倉皇之中決定到英國遊學三個月。會做出這樣的決定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是想要在當地找學校,第二是試水溫,看看自己是否能適應國外的生活。第三個原因說起來有點無聊,但卻是促使我在十七歲離家的主要動力──我想證明給大家看,像我這樣的溫室花朵,也是有能力獨立生活的。
身為獨生女,我從小就被家庭保護得很好(我連短暫離家出走到金石堂都會被我爸跟蹤,自己卻渾然不覺),也處處依賴父母的幫助。
念國中時,因為無法早起趕公車,所以每天我爸爸都開車或坐計程車帶我上學。選高中時,我想要脫離家庭獨立,於是選了離家很遠的景美女中。但是直到甄試錄取,我才晴天霹靂地發現:原來只有外縣市的學生才能住校。打錯如意算盤的我,只好天天通勤,又因為爬不起來,再次讓我爸爸坐計程車帶我上學。
在別人眼中,我確實是個依賴、缺乏生活能力的小孩。許多事我只要表示擔憂,甚至不用開口要求,父母就會自動自發替我著想,幫我處理好。比如,十七歲時第一次當導演做小劇場(我去投一個藝術節的公開徵件計劃,結果被選上了),不知道上哪裡找排練場地,爸爸就把他學校的辦公室借給我用。後來要公演了,劇場卻在滴水,爸媽也到場幫忙拖地板,讓主辦單位嘖嘖稱奇:「別人來搞劇場,父母都威脅要打斷孩子的腿,從來沒見過這麼相挺的。」
我一方面享受父母照顧帶來的方便,另一方面深深引以為恥。當別人對我說:「哎喲,妳就是一個千金大小姐嘛。」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我覺得別人只看到我的先天優勢,卻看不到我的後天努力。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父母的庇蔭和高成就成了我身上一個帶來恥辱的印記。我曾經這麼希望:要是我父母很貧窮、很普通就好了,這樣別人就會把我的成就視為是我自己努力得來的,而不是把它當成理所當然的、我父母的一部分或延伸。
十七歲的我很不獨立,又渴望獨立──或者該說,渴望證明自己的獨立。因為這樣,我鼓起勇氣開始第一趟「自助旅行」:我立志環島一周,到朋友家去住,用攝影機去拍他們的生活。這個計畫一開始聽起來很棒,執行起來卻十分困難。我從來沒有一個人在外旅行過,也缺乏和他人相處的經驗。結果只出去三天,我就夾著尾巴回台北了。這次的失敗讓我感到更加屈辱,於是我痛下決心:下一次,我要去一個更遠的地方,不那麼容易回來的。
我選了英國。為什麼選擇去英國,而不是我父母曾經留學過、較為熟悉的美國?一方面是因為我很喜歡英國導演Danny Boyle拍的《猜火車》,覺得它是關於尋找人生意義的另類經典。
(雖然內容是在講一群無所事事的年輕人,不是在吸食海洛因就是在上床,或是把自己的人生搞砸。)另一方面,我那時極度需要離開父母的保護,當然不能選一個他們熟悉的環境。如我所料,我爸媽對英國很陌生,在那裡也沒什麼熟人。他們本來反對我去,但在我堅持下還是勉強答應了。後來,他們發現我的表哥在倫敦工作,這讓他們放心不少。
我在父母陪伴之下來到了倫敦,開始在滑鐵盧附近的語言學校上課,他們則在英國停留了三個禮拜,帶著我的履歷到各大學去拜訪,幫我詢問申請學校的事。我覺得他們多管閒事,但也沒有拒絕他們的幫助。等到他們飛回台灣,我感到一股前所未有的興奮刺激(我終於可以證明我的獨立了,而且是在這樣一個陌生的大都市!),伴隨著恐懼不安(我真的有辦法證明自己嗎?)。
最初的那段日子處處充滿挑戰。因為英文還不是說得很流利,加上個性退縮,我在與人溝通上遇到許多困難。許多事我不敢問,不敢尋求別人的幫助,不敢向任何人要求任何事,甚至不敢開口和別人聊天,也就很難交到朋友。我在倫敦的第一個寄宿家庭住得不是很舒服,卻沒有勇氣和學校說,於是打公共電話向媽媽求救。媽媽幫我打電話和學校反映,學校於是給我換了一個寄宿家庭。我很感激媽媽出手救我,但同時也感到非常丟臉,覺得我真是遜斃了。我不是要離家證明自己獨立嗎?怎麼現在卻像個在外頭被欺負,哭哭啼啼回家要媽媽安慰的小孩呢?
在第二個寄宿家庭我打定主意所有事情自己解決。我積極和室友社交、和寄宿家庭的女主人聊天,讓別人喜歡我。我給人如此好的印象,後來媽媽來倫敦看我一個禮拜,寄宿家庭的女主人還邀請媽媽來她家吃晚餐。有一個在英國住了很久的朋友後來對我說:「這表示她很喜歡妳,英國人不常請陌生人到家裡吃飯的。」
也許就是基於這種好感,以及害怕打破這種好感的顧慮──當我知道寄宿家庭的貓身上有貓蚤,而且我還被牠們咬了的時候,我不敢採取任何行動。
我的德國室友就不一樣。她不喜歡女主人,女主人也不喜歡她。所以當她被貓蚤咬,就義無反顧地搬了出去
(不過,她事後才告訴我關於貓蚤的事,那時我已經被咬得慘兮兮了。旁邊的西班牙同學還開玩笑地指著滿臉血痕的我和已經康復的她對大家說:「你們看,這就是『整形前』和『整形後』的差別喔!」)。我一方面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被咬,另一方面不想破壞和女主人的關係,所以只暗示性地對她提到:我「可能」有被跳蚤咬,「也許」是來自她的貓。
女主人的反應比我預期的激烈,她用比平常高八度的聲音說:「這是不可能的!傑克是一隻好貓!妳大概是過敏吧!」
在語言學校的心目中,她是個優秀的寄宿家庭主人。如果他們知道她家有貓蚤,可能就不會再送學生到這裡來了。我和媽媽訴苦,但是同時央求她嚴守秘密,不要和任何人說這件事,免得破壞我和女主人的關係。「反正再沒多久就要回台灣了,現在搬家很麻煩,而且我和女主人約好要把一部分行李寄放在她家,之後回英國可以直接帶到大學宿舍(是的,感謝父母的奔走,我申請到了愛丁堡一所學院的大學預科課程),現在我們就不要撕破臉吧。」我對媽媽說。
「也許妳可以抓一隻跳蚤給她看,這樣她就沒話說了呀。」媽媽建議。
我本來嗤之以鼻地想「跳蚤哪有那麼容易抓啊」、「牠還真的那麼笨,會跳出來給我看喔?」然而,命運似乎是想給我一個機會/考驗。於是有一天,我真的在房間地板上看到那黑褐色的扁平生物。
看到跳蚤的時候,我整個人愣在原地,不知道如何反應。要把牠抓起來當成物證拿去給女主人看嗎?「妳看妳看,妳的貓真的有跳蚤!」接下來要怎麼處理?去和學校反映?搬家的話要搬到哪裡?行李要怎麼寄放?還是再忍耐一下就過去了(反正都忍那麼久了)?
我的天人交戰還沒有結束,跳蚤就已經跳走了。不像我,它沒有時間考慮這些,它的生命只有「存活」和「死亡」這兩件事,容不下「關係」、「面子」、「身段」這一類的問題。我有點遺憾,但是沒有很後悔。我想就算我抓到跳蚤,大概也不會有任何作為。因為那時候的我就是如此懦弱,寧可自己受苦(那是我定義中的「獨立」),也不願找人幫忙,或和人起衝突。
我像是一隻大型跳蚤,從台灣跳到英國,想要過獨立的生活,但我缺乏獨立生活的勇氣和決心,於是只能縮在自己的角落,像一隻躲在地板縫隙的跳蚤忍受飢餓痛苦,只為了找到下一個可以照顧我的人,下一個可以讓我吸他/她的血,好讓我活下去的宿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