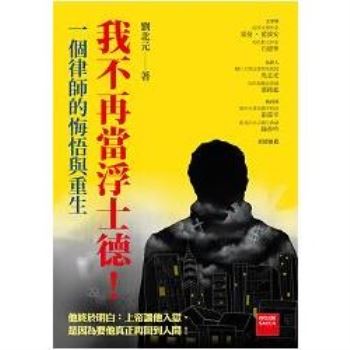1 被繞過的防線:富者的正義
在自己正式開業前,我曾在其他事務所擔任受僱律師,時間約有三年。
每家法律事務所,因著老闆的價值觀的差異,會有不同的接案標準,標準較為寬鬆的事務所,對受僱律師而言,每一個案件都會是場硬仗。這話怎麼說呢?讓我們先從美國職棒大聯盟找些隱喻吧!
每當一場比賽的勝負差距大到無可挽回時,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轉播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輸方為了保留戰力,派上所謂的「敗戰處理投手」上場,把剩餘的局數吃掉。也許是派牛棚內的投手,也許是派某個外野手踏上投手丘,最離譜時,連捕手都上場當投手了。
現在把場景拉回到律師工作的職場上來談。有部分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接案標準超級寬鬆,甚至飢不擇食,不論什麼案子他都願意承接。一旦接下了必敗或將會影響自身法律人的形象的案件後,部分老闆們又開始愛惜起自己的羽毛,於是,腦筋便變動到受僱律師的身上,讓受僱律師去接這種案子。這樣一來,就算打輸了官司,也有個背起黑鍋的替死鬼,形象不好也沾不上自己的邊。所以,受僱律師在事務所處理的案子,有些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律師事務所中的「敗戰處理投手」。
我在受僱於他人不久後,曾經被指派處理一件令人束手無策、讓人傷心落淚的案子。
那是一件很平常的車禍案件。當事人,也就是車禍被害人小陳,他原本是位保險行銷業務員,與交往多年的女友訂婚後,為了多掙些錢買房子,晚上還兼差去開計程車;而車禍肇事者范董是企業負責人,事發當天談完生意應酬想回飯店已經是深夜了,他開著賓士豪華房車,途中酒駕又闖紅燈,攔腰撞上小陳所駕駛的小黃。
國產小黃肯定是禁不起賓士車的衝撞,小陳當場重傷被緊急送醫急救。所幸,他的生命在與死神拔河的過程中,被醫師硬拉了回來,但卻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脊髓神經受損,終生下半身癱瘓。 事後小陳委託律師對范董提出了民、刑事訴訟,經歷了多年的纏訟,最終刑事部分范董被判有期徒刑十個月,民事部分隨後也被判賠新臺幣九百餘萬元。弔詭的是,這場官司范董聘請了全臺灣最昂貴的律師為他辯護,律師費至少可能超過數百萬,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訴訟過程中他竟然進行脫產的舉動,將名下財產移轉殆盡。也就是說,范董寧可選擇坐牢,花數百萬打官司,但就是不肯賠給小陳一分一毫。等到小陳的律師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范董的名下已經空無一物,小陳拿到的勝訴判決,成了一張壁紙。
既然官司都打完了,小陳為何還要來找律師?其實他是為了保險理賠而來。范董所駕駛的車子有投保任意責任保險,每一體傷事故最高可以賠償三百萬元。但是,由於事發當時范董是酒醉駕車,依照保單的除外不保事項,酒駕所造成的事故是不理賠的,以避免有鼓勵酒駕之嫌。所以,小陳與保險公司多次溝通,均遭到無情地拒絕。
與小陳談話當日,我一走進會議室,便看到一名衣著邋遢輕便、臉色蒼白的男子坐在輪椅上抽菸。聽他娓娓道來案情後,我心裡頭已有定見,卻猶豫再三,不知道該用什麼語氣來斷絕小陳的希望,比較不會傷害到他。刻意沉默了一會兒,最終,我不得不選擇誠實告訴他,他的案子保險公司不會理賠,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改變酒駕拒賠的結果。
他聽完我的意見後,突然將自己的長褲褪下,用手中尚在燃燒的香菸燒灼自己的下體,同時流著淚,情緒激動地說:「劉律師,你看到沒有?我的生殖器官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如今未婚妻離我而去,自己又喪失工作能力,法院判我勝訴的判決書已經當成壁紙貼在牆上。對方有能力花大錢請名律師打官司,卻連一塊錢都不願意賠給我,這個司法制度還有正義嗎?劉律師,請你幫幫我,拿到保險理賠,我會分給你一半作為酬勞。」
除了請他穿上褲子外,我默然無語……(低頭)
處理這個案件時,我大約三十歲,還是律師界的一隻菜鳥,碰上如此強烈的質疑,對司法正義的質疑,我也不禁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工作價值是否僅僅在宣示著司法正義,而不是實踐它?學校教授告訴我們,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見到小陳的當下,我開始有了全新的體會,它真的就只是一條防線,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為防範德國入侵所建立的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在當時宣稱是固若金湯,牢不可破,然為德國規劃入侵法國閃擊戰的曼斯坦元帥(Von Manstein)(當時只是上校),只在地圖上劃一道弧線,繞過它從法比邊境的阿登高地突入,就解決問題了;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亦復如此。
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阿納卡西斯(Anacharsis Cloots)曾主張:
「法律就像蜘蛛網,只捕捉入網中的小者,而遇到富者和強者就只好聽任其把網子扯得粉碎。」
這話法律人讀起來,或許有些刺耳,或許有人會有些話想說,但我不得不承認,這段話並不偏離司法現況太多。范董不就是個好例子嗎?
從此之後,我也開始學習如何幫客戶繞過司法防線,因為從生意的角度而言,范董之流的客戶,才是拿得出重金聘請律師的大咖,誠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說:「就算要出賣靈魂,也要找個付得起價錢的人。」至於正義那是法官及檢察官的事,與我律師沒有太大關係了,我只在意輸贏,忽略了律師也是在野法曹的角色。9 誘使對方犯錯:不求救的船長
律師在法庭上,有時一個庭期只面對一個證人,可是有許多時候,律師要一口氣面對一群對方傳訊的敵意證人,非常難以處裡。這時候,我個人的經驗是,與法官協商眾多證人上庭作證的順序,往往是成功與否的關鍵。
記得我曾經承辦過一件商船沉沒的保險理賠案,由於保險契約條款約定,契約雙方當事人若有爭執產生,應以商務仲裁方式處理。於是,這個案子在保險公司依法主張,船長的操駕及危機處理的判斷有重大過失,不願意理賠後,船東便向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申請,請求判斷保險公司應給付給他二千萬美金。
根據我手頭上拿到的航海日誌,該船由基隆出港,航行到東海便因遭遇風浪,使船艙內的鋼樑掉落(船齡過高),由內向外將船撞破一個大洞,船艙開始進水,而這位船長認為它能夠撐得住眼前所發生的狀況,也就沒發出SOS緊急求救訊號;更因遭遇特殊情形,大陸沿海港口不願讓它駛入港內維修,船長只能將船碇泊於上海港外海待援。船沉的那一天,船長正在艦橋上看雜誌,一聲巨響後,船身開始加速傾斜,他研判大勢已去,便趕緊領著船員棄船逃生而去。
這個仲裁事件,雙方都有委請律師出席詢問會,而為了釐清船舶沉沒的原因經過,船東的律師要求傳訊船長與出航前船舶的驗船師同時到庭,一是為證明船舶出航前是適合在大海航行的,二是要說明船長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仍無法避免船隻沉沒的結果。
證人出席詢問會當天,主任仲裁人問我,對證人作證的順序有什麼意見?我用眼睛的餘光掃過證人後答稱:「先詢問船長,再問驗船師。」對方律師一副老神在在,胸有成竹的表情,完全不介意哪一位證人先上場。我猜,他當時一定在想:今天是你的死期,就由你問吧!
其實,我這樣的安排是有道理的。我的直覺告訴我,那位驗船師非常精明厲害,不便招惹,若讓他先出庭陳述,接下來船長只要循著驗船師的說法作證,我恐怕就一點機會都沒有了;而船長的舉止動作則活像個大老粗,我想讓他先上證人席,由他身上也許可以有所突破,屆時驗船師怎麼說,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船長一座上證人席,我開始請教他有關風浪等級與船隻的狀態。
「一、二級風浪,在船上是什麼感覺?」
「好像車子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穩穩當當的。」
「三、四級風浪呢?」
「船身開始有輕微的搖晃。」
「那七、八級風浪呢?應該很可怕吧!」(這個問題有點誘導詢問了,但對敵意證人可以做誘導)
「船身搖晃地非常厲害,約有四十五度的傾斜了。」
「事發當天是幾級風浪?」
「大概四、五級,東海在冬天大約都是這樣的航海條件。」
我拿出手上所掌握的事發當天,大陸氣象單位發布的東海海上風浪報告,交給船長,麻煩他唸給大家聽。
他從口袋裡掏出眼鏡戴上,用他宏亮的聲音讀著:「○年○月○日,東海海面平均風浪七至八級……」 唸完之後船長立刻想開口解釋什麼,我沒給他機會,道:「我沒問你問題,你沒有權利說話,謝謝。」
「根據航海日誌記載,船舶沉沒前你在艦橋上看雜誌?」
「是。」
「船舶在大風大浪中進水,身為船長,你沒事做嗎?」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放心的很。」
「你的船當時已經進水好幾天,一直沒得到救援,你什麼都不做,看起雜誌來?」
「我完全掌握狀況啊,所以沒什麼好擔心。」
「所以你連SOS的求救訊號都沒有發出?」
「我已經說過,我當了三十年船長,經驗豐富,更危險的狀況我都碰過,一切都在掌握中。」
「可不可以聊聊你遇過最危險的情況?」
「有一次我從印尼在原木回花蓮港,才出發沒多久,船上固定原木的鐵鍊就鬆脫,原木滾向船的右舷,導致船身傾斜。我就這樣船歪著一邊的開回花蓮港。」
「船長先生,聽完你的敘述,我如果說你是藝高人膽大,你接受嗎?」
「我接受你的讚美。」
我不再追問他當天船舶為何會沉沒,但我相信,大家都心照不宣,船長已經露出他的破綻。
我一開始就用氣象資料來證明船長在掩飾自己的輕忽,接著再證明他極愛冒險駛船。以前有成功的案例,固然令人敬佩,但這一回把船駛沉了,他該面對的責任,也無法逃避。仲裁人的心中已經在用最嚴厲的尺衡量著船長的疏失了,接下來驗船師說什麼,對於大局也沒有太多的助益。
法庭上的勝利,固然屬於比較會在法庭上建立起事實的律師,但在法庭上技巧性引誘證人犯錯,打破對方企圖建立的事實,一樣可以成為致勝關鍵。至於真相是什麼?當時我的想法是「法官相信就好。」然而,在一個訴訟案件中,最直接頻繁而深入接觸原告或被告的人就是律師,如果律師不願協助法官在法庭上發現真實,那麼法官誤判的可能性是相當高的。如此說來,社會大眾對司法判決的信賴度不足,不全然都是法官的問題,律師們恐怕也難辭其咎吧。 12 複製階級的犯罪家族:安靜的殺手
在將近八年的服刑過程中,有一回,於要收封晚點名前,主管忽然宣布,法務部要調查有親人同在監獄服刑的人數,要求有此情形者舉手接受登記。我聽完這段話,心中想的是:應該沒幾個人,很快就可以進房休息了。沒有想到,舉起手的人數,超乎我的想像了,竟然約有三分之一左右!我用目視法初估,應該與實際人數有些落差,但無論如何,一百二十人的工場,二、三十人有家族(註1)犯罪史,也是相當讓人震驚。
在臺中監獄待了六年,我的乾弟弟阿華(化名),他的家族犯罪情況,也是令人不勝唏噓。
年紀約三十歲左右的阿華,身負數件重大刑案,包括槍枝、毒品、殺人,到監獄時,仍有殺人一案尚未定讞,因此,當他知道我曾經是位律師後,便來拜託我為他想想辦法。剛開始我根本不願意處理這個請託,因為阿華的殺氣太重,令人不想靠近。後來一位熟識的長官來找我,稱與阿華的父親是舊識,他父親因為販毒,目前被通緝中,無法出面幫兒子的忙,所以請我在阿華的案件上多多用心。最終我接受了長官的請託,同時我也要求阿華,他必須每天讀《聖經》,他同意了。
之後,我們倆常聚在一起討論案情,偶而也談談《聖經》內容,教他面對與交託對未來憂懼的方法。相處的時間一長,我才慢慢地了解到他的家庭狀況。
阿華還有一位弟弟,因為販賣毒品被判刑十六年,人在彰化監獄服刑;不久後,阿華的父親通緝到案,也來到臺中監獄服刑,而這三人所有的經濟來源,全仰仗阿華高齡八十幾歲的老阿嬤。
有一回我與阿華一同辦理會客,窗號正巧在隔壁,我第一次見到那位身形佝僂、步履蹣跚的老阿嬤,她朝著我揮手微笑,我跟著揮手、傻笑,心卻不由自主地感到苦澀,她的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時間往返在探監的旅途中,先是兒子,如今是孫子。
後來,我離開工場,與阿華分別,但他仍會託正巧要到我服務的單位洽公的人,帶口信給我,問我過得好不好,告訴我他每日他仍會讀《聖經》,也會為自己與我的平安禱告。可惜的是,當我覺得阿華的戾氣因宗教感化時,最高法院針對他的殺人案,判處無期徒刑定讞,也就是說,從那時起,他得蹲三十年以上苦窯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我難過了許多天,反倒是他又託人帶口信來安慰我,說他會接受上帝安排的一切。 阿華雖然是個殺手,但也有他安靜的一面。他會美工,也學書法,手藝更是精巧,做起花燈可是美輪美奐、巧奪天工,我在獄中唯一的十字架,就是他利用廢棄的小東西編織裝飾而成,去到哪兒,我總是帶著它。我常想,如果阿華沒有犯下這些案子,會是怎樣的一個人?是不是有機會利用這個獨特的天賦,翻轉自己的社會階級,向上層流動?
無奈呀!他選擇在街頭扣下衝鋒槍的扳機,一分鐘超過三百發的射速,不消五秒鐘,他的人生就已有如掉落一地的彈殼,四處飛散,再也無法完整了。他告訴我,開槍時他已數日未眠,不停吸食海洛因與安非他命,導致行為錯亂。我也告訴他,這不是開槍傷人的理由,你是自願被毒品戕害的。
當時他的案子有許多疑義尚待澄清,我也幫他找出許多問題。但我一再告誡他,這些都是委任律師的工作,在法庭上為你辯護,而你自己在法庭上,只有一個答辯內容:「我錯了!」再多一個字,便顯得多餘且刺耳了。他接受了,悔改了,但法律並沒有放棄譴責他的任何機會,對他處以幾乎是極刑的懲罰。
有關階級複製(註2)的現象,我曾聽聞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有部相當驚人的紀錄片《56UP》,導演麥可艾普泰原先是想驗證,是否在英國的社會裡,階級是很難逾越的;富人的孩子長大依然是富人,窮人的孩子長大成家依然是窮人。於是,選擇了十四個不同階層的孩子進行跟踪拍攝,從一九六四年起,每七年記錄一次:從七歲開始,十四歲、二十一歲、二十八歲……,一直到五十六歲。幾十年過去,直到二○一三年才完成最後拍攝,累積了七部影片。
在片中,可以看見最平凡的英國人的人生,此片濃縮了近五十年來的英國社會變遷,並凸顯出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化等現象……
然而同樣的事情,在臺灣也正發生著……
註:
1.家族,指基於血緣、婚姻、生命共同體所構成的利益共同體,通常表現為以一個家庭為主構成中心。不過現代社會工商業發達,個人主義當道,人情淡薄,家族已不再是現代人的生活中心,其象徵性的意義,已大於提供家族成員生活保障的實質功能。所以,這一輩的年輕人,對於家族的觀念已經模糊了。
2.階級複製,就是說社會階級流動僵固化,造就了下一代複製上一代的社會階級地位,優勢階級可以自然地在社會競爭中保持優勢,劣勢階級則喪失了翻身的機會。 15 錯誤的崇拜:金錢的奴隸「小屁」
記得二○一一年,我人仍在臺中監獄,但已離開作業工場的環境,調到新收舍房擔任文書雜役的工作,負責初入監受刑人的新生文書作業,為乍到初來的人犯製作入監相關表格文件,並處理受刑人信件的收發、就醫的申請,以及最後的作業工場分發作業。
臺中監獄新收舍的工作量十分可怕,收監人犯如排山倒海般似地來自全國各地,每天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上百人,往往都得加班到晚上七、八點才能休息,半夜還有地檢署送來剛剛逮捕的通緝犯,整體工作量不比當年擔任律師輕鬆。
有一天,主管正在進行新收人員個別教誨,我當時坐在一旁忙自己的工作,忽然就聽他叫喊著我,說:「北元,來來來,你曾經在東海大學法律系教書吧!這一個是你的學生。哈!念法律系的還販毒,這怎麼回事啊?你好好跟他談談。」
主管這一番話,仿如五雷轟頂,怎麼自己的學生會販毒呢?主管要我跟他談談是玩笑話?還是認真地交辦工作?我已經傻傻分不清,連忙回應主管,道:「報告主管,我上課沒有教學生不要販毒,害得學生販毒被抓,真是不好意思,我會好好教化他。」我邊說邊趕緊將人帶到一旁詢問情形。
細問之後我才知道,小屁(化名)果真是我的學生,是我任教東海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入獄當時還不到三十歲,父親是任職法院的公務人員。東海大學法律系畢業後,他還進入某大學法律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可是,這麼優秀的學業表現,小屁居然沒有做過任何一份與法律相關的工作,這讓我感到非常驚訝,也難以想像,現在的年輕人的腦袋到底都在想些什麼?小屁在入獄前僅僅只做過數個月的房屋仲介,其他多數的時間,他都流連在各夜店之間,尋求刺激,也順便販毒(安非他命與K他命)。這次是他第一次被逮入獄,刑期七年整。
小屁初來乍到,各種生活物資缺乏,本著天地會的精神,我試著在合乎監規的範圍內,盡力幫他備齊;同房室友也先幫他打個招呼,讓他在未來的新生訓練中,日子能過得稍微舒坦一點。 小屁在新收舍房待了將近一個月,才轉配到作業工場。這一段時間,我有空便會找他聊聊,想了解他販毒的理由。與他對談間,我注意到這個孩子的想法,充滿了物質的慾望,口裡崇拜著傳說中以販毒起家的大亨。說的直白一點,小屁的心中只有「錢」,只要能快速致富,什麼事他都會願意去嘗試。這個想法,與現今社會笑貧不笑娼的拜金主義,似乎沒什麼兩樣,他一定不知道,哲學家培根說過的一句話:
「金錢是好的僕人,卻是不好的主人。」
追求物質是個人的生活滿足方式,可是一旦迷失在其中,就再也難保追求慾望滿足的手段,是否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小屁的想法中,踏實的法律工作賺錢速度太慢,所以,他先鎖定了具有高獲利特質的房地產,但做了幾個月後,覺得房屋仲介工作十分辛苦,帶客看屋,風吹雨淋,最後他還是決定辭掉工作。
小屁本來就有泡夜店的習慣,於是他相中了可以快速賺取暴利的毒品。這樣的結果正如名作家三毛所言:
「世上的喜劇不需要金錢就能產生,世上的悲劇大半和金錢脫不了關係。」──(三毛,《親愛的三毛》)
依照現行毒品防制法,海洛英是一級毒品,販賣它被抓,法官隨便判都是十幾年、甚至是無期徒刑的刑期,而小屁選擇販賣低風險的安非他命與K他命,法院量刑的標準都會在十年以下,如他這一趟被判七年的有期徒刑,相信是他內心預期的結果。
憑良心說,小屁歷經起訴、審判、入監,我並沒有感受到他的悔意,一絲絲都沒有,他不過是認為自己倒楣,被人出賣才會被逮住。當我問他將來出去有什麼打算?小屁自己也說不上來。根據我的觀察,他在獄中相當積極認識新朋友,擴展新的人際關係,這點令我十分擔憂。
「是誰把這個學業成績優異的小孩教成這樣?」
小屁在的那些日子裡,我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最終我承認,恐怕自己也脫不了關係!在我教書的那些時日,上課時,手上戴著百萬名錶,停在教室外的還是賓士AMG猛獸,口裡聊的笑話是酒店的風花雪月,神態自若是桀傲不遜地囂張。即便我和小屁是在獄中再度相見,我仍能看見小屁望著我時的崇拜眼神。我好想告訴小屁,老師當年錯了,但終究這一句話沒說出口,只是每天找他說教,盼望他能有所領悟。
在自己正式開業前,我曾在其他事務所擔任受僱律師,時間約有三年。
每家法律事務所,因著老闆的價值觀的差異,會有不同的接案標準,標準較為寬鬆的事務所,對受僱律師而言,每一個案件都會是場硬仗。這話怎麼說呢?讓我們先從美國職棒大聯盟找些隱喻吧!
每當一場比賽的勝負差距大到無可挽回時,在美國職棒大聯盟的轉播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輸方為了保留戰力,派上所謂的「敗戰處理投手」上場,把剩餘的局數吃掉。也許是派牛棚內的投手,也許是派某個外野手踏上投手丘,最離譜時,連捕手都上場當投手了。
現在把場景拉回到律師工作的職場上來談。有部分律師事務所的負責人,接案標準超級寬鬆,甚至飢不擇食,不論什麼案子他都願意承接。一旦接下了必敗或將會影響自身法律人的形象的案件後,部分老闆們又開始愛惜起自己的羽毛,於是,腦筋便變動到受僱律師的身上,讓受僱律師去接這種案子。這樣一來,就算打輸了官司,也有個背起黑鍋的替死鬼,形象不好也沾不上自己的邊。所以,受僱律師在事務所處理的案子,有些就是屬於這一類的──律師事務所中的「敗戰處理投手」。
我在受僱於他人不久後,曾經被指派處理一件令人束手無策、讓人傷心落淚的案子。
那是一件很平常的車禍案件。當事人,也就是車禍被害人小陳,他原本是位保險行銷業務員,與交往多年的女友訂婚後,為了多掙些錢買房子,晚上還兼差去開計程車;而車禍肇事者范董是企業負責人,事發當天談完生意應酬想回飯店已經是深夜了,他開著賓士豪華房車,途中酒駕又闖紅燈,攔腰撞上小陳所駕駛的小黃。
國產小黃肯定是禁不起賓士車的衝撞,小陳當場重傷被緊急送醫急救。所幸,他的生命在與死神拔河的過程中,被醫師硬拉了回來,但卻也付出了慘痛的代價──脊髓神經受損,終生下半身癱瘓。 事後小陳委託律師對范董提出了民、刑事訴訟,經歷了多年的纏訟,最終刑事部分范董被判有期徒刑十個月,民事部分隨後也被判賠新臺幣九百餘萬元。弔詭的是,這場官司范董聘請了全臺灣最昂貴的律師為他辯護,律師費至少可能超過數百萬,但令人意外的是,在訴訟過程中他竟然進行脫產的舉動,將名下財產移轉殆盡。也就是說,范董寧可選擇坐牢,花數百萬打官司,但就是不肯賠給小陳一分一毫。等到小陳的律師向法院聲請強制執行時,范董的名下已經空無一物,小陳拿到的勝訴判決,成了一張壁紙。
既然官司都打完了,小陳為何還要來找律師?其實他是為了保險理賠而來。范董所駕駛的車子有投保任意責任保險,每一體傷事故最高可以賠償三百萬元。但是,由於事發當時范董是酒醉駕車,依照保單的除外不保事項,酒駕所造成的事故是不理賠的,以避免有鼓勵酒駕之嫌。所以,小陳與保險公司多次溝通,均遭到無情地拒絕。
與小陳談話當日,我一走進會議室,便看到一名衣著邋遢輕便、臉色蒼白的男子坐在輪椅上抽菸。聽他娓娓道來案情後,我心裡頭已有定見,卻猶豫再三,不知道該用什麼語氣來斷絕小陳的希望,比較不會傷害到他。刻意沉默了一會兒,最終,我不得不選擇誠實告訴他,他的案子保險公司不會理賠,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改變酒駕拒賠的結果。
他聽完我的意見後,突然將自己的長褲褪下,用手中尚在燃燒的香菸燒灼自己的下體,同時流著淚,情緒激動地說:「劉律師,你看到沒有?我的生殖器官已經沒有任何感覺了,如今未婚妻離我而去,自己又喪失工作能力,法院判我勝訴的判決書已經當成壁紙貼在牆上。對方有能力花大錢請名律師打官司,卻連一塊錢都不願意賠給我,這個司法制度還有正義嗎?劉律師,請你幫幫我,拿到保險理賠,我會分給你一半作為酬勞。」
除了請他穿上褲子外,我默然無語……(低頭)
處理這個案件時,我大約三十歲,還是律師界的一隻菜鳥,碰上如此強烈的質疑,對司法正義的質疑,我也不禁開始懷疑起自己的工作價值是否僅僅在宣示著司法正義,而不是實踐它?學校教授告訴我們,司法是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見到小陳的當下,我開始有了全新的體會,它真的就只是一條防線,如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法國為防範德國入侵所建立的馬其諾防線(Maginot Line),在當時宣稱是固若金湯,牢不可破,然為德國規劃入侵法國閃擊戰的曼斯坦元帥(Von Manstein)(當時只是上校),只在地圖上劃一道弧線,繞過它從法比邊境的阿登高地突入,就解決問題了;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亦復如此。
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阿納卡西斯(Anacharsis Cloots)曾主張:
「法律就像蜘蛛網,只捕捉入網中的小者,而遇到富者和強者就只好聽任其把網子扯得粉碎。」
這話法律人讀起來,或許有些刺耳,或許有人會有些話想說,但我不得不承認,這段話並不偏離司法現況太多。范董不就是個好例子嗎?
從此之後,我也開始學習如何幫客戶繞過司法防線,因為從生意的角度而言,范董之流的客戶,才是拿得出重金聘請律師的大咖,誠如歌德在《浮士德》中所說:「就算要出賣靈魂,也要找個付得起價錢的人。」至於正義那是法官及檢察官的事,與我律師沒有太大關係了,我只在意輸贏,忽略了律師也是在野法曹的角色。9 誘使對方犯錯:不求救的船長
律師在法庭上,有時一個庭期只面對一個證人,可是有許多時候,律師要一口氣面對一群對方傳訊的敵意證人,非常難以處裡。這時候,我個人的經驗是,與法官協商眾多證人上庭作證的順序,往往是成功與否的關鍵。
記得我曾經承辦過一件商船沉沒的保險理賠案,由於保險契約條款約定,契約雙方當事人若有爭執產生,應以商務仲裁方式處理。於是,這個案子在保險公司依法主張,船長的操駕及危機處理的判斷有重大過失,不願意理賠後,船東便向中華民國商務仲裁協會申請,請求判斷保險公司應給付給他二千萬美金。
根據我手頭上拿到的航海日誌,該船由基隆出港,航行到東海便因遭遇風浪,使船艙內的鋼樑掉落(船齡過高),由內向外將船撞破一個大洞,船艙開始進水,而這位船長認為它能夠撐得住眼前所發生的狀況,也就沒發出SOS緊急求救訊號;更因遭遇特殊情形,大陸沿海港口不願讓它駛入港內維修,船長只能將船碇泊於上海港外海待援。船沉的那一天,船長正在艦橋上看雜誌,一聲巨響後,船身開始加速傾斜,他研判大勢已去,便趕緊領著船員棄船逃生而去。
這個仲裁事件,雙方都有委請律師出席詢問會,而為了釐清船舶沉沒的原因經過,船東的律師要求傳訊船長與出航前船舶的驗船師同時到庭,一是為證明船舶出航前是適合在大海航行的,二是要說明船長已經盡了最大努力,仍無法避免船隻沉沒的結果。
證人出席詢問會當天,主任仲裁人問我,對證人作證的順序有什麼意見?我用眼睛的餘光掃過證人後答稱:「先詢問船長,再問驗船師。」對方律師一副老神在在,胸有成竹的表情,完全不介意哪一位證人先上場。我猜,他當時一定在想:今天是你的死期,就由你問吧!
其實,我這樣的安排是有道理的。我的直覺告訴我,那位驗船師非常精明厲害,不便招惹,若讓他先出庭陳述,接下來船長只要循著驗船師的說法作證,我恐怕就一點機會都沒有了;而船長的舉止動作則活像個大老粗,我想讓他先上證人席,由他身上也許可以有所突破,屆時驗船師怎麼說,就不是那麼重要了。
船長一座上證人席,我開始請教他有關風浪等級與船隻的狀態。
「一、二級風浪,在船上是什麼感覺?」
「好像車子行駛在高速公路上,穩穩當當的。」
「三、四級風浪呢?」
「船身開始有輕微的搖晃。」
「那七、八級風浪呢?應該很可怕吧!」(這個問題有點誘導詢問了,但對敵意證人可以做誘導)
「船身搖晃地非常厲害,約有四十五度的傾斜了。」
「事發當天是幾級風浪?」
「大概四、五級,東海在冬天大約都是這樣的航海條件。」
我拿出手上所掌握的事發當天,大陸氣象單位發布的東海海上風浪報告,交給船長,麻煩他唸給大家聽。
他從口袋裡掏出眼鏡戴上,用他宏亮的聲音讀著:「○年○月○日,東海海面平均風浪七至八級……」 唸完之後船長立刻想開口解釋什麼,我沒給他機會,道:「我沒問你問題,你沒有權利說話,謝謝。」
「根據航海日誌記載,船舶沉沒前你在艦橋上看雜誌?」
「是。」
「船舶在大風大浪中進水,身為船長,你沒事做嗎?」
「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中,放心的很。」
「你的船當時已經進水好幾天,一直沒得到救援,你什麼都不做,看起雜誌來?」
「我完全掌握狀況啊,所以沒什麼好擔心。」
「所以你連SOS的求救訊號都沒有發出?」
「我已經說過,我當了三十年船長,經驗豐富,更危險的狀況我都碰過,一切都在掌握中。」
「可不可以聊聊你遇過最危險的情況?」
「有一次我從印尼在原木回花蓮港,才出發沒多久,船上固定原木的鐵鍊就鬆脫,原木滾向船的右舷,導致船身傾斜。我就這樣船歪著一邊的開回花蓮港。」
「船長先生,聽完你的敘述,我如果說你是藝高人膽大,你接受嗎?」
「我接受你的讚美。」
我不再追問他當天船舶為何會沉沒,但我相信,大家都心照不宣,船長已經露出他的破綻。
我一開始就用氣象資料來證明船長在掩飾自己的輕忽,接著再證明他極愛冒險駛船。以前有成功的案例,固然令人敬佩,但這一回把船駛沉了,他該面對的責任,也無法逃避。仲裁人的心中已經在用最嚴厲的尺衡量著船長的疏失了,接下來驗船師說什麼,對於大局也沒有太多的助益。
法庭上的勝利,固然屬於比較會在法庭上建立起事實的律師,但在法庭上技巧性引誘證人犯錯,打破對方企圖建立的事實,一樣可以成為致勝關鍵。至於真相是什麼?當時我的想法是「法官相信就好。」然而,在一個訴訟案件中,最直接頻繁而深入接觸原告或被告的人就是律師,如果律師不願協助法官在法庭上發現真實,那麼法官誤判的可能性是相當高的。如此說來,社會大眾對司法判決的信賴度不足,不全然都是法官的問題,律師們恐怕也難辭其咎吧。 12 複製階級的犯罪家族:安靜的殺手
在將近八年的服刑過程中,有一回,於要收封晚點名前,主管忽然宣布,法務部要調查有親人同在監獄服刑的人數,要求有此情形者舉手接受登記。我聽完這段話,心中想的是:應該沒幾個人,很快就可以進房休息了。沒有想到,舉起手的人數,超乎我的想像了,竟然約有三分之一左右!我用目視法初估,應該與實際人數有些落差,但無論如何,一百二十人的工場,二、三十人有家族(註1)犯罪史,也是相當讓人震驚。
在臺中監獄待了六年,我的乾弟弟阿華(化名),他的家族犯罪情況,也是令人不勝唏噓。
年紀約三十歲左右的阿華,身負數件重大刑案,包括槍枝、毒品、殺人,到監獄時,仍有殺人一案尚未定讞,因此,當他知道我曾經是位律師後,便來拜託我為他想想辦法。剛開始我根本不願意處理這個請託,因為阿華的殺氣太重,令人不想靠近。後來一位熟識的長官來找我,稱與阿華的父親是舊識,他父親因為販毒,目前被通緝中,無法出面幫兒子的忙,所以請我在阿華的案件上多多用心。最終我接受了長官的請託,同時我也要求阿華,他必須每天讀《聖經》,他同意了。
之後,我們倆常聚在一起討論案情,偶而也談談《聖經》內容,教他面對與交託對未來憂懼的方法。相處的時間一長,我才慢慢地了解到他的家庭狀況。
阿華還有一位弟弟,因為販賣毒品被判刑十六年,人在彰化監獄服刑;不久後,阿華的父親通緝到案,也來到臺中監獄服刑,而這三人所有的經濟來源,全仰仗阿華高齡八十幾歲的老阿嬤。
有一回我與阿華一同辦理會客,窗號正巧在隔壁,我第一次見到那位身形佝僂、步履蹣跚的老阿嬤,她朝著我揮手微笑,我跟著揮手、傻笑,心卻不由自主地感到苦澀,她的一生中,不知道有多少時間往返在探監的旅途中,先是兒子,如今是孫子。
後來,我離開工場,與阿華分別,但他仍會託正巧要到我服務的單位洽公的人,帶口信給我,問我過得好不好,告訴我他每日他仍會讀《聖經》,也會為自己與我的平安禱告。可惜的是,當我覺得阿華的戾氣因宗教感化時,最高法院針對他的殺人案,判處無期徒刑定讞,也就是說,從那時起,他得蹲三十年以上苦窯才有重見天日的機會。我難過了許多天,反倒是他又託人帶口信來安慰我,說他會接受上帝安排的一切。 阿華雖然是個殺手,但也有他安靜的一面。他會美工,也學書法,手藝更是精巧,做起花燈可是美輪美奐、巧奪天工,我在獄中唯一的十字架,就是他利用廢棄的小東西編織裝飾而成,去到哪兒,我總是帶著它。我常想,如果阿華沒有犯下這些案子,會是怎樣的一個人?是不是有機會利用這個獨特的天賦,翻轉自己的社會階級,向上層流動?
無奈呀!他選擇在街頭扣下衝鋒槍的扳機,一分鐘超過三百發的射速,不消五秒鐘,他的人生就已有如掉落一地的彈殼,四處飛散,再也無法完整了。他告訴我,開槍時他已數日未眠,不停吸食海洛因與安非他命,導致行為錯亂。我也告訴他,這不是開槍傷人的理由,你是自願被毒品戕害的。
當時他的案子有許多疑義尚待澄清,我也幫他找出許多問題。但我一再告誡他,這些都是委任律師的工作,在法庭上為你辯護,而你自己在法庭上,只有一個答辯內容:「我錯了!」再多一個字,便顯得多餘且刺耳了。他接受了,悔改了,但法律並沒有放棄譴責他的任何機會,對他處以幾乎是極刑的懲罰。
有關階級複製(註2)的現象,我曾聽聞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有部相當驚人的紀錄片《56UP》,導演麥可艾普泰原先是想驗證,是否在英國的社會裡,階級是很難逾越的;富人的孩子長大依然是富人,窮人的孩子長大成家依然是窮人。於是,選擇了十四個不同階層的孩子進行跟踪拍攝,從一九六四年起,每七年記錄一次:從七歲開始,十四歲、二十一歲、二十八歲……,一直到五十六歲。幾十年過去,直到二○一三年才完成最後拍攝,累積了七部影片。
在片中,可以看見最平凡的英國人的人生,此片濃縮了近五十年來的英國社會變遷,並凸顯出貧富差距擴大、社會階層化等現象……
然而同樣的事情,在臺灣也正發生著……
註:
1.家族,指基於血緣、婚姻、生命共同體所構成的利益共同體,通常表現為以一個家庭為主構成中心。不過現代社會工商業發達,個人主義當道,人情淡薄,家族已不再是現代人的生活中心,其象徵性的意義,已大於提供家族成員生活保障的實質功能。所以,這一輩的年輕人,對於家族的觀念已經模糊了。
2.階級複製,就是說社會階級流動僵固化,造就了下一代複製上一代的社會階級地位,優勢階級可以自然地在社會競爭中保持優勢,劣勢階級則喪失了翻身的機會。 15 錯誤的崇拜:金錢的奴隸「小屁」
記得二○一一年,我人仍在臺中監獄,但已離開作業工場的環境,調到新收舍房擔任文書雜役的工作,負責初入監受刑人的新生文書作業,為乍到初來的人犯製作入監相關表格文件,並處理受刑人信件的收發、就醫的申請,以及最後的作業工場分發作業。
臺中監獄新收舍的工作量十分可怕,收監人犯如排山倒海般似地來自全國各地,每天少則一、二十人,多則上百人,往往都得加班到晚上七、八點才能休息,半夜還有地檢署送來剛剛逮捕的通緝犯,整體工作量不比當年擔任律師輕鬆。
有一天,主管正在進行新收人員個別教誨,我當時坐在一旁忙自己的工作,忽然就聽他叫喊著我,說:「北元,來來來,你曾經在東海大學法律系教書吧!這一個是你的學生。哈!念法律系的還販毒,這怎麼回事啊?你好好跟他談談。」
主管這一番話,仿如五雷轟頂,怎麼自己的學生會販毒呢?主管要我跟他談談是玩笑話?還是認真地交辦工作?我已經傻傻分不清,連忙回應主管,道:「報告主管,我上課沒有教學生不要販毒,害得學生販毒被抓,真是不好意思,我會好好教化他。」我邊說邊趕緊將人帶到一旁詢問情形。
細問之後我才知道,小屁(化名)果真是我的學生,是我任教東海大學法律系的學生。入獄當時還不到三十歲,父親是任職法院的公務人員。東海大學法律系畢業後,他還進入某大學法律研究所取得碩士學位。可是,這麼優秀的學業表現,小屁居然沒有做過任何一份與法律相關的工作,這讓我感到非常驚訝,也難以想像,現在的年輕人的腦袋到底都在想些什麼?小屁在入獄前僅僅只做過數個月的房屋仲介,其他多數的時間,他都流連在各夜店之間,尋求刺激,也順便販毒(安非他命與K他命)。這次是他第一次被逮入獄,刑期七年整。
小屁初來乍到,各種生活物資缺乏,本著天地會的精神,我試著在合乎監規的範圍內,盡力幫他備齊;同房室友也先幫他打個招呼,讓他在未來的新生訓練中,日子能過得稍微舒坦一點。 小屁在新收舍房待了將近一個月,才轉配到作業工場。這一段時間,我有空便會找他聊聊,想了解他販毒的理由。與他對談間,我注意到這個孩子的想法,充滿了物質的慾望,口裡崇拜著傳說中以販毒起家的大亨。說的直白一點,小屁的心中只有「錢」,只要能快速致富,什麼事他都會願意去嘗試。這個想法,與現今社會笑貧不笑娼的拜金主義,似乎沒什麼兩樣,他一定不知道,哲學家培根說過的一句話:
「金錢是好的僕人,卻是不好的主人。」
追求物質是個人的生活滿足方式,可是一旦迷失在其中,就再也難保追求慾望滿足的手段,是否具有合法性與正當性。小屁的想法中,踏實的法律工作賺錢速度太慢,所以,他先鎖定了具有高獲利特質的房地產,但做了幾個月後,覺得房屋仲介工作十分辛苦,帶客看屋,風吹雨淋,最後他還是決定辭掉工作。
小屁本來就有泡夜店的習慣,於是他相中了可以快速賺取暴利的毒品。這樣的結果正如名作家三毛所言:
「世上的喜劇不需要金錢就能產生,世上的悲劇大半和金錢脫不了關係。」──(三毛,《親愛的三毛》)
依照現行毒品防制法,海洛英是一級毒品,販賣它被抓,法官隨便判都是十幾年、甚至是無期徒刑的刑期,而小屁選擇販賣低風險的安非他命與K他命,法院量刑的標準都會在十年以下,如他這一趟被判七年的有期徒刑,相信是他內心預期的結果。
憑良心說,小屁歷經起訴、審判、入監,我並沒有感受到他的悔意,一絲絲都沒有,他不過是認為自己倒楣,被人出賣才會被逮住。當我問他將來出去有什麼打算?小屁自己也說不上來。根據我的觀察,他在獄中相當積極認識新朋友,擴展新的人際關係,這點令我十分擔憂。
「是誰把這個學業成績優異的小孩教成這樣?」
小屁在的那些日子裡,我不斷地思考這個問題。最終我承認,恐怕自己也脫不了關係!在我教書的那些時日,上課時,手上戴著百萬名錶,停在教室外的還是賓士AMG猛獸,口裡聊的笑話是酒店的風花雪月,神態自若是桀傲不遜地囂張。即便我和小屁是在獄中再度相見,我仍能看見小屁望著我時的崇拜眼神。我好想告訴小屁,老師當年錯了,但終究這一句話沒說出口,只是每天找他說教,盼望他能有所領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