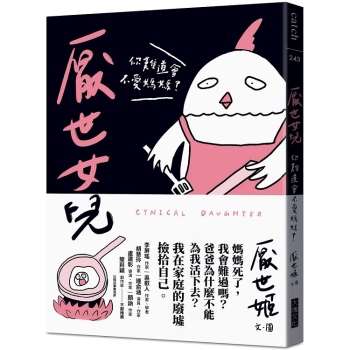我命太好了?
我去催眠。
看了兩段前世,第一段裡,我是一個在沙漠中守城牆的士兵。家裡只有我跟媽媽,好像還養了幾隻雞。後來結婚了,媽媽也死掉了。老婆生了一個兒子,兒子又生了孫子,然後我腳受傷感染就死掉了。臨死的時候身邊只有兒子和孫子,老婆不知道跑去哪。孫子好像很怕我的樣子,一點也不親。兒子也沒什麼表情,就默默的看著我。那個時候的我心想,好無聊的一生啊,真後悔沒去旅行。另一段是在海島,我是一個美麗又備受寵愛的少女,爸爸好像是頭目吧,家裡的屋簷下都會掛著一串串的白色貝殼。我每天都和隔壁青梅竹馬的少年在海裡玩,十六歲的時候就跟他結婚了。
也看到了今生。
七歲的我在我們家三樓吹頭髮,媽媽在二樓講電話。我都自己吹頭髮喔,因為我媽不喜歡幫我做這些事,她想訓練我獨立。我頭髮很長,吹一吹就被吹風機捲進去了,吹風機劈劈啪啪起了火花。我嚇死了,但只發出一聲「啊!」 媽在二樓,對我喊了一聲:「怎麼了?」因為我太驚嚇了,以至於什麼都說不出來。我自己把吹風機的插頭拔掉,把頭髮從吹風機裡面扯出來。頭髮被捲進去的時候很痛,而且還有燒焦味,所以我哭了。媽媽講完電話才來看我怎麼了,看到我在哭,她說:「我想你只是叫了一聲嘛,應該沒有很嚴重。」
催眠師說:「這就是你安全感匱乏的源頭。」
催眠一次要三千元,這個價錢可以吃有生蠔和海膽的無菜單日本料理。爸爸自殺過世後,我看了好幾年的心理諮商。諮商一次要一千五,累積下來應該已經可以買台摩托車了。所以說,要搞清楚自己心裡有什麼問題是很花錢的。
本來是因為爸爸自殺才去心理諮商,但大部分時間都在談媽媽的事。我媽有憂鬱症或是躁鬱症之類的精神疾病,曾經住過兩次療養院,但是沒有人願意跟我談這個問題。媽媽第二次住療養院的時候,爸爸還騙我是因為我不乖,所以媽媽離家出走了。
我長期處在自厭的情緒之中。
媽媽總是說我三分鐘熱度、粗心、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叫我不要太得意忘形,說我驕傲。「我把你生得這麼漂亮,你怎麼把自己搞得這麼醜?」每次看到我臉上的青春痘疤,她必定碎念一番,彷彿長青春痘是我的錯。
「你真的覺得自己三分鐘熱度嗎?或是粗心?」有次諮商師這樣問我。
「其實好像也還好,畢竟我現在也常常幫同事看帳,如果我很粗心的話,應該不會有人找我幫忙吧?」
諮商師給了我一個「那就對了」的眼神。我終於發現,原來我不是自己一直以為的那樣。
媽媽喜歡定義別人,而且往往是錯誤的定義。爸爸生肖屬狗,媽媽總是說爸爸愛狗,所以買了很多和狗相關的小東西給他,狗杯子、小型狗雕像、狗紙鎮等等。媽媽過世後,我和爸爸領養了一隻貓,他每天花很多時間陪貓玩,甚至買肯德基餵貓吃。
「其實我一直都比較喜歡貓。」有次爸爸脫口而出。我很訝異,但馬上想到家裡門口的鞋櫃上,放著五歲的爸爸抱著一隻小貓的照片。
就那麼顯眼的地方,媽媽還是自顧自的相信「爸爸愛狗」。而且她不只自己相信,還說服我一起相信。
我也被她說服自己是個充滿缺陷的人,自大、驕傲、沒定性、沒耐心、三分鐘熱度又粗心大意。我是個糟糕的人,我不值得被愛,我永遠不會成功。可是每當這麼喪氣的時候,媽媽又正面了起來。「你很有創意、有管理天分,還有語言天分。」她會這樣說。
「天分」是媽媽很在意的事,她覺得我有語言天分,就送我去上美語補習班;也覺得我有管理天分,EQ很高,就買了一堆卡內基的書給我看,希望我未來能成為高階經理人。但她從不覺得我有繪畫天分。國中時我熱中畫漫畫,有時半夜爬起來偷畫,她發現後,把我的稿子拿起來,說:「畫這麼醜,還是別畫了吧,不如去睡覺。」
媽媽似乎有種本能以打擊我為樂。小時候的我和大部分的小女孩一樣,都喜歡畫一些花或仙女之類的漂亮玩意兒。大約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得到一盒十二色的彩色鉛筆,外裝的鐵盒上印了五六種繪製得栩栩如生的花卉,有紫羅蘭、水仙、百合等。我照著畫,畫完了花,不免俗地又加了幾個小仙女。媽媽看到了就說:「你畫的不對。」隨即就在我的紙上、我畫的小仙女旁邊,畫了一個漂亮得不得了的娃娃。
「這樣才對。」媽媽有些得意洋洋。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她如何神氣地把那張紙交還給我。
到底什麼樣的人會以打擊自己的小孩為樂?
她沒有要教我怎麼畫,也沒有勉勵我將來會畫更好。她只是想告訴我:「你沒天分。」我所有的「天分」都是媽媽欽點的,她說什麼便是什麼,就像童話裡專事下咒的魔女。只要媽媽認定的事情,經由她的口講出來,就會成真。
我曾經嚮往當作家,她的建議是:「你命太好,寫不出好作品。」這次她倒不講天分了,在她眼裡,我是能寫的。她從未以「搞這些沒飯吃」或是「你靠什麼養活自己」阻止我走上創作這條路,而是更激進,或者說更浪漫的方式。「如果沒有受盡痛苦與折磨,是寫不出好作品的。你看那些文豪,不是很窮就是有病,不然就是身世坎坷。你啊,就是命太好,沒辦法當一個好的創作者。」她認為只有經過磨難、受苦的靈魂才能淬煉出曠世巨作。
這個說法太悲壯了,以至於我深信不疑。「啊,也許我不適合創作吧,畢竟我的命這麼好。」
反倒是後來我把這個說法講給人聽,有人皺著眉說:「你真是老派文青啊!」
對於我的命很好這點,我也是深信不疑。就算因為媽媽的關係受了不少苦,我還是覺得自己命很好。「誰像你一樣這麼小就去過那麼多國家呢?」「誰像你一樣看這麼多舞台劇呢?」「這是因為爸爸媽媽愛你,才讓你過這麼好的生活啊!」這是媽媽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以至於媽媽過世後不久,當我發現爸爸陳屍在家中浴缸的那一刻,我就像演戲一樣,仰頭對著空氣中某個地方:「媽媽,你看看吧,這就是你所謂的好命嗎?」
而即使是提筆的現在,我還是會忍不住忿忿地問:我夠格了嗎?我可以當一個創作者了嗎?
但,也已經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了。
不願忍耐,就會沒有媽媽?
很小的時候,我就隱隱約約知道媽媽生病了。稍微長大一點之後,爸爸告訴我,媽媽生的病叫作憂鬱症。當時我年紀太小,憂鬱症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我沒辦法把它和媽媽激烈的情緒起伏、暴怒和歇斯底里聯想在一起。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爸爸時不時就對我說:「媽媽生病了,你要讓著媽媽一點。」可能是因為我漸漸長大了,所以媽媽暴怒發脾氣之後,爸爸也不再安慰我,而是要求我再多忍耐一點。
「沒辦法,她就是你媽嘛。你不願意忍耐,你就沒有媽媽了。」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選擇了忍耐。
媽媽第一次因憂鬱症住院的時候,我念幼稚園中班,應該是四歲或五歲的年紀。平常早上媽媽都會送我去巷子口搭校車,下午校車會把我送回巷子口,媽媽再把我從巷口領回家。媽媽住院之後,早上爸爸載我去上學,我得等到晚上六、七點,爸爸下班之後才會來幼稚園接我回家。
有一天晚上,同學們全都回家了,只剩下一個同學和我還遲遲無人領回。那時候我默默祈禱,希望自己不要最後一個離開。我告訴自己,我的爸爸一定會比同學的爸爸更早來接我。那時,我已經緊張得想哭了,等到同學的爸爸出現在門口時,我終於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全校只剩我一個小孩了,爸爸忘記我了嗎?到現在,我連另外那個孩子是男是女都不記得,但差點被拋棄的恐懼,卻永遠都忘不了。
爸爸接我回家之後,就會煮晚餐給我吃。煮來煮去就那幾道菜,不是肉丸湯,就是煮泡麵。肉丸有點費事但並不困難,家裡有一台食物調理機,把雞胸肉和蔬菜一起放進去磨成泥,再丟到湯裡面煮熟就可以了。湯裡還放了大白菜,煮得爛爛的,吸飽了肉湯很好吃。煮泡麵就再加上青江菜和雞蛋而已。
我們都在吃完晚餐後,去醫院看媽媽。媽媽當時住的是台北市立療養院,也就是現在的松德院區。有時,爸爸會先帶我去夜市,在販售錄音帶的攤子買幾張暢銷金曲合輯,帶去給媽媽。不過,通常還沒到醫院,就被我迫不及待地先拆開來,用隨身聽聽。我常常會想起自己坐在粉紅色塑膠候診椅上聽隨身聽的樣子,頭頂死氣沈沈的日光燈白光,腳下的磨石子地板,耳機裡的〈針線情〉和〈雙人枕頭〉,都像電影畫面般清晰。
〈針線情〉是我那時最喜歡的歌,常常進了媽媽的病房,我就會爬到她床上唱給她聽。我其實並不懂歌詞的意思,也只會唱「你是針,我是線」這一句,後面都咿咿呀呀亂哼,但爸爸媽媽不以為意,只要我唱,他們都特別高興。
住院的媽媽很溫柔,總是笑容滿面。跟她同房的病友是個短頭髮的阿姨,也都笑盈盈的。病友阿姨很喜歡我,會拿她做的捏麵小動物送我。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憂鬱症」這三個字,卻不懂它的意思。得了這個病的人會憂鬱嗎?但是住院的媽媽和隔壁床的阿姨,都讓我無法和「憂鬱」聯想在一起。媽媽第二次住院,我以為是被我氣到離家出走。爸爸知道事情真相,卻選擇不告訴我,我學得的教訓是:如果我不忍耐、不讓媽媽,媽媽就會消失不見。為了不讓媽媽消失,我得不斷不斷忍耐,直到上了高中。
一開始是這樣的,我和幾個同學不想上課,翹課躲到通往頂樓的樓梯間閒聊打混。那是我第一次翹課,過去讀私立國中,當好學生當慣了,一下子不合規矩,心裡難免緊張。同學倒是安撫我說,沒關係,萬一被發現缺席,只要去輔導室拿假條就可以了。蛤?原來可以這樣喔?我驚呼,讚嘆公立學校的自由風氣。其實也可以順便跟輔導老師聊聊啦!同學補充。我也才發現,在場幾個同學,都有去輔導室「聊聊」的經驗。
於是就這樣,原本只是去拿假條,卻變成輔導室的常客。我開始固定去輔導室報到,和輔導老師「聊聊」。
或許是因為年紀漸長,過去不了解的事情,逐漸浮現清晰的輪廓。在我原本渾沌的腦袋裡,媽媽的暴躁與她的病,終於產生了連結。我開始察覺,或許媽媽本來就有病,或許我根本就沒有做錯什麼。
已經不太記得和輔導老師談了什麼,只記得自己一直哭,憤怒和委屈從心底湧出,像水壩潰堤一般。我細數從小到大媽媽各種毫無道理的打罵,滔滔不絕,而輔導室宣泄的痛快一直延續到家裡,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決定不再忍耐。我擬好說詞,在心中一再演練。我要向媽媽討回公道,我要告訴她,你不該這樣對待我。
那是一次激烈的爭吵。我預備好的說詞才講到第三句,媽媽就開始尖叫嘶吼。
你現在是要來檢討我了嗎?」
「我這麼多年做牛做馬,你怎麼這麼不知感恩?」
「我養你這種小孩做什麼?」
我知道我已經失敗,無論我怎麼說,媽媽都不願意承認她帶給我的痛苦。
「你不高興嗎?告訴你,人不能選擇父母,這就是你的命,不喜歡也得接受。」
這句話徹底擊垮了我,從那之後,我知道再也沒什麼好說的了。但對媽媽的態度,已經無法再如過去般惟命是從。
高三時,一位轉班的同學被安排坐在我旁邊。她是一位皮膚白皙、五官精緻美麗、充滿仙氣的女孩,同學都戲稱她林黛玉。她也像林黛玉一樣多愁善感,甚至太多愁善感了,常常課上到一半就忽然哭了起來。我幾乎同時有所警覺,果然耳語傳來,黛玉同學似乎有憂鬱症。
從此,我沒辦法直視黛玉同學,我不知道她哭的時候我該怎麼辦。輔導老師說,她的情緒不是我的責任,我不需要為她負責。但是我無法控制,爸爸那句「媽媽生病了,你要讓著她一點」已成了我的緊箍咒,甚至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只要聽到「生病」這個關鍵詞,我就會不由自主的避著對方,即使對方並不是我媽。
黛玉同學,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故意冷眼看著你哭,我只是害怕一旦關心你,你就會變成我的責任,需要一直一直照顧。而我已經累了,沒力氣可以再照顧另一個人。即使我知道你或許只需一句安慰,但我真的太害怕了,只能逃避。
成年後,憂鬱症更成了我的罩門,有些心懷不軌的人利用這點佔了我不少便宜。有些人把憂鬱症當免死金牌,做了許多傷害別人的事,卻逃避責任。這些都讓我對這個疾病充滿複雜的情緒。每當社會上有重度憂鬱症患者自殺,社群網路一片哀悼聲中,我卻一點感覺都沒有。為此,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為何從不那樣稱讚我?
小學一年級的第一次隨堂考試,我考了七十分。由於之前就讀公立幼稚園,當時禁止教授注音,而小學老師卻考了注音聽寫。十題注音符號,一題十分,我憑著生活中的朦朧印象,居然也猜對了七題。爸爸媽媽看到成績,簡直嚇死了,尤其媽媽更是哭天喊地,馬上打電話向親友求助。
其實那次測驗只是老師用來評估學生的程度,注音符號還是從頭教起。之後,我的考試成績從來沒低於九十分。
我常開玩笑說自己是所謂的「學霸」,從小就名列前茅。考取台大法律系的時候,成績還是全國第一類組的前百名。那大概是媽媽首次打從心底對我滿意,她興奮的到處報喜,讓我也沈浸於快樂之中。
「你爸爸很高興,我很少看到他這麼高興。」媽媽等不及爸爸下班回家就打電話向他通報消息,之後這樣對我說,「如果可以的話,你爸會去放鞭炮。」
我去催眠。
看了兩段前世,第一段裡,我是一個在沙漠中守城牆的士兵。家裡只有我跟媽媽,好像還養了幾隻雞。後來結婚了,媽媽也死掉了。老婆生了一個兒子,兒子又生了孫子,然後我腳受傷感染就死掉了。臨死的時候身邊只有兒子和孫子,老婆不知道跑去哪。孫子好像很怕我的樣子,一點也不親。兒子也沒什麼表情,就默默的看著我。那個時候的我心想,好無聊的一生啊,真後悔沒去旅行。另一段是在海島,我是一個美麗又備受寵愛的少女,爸爸好像是頭目吧,家裡的屋簷下都會掛著一串串的白色貝殼。我每天都和隔壁青梅竹馬的少年在海裡玩,十六歲的時候就跟他結婚了。
也看到了今生。
七歲的我在我們家三樓吹頭髮,媽媽在二樓講電話。我都自己吹頭髮喔,因為我媽不喜歡幫我做這些事,她想訓練我獨立。我頭髮很長,吹一吹就被吹風機捲進去了,吹風機劈劈啪啪起了火花。我嚇死了,但只發出一聲「啊!」 媽在二樓,對我喊了一聲:「怎麼了?」因為我太驚嚇了,以至於什麼都說不出來。我自己把吹風機的插頭拔掉,把頭髮從吹風機裡面扯出來。頭髮被捲進去的時候很痛,而且還有燒焦味,所以我哭了。媽媽講完電話才來看我怎麼了,看到我在哭,她說:「我想你只是叫了一聲嘛,應該沒有很嚴重。」
催眠師說:「這就是你安全感匱乏的源頭。」
催眠一次要三千元,這個價錢可以吃有生蠔和海膽的無菜單日本料理。爸爸自殺過世後,我看了好幾年的心理諮商。諮商一次要一千五,累積下來應該已經可以買台摩托車了。所以說,要搞清楚自己心裡有什麼問題是很花錢的。
本來是因為爸爸自殺才去心理諮商,但大部分時間都在談媽媽的事。我媽有憂鬱症或是躁鬱症之類的精神疾病,曾經住過兩次療養院,但是沒有人願意跟我談這個問題。媽媽第二次住療養院的時候,爸爸還騙我是因為我不乖,所以媽媽離家出走了。
我長期處在自厭的情緒之中。
媽媽總是說我三分鐘熱度、粗心、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叫我不要太得意忘形,說我驕傲。「我把你生得這麼漂亮,你怎麼把自己搞得這麼醜?」每次看到我臉上的青春痘疤,她必定碎念一番,彷彿長青春痘是我的錯。
「你真的覺得自己三分鐘熱度嗎?或是粗心?」有次諮商師這樣問我。
「其實好像也還好,畢竟我現在也常常幫同事看帳,如果我很粗心的話,應該不會有人找我幫忙吧?」
諮商師給了我一個「那就對了」的眼神。我終於發現,原來我不是自己一直以為的那樣。
媽媽喜歡定義別人,而且往往是錯誤的定義。爸爸生肖屬狗,媽媽總是說爸爸愛狗,所以買了很多和狗相關的小東西給他,狗杯子、小型狗雕像、狗紙鎮等等。媽媽過世後,我和爸爸領養了一隻貓,他每天花很多時間陪貓玩,甚至買肯德基餵貓吃。
「其實我一直都比較喜歡貓。」有次爸爸脫口而出。我很訝異,但馬上想到家裡門口的鞋櫃上,放著五歲的爸爸抱著一隻小貓的照片。
就那麼顯眼的地方,媽媽還是自顧自的相信「爸爸愛狗」。而且她不只自己相信,還說服我一起相信。
我也被她說服自己是個充滿缺陷的人,自大、驕傲、沒定性、沒耐心、三分鐘熱度又粗心大意。我是個糟糕的人,我不值得被愛,我永遠不會成功。可是每當這麼喪氣的時候,媽媽又正面了起來。「你很有創意、有管理天分,還有語言天分。」她會這樣說。
「天分」是媽媽很在意的事,她覺得我有語言天分,就送我去上美語補習班;也覺得我有管理天分,EQ很高,就買了一堆卡內基的書給我看,希望我未來能成為高階經理人。但她從不覺得我有繪畫天分。國中時我熱中畫漫畫,有時半夜爬起來偷畫,她發現後,把我的稿子拿起來,說:「畫這麼醜,還是別畫了吧,不如去睡覺。」
媽媽似乎有種本能以打擊我為樂。小時候的我和大部分的小女孩一樣,都喜歡畫一些花或仙女之類的漂亮玩意兒。大約小學一年級的時候,我得到一盒十二色的彩色鉛筆,外裝的鐵盒上印了五六種繪製得栩栩如生的花卉,有紫羅蘭、水仙、百合等。我照著畫,畫完了花,不免俗地又加了幾個小仙女。媽媽看到了就說:「你畫的不對。」隨即就在我的紙上、我畫的小仙女旁邊,畫了一個漂亮得不得了的娃娃。
「這樣才對。」媽媽有些得意洋洋。直到現在,我都還記得她如何神氣地把那張紙交還給我。
到底什麼樣的人會以打擊自己的小孩為樂?
她沒有要教我怎麼畫,也沒有勉勵我將來會畫更好。她只是想告訴我:「你沒天分。」我所有的「天分」都是媽媽欽點的,她說什麼便是什麼,就像童話裡專事下咒的魔女。只要媽媽認定的事情,經由她的口講出來,就會成真。
我曾經嚮往當作家,她的建議是:「你命太好,寫不出好作品。」這次她倒不講天分了,在她眼裡,我是能寫的。她從未以「搞這些沒飯吃」或是「你靠什麼養活自己」阻止我走上創作這條路,而是更激進,或者說更浪漫的方式。「如果沒有受盡痛苦與折磨,是寫不出好作品的。你看那些文豪,不是很窮就是有病,不然就是身世坎坷。你啊,就是命太好,沒辦法當一個好的創作者。」她認為只有經過磨難、受苦的靈魂才能淬煉出曠世巨作。
這個說法太悲壯了,以至於我深信不疑。「啊,也許我不適合創作吧,畢竟我的命這麼好。」
反倒是後來我把這個說法講給人聽,有人皺著眉說:「你真是老派文青啊!」
對於我的命很好這點,我也是深信不疑。就算因為媽媽的關係受了不少苦,我還是覺得自己命很好。「誰像你一樣這麼小就去過那麼多國家呢?」「誰像你一樣看這麼多舞台劇呢?」「這是因為爸爸媽媽愛你,才讓你過這麼好的生活啊!」這是媽媽常常掛在嘴邊的話。
以至於媽媽過世後不久,當我發現爸爸陳屍在家中浴缸的那一刻,我就像演戲一樣,仰頭對著空氣中某個地方:「媽媽,你看看吧,這就是你所謂的好命嗎?」
而即使是提筆的現在,我還是會忍不住忿忿地問:我夠格了嗎?我可以當一個創作者了嗎?
但,也已經沒有人能回答這個問題了。
不願忍耐,就會沒有媽媽?
很小的時候,我就隱隱約約知道媽媽生病了。稍微長大一點之後,爸爸告訴我,媽媽生的病叫作憂鬱症。當時我年紀太小,憂鬱症對我來說只是一個模糊的概念,我沒辦法把它和媽媽激烈的情緒起伏、暴怒和歇斯底里聯想在一起。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爸爸時不時就對我說:「媽媽生病了,你要讓著媽媽一點。」可能是因為我漸漸長大了,所以媽媽暴怒發脾氣之後,爸爸也不再安慰我,而是要求我再多忍耐一點。
「沒辦法,她就是你媽嘛。你不願意忍耐,你就沒有媽媽了。」大概是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選擇了忍耐。
媽媽第一次因憂鬱症住院的時候,我念幼稚園中班,應該是四歲或五歲的年紀。平常早上媽媽都會送我去巷子口搭校車,下午校車會把我送回巷子口,媽媽再把我從巷口領回家。媽媽住院之後,早上爸爸載我去上學,我得等到晚上六、七點,爸爸下班之後才會來幼稚園接我回家。
有一天晚上,同學們全都回家了,只剩下一個同學和我還遲遲無人領回。那時候我默默祈禱,希望自己不要最後一個離開。我告訴自己,我的爸爸一定會比同學的爸爸更早來接我。那時,我已經緊張得想哭了,等到同學的爸爸出現在門口時,我終於忍不住大聲哭了出來。全校只剩我一個小孩了,爸爸忘記我了嗎?到現在,我連另外那個孩子是男是女都不記得,但差點被拋棄的恐懼,卻永遠都忘不了。
爸爸接我回家之後,就會煮晚餐給我吃。煮來煮去就那幾道菜,不是肉丸湯,就是煮泡麵。肉丸有點費事但並不困難,家裡有一台食物調理機,把雞胸肉和蔬菜一起放進去磨成泥,再丟到湯裡面煮熟就可以了。湯裡還放了大白菜,煮得爛爛的,吸飽了肉湯很好吃。煮泡麵就再加上青江菜和雞蛋而已。
我們都在吃完晚餐後,去醫院看媽媽。媽媽當時住的是台北市立療養院,也就是現在的松德院區。有時,爸爸會先帶我去夜市,在販售錄音帶的攤子買幾張暢銷金曲合輯,帶去給媽媽。不過,通常還沒到醫院,就被我迫不及待地先拆開來,用隨身聽聽。我常常會想起自己坐在粉紅色塑膠候診椅上聽隨身聽的樣子,頭頂死氣沈沈的日光燈白光,腳下的磨石子地板,耳機裡的〈針線情〉和〈雙人枕頭〉,都像電影畫面般清晰。
〈針線情〉是我那時最喜歡的歌,常常進了媽媽的病房,我就會爬到她床上唱給她聽。我其實並不懂歌詞的意思,也只會唱「你是針,我是線」這一句,後面都咿咿呀呀亂哼,但爸爸媽媽不以為意,只要我唱,他們都特別高興。
住院的媽媽很溫柔,總是笑容滿面。跟她同房的病友是個短頭髮的阿姨,也都笑盈盈的。病友阿姨很喜歡我,會拿她做的捏麵小動物送我。
那是我第一次聽到「憂鬱症」這三個字,卻不懂它的意思。得了這個病的人會憂鬱嗎?但是住院的媽媽和隔壁床的阿姨,都讓我無法和「憂鬱」聯想在一起。媽媽第二次住院,我以為是被我氣到離家出走。爸爸知道事情真相,卻選擇不告訴我,我學得的教訓是:如果我不忍耐、不讓媽媽,媽媽就會消失不見。為了不讓媽媽消失,我得不斷不斷忍耐,直到上了高中。
一開始是這樣的,我和幾個同學不想上課,翹課躲到通往頂樓的樓梯間閒聊打混。那是我第一次翹課,過去讀私立國中,當好學生當慣了,一下子不合規矩,心裡難免緊張。同學倒是安撫我說,沒關係,萬一被發現缺席,只要去輔導室拿假條就可以了。蛤?原來可以這樣喔?我驚呼,讚嘆公立學校的自由風氣。其實也可以順便跟輔導老師聊聊啦!同學補充。我也才發現,在場幾個同學,都有去輔導室「聊聊」的經驗。
於是就這樣,原本只是去拿假條,卻變成輔導室的常客。我開始固定去輔導室報到,和輔導老師「聊聊」。
或許是因為年紀漸長,過去不了解的事情,逐漸浮現清晰的輪廓。在我原本渾沌的腦袋裡,媽媽的暴躁與她的病,終於產生了連結。我開始察覺,或許媽媽本來就有病,或許我根本就沒有做錯什麼。
已經不太記得和輔導老師談了什麼,只記得自己一直哭,憤怒和委屈從心底湧出,像水壩潰堤一般。我細數從小到大媽媽各種毫無道理的打罵,滔滔不絕,而輔導室宣泄的痛快一直延續到家裡,不知道哪來的勇氣,我決定不再忍耐。我擬好說詞,在心中一再演練。我要向媽媽討回公道,我要告訴她,你不該這樣對待我。
那是一次激烈的爭吵。我預備好的說詞才講到第三句,媽媽就開始尖叫嘶吼。
你現在是要來檢討我了嗎?」
「我這麼多年做牛做馬,你怎麼這麼不知感恩?」
「我養你這種小孩做什麼?」
我知道我已經失敗,無論我怎麼說,媽媽都不願意承認她帶給我的痛苦。
「你不高興嗎?告訴你,人不能選擇父母,這就是你的命,不喜歡也得接受。」
這句話徹底擊垮了我,從那之後,我知道再也沒什麼好說的了。但對媽媽的態度,已經無法再如過去般惟命是從。
高三時,一位轉班的同學被安排坐在我旁邊。她是一位皮膚白皙、五官精緻美麗、充滿仙氣的女孩,同學都戲稱她林黛玉。她也像林黛玉一樣多愁善感,甚至太多愁善感了,常常課上到一半就忽然哭了起來。我幾乎同時有所警覺,果然耳語傳來,黛玉同學似乎有憂鬱症。
從此,我沒辦法直視黛玉同學,我不知道她哭的時候我該怎麼辦。輔導老師說,她的情緒不是我的責任,我不需要為她負責。但是我無法控制,爸爸那句「媽媽生病了,你要讓著她一點」已成了我的緊箍咒,甚至就像巴甫洛夫的狗,只要聽到「生病」這個關鍵詞,我就會不由自主的避著對方,即使對方並不是我媽。
黛玉同學,真的很抱歉,我不是故意冷眼看著你哭,我只是害怕一旦關心你,你就會變成我的責任,需要一直一直照顧。而我已經累了,沒力氣可以再照顧另一個人。即使我知道你或許只需一句安慰,但我真的太害怕了,只能逃避。
成年後,憂鬱症更成了我的罩門,有些心懷不軌的人利用這點佔了我不少便宜。有些人把憂鬱症當免死金牌,做了許多傷害別人的事,卻逃避責任。這些都讓我對這個疾病充滿複雜的情緒。每當社會上有重度憂鬱症患者自殺,社群網路一片哀悼聲中,我卻一點感覺都沒有。為此,我真的感到非常抱歉。
為何從不那樣稱讚我?
小學一年級的第一次隨堂考試,我考了七十分。由於之前就讀公立幼稚園,當時禁止教授注音,而小學老師卻考了注音聽寫。十題注音符號,一題十分,我憑著生活中的朦朧印象,居然也猜對了七題。爸爸媽媽看到成績,簡直嚇死了,尤其媽媽更是哭天喊地,馬上打電話向親友求助。
其實那次測驗只是老師用來評估學生的程度,注音符號還是從頭教起。之後,我的考試成績從來沒低於九十分。
我常開玩笑說自己是所謂的「學霸」,從小就名列前茅。考取台大法律系的時候,成績還是全國第一類組的前百名。那大概是媽媽首次打從心底對我滿意,她興奮的到處報喜,讓我也沈浸於快樂之中。
「你爸爸很高興,我很少看到他這麼高興。」媽媽等不及爸爸下班回家就打電話向他通報消息,之後這樣對我說,「如果可以的話,你爸會去放鞭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