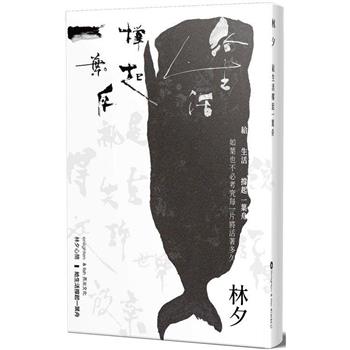〈不需要命書〉
當 害怕有朝一日
恐懼已經存在
那一刻也
提早到來
因為害怕會
所以就會
情緒不是因
卻很會結果
正如憂鬱
憂心會有鬱結
憂慮就開始打結
像小偷一樣
看著別人的日記
記載的卻是自己
一頁一頁
就這樣按著猜想
成真
不需要甚麼命書
在很想知道明天將會發生甚麼
的時候
緊張 懸疑
已經決定了
劇情將會發展成
一個人
驚慄劇
的一生
〈心田〉
如果說「心窗」、「心扉」有一陣陳腐氣,也許還有別的詞語可以取代,像「心田」,還有甚麼比「田」更能形容人心的奧妙。
心的確就像塊田,放過甚麼進去,都會播下種子,或早或晚,在條件成熟時種出果實,或甜或苦,或綠樹成蔭,或芒刺滿地。心念一動,即如撒種,有時連收了成也毫無知覺。
一般的田,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只有心田會變戲法,同一樣的東西,放進不同人的心裡,有不同的因緣,得出不一樣的結果。被人傷盡了心,有人會種出枯木死灰,有人會種出橫練不死身,堅毅如松。挨了一頓罵,吃了個耳光,心裡留下了疙瘩,有人會生出以暴易暴之心,有人會失去了自尊心,生出了自卑感,也許,有人會從最初深深不忿,慢慢消化之後,體驗到暴力令人如何難受,施與受者同樣成為火宅之人,興許會生出一顆同理心。
那天看一篇寫跨代貧窮的文章,說倘若一家之主無業又無賴,母親則不做飯不管事,不打麻將便打罵子女,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的孩子,會變出怎樣的個性,還能有甚麼前途。成長的環境也是一塊田,在如此不堪的土壤,就一定開不出花來嗎?
孩子的眼睛看著些難看的景,就只會得出一樣的心境?為甚麼不可能因為自小就知道快樂是如何失去的,以後更懂得幸福是怎樣煉成的。不指望旁人的呵護,於是比誰都活得更強壯。屎一樣的童年往事,在泥土中醞釀發酵,說不準就培育出不讓別人重蹈自己覆轍的心。每個人活到甚麼田地,最重要的可能是心田的耕耘法。
〈道無名〉
有次在日本京都一人行,在地圖上看見有道路名曰「哲學大道」,也不管是否曾有哲人在此悟道論道,或有像智者如蘇格拉底那樣與學生邊談邊論道之類的逸事而得名,走一趟就是了。
走在那條山蔭小徑,沒有從鬱鬱黃花悟到甚麼般若智慧,只是想到很低層次「名」的問題,關於街道的名字。想起香港有些主要街道都是從英國歷任港督的洋名中譯了事,像彌敦道羅便臣道麥當勞道,有些是無心考究來源的英語中譯,如告士打道、梭士巴利道、盧押道、莊士敦道,毫無感情色彩,又陌生拗口,一條街道只落得一條街道,名字沒有為路名增添氣氛的附加價值。
不過想到台灣的大道,名仁愛,名忠孝,名信義,名建國,名敦化,名光復,名和平,又未免太大道了。不是不忘教化,就是背著使命的包袱,一路走來,活在其中,潛移默化,對名字或文字過敏的人,怕會步步為營,沒事人處在這氛圍當中,也會不自覺有修身治國疲勞感嗎?
說到底,從地圖看街道的名字,跟活在真實的街道是兩碼子事。一切過分的聯想都是多餘的,台北信義區是高貴地段的代表,信義信義叫慣了就不會再有信義帶來的壓力,正如香港一條不知出於何故何典而命名的利東街,因為有了風俗而多了囍帖街之名,再因為有了故事,即使依然叫利東,從此也色味雙全。
多虧有一種叫集體回憶的染料,為乏味或失效的名字添上感情。
不曉得有多少人知道台北陽明山是由蔣介石從草山改為陽明,只為老蔣自認是明代大哲學家教育家政治家王陽明的追隨者,為揚陽明之學,為紀陽明之名,陽明山外再添陽明山莊。
只是王陽明知行合一有我無我之心學,並沒有因此讓草山一夜間變成領悟「除心以外無外物」的聖地,反倒是悠閒度假吃土雞泡溫泉賞花之好去處,給招待在陽明山莊的貴賓大人物,也不會在籌劃計算時向王陽明取經。名字敵不過事件,敵不過生活。
〈外出恐懼症〉
我知道我知道別說我不知道
門
就是矮一點的牆
開
只比鑽洞輕鬆點
廳
房
廚
廁
重重關卡一動一心跳
在臥室醒來
倒不如繼續
在臥室睡去
我了解我了解別說我不了解
比生命還大
的大門
走到電梯的路恍如隔世
一旦下樓一步一生
外出再歸來就是死了又要重生
分不出活得太累抑或死得太多
外面
有路有車還有
人
珍惜生命遠離眼神
我明白我明白別說我不明白
明明是
捨不得孤獨為王淪為人海一粟
明明只是
習慣了自囚多福
明明只是
懶於與空氣打交道
要開的不是門
是內藏過期蛋白質的保鮮袋
要拆的不是牆 是自己這副本來會動的
木乃伊
別以為我沒有曾經這樣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