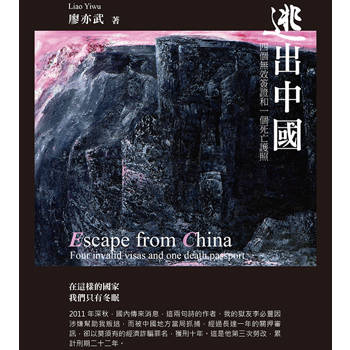楔子
話說老母今年九十有四,可外人問起,從來都未滿八十。她至今獨居,除了我和我早就遠行的老爸,從來沒誰和她相處過兩天以上。
老母文化偏低,性格也獨特,文革初期因投機倒把(倒賣布票)被揪鬥過一次,居然在戲台上和按她腦袋的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打成一團,轟動一時,民憤極大。最終賬卻算在文化偏高的老父頭上……
再話說我逃出中國不久,專門負責我的警官李胖子提了月餅登門,問她:二毛是咋個跑的?她回答:你都不曉得,我咋個曉得呢?李胖子哭笑不得,臉色比餓鬼難看。老母於心不忍,殷勤留飯,數日後還在越洋電話中對我說:二毛啊,改天你還是給人家去個電話,陪個不是,人家因為你官也升不成,獎金也拿不成,還給你媽送月餅。你啥子時候給老娘送過月餅?
我很不以為然。老母感覺出來了。就嘆氣道:就你把老娘拿得住。
拿得住?回憶的閘門就這樣打開了。
跨過界河
2011 年 7 月 2 日,上午九點四十五分,我離開酒店,按黑道約定,十點我準時抵達海關。稀稀拉拉幾個背包客,海關櫃檯後是個戴眼鏡的胖子,我倆無限深情地對視了幾秒,我都汗毛倒豎了,他卻在我的護照上啪地蓋戳。從安檢機器口拎起行囊,我滿面潮紅,醉漢般搖晃,雖極力鎮定,卻走不了直線,當來到中越大橋中央,竟膝蓋一軟,跪下去了。我把住橋欄,撐起身子,冷汗淋漓。腳底波濤比血還紅,陽光猶如刺刀,劃出滾滾東去的一道道傷口。我突然看見多年前去世的姐姐,長長的辮子,大大的眼睛;接著是爸爸,年輕時穿著西裝,年老時戴著帽子;我眨眨眼,在姐姐和爸爸的記憶漩渦間,又湧現出兩個舅舅,從未謀面的敗逃的大舅躲在落網的戰犯四舅後面,猶如月亮躲在太陽後面……再接著,逝者如雪,紛紛揚揚,我追隨著他們,穿過三百多米長橋,抵達越南老街海關,出了大樓還魂不守舍。
下臺階時,接應我的黑道小劉迎面而來……
※※※
這是我二次跨過同一界河。驚魂稍定,就跟小劉去一露天咖啡店,要了越南特色的滴漏冰咖啡。東張西望,二話不說,我就從登山包深處挖出幾沓人民幣,一五一十數起來。小劉接過去繼續數。眼看著交易圓滿完成,我才笑道:「幹這行當賺錢挺容易。」
小劉道:「容易個屁。這四萬元,放你過關的胖子要抽三萬,剩下一萬,兩個人均分。沒辦法,小泥鰍嘛,泥裡水裡亂鑽,也就掙幾個活命小錢。」
「死胖子也太貪了。」
「他是國家的人,要承擔風險囉。」
「放我的風險不算大吧?」
「比放販毒和走私小。」
「這也敢放?」
「有錢能使鬼推磨。給胖子一百萬,殺人犯都敢放。」
「出事兒呢?」
「調離崗位,記過,開除,頂破天坐兩年牢吧。只要一夜暴富,四年也值。」
「腐敗令人膽兒肥。」我讚嘆道。「毛主席說,歷史由膽兒肥的英雄們創造。」
「沒腐敗就沒自由,」小劉擡頭盯了我兩秒鐘,將數過兩遍的鈔票塞進隨身軍挎包,「理解你的心情。」
內心莫名酸楚,我又掏二百塊錢塞過去,小劉忙道:「道有道規,說多少是多少。」於是我起立,模仿舊時代讀書人,拱手兼鞠躬:「活命之恩,無以為報。」
小劉驚道:「老師您別、別、別折煞我。」越南老闆見狀,從另一頂遮陽傘下過來,嘰哩哇啦了一通。小劉翻譯道:「老闆大發感慨,說你行禮的樣子像附近孔夫子廟的泥胎。」
※※※
日漸當頂,雖然昨夜暴風雨,但此時的天地仍然如一口無形的高壓鍋,我感覺渾身散發著熟肉味兒。越南老闆再三招呼進屋,我們謝絕了。接著橫穿大片空地,去一電訊商店買手機卡。小劉用結結巴巴的越南話交涉了半天,店員卻敲竹槓,非要手機和電話卡一起賣。於是我掏三百元人民幣,購得第五隻諾基亞原始版手機,鴨蛋大小,屏幕顯示深奧莫測的越南拼音。據說這種文字才一百多年歷史,是法國傳教士仿照當地土著發音,結合法語創造出來的,在此之前,越南的官方文字是漢語。
我用越南手機給德國科隆的天琪打通了電話,她驚喜異常,並記下號碼。我讓她儘快轉告漁夫出版社責任編輯彼得‧西冷,譯者黃文,以及紐約經紀人彼得‧伯恩斯坦。天琪說會的,我們隨時保持聯繫。接著我打第二個電話給臺灣新竹的文賢,才說了幾句,就突然欠費停機。我只好摸出國內帶出來的四個手機,都是一模一樣的諾基亞,我選擇其中一隻,給好幾個人發簡訊。天熱得快爆炸,地面像潑了一層滾沸的辣椒油,四處冒泡。小劉蹲在階沿下,焦炭般黑糊糊地冒煙。幸而還沒遠離界河,有比較微弱的信號。
我從小劉眼裡讀出了疑問,就解釋道:「公開的已關機,電池也拿掉了,兩天前我用它給國保李警官打了最後的電話,強烈要求喝茶談心,遭嚴詞謝絕。私下的三隻手機,都是單線聯繫。」
「哼哼,你這個笨特務。」
「這年頭哪來的特務?」
「我是 1979 年中越戰爭期間生的,我爸是邊防軍,參加過老山守衛戰,活捉過不少越南特務。搞情報,埋地雷,殺人放火,無惡不作。」
「老黃曆啦。估計你爸也是無惡不作的中國特務。」
「我爸退役時,中越拉鋸戰還沒結束,老人家就從戰友那兒,弄了不少槍支彈藥回家倒賣。文山縣的邊境村子,退役老兵倒賣軍火蔚然成風,全國各地的黑社會都聞風而至,錢賺瘋了。殺人越貨的案子多了,最後政府也聞風而至,一遍遍廣播通令,上千武警包圍,並挨家挨戶搜繳,最終引發大規模巷戰。我們村子交火一晝夜,火焰噴射器都派上用場。成年男人被擊斃一半,坐牢一半,寡婦們不得不當家作主。」
「你爸也被擊斃了?」
「我爸腰椎中槍,坐輪椅了。」
「不錯不錯,有其父必有其子。」
「天壤之別。我爸就是殘廢了,氣勢也能壓倒我。」
話說老母今年九十有四,可外人問起,從來都未滿八十。她至今獨居,除了我和我早就遠行的老爸,從來沒誰和她相處過兩天以上。
老母文化偏低,性格也獨特,文革初期因投機倒把(倒賣布票)被揪鬥過一次,居然在戲台上和按她腦袋的毛澤東思想戰鬥隊打成一團,轟動一時,民憤極大。最終賬卻算在文化偏高的老父頭上……
再話說我逃出中國不久,專門負責我的警官李胖子提了月餅登門,問她:二毛是咋個跑的?她回答:你都不曉得,我咋個曉得呢?李胖子哭笑不得,臉色比餓鬼難看。老母於心不忍,殷勤留飯,數日後還在越洋電話中對我說:二毛啊,改天你還是給人家去個電話,陪個不是,人家因為你官也升不成,獎金也拿不成,還給你媽送月餅。你啥子時候給老娘送過月餅?
我很不以為然。老母感覺出來了。就嘆氣道:就你把老娘拿得住。
拿得住?回憶的閘門就這樣打開了。
跨過界河
2011 年 7 月 2 日,上午九點四十五分,我離開酒店,按黑道約定,十點我準時抵達海關。稀稀拉拉幾個背包客,海關櫃檯後是個戴眼鏡的胖子,我倆無限深情地對視了幾秒,我都汗毛倒豎了,他卻在我的護照上啪地蓋戳。從安檢機器口拎起行囊,我滿面潮紅,醉漢般搖晃,雖極力鎮定,卻走不了直線,當來到中越大橋中央,竟膝蓋一軟,跪下去了。我把住橋欄,撐起身子,冷汗淋漓。腳底波濤比血還紅,陽光猶如刺刀,劃出滾滾東去的一道道傷口。我突然看見多年前去世的姐姐,長長的辮子,大大的眼睛;接著是爸爸,年輕時穿著西裝,年老時戴著帽子;我眨眨眼,在姐姐和爸爸的記憶漩渦間,又湧現出兩個舅舅,從未謀面的敗逃的大舅躲在落網的戰犯四舅後面,猶如月亮躲在太陽後面……再接著,逝者如雪,紛紛揚揚,我追隨著他們,穿過三百多米長橋,抵達越南老街海關,出了大樓還魂不守舍。
下臺階時,接應我的黑道小劉迎面而來……
※※※
這是我二次跨過同一界河。驚魂稍定,就跟小劉去一露天咖啡店,要了越南特色的滴漏冰咖啡。東張西望,二話不說,我就從登山包深處挖出幾沓人民幣,一五一十數起來。小劉接過去繼續數。眼看著交易圓滿完成,我才笑道:「幹這行當賺錢挺容易。」
小劉道:「容易個屁。這四萬元,放你過關的胖子要抽三萬,剩下一萬,兩個人均分。沒辦法,小泥鰍嘛,泥裡水裡亂鑽,也就掙幾個活命小錢。」
「死胖子也太貪了。」
「他是國家的人,要承擔風險囉。」
「放我的風險不算大吧?」
「比放販毒和走私小。」
「這也敢放?」
「有錢能使鬼推磨。給胖子一百萬,殺人犯都敢放。」
「出事兒呢?」
「調離崗位,記過,開除,頂破天坐兩年牢吧。只要一夜暴富,四年也值。」
「腐敗令人膽兒肥。」我讚嘆道。「毛主席說,歷史由膽兒肥的英雄們創造。」
「沒腐敗就沒自由,」小劉擡頭盯了我兩秒鐘,將數過兩遍的鈔票塞進隨身軍挎包,「理解你的心情。」
內心莫名酸楚,我又掏二百塊錢塞過去,小劉忙道:「道有道規,說多少是多少。」於是我起立,模仿舊時代讀書人,拱手兼鞠躬:「活命之恩,無以為報。」
小劉驚道:「老師您別、別、別折煞我。」越南老闆見狀,從另一頂遮陽傘下過來,嘰哩哇啦了一通。小劉翻譯道:「老闆大發感慨,說你行禮的樣子像附近孔夫子廟的泥胎。」
※※※
日漸當頂,雖然昨夜暴風雨,但此時的天地仍然如一口無形的高壓鍋,我感覺渾身散發著熟肉味兒。越南老闆再三招呼進屋,我們謝絕了。接著橫穿大片空地,去一電訊商店買手機卡。小劉用結結巴巴的越南話交涉了半天,店員卻敲竹槓,非要手機和電話卡一起賣。於是我掏三百元人民幣,購得第五隻諾基亞原始版手機,鴨蛋大小,屏幕顯示深奧莫測的越南拼音。據說這種文字才一百多年歷史,是法國傳教士仿照當地土著發音,結合法語創造出來的,在此之前,越南的官方文字是漢語。
我用越南手機給德國科隆的天琪打通了電話,她驚喜異常,並記下號碼。我讓她儘快轉告漁夫出版社責任編輯彼得‧西冷,譯者黃文,以及紐約經紀人彼得‧伯恩斯坦。天琪說會的,我們隨時保持聯繫。接著我打第二個電話給臺灣新竹的文賢,才說了幾句,就突然欠費停機。我只好摸出國內帶出來的四個手機,都是一模一樣的諾基亞,我選擇其中一隻,給好幾個人發簡訊。天熱得快爆炸,地面像潑了一層滾沸的辣椒油,四處冒泡。小劉蹲在階沿下,焦炭般黑糊糊地冒煙。幸而還沒遠離界河,有比較微弱的信號。
我從小劉眼裡讀出了疑問,就解釋道:「公開的已關機,電池也拿掉了,兩天前我用它給國保李警官打了最後的電話,強烈要求喝茶談心,遭嚴詞謝絕。私下的三隻手機,都是單線聯繫。」
「哼哼,你這個笨特務。」
「這年頭哪來的特務?」
「我是 1979 年中越戰爭期間生的,我爸是邊防軍,參加過老山守衛戰,活捉過不少越南特務。搞情報,埋地雷,殺人放火,無惡不作。」
「老黃曆啦。估計你爸也是無惡不作的中國特務。」
「我爸退役時,中越拉鋸戰還沒結束,老人家就從戰友那兒,弄了不少槍支彈藥回家倒賣。文山縣的邊境村子,退役老兵倒賣軍火蔚然成風,全國各地的黑社會都聞風而至,錢賺瘋了。殺人越貨的案子多了,最後政府也聞風而至,一遍遍廣播通令,上千武警包圍,並挨家挨戶搜繳,最終引發大規模巷戰。我們村子交火一晝夜,火焰噴射器都派上用場。成年男人被擊斃一半,坐牢一半,寡婦們不得不當家作主。」
「你爸也被擊斃了?」
「我爸腰椎中槍,坐輪椅了。」
「不錯不錯,有其父必有其子。」
「天壤之別。我爸就是殘廢了,氣勢也能壓倒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