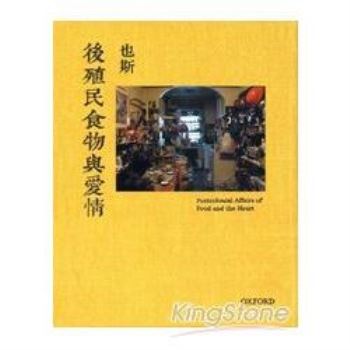後殖民食物與愛情(節錄)
黃昏時分許久不見的阿李拐進我的酒吧,手裏拎著從下面卑利街街世買來一袋叫不出名字的水果。他坐近酒吧櫃圍,剝開狹長的棕色果殼叫我試味,一邊說許久不見了,甚麼時候大伙兒一起熱鬧熱鬧,要不就趁我生日快到了,在那天一起聚首吃頓飯。我試著這怪果子,覺得味道還有趣,核大殼脆,果肉味道有點像曬乾了的龍眼肉,形狀像豆夾那樣是一彎新月,叫人疑心是荷蘭豆跟龍眼雜交以後的私生子。我這麼大一個人,過去一直沒有做生日的習慣。大概因為當年父母偷渡來港,我是私家接生的,連出世紙也沒有。長大以後去領身份證,看不懂英文,就把當天的日期當生日寫上去了。家裏提的是中國陰曆的日子,身份證上是應付官方的虛構日期,還有阿姨後來替我從萬年曆推算出來的陽曆日子,我備而不用,也沒有真正核對過。就這樣三個日子在不同場合輪番使用,隨便應付過去,倒也適合我散漫善變的個性。
前年我的酒吧開張不久,大伙兒晚上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不知怎的說起原來在大學教書的老何跟我同一天生日(即是說跟我三個生日的其中一天相同),結果後來就在酒吧裏搞了個生日派對,各人帶來不同的食物:中東蘸醬、西班牙頭盆、意大利麵條、葡式鴨飯、日本壽司。伊莎貝帶來兩瓶難得的佳釀,是她新婚時在葡國酒區試酒的收獲。老何沒有女朋友,他帶來大學的同事、美國人羅傑。我還請來了有名的前輩食評人薛公,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在不能舉炊的酒吧裏弄出了熱辣辣的夫妻肺片、甚至誇張地用油鍋燒出了糯米釀豬腸。白天髮廊用的洗頭盆正好用來洗菜,風筒用來烤魚乾。這些誇張的食物配合回歸前歇斯底里的氣氛,一方面是民族氣節高昂的電視愛國歌曲晚會,一方面是蘭桂坊洋人頹廢的世紀末狂歡,不是只有明天就是沒有明天,好像這明天就是日曆上一個印成紅色的日子,代表了某些偉大事物的誕辰或是死忌。我想那是日子崇拜。我對甚麼大日子都無所謂。但在那段日子裏我們也不能倖免地大吃大喝,荒腔走板地亂唱一通,又戀愛又失戀,整個人好似處於一種身不由己的失重飄浮狀態。
翌日醒來,我發覺頭痛得厲害,我只好在髮廊的門口掛上「休息一天」的牌子。整個早上只覺得口渴,好似是永遠沒法止住的渴。我到處找水喝,嘗試在騷動過從頭收拾舊山河,從新去過新日子,結果卻只是一片空虛。櫃裏的好酒不見了幾瓶,禮物還未有機會收好,也不知放到哪裏去了。在這個空盪盪的髮廊酒吧裏,我覺得自己也是空空的,不知用甚麼才能實實在在把一切填滿。在這種狂歡過去以後的「產後憂鬱症」裏,我開始對於搞派對這一類事情,有一點意興闌珊了。
現在在這生意冷清的酒吧裏,聽他再提起生日派對,我不禁想起之前那些瘋狂派對,好似只剩下凌亂的影子。生活迫人,我們一群朋友也的確好久未曾聚首了。阿李提議去屈地街「地痞」小店釗記。我剛去過一次,食物夠鑊氣,就嫌師傅下味精手重了,我回來後整晚要不停喝水。還有那兒地方骯髒,而且只有圓凳,連有靠背的椅子也沒一張,我說。伊莎貝去了越南,我不能想像貴婦人或是新潮女子瑪利安會願意在那兒獃上一刻。可是為了你們,她們都願意去呀,阿李說。原來他跟她們說過了。好似大家想回到過去一段比較開心的日子。再多說幾句,我就明白過來,整件事敢情是瑪利安發起的。我跟瑪利安也有一段日子沒見面了。
我記起瑪利安第一次來洗頭。她倒過身仰臥在磁盆上的臉孔看來像個成熟婦人,真人平常的樣子卻像個女孩,是個奇異的混合,我永遠沒法去猜透她的年紀。她告訴我在半島工作。沒想到這麼年輕,已經在香港歷史悠久的酒店位居要職。可是她似乎不知道日軍侵略九龍時,英軍如何以那兒為戰時總部,在天台上架起高射炮俯臨長長的彌敦道。她倒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在聽神奇的天方夜譚,倒轉的嘴巴張開來:「你說話真像我老豆!」我不知道這是恭維還是嘲笑。
其實我當然沒趕上那個時代,我是從教歷史的老何那兒知道這些軼事的。老何有一把有性格的頭髮,近年開始脫髮了,他不得不接受這歷史的必然。我認識老何多年,也看著他走下坡。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每天會接觸個種各樣不同的頭髮:暗啞的、光澤的、油膩的、有層次的、有份量的、硬得像鐵擦的、柔軟得像絲綢的、刺蝟或是狐狸、鞋刷或是麵餅…….但它們跟它們的主人未必有一種直接反映的關係,即是說,富家小姐未必有一把豐澤的頭髮,大學講師未必有一把學術性的頭髮,而建築師也就未必有一把建設性的頭髮。對,我在報上撰寫專欄,由髮式說到時裝和飲食,現在也開始有不少讀者。老何太執著了,老要談嚴肅問題,結果弄得報紙也不要他寫;我倒是開始執筆寫專欄,寫起我自己的故事來。我在唸書的日子也曾舞文弄墨,隔了多年再拿起筆來,愈寫愈順利。倒是老何的文字變得糾纏不清。他好似覺得愈來愈難面對種種說不清楚的人和事,像面對打了結的團團頭髮,不知從何開始。
我和瑪利安是從頭髮開始,也可以說是從飲食開始,如果不是從飲食結束的話。第一次洗頭,我們已經發覺彼此對飲食有一種瘋狂的愛好。不僅是喜歡吃喝,而且是喜歡到處尋幽探秘找好東西來吃,還要好似集郵或搜羅舊版唱片的發燒友,與同好交換情報。當她說起很可惜現在再也吃不到禾花雀了,我說不是呀,最近我還吃過。她喃喃自語說:不對,不對,我爸爸說今年沒有禾花雀運來香港了,可能以後也吃不到了。我向她保證,我可以帶她找到禾花雀,就是這樣,我們約了一起去吃禾花雀。
我們第一次約會完全沒有鮮花和燭光,與其說是男女約會,不如說是兩個老饕的飲食心得交流。在大喜慶那樣的舊式茶居裏,穿著Jil Sander的瑪利安也可以如魚得水。周圍都是上了年紀的商家,或者一家人攜老扶幼,在這鬧哄哄的氣氛裏我們打開帶去的紅酒,瑪利安的口味像老頭子:禾花雀、金銀(月閏)、冬菇、魚翅……我納罕口味是怎樣形成的?她告訴所她父親怎樣講究飲食,每次她回去吃飯他都要弄出一整桌的菜,賣弄他的廚藝。出外上館子,他的嘴夠尖,甚麼都逃不過他的法眼,而他說話又不容情,可以整碟菜教人端回;鼻孔裏哼一聲:「這樣的菜也可以吃?」這晚上每次當瑪利安說這菜炒得鹹了點,我就彷彿感覺老先生的幽靈來回在我們頭頂盤旋。
瑪利安說,即使她後來在法國讀酒店管理的時候,她父親還是不斷給她寄去一箱箱食物。她早年幾次不成功的戀愛,也都似乎與食物有關。她記得早年跟一個對象鬧翻的原因,是他提議去吃麥當奴。站在路中央,她瞪大了眼睛:「呀,唔係嘛?」然後就掉頭而去了。最近一次機驗是在日本餐廳裏,她上一任男友的選擇出了問題。當她覺得整桌人盡在讚美平庸的壽司,忍不住拿起手袋穿上鞋子推門就走。那個可憐的男子至今還沒弄明白分手的真正原因。
我其實也沒法理解瑪利安判別事情好壞的標準是怎樣形成的。不過她似乎對禾花雀的印象還好,也許是我帶的波爾多還可以,僅管我整晚不時感覺老伯的挑剔隨時要從這年輕美麗的女子口中吐出。幸好她興致高昂,尤其知道我晚上兼營酒吧,雀躍不已,一定要回去看看那地方晚上的另一副面貌。當她看見白天做頭髮的髮廊在晚上改頭換面,理髮的大鏡貼牆靠邊站,在昏暗的燈光中映照瓶瓶佳釀暗紅梨渦,她在鏡中回望我,彷彿突然發現了青蛙的我原來是一個王子,她回頭溫熱的面頰猶似吻了我的臉。不知誰違例開了牆角的電視,我也懶得去維持我自己定下的規矩。好像有煙花慶典,幸好沒有聲音,我只是不時從字幕上看見有人在高歌血濃於水的愛情、千萬年的愛情、母親的愛情。我並沒有因為這些無聲而失當的激情分心,我們還是一本正經繼續談論食物,試了一瓶又 瓶我私下的收藏。我隱約感覺客人逐漸散去。但我實在記不起發生了甚麼事。我只知道翌日早上醒來,發覺兩人赤裸睡在床上,本來好似毫無關連的兩個人,現在我的胸膛感到她的呼息,她的手擱在我腰間,但我卻記不起做過甚麼事。我感覺她緩緩醒轉過來,我有點尷尬地嘗試去面對那瘋狂夜晚翌晨的日常生活。
黃昏時分許久不見的阿李拐進我的酒吧,手裏拎著從下面卑利街街世買來一袋叫不出名字的水果。他坐近酒吧櫃圍,剝開狹長的棕色果殼叫我試味,一邊說許久不見了,甚麼時候大伙兒一起熱鬧熱鬧,要不就趁我生日快到了,在那天一起聚首吃頓飯。我試著這怪果子,覺得味道還有趣,核大殼脆,果肉味道有點像曬乾了的龍眼肉,形狀像豆夾那樣是一彎新月,叫人疑心是荷蘭豆跟龍眼雜交以後的私生子。我這麼大一個人,過去一直沒有做生日的習慣。大概因為當年父母偷渡來港,我是私家接生的,連出世紙也沒有。長大以後去領身份證,看不懂英文,就把當天的日期當生日寫上去了。家裏提的是中國陰曆的日子,身份證上是應付官方的虛構日期,還有阿姨後來替我從萬年曆推算出來的陽曆日子,我備而不用,也沒有真正核對過。就這樣三個日子在不同場合輪番使用,隨便應付過去,倒也適合我散漫善變的個性。
前年我的酒吧開張不久,大伙兒晚上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不知怎的說起原來在大學教書的老何跟我同一天生日(即是說跟我三個生日的其中一天相同),結果後來就在酒吧裏搞了個生日派對,各人帶來不同的食物:中東蘸醬、西班牙頭盆、意大利麵條、葡式鴨飯、日本壽司。伊莎貝帶來兩瓶難得的佳釀,是她新婚時在葡國酒區試酒的收獲。老何沒有女朋友,他帶來大學的同事、美國人羅傑。我還請來了有名的前輩食評人薛公,在他的領導下,我們在不能舉炊的酒吧裏弄出了熱辣辣的夫妻肺片、甚至誇張地用油鍋燒出了糯米釀豬腸。白天髮廊用的洗頭盆正好用來洗菜,風筒用來烤魚乾。這些誇張的食物配合回歸前歇斯底里的氣氛,一方面是民族氣節高昂的電視愛國歌曲晚會,一方面是蘭桂坊洋人頹廢的世紀末狂歡,不是只有明天就是沒有明天,好像這明天就是日曆上一個印成紅色的日子,代表了某些偉大事物的誕辰或是死忌。我想那是日子崇拜。我對甚麼大日子都無所謂。但在那段日子裏我們也不能倖免地大吃大喝,荒腔走板地亂唱一通,又戀愛又失戀,整個人好似處於一種身不由己的失重飄浮狀態。
翌日醒來,我發覺頭痛得厲害,我只好在髮廊的門口掛上「休息一天」的牌子。整個早上只覺得口渴,好似是永遠沒法止住的渴。我到處找水喝,嘗試在騷動過從頭收拾舊山河,從新去過新日子,結果卻只是一片空虛。櫃裏的好酒不見了幾瓶,禮物還未有機會收好,也不知放到哪裏去了。在這個空盪盪的髮廊酒吧裏,我覺得自己也是空空的,不知用甚麼才能實實在在把一切填滿。在這種狂歡過去以後的「產後憂鬱症」裏,我開始對於搞派對這一類事情,有一點意興闌珊了。
現在在這生意冷清的酒吧裏,聽他再提起生日派對,我不禁想起之前那些瘋狂派對,好似只剩下凌亂的影子。生活迫人,我們一群朋友也的確好久未曾聚首了。阿李提議去屈地街「地痞」小店釗記。我剛去過一次,食物夠鑊氣,就嫌師傅下味精手重了,我回來後整晚要不停喝水。還有那兒地方骯髒,而且只有圓凳,連有靠背的椅子也沒一張,我說。伊莎貝去了越南,我不能想像貴婦人或是新潮女子瑪利安會願意在那兒獃上一刻。可是為了你們,她們都願意去呀,阿李說。原來他跟她們說過了。好似大家想回到過去一段比較開心的日子。再多說幾句,我就明白過來,整件事敢情是瑪利安發起的。我跟瑪利安也有一段日子沒見面了。
我記起瑪利安第一次來洗頭。她倒過身仰臥在磁盆上的臉孔看來像個成熟婦人,真人平常的樣子卻像個女孩,是個奇異的混合,我永遠沒法去猜透她的年紀。她告訴我在半島工作。沒想到這麼年輕,已經在香港歷史悠久的酒店位居要職。可是她似乎不知道日軍侵略九龍時,英軍如何以那兒為戰時總部,在天台上架起高射炮俯臨長長的彌敦道。她倒轉的眼睛瞪得大大的,好像在聽神奇的天方夜譚,倒轉的嘴巴張開來:「你說話真像我老豆!」我不知道這是恭維還是嘲笑。
其實我當然沒趕上那個時代,我是從教歷史的老何那兒知道這些軼事的。老何有一把有性格的頭髮,近年開始脫髮了,他不得不接受這歷史的必然。我認識老何多年,也看著他走下坡。由於工作的關係,我每天會接觸個種各樣不同的頭髮:暗啞的、光澤的、油膩的、有層次的、有份量的、硬得像鐵擦的、柔軟得像絲綢的、刺蝟或是狐狸、鞋刷或是麵餅…….但它們跟它們的主人未必有一種直接反映的關係,即是說,富家小姐未必有一把豐澤的頭髮,大學講師未必有一把學術性的頭髮,而建築師也就未必有一把建設性的頭髮。對,我在報上撰寫專欄,由髮式說到時裝和飲食,現在也開始有不少讀者。老何太執著了,老要談嚴肅問題,結果弄得報紙也不要他寫;我倒是開始執筆寫專欄,寫起我自己的故事來。我在唸書的日子也曾舞文弄墨,隔了多年再拿起筆來,愈寫愈順利。倒是老何的文字變得糾纏不清。他好似覺得愈來愈難面對種種說不清楚的人和事,像面對打了結的團團頭髮,不知從何開始。
我和瑪利安是從頭髮開始,也可以說是從飲食開始,如果不是從飲食結束的話。第一次洗頭,我們已經發覺彼此對飲食有一種瘋狂的愛好。不僅是喜歡吃喝,而且是喜歡到處尋幽探秘找好東西來吃,還要好似集郵或搜羅舊版唱片的發燒友,與同好交換情報。當她說起很可惜現在再也吃不到禾花雀了,我說不是呀,最近我還吃過。她喃喃自語說:不對,不對,我爸爸說今年沒有禾花雀運來香港了,可能以後也吃不到了。我向她保證,我可以帶她找到禾花雀,就是這樣,我們約了一起去吃禾花雀。
我們第一次約會完全沒有鮮花和燭光,與其說是男女約會,不如說是兩個老饕的飲食心得交流。在大喜慶那樣的舊式茶居裏,穿著Jil Sander的瑪利安也可以如魚得水。周圍都是上了年紀的商家,或者一家人攜老扶幼,在這鬧哄哄的氣氛裏我們打開帶去的紅酒,瑪利安的口味像老頭子:禾花雀、金銀(月閏)、冬菇、魚翅……我納罕口味是怎樣形成的?她告訴所她父親怎樣講究飲食,每次她回去吃飯他都要弄出一整桌的菜,賣弄他的廚藝。出外上館子,他的嘴夠尖,甚麼都逃不過他的法眼,而他說話又不容情,可以整碟菜教人端回;鼻孔裏哼一聲:「這樣的菜也可以吃?」這晚上每次當瑪利安說這菜炒得鹹了點,我就彷彿感覺老先生的幽靈來回在我們頭頂盤旋。
瑪利安說,即使她後來在法國讀酒店管理的時候,她父親還是不斷給她寄去一箱箱食物。她早年幾次不成功的戀愛,也都似乎與食物有關。她記得早年跟一個對象鬧翻的原因,是他提議去吃麥當奴。站在路中央,她瞪大了眼睛:「呀,唔係嘛?」然後就掉頭而去了。最近一次機驗是在日本餐廳裏,她上一任男友的選擇出了問題。當她覺得整桌人盡在讚美平庸的壽司,忍不住拿起手袋穿上鞋子推門就走。那個可憐的男子至今還沒弄明白分手的真正原因。
我其實也沒法理解瑪利安判別事情好壞的標準是怎樣形成的。不過她似乎對禾花雀的印象還好,也許是我帶的波爾多還可以,僅管我整晚不時感覺老伯的挑剔隨時要從這年輕美麗的女子口中吐出。幸好她興致高昂,尤其知道我晚上兼營酒吧,雀躍不已,一定要回去看看那地方晚上的另一副面貌。當她看見白天做頭髮的髮廊在晚上改頭換面,理髮的大鏡貼牆靠邊站,在昏暗的燈光中映照瓶瓶佳釀暗紅梨渦,她在鏡中回望我,彷彿突然發現了青蛙的我原來是一個王子,她回頭溫熱的面頰猶似吻了我的臉。不知誰違例開了牆角的電視,我也懶得去維持我自己定下的規矩。好像有煙花慶典,幸好沒有聲音,我只是不時從字幕上看見有人在高歌血濃於水的愛情、千萬年的愛情、母親的愛情。我並沒有因為這些無聲而失當的激情分心,我們還是一本正經繼續談論食物,試了一瓶又 瓶我私下的收藏。我隱約感覺客人逐漸散去。但我實在記不起發生了甚麼事。我只知道翌日早上醒來,發覺兩人赤裸睡在床上,本來好似毫無關連的兩個人,現在我的胸膛感到她的呼息,她的手擱在我腰間,但我卻記不起做過甚麼事。我感覺她緩緩醒轉過來,我有點尷尬地嘗試去面對那瘋狂夜晚翌晨的日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