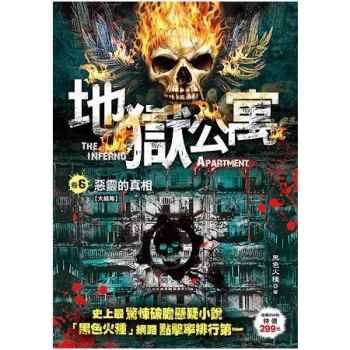三名來自五十年前的新住戶的加入,在公寓內引起了軒然大波。
蒲連生的房間是二九○五室,這個房間五十年來一直空著。他發現房間裏的佈置完全不同了,不止這裏,這個城市的街道、人們的服裝都和以前很不一樣了。
「變了……一切都變了……」以前生死相依的住戶都死了,他的父母自然早就過世了,女兒緋靈也不知所蹤。半個世紀,滄海桑田。
門輕輕地開了。蒲連生回過頭一看,是莫水瞳。
「連生大哥……」莫水瞳走進這個熟悉卻又陌生的房間,「我們只能接受了,不是嗎?影子詛咒沒有開啟,我們活下來了。」
莫水瞳從小就失去了父親,她的童年過得很艱辛,但是,她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和希望。她進入公寓的時候,覺得天都塌了,卻咬牙扛了下來。她勸服那些絕望的住戶,讓大家團結一心。以前的公寓住戶都是生死之交,不像現在,公寓要分裂為三個聯盟,聯盟內部還內鬥連連。
蒲連生的心很痛,很痛。妻子死在魔王級血字中,讓他悲痛欲絕。他是靠著生死相依的住戶陪伴,才能挺了下來。他們都是有血性的漢子,就算面臨恐懼,也會互相鼓勵安慰,那些過命的兄弟對他來說還是嶄新的記憶,可現在卻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
「我們不該釋放那個惡魔的……」蒲連生說道,「我沒能保護好葉寒,後來我想彌補,可是,卻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是因為他能夠預知未來,所以你才會那麼做,不是嗎?他可以預知血字,這個能力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莫水瞳問道,「三大聯盟都有意讓你加入,你有什麼打算?」
「我暫時還沒有打算。那個叫李隱的前樓長,他提供的很多情報都讓我在意。對了,離厭呢?」
「他出去了。他說,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找到他妻子,也許她還活著。」
白離厭平時略顯陰沉,卻是個面冷心熱的人。他對妻子一往情深,進入公寓時,他的妻子剛生下兒子不久。如今他的兒子應該是五十歲了,妻子也是七十多歲了,離厭該如何面對他們?
「我今天去為父母掃墓了。」莫水瞳說道,「母親在我進入公寓的第七年過世了,她和爸爸葬在一起。我失蹤後,她該有多痛苦……」莫水瞳掩面而泣。她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雖然早就有心理準備,還是很悲痛。她看到墓碑顯然已經很多年沒有人來過了,這個城市裏已經沒有認識她的人了。蒲連生還不知道,他的女兒早就在六號林區被殺死了,而她至死都沒有結婚,也不知道父母的下落。而一切,都是蒲靡靈造成的。這個惡魔的出現改變了一切,所有人的記憶都被他篡改了,他以「蒲靡靈」這個身分而活著,死後化為厲鬼殘殺了無數住戶,蒲家祖屋也成為了鬼屋。
住戶們向蒲連生提出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蒲靡靈封印了魔王是怎麼回事?他不是一個心魔嗎?心魔怎麼封印了魔王?」
然而,蒲連生對此事也是完全不知情。他執行血字的時候,地獄契約碎片只發佈了三張,這之後發生的事情,他根本不瞭解。但是,既然封印了魔王,他內心就有些安慰了。當年的住戶,說不定還有少數倖存者。
住戶們對於當年的倖存者也很感興趣,如果可以找到,就能夠知道魔王級血字的內幕。所以,三大聯盟都要求蒲連生提供一份當年住戶的詳細名單。作為交換,會竭盡全力幫助他們三人執行餘下的血字。
蒲連生沒有猶豫,立刻把詳細名單交給了他們。住戶的數量很多,雖然名字都記得,但是無法全部提供地址。僅僅靠名字和外貌,要查一個五十年前的人難如登天,而有地址的十二個人,原地址全都拆遷了……蒲連生還不知道,他的女兒早就在六號林區被殺死了,而她至死都沒有結婚,也不知道父母的下落。而一切,都是蒲靡靈造成的。這個惡魔的出現改變了一切,所有人的記憶都被他篡改了,他以「蒲靡靈」這個身分而活著,死後化為厲鬼殘殺了無數住戶,蒲家祖屋也成為了鬼屋。
住戶們向蒲連生提出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蒲靡靈封印了魔王是怎麼回事?他不是一個心魔嗎?心魔怎麼封印了魔王?」
然而,蒲連生對此事也是完全不知情。他執行血字的時候,地獄契約碎片只發佈了三張,這之後發生的事情,他根本不瞭解。但是,既然封印了魔王,他內心就有些安慰了。當年的住戶,說不定還有少數倖存者。
住戶們對於當年的倖存者也很感興趣,如果可以找到,就能夠知道魔王級血字的內幕。所以,三大聯盟都要求蒲連生提供一份當年住戶的詳細名單。作為交換,會竭盡全力幫助他們三人執行餘下的血字。
蒲連生沒有猶豫,立刻把詳細名單交給了他們。住戶的數量很多,雖然名字都記得,但是無法全部提供地址。僅僅靠名字和外貌,要查一個五十年前的人難如登天,而有地址的十二個人,原地址全都拆遷了……趙鑒皺了皺眉想說點什麼,卻見秦堪一臉山雨欲來的鐵青色,趙鑒終究沒敢開口。大家看著秦堪鐵青的臉色,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不知過了多久,秦堪終於開口,語出如冰。
「我記得丁順出京時帶了三百多人吧?」
常鳳渾身一顫,垂首道:「是,一行總共三百二十人。」
秦堪瞪著他:「三百多人都護不住一個丁順,還折損數十。天津難道是龍潭虎穴麼?」
常鳳一個頭狠狠磕在地上,悲憤道:「侯爺明鑒!丁鎮撫是中了白蓮教的埋伏……」
秦堪冷笑:「東廠兩名大檔頭中了埋伏,天津衛千戶牟斌也中了埋伏,丁順和你們也中了埋伏……是白蓮教的妖人會隱身的法術,還是咱們廠衛的人馬全是飯桶?」
常鳳惶然道:「侯爺,天津的白蓮教已鬧得非常猖獗,城中多有百姓民眾入教,甚至連天津三衛的武將軍士也有不少人暗裏入了教,屬下大膽說一句,侯爺剛才並沒說錯,天津衛對咱們來說,就是個龍潭虎穴。」
秦堪森然道:「白蓮教在天津鬧得如此厲害?丁順是怎麼中的埋伏?」
「丁鎮撫奉侯爺之命,十日前率屬下等進了天津衛,與天津左衛都指揮使錢貴相談數個時辰。鑒於東廠和牟斌相繼被刺殺,顯然有人對朝廷派來的人的舉動了若指掌,其中必有內奸。丁鎮撫決定從天津三衛的下層開始查起,一路順藤摸瓜,尋根溯源。
「進駐天津四天,丁鎮撫一直很小心,他住在錦衣衛天津總署衙門裏,無論進出身邊皆有數百人護衛。而且案情查得很順利,丁鎮撫甚至揪出了天津右衛裏的一名指揮僉事,天津衛裏的兩名副千戶,他們已是白蓮教天津香堂的重要頭目……」
秦堪冷著臉道:「以丁順的性子,揪住如此重要的人物恐怕有點得意忘形了吧?」
常鳳羞慚道:「侯爺說得正是,丁鎮撫他……剛得知消息便興奮得不能自已,當時他身邊的人都被派出去查案,他只領著三十餘人便匆匆出了錦衣衛天津總署衙門,準備連夜提審這三名重要人犯,結果離開衙門不到一炷香時辰,便當街遭到白蓮教的伏擊,白蓮逆賊多達二百餘人,其中多有精於技擊之輩,屬下等拼死護衛,折了十多個弟兄,才保住了丁鎮撫……」
秦堪怒而長嘆道:「你們這是中了白蓮教的計啊,查到的這三個人根本就是誘丁順輕裝簡騎出門的誘餌,我若猜得沒錯的話,這三個人恐怕也已被白蓮教滅口了吧?」常鳳愈發慚愧無比:「侯爺明見萬里,這三名重要人犯當晚死於衛所大獄中,事後天津三衛指揮使大為震驚,遂封城五日嚴查,卻查不出任何結果,丁鎮撫受傷昏迷之前交代屬下,要我們一定將他送回京師……」
常鳳正說著,躺在軟褥上的丁順忽然呻吟出聲,斷斷續續喊著:「水……水……」眾人急忙端了一杯溫水過來,先潤濕了他乾枯的嘴唇,再用銀勺餵了一點點水。
喝了水後的丁順不知怎地恢復了神志,睜開眼卻見秦堪靜靜站在他身前,丁順頓時眼眶一紅,哽咽道:「侯爺……老丁我,我對不住你,差事……辦砸了,請侯爺責罪。」
秦堪搖搖頭,臉色和聲音放得無比柔和:「你已做得很好了,我不怪你。撿回一條命已是萬幸,好好回府養傷,將來隨我建功立業的機會多著呢。」
丁順抽噎著點頭。
秦堪頓了頓,眼中殺機盡現,森然道:「一個邪教害得朝廷廠衛損兵折將,我倒要親自見識見識它到底哪裡厲害!」
丁順不知哪來的力氣,忽然伸手緊緊抓住了秦堪的袍袖,神情緊張道:「侯爺萬萬不可親自赴險!侯爺,聽屬下一句,天津衛的白蓮教……已成氣候了!」
秦堪大怒:「放屁!唯時勢造英雄,唯時勢成氣候,非時又非勢,何來氣候?終究不過一群見不得光的蟊賊而已!」
秦堪命人將丁順小心送回府裏養傷,滿懷怒火準備進宮。
時已歲尾臘月,正值寒冬。京師城內一片歡騰景象,處處洋溢著過年的喜悅氣氛。街面越來越繁華,離過年只有幾天了,家家戶戶忙著請神送灶辦年貨。
官轎外一片歡騰,秦堪靜靜地聽著繁華塵世的喧囂,暴怒的心情卻莫名平復下來,漸漸地,他的臉上甚至浮出一絲淡笑。
有什麼好氣的?熙熙攘攘,利來利往,一邊是統治階級保江山,一邊是反賊奪江山,輸贏各憑本事,各憑手段而已,其實爭來爭去,還不就是為了轎子外面這一片熙熙攘攘?!
聽著轎外不時傳來的炮竹聲,秦堪若有所失地嘆了口氣。家中嬌妻興致勃勃地置辦年貨,打掃祠堂,剪窗花,可是怎想到她們的相公卻必須在年前離京?!屈指算算日子,四個月後金柳便要臨盆,那時還不知自己能不能趕回來讓孩子第一眼見到自己……
時而安寧恬靜,時而煩躁不安,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秦堪走進了皇宮。朱厚照穿著龍袍,盤著腿坐在乾清宮東暖閣的炕上,雖然坐沒坐相,大失皇帝威儀,但神情倒是難得的正經,他正聚精會神地批閱著內閣票擬的奏疏。
司禮監掌印劉瑾陪著笑恭立他身旁,偶爾為朱厚照輕聲講解每份奏疏上所述事情的前因後果,以及如何處置的建議等等。
上次太廟請罪的風波過後,文官們被朱厚照和秦堪合起夥來狠狠整治了一回,雖然口頭上仍舊硬氣得一塌糊塗,然而大部分文官終究對皇權生了畏懼,以往朱厚照說一件事便反對一件,如今卻沒遇到什麼阻礙,只要對朝政不是處理得太過糊塗荒唐,連御史言官都不出聲了。
如此喜聞樂見的良好氛圍,朱厚照自然不介意親自處理一下國事,儘管他很清楚,文官們的退縮妥協只是暫時,時日一久恐怕又會故態復萌稱霸朝堂了,不過朱厚照還是很滿足。
當然,朱厚照的勵精圖治也是暫時性的,在繁瑣枯燥的朝政事務裏,他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連劉瑾都不認為他能堅持多久。
朱厚照專心批閱奏疏,劉瑾在旁邊神態恭敬地指點建議,還有一個張永也不甘寂寞,彷彿存心跟劉瑾較勁似的,端著一個裝滿了各式點心零嘴的玉盤,抽冷子便殷勤地捧上前,讓朱厚照漫不經心地隨手取一樣塞進嘴裏。
見秦堪進來,朱厚照將手中的名貴紫貂湖筆朝筆架上一擱,高興地道:「秦堪,你快過來瞧瞧,朕這幾日處理朝政很順手呢,那幫碎嘴的文官們竟然都老實了,全托你出的壞主意才讓朕最近如此順心,朕終於可以過個開心的新年了。」
劉瑾見秦堪進殿,諂媚的神色頓時變得有些僵硬,目光飛快閃過一絲嫉恨,顯然自上次合夥整過文官之後,秦堪和劉瑾的蜜月期已經快過完了……
秦堪上前兩步,苦笑道:「陛下可否低調點?咱們不是說好了把此事爛在肚裏的嗎?若被大臣們知曉了內幕,陛下倒是沒事,臣卻必死無疑啊。」
朱厚照樂得哈哈大笑:「你和劉瑾都被滿朝文武罵為奸佞,但你的壞和劉瑾不一樣,劉瑾脾氣剛直一些;而你,卻實實在在壞到了骨子裏,一不留神便被你坑了……朕一想起你上次出的壞主意便忍不住想笑,這張嘴怎麼也管不住秘密,你說怎麼辦?」秦堪笑道:「其實也好辦,臣聽說極西之地的歐洲有個習俗,那裏無論王公貴族還是百姓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通常會跑到山上找一棵樹,在樹下挖一個洞,然後朝著洞口將秘密全部說出來,再用泥土把洞封死埋實,那個秘密便會埋在洞裏,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朱厚照眼睛大亮,道:「聽起來倒是有趣兒,趕明兒朕就把咱們的秘密埋進洞裏……」
彷彿在嚴肅商議國事一般,秦堪忽然指了指劉瑾,語氣無比正經地道:「陛下,劉公公也知道這個秘密,要不要順便把他也……」
猝不及防的劉瑾一呆,接著嚇得魂飛魄散,瘋子般嘶聲道:「秦堪,你一次又一次嚇唬咱家,覺得有意思嗎?」
朱厚照哭笑不得:「秦堪,你別老是嚇唬劉瑾,人家好歹一把年紀了,經不得你三番五次捉弄。」
劉瑾眼眶泛紅,連連點頭:「老奴膽兒小,真的經不得嚇的……」
秦堪無比失望地仰天長嘆:劉瑾氣數未盡吶!
朱厚照隨意指了指張永手裏捧著的玉盤,讓秦堪自己取用零嘴點心,揚了揚眉道:「進宮找朕有事?」
秦堪拱手道:「是。」
「說吧,大過年的,最好說點開心事。不開心的事緩緩,留到過完上元節再說,朝臣們都休沐半個月呢,你也讓朕緩口氣。」
秦堪苦笑道:「陛下,實在對不住,臣要說的事真不是什麼好消息……」
朱厚照愣了一下,然後愁意深深地嘆了口氣,連嘴裏的點心也變得沒滋沒味起來。
劉瑾彷彿刻意要報剛才的一箭之仇似的,在一旁不無恨意地冷笑道:「陛下,秦侯爺可真是運道背,老奴就沒聽他跟陛下說過什麼好事,大過年的還跑來惹陛下不痛快。」
秦堪不軟不硬地回道:「劉公公,大過年的,你又何必惹我不痛快?我向陛下稟報的皆是關乎祖宗社稷的國事,陛下既為江山共主,聽取國事難道還分痛快和不痛快兩種?」
劉瑾一滯,接著怨毒地瞟了他一眼,沒再吱聲兒。
朱厚照嘆道:「得了得了,你們已經惹朕不痛快了。秦堪,到底何事,你儘管奏來。」
秦堪靜靜道:「陛下,白蓮邪教在天津衛鬧事,已有愈演愈烈之勢,時至今日,已有東廠兩位大檔頭以及錦衣衛一位千戶、一位鎮撫在天津被刺,可謂猖獗張狂之至,臣左思右想,不得不稟于陛下玉階前,伏請陛下聖裁決斷。」
一聽到「白蓮教」三個字,朱厚照漫不經心的神色頓時變得很難看。怠政嬉玩不代表真的對國事毫不關心,白蓮教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朱厚照非常清楚,畢竟是祖宗傳下來的江山,弘治帝在世之時想必告誡過他,白蓮教絕對是歷代大明皇帝嚴防痛剿的組織之一;論大明開國百餘年來各地此消彼長大小規模不一的造反事例,白蓮教早已是帝王們心頭的一根毒刺,欲拔而不能。
「白蓮教已在天津衛成氣候了?」朱厚照神情陰沉道。
秦堪道:「陛下君權天授,堂堂貴胄正統,不論成不成氣候,在陛下面前都是宵小,陛下何懼耶。」
朱厚照臉色略為緩和道:「賊子們狗膽包天,竟敢公然刺我朝廷廠衛,朕絕不能容!秦堪,你意若何?」
秦堪拱手肅然道:「只求陛下一道聖旨,臣願為陛下赴天津衛,親領廠衛剿除白蓮邪教。」
朱厚照和劉瑾聞言同時一愣。
「去天津衛?你又要親自涉險地麼?不行!朕不准!」朱厚照決然搖頭:「上回你去一趟遼東差點喪命,朕內疚得給你陪葬的心思都有了,這回說什麼也不讓你去!秦堪,你讓朕省省心吧。」
秦堪道:「陛下,天津不是遼東,臣在遼東要面對敵人,是手握邊鎮兵權的大將以及最大的外敵韃靼騎兵,內憂外患皆俱,那才叫真的危險。但天津衛不一樣,臣去天津要查的是白蓮教逆賊,這是一群上不了臺面的蟊賊,臣要做的只是抽絲剝繭把他們從洞裏挖出來而已,談不上危險……」
朱厚照哼道:「東廠折了兩個大檔頭,錦衣衛折了一個鎮撫,一個千戶,這還不叫危險?秦堪,朕身邊的太監和大臣們常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來勸諫朕不要做那些危險的事情,朕也用這句話來勸你,你如今貴為侯爵,也是朕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何必親身涉險?叫下面麵的人去做便是了,朕不信我大明除了你就沒別的能人了……」
秦堪無奈苦笑,目光朝旁邊的劉瑾一瞥,帶著幾分邪味。
劉瑾渾身一顫,讀懂了秦堪的眼神,此刻他若不為秦堪遊說一番,想必秦堪下一句話絕對會把他推薦到天津去!
劉瑾忍住滿腔怒火,擠出個笑臉道:「陛下,廠衛之前派過去的人馬折了好幾個,那都是因為他們太過大意,若秦侯爺凡事小心些,必然無礙的。白蓮邪教自南宋以來,雖頻頻聚眾造反,然則都成不了氣候;我大明立國之後,雖然也常有白蓮造反,但隨便一支朝廷兵馬便將他們輕鬆滅掉。此何以故?只因白蓮教所納信徒皆為粗鄙村夫愚民也,說白了,他們其實是一群烏合之眾,王師所指,一擊即潰,秦侯爺是有大本事的人,區區白蓮教自然手到擒來,陛下不用擔心。」
朱厚照聞言想了想,覺得也有道理,不由遲疑道:「是……這樣的嗎?」
秦堪微笑拱手道:「劉公公所言甚是,陛下,臣也是為陛下的江山萬年久安計啊,還請陛下成全。」
朱厚照猶豫半晌,終於點點頭:「好,朕這次便允了你,稍晚朕便將欽差聖旨派人送到你府上,此行一應人馬器物皆由你選。秦堪,你可萬萬要小心,不然朕真沒臉見你秦府夫人們了……」
「多謝陛下成全。」
目的達到,秦堪慢慢走出殿門,沒走幾步,卻發現身後張永也跟了上來。
秦堪停下腳步,朝張永拱手:「張公公有事嗎?」
張永嘆道:「侯爺,此去天津,你可要好好保重,萬不可再出事了……咱家剛才一直盯著劉瑾呢,你在陛下面前一提去天津,劉瑾當即目露殺機,侯爺天津之行,恐怕劉瑾會暗中使壞,萬萬小心啊!」
秦堪笑道:「多謝張公公提醒,我記住了。」
二人站在乾清宮外閒聊了幾句,張永不知有何心事,神情猶豫不安,拉著秦堪說些毫無營養漫無邊際的話,卻遲遲不放他離開。
秦堪笑道:「張公公一定有別的事吧?我與張公公皆是東宮舊人,而且咱們的關係……呵呵,公公有話不妨直言,能幫得上忙的我一定幫。」
張永感激莫名道:「秦侯爺果真是好人吶,咱家能認識侯爺,這輩子算沒白活。」
秦堪摸了摸鼻子,別人怎麼罵他無所謂,一旦聽有人稱讚他是好人,他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對方,第一反應便是別人拐著彎兒罵他。
張永猶豫片刻,這才期期開口道:「不瞞侯爺說,咱家如今在宮裏越混越窩囊了……」
「哦?此話何解?」張永神情浮上憤恨之色:「還不是因為劉瑾那個老雜碎!陛下欲建豹房,內庫全部提現全安排到豹房修建上去了,劉瑾那老雜碎只留了三十萬兩給十一監,咱家所領的御馬監唯獨排除在外;咱家找他理論,老雜碎卻說御馬監掌禁中兵事,欲討餉銀可問戶部和兵部,內庫支出太多,不堪敷出,或者等明年開春以後各地押解京師的下一批礦稅銀子。侯爺,咱家掌的是禁中兵權,掌兵是要銀子的呀,咱家開不出餉銀,那些軍士誰會服咱家管?龍驤四營的將士們誰會給咱家好臉色?劉瑾這是生生把咱家往絕路上逼呀……」
秦堪同情地點點頭:「張公公的難處我已知曉,不知公公的意思是……」
張永愁眉苦臉道:「眼看要過年了,御馬監若再不發一批餉銀,怕是禁中官兵要嘩變,那時咱家的腦袋可危險了,還請侯爺救我!侯爺麾下錦衣衛進項甚多,若能臨時調撥一批銀子過來,咱家此生必感侯爺大恩大德。」
秦堪沉吟不語,良久才緩緩道:「公公言重了,我與公公相交莫逆,怎會見死不救!這樣吧,我私人出銀五十萬兩,走錦衣衛的帳上調撥給你,將來御馬監緩過勁了再還我,此事不宜宣揚,說出去是犯忌諱的事。」
五十萬兩銀子不是小數,若擱了以前,秦堪肯定拿不出來,不過上次秦堪設計幫劉瑾坑了數百萬兩銀子,其中有一百萬兩落了自己的口袋,拿五十萬兩出來還是不難的。
張永大喜過望,眼眶頓時泛了淚,一撩下擺便打算給秦堪跪拜下去,秦堪急忙扶住了他。
「侯爺……你是咱家的再生父母呀!」
「別……我生不出你這樣的兒子,難度太高了。」秦堪急忙謙讓。
「以後侯爺但有所命,我願為侯爺赴湯蹈火!」
秦堪嘆了口氣,道:「張公公,我的能力有限。一次兩次我能幫你,可無法每次都幫到你呀!公公與劉瑾交惡,已成了解不開的死結,說句不中聽的話,將來不是你死便是他死,張公公,早做打算才是正理啊。」
張永悚然一驚,「侯爺的意思是……」
秦堪笑了笑:「我沒什麼意思,張公公,我還有事,先告辭了。五十萬兩銀子晚間我會命人押解御馬監署衙。」
秦堪轉身離去,背對著張永時,他的嘴角露出一抹不懷善意的笑容。
張永一直處於呆滯中,心不在焉地朝秦堪拱拱手,直到秦堪的身影消失不見,仍呆呆地站著,眼中懼意和殺意相互交替,變幻不休。
蒲連生的房間是二九○五室,這個房間五十年來一直空著。他發現房間裏的佈置完全不同了,不止這裏,這個城市的街道、人們的服裝都和以前很不一樣了。
「變了……一切都變了……」以前生死相依的住戶都死了,他的父母自然早就過世了,女兒緋靈也不知所蹤。半個世紀,滄海桑田。
門輕輕地開了。蒲連生回過頭一看,是莫水瞳。
「連生大哥……」莫水瞳走進這個熟悉卻又陌生的房間,「我們只能接受了,不是嗎?影子詛咒沒有開啟,我們活下來了。」
莫水瞳從小就失去了父親,她的童年過得很艱辛,但是,她對生活充滿了信心和希望。她進入公寓的時候,覺得天都塌了,卻咬牙扛了下來。她勸服那些絕望的住戶,讓大家團結一心。以前的公寓住戶都是生死之交,不像現在,公寓要分裂為三個聯盟,聯盟內部還內鬥連連。
蒲連生的心很痛,很痛。妻子死在魔王級血字中,讓他悲痛欲絕。他是靠著生死相依的住戶陪伴,才能挺了下來。他們都是有血性的漢子,就算面臨恐懼,也會互相鼓勵安慰,那些過命的兄弟對他來說還是嶄新的記憶,可現在卻已經是遙遠的過去了。
「我們不該釋放那個惡魔的……」蒲連生說道,「我沒能保護好葉寒,後來我想彌補,可是,卻變成了現在這個樣子。」
「是因為他能夠預知未來,所以你才會那麼做,不是嗎?他可以預知血字,這個能力對我們而言是很重要的。」莫水瞳問道,「三大聯盟都有意讓你加入,你有什麼打算?」
「我暫時還沒有打算。那個叫李隱的前樓長,他提供的很多情報都讓我在意。對了,離厭呢?」
「他出去了。他說,無論如何都要想辦法找到他妻子,也許她還活著。」
白離厭平時略顯陰沉,卻是個面冷心熱的人。他對妻子一往情深,進入公寓時,他的妻子剛生下兒子不久。如今他的兒子應該是五十歲了,妻子也是七十多歲了,離厭該如何面對他們?
「我今天去為父母掃墓了。」莫水瞳說道,「母親在我進入公寓的第七年過世了,她和爸爸葬在一起。我失蹤後,她該有多痛苦……」莫水瞳掩面而泣。她是一個很孝順的孩子,雖然早就有心理準備,還是很悲痛。她看到墓碑顯然已經很多年沒有人來過了,這個城市裏已經沒有認識她的人了。蒲連生還不知道,他的女兒早就在六號林區被殺死了,而她至死都沒有結婚,也不知道父母的下落。而一切,都是蒲靡靈造成的。這個惡魔的出現改變了一切,所有人的記憶都被他篡改了,他以「蒲靡靈」這個身分而活著,死後化為厲鬼殘殺了無數住戶,蒲家祖屋也成為了鬼屋。
住戶們向蒲連生提出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蒲靡靈封印了魔王是怎麼回事?他不是一個心魔嗎?心魔怎麼封印了魔王?」
然而,蒲連生對此事也是完全不知情。他執行血字的時候,地獄契約碎片只發佈了三張,這之後發生的事情,他根本不瞭解。但是,既然封印了魔王,他內心就有些安慰了。當年的住戶,說不定還有少數倖存者。
住戶們對於當年的倖存者也很感興趣,如果可以找到,就能夠知道魔王級血字的內幕。所以,三大聯盟都要求蒲連生提供一份當年住戶的詳細名單。作為交換,會竭盡全力幫助他們三人執行餘下的血字。
蒲連生沒有猶豫,立刻把詳細名單交給了他們。住戶的數量很多,雖然名字都記得,但是無法全部提供地址。僅僅靠名字和外貌,要查一個五十年前的人難如登天,而有地址的十二個人,原地址全都拆遷了……蒲連生還不知道,他的女兒早就在六號林區被殺死了,而她至死都沒有結婚,也不知道父母的下落。而一切,都是蒲靡靈造成的。這個惡魔的出現改變了一切,所有人的記憶都被他篡改了,他以「蒲靡靈」這個身分而活著,死後化為厲鬼殘殺了無數住戶,蒲家祖屋也成為了鬼屋。
住戶們向蒲連生提出了一個最關鍵的問題:「蒲靡靈封印了魔王是怎麼回事?他不是一個心魔嗎?心魔怎麼封印了魔王?」
然而,蒲連生對此事也是完全不知情。他執行血字的時候,地獄契約碎片只發佈了三張,這之後發生的事情,他根本不瞭解。但是,既然封印了魔王,他內心就有些安慰了。當年的住戶,說不定還有少數倖存者。
住戶們對於當年的倖存者也很感興趣,如果可以找到,就能夠知道魔王級血字的內幕。所以,三大聯盟都要求蒲連生提供一份當年住戶的詳細名單。作為交換,會竭盡全力幫助他們三人執行餘下的血字。
蒲連生沒有猶豫,立刻把詳細名單交給了他們。住戶的數量很多,雖然名字都記得,但是無法全部提供地址。僅僅靠名字和外貌,要查一個五十年前的人難如登天,而有地址的十二個人,原地址全都拆遷了……趙鑒皺了皺眉想說點什麼,卻見秦堪一臉山雨欲來的鐵青色,趙鑒終究沒敢開口。大家看著秦堪鐵青的臉色,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不知過了多久,秦堪終於開口,語出如冰。
「我記得丁順出京時帶了三百多人吧?」
常鳳渾身一顫,垂首道:「是,一行總共三百二十人。」
秦堪瞪著他:「三百多人都護不住一個丁順,還折損數十。天津難道是龍潭虎穴麼?」
常鳳一個頭狠狠磕在地上,悲憤道:「侯爺明鑒!丁鎮撫是中了白蓮教的埋伏……」
秦堪冷笑:「東廠兩名大檔頭中了埋伏,天津衛千戶牟斌也中了埋伏,丁順和你們也中了埋伏……是白蓮教的妖人會隱身的法術,還是咱們廠衛的人馬全是飯桶?」
常鳳惶然道:「侯爺,天津的白蓮教已鬧得非常猖獗,城中多有百姓民眾入教,甚至連天津三衛的武將軍士也有不少人暗裏入了教,屬下大膽說一句,侯爺剛才並沒說錯,天津衛對咱們來說,就是個龍潭虎穴。」
秦堪森然道:「白蓮教在天津鬧得如此厲害?丁順是怎麼中的埋伏?」
「丁鎮撫奉侯爺之命,十日前率屬下等進了天津衛,與天津左衛都指揮使錢貴相談數個時辰。鑒於東廠和牟斌相繼被刺殺,顯然有人對朝廷派來的人的舉動了若指掌,其中必有內奸。丁鎮撫決定從天津三衛的下層開始查起,一路順藤摸瓜,尋根溯源。
「進駐天津四天,丁鎮撫一直很小心,他住在錦衣衛天津總署衙門裏,無論進出身邊皆有數百人護衛。而且案情查得很順利,丁鎮撫甚至揪出了天津右衛裏的一名指揮僉事,天津衛裏的兩名副千戶,他們已是白蓮教天津香堂的重要頭目……」
秦堪冷著臉道:「以丁順的性子,揪住如此重要的人物恐怕有點得意忘形了吧?」
常鳳羞慚道:「侯爺說得正是,丁鎮撫他……剛得知消息便興奮得不能自已,當時他身邊的人都被派出去查案,他只領著三十餘人便匆匆出了錦衣衛天津總署衙門,準備連夜提審這三名重要人犯,結果離開衙門不到一炷香時辰,便當街遭到白蓮教的伏擊,白蓮逆賊多達二百餘人,其中多有精於技擊之輩,屬下等拼死護衛,折了十多個弟兄,才保住了丁鎮撫……」
秦堪怒而長嘆道:「你們這是中了白蓮教的計啊,查到的這三個人根本就是誘丁順輕裝簡騎出門的誘餌,我若猜得沒錯的話,這三個人恐怕也已被白蓮教滅口了吧?」常鳳愈發慚愧無比:「侯爺明見萬里,這三名重要人犯當晚死於衛所大獄中,事後天津三衛指揮使大為震驚,遂封城五日嚴查,卻查不出任何結果,丁鎮撫受傷昏迷之前交代屬下,要我們一定將他送回京師……」
常鳳正說著,躺在軟褥上的丁順忽然呻吟出聲,斷斷續續喊著:「水……水……」眾人急忙端了一杯溫水過來,先潤濕了他乾枯的嘴唇,再用銀勺餵了一點點水。
喝了水後的丁順不知怎地恢復了神志,睜開眼卻見秦堪靜靜站在他身前,丁順頓時眼眶一紅,哽咽道:「侯爺……老丁我,我對不住你,差事……辦砸了,請侯爺責罪。」
秦堪搖搖頭,臉色和聲音放得無比柔和:「你已做得很好了,我不怪你。撿回一條命已是萬幸,好好回府養傷,將來隨我建功立業的機會多著呢。」
丁順抽噎著點頭。
秦堪頓了頓,眼中殺機盡現,森然道:「一個邪教害得朝廷廠衛損兵折將,我倒要親自見識見識它到底哪裡厲害!」
丁順不知哪來的力氣,忽然伸手緊緊抓住了秦堪的袍袖,神情緊張道:「侯爺萬萬不可親自赴險!侯爺,聽屬下一句,天津衛的白蓮教……已成氣候了!」
秦堪大怒:「放屁!唯時勢造英雄,唯時勢成氣候,非時又非勢,何來氣候?終究不過一群見不得光的蟊賊而已!」
秦堪命人將丁順小心送回府裏養傷,滿懷怒火準備進宮。
時已歲尾臘月,正值寒冬。京師城內一片歡騰景象,處處洋溢著過年的喜悅氣氛。街面越來越繁華,離過年只有幾天了,家家戶戶忙著請神送灶辦年貨。
官轎外一片歡騰,秦堪靜靜地聽著繁華塵世的喧囂,暴怒的心情卻莫名平復下來,漸漸地,他的臉上甚至浮出一絲淡笑。
有什麼好氣的?熙熙攘攘,利來利往,一邊是統治階級保江山,一邊是反賊奪江山,輸贏各憑本事,各憑手段而已,其實爭來爭去,還不就是為了轎子外面這一片熙熙攘攘?!
聽著轎外不時傳來的炮竹聲,秦堪若有所失地嘆了口氣。家中嬌妻興致勃勃地置辦年貨,打掃祠堂,剪窗花,可是怎想到她們的相公卻必須在年前離京?!屈指算算日子,四個月後金柳便要臨盆,那時還不知自己能不能趕回來讓孩子第一眼見到自己……
時而安寧恬靜,時而煩躁不安,懷著這種矛盾的心情,秦堪走進了皇宮。朱厚照穿著龍袍,盤著腿坐在乾清宮東暖閣的炕上,雖然坐沒坐相,大失皇帝威儀,但神情倒是難得的正經,他正聚精會神地批閱著內閣票擬的奏疏。
司禮監掌印劉瑾陪著笑恭立他身旁,偶爾為朱厚照輕聲講解每份奏疏上所述事情的前因後果,以及如何處置的建議等等。
上次太廟請罪的風波過後,文官們被朱厚照和秦堪合起夥來狠狠整治了一回,雖然口頭上仍舊硬氣得一塌糊塗,然而大部分文官終究對皇權生了畏懼,以往朱厚照說一件事便反對一件,如今卻沒遇到什麼阻礙,只要對朝政不是處理得太過糊塗荒唐,連御史言官都不出聲了。
如此喜聞樂見的良好氛圍,朱厚照自然不介意親自處理一下國事,儘管他很清楚,文官們的退縮妥協只是暫時,時日一久恐怕又會故態復萌稱霸朝堂了,不過朱厚照還是很滿足。
當然,朱厚照的勵精圖治也是暫時性的,在繁瑣枯燥的朝政事務裏,他只是個跑龍套的角色,連劉瑾都不認為他能堅持多久。
朱厚照專心批閱奏疏,劉瑾在旁邊神態恭敬地指點建議,還有一個張永也不甘寂寞,彷彿存心跟劉瑾較勁似的,端著一個裝滿了各式點心零嘴的玉盤,抽冷子便殷勤地捧上前,讓朱厚照漫不經心地隨手取一樣塞進嘴裏。
見秦堪進來,朱厚照將手中的名貴紫貂湖筆朝筆架上一擱,高興地道:「秦堪,你快過來瞧瞧,朕這幾日處理朝政很順手呢,那幫碎嘴的文官們竟然都老實了,全托你出的壞主意才讓朕最近如此順心,朕終於可以過個開心的新年了。」
劉瑾見秦堪進殿,諂媚的神色頓時變得有些僵硬,目光飛快閃過一絲嫉恨,顯然自上次合夥整過文官之後,秦堪和劉瑾的蜜月期已經快過完了……
秦堪上前兩步,苦笑道:「陛下可否低調點?咱們不是說好了把此事爛在肚裏的嗎?若被大臣們知曉了內幕,陛下倒是沒事,臣卻必死無疑啊。」
朱厚照樂得哈哈大笑:「你和劉瑾都被滿朝文武罵為奸佞,但你的壞和劉瑾不一樣,劉瑾脾氣剛直一些;而你,卻實實在在壞到了骨子裏,一不留神便被你坑了……朕一想起你上次出的壞主意便忍不住想笑,這張嘴怎麼也管不住秘密,你說怎麼辦?」秦堪笑道:「其實也好辦,臣聽說極西之地的歐洲有個習俗,那裏無論王公貴族還是百姓若有了不可告人的秘密,通常會跑到山上找一棵樹,在樹下挖一個洞,然後朝著洞口將秘密全部說出來,再用泥土把洞封死埋實,那個秘密便會埋在洞裏,永遠不會有人知道……」
朱厚照眼睛大亮,道:「聽起來倒是有趣兒,趕明兒朕就把咱們的秘密埋進洞裏……」
彷彿在嚴肅商議國事一般,秦堪忽然指了指劉瑾,語氣無比正經地道:「陛下,劉公公也知道這個秘密,要不要順便把他也……」
猝不及防的劉瑾一呆,接著嚇得魂飛魄散,瘋子般嘶聲道:「秦堪,你一次又一次嚇唬咱家,覺得有意思嗎?」
朱厚照哭笑不得:「秦堪,你別老是嚇唬劉瑾,人家好歹一把年紀了,經不得你三番五次捉弄。」
劉瑾眼眶泛紅,連連點頭:「老奴膽兒小,真的經不得嚇的……」
秦堪無比失望地仰天長嘆:劉瑾氣數未盡吶!
朱厚照隨意指了指張永手裏捧著的玉盤,讓秦堪自己取用零嘴點心,揚了揚眉道:「進宮找朕有事?」
秦堪拱手道:「是。」
「說吧,大過年的,最好說點開心事。不開心的事緩緩,留到過完上元節再說,朝臣們都休沐半個月呢,你也讓朕緩口氣。」
秦堪苦笑道:「陛下,實在對不住,臣要說的事真不是什麼好消息……」
朱厚照愣了一下,然後愁意深深地嘆了口氣,連嘴裏的點心也變得沒滋沒味起來。
劉瑾彷彿刻意要報剛才的一箭之仇似的,在一旁不無恨意地冷笑道:「陛下,秦侯爺可真是運道背,老奴就沒聽他跟陛下說過什麼好事,大過年的還跑來惹陛下不痛快。」
秦堪不軟不硬地回道:「劉公公,大過年的,你又何必惹我不痛快?我向陛下稟報的皆是關乎祖宗社稷的國事,陛下既為江山共主,聽取國事難道還分痛快和不痛快兩種?」
劉瑾一滯,接著怨毒地瞟了他一眼,沒再吱聲兒。
朱厚照嘆道:「得了得了,你們已經惹朕不痛快了。秦堪,到底何事,你儘管奏來。」
秦堪靜靜道:「陛下,白蓮邪教在天津衛鬧事,已有愈演愈烈之勢,時至今日,已有東廠兩位大檔頭以及錦衣衛一位千戶、一位鎮撫在天津被刺,可謂猖獗張狂之至,臣左思右想,不得不稟于陛下玉階前,伏請陛下聖裁決斷。」
一聽到「白蓮教」三個字,朱厚照漫不經心的神色頓時變得很難看。怠政嬉玩不代表真的對國事毫不關心,白蓮教是個什麼性質的組織,朱厚照非常清楚,畢竟是祖宗傳下來的江山,弘治帝在世之時想必告誡過他,白蓮教絕對是歷代大明皇帝嚴防痛剿的組織之一;論大明開國百餘年來各地此消彼長大小規模不一的造反事例,白蓮教早已是帝王們心頭的一根毒刺,欲拔而不能。
「白蓮教已在天津衛成氣候了?」朱厚照神情陰沉道。
秦堪道:「陛下君權天授,堂堂貴胄正統,不論成不成氣候,在陛下面前都是宵小,陛下何懼耶。」
朱厚照臉色略為緩和道:「賊子們狗膽包天,竟敢公然刺我朝廷廠衛,朕絕不能容!秦堪,你意若何?」
秦堪拱手肅然道:「只求陛下一道聖旨,臣願為陛下赴天津衛,親領廠衛剿除白蓮邪教。」
朱厚照和劉瑾聞言同時一愣。
「去天津衛?你又要親自涉險地麼?不行!朕不准!」朱厚照決然搖頭:「上回你去一趟遼東差點喪命,朕內疚得給你陪葬的心思都有了,這回說什麼也不讓你去!秦堪,你讓朕省省心吧。」
秦堪道:「陛下,天津不是遼東,臣在遼東要面對敵人,是手握邊鎮兵權的大將以及最大的外敵韃靼騎兵,內憂外患皆俱,那才叫真的危險。但天津衛不一樣,臣去天津要查的是白蓮教逆賊,這是一群上不了臺面的蟊賊,臣要做的只是抽絲剝繭把他們從洞裏挖出來而已,談不上危險……」
朱厚照哼道:「東廠折了兩個大檔頭,錦衣衛折了一個鎮撫,一個千戶,這還不叫危險?秦堪,朕身邊的太監和大臣們常以『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來勸諫朕不要做那些危險的事情,朕也用這句話來勸你,你如今貴為侯爵,也是朕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何必親身涉險?叫下面麵的人去做便是了,朕不信我大明除了你就沒別的能人了……」
秦堪無奈苦笑,目光朝旁邊的劉瑾一瞥,帶著幾分邪味。
劉瑾渾身一顫,讀懂了秦堪的眼神,此刻他若不為秦堪遊說一番,想必秦堪下一句話絕對會把他推薦到天津去!
劉瑾忍住滿腔怒火,擠出個笑臉道:「陛下,廠衛之前派過去的人馬折了好幾個,那都是因為他們太過大意,若秦侯爺凡事小心些,必然無礙的。白蓮邪教自南宋以來,雖頻頻聚眾造反,然則都成不了氣候;我大明立國之後,雖然也常有白蓮造反,但隨便一支朝廷兵馬便將他們輕鬆滅掉。此何以故?只因白蓮教所納信徒皆為粗鄙村夫愚民也,說白了,他們其實是一群烏合之眾,王師所指,一擊即潰,秦侯爺是有大本事的人,區區白蓮教自然手到擒來,陛下不用擔心。」
朱厚照聞言想了想,覺得也有道理,不由遲疑道:「是……這樣的嗎?」
秦堪微笑拱手道:「劉公公所言甚是,陛下,臣也是為陛下的江山萬年久安計啊,還請陛下成全。」
朱厚照猶豫半晌,終於點點頭:「好,朕這次便允了你,稍晚朕便將欽差聖旨派人送到你府上,此行一應人馬器物皆由你選。秦堪,你可萬萬要小心,不然朕真沒臉見你秦府夫人們了……」
「多謝陛下成全。」
目的達到,秦堪慢慢走出殿門,沒走幾步,卻發現身後張永也跟了上來。
秦堪停下腳步,朝張永拱手:「張公公有事嗎?」
張永嘆道:「侯爺,此去天津,你可要好好保重,萬不可再出事了……咱家剛才一直盯著劉瑾呢,你在陛下面前一提去天津,劉瑾當即目露殺機,侯爺天津之行,恐怕劉瑾會暗中使壞,萬萬小心啊!」
秦堪笑道:「多謝張公公提醒,我記住了。」
二人站在乾清宮外閒聊了幾句,張永不知有何心事,神情猶豫不安,拉著秦堪說些毫無營養漫無邊際的話,卻遲遲不放他離開。
秦堪笑道:「張公公一定有別的事吧?我與張公公皆是東宮舊人,而且咱們的關係……呵呵,公公有話不妨直言,能幫得上忙的我一定幫。」
張永感激莫名道:「秦侯爺果真是好人吶,咱家能認識侯爺,這輩子算沒白活。」
秦堪摸了摸鼻子,別人怎麼罵他無所謂,一旦聽有人稱讚他是好人,他總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度對方,第一反應便是別人拐著彎兒罵他。
張永猶豫片刻,這才期期開口道:「不瞞侯爺說,咱家如今在宮裏越混越窩囊了……」
「哦?此話何解?」張永神情浮上憤恨之色:「還不是因為劉瑾那個老雜碎!陛下欲建豹房,內庫全部提現全安排到豹房修建上去了,劉瑾那老雜碎只留了三十萬兩給十一監,咱家所領的御馬監唯獨排除在外;咱家找他理論,老雜碎卻說御馬監掌禁中兵事,欲討餉銀可問戶部和兵部,內庫支出太多,不堪敷出,或者等明年開春以後各地押解京師的下一批礦稅銀子。侯爺,咱家掌的是禁中兵權,掌兵是要銀子的呀,咱家開不出餉銀,那些軍士誰會服咱家管?龍驤四營的將士們誰會給咱家好臉色?劉瑾這是生生把咱家往絕路上逼呀……」
秦堪同情地點點頭:「張公公的難處我已知曉,不知公公的意思是……」
張永愁眉苦臉道:「眼看要過年了,御馬監若再不發一批餉銀,怕是禁中官兵要嘩變,那時咱家的腦袋可危險了,還請侯爺救我!侯爺麾下錦衣衛進項甚多,若能臨時調撥一批銀子過來,咱家此生必感侯爺大恩大德。」
秦堪沉吟不語,良久才緩緩道:「公公言重了,我與公公相交莫逆,怎會見死不救!這樣吧,我私人出銀五十萬兩,走錦衣衛的帳上調撥給你,將來御馬監緩過勁了再還我,此事不宜宣揚,說出去是犯忌諱的事。」
五十萬兩銀子不是小數,若擱了以前,秦堪肯定拿不出來,不過上次秦堪設計幫劉瑾坑了數百萬兩銀子,其中有一百萬兩落了自己的口袋,拿五十萬兩出來還是不難的。
張永大喜過望,眼眶頓時泛了淚,一撩下擺便打算給秦堪跪拜下去,秦堪急忙扶住了他。
「侯爺……你是咱家的再生父母呀!」
「別……我生不出你這樣的兒子,難度太高了。」秦堪急忙謙讓。
「以後侯爺但有所命,我願為侯爺赴湯蹈火!」
秦堪嘆了口氣,道:「張公公,我的能力有限。一次兩次我能幫你,可無法每次都幫到你呀!公公與劉瑾交惡,已成了解不開的死結,說句不中聽的話,將來不是你死便是他死,張公公,早做打算才是正理啊。」
張永悚然一驚,「侯爺的意思是……」
秦堪笑了笑:「我沒什麼意思,張公公,我還有事,先告辭了。五十萬兩銀子晚間我會命人押解御馬監署衙。」
秦堪轉身離去,背對著張永時,他的嘴角露出一抹不懷善意的笑容。
張永一直處於呆滯中,心不在焉地朝秦堪拱拱手,直到秦堪的身影消失不見,仍呆呆地站著,眼中懼意和殺意相互交替,變幻不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