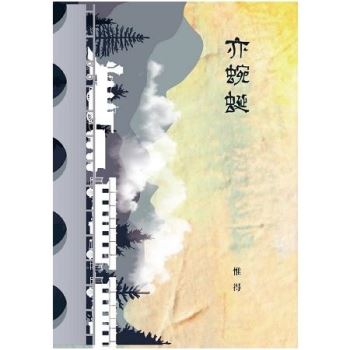停電
大哥壓根兒也不知道家裏停電,吃過晚飯後,他照例孵在牀上,掛着耳筒,陶醉在iPod的旋律中,(iPod 起碼可以下載一千多首歌,彷彿唱也唱不完,在未有激光唱片和智能手機的年代,就只好靠電唱機娛樂,就算歌曲早已播完,也不要緊,反正電唱機是自動的),含含糊糊的竟又睡熟了,是一陣很大的聲響教他完全清醒過來。歌曲早已播完,他並不在意,四周很暗,他以為已是深夜,望向對面的大廈,卻又燈火通明,有點奇怪,卻未加深究,其實他坐起來,便可以看到壁鐘,他沒有這樣做,時間對他並不重要,倒是房間出奇的燠熱,濕度在頸項擴散,漸漸佔領汗衫,黏在身上,十分難受,原來電風扇也停了,他暗罵一聲,勉力從牀上爬起來,想到毛病可能出在機件本身,但額上不斷流出的汗又令他無心細看,想起客廳的冷氣機,忙不迭把雙腳伸到地上,一隻拖鞋又不知去向,伸手按向開關,連燈泡也不聽使喚,他這才意識到,屋內有點不妥,猛力拉開房門,外面,一場爭執正迎着他。
「我有甚麼錯?」漆黑的客廳裏,就着茶几上的一根短燭,父親揚起聲音說話,父親平時很少這樣失態,今晚卻份外激動,彷彿在黑暗中可以隨意釋放心中的桎梏,真的,他覺得自己並沒有錯,不過差遣小兒子到街上買煙,誰會料到停電,老妻卻向自己埋怨,難道讓兒女為自己做點小事也算犯了瀰天大罪?她也不想想兒女,多麼叛逆,比如今晚,小兒子正在房裏砌樂高,(在未發明樂高的年代,他就只好砌積木了),他拿着買煙的錢進去,小兒子就避到洗手間,走投無路時又推說怕隔壁的狗,直到他答應,買完煙的找錢全歸小兒子所有,還陪他去搭電梯,小兒子才勉強就範,想不到一把年紀還要看兒女的面色,愈想愈氣憤,怨氣隨着熱氣不斷上升,抖動着汗衫,也難以控制,加上沒有香煙提神,精神有點恍惚,不斷地打呵欠,又唇乾舌結,實在不願多話,衝着老妻的嘴臉就冒出一句:「你真蠻不講理!」「甚麼?居然罵我?你也不想想自己,好端端的又指使小弟出去買煙,現在停電了,小弟不知所蹤,你還心安理得,告訴你,小弟才八歲,萬一有了三長兩短,我才不放過你。你在想辦法?你會想到甚麼?我不過到隔壁走了一趟,家裏便發生這麼多事,你就想把我煩死,其實,少吸一晚煙還不是對你有益,你又不是沒有聽過,吸煙會引致肺癌,嘿!那可不是風涼話,何況,你省下買煙的錢,遲些時起碼可以為我添置一部洗衣機,隔壁的陳先生,連洗碗碟機也買給太太,你就不會為我設想一下,你們全是涼血的,小弟不見了,老大還去睡覺,怎麼?捨得出來了嗎?還以為你要躺在夢中做人?甚麼?電筒?不就在房裏第二格抽屜?這點小事還要我服侍?小妹呢?你就只會整天對着手機雞啄不斷,(就算未發明智能手機,也可以用電話。)早知這樣,索性不買給你,還哭?難道我冤枉了你?」
妹妹不敢聲張,躲在大廳暗處,兀自嗚咽,並非受了委屈,她在恐懼,明天上體育課時,若是自己沒有穿上一條整潔的白褲,老師會罰留堂,她知道白褲就躺在一堆未燙的衣物內,但飯後她只顧着講電話,忘記對母親說,現在卻不敢說,說了也沒有用,已經停電了,母親反為加倍責備自己,放着重要的事情不顧,整天只會和同學在手機中搬弄是非,甚至把手機沒收,剝削了自己的生活情趣,不!妹妹不敢聲張。
大哥也不敢招惹母親,拿了電筒,趕忙逃回房裏,原來拖鞋就在牀的另一邊,黑暗中,自己幾乎盲了,在電筒的照射下,他還看到地上有張教砌樂高的圖樣,知道是弟弟的,也拾起來,放在弟弟牀上。圖樣是弟弟最寶貝的,平時他總愛把圖樣攤在跟前,依着它的指示來砌,有一次弟弟把圖樣遺失了,足足哭了好半天,以後就只會呆呆地對着樂高,變不出任何花樣,直到母親從衣櫃底把圖樣掃出來,弟弟才恢復以前的熱忱。失去圖樣的一段時期,弟弟就算堆起樂高,也頹然把它們拆掉,活像此刻鼓噪着的母親,因為發覺生活上驟然的欠缺,而手足無措,他知道自己也應該去找尋弟弟,卻總是提不起勁,終於等到母親走進來,他才懶洋洋地提着電筒出去。梯間很暗,大哥拿着電筒,仍得小心摸索,起初他數着梯級,以為心裏有數,便可放膽地走,誰知轉彎後,樓梯平白少了一級,他踏了個空,登時摔倒,幸虧電筒沒有跌壞,買蠟燭的幾個硬幣卻丟了,他又得四下尋找。再不敢依着慣性行事,步步為營,彷彿走了一個世紀,才到了樓下。電梯口,弟弟站在那裏,抽噎着,看見他,再不肯放過,緊抓着他的臂膀,直到雜貨店前。店內人頭湧湧,大哥囑咐弟弟在門口小候,弟弟寧死不從,只好把他也帶進去。連蠟燭也漲了價,大概老闆知道附近停電,乘機坐地起價,大哥有些不服氣,但看看後面蠢蠢欲動的群眾,想到家裏惟一的短燭快要燒完,只好任由宰割。上樓時大哥本來不為意,弟弟卻警告他提防惡犬,他心內頓時蒙上一層陰影,大哥並不怕狗,但在這個悶熱的黑夜,誰知犬隻會否獸性大發?心內愈怕,偏偏碰上,大哥忽然踢到一樣東西,一聲響後,弟弟首先大叫,大哥幾乎把電筒拋掉,細心一照,原來是一個鐵罐。他們住在九樓,不算太高,大概平時缺少運動,回家後大哥差點喘不過氣,攤在牀上十多分鐘,又覺得熱,摸黑在浴室洗了個冷水澡,換了背心,重新回房,習慣地按動電風扇,才記得停了電,躺在牀上,不能成寐,無聊地看看枱上的錶,剛過了九時,儘管可以繼續聽iPod,身上的背心卻已經滲滿了汗,脫掉一扭,居然擰出水來,反正烏燈黑火無人理會,懶得再套上身,懸在牀沿,任它風乾。然而,下半晚如何打發?只好走出大廳,心理上感覺稍為涼快。大廳中,父親接過香煙,連忙拆開,忙亂了好一會,才發覺家人都以一種奇怪的眼光望着自己,好像把他當作癮君子,母親看見弟弟回來,雀躍了好一會,只是屋內仍熱,葵扇撥出來的風又弱,弟弟老是黏在自己身邊,她感到混身不舒服,「你自己就去玩玩吧!」「我怕!」不止弟弟害怕,妹妹也有點心怯,剛才還捧着手機入房向同學訴苦,不一會又氣急敗壞地走出來,她看見房裏有一個黑影,一家五口就散坐在大廳內,氣氛出奇的冷,大哥有點吃驚,彼此之間原來如此隔膜,難得聚在一起,竟然無話可說。平時這個時候,大家同看電視劇倒還不太顯眼,今晚卻份外突兀,他們就這樣,你望我,我望你,望向窗口望向牆,又不約而同的望向電視機,熒光幕一片空白,他們也不把視線移開,好像要看出一個奇跡,奇跡果然出現了,熒光幕忽然閃了一下,畫面隨着重新出現,電光管眨了兩下,又大放光明,冷氣機也繼續工作,大哥回房把脫掉的背心重新披回身上,弟妹歡呼起來,父母示意他們肅靜,電視正在播映一幕公堂鬧劇,兩兄弟爭家產吵個不休,烏龍知縣打了一會瞌睡,便胡亂抓起驚堂木,假作威風的拍着說:「你們這班糊塗蟲,都給我跪下!」
原載《星島日報》
二〇一五年修訂
大哥壓根兒也不知道家裏停電,吃過晚飯後,他照例孵在牀上,掛着耳筒,陶醉在iPod的旋律中,(iPod 起碼可以下載一千多首歌,彷彿唱也唱不完,在未有激光唱片和智能手機的年代,就只好靠電唱機娛樂,就算歌曲早已播完,也不要緊,反正電唱機是自動的),含含糊糊的竟又睡熟了,是一陣很大的聲響教他完全清醒過來。歌曲早已播完,他並不在意,四周很暗,他以為已是深夜,望向對面的大廈,卻又燈火通明,有點奇怪,卻未加深究,其實他坐起來,便可以看到壁鐘,他沒有這樣做,時間對他並不重要,倒是房間出奇的燠熱,濕度在頸項擴散,漸漸佔領汗衫,黏在身上,十分難受,原來電風扇也停了,他暗罵一聲,勉力從牀上爬起來,想到毛病可能出在機件本身,但額上不斷流出的汗又令他無心細看,想起客廳的冷氣機,忙不迭把雙腳伸到地上,一隻拖鞋又不知去向,伸手按向開關,連燈泡也不聽使喚,他這才意識到,屋內有點不妥,猛力拉開房門,外面,一場爭執正迎着他。
「我有甚麼錯?」漆黑的客廳裏,就着茶几上的一根短燭,父親揚起聲音說話,父親平時很少這樣失態,今晚卻份外激動,彷彿在黑暗中可以隨意釋放心中的桎梏,真的,他覺得自己並沒有錯,不過差遣小兒子到街上買煙,誰會料到停電,老妻卻向自己埋怨,難道讓兒女為自己做點小事也算犯了瀰天大罪?她也不想想兒女,多麼叛逆,比如今晚,小兒子正在房裏砌樂高,(在未發明樂高的年代,他就只好砌積木了),他拿着買煙的錢進去,小兒子就避到洗手間,走投無路時又推說怕隔壁的狗,直到他答應,買完煙的找錢全歸小兒子所有,還陪他去搭電梯,小兒子才勉強就範,想不到一把年紀還要看兒女的面色,愈想愈氣憤,怨氣隨着熱氣不斷上升,抖動着汗衫,也難以控制,加上沒有香煙提神,精神有點恍惚,不斷地打呵欠,又唇乾舌結,實在不願多話,衝着老妻的嘴臉就冒出一句:「你真蠻不講理!」「甚麼?居然罵我?你也不想想自己,好端端的又指使小弟出去買煙,現在停電了,小弟不知所蹤,你還心安理得,告訴你,小弟才八歲,萬一有了三長兩短,我才不放過你。你在想辦法?你會想到甚麼?我不過到隔壁走了一趟,家裏便發生這麼多事,你就想把我煩死,其實,少吸一晚煙還不是對你有益,你又不是沒有聽過,吸煙會引致肺癌,嘿!那可不是風涼話,何況,你省下買煙的錢,遲些時起碼可以為我添置一部洗衣機,隔壁的陳先生,連洗碗碟機也買給太太,你就不會為我設想一下,你們全是涼血的,小弟不見了,老大還去睡覺,怎麼?捨得出來了嗎?還以為你要躺在夢中做人?甚麼?電筒?不就在房裏第二格抽屜?這點小事還要我服侍?小妹呢?你就只會整天對着手機雞啄不斷,(就算未發明智能手機,也可以用電話。)早知這樣,索性不買給你,還哭?難道我冤枉了你?」
妹妹不敢聲張,躲在大廳暗處,兀自嗚咽,並非受了委屈,她在恐懼,明天上體育課時,若是自己沒有穿上一條整潔的白褲,老師會罰留堂,她知道白褲就躺在一堆未燙的衣物內,但飯後她只顧着講電話,忘記對母親說,現在卻不敢說,說了也沒有用,已經停電了,母親反為加倍責備自己,放着重要的事情不顧,整天只會和同學在手機中搬弄是非,甚至把手機沒收,剝削了自己的生活情趣,不!妹妹不敢聲張。
大哥也不敢招惹母親,拿了電筒,趕忙逃回房裏,原來拖鞋就在牀的另一邊,黑暗中,自己幾乎盲了,在電筒的照射下,他還看到地上有張教砌樂高的圖樣,知道是弟弟的,也拾起來,放在弟弟牀上。圖樣是弟弟最寶貝的,平時他總愛把圖樣攤在跟前,依着它的指示來砌,有一次弟弟把圖樣遺失了,足足哭了好半天,以後就只會呆呆地對着樂高,變不出任何花樣,直到母親從衣櫃底把圖樣掃出來,弟弟才恢復以前的熱忱。失去圖樣的一段時期,弟弟就算堆起樂高,也頹然把它們拆掉,活像此刻鼓噪着的母親,因為發覺生活上驟然的欠缺,而手足無措,他知道自己也應該去找尋弟弟,卻總是提不起勁,終於等到母親走進來,他才懶洋洋地提着電筒出去。梯間很暗,大哥拿着電筒,仍得小心摸索,起初他數着梯級,以為心裏有數,便可放膽地走,誰知轉彎後,樓梯平白少了一級,他踏了個空,登時摔倒,幸虧電筒沒有跌壞,買蠟燭的幾個硬幣卻丟了,他又得四下尋找。再不敢依着慣性行事,步步為營,彷彿走了一個世紀,才到了樓下。電梯口,弟弟站在那裏,抽噎着,看見他,再不肯放過,緊抓着他的臂膀,直到雜貨店前。店內人頭湧湧,大哥囑咐弟弟在門口小候,弟弟寧死不從,只好把他也帶進去。連蠟燭也漲了價,大概老闆知道附近停電,乘機坐地起價,大哥有些不服氣,但看看後面蠢蠢欲動的群眾,想到家裏惟一的短燭快要燒完,只好任由宰割。上樓時大哥本來不為意,弟弟卻警告他提防惡犬,他心內頓時蒙上一層陰影,大哥並不怕狗,但在這個悶熱的黑夜,誰知犬隻會否獸性大發?心內愈怕,偏偏碰上,大哥忽然踢到一樣東西,一聲響後,弟弟首先大叫,大哥幾乎把電筒拋掉,細心一照,原來是一個鐵罐。他們住在九樓,不算太高,大概平時缺少運動,回家後大哥差點喘不過氣,攤在牀上十多分鐘,又覺得熱,摸黑在浴室洗了個冷水澡,換了背心,重新回房,習慣地按動電風扇,才記得停了電,躺在牀上,不能成寐,無聊地看看枱上的錶,剛過了九時,儘管可以繼續聽iPod,身上的背心卻已經滲滿了汗,脫掉一扭,居然擰出水來,反正烏燈黑火無人理會,懶得再套上身,懸在牀沿,任它風乾。然而,下半晚如何打發?只好走出大廳,心理上感覺稍為涼快。大廳中,父親接過香煙,連忙拆開,忙亂了好一會,才發覺家人都以一種奇怪的眼光望着自己,好像把他當作癮君子,母親看見弟弟回來,雀躍了好一會,只是屋內仍熱,葵扇撥出來的風又弱,弟弟老是黏在自己身邊,她感到混身不舒服,「你自己就去玩玩吧!」「我怕!」不止弟弟害怕,妹妹也有點心怯,剛才還捧着手機入房向同學訴苦,不一會又氣急敗壞地走出來,她看見房裏有一個黑影,一家五口就散坐在大廳內,氣氛出奇的冷,大哥有點吃驚,彼此之間原來如此隔膜,難得聚在一起,竟然無話可說。平時這個時候,大家同看電視劇倒還不太顯眼,今晚卻份外突兀,他們就這樣,你望我,我望你,望向窗口望向牆,又不約而同的望向電視機,熒光幕一片空白,他們也不把視線移開,好像要看出一個奇跡,奇跡果然出現了,熒光幕忽然閃了一下,畫面隨着重新出現,電光管眨了兩下,又大放光明,冷氣機也繼續工作,大哥回房把脫掉的背心重新披回身上,弟妹歡呼起來,父母示意他們肅靜,電視正在播映一幕公堂鬧劇,兩兄弟爭家產吵個不休,烏龍知縣打了一會瞌睡,便胡亂抓起驚堂木,假作威風的拍着說:「你們這班糊塗蟲,都給我跪下!」
原載《星島日報》
二〇一五年修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