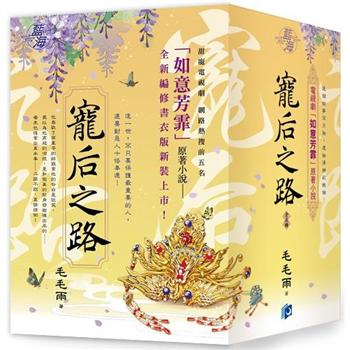噩間,傅容聽到有人焦急的吶喊。
她們在喊什麼?皇上駕臨牡丹園怎有人膽敢大聲喧嘩?
「牡丹園」三字湧入腦海,彷彿耀眼亮光突然劃破黑暗,一幕幕紛雜場景接連湧了進來—— 肅王徐晉戰死,太子弒弟謀反,七皇叔安王臨危鎮亂,先皇重病退位,安王登基。
安王登基……是了,那個一直沒有娶妻的七皇叔成了新君,她父兄相繼升官,傅家聖眷隆寵,因此她得以從廢棄的肅王府裏恢復自由身回娘家。
她才二十一,依舊貌美無雙,聽說皇上要去牡丹園,她仗著哥哥御前侍衛統領的身分得以進園,想要和那些貴女們一樣搏一次機會,她對將來沒有太大的野心,就是想為後半輩子找個依靠,為自己爭取舒適生活,可就在即將面聖時,她被一雙手推入湖中,冰冷的水灌入喉嚨,難受得無法呼吸,她還年輕,她不想死……
「哇」的一聲,身穿水紅色繡花長裙的傅容突然吐出一口水,跟著就連續不停地嗆咳起來。
「好了好了,三姑娘沒事了!」渾身濕透的婆子大喜,抬頭大喊。
府裏三個姑娘,二姑娘溫婉端莊,六姑娘知書達禮,只有這三姑娘從小就被老爺、夫人寵得肆無忌憚,今日竟趁丫鬟們打盹偷偷溜到湖邊划船玩,不知怎麼落水了,幸好被她瞧見,及時救了上來。
傅家還有兩房,在冀州的傅容兄妹們都是跟京城那邊統一排的序。
「濃濃!」
喚她小名的聲音柔中帶剛,既熟悉又好像極為遙遠,久未聽聞,傅容難以置信地抬起頭,就見一個穿綠裙的荳蔻少女神色慌張地朝她跑了過來,後面跟著一眾丫鬟。
傅容的眼淚登時落了下來—— 她還是死了嗎?竟然見到了姊姊?既然能與姊姊團聚,死了也還好……
貪戀地看著越來越近的姊姊,傅容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
***
「父親,明日你還要去衙門,母親,弟弟夜裏離不開妳,還有宣宣,妳年紀太小了,你們都先回去吧,我跟哥哥在這裏守著濃濃就夠了,有什麼事我會派人去叫你們的。」整齊莊嚴的嗡嗡念經聲裏,傅宛再次勸道。
「我不走。」九歲的傅宣坐在床邊,小臉繃著,兩道眉毛緊緊蹙起,煞有介事。
傅品言看看小女兒,再看看滿臉憂愁凝望床上次女的妻子,歎道:「宛姐兒說的對,素娘,妳帶宣姐兒先回去,妳們身子弱,別濃濃還沒好妳們兩個又病了。衙門最近無事,我也留在這裏陪濃濃,妳們不用擔心。」
喬氏雖然擔心女兒,奈何正房還有個不滿周歲的小兒子需要照看,便點點頭,伸手去領傅宣,「宣宣聽話,明早再過來看妳三姊姊。」
「我不走!」向來不愛哭的傅宣低頭哭了,趴在床上不肯走,她要守著三姊姊。
「正堂,去送你母親、妹妹。」傅品言皺眉,低喊了兒子的字。
父親發話,傅宸上前抱起小妹妹,邊往外走邊柔聲安撫,「宣宣聽話,妳三姊姊沒事的,妳再哭,小心明早她知道了笑話妳,妳不是最討厭她欺負妳嗎?」
少年清朗溫柔的聲音漸漸消失在僧人的念經聲裏,面朝裏面側躺的傅容悄悄用被角擦了眼淚。
她在作夢嗎?夢怎麼會如此真實?所以不是夢吧?畢竟她掐了自己好幾下,都那麼疼。可如果不是夢,她為何回到了十三歲這年……死後重生?
傅容想跟父親母親說未來那些大事,才開口說沒幾句就被父親喝住了,厲聲告誡她不許胡言亂語,她搖著頭跟他們解釋,母親卻抱著她哄,說她昏迷時魘到了,那些都不是真的。
傅容不信,那些不是噩夢,眼下也不是美夢,都是真實的,然而寵她如寶的父親懷疑她落水後沾了髒東西,先用帕子堵了她的嘴,省得她繼續說些「大逆不道」的話,又請郎中開寧神丸,又請竹林寺高僧在院中做法事,只求女兒健康平安。
長夜漫漫,傅容沒有半點睡意,聽著身後父親、哥哥、姊姊低聲細語,感受他們語氣裏的憂慮,再回想她說那些話時他們眼中的驚駭,傅容閉上眼睛。
死後重生,連她自己都覺得荒誕,怪不得親人們都不肯相信……罷了,到底是十三歲的她在昏迷期間作了個恍如真實的漫長噩夢,還是她真的在二十一歲那年遇害並起死回生了,日子繼續過下去就知道了,如果以後發生的一切都跟記憶重合,就說明……
等等,假如不是噩夢,接下來七、八日後她會發痘,郎中勸她去莊子上休養,以免傳染給家人,她由乳母孫嬤嬤陪著去了,待了將近一個月才徹底養好,回家後震驚得知,在她抵達莊子當晚,弟弟就因染病去了,父母擔心她胡思亂想,一直瞞著她。
她那喜歡抓她手指含的弟弟啊!
想到此,傅容登時滿頭大汗地坐了起來。
「濃濃怎麼了?」聽見響動,傅品言幾個箭步衝了過來,扶住女兒肩膀看她。
「爹爹!」傅容撲到父親懷裏悲痛大哭,「我……我作噩夢了,在水裏沒有人救我。」擔心父親又堵她的嘴,臨時改了口,沒有說弟弟的事。
傅品言心疼死了,三女二子裏就這個從小黏他,長得又粉雕玉琢、嬌憨可愛,他就是再不想偏心也偏了大半,面對二女兒所有要求,各種軟磨硬泡手段輪番用上後,他幾乎沒有不應的,哪想今日鬧出此等禍事。
「不怕不怕,爹爹在這兒,妳哥哥、姊姊也都在,濃濃不用怕啊!」輕輕拍拍女兒肩膀,傅品言的下巴抵著她腦頂哄道。
傅容哭個不停,將那噩夢般記憶裏的所有心酸委屈都哭了出來,停下時外面剛好傳來三更鼓響。
「爹爹,你別罵我,我以後再也不淘氣了。」哭夠了,傅容埋在父親胸前悶悶地道。
女兒聲音都哭啞了,卻帶了熟悉的討好求饒,傅品言挑了挑眉,扶正女兒肩膀,見她目光躲閃就是不肯看他,跟以前闖禍時一模一樣,冷哼道:「這話妳說了多少遍了?」
「每年都得說個百八十遍吧?」旁邊的傅宸加油添醋。
傅容瞪了哥哥一眼,撒嬌地扯著傅品言腰間玉佩晃,「爹爹,我都這樣了,你還捨得罰我嗎?要罰也得等我好了再罰啊?」
女兒恢復正常,不再說些大逆不道的話,傅品言鬆口氣,高興還來不及,哪裏捨得罰?只讓女兒平躺下去,替她掩了被子,又怕她恃寵不記教訓,故意冷著臉問她的身體情況。
「爹爹放心,都沒事了。」傅容伸手握住床頭姊姊的手,朝父親和兄長道:「這麼晚了,爹爹、哥哥都回去吧,姊姊在這裏陪我就好。」
家人都認為她受了驚嚇,眼下就算想把人全部趕走,減少傳染可能,他們也不會答應,何況說了也沒人信,只好留下姊姊陪她。
但傅容不是很擔心姊姊會被她傳染,郎中說過,水痘多見於十歲以下的孩子,發痘前兩日時最容易傳染,得了也不算大病,只有小孩子略加危險些,得仔細照看。
夢裏……暫且就當是夢好了,或許是距離她發痘還有些時日,落水後姊姊連續陪她睡了三晚都沒事,只有弟弟不知何時染病的。
過去自己從來沒有碰過發痘的人,第一個痘出來之前哪知道自己染了病,幾乎每天都要抱弟弟……暗暗抓緊被子,傅容強迫自己不要再想下去,後悔沒用,重要的是眼下,是將來。
見女兒只是臉色有些白,精神還算不錯,傅品言放了心,柔聲叮囑幾句便站了起來,領著長子離去。
傅宸臨走前朝傅容做了一個寫字的動作,臉上笑得特別燦爛,露出幾顆白牙。
那是在告訴她,父親這次肯定還會罰她抄書呢,讓她先別得意!
換做以前,傅容定會氣得把枕頭丟過去,可那是她的哥哥啊,牢牢護著她的哥哥。看到還帶著青澀頑皮勁兒的哥哥,傅容只覺得好玩有趣,難以想像哥哥會變成那個冷峻似鐵的侍衛統領。
「哥哥逗妳玩呢,別理他!」擔心妹妹動怒,傅宛故意往外坐了坐,擋住傅宸身影。
傅容收回視線,看著面前嬌美如盛開牡丹的姊姊,什麼都沒說,撒嬌般抱住了她。
如果她發痘了,那一切就是真的,父母不信她沒關係,她會盡所有努力護住姊姊、弟弟,不讓弟弟夭折,不讓姊姊嫁給齊策那個混蛋,錯付真心,在大好年華香消玉殞。
傅宛只當妹妹後怕,笑著道:「沒事了,好好睡一覺,把噩夢都忘了,爹爹捨不得罰妳的。」
「嗯,姊姊上來吧,咱們一起睡。」抹抹眼睛,傅容拽著姊姊的手道。
「等等,我去叫水給妳擦擦臉,哭了半天,明早眼睛肯定腫得跟核桃似的。」傅宛打趣她。
傅容捨不得姊姊走,朝外面努努嘴,「讓梅香、蘭香去不就成了。」都是她的丫鬟。
傅宛看看她,平靜地道:「她們沒有伺候好妳,一人領了十板子。妹妹,妳真為她們好,以後就學乖點。」妹妹受了驚嚇,哄是該哄,訓斥告誡也不能少。
傅容乖乖低頭認錯。她怎麼忘了,父親、母親疼他們,對別人可是賞罰分明的。
見她明白了,傅宛這才起身,吩咐守在外間的她的大丫鬟白芷去端熱水。
白芷嗎?聽到這名字,傅容垂眸,嘴角浮起冷笑—— 不怕,慢慢來,該收拾的她一個都不會放過!
擦過臉,姊妹倆熄了燈,同被而眠。
第二天早上,傅品言夫妻一起床就趕過來看女兒,院子裏的僧人們還在念經。
傅容早醒了,咳個不停,見到父親、母親,她淚眼模糊地訴苦,「我頭疼,爹爹你快快把那些人趕走,吵了一晚我都睡不好覺,現在,咳……嗡嗡的我好難受。」
落水著涼本就容易生病,既然女兒神智已清醒,自然不用再做法驅邪,傅品言馬上吩咐管家好言好語送眾僧回去,又請來用慣了的李郎中。
傅容的病是裝的,李郎中沒看出什麼,見小姑娘悄悄朝他眨眼睛,頓時心裏有數,開了副驅寒治咳的方子。
傅品言乃進士出身,浸淫官場多年,能升到冀州知府的位置必不可小覷,他不敢開假方子糊弄,反正三姑娘知道自己沒病,肯定不會真的喝藥。
李郎中走後,傅容再三叮囑身邊的親人們,「官哥兒還小,我病好之前,娘就別抱他來看我了,還有你們,從我這兒回去後一定要洗漱乾淨,換身衣裳後再去看官哥兒,免得把病氣過給他。反正我醜話說在前頭,我最喜歡官哥兒了,要是有人不聽我的話害他生病,我就一個月都不理他!」在她想到辦法提前搬去莊子之前,只能這樣護住弟弟了。
「才一個月?」傅宸不太滿意這個期限。
傅容鼓了鼓腮幫子,惡狠狠瞪著他,「你到底聽不聽?娘,哥哥不換衣裳妳就別讓他抱弟弟!」
喬氏笑著點點女兒紅撲撲的小臉,「好了好了,知道妳愛護弟弟,放心吧,我們都聽妳的,妳先別管官哥兒,自己早點把病養好才是。」
「娘別糊弄我,一定要照顧好官哥兒。」傅容抱著母親撒嬌,大眼睛裏滿是哀求。
「不糊弄,娘什麼時候糊弄過妳?」喬氏被愛女看得心軟軟的,再三保證。
傅容這才放心。
傅品言乃冀州知府,傅容落水一事傳出去後,與傅家交好的幾戶人家紛紛前來探望。
其實傅容醒來後什麼事都沒有,只是表面功夫還是要做,所以當喬氏跟那些夫人、太太敘話時,便由傅宛、傅宣兩人領著幾個姑娘去園子裏玩。
眼下傅容裝病,以怕過了病氣為由謝絕了眾人探訪,只有梁家二姑娘逛完園子後天不怕地不怕地跑了進來。
「活該,叫妳貪玩不叫我,我會划船也會泅水,跟我在一起,保妳不會淹死!」梁映芳一屁股坐在床邊,拿著剛剛在園子裏隨手摘的薔薇花往傅容臉上掃。
梁家是武學世家,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一手八卦拳更是赫赫有名,上至京城勳貴,下至地主豪紳,都想把自家兒子送到梁家習武強身,再憑一身好武藝功成名就。
可惜家世越好公子哥兒們的性子越嬌氣,不過梁家老爺子可不管,通不過他家收徒考試的,一律趕走。
傅品言出自京城景陽侯府,生母是姨娘,從小苦讀中了進士,兒子傅宸的脾性卻酷似故去的老侯爺,喜歡舞刀弄槍,偏偏傅宸又聰明,先把傅品言交代的功課都做好,不給父親挑剔的理由,然後就去翻自己搜羅來的「武功祕笈」練功。
傅品言見長子嗜武成癡,怕他瞎折騰傷了身,就給他請了武師父。去年一家人搬到冀州治所所在的信都城,恰逢梁家收徒,父子倆早聽說過梁家大名,立即攜禮去拜師,傅宸也爭氣,不但通過考核,更被梁老爺子收到門下,成了嫡傳弟子。
有了這層關係,梁、傅兩家很快交好,無形中幫傅品言早早在信都城站穩腳跟,讓城裏一些原打算送新任知府一些「見面禮」的地頭蛇礙於梁家名望不好動手。
當然,這是傅品言最看重的事,傅容一個小姑娘還不懂,她只覺得梁映芳熱情大方、坦率真誠,不像其他大家閨秀那樣做什麼都束手束腳,簡直對極了她的性子,兩人迅速成為好姊妹,平日裏傅容跟梁映芳一起玩的時候甚至比跟家裏兩個親姊妹多。
「別鬧了,沒看我病著呢。」即便是夢,因為太過真實,傅容真的覺得自己過了那樣的幾年,所以現在看梁映芳就好比故人重逢,高興極了,一點都不生氣,只笑盈盈看著她。
梁映芳警惕地看她兩眼,忽的挪遠了些,「笑得跟花似的,肯定沒安好心,是不是又在打什麼壞主意?」在她眼裏,傅容就是個小狐狸,雖然打不過自己,可傅容心眼多,總能在別的地方討回去,讓她吃虧。
受了冤枉,傅容起身就想打梁映芳兩下,抬手時忽的想到她剛剛的嘲諷,心中一動,高高抬起的手就放下了,趁梁映芳放下戒備時抱住她的胳膊,「映芳,等我養好病,妳教我泅水吧?」這次的事是個教訓,夢裏的災禍也是教訓,會了水以後總不至於淹死。
梁映芳好動,一聽這話馬上就應了,「好啊,咱們去我們家在紫薇山的莊子,那裏有溫泉,正好妳大病初癒,泡泡對身體好。」
傅容也很興奮,只可惜她真正的「大病初癒」,肯定要等一個月後了。
梁映芳走後,傅宛走了進來,見妹妹臉色紅潤,笑道:「見了好姊妹,病就好了大半是不是?」
「都是親姊姊照顧得好。」傅容抱著枕頭靠在床頭,甜甜地道:「客人都走了嗎?」
傅宛點點頭,倒了杯熱茶給妹妹,閒聊道:「齊夫人今早帶阿竺去保定探親沒空過來,只讓人送了禮,說回來再看妳,讓妳好好養病。」
齊家啊……傅容低頭吹茶,兩排濃密微翹的睫毛遮掩了眼中陰鬱。
齊家也是信都城裏的大戶,齊大老爺任陝西巡撫,留妻子兒女在老家信都城奉養老太太,兩家關係不錯,她跟同歲的齊竺也算手帕交,因此在那恍若前世的夢裏得知齊竺的哥哥齊策喜歡姊姊,她也樂見其成。
齊策英氣挺拔,姊姊溫婉秀麗,兩人不論才貌家世都極為相配,她還幫齊策在姊姊面前說了不少好話,姊姊漸漸心動,等齊策來提親時,姊姊羞澀地應了。
婚後兩人如膠似漆,等傅容自己嫁給徐晏的時候,姊姊有了身孕,可謂雙喜臨門,誰料沒過多久,姊姊的大丫鬟白芷也傳出喜訊,甚至跪到姊姊面前求姊姊准她生下那個孩子,直到那一刻,姊姊才知道白芷早就爬上了齊策的床。
換做發生在年少無知的自己身上,她定要大鬧一場,但姊姊只是命人給白芷灌落胎藥後發賣出去,齊策對此什麼都沒說。
齊夫人本想留下孩子,姊姊卻平靜地說她並非容不下姨娘,只是白芷是她的人,如今做出此等背主之事,她若不嚴加懲戒,以後可能會有更多的白芷,齊夫人便不再多言。
賣了白芷第二天,姊姊主動給齊策納了兩房姨娘,因有孕在身,姊姊不讓齊策再進她的房。
傅容去看姊姊時,姊姊什麼苦都不說,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只問她跟徐晏相處得如何,又勸她好好跟徐晏過,但不要把整顆心都放在徐晏身上,這樣將來出了事才不會太傷心。她以為姊姊真的放下了,可幾個月後,姊姊難產而亡,一屍兩命。
這都是齊策的錯!男人有妾不算什麼,可他為何要動姊姊身邊的人?就算是白芷勾引他,他不會拒絕嗎?一邊是貼身丫鬟的狠心背叛,一邊是溫柔丈夫的虛情假意,雙重打擊下,姊姊哪可能淡然處之、毫不介意?
提親的時候說得天花亂墜,表示不讓姊姊受半點委屈,娶回家馬上就忘了。
這就是男人,一個個都是如此,半斤八兩。
等著吧,這次齊策休想再碰姊姊一根手指頭。
她們在喊什麼?皇上駕臨牡丹園怎有人膽敢大聲喧嘩?
「牡丹園」三字湧入腦海,彷彿耀眼亮光突然劃破黑暗,一幕幕紛雜場景接連湧了進來—— 肅王徐晉戰死,太子弒弟謀反,七皇叔安王臨危鎮亂,先皇重病退位,安王登基。
安王登基……是了,那個一直沒有娶妻的七皇叔成了新君,她父兄相繼升官,傅家聖眷隆寵,因此她得以從廢棄的肅王府裏恢復自由身回娘家。
她才二十一,依舊貌美無雙,聽說皇上要去牡丹園,她仗著哥哥御前侍衛統領的身分得以進園,想要和那些貴女們一樣搏一次機會,她對將來沒有太大的野心,就是想為後半輩子找個依靠,為自己爭取舒適生活,可就在即將面聖時,她被一雙手推入湖中,冰冷的水灌入喉嚨,難受得無法呼吸,她還年輕,她不想死……
「哇」的一聲,身穿水紅色繡花長裙的傅容突然吐出一口水,跟著就連續不停地嗆咳起來。
「好了好了,三姑娘沒事了!」渾身濕透的婆子大喜,抬頭大喊。
府裏三個姑娘,二姑娘溫婉端莊,六姑娘知書達禮,只有這三姑娘從小就被老爺、夫人寵得肆無忌憚,今日竟趁丫鬟們打盹偷偷溜到湖邊划船玩,不知怎麼落水了,幸好被她瞧見,及時救了上來。
傅家還有兩房,在冀州的傅容兄妹們都是跟京城那邊統一排的序。
「濃濃!」
喚她小名的聲音柔中帶剛,既熟悉又好像極為遙遠,久未聽聞,傅容難以置信地抬起頭,就見一個穿綠裙的荳蔻少女神色慌張地朝她跑了過來,後面跟著一眾丫鬟。
傅容的眼淚登時落了下來—— 她還是死了嗎?竟然見到了姊姊?既然能與姊姊團聚,死了也還好……
貪戀地看著越來越近的姊姊,傅容身子一軟,倒了下去。
***
***
「父親,明日你還要去衙門,母親,弟弟夜裏離不開妳,還有宣宣,妳年紀太小了,你們都先回去吧,我跟哥哥在這裏守著濃濃就夠了,有什麼事我會派人去叫你們的。」整齊莊嚴的嗡嗡念經聲裏,傅宛再次勸道。
「我不走。」九歲的傅宣坐在床邊,小臉繃著,兩道眉毛緊緊蹙起,煞有介事。
傅品言看看小女兒,再看看滿臉憂愁凝望床上次女的妻子,歎道:「宛姐兒說的對,素娘,妳帶宣姐兒先回去,妳們身子弱,別濃濃還沒好妳們兩個又病了。衙門最近無事,我也留在這裏陪濃濃,妳們不用擔心。」
喬氏雖然擔心女兒,奈何正房還有個不滿周歲的小兒子需要照看,便點點頭,伸手去領傅宣,「宣宣聽話,明早再過來看妳三姊姊。」
「我不走!」向來不愛哭的傅宣低頭哭了,趴在床上不肯走,她要守著三姊姊。
「正堂,去送你母親、妹妹。」傅品言皺眉,低喊了兒子的字。
父親發話,傅宸上前抱起小妹妹,邊往外走邊柔聲安撫,「宣宣聽話,妳三姊姊沒事的,妳再哭,小心明早她知道了笑話妳,妳不是最討厭她欺負妳嗎?」
少年清朗溫柔的聲音漸漸消失在僧人的念經聲裏,面朝裏面側躺的傅容悄悄用被角擦了眼淚。
她在作夢嗎?夢怎麼會如此真實?所以不是夢吧?畢竟她掐了自己好幾下,都那麼疼。可如果不是夢,她為何回到了十三歲這年……死後重生?
傅容想跟父親母親說未來那些大事,才開口說沒幾句就被父親喝住了,厲聲告誡她不許胡言亂語,她搖著頭跟他們解釋,母親卻抱著她哄,說她昏迷時魘到了,那些都不是真的。
傅容不信,那些不是噩夢,眼下也不是美夢,都是真實的,然而寵她如寶的父親懷疑她落水後沾了髒東西,先用帕子堵了她的嘴,省得她繼續說些「大逆不道」的話,又請郎中開寧神丸,又請竹林寺高僧在院中做法事,只求女兒健康平安。
長夜漫漫,傅容沒有半點睡意,聽著身後父親、哥哥、姊姊低聲細語,感受他們語氣裏的憂慮,再回想她說那些話時他們眼中的驚駭,傅容閉上眼睛。
死後重生,連她自己都覺得荒誕,怪不得親人們都不肯相信……罷了,到底是十三歲的她在昏迷期間作了個恍如真實的漫長噩夢,還是她真的在二十一歲那年遇害並起死回生了,日子繼續過下去就知道了,如果以後發生的一切都跟記憶重合,就說明……
等等,假如不是噩夢,接下來七、八日後她會發痘,郎中勸她去莊子上休養,以免傳染給家人,她由乳母孫嬤嬤陪著去了,待了將近一個月才徹底養好,回家後震驚得知,在她抵達莊子當晚,弟弟就因染病去了,父母擔心她胡思亂想,一直瞞著她。
她那喜歡抓她手指含的弟弟啊!
想到此,傅容登時滿頭大汗地坐了起來。
「濃濃怎麼了?」聽見響動,傅品言幾個箭步衝了過來,扶住女兒肩膀看她。
「爹爹!」傅容撲到父親懷裏悲痛大哭,「我……我作噩夢了,在水裏沒有人救我。」擔心父親又堵她的嘴,臨時改了口,沒有說弟弟的事。
傅品言心疼死了,三女二子裏就這個從小黏他,長得又粉雕玉琢、嬌憨可愛,他就是再不想偏心也偏了大半,面對二女兒所有要求,各種軟磨硬泡手段輪番用上後,他幾乎沒有不應的,哪想今日鬧出此等禍事。
「不怕不怕,爹爹在這兒,妳哥哥、姊姊也都在,濃濃不用怕啊!」輕輕拍拍女兒肩膀,傅品言的下巴抵著她腦頂哄道。
傅容哭個不停,將那噩夢般記憶裏的所有心酸委屈都哭了出來,停下時外面剛好傳來三更鼓響。
「爹爹,你別罵我,我以後再也不淘氣了。」哭夠了,傅容埋在父親胸前悶悶地道。
女兒聲音都哭啞了,卻帶了熟悉的討好求饒,傅品言挑了挑眉,扶正女兒肩膀,見她目光躲閃就是不肯看他,跟以前闖禍時一模一樣,冷哼道:「這話妳說了多少遍了?」
「每年都得說個百八十遍吧?」旁邊的傅宸加油添醋。
傅容瞪了哥哥一眼,撒嬌地扯著傅品言腰間玉佩晃,「爹爹,我都這樣了,你還捨得罰我嗎?要罰也得等我好了再罰啊?」
女兒恢復正常,不再說些大逆不道的話,傅品言鬆口氣,高興還來不及,哪裏捨得罰?只讓女兒平躺下去,替她掩了被子,又怕她恃寵不記教訓,故意冷著臉問她的身體情況。
「爹爹放心,都沒事了。」傅容伸手握住床頭姊姊的手,朝父親和兄長道:「這麼晚了,爹爹、哥哥都回去吧,姊姊在這裏陪我就好。」
家人都認為她受了驚嚇,眼下就算想把人全部趕走,減少傳染可能,他們也不會答應,何況說了也沒人信,只好留下姊姊陪她。
但傅容不是很擔心姊姊會被她傳染,郎中說過,水痘多見於十歲以下的孩子,發痘前兩日時最容易傳染,得了也不算大病,只有小孩子略加危險些,得仔細照看。
夢裏……暫且就當是夢好了,或許是距離她發痘還有些時日,落水後姊姊連續陪她睡了三晚都沒事,只有弟弟不知何時染病的。
過去自己從來沒有碰過發痘的人,第一個痘出來之前哪知道自己染了病,幾乎每天都要抱弟弟……暗暗抓緊被子,傅容強迫自己不要再想下去,後悔沒用,重要的是眼下,是將來。
見女兒只是臉色有些白,精神還算不錯,傅品言放了心,柔聲叮囑幾句便站了起來,領著長子離去。
傅宸臨走前朝傅容做了一個寫字的動作,臉上笑得特別燦爛,露出幾顆白牙。
那是在告訴她,父親這次肯定還會罰她抄書呢,讓她先別得意!
換做以前,傅容定會氣得把枕頭丟過去,可那是她的哥哥啊,牢牢護著她的哥哥。看到還帶著青澀頑皮勁兒的哥哥,傅容只覺得好玩有趣,難以想像哥哥會變成那個冷峻似鐵的侍衛統領。
「哥哥逗妳玩呢,別理他!」擔心妹妹動怒,傅宛故意往外坐了坐,擋住傅宸身影。
傅容收回視線,看著面前嬌美如盛開牡丹的姊姊,什麼都沒說,撒嬌般抱住了她。
如果她發痘了,那一切就是真的,父母不信她沒關係,她會盡所有努力護住姊姊、弟弟,不讓弟弟夭折,不讓姊姊嫁給齊策那個混蛋,錯付真心,在大好年華香消玉殞。
傅宛只當妹妹後怕,笑著道:「沒事了,好好睡一覺,把噩夢都忘了,爹爹捨不得罰妳的。」
「嗯,姊姊上來吧,咱們一起睡。」抹抹眼睛,傅容拽著姊姊的手道。
「等等,我去叫水給妳擦擦臉,哭了半天,明早眼睛肯定腫得跟核桃似的。」傅宛打趣她。
傅容捨不得姊姊走,朝外面努努嘴,「讓梅香、蘭香去不就成了。」都是她的丫鬟。
傅宛看看她,平靜地道:「她們沒有伺候好妳,一人領了十板子。妹妹,妳真為她們好,以後就學乖點。」妹妹受了驚嚇,哄是該哄,訓斥告誡也不能少。
傅容乖乖低頭認錯。她怎麼忘了,父親、母親疼他們,對別人可是賞罰分明的。
見她明白了,傅宛這才起身,吩咐守在外間的她的大丫鬟白芷去端熱水。
白芷嗎?聽到這名字,傅容垂眸,嘴角浮起冷笑—— 不怕,慢慢來,該收拾的她一個都不會放過!
擦過臉,姊妹倆熄了燈,同被而眠。
第二天早上,傅品言夫妻一起床就趕過來看女兒,院子裏的僧人們還在念經。
傅容早醒了,咳個不停,見到父親、母親,她淚眼模糊地訴苦,「我頭疼,爹爹你快快把那些人趕走,吵了一晚我都睡不好覺,現在,咳……嗡嗡的我好難受。」
落水著涼本就容易生病,既然女兒神智已清醒,自然不用再做法驅邪,傅品言馬上吩咐管家好言好語送眾僧回去,又請來用慣了的李郎中。
傅容的病是裝的,李郎中沒看出什麼,見小姑娘悄悄朝他眨眼睛,頓時心裏有數,開了副驅寒治咳的方子。
傅品言乃進士出身,浸淫官場多年,能升到冀州知府的位置必不可小覷,他不敢開假方子糊弄,反正三姑娘知道自己沒病,肯定不會真的喝藥。
李郎中走後,傅容再三叮囑身邊的親人們,「官哥兒還小,我病好之前,娘就別抱他來看我了,還有你們,從我這兒回去後一定要洗漱乾淨,換身衣裳後再去看官哥兒,免得把病氣過給他。反正我醜話說在前頭,我最喜歡官哥兒了,要是有人不聽我的話害他生病,我就一個月都不理他!」在她想到辦法提前搬去莊子之前,只能這樣護住弟弟了。
「才一個月?」傅宸不太滿意這個期限。
傅容鼓了鼓腮幫子,惡狠狠瞪著他,「你到底聽不聽?娘,哥哥不換衣裳妳就別讓他抱弟弟!」
喬氏笑著點點女兒紅撲撲的小臉,「好了好了,知道妳愛護弟弟,放心吧,我們都聽妳的,妳先別管官哥兒,自己早點把病養好才是。」
「娘別糊弄我,一定要照顧好官哥兒。」傅容抱著母親撒嬌,大眼睛裏滿是哀求。
「不糊弄,娘什麼時候糊弄過妳?」喬氏被愛女看得心軟軟的,再三保證。
傅容這才放心。
傅品言乃冀州知府,傅容落水一事傳出去後,與傅家交好的幾戶人家紛紛前來探望。
其實傅容醒來後什麼事都沒有,只是表面功夫還是要做,所以當喬氏跟那些夫人、太太敘話時,便由傅宛、傅宣兩人領著幾個姑娘去園子裏玩。
眼下傅容裝病,以怕過了病氣為由謝絕了眾人探訪,只有梁家二姑娘逛完園子後天不怕地不怕地跑了進來。
「活該,叫妳貪玩不叫我,我會划船也會泅水,跟我在一起,保妳不會淹死!」梁映芳一屁股坐在床邊,拿著剛剛在園子裏隨手摘的薔薇花往傅容臉上掃。
梁家是武學世家,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一手八卦拳更是赫赫有名,上至京城勳貴,下至地主豪紳,都想把自家兒子送到梁家習武強身,再憑一身好武藝功成名就。
可惜家世越好公子哥兒們的性子越嬌氣,不過梁家老爺子可不管,通不過他家收徒考試的,一律趕走。
傅品言出自京城景陽侯府,生母是姨娘,從小苦讀中了進士,兒子傅宸的脾性卻酷似故去的老侯爺,喜歡舞刀弄槍,偏偏傅宸又聰明,先把傅品言交代的功課都做好,不給父親挑剔的理由,然後就去翻自己搜羅來的「武功祕笈」練功。
傅品言見長子嗜武成癡,怕他瞎折騰傷了身,就給他請了武師父。去年一家人搬到冀州治所所在的信都城,恰逢梁家收徒,父子倆早聽說過梁家大名,立即攜禮去拜師,傅宸也爭氣,不但通過考核,更被梁老爺子收到門下,成了嫡傳弟子。
有了這層關係,梁、傅兩家很快交好,無形中幫傅品言早早在信都城站穩腳跟,讓城裏一些原打算送新任知府一些「見面禮」的地頭蛇礙於梁家名望不好動手。
當然,這是傅品言最看重的事,傅容一個小姑娘還不懂,她只覺得梁映芳熱情大方、坦率真誠,不像其他大家閨秀那樣做什麼都束手束腳,簡直對極了她的性子,兩人迅速成為好姊妹,平日裏傅容跟梁映芳一起玩的時候甚至比跟家裏兩個親姊妹多。
「別鬧了,沒看我病著呢。」即便是夢,因為太過真實,傅容真的覺得自己過了那樣的幾年,所以現在看梁映芳就好比故人重逢,高興極了,一點都不生氣,只笑盈盈看著她。
梁映芳警惕地看她兩眼,忽的挪遠了些,「笑得跟花似的,肯定沒安好心,是不是又在打什麼壞主意?」在她眼裏,傅容就是個小狐狸,雖然打不過自己,可傅容心眼多,總能在別的地方討回去,讓她吃虧。
受了冤枉,傅容起身就想打梁映芳兩下,抬手時忽的想到她剛剛的嘲諷,心中一動,高高抬起的手就放下了,趁梁映芳放下戒備時抱住她的胳膊,「映芳,等我養好病,妳教我泅水吧?」這次的事是個教訓,夢裏的災禍也是教訓,會了水以後總不至於淹死。
梁映芳好動,一聽這話馬上就應了,「好啊,咱們去我們家在紫薇山的莊子,那裏有溫泉,正好妳大病初癒,泡泡對身體好。」
傅容也很興奮,只可惜她真正的「大病初癒」,肯定要等一個月後了。
梁映芳走後,傅宛走了進來,見妹妹臉色紅潤,笑道:「見了好姊妹,病就好了大半是不是?」
「都是親姊姊照顧得好。」傅容抱著枕頭靠在床頭,甜甜地道:「客人都走了嗎?」
傅宛點點頭,倒了杯熱茶給妹妹,閒聊道:「齊夫人今早帶阿竺去保定探親沒空過來,只讓人送了禮,說回來再看妳,讓妳好好養病。」
齊家啊……傅容低頭吹茶,兩排濃密微翹的睫毛遮掩了眼中陰鬱。
齊家也是信都城裏的大戶,齊大老爺任陝西巡撫,留妻子兒女在老家信都城奉養老太太,兩家關係不錯,她跟同歲的齊竺也算手帕交,因此在那恍若前世的夢裏得知齊竺的哥哥齊策喜歡姊姊,她也樂見其成。
齊策英氣挺拔,姊姊溫婉秀麗,兩人不論才貌家世都極為相配,她還幫齊策在姊姊面前說了不少好話,姊姊漸漸心動,等齊策來提親時,姊姊羞澀地應了。
婚後兩人如膠似漆,等傅容自己嫁給徐晏的時候,姊姊有了身孕,可謂雙喜臨門,誰料沒過多久,姊姊的大丫鬟白芷也傳出喜訊,甚至跪到姊姊面前求姊姊准她生下那個孩子,直到那一刻,姊姊才知道白芷早就爬上了齊策的床。
換做發生在年少無知的自己身上,她定要大鬧一場,但姊姊只是命人給白芷灌落胎藥後發賣出去,齊策對此什麼都沒說。
齊夫人本想留下孩子,姊姊卻平靜地說她並非容不下姨娘,只是白芷是她的人,如今做出此等背主之事,她若不嚴加懲戒,以後可能會有更多的白芷,齊夫人便不再多言。
賣了白芷第二天,姊姊主動給齊策納了兩房姨娘,因有孕在身,姊姊不讓齊策再進她的房。
傅容去看姊姊時,姊姊什麼苦都不說,一副雲淡風輕的樣子,只問她跟徐晏相處得如何,又勸她好好跟徐晏過,但不要把整顆心都放在徐晏身上,這樣將來出了事才不會太傷心。她以為姊姊真的放下了,可幾個月後,姊姊難產而亡,一屍兩命。
這都是齊策的錯!男人有妾不算什麼,可他為何要動姊姊身邊的人?就算是白芷勾引他,他不會拒絕嗎?一邊是貼身丫鬟的狠心背叛,一邊是溫柔丈夫的虛情假意,雙重打擊下,姊姊哪可能淡然處之、毫不介意?
提親的時候說得天花亂墜,表示不讓姊姊受半點委屈,娶回家馬上就忘了。
這就是男人,一個個都是如此,半斤八兩。
等著吧,這次齊策休想再碰姊姊一根手指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