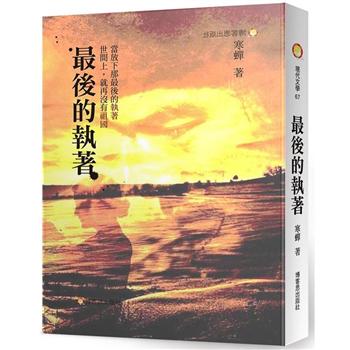第一章 亂世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餚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寫的雖是朝鮮之境,道是中國又有何不可?
一個大餅子,什麼時候可以換走一個大姑娘?
如今在韓家屯,足矣。
遠方山上還有一點紅霞,但已成弩末,黑暗正如海嘯般吞噬著大地。一隻螞蟻大的身影正向韓家屯這大海中的孤島爬去。
血跡斑駁的臉上,是一雙茫然的眼睛。散髮隨著腥風飄揚,下顎長滿了頹唐的鬍渣。破爛不堪的號衣下,是無盡的傷口和疲憊的軀體。
他叫岳冬。一個十八九歲,相貌平凡的清兵。
前方,應該是上百支洋槍。槍眼,應該是對準自己。白天看見是這樣的,只是天黑看不見吧?
回頭,兄弟們的身影已經消失在死寂的黑夜裡。汗流浹背。聽見的,只有自己紊亂的呼吸聲。岳冬當然知道,之前兩個去勸降的,屍首早已被掛在村口上。
但他不能不去。
岳冬背著一個插著白旗的包,輕輕地仰著臉,咬緊牙關,高舉雙手,只有四根指頭的左手緊緊地捏著一封信函,拖著沉重而抖顫的腳步步向韓家屯──一個如今附近村民聞之色變的地方。
叱吒一時,曾經走遍大江南北,官府多次圍剿無果,連慈禧太后也過問的匪首趙西來,如今正虎落平陽,被困於奉天金州以東兩百里的這個小城寨裡。
數千清兵把韓家屯圍個水泄不通,但就是不攻進去。裡邊的人,包括上千個村民,也不許出來。
就是這樣──耗著。
當然,官府的說法是──村民都被趙西來挾持了。
屯外放著兩大堆屍體:一堆散落一地,是雙方廝殺過後剩下的胡匪屍體。另一堆在屯的旁邊堆積如山,是屯裡餓死的被人扔出來的屍體。
三個月過去了,盛夏已至,一些已經腐爛見骨,血水一地。蒼蠅如雲,岳冬不停地用手和信函在耳邊亂撥。
「狗賊!我操你祖宗!……哇……」
看見地上的屍體,岳冬再次想起,那些旗兵是怎樣處死那些已經繳械投降的胡匪……
從山坡上往下看去,人都像螞蟻般小。岳冬只勉強看到有二十多個人跪著,全都被勇兵按住身體,辮子則被另一人往前拉,伸出脖子好讓劊子手幹活。
無論胡匪們如何掙扎,如何喊叫,他們的頭,始終一個一個地離開其身體。餘下的,開始連喊也放棄了,認命似的跪著,仿佛在盤算,早點投胎是否更划算。
沒人喊了,一切都歸於寂靜。時間久了,誰都沒有表情,如屠房裡宰殺畜牲一樣。鮮血,不過像捏破柚子肉所噴出來那丁點的汁液。一切,仿佛都是可有可無。
「他們……不是都投降了嗎?」作為新兵的岳冬聲音嘶嗄,雙目放空地看著遠方。
旁邊的奉軍副統領慕奇眼睛斜了斜,像是不屑他的婦人之仁:「投降就不是賊了嗎?幾百人哪!要是都把他們都關進大牢,誰給他們飯吃?」咬一口饅頭又說:「何況,他們是趙逆的人,壓根不可能有活路。」
岳冬心有不忍,扭頭對著慕奇說:「但殺了他們,以後還有誰會投降?」
慕奇不以為然,但略帶感慨道:「但不殺死那些想吃飽的……以後還有誰願意乖乖地挨餓啊?」接著把最後一口饅頭放進嘴裡,放眼遠方在看熱鬧但又呆若木雞的百姓。
岳冬心頭一震。
這三個月來,岳冬咬緊牙關,衝鋒陷陣,死裡求生,為的,就是回去見那日夜思念之人。
但,為什麼條件竟然是──把只求一條活路的人殺死?!
◐ ◐ ◐ ◑ ◑ ◑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要讓我們回去行不!」
「我跟你磕頭!我跟你磕頭!」
「裡邊都沒吃的了!」
「給我吃的,我把我兒子給你也行!」
那晚村民向著包圍他們的官兵跪地哀求一幕,再次在岳冬的腦海裡浮現。
「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見官兵們始終不說話,但又不讓自己離開,一個村民終於力竭聲嘶地喝問了一聲。
「誰讓你投胎到這兒?!」一個官兵終於回答,接著就是用槍托狠狠地砸下去。
岳冬雖然在遠處,那句話聽得不太清楚,但已經深深地紮在他內心深處。
誰,讓我們投胎到這兒了?
在養父口中,岳冬不知聽過多少遍,當兵,就是要「保家衛國」、「愛民如子」。的確,岳冬這幾年來都是跟隨養父驅趕胡匪、保衛百姓、賑災施粥、修橋補路……但,經歷了這三個月,如人間煉獄的三個月,岳冬開始明白,為什麼百姓看著自己的眼神總是那麼怪異,為什麼他們總是誠惶誠恐,為什麼他們會簞食壺漿以迎趙西來,為什麼趙西來每次把官兵殺掉,把屍首高懸示眾,有百姓要樂得放鞭炮……
其實,尋父十多年的他哪會忘記,當年自己的親生父親,不就是在他小時候被官兵捉走?
但他此刻絕不會想到,只要能把那些貪官污吏殺掉,只要能讓百姓不再受官府勞役和壓迫,只要能讓百姓吃上口飽飯,不管什麼人,千百年來只有天下,沒有國家的中國百姓,都會照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包括,半年後踏上這片土地的──日本人!
………
………
「金樽美酒千人血,玉盤佳餚萬姓膏。燭淚落時民淚落,歌聲高處怨聲高。」寫的雖是朝鮮之境,道是中國又有何不可?
一個大餅子,什麼時候可以換走一個大姑娘?
如今在韓家屯,足矣。
遠方山上還有一點紅霞,但已成弩末,黑暗正如海嘯般吞噬著大地。一隻螞蟻大的身影正向韓家屯這大海中的孤島爬去。
血跡斑駁的臉上,是一雙茫然的眼睛。散髮隨著腥風飄揚,下顎長滿了頹唐的鬍渣。破爛不堪的號衣下,是無盡的傷口和疲憊的軀體。
他叫岳冬。一個十八九歲,相貌平凡的清兵。
前方,應該是上百支洋槍。槍眼,應該是對準自己。白天看見是這樣的,只是天黑看不見吧?
回頭,兄弟們的身影已經消失在死寂的黑夜裡。汗流浹背。聽見的,只有自己紊亂的呼吸聲。岳冬當然知道,之前兩個去勸降的,屍首早已被掛在村口上。
但他不能不去。
岳冬背著一個插著白旗的包,輕輕地仰著臉,咬緊牙關,高舉雙手,只有四根指頭的左手緊緊地捏著一封信函,拖著沉重而抖顫的腳步步向韓家屯──一個如今附近村民聞之色變的地方。
叱吒一時,曾經走遍大江南北,官府多次圍剿無果,連慈禧太后也過問的匪首趙西來,如今正虎落平陽,被困於奉天金州以東兩百里的這個小城寨裡。
數千清兵把韓家屯圍個水泄不通,但就是不攻進去。裡邊的人,包括上千個村民,也不許出來。
就是這樣──耗著。
當然,官府的說法是──村民都被趙西來挾持了。
屯外放著兩大堆屍體:一堆散落一地,是雙方廝殺過後剩下的胡匪屍體。另一堆在屯的旁邊堆積如山,是屯裡餓死的被人扔出來的屍體。
三個月過去了,盛夏已至,一些已經腐爛見骨,血水一地。蒼蠅如雲,岳冬不停地用手和信函在耳邊亂撥。
「狗賊!我操你祖宗!……哇……」
看見地上的屍體,岳冬再次想起,那些旗兵是怎樣處死那些已經繳械投降的胡匪……
從山坡上往下看去,人都像螞蟻般小。岳冬只勉強看到有二十多個人跪著,全都被勇兵按住身體,辮子則被另一人往前拉,伸出脖子好讓劊子手幹活。
無論胡匪們如何掙扎,如何喊叫,他們的頭,始終一個一個地離開其身體。餘下的,開始連喊也放棄了,認命似的跪著,仿佛在盤算,早點投胎是否更划算。
沒人喊了,一切都歸於寂靜。時間久了,誰都沒有表情,如屠房裡宰殺畜牲一樣。鮮血,不過像捏破柚子肉所噴出來那丁點的汁液。一切,仿佛都是可有可無。
「他們……不是都投降了嗎?」作為新兵的岳冬聲音嘶嗄,雙目放空地看著遠方。
旁邊的奉軍副統領慕奇眼睛斜了斜,像是不屑他的婦人之仁:「投降就不是賊了嗎?幾百人哪!要是都把他們都關進大牢,誰給他們飯吃?」咬一口饅頭又說:「何況,他們是趙逆的人,壓根不可能有活路。」
岳冬心有不忍,扭頭對著慕奇說:「但殺了他們,以後還有誰會投降?」
慕奇不以為然,但略帶感慨道:「但不殺死那些想吃飽的……以後還有誰願意乖乖地挨餓啊?」接著把最後一口饅頭放進嘴裡,放眼遠方在看熱鬧但又呆若木雞的百姓。
岳冬心頭一震。
這三個月來,岳冬咬緊牙關,衝鋒陷陣,死裡求生,為的,就是回去見那日夜思念之人。
但,為什麼條件竟然是──把只求一條活路的人殺死?!
◐ ◐ ◐ ◑ ◑ ◑
「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不要讓我們回去行不!」
「我跟你磕頭!我跟你磕頭!」
「裡邊都沒吃的了!」
「給我吃的,我把我兒子給你也行!」
那晚村民向著包圍他們的官兵跪地哀求一幕,再次在岳冬的腦海裡浮現。
「我們究竟做錯了什麼?!」見官兵們始終不說話,但又不讓自己離開,一個村民終於力竭聲嘶地喝問了一聲。
「誰讓你投胎到這兒?!」一個官兵終於回答,接著就是用槍托狠狠地砸下去。
岳冬雖然在遠處,那句話聽得不太清楚,但已經深深地紮在他內心深處。
誰,讓我們投胎到這兒了?
在養父口中,岳冬不知聽過多少遍,當兵,就是要「保家衛國」、「愛民如子」。的確,岳冬這幾年來都是跟隨養父驅趕胡匪、保衛百姓、賑災施粥、修橋補路……但,經歷了這三個月,如人間煉獄的三個月,岳冬開始明白,為什麼百姓看著自己的眼神總是那麼怪異,為什麼他們總是誠惶誠恐,為什麼他們會簞食壺漿以迎趙西來,為什麼趙西來每次把官兵殺掉,把屍首高懸示眾,有百姓要樂得放鞭炮……
其實,尋父十多年的他哪會忘記,當年自己的親生父親,不就是在他小時候被官兵捉走?
但他此刻絕不會想到,只要能把那些貪官污吏殺掉,只要能讓百姓不再受官府勞役和壓迫,只要能讓百姓吃上口飽飯,不管什麼人,千百年來只有天下,沒有國家的中國百姓,都會照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包括,半年後踏上這片土地的──日本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