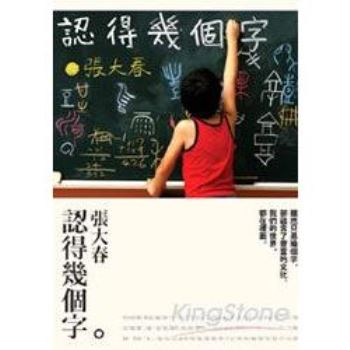命名
我所認識的幾個小孩子都曾經「虛構」過自己的朋友。朱天心的女兒謝海盟是其中佼佼者──她創造出來的小朋友「寶福」一直真實地活在父母的心裡,直到幼稚園畢業典禮那天,朱天心向老師打聽「寶福」的下落,甚至具體地描述了「寶福」的長相和性格特徵,所得到的回應居然是:「沒有這個孩子。」做媽媽的才明白:女兒發明了一個朋友,長達數年之久。
我自己的女兒給他的娃娃取名叫「蔡佳佳」,蔡佳佳的妹妹(一個長相一樣而體型較小的娃娃)則取名叫「蔡花」。我和她討論了很久,終於說服他:「蔡花」這個名子不太好聽,她讓步的底線是可以換成「蔡小花」,可是不能沒有「花」。理由很簡單:已經決定的事情不能隨便更改。「蔡小花很在意這種事情!」──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小分別:雖然「蔡花」祇不過是個玩偶,而「蔡小花」已經具備了充分完足的性格。
就在這一對姊妹剛加入我們的生活圈的這一段期間,女兒對她自己的名字「張宜」也開始不滿起來。有一天她忽然問我:「『ㄆˊㄠ』這個字怎麼寫?」我說看意思是甚麼,有幾個不同的寫法,於是順手寫了「袍」、「刨」、「庖」、「咆」,也解釋了每個字的意思。她問得很仔細,每個字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後慎重地指著「庖丁」的「庖」說:「這個字還不錯,就是這個字好了。」
「這個字怎麼樣了?」
「就是我的新名字呀!」
「你要叫『張庖」嗎?那樣好聽嗎?」我誇張地搖著頭、皺著眉,想要再使出對付「蔡花」的那一招。
「誰要姓『張』呀?我要姓『庖』,我要叫『庖子宜』。」
她哥哥張容這時在一旁聳聳肩,說:「那是因為我先給我自己取名字叫『跑庖』,所以她才一定要這樣的,沒辦法。」
「我給你取的名字不好嗎?」我已經開始覺得有點委屈了。
「我喜歡跑步呀,你給我取的名字裡面又沒有跑步,我只好自己取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呀!」
我祇好說「庖」不算是一個姓氏,勉強要算,祇能算是「庖犧」(廚房裡殺牛?)這個姓氏的一半。
「『廚房裡殺牛』這個姓也不錯呀?總比『張』好吧?」張容說。
「我姓張,你們也應該姓張,我們都是張家門的人。」
「我不要。」妹妹接著說:「我的娃娃也不姓張,她姓蔡,我也一樣很愛她呀。姓甚麼跟我們是不是一家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媽媽也不姓張。」
他們談的問題──在過去幾千年以來──換個不同的場域,就是宗法、是傳承、是家國起源、是千古以來為了區處內外、鞏固本根、以及分別敵我而必爭必辨的大計。然而用他們這樣的說法,好像意義完全消解了。
「你也可以跟我們一樣姓庖呀?」妹妹說。
「你就叫『庖哥』好了,這個名字蠻適合你的。」哥哥說。
「對呀!蠻適和你的。」庖子宜接腔做成了結論。
揍
幾十年前,毎當我仰著頭,跟父親問起我爺爺這個人的任何事,他總說得極簡略,末了還補一句:「我跟他關係不好,說甚麼都不對的。」這話使我十分受用,起碼在教訓兒子的時候不免想到:這小子將來也要養而育女的,萬一我孫子孫女問起我來,得到的答案跟我父親的言詞一致,那麼,我這一輩應該就算是白活了。
可即使再小心謹慎,在管教兒女這件事上,必有大不可忍之時。人都說孩子打不得,吼吼總還稱得上是聊表心意;然而我現在連吼兩聲都有「憮然內慚」之感,儘管有著極其嚴正的管教目的,也像是在欺凌幼弱,自覺面目猙獰得可以。如果有那麼一天,驀然回首,發現居然有一整個禮拜沒吼過孩子,就會猛可心生竊喜:莫不是自己的修養又暗暗提升了一個境界?
吼孩子當然意味著警告,我的父親在動手修理我之前慣用的詞兒是:「我看你是差不多了。」在這之前是「你是有點兒過意不去了,我看。」在這之前則是:「叫你媽說這就是要捱揍了。」三部曲,從來沒有換過或是錯亂過台詞。至於我母親,沒有那麼多廢話,她就是一句:「你要我開戒了嗎?」
有一回我母親拿板子開了戒,我父親手扠著腰在一旁看熱鬧,過後把我叫到屋後小天井裡,拉把凳子叫我坐了,說:「揍你也是應該,咱們鄉里人說話,『誰不是人生父母揍的?』揍就是生養的意思,懂嗎?」鄉里人說話沒講究,同音字互用到無法無天的地步,沒聽說過嗎──「大過年的,給孩子揍兩件新衣服穿。」無論如何,揍,不是一個簡單的字。
捱板子當下,我肯定不服氣。可後來讀曹禺的《日出》,在第三幕上,還真讀到了這麼個說法:「你今兒要不打死我,你就不是你爸爸揍的!」翻翻《集韻》就明白,鄉里人不是沒學問才這麼說話:「揍,插也。」
唸書時讀宋元戲文,偶爾也會看見這個「揍」字。在古代的劇本裡,這是一種表演提示,意思就是一個角色緊接著另一個角色唱了一半兒的腔接唱,由於必須接得很緊密,又叫「插唱」。仔細推敲,這「插」的字義又跟「輻輳」、「湊集」的意思相關。
試想:輪圈兒裡一條條支撐的直木叫「輻」,「輻」畢集於車輪中心的「轂」,這個聚集的狀態就叫「輳」,的確也帶來一種「插入」的感覺。如此體會,曹禺那句「你就不是你爸爸揍的!」別有深意──卻不方便跟年紀幼小的孩子解釋得太明白──可別說我想歪了,鄉里之人運用的那個「揍」字,的確就是「插入」的意思。「插入」何解?應該不必進一步說明了。
正因為這「揍」字還有令教養完足之士不忍說道的含意,所以漸漸地,在我們家裡也就不大用這話,偶爾地聽見孩子們教訓他們的娃娃玩偶,用的居然是這樣的話:「再不聽話就要開扁了!」不過,語言是活的,誰知道這「開扁」之詞,日後會不會也被當成髒話呢?
黑
今天這篇文字會讓我想到薇薇夫人或是馬它;如果讀者不知道這兩位是誰,可以繼續看下去。
我在部落格上收到一封信,大意如此:
有個很迫切的問題想請教你。我兒子已十個月大,即將進入牙牙學語的階段,在民進黨政府急欲去中國化的情況下,我很擔心將來我兒子的中文一塌糊塗。我知道你對培養自己小孩的文學基礎有一套方法;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讀物,可否請你詳細的告訴我:從現在開始,到小學前,我該如何在每個階段讓小孩分別接觸哪些書?每階段不同書的順序又是如何?拜託了,大春兄。謝謝啦!一個憂心小孩將來忘根的父親。
我的答覆是這樣的:
「每個家庭的焦慮程度不同,我說不上來該有甚麼值得提供給任何非我家人的朋友應該幹嘛的建議。因為連我自己對於我的老婆孩子的中文程度該如何?或者是該提供給他們甚至我自己一些甚麼樣的教育?我都說不上來。
「在我自己家裡,就祇一樣跟許多人家不同,那就是我們有長達兩個小時的晚餐時間。全家一起說話。大人孩子分享共同的話題。有很多時候,我會隨機運用當天的各種話題,設計孩子們能夠吸收而且應該理解的知識。最重要的是在提出那學習的問題之前,我並不知道他們想學甚麼?不想學甚麼?該學甚麼?不該學甚麼?
「忽然有一天,我兒子問我:『你覺得這個世界上佔最多的顏色是甚麼?』我想了一會兒,說:『是黑色罷?』我兒子立刻點點頭說:『對了!你說的應該沒錯。這個宇宙大部分的地方是黑的。』他剛滿七歲,小一生,我從來沒有跟他談過『黑暗物質』、『黑暗能量』,也不認為他讀過那樣的書。但是那天我很高興,不是因為他說的對──也許我對宇宙的瞭解還不夠資格說他對或不對──但是我有資格說:他開始思考宇宙問題的習慣,真讓我感動。
「重要的不是中文程度、或任何一科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哪一本書、或哪些是非讀不可的好書,重要的是你和你的孩子能不能一頓晚飯吃兩個鐘頭,無話不談──而且就從他想學說話的時候開始。」
看到這裡,如果讀者諸君還是不知道薇薇夫人或馬它是誰,就表示你年輕得不必擔心教養問題了。薇薇夫人和馬它是我最早接觸到在媒體上公開解答他人生活疑難的專欄作家。從情感、家庭、職場到化妝、保養和健身,多年以來,她們一定幫助過不少人。
但是所有的生活疑難總在降臨之際重新折磨一個人。我其實沒有回答那位憂心小孩忘根的父親,我恐怕也不能回答任何一個總體上關於文化教養的問題。而且,就在我回貼之後立刻有瞭解我素行如何的知音人前來提醒:「有機會跟兒子說話時注意自己的談吐水準和內容,孩子是麵糰,家長是印模,久之自會從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模印成績。」
宇宙是黑的,想它時偶而會他媽的發亮。
張容的第一首詩:
「你們留下了」──給畢業班的學長和學姊
你們就要離開了
可是你們卻留下了
你們留下了校園
留下了教室
留下了課桌椅和黑板
還有親愛的老師
你們就要離開了
可是你們卻留下了
你們留下了歌聲
留下了笑聲
留下了吵鬧和讀書聲
還有離別的祝福
我所認識的幾個小孩子都曾經「虛構」過自己的朋友。朱天心的女兒謝海盟是其中佼佼者──她創造出來的小朋友「寶福」一直真實地活在父母的心裡,直到幼稚園畢業典禮那天,朱天心向老師打聽「寶福」的下落,甚至具體地描述了「寶福」的長相和性格特徵,所得到的回應居然是:「沒有這個孩子。」做媽媽的才明白:女兒發明了一個朋友,長達數年之久。
我自己的女兒給他的娃娃取名叫「蔡佳佳」,蔡佳佳的妹妹(一個長相一樣而體型較小的娃娃)則取名叫「蔡花」。我和她討論了很久,終於說服他:「蔡花」這個名子不太好聽,她讓步的底線是可以換成「蔡小花」,可是不能沒有「花」。理由很簡單:已經決定的事情不能隨便更改。「蔡小花很在意這種事情!」──這裡有一個值得注意的小分別:雖然「蔡花」祇不過是個玩偶,而「蔡小花」已經具備了充分完足的性格。
就在這一對姊妹剛加入我們的生活圈的這一段期間,女兒對她自己的名字「張宜」也開始不滿起來。有一天她忽然問我:「『ㄆˊㄠ』這個字怎麼寫?」我說看意思是甚麼,有幾個不同的寫法,於是順手寫了「袍」、「刨」、「庖」、「咆」,也解釋了每個字的意思。她問得很仔細,每個字都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後慎重地指著「庖丁」的「庖」說:「這個字還不錯,就是這個字好了。」
「這個字怎麼樣了?」
「就是我的新名字呀!」
「你要叫『張庖」嗎?那樣好聽嗎?」我誇張地搖著頭、皺著眉,想要再使出對付「蔡花」的那一招。
「誰要姓『張』呀?我要姓『庖』,我要叫『庖子宜』。」
她哥哥張容這時在一旁聳聳肩,說:「那是因為我先給我自己取名字叫『跑庖』,所以她才一定要這樣的,沒辦法。」
「我給你取的名字不好嗎?」我已經開始覺得有點委屈了。
「我喜歡跑步呀,你給我取的名字裡面又沒有跑步,我只好自己取了。這也是沒辦法的事呀!」
我祇好說「庖」不算是一個姓氏,勉強要算,祇能算是「庖犧」(廚房裡殺牛?)這個姓氏的一半。
「『廚房裡殺牛』這個姓也不錯呀?總比『張』好吧?」張容說。
「我姓張,你們也應該姓張,我們都是張家門的人。」
「我不要。」妹妹接著說:「我的娃娃也不姓張,她姓蔡,我也一樣很愛她呀。姓甚麼跟我們是不是一家人一點關係也沒有。媽媽也不姓張。」
他們談的問題──在過去幾千年以來──換個不同的場域,就是宗法、是傳承、是家國起源、是千古以來為了區處內外、鞏固本根、以及分別敵我而必爭必辨的大計。然而用他們這樣的說法,好像意義完全消解了。
「你也可以跟我們一樣姓庖呀?」妹妹說。
「你就叫『庖哥』好了,這個名字蠻適合你的。」哥哥說。
「對呀!蠻適和你的。」庖子宜接腔做成了結論。
揍
幾十年前,毎當我仰著頭,跟父親問起我爺爺這個人的任何事,他總說得極簡略,末了還補一句:「我跟他關係不好,說甚麼都不對的。」這話使我十分受用,起碼在教訓兒子的時候不免想到:這小子將來也要養而育女的,萬一我孫子孫女問起我來,得到的答案跟我父親的言詞一致,那麼,我這一輩應該就算是白活了。
可即使再小心謹慎,在管教兒女這件事上,必有大不可忍之時。人都說孩子打不得,吼吼總還稱得上是聊表心意;然而我現在連吼兩聲都有「憮然內慚」之感,儘管有著極其嚴正的管教目的,也像是在欺凌幼弱,自覺面目猙獰得可以。如果有那麼一天,驀然回首,發現居然有一整個禮拜沒吼過孩子,就會猛可心生竊喜:莫不是自己的修養又暗暗提升了一個境界?
吼孩子當然意味著警告,我的父親在動手修理我之前慣用的詞兒是:「我看你是差不多了。」在這之前是「你是有點兒過意不去了,我看。」在這之前則是:「叫你媽說這就是要捱揍了。」三部曲,從來沒有換過或是錯亂過台詞。至於我母親,沒有那麼多廢話,她就是一句:「你要我開戒了嗎?」
有一回我母親拿板子開了戒,我父親手扠著腰在一旁看熱鬧,過後把我叫到屋後小天井裡,拉把凳子叫我坐了,說:「揍你也是應該,咱們鄉里人說話,『誰不是人生父母揍的?』揍就是生養的意思,懂嗎?」鄉里人說話沒講究,同音字互用到無法無天的地步,沒聽說過嗎──「大過年的,給孩子揍兩件新衣服穿。」無論如何,揍,不是一個簡單的字。
捱板子當下,我肯定不服氣。可後來讀曹禺的《日出》,在第三幕上,還真讀到了這麼個說法:「你今兒要不打死我,你就不是你爸爸揍的!」翻翻《集韻》就明白,鄉里人不是沒學問才這麼說話:「揍,插也。」
唸書時讀宋元戲文,偶爾也會看見這個「揍」字。在古代的劇本裡,這是一種表演提示,意思就是一個角色緊接著另一個角色唱了一半兒的腔接唱,由於必須接得很緊密,又叫「插唱」。仔細推敲,這「插」的字義又跟「輻輳」、「湊集」的意思相關。
試想:輪圈兒裡一條條支撐的直木叫「輻」,「輻」畢集於車輪中心的「轂」,這個聚集的狀態就叫「輳」,的確也帶來一種「插入」的感覺。如此體會,曹禺那句「你就不是你爸爸揍的!」別有深意──卻不方便跟年紀幼小的孩子解釋得太明白──可別說我想歪了,鄉里之人運用的那個「揍」字,的確就是「插入」的意思。「插入」何解?應該不必進一步說明了。
正因為這「揍」字還有令教養完足之士不忍說道的含意,所以漸漸地,在我們家裡也就不大用這話,偶爾地聽見孩子們教訓他們的娃娃玩偶,用的居然是這樣的話:「再不聽話就要開扁了!」不過,語言是活的,誰知道這「開扁」之詞,日後會不會也被當成髒話呢?
黑
今天這篇文字會讓我想到薇薇夫人或是馬它;如果讀者不知道這兩位是誰,可以繼續看下去。
我在部落格上收到一封信,大意如此:
有個很迫切的問題想請教你。我兒子已十個月大,即將進入牙牙學語的階段,在民進黨政府急欲去中國化的情況下,我很擔心將來我兒子的中文一塌糊塗。我知道你對培養自己小孩的文學基礎有一套方法;在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讀物,可否請你詳細的告訴我:從現在開始,到小學前,我該如何在每個階段讓小孩分別接觸哪些書?每階段不同書的順序又是如何?拜託了,大春兄。謝謝啦!一個憂心小孩將來忘根的父親。
我的答覆是這樣的:
「每個家庭的焦慮程度不同,我說不上來該有甚麼值得提供給任何非我家人的朋友應該幹嘛的建議。因為連我自己對於我的老婆孩子的中文程度該如何?或者是該提供給他們甚至我自己一些甚麼樣的教育?我都說不上來。
「在我自己家裡,就祇一樣跟許多人家不同,那就是我們有長達兩個小時的晚餐時間。全家一起說話。大人孩子分享共同的話題。有很多時候,我會隨機運用當天的各種話題,設計孩子們能夠吸收而且應該理解的知識。最重要的是在提出那學習的問題之前,我並不知道他們想學甚麼?不想學甚麼?該學甚麼?不該學甚麼?
「忽然有一天,我兒子問我:『你覺得這個世界上佔最多的顏色是甚麼?』我想了一會兒,說:『是黑色罷?』我兒子立刻點點頭說:『對了!你說的應該沒錯。這個宇宙大部分的地方是黑的。』他剛滿七歲,小一生,我從來沒有跟他談過『黑暗物質』、『黑暗能量』,也不認為他讀過那樣的書。但是那天我很高興,不是因為他說的對──也許我對宇宙的瞭解還不夠資格說他對或不對──但是我有資格說:他開始思考宇宙問題的習慣,真讓我感動。
「重要的不是中文程度、或任何一科的程度,重要的也不是哪一本書、或哪些是非讀不可的好書,重要的是你和你的孩子能不能一頓晚飯吃兩個鐘頭,無話不談──而且就從他想學說話的時候開始。」
看到這裡,如果讀者諸君還是不知道薇薇夫人或馬它是誰,就表示你年輕得不必擔心教養問題了。薇薇夫人和馬它是我最早接觸到在媒體上公開解答他人生活疑難的專欄作家。從情感、家庭、職場到化妝、保養和健身,多年以來,她們一定幫助過不少人。
但是所有的生活疑難總在降臨之際重新折磨一個人。我其實沒有回答那位憂心小孩忘根的父親,我恐怕也不能回答任何一個總體上關於文化教養的問題。而且,就在我回貼之後立刻有瞭解我素行如何的知音人前來提醒:「有機會跟兒子說話時注意自己的談吐水準和內容,孩子是麵糰,家長是印模,久之自會從孩子身上看到自己的模印成績。」
宇宙是黑的,想它時偶而會他媽的發亮。
張容的第一首詩:
「你們留下了」──給畢業班的學長和學姊
你們就要離開了
可是你們卻留下了
你們留下了校園
留下了教室
留下了課桌椅和黑板
還有親愛的老師
你們就要離開了
可是你們卻留下了
你們留下了歌聲
留下了笑聲
留下了吵鬧和讀書聲
還有離別的祝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