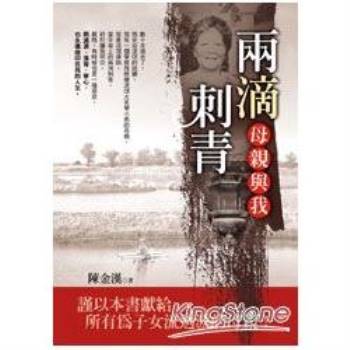1.愧疚
不聽話的淚水把母親蒼白的病容映得模糊,深怕母親發覺,趕緊側臉躲開她的視線,但從她眼角滑落的淚水,我深深明白,縱使她閉著雙眼,都可以把我讀得清清楚楚。
時間的河,總在年少催趕時徐緩而行,中年奮鬥時疾疾而行,老邁殘燭時箭穿而行,臨盡頭前,才讓人驚覺到它是如此湍急,快速得令人抓不住,偶爾抓得,卻已到了盡頭,回首,已錯過太多太多了。
記憶中,三十年來,母親總共經歷過四次住院開刀手術,二○○九年八月八日(八八風災那一日),母親又住進大林慈濟醫院,進行人工膝關節更換手術。
以台灣醫療水平,人工膝關節手術已不算大手術,但,這一次令我感到不安,畢竟,母親已高齡八十三歲,即使是個小感冒、小跌跤,都可能是死神的挑釁,更遑論是開刀手術。
一開完庭,立刻驅車南下,沿路風強雨驟,心急路遠,到達醫院時已是向晚黃昏。
離家卅二年,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為了跳脫兒時窮困的記憶,忙忙碌碌,汲汲營營,不斷努力的賺錢,彷彿只有財富才能架構自己完整的人生。
當一推開病房門,看見母親腫黑的腳、綣縮的身軀、如紙蒼白的臉,以及那幾乎睜不開眼的病容,才恍悟,自己已在世俗財富追逐中掛漏了人生最該珍惜的,遺失了早該拾取的,悄悄地,歲月已在不察間,催索著這幾十年來自己在母親身上所積欠的一切,而某些人生的價值觀,也已在自己的盲目中嚴重的扭曲,錯過的,已經太多了。
緊握著母親癱軟的手,貼耳輕喚,一聲一聲地,只見母親眼微睜,略顯凹陷的唇頰輕顫,欲言乏力,俟嫂嫂為她裝上假牙,才吃力的擠出一句:「吃飽沒?」多麼令人割心不捨的一幕。幾十年來,每次見面都是相同的第一句話,始終停留在那衣無暖、食無飽的年代,把我們當成三歲小孩,深怕孩子們挨餓受凍。
而此時,不聽話的淚水已把母親蒼白的病容映得模糊,深怕母親發覺,趕緊側臉躲開她的視線,但從她眼角滑落的淚水,我深深明白,縱使她閉上雙眼,都可以把我讀得清清楚楚。
淚無語,語無聲。如果可以,多麼希望自己能夠替代她所有的苦和所有的痛。
臨回台北前,母親精神稍稍好轉,她緊握我的手說道:「颱風天,哥哥嫂嫂們都在,不是叫你不用下來。」但從牢抓不放的手,我感受到母親的寬慰,也看穿母親的口是心非,畢竟,母子連心。
回程路上,車窗掠影,自忖思索著,母親守寡單親四十年,一路從艱辛的歲月中走來,為六個孩子,為撐起一個家,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健康……,除了靈肉,付出了女人一生所能付出的一切,而我,又曾為母親做了些什麼?
一路上努力地回想,除了添憂惹煩,這一生,竟未曾為母親做過任何一件讓人刻骨銘心的事,而我,是兄弟姊妹六人中最被寵遇的,享盡榮寵,卻未曾盡一分孝責,除了愧疚,仍是很深很深的愧疚。
回到台北,一進家門,沒有開燈,癱坐沙發,彷如漆黑是這些年來我為自己與母親間所上過的唯一色彩,她窮盡一生給我豐足,我卻貧乏空無的回報,這一夜,浸蝕在黑無中,希望讓空洞失孝的靈魂,能在驚惶悔恨中任憑黑暗吞噬,而後啟迪重生,再引一線光,再開一扇窗,彌補曾經的掛漏。
白鴿奉獻給藍天,星光奉獻給長夜,而我,拿什麼奉獻給母親?我在黑暗中捫心自問著。
金錢,是母親一輩子的缺欠,賣牛葬夫和不斷賒欠舉債的日子,母親前半輩子都纏繞在窮困中,而今,金錢對母親而言,已毫無意義。
思索的瞬間,突然明白地領悟到,母親一生,所有的幸與不幸,所有的滿足與欠缺,都在那幾分薄田中;所有的勞苦和努力,所有的血與淚,為的只不過是生活中的柴米油鹽,也簡單得只是養兒育女中的甘甘苦苦,單調的人生,坎坷的歲月,孤苦的靈魂。
我能為母親做些什麼?就以拙筆,為她寫寫那單調孤苦的草木人生吧!
8.兩滴刺青
為什麼不問對錯?為什麼要打給人家看?為什麼窮人家就要過得如此卑微?為什麼母親的生活總是逃不出父親的死?而我和妹妹的童年總是躲不過母親的淚?
走過的童年,不論貧富,不論苦樂,是每個人一生中最回味的一部分,也是每個人歲月的起站。
十歲那年,我的背上多了一道刺青!
那年的某個黃昏,所有鄰居的小孩結群嬉鬧,最後大家以馬路為河,兩旁的矮牆為界,楚漢分國,玩起擲土丟石,外加砸泥巴的打仗遊戲,頓時,開啟了一場大混戰,每個人時而英勇衝鋒,深入敵營,時而鼠輩躲藏,正興高烈采難分難解時,敵營有個小女孩右額遭亂石擊中,鮮血如注,見狀,混亂中,所有小孩四散流竄,我亦若無其事的走回家,若無其事的寫功課,也若無其事的晚餐,但小腦袋中不時浮映著小女孩那張噴血的哭臉。
晚飯後,聽到母親與人在屋外大埕的交談聲,深覺不祥之兆。
突然,母親急喚我,我故作鎮定地慢走到母親身旁,母親厲色斥問:「為何拿石頭砸人?」我急回:「又不是……。」語未畢,母親一箭步,巴掌已落在我左臉頰。鄰婦不悅的補上:「還說沒有,所有小孩都有看到,如果砸到眼睛不就變瞎子,這麼小就愛說謊,大了還得了。」
母親聽完再問一次,我低頭咬牙不語,母親一巴掌又落下,接著一連數問,一問一掌,一掌一問,我感到臉頰又痛又熱,沒有哭,狠瞪小女生一眼,小女孩緊拉鄰婦衣角,急縮到婦人背後。
母親急急回到廚房,拿了那根賣牛後留下的籐條直指著我:「再問你一次,有沒有?」我依然咬牙不語,母親的籐條重重的落在我的小腿上,我仍沒哭,不語不屈。
母親終於抓狂了:「你老爸早死,才會沒人教示,才會變款,不說就打到說。」邊說邊抽打,很有節奏感。
嬸嬸急忙趕來勸阻,鄰婦見狀,即提高假同情的聲音:「氆啊!都是小孩在玩嘛,誤傷難免,都流血了,不要再打了。」隨即帶著小女孩得意的離去,嬸嬸背向母親護抱著我。
母親丟下籐條,氣哭著走回屋內。
終於再也忍不住,我放聲大哭在嬸嬸懷裡,斷續啜泣地說著:「又…不是我,又不是我。」嬸嬸連聲的安慰著:「不要哭了,我知道不是你,我知道,以後乖一點就好,乖,不要再哭了。」
洗澡時,小腿刺痛得令人想再哭一場,擦拭時,感覺得到兩邊臉頰明顯一大一小,和小腿上紅腫滲血的藤條印,緩緩抹去鏡上的白霧,小小年紀,心中充滿怨恨,眼神中充滿著怒與火,恨透了那個誣告的小女孩,恨透了那個得意的鄰婦,也恨透了母親的不分青紅皂白。
從那次以後,我不再和那小女孩講話,不再到那戶人家去看電視,也負氣地和母親冷戰了好幾天。
晚上,獨坐在簷下小凳上,無語,只是撫腿摸臉自憐,仍感痛與熱,任誰叫我都不應,學著母親,把空洞的眼神盯落在黑暗中的遠方,若有似無地,想著那血臉的女孩,得意的鄰婦,嚴刑逼供的母親,和丟在一旁的那根大籐條。
回過神,驚見母親蹲靠一旁,拿著一盒褐黑色的藥膏要幫我敷藥,我噘嘴假裝沒看到,俟母親一伸過手來,我以手推開,藥盒滑落,母親起身側臉站著,沒罵我,沒看我,也沒安慰我,許久許久,時空頓時凝結,沒有半句話,等母親彎腰撿起藥盒轉頭離去時,我看見母親含淚的眼。
睡夢中,突然有一隻手,輕撫我腫痛的左臉頰和左小腿,輕輕側翻我的身子,我假裝沒醒來,憑觸覺就知道那是母親的手,邊敷藥邊說著:「人家是有錢有勢的小千金,我們不同,要認份,玩到沒分沒寸,玩到人家侵門踏戶來理論,我總是要打給人家看才行,你自己也逞強,不管有沒有,早承認就不必多討打,嘴硬就是找死,你若有聽到,以後就要記得,不要讓人家說你老爸早死,孩子就沒規矩、沒教養。」哽咽中,兩滴淚滑落在我側身的背上。
等母親離去,我掩被縮曲著全身,雙手摀臉痛哭,小小年紀,再一次地痛恨著一切。
為什麼不問對錯?為什麼有沒有都要早承認?為什麼要打給人家看?為什麼窮人家就要過得如此卑微?為什麼母親的生活總是逃不出父親的死?而我和妹妹的童年總是躲不過母親的淚?
明明是暮春轉夏的季節,天氣應該是溫暖的,我的心卻因為背上母親的淚而降到冰點。背上的兩滴淚,好比浪子的刺青,有痛、有恨、有淚、也有後悔,是縮影,也是宣示的圖騰。
兩滴淚,落背,穿心,也永遠烙印在我的人生。
而今,數十年過去了,我來自於流氓的故鄉,我有一個管教我就像流氓大哥管小弟的母親,我是流氓律師,當年背上的兩滴刺青,終於讓我明白,沒有揭開女人心中最深的那一層紗,你根本無法分辨好女人與壞女人,嚴格,有時候也是一種慈悲。
不聽話的淚水把母親蒼白的病容映得模糊,深怕母親發覺,趕緊側臉躲開她的視線,但從她眼角滑落的淚水,我深深明白,縱使她閉著雙眼,都可以把我讀得清清楚楚。
時間的河,總在年少催趕時徐緩而行,中年奮鬥時疾疾而行,老邁殘燭時箭穿而行,臨盡頭前,才讓人驚覺到它是如此湍急,快速得令人抓不住,偶爾抓得,卻已到了盡頭,回首,已錯過太多太多了。
記憶中,三十年來,母親總共經歷過四次住院開刀手術,二○○九年八月八日(八八風災那一日),母親又住進大林慈濟醫院,進行人工膝關節更換手術。
以台灣醫療水平,人工膝關節手術已不算大手術,但,這一次令我感到不安,畢竟,母親已高齡八十三歲,即使是個小感冒、小跌跤,都可能是死神的挑釁,更遑論是開刀手術。
一開完庭,立刻驅車南下,沿路風強雨驟,心急路遠,到達醫院時已是向晚黃昏。
離家卅二年,尤其是近二十年來,為了跳脫兒時窮困的記憶,忙忙碌碌,汲汲營營,不斷努力的賺錢,彷彿只有財富才能架構自己完整的人生。
當一推開病房門,看見母親腫黑的腳、綣縮的身軀、如紙蒼白的臉,以及那幾乎睜不開眼的病容,才恍悟,自己已在世俗財富追逐中掛漏了人生最該珍惜的,遺失了早該拾取的,悄悄地,歲月已在不察間,催索著這幾十年來自己在母親身上所積欠的一切,而某些人生的價值觀,也已在自己的盲目中嚴重的扭曲,錯過的,已經太多了。
緊握著母親癱軟的手,貼耳輕喚,一聲一聲地,只見母親眼微睜,略顯凹陷的唇頰輕顫,欲言乏力,俟嫂嫂為她裝上假牙,才吃力的擠出一句:「吃飽沒?」多麼令人割心不捨的一幕。幾十年來,每次見面都是相同的第一句話,始終停留在那衣無暖、食無飽的年代,把我們當成三歲小孩,深怕孩子們挨餓受凍。
而此時,不聽話的淚水已把母親蒼白的病容映得模糊,深怕母親發覺,趕緊側臉躲開她的視線,但從她眼角滑落的淚水,我深深明白,縱使她閉上雙眼,都可以把我讀得清清楚楚。
淚無語,語無聲。如果可以,多麼希望自己能夠替代她所有的苦和所有的痛。
臨回台北前,母親精神稍稍好轉,她緊握我的手說道:「颱風天,哥哥嫂嫂們都在,不是叫你不用下來。」但從牢抓不放的手,我感受到母親的寬慰,也看穿母親的口是心非,畢竟,母子連心。
回程路上,車窗掠影,自忖思索著,母親守寡單親四十年,一路從艱辛的歲月中走來,為六個孩子,為撐起一個家,付出了青春,付出了健康……,除了靈肉,付出了女人一生所能付出的一切,而我,又曾為母親做了些什麼?
一路上努力地回想,除了添憂惹煩,這一生,竟未曾為母親做過任何一件讓人刻骨銘心的事,而我,是兄弟姊妹六人中最被寵遇的,享盡榮寵,卻未曾盡一分孝責,除了愧疚,仍是很深很深的愧疚。
回到台北,一進家門,沒有開燈,癱坐沙發,彷如漆黑是這些年來我為自己與母親間所上過的唯一色彩,她窮盡一生給我豐足,我卻貧乏空無的回報,這一夜,浸蝕在黑無中,希望讓空洞失孝的靈魂,能在驚惶悔恨中任憑黑暗吞噬,而後啟迪重生,再引一線光,再開一扇窗,彌補曾經的掛漏。
白鴿奉獻給藍天,星光奉獻給長夜,而我,拿什麼奉獻給母親?我在黑暗中捫心自問著。
金錢,是母親一輩子的缺欠,賣牛葬夫和不斷賒欠舉債的日子,母親前半輩子都纏繞在窮困中,而今,金錢對母親而言,已毫無意義。
思索的瞬間,突然明白地領悟到,母親一生,所有的幸與不幸,所有的滿足與欠缺,都在那幾分薄田中;所有的勞苦和努力,所有的血與淚,為的只不過是生活中的柴米油鹽,也簡單得只是養兒育女中的甘甘苦苦,單調的人生,坎坷的歲月,孤苦的靈魂。
我能為母親做些什麼?就以拙筆,為她寫寫那單調孤苦的草木人生吧!
8.兩滴刺青
為什麼不問對錯?為什麼要打給人家看?為什麼窮人家就要過得如此卑微?為什麼母親的生活總是逃不出父親的死?而我和妹妹的童年總是躲不過母親的淚?
走過的童年,不論貧富,不論苦樂,是每個人一生中最回味的一部分,也是每個人歲月的起站。
十歲那年,我的背上多了一道刺青!
那年的某個黃昏,所有鄰居的小孩結群嬉鬧,最後大家以馬路為河,兩旁的矮牆為界,楚漢分國,玩起擲土丟石,外加砸泥巴的打仗遊戲,頓時,開啟了一場大混戰,每個人時而英勇衝鋒,深入敵營,時而鼠輩躲藏,正興高烈采難分難解時,敵營有個小女孩右額遭亂石擊中,鮮血如注,見狀,混亂中,所有小孩四散流竄,我亦若無其事的走回家,若無其事的寫功課,也若無其事的晚餐,但小腦袋中不時浮映著小女孩那張噴血的哭臉。
晚飯後,聽到母親與人在屋外大埕的交談聲,深覺不祥之兆。
突然,母親急喚我,我故作鎮定地慢走到母親身旁,母親厲色斥問:「為何拿石頭砸人?」我急回:「又不是……。」語未畢,母親一箭步,巴掌已落在我左臉頰。鄰婦不悅的補上:「還說沒有,所有小孩都有看到,如果砸到眼睛不就變瞎子,這麼小就愛說謊,大了還得了。」
母親聽完再問一次,我低頭咬牙不語,母親一巴掌又落下,接著一連數問,一問一掌,一掌一問,我感到臉頰又痛又熱,沒有哭,狠瞪小女生一眼,小女孩緊拉鄰婦衣角,急縮到婦人背後。
母親急急回到廚房,拿了那根賣牛後留下的籐條直指著我:「再問你一次,有沒有?」我依然咬牙不語,母親的籐條重重的落在我的小腿上,我仍沒哭,不語不屈。
母親終於抓狂了:「你老爸早死,才會沒人教示,才會變款,不說就打到說。」邊說邊抽打,很有節奏感。
嬸嬸急忙趕來勸阻,鄰婦見狀,即提高假同情的聲音:「氆啊!都是小孩在玩嘛,誤傷難免,都流血了,不要再打了。」隨即帶著小女孩得意的離去,嬸嬸背向母親護抱著我。
母親丟下籐條,氣哭著走回屋內。
終於再也忍不住,我放聲大哭在嬸嬸懷裡,斷續啜泣地說著:「又…不是我,又不是我。」嬸嬸連聲的安慰著:「不要哭了,我知道不是你,我知道,以後乖一點就好,乖,不要再哭了。」
洗澡時,小腿刺痛得令人想再哭一場,擦拭時,感覺得到兩邊臉頰明顯一大一小,和小腿上紅腫滲血的藤條印,緩緩抹去鏡上的白霧,小小年紀,心中充滿怨恨,眼神中充滿著怒與火,恨透了那個誣告的小女孩,恨透了那個得意的鄰婦,也恨透了母親的不分青紅皂白。
從那次以後,我不再和那小女孩講話,不再到那戶人家去看電視,也負氣地和母親冷戰了好幾天。
晚上,獨坐在簷下小凳上,無語,只是撫腿摸臉自憐,仍感痛與熱,任誰叫我都不應,學著母親,把空洞的眼神盯落在黑暗中的遠方,若有似無地,想著那血臉的女孩,得意的鄰婦,嚴刑逼供的母親,和丟在一旁的那根大籐條。
回過神,驚見母親蹲靠一旁,拿著一盒褐黑色的藥膏要幫我敷藥,我噘嘴假裝沒看到,俟母親一伸過手來,我以手推開,藥盒滑落,母親起身側臉站著,沒罵我,沒看我,也沒安慰我,許久許久,時空頓時凝結,沒有半句話,等母親彎腰撿起藥盒轉頭離去時,我看見母親含淚的眼。
睡夢中,突然有一隻手,輕撫我腫痛的左臉頰和左小腿,輕輕側翻我的身子,我假裝沒醒來,憑觸覺就知道那是母親的手,邊敷藥邊說著:「人家是有錢有勢的小千金,我們不同,要認份,玩到沒分沒寸,玩到人家侵門踏戶來理論,我總是要打給人家看才行,你自己也逞強,不管有沒有,早承認就不必多討打,嘴硬就是找死,你若有聽到,以後就要記得,不要讓人家說你老爸早死,孩子就沒規矩、沒教養。」哽咽中,兩滴淚滑落在我側身的背上。
等母親離去,我掩被縮曲著全身,雙手摀臉痛哭,小小年紀,再一次地痛恨著一切。
為什麼不問對錯?為什麼有沒有都要早承認?為什麼要打給人家看?為什麼窮人家就要過得如此卑微?為什麼母親的生活總是逃不出父親的死?而我和妹妹的童年總是躲不過母親的淚?
明明是暮春轉夏的季節,天氣應該是溫暖的,我的心卻因為背上母親的淚而降到冰點。背上的兩滴淚,好比浪子的刺青,有痛、有恨、有淚、也有後悔,是縮影,也是宣示的圖騰。
兩滴淚,落背,穿心,也永遠烙印在我的人生。
而今,數十年過去了,我來自於流氓的故鄉,我有一個管教我就像流氓大哥管小弟的母親,我是流氓律師,當年背上的兩滴刺青,終於讓我明白,沒有揭開女人心中最深的那一層紗,你根本無法分辨好女人與壞女人,嚴格,有時候也是一種慈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