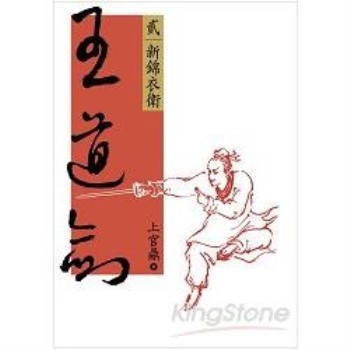傅翔見那蛇並無意攻擊,略感放心,想到那天尊、地尊處心積慮在少林寺中埋伏臥底,在緊要關頭盜走了少林絕學的秘笈,又聯手偷襲把自己打下絕崖,卻料不到這包秘笈最後全部到了自己手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呵!
略一轉頭,看到不遠處一片瀰漫的蒸氣冒向天空,形成龐大的氣柱,蔚為奇觀。這時前方傳來一陣咩咩之聲,傅翔精神一振,暗道:「有牧羊人經過?」
過了片刻,羊咩之聲更近,他努力抬頭,看到有十幾隻羊朝著自己這邊走來,羊群後面有一個童子,一手拿著一根剝光了皮的樹枝枒,一手抱著一隻小羊,他一面學著羊叫聲,一面驅趕羊,很快便走到傅翔身前。
那群羊停在灌木叢外尋嫩草吃,童子卻看見了傅翔,他緩步走近,傅翔正想開口,那童子已一步跨前,就在傅翔身邊坐了下來。他一面抱著那隻小羊,一面對那條怪蛇道:「小花,你怎麼不在守廟?到這裡來幹麼?」
傅翔見這小牧童生得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頭黑髮如鳥巢般雜亂,臉上有幾條污黑的手指印,鼻上掛著兩條濃鼻涕。兩人對望了一會兒,那牧童問道:「你怎麼睡這裡?」傅翔道:「我從山上跌落下來,便躺在這裡過了一夜。」那童子道:「你受傷了?」傅翔道:「傷得很重。」童子道:「我帶你去看阿茹娜姐姐。你痛不痛?」傅翔道:「快痛死了,眼下動不得,如何去看……去看阿茹娜姐姐……她是醫生嗎?」
那童子將小羊放在地上,那羊也不跑開。童子用手中樹枝一指前方,對那條怪蛇叫道:「小花,快回廟裡去。」一面用樹枝輕撥蛇頭,一面又指指前方。傅翔抬頭朝他指的方向看去,這才發現數十步之外,真有一座小土地廟,自己昨晚跌落,黑暗中並未發現,難道那怪蛇竟是土地廟的守護?那蛇被童子的樹枝撥弄了幾下,咻咻吐了一陣長舌,倖倖然朝那土地廟遊去。傅翔看得暗中嘖嘖稱奇。
那牧童見小花蛇聽他指揮回土地廟去了,便笑嘻嘻地道:「小花最愛聞燒香的味兒,住在廟裡若是有人來燒香,牠就高興了。」傅翔暗忖自己猜得沒錯,那怪蛇定是貪聞這包袱上濃郁的檀香味,才遊來此處。他見小童沒有回答問題,便再問道:「阿茹娜姐姐是醫生嗎?」
那牧童睜大了雙眼,好像聽到什麼稀奇古怪的話,又像是奇怪傅翔怎麼如此孤陋寡聞,便搖搖頭道:「阿茹娜姐姐的媽是個醫生,阿茹娜是仙女。」
傅翔道:「仙女?可我現在完全動不得,如何是好?」牧童道:「阿茹娜等會兒就會來採草藥。」他把地上的小羊抱起,一手撫摩小羊的頭、臉、身子,百般愛憐。傅翔強忍著身上的疼痛,搭訕道:「你這隻小羊長得好。」牧童喜道:「你也說牠好?要不要抱抱?」傅翔想說不要,已經來不及了。
那牧童將手中的小羊塞在傅翔懷中,那羊咩咩叫了兩聲,傅翔只好胡亂問道:「你這羊有名沒有?」童子道:「牠的名兒叫做香。」傅翔只覺懷中的小羊其實很臭,不禁好奇地問:「香?為啥叫香?」童子道:「我覺牠挺香。」
傅翔把「香」還給那童子,又問道:「那你叫啥名兒?」那孩子道:「俺叫巴根。」一面把那根剝光皮的樹棍遞給傅翔看,一面重覆道:「巴根,巴根。」傅翔不解,問道:「什麼是巴根?是樹棍兒嗎?」那童子搖頭道:「巴根就是柱子,蒙古名字。」傅翔恍然大悟道:「啊,是蒙古人名。阿茹娜是你姐姐?這名字是啥意思?」小牧童道:「阿茹娜不是俺姐,是仙女。阿茹娜是……是乾淨的意思。」
傅翔正要再問,那羊群外傳來一串清脆如銀鈴的笑聲,一個白衣少女笑著說:「巴根又在亂講,你的羊少了兩隻都不知道,還當什麼牧羊人?」
傅翔朝那發話的聲音看去,只見那少女頂著剛升起的朝陽走來,身後跟著兩隻黑羊,想是走遠了的兩隻羊被她趕回來,她背著一隻布袋,手中挽著一個竹籃,籃子裡放了一把一把採來的植物。
傅翔看那少女的臉和露在袖外的手,在陽光下像是白玉雕成的一般,少女頭髮烏黑,眉彎而秀氣,一雙大眼睛似乎會笑,鼻挺而嘴俏,雖然半背著陽光,傅翔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粉裡透紅的面頰及向上彎翹的睫毛。傅翔從來沒見過如此美麗的女子,不禁看得呆住,連身上的疼痛也不覺得了,心想:「巴根沒有亂講,阿茹娜姐姐是仙女。」
那少女走到傅翔躺身的灌木叢前,微笑道:「我就是阿茹娜,兄弟你貴姓大名,為何躺在野外?」傅翔連忙收起心猿意馬,回答道:「我……我姓傅名翔,飛翔的翔。昨晚被……被惡人從山頂打落下來,背上受了很重的外傷,胸前中了一掌,有很重的內傷,全身經絡走了位,一動也不能動,是以躺在這裡挨了一夜。」
那少女面上露出極為驚詫之色,有些不相信地問道:「你是說……你從山頂上跌落下來?從這山崖之頂落到咱們這深谷,怕不有一兩百仞之高?你怎麼沒有……沒有……」傅翔接口道:「沒有死?不瞞姑娘,我略有一些功夫在身。功夫,妳知道嗎?便如少林寺和尚的那種功夫。」他心想這裡離少林寺近,提起少林功夫,大家定是一聽便懂。
儘管如此,那少女似乎仍難相信,她仔細瞧了傅翔一眼,喃喃道:「從百仞山巔落下居然活著,除非你會飛……」她忽然面含笑意,俏麗的臉上有如芙蓉乍放,美豔不可方物,原來她忽然想到傅翔方才說他「姓傅名翔,飛翔的翔」,便忍不住笑了。
傅翔立刻明白她笑什麼,便道:「昨夜我跌落下來時,確實飛了一會兒……有隻大鷹從我面前飛過,翅膀張著不動,迎著氣流直翔而上,我便想學著牠的方法飛起來……」那阿茹娜睜大雙眼,問道:「你就飛起來了?」傅翔道:「沒有飛起來,可是下落之勢的確緩慢了些。」阿茹娜點頭道:「難怪。」那小童巴根問:「難怪啥?」阿茹娜拍了拍巴根的頭,低聲對他道:「難怪他沒摔死。」
傅翔全身的劇痛忽然「回」到身上,臉上的表情痛苦之極。阿茹娜走到他面前,蹲下身來,摸了摸他的前額,試著要把傅翔翻動,檢查背上的傷勢。傅翔強忍疼痛努力配合,只能略為翻動一下身軀。
阿茹娜只瞧了一眼,便驚叫道:「傅兄弟,你背上傷得極厲害,要趕快治療。」說著從背上的布袋裡揀了兩種樹根,用一把小刀各切下一小段,又從竹籃中揀出一束綠中帶紅紋路的葉子,摘了兩片,一併塞向傅翔的嘴邊,道:「傅兄弟,你先把這三樣藥嚼爛了,把汁吞下,渣吐了,好好睡一會,我再設法把你弄回家,找我媽給你治治。」
傅翔聞到她身上的氣息,是一種極為純淨、微帶乳香的好聞味兒,盯著她粉中透紅的臉上一雙清澈烏黑的眼睛,似乎從那眸子中都能看到自己臉孔的反射,不禁又是一陣迷糊,竟然忘了反應。
阿茹娜這時才仔細看清楚傅翔的面孔,倒是沒有想到這來歷古怪的少年,竟然有一張俊秀的臉,頭髮散開,有幾縷為汗濕了黏在臉上,雖然有一些狼狽,但掩不住一股充滿智慧的氣質。阿茹娜柔聲道:「你張嘴啊,我給你吃藥草……」忽然她好像聽到自己說話的聲音,一陣莫名心慌讓她紅了臉,再也說不下去。
傅翔真聽話,張嘴把那兩小段樹根及兩片葉子全都噙在口裡咀嚼起來,阿茹娜看了他一眼,正與傅翔的目光相遇,她臉頰又是一熱,忙站起身來對那童子道:「巴根,你好生看著這傅……傅兄弟,待會讓他把藥渣吐了就睡下,我去找人來幫忙。」巴根對她敬如仙女,連忙應道:「阿茹娜姐姐快去啊,巴根曉得。」
傅翔嚼著的那些草藥,全是他不認識的植物,他竟然不假思索便照著這頭一回見面的女子的吩咐,把嚼出的藥汁和著口水吞嚥了。他自己對醫藥也頗有造詣,竟對阿茹娜的話言從計聽,只覺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對自己都產生了無從抗拒的力量。他一面嚼藥,一面暗忖:「傅翔啊,定是你傷得奄奄一息,便是毒藥也得張口試試了。」他一面這樣想,一面清楚地知道,這話其實不對,原因不是那草藥,而是那女子。
傅翔吐出了藥渣,只過了片刻,發覺身上的疼痛減輕了不少,胸背都不再感到原先那種刺骨銘心的劇痛,正覺得高興,暗道:「這是什麼草藥?蒙古的醫藥麼……」腦中一陣迷糊,竟然漸漸昏睡了過去。
摘自《王道劍》(貳) 新錦衣衛 第十回 蒙古大夫
略一轉頭,看到不遠處一片瀰漫的蒸氣冒向天空,形成龐大的氣柱,蔚為奇觀。這時前方傳來一陣咩咩之聲,傅翔精神一振,暗道:「有牧羊人經過?」
過了片刻,羊咩之聲更近,他努力抬頭,看到有十幾隻羊朝著自己這邊走來,羊群後面有一個童子,一手拿著一根剝光了皮的樹枝枒,一手抱著一隻小羊,他一面學著羊叫聲,一面驅趕羊,很快便走到傅翔身前。
那群羊停在灌木叢外尋嫩草吃,童子卻看見了傅翔,他緩步走近,傅翔正想開口,那童子已一步跨前,就在傅翔身邊坐了下來。他一面抱著那隻小羊,一面對那條怪蛇道:「小花,你怎麼不在守廟?到這裡來幹麼?」
傅翔見這小牧童生得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一頭黑髮如鳥巢般雜亂,臉上有幾條污黑的手指印,鼻上掛著兩條濃鼻涕。兩人對望了一會兒,那牧童問道:「你怎麼睡這裡?」傅翔道:「我從山上跌落下來,便躺在這裡過了一夜。」那童子道:「你受傷了?」傅翔道:「傷得很重。」童子道:「我帶你去看阿茹娜姐姐。你痛不痛?」傅翔道:「快痛死了,眼下動不得,如何去看……去看阿茹娜姐姐……她是醫生嗎?」
那童子將小羊放在地上,那羊也不跑開。童子用手中樹枝一指前方,對那條怪蛇叫道:「小花,快回廟裡去。」一面用樹枝輕撥蛇頭,一面又指指前方。傅翔抬頭朝他指的方向看去,這才發現數十步之外,真有一座小土地廟,自己昨晚跌落,黑暗中並未發現,難道那怪蛇竟是土地廟的守護?那蛇被童子的樹枝撥弄了幾下,咻咻吐了一陣長舌,倖倖然朝那土地廟遊去。傅翔看得暗中嘖嘖稱奇。
那牧童見小花蛇聽他指揮回土地廟去了,便笑嘻嘻地道:「小花最愛聞燒香的味兒,住在廟裡若是有人來燒香,牠就高興了。」傅翔暗忖自己猜得沒錯,那怪蛇定是貪聞這包袱上濃郁的檀香味,才遊來此處。他見小童沒有回答問題,便再問道:「阿茹娜姐姐是醫生嗎?」
那牧童睜大了雙眼,好像聽到什麼稀奇古怪的話,又像是奇怪傅翔怎麼如此孤陋寡聞,便搖搖頭道:「阿茹娜姐姐的媽是個醫生,阿茹娜是仙女。」
傅翔道:「仙女?可我現在完全動不得,如何是好?」牧童道:「阿茹娜等會兒就會來採草藥。」他把地上的小羊抱起,一手撫摩小羊的頭、臉、身子,百般愛憐。傅翔強忍著身上的疼痛,搭訕道:「你這隻小羊長得好。」牧童喜道:「你也說牠好?要不要抱抱?」傅翔想說不要,已經來不及了。
那牧童將手中的小羊塞在傅翔懷中,那羊咩咩叫了兩聲,傅翔只好胡亂問道:「你這羊有名沒有?」童子道:「牠的名兒叫做香。」傅翔只覺懷中的小羊其實很臭,不禁好奇地問:「香?為啥叫香?」童子道:「我覺牠挺香。」
傅翔把「香」還給那童子,又問道:「那你叫啥名兒?」那孩子道:「俺叫巴根。」一面把那根剝光皮的樹棍遞給傅翔看,一面重覆道:「巴根,巴根。」傅翔不解,問道:「什麼是巴根?是樹棍兒嗎?」那童子搖頭道:「巴根就是柱子,蒙古名字。」傅翔恍然大悟道:「啊,是蒙古人名。阿茹娜是你姐姐?這名字是啥意思?」小牧童道:「阿茹娜不是俺姐,是仙女。阿茹娜是……是乾淨的意思。」
傅翔正要再問,那羊群外傳來一串清脆如銀鈴的笑聲,一個白衣少女笑著說:「巴根又在亂講,你的羊少了兩隻都不知道,還當什麼牧羊人?」
傅翔朝那發話的聲音看去,只見那少女頂著剛升起的朝陽走來,身後跟著兩隻黑羊,想是走遠了的兩隻羊被她趕回來,她背著一隻布袋,手中挽著一個竹籃,籃子裡放了一把一把採來的植物。
傅翔看那少女的臉和露在袖外的手,在陽光下像是白玉雕成的一般,少女頭髮烏黑,眉彎而秀氣,一雙大眼睛似乎會笑,鼻挺而嘴俏,雖然半背著陽光,傅翔可以清楚地看到她粉裡透紅的面頰及向上彎翹的睫毛。傅翔從來沒見過如此美麗的女子,不禁看得呆住,連身上的疼痛也不覺得了,心想:「巴根沒有亂講,阿茹娜姐姐是仙女。」
那少女走到傅翔躺身的灌木叢前,微笑道:「我就是阿茹娜,兄弟你貴姓大名,為何躺在野外?」傅翔連忙收起心猿意馬,回答道:「我……我姓傅名翔,飛翔的翔。昨晚被……被惡人從山頂打落下來,背上受了很重的外傷,胸前中了一掌,有很重的內傷,全身經絡走了位,一動也不能動,是以躺在這裡挨了一夜。」
那少女面上露出極為驚詫之色,有些不相信地問道:「你是說……你從山頂上跌落下來?從這山崖之頂落到咱們這深谷,怕不有一兩百仞之高?你怎麼沒有……沒有……」傅翔接口道:「沒有死?不瞞姑娘,我略有一些功夫在身。功夫,妳知道嗎?便如少林寺和尚的那種功夫。」他心想這裡離少林寺近,提起少林功夫,大家定是一聽便懂。
儘管如此,那少女似乎仍難相信,她仔細瞧了傅翔一眼,喃喃道:「從百仞山巔落下居然活著,除非你會飛……」她忽然面含笑意,俏麗的臉上有如芙蓉乍放,美豔不可方物,原來她忽然想到傅翔方才說他「姓傅名翔,飛翔的翔」,便忍不住笑了。
傅翔立刻明白她笑什麼,便道:「昨夜我跌落下來時,確實飛了一會兒……有隻大鷹從我面前飛過,翅膀張著不動,迎著氣流直翔而上,我便想學著牠的方法飛起來……」那阿茹娜睜大雙眼,問道:「你就飛起來了?」傅翔道:「沒有飛起來,可是下落之勢的確緩慢了些。」阿茹娜點頭道:「難怪。」那小童巴根問:「難怪啥?」阿茹娜拍了拍巴根的頭,低聲對他道:「難怪他沒摔死。」
傅翔全身的劇痛忽然「回」到身上,臉上的表情痛苦之極。阿茹娜走到他面前,蹲下身來,摸了摸他的前額,試著要把傅翔翻動,檢查背上的傷勢。傅翔強忍疼痛努力配合,只能略為翻動一下身軀。
阿茹娜只瞧了一眼,便驚叫道:「傅兄弟,你背上傷得極厲害,要趕快治療。」說著從背上的布袋裡揀了兩種樹根,用一把小刀各切下一小段,又從竹籃中揀出一束綠中帶紅紋路的葉子,摘了兩片,一併塞向傅翔的嘴邊,道:「傅兄弟,你先把這三樣藥嚼爛了,把汁吞下,渣吐了,好好睡一會,我再設法把你弄回家,找我媽給你治治。」
傅翔聞到她身上的氣息,是一種極為純淨、微帶乳香的好聞味兒,盯著她粉中透紅的臉上一雙清澈烏黑的眼睛,似乎從那眸子中都能看到自己臉孔的反射,不禁又是一陣迷糊,竟然忘了反應。
阿茹娜這時才仔細看清楚傅翔的面孔,倒是沒有想到這來歷古怪的少年,竟然有一張俊秀的臉,頭髮散開,有幾縷為汗濕了黏在臉上,雖然有一些狼狽,但掩不住一股充滿智慧的氣質。阿茹娜柔聲道:「你張嘴啊,我給你吃藥草……」忽然她好像聽到自己說話的聲音,一陣莫名心慌讓她紅了臉,再也說不下去。
傅翔真聽話,張嘴把那兩小段樹根及兩片葉子全都噙在口裡咀嚼起來,阿茹娜看了他一眼,正與傅翔的目光相遇,她臉頰又是一熱,忙站起身來對那童子道:「巴根,你好生看著這傅……傅兄弟,待會讓他把藥渣吐了就睡下,我去找人來幫忙。」巴根對她敬如仙女,連忙應道:「阿茹娜姐姐快去啊,巴根曉得。」
傅翔嚼著的那些草藥,全是他不認識的植物,他竟然不假思索便照著這頭一回見面的女子的吩咐,把嚼出的藥汁和著口水吞嚥了。他自己對醫藥也頗有造詣,竟對阿茹娜的話言從計聽,只覺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對自己都產生了無從抗拒的力量。他一面嚼藥,一面暗忖:「傅翔啊,定是你傷得奄奄一息,便是毒藥也得張口試試了。」他一面這樣想,一面清楚地知道,這話其實不對,原因不是那草藥,而是那女子。
傅翔吐出了藥渣,只過了片刻,發覺身上的疼痛減輕了不少,胸背都不再感到原先那種刺骨銘心的劇痛,正覺得高興,暗道:「這是什麼草藥?蒙古的醫藥麼……」腦中一陣迷糊,竟然漸漸昏睡了過去。
摘自《王道劍》(貳) 新錦衣衛 第十回 蒙古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