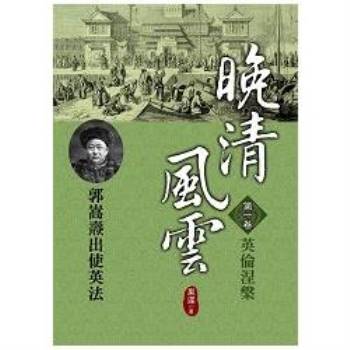第一章 使西紀程
引 子
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冬,北京城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親政才兩年的皇帝,如日中天之年卻突患天花,英年早逝。因無子嗣,東西太后乃傳懿旨,立醇親王奕譞之長子載湉為嗣皇帝,改年號為光緒,以明年為光緒元年。
就在這國喪之期,上下手忙腳亂之際,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卻發生了一件大事--英國駐華使館的翻譯官馬嘉理在雲南的騰衝地方被土人殺死。消息傳出,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立即趕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怒氣沖沖,虛聲恫嚇,並提出了三條要求:懲凶、賠款外,還要增開商埠,否則即以開戰相要脅。
其時,一向臣服中國的緬甸已淪為英國東印度的一個省,英國人早想通過緬甸這塊跳板,把勢力擴張到中國西南,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事實。面對威妥瑪氣勢洶洶的訛詐,總理衙門大臣們束手無策,加之此時小小的島夷日本也來湊熱鬧--竟以琉球船民在臺灣被殺為由,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領兵犯台,上海的報紙一尺風三尺浪,紛紛報導不利中國的消息,謂英倭將聯手圖我。
消息傳出,朝野上下,沸沸揚揚。軍機處議來議去,決定仍以和諧為主,乃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率福建水師赴台與西鄉從道談判,經雙方協商,由大清國賠白銀五十萬兩為軍費及撫金,促西鄉從道退兵;英國方面,乃派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威妥瑪談判,終於達成妥協:幾乎全部滿足了英國人的要求。
另外,大清國為表示誠意,將派一名名位相當的全權大臣去倫敦,向英國女王當面謝罪,之後留駐倫敦,作為大清國的首任駐英公使。這可是中國有史以來破天荒頭一遭。
「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兩千年來,讀書人以天朝上國自居,在他們眼中,只有四夷朝貢中國的,沒有中國派人朝拜四夷的,所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如今,堂堂天朝上國,孔孟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歷兩千年而不衰,而孔孟之徒卻要「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那蠻荒之邦朝拜夷人女主。消息傳出,有人頷首有人罵,有人歎息有人愁……
到九洲外國去
千難萬難,郭嵩燾終於踏上了西去郵輪「大礬廓號」。
此刻,這艘懸掛了大清帝國黃龍旗和大英帝國米字旗的遠洋客輪已駛出了長江口,來到大海上,隨著夜幕的降臨,十里洋場的上海那繁星一般的燈火已化成了一片紅雲,漸行漸遠,慢慢為黑暗所吞噬,喧囂的街市聲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風聲、濤聲,四周是那麼寂靜和空曠,站在甲板上眺望,眼前漆黑一團,除了一不知名的小島上有座燈塔發出忽閃忽閃的光,向人們顯示時空的存在外,人,就如回到了混沌初開的洪荒時代……
也不知過了多久,夜色更濃了,天空中不時飄來片片雨絲,沾在他臉上,涼沁沁的。身後的小妾梁氏終於耐不住了,挨上來柔聲細語地說:「老爺,我們真的是要到九洲外國去嗎?」
梁姬的語調有些興奮,終於感染了他,於是轉過身來,頗有興致的拍拍她的肩,說:「是啊,我們眼下正漂洋過海去九洲外國,你怕嗎?」
「有老爺在,奴才我怕什麼?」梁姬一高興,乃把身子緊緊地挨上來,把頭偎在他懷中。他不由也興奮起來,忙把她那一雙冰涼的小手抓在自己寬大的掌心裡,輕輕摩挲著說:「不怕就好,我會照護你的。」說著,他似乎記起了什麼,乃用調侃的語氣喚著梁氏的乳名說:「槿兒,你怎麼仍是老爺奴才地叫呢?」
她有些為難地說:「我巳經習慣了,好難改口的,再說怎麼稱呼也不打緊的。」
一聽槿兒提到習慣,郭嵩燾不由皺起了眉頭……
在他們的護照上,槿兒的身分是公使夫人。為了這個頭銜,使團翻譯馬格里在為他們辦護照時還頗費躊躇。據馬格里說,泰西多是基督徒,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在他們的字典裡是沒有媵、妾、偏房、外室、如夫人、小老婆、姨太太這類名詞的,要麼是夫人,要麼是情人,不然只能填一個奴僕。本來嘛,上帝創造人類時,便只一個亞當一個夏娃,多妻制是不道德的邪教徒所為。
馬格里振振有詞,他知道辯不過,心想,槿兒和她爺爺梁三老漢追隨自己二十餘年,備嘗艱苦,眼下雖不便扶正,但已是面前唯一的女人,若再將她列入奴僕一流,於情於理都不合適,而自己作為大清國皇帝陛下的欽差大臣、派往西方的第一位公使,上任時卻攜情人前往,簡直是天大的笑話,看來槿兒的身分是非填上夫人不可了。
然而,根據朝廷制度,像他這種正二品大員,正式配偶必然是受過皇封誥命的命婦,而該他名下有的那個「命婦」頭銜先是理所當然地為原配陳氏夫人所得,陳氏病故後,夫人又是續娶的太倉錢氏瑞雲了。
一提起這個繼室他就頭痛,已下決心讓這個生長書香門第卻缺乏教養的潑婦老死上海娘家了。眼下槿兒雖為他主中饋,卻沒有正式名份,稱不得夫人。
他左右為難,真沒料到此番出使,阻力重重,困難重重,在那千難萬難中,最後還有這麼個難題目,他已是驚弓之鳥,不敢惹事--真怕有人又從他家事中翻出新題目來攻擊他。
而馬格里不管這些,連連催他發話。
這個英國佬雖能說一口流利的華語,但對中國傳統道德和朝廷的典章制度不甚了了,見他尚在猶豫,竟當著英國公使威妥瑪的面,在槿兒身分一欄自作主張地填上「夫人」二字。
為此他頗有些不安,離京前及後來在天津、上海向方方面面的人物辭行時,他都一直避免提到挈內眷同行的事。
馬格里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說公使當然是要攜夫人同行的,在他們泰西,在上流社會,有夫人陪同更受人歡迎,因為他們尊重婦女。再說,尊夫人溫柔美麗,待人彬彬有禮,一看便知是個很有教養的貴婦人,若出現在交際場合,一定會獲得好評。
他只好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後來,馬格里聽見槿兒在他面前自稱奴才,不由大搖其頭,連說不行不行,夫人怎麼可自稱奴才?一旦讓人聽見了,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他於是又請教馬格里,馬格里提議他們互稱大令。
當郭嵩燾告訴槿兒「大令」的意思是「親愛的」時,槿兒一下臉色血紅,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連說不行,太肉麻了。他也覺得肉麻,便說你自稱「我」,稱我為「先生」算了。
槿兒也覺這個稱謂是可以接受的,但有時仍改不了口。
現在,槿兒又提到習慣了,此時的他不知怎麼對這回答聽著不太順耳--習慣,似是人人都有的,很難改變,但認真想來,它也把幾千年來的陳腐俗套固定了,這以前他便想改變某些習慣,卻深知搖撼之難。不是麼,身邊人連一句口語也難改呢!
想到此,他微微歎息,微微搖頭。
這情景,槿兒也看在眼中了,乃嘟噥說:「原以為到了九洲外國便要隨便些,沒想到洋人規矩也不少。」
這又是一個新題目,他一聽不由呆住了……
坐洋船
雨,漸漸下大了,他們攜手回到自己的房間。
這是一間頭等艙,裝飾得十分豪華考究,客廳裡枝形吊燈、沙發、茶几都是奶黃色,工藝精湛;臥室裡寬大的白銅床,雪白的花紋床單顯得十分乾淨、舒適。但他們一步跨進房間,雖感受到它的豪華氣派,卻分明有一種陌生感--這不再是中國仕宦之家的格局了,無論式樣和布局都顯示了一種異國情調,讓他們踟躕不前,尤其是槿兒,她一眼就瞅見對面牆上有一幅洋畫十分剌眼--那是一群在青草池塘邊洗澡的洋女人,全身一絲不掛,嘻嘻哈哈地潑水嘻笑,渾身線條清晰,纖毫畢露,十分逼真,在室內強光的照耀下,好像自己也置身其中。槿兒不由肉麻心跳。
「這不是要下地獄的嗎?」她驚叫起來。
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只有城隍司的壁畫上,才能看到這樣的畫,但那是正在地獄受懲罰的惡人,一個個赤身露體,被一群青面獠牙的惡鬼押著,正在地獄的刀山火海飽受煎熬,哪有如此快活。
一邊的郭嵩燾卻顯得沉靜得多,這以前,在廣州及天津、上海的洋人領事館和教堂,他見過不少洋畫,題材多取自《聖經》和希臘神話,自然有不少裸體人物,算是見多不怪。
他笑道:「這也是洋人的習俗,據說在泰西,越是莊嚴神聖的地方裸體畫越多,教堂的天花板及四壁幾乎全是的,且不但有畫的,還有石頭刻的、木頭雕的、泥巴塑的,今後你看得多了,自然不怪了!」
「不怪?」槿兒羞答答地嗔道:「女人這麼一絲不掛,那些個大男人見了不知會怎麼想?」
他知槿兒一下轉不過彎,只好耐心開導她,槿兒卻說:「洋人真不要臉,什麼好東西不能畫,卻偏偏要畫這個,那教堂不是洋和尚、洋尼姑們住的地方嗎?想必也供奉洋菩薩的,也不怕褻瀆了神靈!」
郭嵩燾於是引經據典,先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又扯上《呂氏春秋》,什麼「禹入裸國,裸入衣出。」
槿兒極佩服老爺的學問,聽他談得頭頭是道,不由點頭。只是一眼望見洋畫上那一群裸女,總是不舒服,於是轉身從箱子中翻出一塊黑縐紗,想了些辦法才把這幅畫遮住,然後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地舒了一口氣,回過頭又雙眼望著老爺說:「我看洋人男女之間不成體統的事只怕多得很。就在我們東土,他們來衙門談公事,有時也帶女人來,且當眾勾肩搭背吊膀子,若在自己的國家,只怕還有更骯髒的事呢!」
郭嵩燾說:「洋人畢竟是洋人,泰西也不比遠東,何必要講求一致?不過,既然領了差事,漂洋過海去了九洲外國,就只好隨和些,先不要這也不是那也看不慣的,若惹惱了洋人,差事辦砸了,回去可不好向兩宮太后、皇上交代。」
槿兒這才不再嘀咕。
因為臥室很暖和,且不再出去了,槿兒開始卸妝。她先褪出手腕上金光燦燦的盤龍鉸絲金釧,再鬆開頭上沉甸甸的元寶髻,讓一頭秀髮披散開,再用一條絲巾稍稍綰起。脫掉上身出鋒皮毛背心,僅著一件墨綠色四面不開岔「一裹圓」旗袍,在大穿衣鏡前走了走,鏡子裡出現了一個十分嬌豔的貴婦人,嫋嫋婷婷,雅淡而別具風韻,槿兒對自己的形象十分滿意,乃走到老爺身邊,低聲問道:「老爺,你看如何?」
「好!」
「可翠蘭說老氣了一些。」
「不見得。」
老爺說話時,眼睛根本不曾瞄槿兒。
槿兒不由生氣--那天為治裝,老爺帶她在上海洋行花去了近百兩銀子,為她買了很多衣料,但高興之餘也不無遺憾--選料子時,她看中了一塊洋紅金線紋花綢,想做一件旗袍,可老爺就是不讓買,她明白老爺不是嫌貴,後來在老爺授意下,店夥計拿出的那塊水綠倭緞要貴得多老爺也毫不猶豫地買下--問題出在顏色上,因為大紅為正室夫人的專用顏色。槿兒到郭家不是三媒六證花紅彩禮聘的,也不是祭告列祖列宗後用大紅花轎抬來的,一個收房丫頭,沒有皇封誥命,大紅裙如何穿得?
不過,槿兒無意爭名份,她只是想穿豔一點。才三十出頭的她,身段很好,這大紅旗袍穿在身上必定好看,但她不願拂老爺的意。眼下燈下試裝這是專給老爺看的,可老爺無心欣賞,如何不氣?正要纏住他好好地理論一番,卻發現老夫子坐在那裡端著水煙筒在拼命抽悶煙,一顆頭隱沒在雲裡霧裡,顯是心思旁逸了。
--自從拜命出使 ,老爺就常常一時歡喜一時愁,常常一人待在房中抽悶煙,老爺的心事沉著呢……
吸洋煙
此刻船上其他地方還是亂糟糟的,使團成員及乘客大多在清理自己的東西,將其擺好位置,有手腳麻利的則在甲板上或過道閒逛,藉以熟悉環境,一時人聲鼎沸,靜不下來。
在使團中有兩個人的行李最多最狼獷。一個是翻譯馬格里,另一個則是副使劉錫鴻。
馬格里是蘇格蘭人,道光末年隨著鴉片戰爭的硝煙來到中國,先在上海海關當差,後來被曾國藩聘為江南機器局的技師,開始出入中國官場,以「客卿」身分受聘中國。為表忠心,他把自己的姓氏譯得頗有些中國化,且仿中國人的習慣也加了一個表字曰:「清臣」--顯然是要死心塌地做大清的臣子。後來,李鴻章籌辦海防,建大沽炮臺,試炮時,江南機器局造出的炮彈出膛便炸,毀了好幾門炮,傷了好幾個人,於是他這個技師被撤了差。但來華幾十年,他已能操一口流利的華語,李鴻章棄其短而用其長,改聘他為北洋大臣衙門翻譯,幾年下來,竟保舉了他一個五品同知銜。
此番郭嵩燾組團使英,馬格里由李鴻章推薦到使團任職,因此,他既是出公差又可了回鄉探親的私願,公私兩便,行李費由公家報銷且可享受外交官所帶物品海關免稅的優待。因此,他在京滬兩地採辦了大量的中國土特產和珍奇古玩,像去參加萬國炫奇會(博覽會)一般。
而劉錫鴻帶的東西卻有些怪,是別人意想不到或認為不必要的。
就說煙具,他們一行幾乎個個都抽煙,但工具各有不同,郭嵩燾抽水煙,一支作工考究、景泰藍底座的白銅煙袋不離左右;馬格里抽雪茄,一支粗大的古巴雪茄長期噙在嘴裡像塞了隻茄子;廣東番禹人劉錫鴻用的卻是一支已被煙薰火燎成醬紅色的竹煙筒。
至於引火之物則差異更大。這幾年歐風東漸,津滬等地得風氣之先,市面上洋貨充盈,就是窮家小戶也用上了火柴,對這小玩意兒,天津人開始叫「洋取燈兒」,上海人則稱「自來火」,後來則統一稱「洋火」。
這種紅頭小木棒才幾個銅子一匣,取一根隨便在什麼硬物上一擦即出火,用起來十分方便,使團成員早用上了,講究一些的更用上了「打火機」。
劉錫鴻對這些卻視而不見,取火仍用老式的火鐮、棉絨,度火用土造毛邊紙捲成的紙煝子;別人早吸上了洋煙他卻仍是吸土煙。因此,他怕在英國買不到這些土特產便帶了一大捆毛邊紙,幾大包雲南煙絲,裝在幾隻大竹簍子裡,上船時由武弁一一背上來。因此,他的行李僅次於馬格里。
眼下,眾人差不多都在休息了,劉錫鴻卻仍在整理行李。隨員劉孚翊見了大惑不解,乃說:「大人這是何苦來,用自來火吸洋紙煙多方便,帶這些東西好狼獷!」
劉錫鴻笑了笑,悠悠地說:「你知道什麼,我輩為朝廷官員,應處處以身作則,可不能一出國門便忘了根本,就如吸煙度火,自我們祖先燧人氏鑽木取火後,火石、火棉、紙煝子用了幾千年,於是就有了專造這些東西的作坊,小民以此為業,若大家見了洋貨就愛,那以此為生的升斗小民豈不要斷了生計,國家不也因此斷了財稅之源?」
劉孚翊不意自己的關心會引來副使大人的訓斥,正懊悔不已,不想一邊的翻譯張德彝卻不以為然地笑了起來。
劉錫鴻忙問笑什麼?張德彝說:「劉大人未免膠柱鼓瑟--單不用洋貨也不是富國的辦法。更何況煙草本身就是泊來品,自古歷來我們的老祖宗只有茶酒的嗜好,哪有什麼煙?所謂淡巴菰(煙絲)還不是從南洋呂宋一帶傳過來的?至於煙具,我們中國人倒是越做越精巧,這是洋人遠遠比不上的,未見得只有你們廣東的破竹筒子才是國粹!」
張德彝說話時笑笑嘻嘻,卻分明有揶揄之意。劉錫鴻頓覺話不投機,不由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張德彝是同治元年同文館第一期的學生,那一期才十個學生,他即其中的佼佼者,畢業後已先後四次赴歐美遊歷,寫過好幾本有關出洋見聞的書,為辦洋務的人所重視,眼下雖只掛兵部員外郎銜,卻是使團中涉洋資歷最深的人之一,加之他又是一個旗人--出身漢軍鑲黃旗,劉錫鴻對他不得不另眼相看,眼下明知張德彝是在挖苦他,也只勉強笑了笑便訕訕地走開了……
與火車較勁
劉錫鴻一走,幾個品級較低的隨員都鬆了一口氣。
年輕氣盛的劉孚翊朝劉錫鴻的背影癟了癟嘴,轉身對張德彝說:「還是老兄見多識廣,一句話便把這老古董給駁回去了。」
參贊黎庶昌在他們爭論時還在碼行李,此時已閒下來,乃插言說:「不要稱他老古董,他畢竟還肯出洋,眼下見洋字就罵的人還不少呢!」
隨員姚若望說:「不過,眼下滬上反對鐵路的那班仕紳,卻和劉大人不謀而合。」
一聽姚若望提到鐵路,眾人的興趣又來了,他們擠在二等艙門口,紛紛要姚若望談上海紳民反對修築淞滬路的新聞。
姚若望是上海人,在京受職為使團隨員後,受正使郭嵩燾委派,提前兩個月便回了上海,因此對滬上鐵路之爭知之甚詳,出事那天他還趕到閘北去看了熱鬧。眼下眾人抬舉,他乃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那天的情景。
四年前,英國人以修馬路為名,在吳淞買了一段直至閘北的地皮,今年初開始動工,滬上紳民見修馬路也未在意,直到六月中旬「馬路」從吳淞口修到了江灣,且鋪上了鐵軌,運來了火車頭及車廂,揚言六月底正式通車,大家這才大吃一驚,明白洋人用的是瞞天過海之計。
在眾人紛紛反對之下,上海道馮焌光以侵犯中國主權為由向英國駐滬領事提出交涉,但英國人不予理睬;馮焌光乃提出收回路權,英國人卻說須待十年之後。雙方交涉未了,洋人卻不顧一切地舉行通車典禮了。
那天,成千上萬的人擁向吳淞和閘北看熱鬧,因洋人免票三天,便也有乘車去「過洋癮」、「開洋葷」的;但多數人卻是來抗議並試圖阻止通車的。他們中有衣冠楚楚的紳士,也有布衣短褐甚至赤膊短褲的苦力。
紳士們反對的理由是鐵路穿山打洞、火車風馳電掣,若讓它在中國推廣,勢必蹂田堙井,破壞風水,更不堪的則是毀墓掘墳,使祖先骸骨暴露。
苦力們卻只看到目前--洋貨從吳淞口上岸,無論水路旱路,少不得由他們肩扛車運、駕船背縴運往內地,好多失業的農戶和小市民以此為生。火車一通,他們的飯碗全砸了。
大家難得如此齊心合力詛咒鐵路。但洋人對眾人的咒罵不加理會,忙著開車的準備。
升火後便吆喝著招呼眾人去坐免費火車。
旁邊有心計的士紳便支使一班苦力,用一根粗麻繩子拴在火車最後一節車廂的橫槓上,當火車啟動時,眾人發聲喊,想拉住已啟動的火車,但拉大繩的人雖多卻不是火車的對手,火車才啟動,眾人便拖不住,待司機加大馬力,黑煙一冒,汽笛一吼,後面的人便紛紛丟手,排頭的幾個力氣大、脾氣強的大漢仍不肯鬆手,結果被拖了幾十步,人跌倒了才不得不罵著娘撂手。
從後面拖不住火車,眾人便成千上萬地在前面攔。洋人不得不停下來與之論理,攔火車的人說火車一開,煙筒火星迸冒,會引燃路邊房屋。洋人說保證不會,若引燃了房屋願予賠償。
但眾人仍是不依。就這樣吵吵嚷嚷,火車時停時開,到七月中旬的一天,終於有不肯讓路的市民被火車軋死的事發生了。於是滬上轟動了,大家紛紛罷市並擁上路基靜坐抗議。英國人也不得不讓火車暫且停開。
此事震動朝野,總理衙門為平息事態,接受李鴻章的建議,派直隸候補道盛宣懷協助兩江總督沈葆楨與英國駐滬領事談判。至於能否收回路權,則尚不知也。
姚若望一口氣說完了經過,劉孚翊馬上補充。
他也是最早到達上海的,也有幸目睹火車通行的情景,他說:「狗日的火車真神奇。據坐過的人說,從吳淞口到江灣二十幾里路只一袋煙久便到了,要說,『不翼而飛』四字安在火車上是再貼切不過了!」
張德彝說:「二十幾里路算什麼?那年我從法國巴黎到德國的柏林也才幾個鐘頭呢!眼下歐洲的鐵路已四通八達,出門真方便,什麼山高路遠、風濤之險的顧慮都沒有了!」
劉孚翊說:「滬上那些人也不知怎麼想的,洋人雖不該瞞天過海,侵犯了我們主權,但火車則沒有錯,要是我們也到處有火車那多好!」
「哼!你說好,可有人偏偏說不呢! 」張德彝冷笑著說,「剛才劉大人不是連洋煙、洋火都不用嗎,說東西雖小卻關係千百萬升斗小民的生計呢!」
「是的是的。」另一隨員張斯栒也插話了。他年過五十,是使團中年齡僅次於正使之人,他沒有劉孚翊那種衝動,也不知張德彝說的是反話,立即附和說:「火車雖神奇,只怕不適宜於中國,正如剛才副使說的,一舉一動,都不能丟開國計民生不想。火車有如此神通,若讓它四通八達起來,那好多販夫走卒、靠肩扛手提的苦力真會喝西北風呢!」
姚若望反駁說:「那也不一定。我聽人說,火車在道光初年才發明出來,這以前洋人往來交通貿易,不也是靠人力嗎,眼下他們那班下人是否都餓死了呢?」
「這話問得極好,」劉孚翊見有人支持便來勁了,他說:「眼下滬上士紳爭論火車是否適用於中國爭得十分起勁,有人說洋人奇技淫巧禍害中國,讓洋貨湧進來會使成千上萬的小康之家破產,窮家小戶更會絕了生路;有人卻認為洋貨見多了也可仿造,大家動手做出來與洋人搶生意,這樣就不僅不會妨害國計民生且有利於國計民生了。」
劉孚翊此說是眼下辦洋務的人的一貫主張,滬紳馮桂芬甚至寫進了他的專著《校邠廬抗議》一書中。姚若望以前在上海看到了這本書,對作者佩服不已。他也認為中國人完全不必畏洋貨,憑自己的聰明才智依樣畫葫蘆,造出與洋貨比美的國貨,與洋人展開商戰,這樣可奪回利權。眼下聽劉孚翊一說,忙笑著喚著劉孚翊的字說:「和伯此說正是馮桂芬書上說的,和伯莫非也看過《校邠廬抗議》?」
劉孚翊說:「當然,那確實是一部奇書,專談當前時政要務,左季高伯相稱它可與賈誼的《治安策》比美,列位不妨都看一看。」
「依我看,看書不如實地考察。」一直不大開口的黎庶昌此時插話了,他說:「《校邠廬抗議》我手中也有一部。據我所知,作者並未去過泰西,故多採用道聽塗說,有人云亦云之弊。此番朝廷派我等出洋,坐探西人國政,不正好對照書本,相互印證麼?」
眼下劉錫鴻回房去了,聚在一起的人中數黎庶昌地位最高,學問也最好,眾人自然以他的話為圭臬,當聽到「坐探國政」四字,便一齊點頭……
坐探國政
其實,此刻在一旁點頭的還有一人,這便是郭嵩燾。
槿兒已上床休息,他卻了無睡意,於是來二等艙看望同僚們,在大餐間拐角處,聽眾人議論,覺得很有意思,尤其是黎庶昌那「坐探國政」四字,他覺得對使團使命概括得十分準確,一時各種念頭湧上心來,乃決定不再去打擾眾人,一人默默地回到了自己房間。
此時槿兒己在床上發出了輕微的鼾聲,他卻坐到了書案前,想把跨出國門頭一天的經過和感受寫進日記。不料翻開日記簿,十多天前寫的一首詩赫然出現在眼前:
大地回環一水涵,乘槎歷斗助清談。
塵中世界原同趣,天外波濤定飽諳。
碧海秋深風正穩,黃花別晚酒初酣。
君歸皓首吾方出,此意憑誰一笑參。
他想起這是送美國人威廉士的詩。威廉士於道光十三年來華傳教,自學中文,於經史子集多有涉獵,居然把詩韻和平仄也弄清了,作的詩也像模像樣的。他咸豐七年開始出任美國駐華使館翻譯,同治六年後以參贊署理公使。前後來華四十三年,此番以近古稀之年回國應聘耶魯大學,講授中文。在京之日,他與郭嵩燾交往頻繁,回國時郭嵩燾賦此七律為贈。
想到威廉士在異國他鄉幾近半世紀,終於功成名就回國執教了,而與他年齡相差無幾的自己則在這時才毅然出國,是不是太晚了呢?
他不由翹首窗外--冬日苦短,眼下海上雖黑漆一團,但時鐘才指著八點半,外面甲板上,在幽幽的燈光下,仍有人影在晃動,船尾傳來一洋人水手的歌聲,是那麼淒切,像是在思念遠方的親人,他不由也想到了自己的命運……
泰西,這是眼下中國人對歐美的統稱,如歐美人稱中國為遠東一樣,都是極遙遠的意思。這以前,泰西和遠東互不通往來,漢代派往西方的使者僅到了中亞,最遠也不過地中海邊。唐僧取經才到了印度,明朝的三寶太監鄭和算是走得最遠,按說已到達了非洲東岸,若再往南出好望角便可到大西洋,可惜功虧一簣。因此之故,東西方隔閡殊深,中國的正史上居然說西方的羊羔是從地裡長出來的,臍帶還牽連著大地;而歐洲人則說中國人用小米餵一種狀似蜘蛛的蟲子,幾年後蟲子肚子開裂,可取出絲來織成綢緞。
不同的是自明朝後,隨著海路開通,泰西源源不斷有人西來,把在遠東的見聞帶回國去,湯若望、利瑪竇、郎世寧等西方人甚至在中國做官,他們對中國的情形可謂瞭若指掌,而堂堂中國對泰西情形仍一無所知。
今天,自己奉旨使西,坐探西人國政,這可是亙古第一遭,本應是一件大好事,但此舉卻為士大夫所不諒,以致他在接受任命後在朋輩及同僚中頗遭白眼,遠在湖南的親友也紛紛寫信阻其行。
他想,親友的不諒不難理解--眼下,同為湘陰人的左宗棠已力排眾議,集兵糧餉運大權於一身,督十萬湘楚健兒大舉西征新疆,且已取得一連串的勝利,煌煌武功大振了民氣、士氣,於萬馬齊喑的局面不啻一聲春雷。
鄉人只看重左宗棠的武功,卻不明白自己使西將對後世帶來的影響,湖南人素以倔強著稱,到了黃河心不死,撞了南牆不回頭。就在他們正做著中興之夢的時候,自己卻充當「謝罪使」,去向「夷人」的女主賠禮道歉,他們能不憤怒嗎?
可眼下己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了!
他就帶著一肚子豪情、一肚子怨氣上床就寢了。
不想就在這時,他感到外面風更大、雨更猛了,人在床上憑直覺感到船的顛簸,似從數丈高的波峰跌入低谷,大浪打在船身上,發出了巨大的轟鳴聲,十分恐怖--出行的第一天便遇上大風暴,不知是什麼兆頭?
引 子
清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冬,北京城籠罩在一片愁雲慘霧之中--親政才兩年的皇帝,如日中天之年卻突患天花,英年早逝。因無子嗣,東西太后乃傳懿旨,立醇親王奕譞之長子載湉為嗣皇帝,改年號為光緒,以明年為光緒元年。
就在這國喪之期,上下手忙腳亂之際,西南邊陲的雲南省卻發生了一件大事--英國駐華使館的翻譯官馬嘉理在雲南的騰衝地方被土人殺死。消息傳出,英國駐華公使威妥瑪立即趕到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怒氣沖沖,虛聲恫嚇,並提出了三條要求:懲凶、賠款外,還要增開商埠,否則即以開戰相要脅。
其時,一向臣服中國的緬甸已淪為英國東印度的一個省,英國人早想通過緬甸這塊跳板,把勢力擴張到中國西南,這是明眼人都能看出的事實。面對威妥瑪氣勢洶洶的訛詐,總理衙門大臣們束手無策,加之此時小小的島夷日本也來湊熱鬧--竟以琉球船民在臺灣被殺為由,派陸軍中將西鄉從道領兵犯台,上海的報紙一尺風三尺浪,紛紛報導不利中國的消息,謂英倭將聯手圖我。
消息傳出,朝野上下,沸沸揚揚。軍機處議來議去,決定仍以和諧為主,乃派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楨率福建水師赴台與西鄉從道談判,經雙方協商,由大清國賠白銀五十萬兩為軍費及撫金,促西鄉從道退兵;英國方面,乃派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與威妥瑪談判,終於達成妥協:幾乎全部滿足了英國人的要求。
另外,大清國為表示誠意,將派一名名位相當的全權大臣去倫敦,向英國女王當面謝罪,之後留駐倫敦,作為大清國的首任駐英公使。這可是中國有史以來破天荒頭一遭。
「天處乎上,地處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國,居天地之偏者曰四夷。」兩千年來,讀書人以天朝上國自居,在他們眼中,只有四夷朝貢中國的,沒有中國派人朝拜四夷的,所謂「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如今,堂堂天朝上國,孔孟之道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歷兩千年而不衰,而孔孟之徒卻要「下喬木而入幽谷」,去那蠻荒之邦朝拜夷人女主。消息傳出,有人頷首有人罵,有人歎息有人愁……
到九洲外國去
千難萬難,郭嵩燾終於踏上了西去郵輪「大礬廓號」。
此刻,這艘懸掛了大清帝國黃龍旗和大英帝國米字旗的遠洋客輪已駛出了長江口,來到大海上,隨著夜幕的降臨,十里洋場的上海那繁星一般的燈火已化成了一片紅雲,漸行漸遠,慢慢為黑暗所吞噬,喧囂的街市聲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風聲、濤聲,四周是那麼寂靜和空曠,站在甲板上眺望,眼前漆黑一團,除了一不知名的小島上有座燈塔發出忽閃忽閃的光,向人們顯示時空的存在外,人,就如回到了混沌初開的洪荒時代……
也不知過了多久,夜色更濃了,天空中不時飄來片片雨絲,沾在他臉上,涼沁沁的。身後的小妾梁氏終於耐不住了,挨上來柔聲細語地說:「老爺,我們真的是要到九洲外國去嗎?」
梁姬的語調有些興奮,終於感染了他,於是轉過身來,頗有興致的拍拍她的肩,說:「是啊,我們眼下正漂洋過海去九洲外國,你怕嗎?」
「有老爺在,奴才我怕什麼?」梁姬一高興,乃把身子緊緊地挨上來,把頭偎在他懷中。他不由也興奮起來,忙把她那一雙冰涼的小手抓在自己寬大的掌心裡,輕輕摩挲著說:「不怕就好,我會照護你的。」說著,他似乎記起了什麼,乃用調侃的語氣喚著梁氏的乳名說:「槿兒,你怎麼仍是老爺奴才地叫呢?」
她有些為難地說:「我巳經習慣了,好難改口的,再說怎麼稱呼也不打緊的。」
一聽槿兒提到習慣,郭嵩燾不由皺起了眉頭……
在他們的護照上,槿兒的身分是公使夫人。為了這個頭銜,使團翻譯馬格里在為他們辦護照時還頗費躊躇。據馬格里說,泰西多是基督徒,實行的是一夫一妻制,在他們的字典裡是沒有媵、妾、偏房、外室、如夫人、小老婆、姨太太這類名詞的,要麼是夫人,要麼是情人,不然只能填一個奴僕。本來嘛,上帝創造人類時,便只一個亞當一個夏娃,多妻制是不道德的邪教徒所為。
馬格里振振有詞,他知道辯不過,心想,槿兒和她爺爺梁三老漢追隨自己二十餘年,備嘗艱苦,眼下雖不便扶正,但已是面前唯一的女人,若再將她列入奴僕一流,於情於理都不合適,而自己作為大清國皇帝陛下的欽差大臣、派往西方的第一位公使,上任時卻攜情人前往,簡直是天大的笑話,看來槿兒的身分是非填上夫人不可了。
然而,根據朝廷制度,像他這種正二品大員,正式配偶必然是受過皇封誥命的命婦,而該他名下有的那個「命婦」頭銜先是理所當然地為原配陳氏夫人所得,陳氏病故後,夫人又是續娶的太倉錢氏瑞雲了。
一提起這個繼室他就頭痛,已下決心讓這個生長書香門第卻缺乏教養的潑婦老死上海娘家了。眼下槿兒雖為他主中饋,卻沒有正式名份,稱不得夫人。
他左右為難,真沒料到此番出使,阻力重重,困難重重,在那千難萬難中,最後還有這麼個難題目,他已是驚弓之鳥,不敢惹事--真怕有人又從他家事中翻出新題目來攻擊他。
而馬格里不管這些,連連催他發話。
這個英國佬雖能說一口流利的華語,但對中國傳統道德和朝廷的典章制度不甚了了,見他尚在猶豫,竟當著英國公使威妥瑪的面,在槿兒身分一欄自作主張地填上「夫人」二字。
為此他頗有些不安,離京前及後來在天津、上海向方方面面的人物辭行時,他都一直避免提到挈內眷同行的事。
馬格里對此很不以為然,他說公使當然是要攜夫人同行的,在他們泰西,在上流社會,有夫人陪同更受人歡迎,因為他們尊重婦女。再說,尊夫人溫柔美麗,待人彬彬有禮,一看便知是個很有教養的貴婦人,若出現在交際場合,一定會獲得好評。
他只好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後來,馬格里聽見槿兒在他面前自稱奴才,不由大搖其頭,連說不行不行,夫人怎麼可自稱奴才?一旦讓人聽見了,豈不是天大的笑話?
他於是又請教馬格里,馬格里提議他們互稱大令。
當郭嵩燾告訴槿兒「大令」的意思是「親愛的」時,槿兒一下臉色血紅,頭搖得像撥浪鼓似的,連說不行,太肉麻了。他也覺得肉麻,便說你自稱「我」,稱我為「先生」算了。
槿兒也覺這個稱謂是可以接受的,但有時仍改不了口。
現在,槿兒又提到習慣了,此時的他不知怎麼對這回答聽著不太順耳--習慣,似是人人都有的,很難改變,但認真想來,它也把幾千年來的陳腐俗套固定了,這以前他便想改變某些習慣,卻深知搖撼之難。不是麼,身邊人連一句口語也難改呢!
想到此,他微微歎息,微微搖頭。
這情景,槿兒也看在眼中了,乃嘟噥說:「原以為到了九洲外國便要隨便些,沒想到洋人規矩也不少。」
這又是一個新題目,他一聽不由呆住了……
坐洋船
雨,漸漸下大了,他們攜手回到自己的房間。
這是一間頭等艙,裝飾得十分豪華考究,客廳裡枝形吊燈、沙發、茶几都是奶黃色,工藝精湛;臥室裡寬大的白銅床,雪白的花紋床單顯得十分乾淨、舒適。但他們一步跨進房間,雖感受到它的豪華氣派,卻分明有一種陌生感--這不再是中國仕宦之家的格局了,無論式樣和布局都顯示了一種異國情調,讓他們踟躕不前,尤其是槿兒,她一眼就瞅見對面牆上有一幅洋畫十分剌眼--那是一群在青草池塘邊洗澡的洋女人,全身一絲不掛,嘻嘻哈哈地潑水嘻笑,渾身線條清晰,纖毫畢露,十分逼真,在室內強光的照耀下,好像自己也置身其中。槿兒不由肉麻心跳。
「這不是要下地獄的嗎?」她驚叫起來。
因為在她的印象中,只有城隍司的壁畫上,才能看到這樣的畫,但那是正在地獄受懲罰的惡人,一個個赤身露體,被一群青面獠牙的惡鬼押著,正在地獄的刀山火海飽受煎熬,哪有如此快活。
一邊的郭嵩燾卻顯得沉靜得多,這以前,在廣州及天津、上海的洋人領事館和教堂,他見過不少洋畫,題材多取自《聖經》和希臘神話,自然有不少裸體人物,算是見多不怪。
他笑道:「這也是洋人的習俗,據說在泰西,越是莊嚴神聖的地方裸體畫越多,教堂的天花板及四壁幾乎全是的,且不但有畫的,還有石頭刻的、木頭雕的、泥巴塑的,今後你看得多了,自然不怪了!」
「不怪?」槿兒羞答答地嗔道:「女人這麼一絲不掛,那些個大男人見了不知會怎麼想?」
他知槿兒一下轉不過彎,只好耐心開導她,槿兒卻說:「洋人真不要臉,什麼好東西不能畫,卻偏偏要畫這個,那教堂不是洋和尚、洋尼姑們住的地方嗎?想必也供奉洋菩薩的,也不怕褻瀆了神靈!」
郭嵩燾於是引經據典,先說十里不同音、百里不同俗,又扯上《呂氏春秋》,什麼「禹入裸國,裸入衣出。」
槿兒極佩服老爺的學問,聽他談得頭頭是道,不由點頭。只是一眼望見洋畫上那一群裸女,總是不舒服,於是轉身從箱子中翻出一塊黑縐紗,想了些辦法才把這幅畫遮住,然後好像完成了一件大事似地舒了一口氣,回過頭又雙眼望著老爺說:「我看洋人男女之間不成體統的事只怕多得很。就在我們東土,他們來衙門談公事,有時也帶女人來,且當眾勾肩搭背吊膀子,若在自己的國家,只怕還有更骯髒的事呢!」
郭嵩燾說:「洋人畢竟是洋人,泰西也不比遠東,何必要講求一致?不過,既然領了差事,漂洋過海去了九洲外國,就只好隨和些,先不要這也不是那也看不慣的,若惹惱了洋人,差事辦砸了,回去可不好向兩宮太后、皇上交代。」
槿兒這才不再嘀咕。
因為臥室很暖和,且不再出去了,槿兒開始卸妝。她先褪出手腕上金光燦燦的盤龍鉸絲金釧,再鬆開頭上沉甸甸的元寶髻,讓一頭秀髮披散開,再用一條絲巾稍稍綰起。脫掉上身出鋒皮毛背心,僅著一件墨綠色四面不開岔「一裹圓」旗袍,在大穿衣鏡前走了走,鏡子裡出現了一個十分嬌豔的貴婦人,嫋嫋婷婷,雅淡而別具風韻,槿兒對自己的形象十分滿意,乃走到老爺身邊,低聲問道:「老爺,你看如何?」
「好!」
「可翠蘭說老氣了一些。」
「不見得。」
老爺說話時,眼睛根本不曾瞄槿兒。
槿兒不由生氣--那天為治裝,老爺帶她在上海洋行花去了近百兩銀子,為她買了很多衣料,但高興之餘也不無遺憾--選料子時,她看中了一塊洋紅金線紋花綢,想做一件旗袍,可老爺就是不讓買,她明白老爺不是嫌貴,後來在老爺授意下,店夥計拿出的那塊水綠倭緞要貴得多老爺也毫不猶豫地買下--問題出在顏色上,因為大紅為正室夫人的專用顏色。槿兒到郭家不是三媒六證花紅彩禮聘的,也不是祭告列祖列宗後用大紅花轎抬來的,一個收房丫頭,沒有皇封誥命,大紅裙如何穿得?
不過,槿兒無意爭名份,她只是想穿豔一點。才三十出頭的她,身段很好,這大紅旗袍穿在身上必定好看,但她不願拂老爺的意。眼下燈下試裝這是專給老爺看的,可老爺無心欣賞,如何不氣?正要纏住他好好地理論一番,卻發現老夫子坐在那裡端著水煙筒在拼命抽悶煙,一顆頭隱沒在雲裡霧裡,顯是心思旁逸了。
--自從拜命出使 ,老爺就常常一時歡喜一時愁,常常一人待在房中抽悶煙,老爺的心事沉著呢……
吸洋煙
此刻船上其他地方還是亂糟糟的,使團成員及乘客大多在清理自己的東西,將其擺好位置,有手腳麻利的則在甲板上或過道閒逛,藉以熟悉環境,一時人聲鼎沸,靜不下來。
在使團中有兩個人的行李最多最狼獷。一個是翻譯馬格里,另一個則是副使劉錫鴻。
馬格里是蘇格蘭人,道光末年隨著鴉片戰爭的硝煙來到中國,先在上海海關當差,後來被曾國藩聘為江南機器局的技師,開始出入中國官場,以「客卿」身分受聘中國。為表忠心,他把自己的姓氏譯得頗有些中國化,且仿中國人的習慣也加了一個表字曰:「清臣」--顯然是要死心塌地做大清的臣子。後來,李鴻章籌辦海防,建大沽炮臺,試炮時,江南機器局造出的炮彈出膛便炸,毀了好幾門炮,傷了好幾個人,於是他這個技師被撤了差。但來華幾十年,他已能操一口流利的華語,李鴻章棄其短而用其長,改聘他為北洋大臣衙門翻譯,幾年下來,竟保舉了他一個五品同知銜。
此番郭嵩燾組團使英,馬格里由李鴻章推薦到使團任職,因此,他既是出公差又可了回鄉探親的私願,公私兩便,行李費由公家報銷且可享受外交官所帶物品海關免稅的優待。因此,他在京滬兩地採辦了大量的中國土特產和珍奇古玩,像去參加萬國炫奇會(博覽會)一般。
而劉錫鴻帶的東西卻有些怪,是別人意想不到或認為不必要的。
就說煙具,他們一行幾乎個個都抽煙,但工具各有不同,郭嵩燾抽水煙,一支作工考究、景泰藍底座的白銅煙袋不離左右;馬格里抽雪茄,一支粗大的古巴雪茄長期噙在嘴裡像塞了隻茄子;廣東番禹人劉錫鴻用的卻是一支已被煙薰火燎成醬紅色的竹煙筒。
至於引火之物則差異更大。這幾年歐風東漸,津滬等地得風氣之先,市面上洋貨充盈,就是窮家小戶也用上了火柴,對這小玩意兒,天津人開始叫「洋取燈兒」,上海人則稱「自來火」,後來則統一稱「洋火」。
這種紅頭小木棒才幾個銅子一匣,取一根隨便在什麼硬物上一擦即出火,用起來十分方便,使團成員早用上了,講究一些的更用上了「打火機」。
劉錫鴻對這些卻視而不見,取火仍用老式的火鐮、棉絨,度火用土造毛邊紙捲成的紙煝子;別人早吸上了洋煙他卻仍是吸土煙。因此,他怕在英國買不到這些土特產便帶了一大捆毛邊紙,幾大包雲南煙絲,裝在幾隻大竹簍子裡,上船時由武弁一一背上來。因此,他的行李僅次於馬格里。
眼下,眾人差不多都在休息了,劉錫鴻卻仍在整理行李。隨員劉孚翊見了大惑不解,乃說:「大人這是何苦來,用自來火吸洋紙煙多方便,帶這些東西好狼獷!」
劉錫鴻笑了笑,悠悠地說:「你知道什麼,我輩為朝廷官員,應處處以身作則,可不能一出國門便忘了根本,就如吸煙度火,自我們祖先燧人氏鑽木取火後,火石、火棉、紙煝子用了幾千年,於是就有了專造這些東西的作坊,小民以此為業,若大家見了洋貨就愛,那以此為生的升斗小民豈不要斷了生計,國家不也因此斷了財稅之源?」
劉孚翊不意自己的關心會引來副使大人的訓斥,正懊悔不已,不想一邊的翻譯張德彝卻不以為然地笑了起來。
劉錫鴻忙問笑什麼?張德彝說:「劉大人未免膠柱鼓瑟--單不用洋貨也不是富國的辦法。更何況煙草本身就是泊來品,自古歷來我們的老祖宗只有茶酒的嗜好,哪有什麼煙?所謂淡巴菰(煙絲)還不是從南洋呂宋一帶傳過來的?至於煙具,我們中國人倒是越做越精巧,這是洋人遠遠比不上的,未見得只有你們廣東的破竹筒子才是國粹!」
張德彝說話時笑笑嘻嘻,卻分明有揶揄之意。劉錫鴻頓覺話不投機,不由恨恨地瞪了他一眼。
張德彝是同治元年同文館第一期的學生,那一期才十個學生,他即其中的佼佼者,畢業後已先後四次赴歐美遊歷,寫過好幾本有關出洋見聞的書,為辦洋務的人所重視,眼下雖只掛兵部員外郎銜,卻是使團中涉洋資歷最深的人之一,加之他又是一個旗人--出身漢軍鑲黃旗,劉錫鴻對他不得不另眼相看,眼下明知張德彝是在挖苦他,也只勉強笑了笑便訕訕地走開了……
與火車較勁
劉錫鴻一走,幾個品級較低的隨員都鬆了一口氣。
年輕氣盛的劉孚翊朝劉錫鴻的背影癟了癟嘴,轉身對張德彝說:「還是老兄見多識廣,一句話便把這老古董給駁回去了。」
參贊黎庶昌在他們爭論時還在碼行李,此時已閒下來,乃插言說:「不要稱他老古董,他畢竟還肯出洋,眼下見洋字就罵的人還不少呢!」
隨員姚若望說:「不過,眼下滬上反對鐵路的那班仕紳,卻和劉大人不謀而合。」
一聽姚若望提到鐵路,眾人的興趣又來了,他們擠在二等艙門口,紛紛要姚若望談上海紳民反對修築淞滬路的新聞。
姚若望是上海人,在京受職為使團隨員後,受正使郭嵩燾委派,提前兩個月便回了上海,因此對滬上鐵路之爭知之甚詳,出事那天他還趕到閘北去看了熱鬧。眼下眾人抬舉,他乃繪聲繪色地描述了那天的情景。
四年前,英國人以修馬路為名,在吳淞買了一段直至閘北的地皮,今年初開始動工,滬上紳民見修馬路也未在意,直到六月中旬「馬路」從吳淞口修到了江灣,且鋪上了鐵軌,運來了火車頭及車廂,揚言六月底正式通車,大家這才大吃一驚,明白洋人用的是瞞天過海之計。
在眾人紛紛反對之下,上海道馮焌光以侵犯中國主權為由向英國駐滬領事提出交涉,但英國人不予理睬;馮焌光乃提出收回路權,英國人卻說須待十年之後。雙方交涉未了,洋人卻不顧一切地舉行通車典禮了。
那天,成千上萬的人擁向吳淞和閘北看熱鬧,因洋人免票三天,便也有乘車去「過洋癮」、「開洋葷」的;但多數人卻是來抗議並試圖阻止通車的。他們中有衣冠楚楚的紳士,也有布衣短褐甚至赤膊短褲的苦力。
紳士們反對的理由是鐵路穿山打洞、火車風馳電掣,若讓它在中國推廣,勢必蹂田堙井,破壞風水,更不堪的則是毀墓掘墳,使祖先骸骨暴露。
苦力們卻只看到目前--洋貨從吳淞口上岸,無論水路旱路,少不得由他們肩扛車運、駕船背縴運往內地,好多失業的農戶和小市民以此為生。火車一通,他們的飯碗全砸了。
大家難得如此齊心合力詛咒鐵路。但洋人對眾人的咒罵不加理會,忙著開車的準備。
升火後便吆喝著招呼眾人去坐免費火車。
旁邊有心計的士紳便支使一班苦力,用一根粗麻繩子拴在火車最後一節車廂的橫槓上,當火車啟動時,眾人發聲喊,想拉住已啟動的火車,但拉大繩的人雖多卻不是火車的對手,火車才啟動,眾人便拖不住,待司機加大馬力,黑煙一冒,汽笛一吼,後面的人便紛紛丟手,排頭的幾個力氣大、脾氣強的大漢仍不肯鬆手,結果被拖了幾十步,人跌倒了才不得不罵著娘撂手。
從後面拖不住火車,眾人便成千上萬地在前面攔。洋人不得不停下來與之論理,攔火車的人說火車一開,煙筒火星迸冒,會引燃路邊房屋。洋人說保證不會,若引燃了房屋願予賠償。
但眾人仍是不依。就這樣吵吵嚷嚷,火車時停時開,到七月中旬的一天,終於有不肯讓路的市民被火車軋死的事發生了。於是滬上轟動了,大家紛紛罷市並擁上路基靜坐抗議。英國人也不得不讓火車暫且停開。
此事震動朝野,總理衙門為平息事態,接受李鴻章的建議,派直隸候補道盛宣懷協助兩江總督沈葆楨與英國駐滬領事談判。至於能否收回路權,則尚不知也。
姚若望一口氣說完了經過,劉孚翊馬上補充。
他也是最早到達上海的,也有幸目睹火車通行的情景,他說:「狗日的火車真神奇。據坐過的人說,從吳淞口到江灣二十幾里路只一袋煙久便到了,要說,『不翼而飛』四字安在火車上是再貼切不過了!」
張德彝說:「二十幾里路算什麼?那年我從法國巴黎到德國的柏林也才幾個鐘頭呢!眼下歐洲的鐵路已四通八達,出門真方便,什麼山高路遠、風濤之險的顧慮都沒有了!」
劉孚翊說:「滬上那些人也不知怎麼想的,洋人雖不該瞞天過海,侵犯了我們主權,但火車則沒有錯,要是我們也到處有火車那多好!」
「哼!你說好,可有人偏偏說不呢! 」張德彝冷笑著說,「剛才劉大人不是連洋煙、洋火都不用嗎,說東西雖小卻關係千百萬升斗小民的生計呢!」
「是的是的。」另一隨員張斯栒也插話了。他年過五十,是使團中年齡僅次於正使之人,他沒有劉孚翊那種衝動,也不知張德彝說的是反話,立即附和說:「火車雖神奇,只怕不適宜於中國,正如剛才副使說的,一舉一動,都不能丟開國計民生不想。火車有如此神通,若讓它四通八達起來,那好多販夫走卒、靠肩扛手提的苦力真會喝西北風呢!」
姚若望反駁說:「那也不一定。我聽人說,火車在道光初年才發明出來,這以前洋人往來交通貿易,不也是靠人力嗎,眼下他們那班下人是否都餓死了呢?」
「這話問得極好,」劉孚翊見有人支持便來勁了,他說:「眼下滬上士紳爭論火車是否適用於中國爭得十分起勁,有人說洋人奇技淫巧禍害中國,讓洋貨湧進來會使成千上萬的小康之家破產,窮家小戶更會絕了生路;有人卻認為洋貨見多了也可仿造,大家動手做出來與洋人搶生意,這樣就不僅不會妨害國計民生且有利於國計民生了。」
劉孚翊此說是眼下辦洋務的人的一貫主張,滬紳馮桂芬甚至寫進了他的專著《校邠廬抗議》一書中。姚若望以前在上海看到了這本書,對作者佩服不已。他也認為中國人完全不必畏洋貨,憑自己的聰明才智依樣畫葫蘆,造出與洋貨比美的國貨,與洋人展開商戰,這樣可奪回利權。眼下聽劉孚翊一說,忙笑著喚著劉孚翊的字說:「和伯此說正是馮桂芬書上說的,和伯莫非也看過《校邠廬抗議》?」
劉孚翊說:「當然,那確實是一部奇書,專談當前時政要務,左季高伯相稱它可與賈誼的《治安策》比美,列位不妨都看一看。」
「依我看,看書不如實地考察。」一直不大開口的黎庶昌此時插話了,他說:「《校邠廬抗議》我手中也有一部。據我所知,作者並未去過泰西,故多採用道聽塗說,有人云亦云之弊。此番朝廷派我等出洋,坐探西人國政,不正好對照書本,相互印證麼?」
眼下劉錫鴻回房去了,聚在一起的人中數黎庶昌地位最高,學問也最好,眾人自然以他的話為圭臬,當聽到「坐探國政」四字,便一齊點頭……
坐探國政
其實,此刻在一旁點頭的還有一人,這便是郭嵩燾。
槿兒已上床休息,他卻了無睡意,於是來二等艙看望同僚們,在大餐間拐角處,聽眾人議論,覺得很有意思,尤其是黎庶昌那「坐探國政」四字,他覺得對使團使命概括得十分準確,一時各種念頭湧上心來,乃決定不再去打擾眾人,一人默默地回到了自己房間。
此時槿兒己在床上發出了輕微的鼾聲,他卻坐到了書案前,想把跨出國門頭一天的經過和感受寫進日記。不料翻開日記簿,十多天前寫的一首詩赫然出現在眼前:
大地回環一水涵,乘槎歷斗助清談。
塵中世界原同趣,天外波濤定飽諳。
碧海秋深風正穩,黃花別晚酒初酣。
君歸皓首吾方出,此意憑誰一笑參。
他想起這是送美國人威廉士的詩。威廉士於道光十三年來華傳教,自學中文,於經史子集多有涉獵,居然把詩韻和平仄也弄清了,作的詩也像模像樣的。他咸豐七年開始出任美國駐華使館翻譯,同治六年後以參贊署理公使。前後來華四十三年,此番以近古稀之年回國應聘耶魯大學,講授中文。在京之日,他與郭嵩燾交往頻繁,回國時郭嵩燾賦此七律為贈。
想到威廉士在異國他鄉幾近半世紀,終於功成名就回國執教了,而與他年齡相差無幾的自己則在這時才毅然出國,是不是太晚了呢?
他不由翹首窗外--冬日苦短,眼下海上雖黑漆一團,但時鐘才指著八點半,外面甲板上,在幽幽的燈光下,仍有人影在晃動,船尾傳來一洋人水手的歌聲,是那麼淒切,像是在思念遠方的親人,他不由也想到了自己的命運……
泰西,這是眼下中國人對歐美的統稱,如歐美人稱中國為遠東一樣,都是極遙遠的意思。這以前,泰西和遠東互不通往來,漢代派往西方的使者僅到了中亞,最遠也不過地中海邊。唐僧取經才到了印度,明朝的三寶太監鄭和算是走得最遠,按說已到達了非洲東岸,若再往南出好望角便可到大西洋,可惜功虧一簣。因此之故,東西方隔閡殊深,中國的正史上居然說西方的羊羔是從地裡長出來的,臍帶還牽連著大地;而歐洲人則說中國人用小米餵一種狀似蜘蛛的蟲子,幾年後蟲子肚子開裂,可取出絲來織成綢緞。
不同的是自明朝後,隨著海路開通,泰西源源不斷有人西來,把在遠東的見聞帶回國去,湯若望、利瑪竇、郎世寧等西方人甚至在中國做官,他們對中國的情形可謂瞭若指掌,而堂堂中國對泰西情形仍一無所知。
今天,自己奉旨使西,坐探西人國政,這可是亙古第一遭,本應是一件大好事,但此舉卻為士大夫所不諒,以致他在接受任命後在朋輩及同僚中頗遭白眼,遠在湖南的親友也紛紛寫信阻其行。
他想,親友的不諒不難理解--眼下,同為湘陰人的左宗棠已力排眾議,集兵糧餉運大權於一身,督十萬湘楚健兒大舉西征新疆,且已取得一連串的勝利,煌煌武功大振了民氣、士氣,於萬馬齊喑的局面不啻一聲春雷。
鄉人只看重左宗棠的武功,卻不明白自己使西將對後世帶來的影響,湖南人素以倔強著稱,到了黃河心不死,撞了南牆不回頭。就在他們正做著中興之夢的時候,自己卻充當「謝罪使」,去向「夷人」的女主賠禮道歉,他們能不憤怒嗎?
可眼下己是開弓沒有回頭箭了!
他就帶著一肚子豪情、一肚子怨氣上床就寢了。
不想就在這時,他感到外面風更大、雨更猛了,人在床上憑直覺感到船的顛簸,似從數丈高的波峰跌入低谷,大浪打在船身上,發出了巨大的轟鳴聲,十分恐怖--出行的第一天便遇上大風暴,不知是什麼兆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