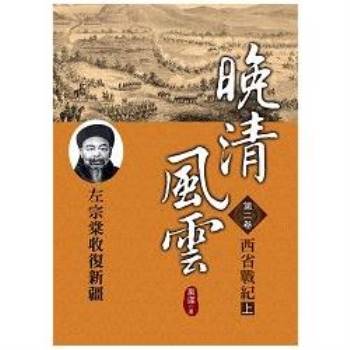第一章 載譽東歸
遇險
年近七旬的左宗棠,近來心境一直處於一種異常的亢奮狀態中。
當六匹高大健壯的汗血馬拉著寬敞富麗的後檔轎車在官道上狂奔時,他仰坐車中靠椅上,不時撫髯望一望窗外。
車窗外,獵獵西風,莽莽黃沙。兩千里的河西走廊上,正行進著一支雄壯的鐵騎。一桿巨大的紅底藍邊大纛在隊伍前面迎風作響,「恪靖侯左」四個大字隨風上下翻動。旗手是一個黑塔似的莽漢,絡腮短鬚,寬膛大臉,處此隆冬塞外,卻只穿一領藍夾綢戰袍,外罩一件紅緞滾邊湖青色馬褂,袖子捲得老高,紅纓帽背在腦後,那一根又粗又黑的辮子挽在頸上,黑煞神一般。隻手擎一桿大旗開道。他的左右各一名與他裝束差不多的副手緊跟護衛,距他們三騎好幾丈遠才是大部隊。
他們是二等恪靖侯東閣大學士太子太保督辦新疆軍務欽差大臣陝甘總督左宗棠的親軍。
左宗棠為大清國西北支柱,光緒二年至四年(西元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指揮十餘萬西征軍,收復了新疆南北路。正當他厲兵秣馬,準備驅兵收復為俄國佔領的伊犁時,接到詔書,令他回京商討戰守。他遂於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年)十月中旬啟節東行。
在戰雲密布、戰爭一觸即發的此時,他舉手投足皆至關重要,俄國人對他的行蹤特別關注,加之動身前一日,又傳來俄國黑海艦隊中最大的一艘海軍旗艦--排水量為九千六百噸的「大彼得號」啟碇東駛的消息,為樹軍威、壯觀瞻、防突變,他特隨帶精兵五千,由王詩正、王德榜率領,轉赴張家口、山海關一線布防。
這五千精騎,皆百戰之師,熟悉歐羅巴新式戰術,足可與俄羅斯的哥薩克騎兵抗衡。把他們擺在京畿一線,京師可高枕無憂。而他此行有此五千精銳護衛,東歸行色頗是壯觀。
左宗棠一向講究軍容,尤其是自己督率的親軍,是從十萬西征軍中精選出的騎兵尖子。他們雖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一口道地的湖南土話,卻生得南人北相,五大三粗且精於騎術。
左宗棠又講究相術。平日甄別部屬,考核將士,面相是首要的一關。他的左右親兵,尤其要注意精選,先看臉型是否端莊、勻稱,再看眼神是否有凶殺之氣。他相信相書上的話,凡田字、國字臉型者是大福大貴之相,由字、甲字或申字臉型者,為小人福薄之相。眼光神采飛揚前途無量,目澤昏濁精神萎靡者有遭凶死的可能,也就是「妨主」之相。因此,由他親自目測的親兵,無一不是團團大臉、高鼻闊口、虎虎而有生氣的偉丈夫。
督標兵餉俸從優,從不拖欠。加之出關後,捷報頻傳,犒賞接連不斷,這些勇丁們真是個個紅光滿面、服飾光鮮,與西北遭連年兵燹而鳩形鵠面、形銷骨立的百姓比,簡直有天神與鬼卒之別。
他們一色嶄新的藍綢戰袍,袖口捲起,露出「蘿蔔絲」或紫羔皮毛裡,戴紅纓帽,著黑漆快靴,肩上扛一色德國造新式毛瑟槍,槍身烤漆簇新,在陽光照射下藍光熠熠,與槍刺交相輝映。軍官肩上還挎一支使士民驚詫不已的單筒望遠鏡--傳說中的千里眼。而最令人咋舌的是隨軍行進的、由三匹馬牽引的克虜伯大炮。那修長而偉岸的炮身,翹然指向藍天,黑洞洞的、足有碗口大的炮口,像張著大口的巨蟒,一下能吞噬無數人的生命。
四年前,大將劉錦棠指揮所部「老湘營」攻烏魯木齊時,在紅廟子只放了一炮,就使有英、俄裝備的安集延人及回民軍炸了鍋,一潰而不可收拾,從而獲得了「一炮成功」的美譽。至今日,它隨隊伍路過關塞或村鎮時,凡聽過「一炮成功」故事的人們,除了爭著瞻仰這位赫赫有名的爵相大人的豐儀,也爭著把目光投向隨行的隊伍,尋覓那威懾敵膽的「紅衣大將軍」。
左宗棠的目光,此刻緊盯著擁在座車前後的精騎。二十餘年的馬上生涯,他這個書生習慣了徜徉在這壯觀的場面和敬畏、戰慄的目光中,習慣了聽這人喊馬嘶、刀槍碰擊的聲音,習慣了聞這一股股馬尿、馬糞摻和的膻臭味,也習慣了這緊張而富於傳奇色彩的生活。他以此為樂,覺得這也是他的文章,他的傑作。他只有生活在這刀與火的氛圍中,才能時時忽發奇想,寫好這樣博大精深的「傑作」。
多麼壯觀的場面,多麼精銳的隊伍啊!這是自己親手締造、親自指揮,與自己聲譽、地位同休戚而共始終的隊伍。想當年,在長沙金盆嶺奉旨草創楚軍,自江西攻入浙江擊長毛,隨後出閩粵而指關隴,攻擊捻軍與回民軍,又馬不停蹄人不卸甲,出嘉峪關而縱橫沙磧,掃蕩了天山南北,立下了永垂後世之功勳,使中國軍人威名遠播,世界列強刮目相看。他們真不愧是支撐大清帝國的精英,三楚士民的驕傲!
左宗棠感歎,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當年在長沙應募的老兵,除了為國捐軀者外,餘下的熬到今天,都已是袍褂鮮明、翎頂輝煌的戰將了。楚軍精神長存。二十餘年中,他們追隨他,這個楚軍老帥,從東南到西北,轉戰十數省,行程幾萬里,大小上千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直令長毛元凶馬前授首,回民軍巨逆傳檄受擒;驅馳塞外,又使有英俄做後盾的安集延人望風而逃。而今,拓疆數萬里,聲威震歐亞。中國外患,常在西陲,周逐獫狁,秦禦強胡,漢擊匈奴,唐征突厥,數千年來,能直搗龍庭,犁庭掃穴,誰可與我相匹敵?
「丞相天威,西人不復反矣。」這是河州回民大阿訇馬占鼇於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春間請降時說的話。此人真不愧為著名「猾賊」,他知左宗棠常以諸葛亮自比,揀了一句現成的話恭維他。
其實,諸葛一生事業,結束在「出師未捷身先死」七個字上,晚年蹉跎祁山,關河阻絕,遙望中原,路漫漫其修遠,後來,就連三分天下也成為泡影。若以功業而論,諸葛亮又何足道哉!
而左宗棠的事業,與之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南疆八城光復,縱橫數千里的新疆全部重歸大清皇輿,紅旗傳露布、捷報達京師時,皇帝的諭旨是這麼褒獎的:
……新疆淪陷,十有餘年,朝廷恭行天討,轉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該大臣剿撫兼籌,議定先規北路,首復烏魯木齊,以扼其總要,旋克瑪納斯,數道並進,規復吐魯番城,力爭南路要隘,然後整旆西行,勢如破竹。現在南八城一律收復,此皆仰賴昊天眷佑,列聖垂休,而兩宮太后,宵旰焦勞,知人善任,用能內外一心,將士同命,成此大功。上慰穆宗毅皇帝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實深欣幸。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恩施,用酬勞績。欽差大臣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籌兵籌餉,備厲艱辛,卒能謀出萬全,膚功迅奏。著加恩由一等伯晉為二等侯。欽此!
舉人出身的左宗棠,文拜相,武封侯,開國以來,能有幾人可與之相比?
想到這一切,他不由意氣發舒,心潮澎湃,產生出一種目空一切,睥睨萬物,直如騰身霄漢的大鵬但恨天低的激情……
然而,當他突然回眸瞥見几上放著的一份文稿時,目光霎時變得陰鷙而凶狠了--這是從北京用四百里加緊快差送來的抄件,作者不是別人,正是繼曾國藩之後,與他暗暗角力的李鴻章。
楚軍在天山南北摧枯拉朽般的勝利,已為四年前左、李之間那一場辯論做了一個很好的結論。如今,「海防」與「塞防」之爭,已以李鴻章的失敗而寫進了國史。此公到底不甘心,在忍氣吞聲三年之後,竟然又一次搖唇鼓舌了:
……往者,微臣籌及西事,每不免鰓鰓過慮者,誠恐恢復故疆,則有名而無實;變通商務或受損於無窮也……
隱隱約約,拐著彎子,不仍是為四年前「興海防,廢塞防」做翻案文章嗎?左宗棠想,什麼「有名無實」,分明是當年論爭時,那「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的老調重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醉翁之意,並不在酒呢。
接下來,李鴻章認為,既然朝廷已賦予崇厚全權,則崇厚所定條約便合法,斷不能輕率更改,不然,恐失信於列強各國。接下來,他又提出了所謂的「補救」之法,而他的「補救」則是趕快恢復與俄人「通商」--所說各項辦法,無一不與左宗棠唱反調。
從附在李鴻章奏稿後面的上諭口氣上看,兩宮太后及輔國恭親王對他此奏未做明確肯定的批示。左宗棠想,只要李鴻章此議未成定局,事情就有挽回的可能。這些年來,遠離京師,所謂一出都門,便成萬里,紙短筆頹,不能把滿腹衷情上達。他想,難得此番奉召,應盡快趕回去,向兩宮太后及執掌樞輔的恭親王爺一吐胸中積愫。
「袁升,已走了幾個台站啦?」
他用那鷹隼一般犀利的目光掃了一眼窗外,又抬腿踢了踢蜷伏在腳邊氊子上打盹的差官袁升。
袁升,一個手極長而身子較矮的長臂猿一樣的漢子。他因多次往返天山南北路及河西走廊,對這一路的軍台道里記得滾瓜爛熟,此刻,他雖如一隻馴服的小犬依伏於一側,但耳目極警覺,一聽左宗棠發問,不再複述,馬上坐起,屈指數道:「快呢,已過了雙井子,前面是今天的宿站--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
「天色不是還挺早嗎?」
「是啊,連日奔波,總算進關了,明日就要進肅州,能不能讓大家整理一下軍容?」
「肅州也不是初次進駐,不必如此張羅。我看,在嘉峪關不要停留,趕到肅州宿營最好。」
「這可要多走七十里。」
「多走七十里無妨,眼前局勢瞬息萬變,可不敢隨便耽擱!」
「您的身子?」
「沒關係。」
左宗棠抖擻精神,在袁升肩上拍了一下,袁升知道主帥犯了倔脾氣,只好掀開車門溜下去傳令。
本來,自劉錦棠從阿克蘇趕到哈密後,前方軍事已做了妥善的交代,十月初完全可以啟節返京的,不料劉錦棠及各路統領一致挽留,因為十月初七日乃是左宗棠的華誕。已是望七之年的左宗棠,頭白臨邊,難有息肩之日,部屬不代為操辦,相與慶賀,又賴何人?
「老師,難得有今日之心境啊。」劉錦棠殷切地挽留。
眼下戡亂的鼙鼓已息,可邊陲烽燧又起。身為國家柱石之臣,正受欽命徵召,所謂「君命不宿於家」,奉旨即須遵行,談不上有清閒之日,善體人意的劉錦棠,說了一句很得體的話。
現在想來,他有些後悔,就為了這個世俗的陋習,耽誤了整整十天時間。在平常人的一生中,十天不過短暫的一瞬,可對運籌帷幄、折衝樽俎的大臣,處此關鍵時刻,十天,或許就是成敗的契機,這時光的價值,實在無法用金錢來估量。
他覺得自己當初似乎有些不能自持,如果堅持原議,十月初二日動了身,眼下已過武威郡,快要望見蘭州城了……
「轟!」
突然,就在近處,似乎就是頭頂上,發出了一聲沉悶的巨響,隨著身子向前一傾,他趕緊扶住了兩邊的扶手,接著,車子停住,人聲、拉槍栓聲、拔刀出鞘聲、吆喝牲口聲立刻響起,鬧成一片,在這一片嘈嘈雜雜的聲音中,似乎有一個粗嗓門喊了一聲「有刺客!」
於是,接下來便是嚷成一片的「抓刺客」聲。
不知幾時又已溜上車的袁升,此刻就像一頭受驚的豹子,「蹭」地一下,操起短槍鑽出了車外……
左宗棠驚魂甫定,也掀簾探出了身子--原來隊伍已進入了一條狹長的、兩邊石壁聳立、形勢極其險峻的峽谷之中。因要在天黑前趕到肅州,隊伍速度加快,不料走至此段,一塊巨石從天而降,正砸在他座車後面的行李車上,一輛四輪大車被砸得粉碎。
這時,眾差官、親信已一齊湧到車前,將左宗棠團團護住,待發現前後左右並無敵蹤而危險來自頭頂後,差官朱信、戴福才分開眾人,將左宗棠攙扶到遠離危險的一處草地上坐好。
左宗棠安下神,順著眾人手勢望去,只見石壁頂上青苔滑脫,這巨石分明是有人從上面推下來的,而不是偶然的坍塌。看來,這是有人趁此機會行刺於他,此人預知他將經過此地,且已偵知他的座車形狀--那華麗的後檔車也是太顯目了,好在車速甚快,石壁又高,終於只誤中副車。
這時,眾人皆紛紛議論,詛咒這刺客用心之惡毒,甚至說若抓住了他,非要予以三萬六千刀的魚鱗剮不可,而袁升已不待吩咐,早率領一小隊親兵,抄小路向壁頂包圍。
只有左宗棠一人置身事外。雖然刺客是向著他來的,可他仍在想李鴻章的事,想他的人及他那一份奏摺……
非常的時代,造就了非常的人物。太平天國的興起,成就了湖南一代非常人物的湧現,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一個個如璀燦的明星,踴躍而出,成為湘人的驕傲。何物李鴻章,竟也想配曾、左而成鼎足之勢?
左宗棠嘴角,漾起一抹輕蔑的冷笑。
酒泉之夜
途中遇險的不快,早被過嘉峪關的興奮沖淡了。左宗棠發現,自己這高亢激昂的情緒,甚至已影響了全體隨行人員--他就親耳聽見車旁有一個老兵在馬上用含混不清的鄉音叨念:「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好啦,總算是直著回來啦!」
是的,總算是直著回來啦!這一句話概括了隨行人員的心境。
想當初,大哥左宗植勸左宗棠功成身退、辭謝陝甘總督之任,謂「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彼時左宗棠已五十有六了,可大哥不了解弟弟的雄心,沒想到弟弟就在望七之年還荷戈西行,渡流沙而涉戈壁呢!然而,想到四年前出兵新疆時的內外形勢,他還有幾分後怕,這當然是局外人所沒有的。
「狐死首丘,代馬依風,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這是班超託妹妹班昭上書漢和帝時的一句名言,也是他齒髮搖落、晚景蒼涼的真實寫照。想當初,班超投筆從戎,入虎穴而獲虎子,立下那永垂後世的功勳,那是何等的英雄!不料竟在暮年,上疏求還時,會發出如許令人心寒齒冷的哀語!人們只知有揚名西域的「定遠侯」,豈知有垂垂老矣而欲歸不得的「班都護」?無邊的戈壁,寂寞的荒漠吞噬了多少英雄豪傑,仁人志士!昔日,他們叱吒風雲,揚威邊塞,而今皆化作了道邊壘壘白骨。「祁連山下草,寂寞少人煙,魂魄千年後,猶思渡酒泉。」人生哀樂,思鄉懷舊之情,舉世一轍。仁人志士,亦在所不免。
左宗棠詫異自己在過嘉峪關時,興奮的情緒中,竟會摻和著這種不協調的思想感情。而這種淡淡哀思和莫名惆悵,又與時下全軍振奮的氣氛多麼地不相稱啊!
望見了,終於望見了,馬兒慢慢地行,車兒慢慢地隨,他,終於望見了夕照下的嘉峪關城樓,望見了自己親筆書寫的「天下第一雄關」六個金光閃閃的大字。
這時,三軍肅穆,一齊向匾額注目,連空氣也似乎凝固了……
他想,此番入京,必然主戰,東北為防俄之前沿,自己當然會義不容辭,那麼,幾個月後,自己可能又要出現在長城的另一端,出現在另一「天下雄關」的城樓上,這巧合,這壯舉,將是後世文人墨客多好的題材啊!
嘉峪關至肅州七十里,道路平坦,兩旁遍栽楊柳。黃昏落日,柳絲悠悠,似乎也會盡人意……
他一直保持著這高亢激昂的情緒,七十里驛道十分輕鬆,倏忽便過。
肅州,又名酒泉。為安西、肅州道駐地,相傳漢代霍去病出擊匈奴,欽使帶來了十瓶御酒,賜賞去病,一向與士卒同艱苦的霍去病以十瓶御酒不夠數萬將士共飲,乃傾酒於泉中,分飲眾將士,「酒泉」因此而得名。
左宗棠當年率軍入隴,先駐節隴東的平涼,次移安定,再小住甘州,然後,督大軍進圍肅州。所謂「平、定、甘、肅」,肅州為最後一站,也是他待得時間最長的地方--後來進軍新疆,為節制前線各路大軍,督促糧餉的轉運,左宗棠又選定肅州為大本營,自光緒二年四月至今年四月,在肅州鳳凰台道署住了整整四年。
今天,肅州城因左宗棠的過境而披上了盛裝--行程改變,一行人提前到達雖使人有些手忙腳亂,但城門口那座特大的牌樓是先一天紮好的,在官府的催督下,從牌樓下起沿街擺起了層層香案,老幼婦孺漢回民眾黑鴉鴉的一片,在留守的肅州同知王仲甫暨道署僚屬率領下頂香恭迎。
待走在隊伍前頭開道的頂馬一過,眾人一齊圍上來,口中不約而同地喊起了「左爵相」、「左宮保」。
因有關外遇險的那一幕,眾人皆有些忐忑。安肅道福裕及道標都司宋玉寬是從安西州一路護送、陪同左宗棠入關的,此時更是惴惴不安,見眾人圍上來,他們又不便吆喝、驅散眾人,於是,他二人只好相約下馬,扶著車輪,緊緊護衛在左宗棠座車左右,雙眼注視兩邊,一刻也不敢懈怠。
左宗棠微笑著,向左右點頭。
進城後,他仍駐節於鳳凰台的安肅道衙門,此地房屋較為寬敞,環境也很幽靜。為了他的安全,安肅道福裕調了兩百名道標兵,由都司宋玉寬率領在圍牆外巡邏。內衙則由左宗棠隨行的親兵警戒。
肅州為東歸途中第一大站,又是左宗棠駐節四年的行轅,很多事須做交代,左宗棠要在此停留兩天,距此不遠的南關,有一座由清真寺改建的定湘王神廟,他要在離開前去廟裡最後一次燒香,這些事雖未寫在注明欽差行止的排單上,但袁升早已知會過福裕了。欽差大臣關防極其縝密,加之旅途勞頓,所以,他一入內衙,即下令放炮下柵,來請安的道、府官員屬吏,一律被擋駕。
刺客
袁升是在起更後才進城的。左宗棠正在房中等他的消息。
「可恥的傢伙,真自不量力!」
據他說,他們在壁頂除發現有人住宿的痕跡外,在撬石頭的地方,有人用刀刻下一句話:為阿拉之道而戰!這是回民起義軍與官軍作戰時常用的一句口號,「阿拉」即真主。
袁升帶人四下追蹤,終於在東北方向發現一匹快馬在飛奔。袁升居高臨下觀察,斷定此人是奔阿拉善額魯特方向。
「我從後面用望遠鏡瞄了他很久。」袁升說,「這是一個好騎手,那馬也絕不是一匹普通的馬,我們徒步根本無法追上他。」
袁升有些後悔,當時沒返回騎馬,他請示左宗棠,是否諮請阿拉善蒙古親王,請他們協助搜捕這個凶狠而狡猾的刺客。
左宗棠未置可否,只揮手讓袁升去用晚餐。
袁升退出後,左宗棠翦著雙手在房中徘徊,晚餐時,他就著火鍋喝了兩小杯酒,這更激發了他的豪情,他只想尋找發洩激情的途徑。
刺客的出現,於他並無大影響,他已料定,此人必來自漏網的回民軍,但單身匹馬又有何作為呢?成千上萬的回民武裝尚可屠戮殆盡,像白彥虎那樣的渠魁巨匪也只能亡命國外,余小虎那樣的凶狠之徒也已喋血轅門,區區一漏網小丑,跳樑於山谷荒漠之中,能興多大的風,起多大的浪呢?我命繫於天,又豈是這等蕞爾小丑所能算計的?
安肅道衙門是一所多院落的府第,內衙分東西跨院,南北廂房,後面還有大小花園及戲臺,布局很講究,而陌生人進來卻有如進了迷魂陣,分不出南北東西。
袁升侍候左宗棠在這座府第住了四年,對府中門徑非常熟悉。因白天出現意外,左宗棠雖是那麼淡然,作為他的貼身親隨,袁升卻不敢稍有鬆懈,他不敢飲一口酒,匆匆吃過飯,燙過腳,已是深夜了,他來在左宗棠房中,見主人正在燈下看一份《申報》。
左宗棠見袁升進來,忙放下報紙,從老花鏡架上望著袁升,沉吟半晌才問:「都睡了嗎?」
「都睡了。」
「去喚那個人來吧。」左宗棠說。
袁升低頭答了一聲是,便轉身退了出來。
這一問一答,只有他們二人明白。約過了兩袋煙工夫,一個嫋嫋婷婷、仍打著呵欠的女子被袁升帶了進來。
待這女子走進左宗棠的屋子,袁升便從外面把房門帶關,他明白,自己連這下半晚也無論如何不能睡了,因為事後這女子還要送回她的住處。自左宗棠今年四月出關,已半年多未見她面了,他知道,他們這一聚,有很多話要說,很多事要做。
袁升伸了一個懶腰,想在門外尋一個避風的地方坐一會兒,打一個盹。安肅道辦差雖格外小心巴結,連欽差一些生活細節也照顧到了,但卻不曾為下人多想一想。此時門外的袁升,連避風的地方也沒有。
袁升蜷伏在門檻上,抄著雙手埋頭打盹,就在這朦朦朧朧中,他似乎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不像失群的孤雁,也不似草間的蟲鳴,它,極其細微而又極其清晰。這是只有像袁升這樣久負警衛重任的人才能在茫茫夜空、萬籟俱寂的情況下捕捉住的。
一下,又是一下……
像夜貓子在沙地上走,像蝮蛇在草地上爬。
袁升昂頭,在心中默數。
猛地,他一下躍起,閃身往前面廊柱後一縱,與此同時,只聽「忽」地一聲,一道白光往他剛才的位置飛來,「錚」地一聲,像有一利刃牢牢地釘到了身後的門框上。
「砰,砰!」袁升以極快的動作,拔出腰間的手槍,對準前面花廳那一道突出的山牆連放兩槍。隨著槍聲,只見山牆後一陣瓦響,突然躍出一個人影,「騰」地一下,落到了西花廳的天井裡。
「抓刺客!」
袁升一面喊,一面跟著追了出去。
這時,已入睡的親兵們一齊驚醒。睡在右廂房的親兵朱信動作極快,他只穿一條褲衩,光著上身,操一把短刀一個縱步衝出了房門,只見庭院裡寂無人影,除了遠去的奔跑聲,就像沒發生任何事一樣。
此時此刻,朱信最關心的當然是主帥的安全。他三步併作兩步跑到正廳,只見左宗棠寢室房門緊閉。他一時忘了自己竟光著上身,只對著房門喊道:「爵相,爵相大人!」
左宗棠早已拜東閣大學士。官場習俗,照例應稱其為「中堂大人」,唯「中堂」與「宗棠」諧音,恭敬的稱呼反易被誤為「稱名道姓大不敬」,下人為避忌這點,一律改稱「爵相」。
「先點燈吧。」房子裡傳出左宗棠極安詳、平穩的聲音。
朱信頓覺懸著的心放了下來,這才發現自己竟光著膀子,冷浸浸的。這時,戴福等親信差官及外院巡邏的兵丁一齊擁了過來,一時燈火通明,人聲鼎沸,朱信乃返回屋去穿衣。
見到主帥無恙,大家寬心,正要詢問槍聲的由來,只見房門「咿呀」一聲,左宗棠已出現在臺階上。
「待著幹什麼?快幫助袁升去。」左宗棠沉著地下令。
一言未了,只聽袁升在外高聲應道:「不必了。」
紅頂差官
袁升在十萬西征軍中,人緣最好。幾乎人人都認識他,知他是左相心腹,是令人羡慕不已的「紅頂子二爺」。
他今年三十六歲,從軍已有二十一年,想當初,他長到十五歲,還沒有名字,「袁升」是他的「三爹」給取的--咸豐十年,左宗棠奉旨在長沙金盆嶺募軍。湘陰柳莊左家的佃戶袁四聽說了,忙帶了幾塊燻狗肉,一罎子泡酸菜,牽了他的二兒子「狗伢子」來看望老東家。
「三爹,」老佃戶不知官場路數,仍用家裡的稱呼,按排行稱已是四品京堂的東家,「我家狗伢子腰上有顆痣,俗話說:一痣痣於腰,騎馬又挎刀,看來是一個吃糧的料子。可他平日沒出過門,嘴笨手笨,不會見風使法。投別棚別哨我不放心,讓他跟您提個夜壺何如?」
左宗棠望一眼面前這個瘦猴一樣的小子,不但面目瘦得像猴,且手長腳短,高顴骨尖下顎--全是猴兒的特徵,尤其是那一雙圓而小、咕嘟嘟四處亂轉的眼睛,活脫脫是猴兒無異--照相書上說,凡人生異相,必獲大貴。
只瞟了一眼,左宗棠心中已喜歡上這個佃戶的兒子了,不等袁四再嘮叨下去,馬上笑著答應留下「狗伢子」。
待老長工一走,左宗棠便使他去營務處上個名字,直到此時,他才突然記起,這些天來此投軍的窮漢多沒名字,是營務處的師爺們隨口取的,為討吉利,一般都叫「連升」「連捷」或「得功」「得勝」之類。幾天下來,已滿營盡是這類名字了,終不成自己面前又冒出個「袁連升」來。
「你就叫袁升吧。」左宗棠口中說著,想到的是「猿臂猱升」的典故。
「是,謝三爹,這名字有什麼來歷沒有呀?」狗伢子窮根究底。
左宗棠很喜歡這副憨大相,乃逗他道:「猿升猱捷,會往上爬啊,我為你取這個名字,將來升官快。」
袁升當時高興極了,忙趴下給左宗棠磕了個響頭,又伶牙俐齒地說:「三爹是『夏尚書做官--一下遮蓋了湖南江西兩個省』,我沾這點光,將來還怕少了官做?只怕做不像呢。」
夏尚書是指明朝名臣夏元吉,他祖籍江西德興,父親做湘陰教諭,後來便落籍湘陰。夏元吉以拔貢出身,歷官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四朝,官至戶部尚書,死後諡忠靖,相傳他在京做官時,多照顧江西、湖南同鄉,故湘陰有那麼一句俗話。佃戶的兒子是個粗人,也只會說這種俗話,碰到當時左宗堂正遺憾自己起家乙榜,與曾國藩帳下李鴻章、郭嵩燾等翰林比,有時難免自慚形穢。一聽今日袁升拿由拔貢出身而官至尚書的夏元吉比他,倒也歪打正著。當下笑顏逐開,把他留在身邊,當一名貼身親隨。
「三爹」也真肯照顧他。每次奏捷、敘軍功請獎時,總囑咐師爺,給袁升上一個名字。只幾年工夫,他的「三爹」做到了正一品封疆大吏,他也水漲船高,以軍功保至紅頂花翎的記名總兵。
「袁升」這名字是左宗棠給取的,也只有左宗棠叫得最多。以前,他是個軍漢,是個「糧子」,同鄉故舊見了他,仍沿習舊稱「狗伢子」或「袁猴子」,出外時,他是左相親隨,別人要叫一聲「總爺」或「二爺」,到現在,堂堂總鎮,武職正二品大員,別人不但不能直呼渾名,且有些不敢貿然犯諱了。
不過,袁升不拿架子,人極隨和。故此,楚軍各營各哨的人,上至統領、營官,下至伍長、護勇無人不喜歡他。他品級雖高,卻從未署過一任實缺,這不是因為軍功保舉太濫,有官銜而無法補上實缺--他若能夠做官又想做官,「三爹」一定設法給他補上了。無奈他一來大字不識,學不好官場應酬,二來也不願離開服侍已久的「三爹」,所以,仍一直在左宗棠身邊當親兵,夜壺當然不讓他提了,可做的事卻也實在比提夜壺高雅不了多少。
為此,別人有時稱他為「紅頂子二爺」。
小虎
「紅頂子二爺」的功名一點也不僥倖,二十多年來,他追隨左相,南征北伐,練就了一身武藝和膽識,作為一名貼身親隨,一身繫主子安危,半點懈怠不得。他摸透了主子的脾氣,人像猴兒一樣機靈,手腳也像猴兒一樣殷勤,無論在何時何地,他都像影子似的、沒沒無聲地跟著他的「三爹」轉,「三爹」也一刻也離不開他。
剛才,他躲過刺客朝他擲來的暗器後,朝山牆連發兩槍,心知未擊中目標,待他衝出院門,來至西花廳臺階上時,只見一個高大的黑影已跳到天井裡,正預備逃往外衙,袁升與他僅五步之遙,於是,他對準此人後胸猛扣扳機,不料就在這節骨眼上,槍子兒卡了殼,袁升好惱火,他用力把槍往刺客頭上擲去,沒想到刺客正好於此時轉彎,拐入通後花園的迴廊,自然沒砸著。
袁升心想,道署內外有巡更護院的兵丁,剛才響槍,料想都已聽到,此人是插翅也逃不出去的了,於是,他拔出腰刀,緊緊跟上去。
刺客是尾隨袁升那一小隊人在起更時混進道署的,目標自然是衙內住著的、一身牽動著西北大局的人物左宗棠。不過,他還從未進過這衙門,只見院落重重,究竟不知他的目標宿於何處,待伏在暗處,認準了目標,卻不料袁升如此竭忠盡職,竟守護在房門口寸步不離,他明白,不收拾門口蜷伏的這名警衛,就根本無法達到目的,只可惜才出手便被察覺。
他見袁升窮追,個頭雖不高大可動作極其敏捷,情知對手身手不凡,這時,四面燈火驟亮,喊叫聲一片響,他不敢怠慢,好在這府院極其寬敞,房間、過道極多,拐彎抹角,縱橫交錯。他利用這複雜地形,七彎八拐地放步猛跑……
跑過幾個院子,又到了內衙東邊的後花園,這安肅道衙門的緊鄰,就是安置土、客回民的屯墾衙門,兩邊花園緊挨,樹木相接,只在中間砌了一道土牆,負責外面警戒的道標兵因思量屯墾局亦駐了衛兵及欽差隨員,所以他們放鬆了這一面的警戒,刺客恰好是朝屯墾局跑的,他躍上土牆,回頭一看,袁升已緊緊追來,此時,已是空蕩、寬敞的大院,無任何遮攔,藉助微弱的月光,雙方把對手看得清清楚楚。刺客見袁升仍緊追不捨,猛地又從腰邊取出一把小刀,手一揚,朝袁升擲來……
袁升看得明白,忙就地一滾,躲過了暗器,待他再翻身撲過來時,對手已不知去向……
在如此戒備森嚴的總督行轅,竟然混入了刺客,且在自己的眼前突然消失,袁升非常惱火。
這時,道標都司宋玉寬已帶領十幾名兵丁執刀槍及燈籠火把從另一個方向跑來了,袁升告訴了他關於刺客的去向,並令他仔細搜索道署及屯墾衙門後便折了回來。
他來至左宗棠身邊,把情況稟報了一遍,眾人聽了,皆有些駭然,袁升分開眾人,在左宗棠住房門前的門框邊上拔下一把鋒利無比的小刀,在手中掂了掂,又於燈下細心察看刀柄,馬上認出了這刀的來歷。
「沒錯,這刀一般打十把,合稱『十錦小飛刀』,由河州的番回打造的!」袁升說。
「哦。」左宗棠瞅了一眼,略顯驚訝地說,「河州番回?這麼說,是馬占鼇的人?」
「不,河州大河家製刀技藝聞名陝甘,這種刀一般逆回都佩有它。」袁升若有所思地說。
眾人紛紛傳觀這把小飛刀。這時,二門外的戈什哈進來稟報,原來內衙的騷動已驚動了安肅道福裕及下屬文武,他們一齊來行轅請安。
左宗棠實在不想就此事張揚,於是吩咐下去,只說欽差無恙,有事等明日衙參時再說。
幾乎折騰了大半晚,直至拂曉時,袁升才回房休息。他躺在炕上,擺弄著這把小飛刀,卻一時無法安眠……
記得在追趕刺客時,他與這亡命之徒相距不足五步,後來,刺客立於土牆之上,二人又對視了一眼,他從此人身材、舉止及面部輪廓上發現有些眼熟,只可惜在對視的那一瞬間,藉助微弱的月光,他只看到這人半邊臉龐,這半邊臉上,傷疤縱橫,肌肉扭曲,非常醜陋,與袁升記憶中那一張熟悉的面孔有些差別。
這人是誰?
據他所知,逃竄新疆的陝西回民起義軍頭目白彥虎及手下幾個頭目,在南疆喀什噶爾城被攻陷前即已逃到了俄國,俄國人把這些人安置在吉爾吉斯,白彥虎不服水土,常思故鄉,不久即患病死了。
據說,白彥虎臨死之際,留下一條遺言:誰能帶大夥打回關中,叩響西安府的城門,誰就為眾回民之主。隨他逃到俄國的有近萬名陝甘穆斯林,被當地人稱為「東干人」,這些人中不乏亡命死士,且與官府有刻骨的仇恨,天知道這刺客不出於其中呢?
想到在關外峽谷中,此人撬石頭以求一逞的狠勁,可見他信息靈通,胸有成算;而且,他在未得手後,又緊躡官軍身後,甘冒危險而深入內衙行刺,這是何等的頑強與執著啊!
白彥虎帳下,還有誰夠得上聶政、荊軻一流人物呢?袁升推斷來,推斷去,最後仍只能歸結到那一個人身上。
誰?余小虎。只有他才有如此狠毒,也只有他才有如此頑強與執著,能在大軍已陷滅頂之災、敗局再也無法挽回的情況下,敢一人而作此孤注。
可是,余小虎不是已俯首就擒,並懸首國門了嗎?
--袁升的思緒,一下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的冬天,南疆喀什噶爾上空的硝煙已開始飄散,這是收復南疆的最後一戰,是役結束,回民軍已在新疆無容身之地,元凶白彥虎、伯克胡里渡納林河逃往俄國。他們雖逃脫了生擒活捉之厄,可白彥虎的副手、義子余小虎卻落入了法網,這於劉錦棠面上真是增光不少。
余小虎本為「渭南四彥」之一余彥祿之子,「四彥」之首白彥虎之義子。所謂「渭南四彥」是指首先在陝西渭南造反的四個回民首領,即馬生彥、禹得彥、白彥虎、余彥祿。他們後來戰死的戰死,受撫的受撫,唯有白彥虎冥頑不化,拒不投降;余小虎追隨白彥虎,以他那年輕氣盛、血氣方剛的闖勁,與白彥虎並稱「大、小虎」,與官軍作對,屠戮官軍、團練及漢民無數,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渠匪」。
當聽到余小虎終於落入法網並被劉錦棠押赴喀什噶爾市曹處以極刑時,袁升當時不由在心中默誦了一句:菩薩保佑,此番總算去掉了一塊心病,了卻了一大心願。
現在想來,當初未免過於輕信。余小虎跟白彥虎一樣,是個出了名的「猾賊」,更何況他又年輕力壯,手段了得,與官軍糾纏十有餘年,好幾次都是在四面圍殲的天羅地網下逃脫了,這一回圍城之役,漏網而逃往俄國者頗多,他未必就「天數已滿」。
想到這裡,袁升不由疑竇大開,浮想聯翩……
刀下留人
同治七年冬,袁升奉令從山西渡黃河,護送營務處師爺何紹南去陝西綏德。
這年冬十一月,湘軍大將劉松山率老湘營全軍於古渡茅津過黃河,十二月軍次綏德,旋即指揮各軍攻擊活動於大、小理川的陝西回民軍,佔領堡寨百餘處,俘獲回民軍丁壯及家屬八千餘人。
此為左宗棠西征第一仗。
回民軍受此重創,主力漸向陝北及隴東轉移,劉松山也抓住戰機,緊追不捨,僅留侄子劉錦棠率後營在綏德善後,為此,左宗棠特委何紹南為辦案委員,前來協助劉錦棠辦理善後--無非是對被俘人員稍作甄別,即處決了事,只要求不留後患。
那一次殺人場面,其規模之大,連從軍多年的袁升也深感震駭。
在小理川的河灘上,河水早已凍結,大雪漫天,遍地皆白,河川雪地上,簇立著黑鴉鴉的一群蓬頭垢面的俘虜,他們一個個手腳被繩子捆著,像一串串玉米棒子,男女老少都有,但沒有一個求饒、叫屈,只瞪著一雙雙充滿仇恨的眼睛,注視著官軍。
官軍當眾活剮了十餘名頭目,霎時鮮血如菰漿茜汁,流滿了溝渠……
袁升一旁肅立,靜靜地注視著。
被俘的回民軍面對同類被戕,竟像是著了魔似的,巋然屹立,毫無戰慄、恐怖之態。有些大約是阿訇,他們念念有詞,在為死者祈誦。
這以前,袁升在他三爹身邊,常聽他叨念「治回」之艱難。三爹認為,「回逆」不比「髮逆」,「髮逆」受人鼓弄,輕信從「賊」,只要官長曉以大義,使之改惡從善,蓄髮後仍為朝廷子民;「回逆」則不然,他心裡只有真主,沒有皇上,縱使一時放下屠刀,日久仍不免反目,唯一之法,只是痛加懲創,毋令死灰復燃。
今天,面對這生死場上,眾回民那一雙雙噴出怒火的眼睛,袁升不得不承認「三爹」有先見之明。
殺完了頭目,凶狠的劊子手開始揮刀殺向密匝匝的群眾,這可沒什麼講究的,只一個勁亂砍,霎時之間,只見人頭滾滾,熱血橫流,眼前漸漸只剩下了兩種顏色--紅的血和白的雪,其餘雜色皆湮沒了。
突然,像有鬼似的,袁升的視線內出現了一個活的女人和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女人個頭很高大,樣子亦很強悍,袁升估計她大概是哪一個首犯的妻子--這一批死囚中,受株連的親屬不少。他們既已陷於漢回的仇殺中,平日結怨不少,對頭很多,一旦被俘,便有所謂「苦主」前來指認,所以,對他們一樣寬仁不得,袁升明白這一層,也絲毫不想憐憫這女人,可他卻對女人身邊的青年人發生了興趣,這娃娃又黑又瘦,顯然還未成人,一身衣褲也很破爛,在這大雪天,已有幾處露出了肉身,脖子上圍一條破圍巾,凍得直發抖……
袁升注視這青年,這青年也注視到了他。忽然,袁升發現他的臉龐和自己家中三弟很相像,特別是那雙眼睛,圓鼓鼓的,瞪著人時露出一種蔑視一切的神色,根本不在乎眼下的危險。
袁升想,他小小年紀,便如此癡迷,這態度,只能激起別人更大的瘋狂與殘忍。要不是自己想起了死去的親弟弟,他也根本不會從這樣的眼光中激發出憐憫心。
原來他三弟死時也是這麼狠狠地瞪著他的。
那時,袁升也才十三四歲,一天,他帶比自己小兩歲的三弟去後山栽竹子。三弟年紀小脾氣強,有些瞧不起比自己個頭大不了多少卻醜得多的哥哥,而袁升平日卻很寬容這個弟弟,當袁升把土坑挖好,準備把母竹放入坑中時,他把三弟招呼到面前,突然一反常態,虎下臉,「啪」地在三弟頭上狠狠敲了一記--這其實是根據一個古老的傳說行事,原來在流傳的《二十四孝》故事中,有「孟宗哭竹」一說,講古時孟宗母親患病,想吃鮮筍,時值隆冬無筍,孟宗撫竹根痛哭,孝心感動天地,致令冬竹也發嫩筍。沿襲下來,就成為定例,凡栽竹之際,身邊最好也有人痛哭,如此則竹子長勢必好。
兒時的袁升很迷信這一說法,這一回特地帶了弟弟來,且怕他不哭下手很重,不料三弟不但沒哭,反抱著頭,狠狠地瞪他一眼就衝下了山。這一跑終於造成了袁升的終身遺憾--他一人在塘邊洗腳,其時水滿池塘,腳下一石塊鬆動,不慎失足落水而死。
袁升記得很清楚,死後的小弟弟仍向他狠狠地瞪著眼,流露出一副桀驁不馴的神情。
後來,他從軍了,雖時隔多年,人世滄桑,可心中對小弟那一份自責自慚的心情從未淡化,他永遠記住了弟弟那滿是輕蔑的眼神。
今天,不知怎的,他一碰上這青年的眼光,馬上穿山渡水,引起聯想,心中那一份憐憫之情油然而生。
他終於猶豫著起身了。稍一打聽,立刻有參與定讞的幕僚告訴他,這個未長成的娃兒乃是聞名遐邇的余彥祿的兒子余小虎。據這幕僚講,余小虎這以前只是跟著流竄,並無罪孽,只是其父為罪大惡極的「四彥」之一,他受到株連。十六七歲的年紀,本在坎兒上,可輕也可重的,為斬草除根,故一併殺了算了。
袁升一聽,立即打定了主意。這時,劉錦棠指派的五百刀斧手已麻利地砍翻了東南角上一大片人犯,十幾名劊子手已連袂殺到了這一邊,眼看就要砍向這青年。袁升心一橫,上前揮手道:「慢來,此人留與老子試刀!」
以袁升的地位,劊子手趕緊收刀佇立,讓袁升把余小虎拉至一邊,袁升只用刀頭在他纏著厚圍巾的脖子上輕輕一抹,隨即一腳將他踢倒在死屍堆裡……
不久,袁升就把此事給忘了。不料一年之後,官軍在對流竄寧靈、金積堡一帶的白彥虎部清剿中,新發現一個厲害的對手,此人年輕力壯,與官軍作戰時勇猛異常;屠戮戰俘時,手段也非常殘忍。
左宗棠根據諜報核查,證實此人名余小虎,但是,案卷上注明,此人應當是早已被正法了的。
余小虎死而復活,成為官軍中一個謎,這個謎只有袁升心中明白,自己一時的惻隱,留下了一個心腹大患,他由此而想起了余小虎在刑場時那一副因仇恨而扭曲了的面孔及那一雙蔑視一切的眼睛。
他從此便一直記住了余小虎。
想起了這些前因後果,他對余小虎已伏法之說愈來愈懷疑,儘管他內心一百個願意,願意劉錦棠的報告是事實。
這些天,他隨左相東歸,途中聽到一個傳說,說流竄在俄國的陝西回民紛紛潛入了內地,他們欲趁中俄戰雲密布、官軍主力集中新疆邊界之際,聯絡內地已就撫的穆斯林,重扯綠旗又造反。余小虎的出現,難道是一個信號?
饑鷹餓虎,獵人難制。
袁升真有幾分擔心,幾分後怕。然而,當他來到左相房中,想將自己的擔憂稟告左相,以期引起他的警惕時,卻瞥見左相仍精神激昂,刺客的第二次出現所帶來的惱怒早又淡化了,載譽東歸,一路觸景生情,他完全陶醉在叱吒風雲的往事中……
遇險
年近七旬的左宗棠,近來心境一直處於一種異常的亢奮狀態中。
當六匹高大健壯的汗血馬拉著寬敞富麗的後檔轎車在官道上狂奔時,他仰坐車中靠椅上,不時撫髯望一望窗外。
車窗外,獵獵西風,莽莽黃沙。兩千里的河西走廊上,正行進著一支雄壯的鐵騎。一桿巨大的紅底藍邊大纛在隊伍前面迎風作響,「恪靖侯左」四個大字隨風上下翻動。旗手是一個黑塔似的莽漢,絡腮短鬚,寬膛大臉,處此隆冬塞外,卻只穿一領藍夾綢戰袍,外罩一件紅緞滾邊湖青色馬褂,袖子捲得老高,紅纓帽背在腦後,那一根又粗又黑的辮子挽在頸上,黑煞神一般。隻手擎一桿大旗開道。他的左右各一名與他裝束差不多的副手緊跟護衛,距他們三騎好幾丈遠才是大部隊。
他們是二等恪靖侯東閣大學士太子太保督辦新疆軍務欽差大臣陝甘總督左宗棠的親軍。
左宗棠為大清國西北支柱,光緒二年至四年(西元一八七六--一八七八年),指揮十餘萬西征軍,收復了新疆南北路。正當他厲兵秣馬,準備驅兵收復為俄國佔領的伊犁時,接到詔書,令他回京商討戰守。他遂於光緒六年(西元一八八○年)十月中旬啟節東行。
在戰雲密布、戰爭一觸即發的此時,他舉手投足皆至關重要,俄國人對他的行蹤特別關注,加之動身前一日,又傳來俄國黑海艦隊中最大的一艘海軍旗艦--排水量為九千六百噸的「大彼得號」啟碇東駛的消息,為樹軍威、壯觀瞻、防突變,他特隨帶精兵五千,由王詩正、王德榜率領,轉赴張家口、山海關一線布防。
這五千精騎,皆百戰之師,熟悉歐羅巴新式戰術,足可與俄羅斯的哥薩克騎兵抗衡。把他們擺在京畿一線,京師可高枕無憂。而他此行有此五千精銳護衛,東歸行色頗是壯觀。
左宗棠一向講究軍容,尤其是自己督率的親軍,是從十萬西征軍中精選出的騎兵尖子。他們雖是清一色的湖南人,一口道地的湖南土話,卻生得南人北相,五大三粗且精於騎術。
左宗棠又講究相術。平日甄別部屬,考核將士,面相是首要的一關。他的左右親兵,尤其要注意精選,先看臉型是否端莊、勻稱,再看眼神是否有凶殺之氣。他相信相書上的話,凡田字、國字臉型者是大福大貴之相,由字、甲字或申字臉型者,為小人福薄之相。眼光神采飛揚前途無量,目澤昏濁精神萎靡者有遭凶死的可能,也就是「妨主」之相。因此,由他親自目測的親兵,無一不是團團大臉、高鼻闊口、虎虎而有生氣的偉丈夫。
督標兵餉俸從優,從不拖欠。加之出關後,捷報頻傳,犒賞接連不斷,這些勇丁們真是個個紅光滿面、服飾光鮮,與西北遭連年兵燹而鳩形鵠面、形銷骨立的百姓比,簡直有天神與鬼卒之別。
他們一色嶄新的藍綢戰袍,袖口捲起,露出「蘿蔔絲」或紫羔皮毛裡,戴紅纓帽,著黑漆快靴,肩上扛一色德國造新式毛瑟槍,槍身烤漆簇新,在陽光照射下藍光熠熠,與槍刺交相輝映。軍官肩上還挎一支使士民驚詫不已的單筒望遠鏡--傳說中的千里眼。而最令人咋舌的是隨軍行進的、由三匹馬牽引的克虜伯大炮。那修長而偉岸的炮身,翹然指向藍天,黑洞洞的、足有碗口大的炮口,像張著大口的巨蟒,一下能吞噬無數人的生命。
四年前,大將劉錦棠指揮所部「老湘營」攻烏魯木齊時,在紅廟子只放了一炮,就使有英、俄裝備的安集延人及回民軍炸了鍋,一潰而不可收拾,從而獲得了「一炮成功」的美譽。至今日,它隨隊伍路過關塞或村鎮時,凡聽過「一炮成功」故事的人們,除了爭著瞻仰這位赫赫有名的爵相大人的豐儀,也爭著把目光投向隨行的隊伍,尋覓那威懾敵膽的「紅衣大將軍」。
左宗棠的目光,此刻緊盯著擁在座車前後的精騎。二十餘年的馬上生涯,他這個書生習慣了徜徉在這壯觀的場面和敬畏、戰慄的目光中,習慣了聽這人喊馬嘶、刀槍碰擊的聲音,習慣了聞這一股股馬尿、馬糞摻和的膻臭味,也習慣了這緊張而富於傳奇色彩的生活。他以此為樂,覺得這也是他的文章,他的傑作。他只有生活在這刀與火的氛圍中,才能時時忽發奇想,寫好這樣博大精深的「傑作」。
多麼壯觀的場面,多麼精銳的隊伍啊!這是自己親手締造、親自指揮,與自己聲譽、地位同休戚而共始終的隊伍。想當年,在長沙金盆嶺奉旨草創楚軍,自江西攻入浙江擊長毛,隨後出閩粵而指關隴,攻擊捻軍與回民軍,又馬不停蹄人不卸甲,出嘉峪關而縱橫沙磧,掃蕩了天山南北,立下了永垂後世之功勳,使中國軍人威名遠播,世界列強刮目相看。他們真不愧是支撐大清帝國的精英,三楚士民的驕傲!
左宗棠感歎,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當年在長沙應募的老兵,除了為國捐軀者外,餘下的熬到今天,都已是袍褂鮮明、翎頂輝煌的戰將了。楚軍精神長存。二十餘年中,他們追隨他,這個楚軍老帥,從東南到西北,轉戰十數省,行程幾萬里,大小上千戰,戰無不勝,攻無不克,直令長毛元凶馬前授首,回民軍巨逆傳檄受擒;驅馳塞外,又使有英俄做後盾的安集延人望風而逃。而今,拓疆數萬里,聲威震歐亞。中國外患,常在西陲,周逐獫狁,秦禦強胡,漢擊匈奴,唐征突厥,數千年來,能直搗龍庭,犁庭掃穴,誰可與我相匹敵?
「丞相天威,西人不復反矣。」這是河州回民大阿訇馬占鼇於同治十一年(西元一八七二年)春間請降時說的話。此人真不愧為著名「猾賊」,他知左宗棠常以諸葛亮自比,揀了一句現成的話恭維他。
其實,諸葛一生事業,結束在「出師未捷身先死」七個字上,晚年蹉跎祁山,關河阻絕,遙望中原,路漫漫其修遠,後來,就連三分天下也成為泡影。若以功業而論,諸葛亮又何足道哉!
而左宗棠的事業,與之簡直不可同日而語--南疆八城光復,縱橫數千里的新疆全部重歸大清皇輿,紅旗傳露布、捷報達京師時,皇帝的諭旨是這麼褒獎的:
……新疆淪陷,十有餘年,朝廷恭行天討,轉命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該大臣剿撫兼籌,議定先規北路,首復烏魯木齊,以扼其總要,旋克瑪納斯,數道並進,規復吐魯番城,力爭南路要隘,然後整旆西行,勢如破竹。現在南八城一律收復,此皆仰賴昊天眷佑,列聖垂休,而兩宮太后,宵旰焦勞,知人善任,用能內外一心,將士同命,成此大功。上慰穆宗毅皇帝在天之靈,下孚薄海臣民之望,實深欣幸。領兵大臣等,櫛風沐雨,艱苦備嘗,允宜特沛恩施,用酬勞績。欽差大臣大學士陝甘總督左宗棠籌兵籌餉,備厲艱辛,卒能謀出萬全,膚功迅奏。著加恩由一等伯晉為二等侯。欽此!
舉人出身的左宗棠,文拜相,武封侯,開國以來,能有幾人可與之相比?
想到這一切,他不由意氣發舒,心潮澎湃,產生出一種目空一切,睥睨萬物,直如騰身霄漢的大鵬但恨天低的激情……
然而,當他突然回眸瞥見几上放著的一份文稿時,目光霎時變得陰鷙而凶狠了--這是從北京用四百里加緊快差送來的抄件,作者不是別人,正是繼曾國藩之後,與他暗暗角力的李鴻章。
楚軍在天山南北摧枯拉朽般的勝利,已為四年前左、李之間那一場辯論做了一個很好的結論。如今,「海防」與「塞防」之爭,已以李鴻章的失敗而寫進了國史。此公到底不甘心,在忍氣吞聲三年之後,竟然又一次搖唇鼓舌了:
……往者,微臣籌及西事,每不免鰓鰓過慮者,誠恐恢復故疆,則有名而無實;變通商務或受損於無窮也……
隱隱約約,拐著彎子,不仍是為四年前「興海防,廢塞防」做翻案文章嗎?左宗棠想,什麼「有名無實」,分明是當年論爭時,那「徒收數千里之曠地而增千百年之漏卮」的老調重彈,明眼人一看就明白,醉翁之意,並不在酒呢。
接下來,李鴻章認為,既然朝廷已賦予崇厚全權,則崇厚所定條約便合法,斷不能輕率更改,不然,恐失信於列強各國。接下來,他又提出了所謂的「補救」之法,而他的「補救」則是趕快恢復與俄人「通商」--所說各項辦法,無一不與左宗棠唱反調。
從附在李鴻章奏稿後面的上諭口氣上看,兩宮太后及輔國恭親王對他此奏未做明確肯定的批示。左宗棠想,只要李鴻章此議未成定局,事情就有挽回的可能。這些年來,遠離京師,所謂一出都門,便成萬里,紙短筆頹,不能把滿腹衷情上達。他想,難得此番奉召,應盡快趕回去,向兩宮太后及執掌樞輔的恭親王爺一吐胸中積愫。
「袁升,已走了幾個台站啦?」
他用那鷹隼一般犀利的目光掃了一眼窗外,又抬腿踢了踢蜷伏在腳邊氊子上打盹的差官袁升。
袁升,一個手極長而身子較矮的長臂猿一樣的漢子。他因多次往返天山南北路及河西走廊,對這一路的軍台道里記得滾瓜爛熟,此刻,他雖如一隻馴服的小犬依伏於一側,但耳目極警覺,一聽左宗棠發問,不再複述,馬上坐起,屈指數道:「快呢,已過了雙井子,前面是今天的宿站--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
「天色不是還挺早嗎?」
「是啊,連日奔波,總算進關了,明日就要進肅州,能不能讓大家整理一下軍容?」
「肅州也不是初次進駐,不必如此張羅。我看,在嘉峪關不要停留,趕到肅州宿營最好。」
「這可要多走七十里。」
「多走七十里無妨,眼前局勢瞬息萬變,可不敢隨便耽擱!」
「您的身子?」
「沒關係。」
左宗棠抖擻精神,在袁升肩上拍了一下,袁升知道主帥犯了倔脾氣,只好掀開車門溜下去傳令。
本來,自劉錦棠從阿克蘇趕到哈密後,前方軍事已做了妥善的交代,十月初完全可以啟節返京的,不料劉錦棠及各路統領一致挽留,因為十月初七日乃是左宗棠的華誕。已是望七之年的左宗棠,頭白臨邊,難有息肩之日,部屬不代為操辦,相與慶賀,又賴何人?
「老師,難得有今日之心境啊。」劉錦棠殷切地挽留。
眼下戡亂的鼙鼓已息,可邊陲烽燧又起。身為國家柱石之臣,正受欽命徵召,所謂「君命不宿於家」,奉旨即須遵行,談不上有清閒之日,善體人意的劉錦棠,說了一句很得體的話。
現在想來,他有些後悔,就為了這個世俗的陋習,耽誤了整整十天時間。在平常人的一生中,十天不過短暫的一瞬,可對運籌帷幄、折衝樽俎的大臣,處此關鍵時刻,十天,或許就是成敗的契機,這時光的價值,實在無法用金錢來估量。
他覺得自己當初似乎有些不能自持,如果堅持原議,十月初二日動了身,眼下已過武威郡,快要望見蘭州城了……
「轟!」
突然,就在近處,似乎就是頭頂上,發出了一聲沉悶的巨響,隨著身子向前一傾,他趕緊扶住了兩邊的扶手,接著,車子停住,人聲、拉槍栓聲、拔刀出鞘聲、吆喝牲口聲立刻響起,鬧成一片,在這一片嘈嘈雜雜的聲音中,似乎有一個粗嗓門喊了一聲「有刺客!」
於是,接下來便是嚷成一片的「抓刺客」聲。
不知幾時又已溜上車的袁升,此刻就像一頭受驚的豹子,「蹭」地一下,操起短槍鑽出了車外……
左宗棠驚魂甫定,也掀簾探出了身子--原來隊伍已進入了一條狹長的、兩邊石壁聳立、形勢極其險峻的峽谷之中。因要在天黑前趕到肅州,隊伍速度加快,不料走至此段,一塊巨石從天而降,正砸在他座車後面的行李車上,一輛四輪大車被砸得粉碎。
這時,眾差官、親信已一齊湧到車前,將左宗棠團團護住,待發現前後左右並無敵蹤而危險來自頭頂後,差官朱信、戴福才分開眾人,將左宗棠攙扶到遠離危險的一處草地上坐好。
左宗棠安下神,順著眾人手勢望去,只見石壁頂上青苔滑脫,這巨石分明是有人從上面推下來的,而不是偶然的坍塌。看來,這是有人趁此機會行刺於他,此人預知他將經過此地,且已偵知他的座車形狀--那華麗的後檔車也是太顯目了,好在車速甚快,石壁又高,終於只誤中副車。
這時,眾人皆紛紛議論,詛咒這刺客用心之惡毒,甚至說若抓住了他,非要予以三萬六千刀的魚鱗剮不可,而袁升已不待吩咐,早率領一小隊親兵,抄小路向壁頂包圍。
只有左宗棠一人置身事外。雖然刺客是向著他來的,可他仍在想李鴻章的事,想他的人及他那一份奏摺……
非常的時代,造就了非常的人物。太平天國的興起,成就了湖南一代非常人物的湧現,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彭玉麟……一個個如璀燦的明星,踴躍而出,成為湘人的驕傲。何物李鴻章,竟也想配曾、左而成鼎足之勢?
左宗棠嘴角,漾起一抹輕蔑的冷笑。
酒泉之夜
途中遇險的不快,早被過嘉峪關的興奮沖淡了。左宗棠發現,自己這高亢激昂的情緒,甚至已影響了全體隨行人員--他就親耳聽見車旁有一個老兵在馬上用含混不清的鄉音叨念:「一出嘉峪關,兩眼淚不乾。好啦,總算是直著回來啦!」
是的,總算是直著回來啦!這一句話概括了隨行人員的心境。
想當初,大哥左宗植勸左宗棠功成身退、辭謝陝甘總督之任,謂「二十行役,六十免役」,彼時左宗棠已五十有六了,可大哥不了解弟弟的雄心,沒想到弟弟就在望七之年還荷戈西行,渡流沙而涉戈壁呢!然而,想到四年前出兵新疆時的內外形勢,他還有幾分後怕,這當然是局外人所沒有的。
「狐死首丘,代馬依風,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這是班超託妹妹班昭上書漢和帝時的一句名言,也是他齒髮搖落、晚景蒼涼的真實寫照。想當初,班超投筆從戎,入虎穴而獲虎子,立下那永垂後世的功勳,那是何等的英雄!不料竟在暮年,上疏求還時,會發出如許令人心寒齒冷的哀語!人們只知有揚名西域的「定遠侯」,豈知有垂垂老矣而欲歸不得的「班都護」?無邊的戈壁,寂寞的荒漠吞噬了多少英雄豪傑,仁人志士!昔日,他們叱吒風雲,揚威邊塞,而今皆化作了道邊壘壘白骨。「祁連山下草,寂寞少人煙,魂魄千年後,猶思渡酒泉。」人生哀樂,思鄉懷舊之情,舉世一轍。仁人志士,亦在所不免。
左宗棠詫異自己在過嘉峪關時,興奮的情緒中,竟會摻和著這種不協調的思想感情。而這種淡淡哀思和莫名惆悵,又與時下全軍振奮的氣氛多麼地不相稱啊!
望見了,終於望見了,馬兒慢慢地行,車兒慢慢地隨,他,終於望見了夕照下的嘉峪關城樓,望見了自己親筆書寫的「天下第一雄關」六個金光閃閃的大字。
這時,三軍肅穆,一齊向匾額注目,連空氣也似乎凝固了……
他想,此番入京,必然主戰,東北為防俄之前沿,自己當然會義不容辭,那麼,幾個月後,自己可能又要出現在長城的另一端,出現在另一「天下雄關」的城樓上,這巧合,這壯舉,將是後世文人墨客多好的題材啊!
嘉峪關至肅州七十里,道路平坦,兩旁遍栽楊柳。黃昏落日,柳絲悠悠,似乎也會盡人意……
他一直保持著這高亢激昂的情緒,七十里驛道十分輕鬆,倏忽便過。
肅州,又名酒泉。為安西、肅州道駐地,相傳漢代霍去病出擊匈奴,欽使帶來了十瓶御酒,賜賞去病,一向與士卒同艱苦的霍去病以十瓶御酒不夠數萬將士共飲,乃傾酒於泉中,分飲眾將士,「酒泉」因此而得名。
左宗棠當年率軍入隴,先駐節隴東的平涼,次移安定,再小住甘州,然後,督大軍進圍肅州。所謂「平、定、甘、肅」,肅州為最後一站,也是他待得時間最長的地方--後來進軍新疆,為節制前線各路大軍,督促糧餉的轉運,左宗棠又選定肅州為大本營,自光緒二年四月至今年四月,在肅州鳳凰台道署住了整整四年。
今天,肅州城因左宗棠的過境而披上了盛裝--行程改變,一行人提前到達雖使人有些手忙腳亂,但城門口那座特大的牌樓是先一天紮好的,在官府的催督下,從牌樓下起沿街擺起了層層香案,老幼婦孺漢回民眾黑鴉鴉的一片,在留守的肅州同知王仲甫暨道署僚屬率領下頂香恭迎。
待走在隊伍前頭開道的頂馬一過,眾人一齊圍上來,口中不約而同地喊起了「左爵相」、「左宮保」。
因有關外遇險的那一幕,眾人皆有些忐忑。安肅道福裕及道標都司宋玉寬是從安西州一路護送、陪同左宗棠入關的,此時更是惴惴不安,見眾人圍上來,他們又不便吆喝、驅散眾人,於是,他二人只好相約下馬,扶著車輪,緊緊護衛在左宗棠座車左右,雙眼注視兩邊,一刻也不敢懈怠。
左宗棠微笑著,向左右點頭。
進城後,他仍駐節於鳳凰台的安肅道衙門,此地房屋較為寬敞,環境也很幽靜。為了他的安全,安肅道福裕調了兩百名道標兵,由都司宋玉寬率領在圍牆外巡邏。內衙則由左宗棠隨行的親兵警戒。
肅州為東歸途中第一大站,又是左宗棠駐節四年的行轅,很多事須做交代,左宗棠要在此停留兩天,距此不遠的南關,有一座由清真寺改建的定湘王神廟,他要在離開前去廟裡最後一次燒香,這些事雖未寫在注明欽差行止的排單上,但袁升早已知會過福裕了。欽差大臣關防極其縝密,加之旅途勞頓,所以,他一入內衙,即下令放炮下柵,來請安的道、府官員屬吏,一律被擋駕。
刺客
袁升是在起更後才進城的。左宗棠正在房中等他的消息。
「可恥的傢伙,真自不量力!」
據他說,他們在壁頂除發現有人住宿的痕跡外,在撬石頭的地方,有人用刀刻下一句話:為阿拉之道而戰!這是回民起義軍與官軍作戰時常用的一句口號,「阿拉」即真主。
袁升帶人四下追蹤,終於在東北方向發現一匹快馬在飛奔。袁升居高臨下觀察,斷定此人是奔阿拉善額魯特方向。
「我從後面用望遠鏡瞄了他很久。」袁升說,「這是一個好騎手,那馬也絕不是一匹普通的馬,我們徒步根本無法追上他。」
袁升有些後悔,當時沒返回騎馬,他請示左宗棠,是否諮請阿拉善蒙古親王,請他們協助搜捕這個凶狠而狡猾的刺客。
左宗棠未置可否,只揮手讓袁升去用晚餐。
袁升退出後,左宗棠翦著雙手在房中徘徊,晚餐時,他就著火鍋喝了兩小杯酒,這更激發了他的豪情,他只想尋找發洩激情的途徑。
刺客的出現,於他並無大影響,他已料定,此人必來自漏網的回民軍,但單身匹馬又有何作為呢?成千上萬的回民武裝尚可屠戮殆盡,像白彥虎那樣的渠魁巨匪也只能亡命國外,余小虎那樣的凶狠之徒也已喋血轅門,區區一漏網小丑,跳樑於山谷荒漠之中,能興多大的風,起多大的浪呢?我命繫於天,又豈是這等蕞爾小丑所能算計的?
安肅道衙門是一所多院落的府第,內衙分東西跨院,南北廂房,後面還有大小花園及戲臺,布局很講究,而陌生人進來卻有如進了迷魂陣,分不出南北東西。
袁升侍候左宗棠在這座府第住了四年,對府中門徑非常熟悉。因白天出現意外,左宗棠雖是那麼淡然,作為他的貼身親隨,袁升卻不敢稍有鬆懈,他不敢飲一口酒,匆匆吃過飯,燙過腳,已是深夜了,他來在左宗棠房中,見主人正在燈下看一份《申報》。
左宗棠見袁升進來,忙放下報紙,從老花鏡架上望著袁升,沉吟半晌才問:「都睡了嗎?」
「都睡了。」
「去喚那個人來吧。」左宗棠說。
袁升低頭答了一聲是,便轉身退了出來。
這一問一答,只有他們二人明白。約過了兩袋煙工夫,一個嫋嫋婷婷、仍打著呵欠的女子被袁升帶了進來。
待這女子走進左宗棠的屋子,袁升便從外面把房門帶關,他明白,自己連這下半晚也無論如何不能睡了,因為事後這女子還要送回她的住處。自左宗棠今年四月出關,已半年多未見她面了,他知道,他們這一聚,有很多話要說,很多事要做。
袁升伸了一個懶腰,想在門外尋一個避風的地方坐一會兒,打一個盹。安肅道辦差雖格外小心巴結,連欽差一些生活細節也照顧到了,但卻不曾為下人多想一想。此時門外的袁升,連避風的地方也沒有。
袁升蜷伏在門檻上,抄著雙手埋頭打盹,就在這朦朦朧朧中,他似乎聽到一種異樣的聲音。不像失群的孤雁,也不似草間的蟲鳴,它,極其細微而又極其清晰。這是只有像袁升這樣久負警衛重任的人才能在茫茫夜空、萬籟俱寂的情況下捕捉住的。
一下,又是一下……
像夜貓子在沙地上走,像蝮蛇在草地上爬。
袁升昂頭,在心中默數。
猛地,他一下躍起,閃身往前面廊柱後一縱,與此同時,只聽「忽」地一聲,一道白光往他剛才的位置飛來,「錚」地一聲,像有一利刃牢牢地釘到了身後的門框上。
「砰,砰!」袁升以極快的動作,拔出腰間的手槍,對準前面花廳那一道突出的山牆連放兩槍。隨著槍聲,只見山牆後一陣瓦響,突然躍出一個人影,「騰」地一下,落到了西花廳的天井裡。
「抓刺客!」
袁升一面喊,一面跟著追了出去。
這時,已入睡的親兵們一齊驚醒。睡在右廂房的親兵朱信動作極快,他只穿一條褲衩,光著上身,操一把短刀一個縱步衝出了房門,只見庭院裡寂無人影,除了遠去的奔跑聲,就像沒發生任何事一樣。
此時此刻,朱信最關心的當然是主帥的安全。他三步併作兩步跑到正廳,只見左宗棠寢室房門緊閉。他一時忘了自己竟光著上身,只對著房門喊道:「爵相,爵相大人!」
左宗棠早已拜東閣大學士。官場習俗,照例應稱其為「中堂大人」,唯「中堂」與「宗棠」諧音,恭敬的稱呼反易被誤為「稱名道姓大不敬」,下人為避忌這點,一律改稱「爵相」。
「先點燈吧。」房子裡傳出左宗棠極安詳、平穩的聲音。
朱信頓覺懸著的心放了下來,這才發現自己竟光著膀子,冷浸浸的。這時,戴福等親信差官及外院巡邏的兵丁一齊擁了過來,一時燈火通明,人聲鼎沸,朱信乃返回屋去穿衣。
見到主帥無恙,大家寬心,正要詢問槍聲的由來,只見房門「咿呀」一聲,左宗棠已出現在臺階上。
「待著幹什麼?快幫助袁升去。」左宗棠沉著地下令。
一言未了,只聽袁升在外高聲應道:「不必了。」
紅頂差官
袁升在十萬西征軍中,人緣最好。幾乎人人都認識他,知他是左相心腹,是令人羡慕不已的「紅頂子二爺」。
他今年三十六歲,從軍已有二十一年,想當初,他長到十五歲,還沒有名字,「袁升」是他的「三爹」給取的--咸豐十年,左宗棠奉旨在長沙金盆嶺募軍。湘陰柳莊左家的佃戶袁四聽說了,忙帶了幾塊燻狗肉,一罎子泡酸菜,牽了他的二兒子「狗伢子」來看望老東家。
「三爹,」老佃戶不知官場路數,仍用家裡的稱呼,按排行稱已是四品京堂的東家,「我家狗伢子腰上有顆痣,俗話說:一痣痣於腰,騎馬又挎刀,看來是一個吃糧的料子。可他平日沒出過門,嘴笨手笨,不會見風使法。投別棚別哨我不放心,讓他跟您提個夜壺何如?」
左宗棠望一眼面前這個瘦猴一樣的小子,不但面目瘦得像猴,且手長腳短,高顴骨尖下顎--全是猴兒的特徵,尤其是那一雙圓而小、咕嘟嘟四處亂轉的眼睛,活脫脫是猴兒無異--照相書上說,凡人生異相,必獲大貴。
只瞟了一眼,左宗棠心中已喜歡上這個佃戶的兒子了,不等袁四再嘮叨下去,馬上笑著答應留下「狗伢子」。
待老長工一走,左宗棠便使他去營務處上個名字,直到此時,他才突然記起,這些天來此投軍的窮漢多沒名字,是營務處的師爺們隨口取的,為討吉利,一般都叫「連升」「連捷」或「得功」「得勝」之類。幾天下來,已滿營盡是這類名字了,終不成自己面前又冒出個「袁連升」來。
「你就叫袁升吧。」左宗棠口中說著,想到的是「猿臂猱升」的典故。
「是,謝三爹,這名字有什麼來歷沒有呀?」狗伢子窮根究底。
左宗棠很喜歡這副憨大相,乃逗他道:「猿升猱捷,會往上爬啊,我為你取這個名字,將來升官快。」
袁升當時高興極了,忙趴下給左宗棠磕了個響頭,又伶牙俐齒地說:「三爹是『夏尚書做官--一下遮蓋了湖南江西兩個省』,我沾這點光,將來還怕少了官做?只怕做不像呢。」
夏尚書是指明朝名臣夏元吉,他祖籍江西德興,父親做湘陰教諭,後來便落籍湘陰。夏元吉以拔貢出身,歷官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四朝,官至戶部尚書,死後諡忠靖,相傳他在京做官時,多照顧江西、湖南同鄉,故湘陰有那麼一句俗話。佃戶的兒子是個粗人,也只會說這種俗話,碰到當時左宗堂正遺憾自己起家乙榜,與曾國藩帳下李鴻章、郭嵩燾等翰林比,有時難免自慚形穢。一聽今日袁升拿由拔貢出身而官至尚書的夏元吉比他,倒也歪打正著。當下笑顏逐開,把他留在身邊,當一名貼身親隨。
「三爹」也真肯照顧他。每次奏捷、敘軍功請獎時,總囑咐師爺,給袁升上一個名字。只幾年工夫,他的「三爹」做到了正一品封疆大吏,他也水漲船高,以軍功保至紅頂花翎的記名總兵。
「袁升」這名字是左宗棠給取的,也只有左宗棠叫得最多。以前,他是個軍漢,是個「糧子」,同鄉故舊見了他,仍沿習舊稱「狗伢子」或「袁猴子」,出外時,他是左相親隨,別人要叫一聲「總爺」或「二爺」,到現在,堂堂總鎮,武職正二品大員,別人不但不能直呼渾名,且有些不敢貿然犯諱了。
不過,袁升不拿架子,人極隨和。故此,楚軍各營各哨的人,上至統領、營官,下至伍長、護勇無人不喜歡他。他品級雖高,卻從未署過一任實缺,這不是因為軍功保舉太濫,有官銜而無法補上實缺--他若能夠做官又想做官,「三爹」一定設法給他補上了。無奈他一來大字不識,學不好官場應酬,二來也不願離開服侍已久的「三爹」,所以,仍一直在左宗棠身邊當親兵,夜壺當然不讓他提了,可做的事卻也實在比提夜壺高雅不了多少。
為此,別人有時稱他為「紅頂子二爺」。
小虎
「紅頂子二爺」的功名一點也不僥倖,二十多年來,他追隨左相,南征北伐,練就了一身武藝和膽識,作為一名貼身親隨,一身繫主子安危,半點懈怠不得。他摸透了主子的脾氣,人像猴兒一樣機靈,手腳也像猴兒一樣殷勤,無論在何時何地,他都像影子似的、沒沒無聲地跟著他的「三爹」轉,「三爹」也一刻也離不開他。
剛才,他躲過刺客朝他擲來的暗器後,朝山牆連發兩槍,心知未擊中目標,待他衝出院門,來至西花廳臺階上時,只見一個高大的黑影已跳到天井裡,正預備逃往外衙,袁升與他僅五步之遙,於是,他對準此人後胸猛扣扳機,不料就在這節骨眼上,槍子兒卡了殼,袁升好惱火,他用力把槍往刺客頭上擲去,沒想到刺客正好於此時轉彎,拐入通後花園的迴廊,自然沒砸著。
袁升心想,道署內外有巡更護院的兵丁,剛才響槍,料想都已聽到,此人是插翅也逃不出去的了,於是,他拔出腰刀,緊緊跟上去。
刺客是尾隨袁升那一小隊人在起更時混進道署的,目標自然是衙內住著的、一身牽動著西北大局的人物左宗棠。不過,他還從未進過這衙門,只見院落重重,究竟不知他的目標宿於何處,待伏在暗處,認準了目標,卻不料袁升如此竭忠盡職,竟守護在房門口寸步不離,他明白,不收拾門口蜷伏的這名警衛,就根本無法達到目的,只可惜才出手便被察覺。
他見袁升窮追,個頭雖不高大可動作極其敏捷,情知對手身手不凡,這時,四面燈火驟亮,喊叫聲一片響,他不敢怠慢,好在這府院極其寬敞,房間、過道極多,拐彎抹角,縱橫交錯。他利用這複雜地形,七彎八拐地放步猛跑……
跑過幾個院子,又到了內衙東邊的後花園,這安肅道衙門的緊鄰,就是安置土、客回民的屯墾衙門,兩邊花園緊挨,樹木相接,只在中間砌了一道土牆,負責外面警戒的道標兵因思量屯墾局亦駐了衛兵及欽差隨員,所以他們放鬆了這一面的警戒,刺客恰好是朝屯墾局跑的,他躍上土牆,回頭一看,袁升已緊緊追來,此時,已是空蕩、寬敞的大院,無任何遮攔,藉助微弱的月光,雙方把對手看得清清楚楚。刺客見袁升仍緊追不捨,猛地又從腰邊取出一把小刀,手一揚,朝袁升擲來……
袁升看得明白,忙就地一滾,躲過了暗器,待他再翻身撲過來時,對手已不知去向……
在如此戒備森嚴的總督行轅,竟然混入了刺客,且在自己的眼前突然消失,袁升非常惱火。
這時,道標都司宋玉寬已帶領十幾名兵丁執刀槍及燈籠火把從另一個方向跑來了,袁升告訴了他關於刺客的去向,並令他仔細搜索道署及屯墾衙門後便折了回來。
他來至左宗棠身邊,把情況稟報了一遍,眾人聽了,皆有些駭然,袁升分開眾人,在左宗棠住房門前的門框邊上拔下一把鋒利無比的小刀,在手中掂了掂,又於燈下細心察看刀柄,馬上認出了這刀的來歷。
「沒錯,這刀一般打十把,合稱『十錦小飛刀』,由河州的番回打造的!」袁升說。
「哦。」左宗棠瞅了一眼,略顯驚訝地說,「河州番回?這麼說,是馬占鼇的人?」
「不,河州大河家製刀技藝聞名陝甘,這種刀一般逆回都佩有它。」袁升若有所思地說。
眾人紛紛傳觀這把小飛刀。這時,二門外的戈什哈進來稟報,原來內衙的騷動已驚動了安肅道福裕及下屬文武,他們一齊來行轅請安。
左宗棠實在不想就此事張揚,於是吩咐下去,只說欽差無恙,有事等明日衙參時再說。
幾乎折騰了大半晚,直至拂曉時,袁升才回房休息。他躺在炕上,擺弄著這把小飛刀,卻一時無法安眠……
記得在追趕刺客時,他與這亡命之徒相距不足五步,後來,刺客立於土牆之上,二人又對視了一眼,他從此人身材、舉止及面部輪廓上發現有些眼熟,只可惜在對視的那一瞬間,藉助微弱的月光,他只看到這人半邊臉龐,這半邊臉上,傷疤縱橫,肌肉扭曲,非常醜陋,與袁升記憶中那一張熟悉的面孔有些差別。
這人是誰?
據他所知,逃竄新疆的陝西回民起義軍頭目白彥虎及手下幾個頭目,在南疆喀什噶爾城被攻陷前即已逃到了俄國,俄國人把這些人安置在吉爾吉斯,白彥虎不服水土,常思故鄉,不久即患病死了。
據說,白彥虎臨死之際,留下一條遺言:誰能帶大夥打回關中,叩響西安府的城門,誰就為眾回民之主。隨他逃到俄國的有近萬名陝甘穆斯林,被當地人稱為「東干人」,這些人中不乏亡命死士,且與官府有刻骨的仇恨,天知道這刺客不出於其中呢?
想到在關外峽谷中,此人撬石頭以求一逞的狠勁,可見他信息靈通,胸有成算;而且,他在未得手後,又緊躡官軍身後,甘冒危險而深入內衙行刺,這是何等的頑強與執著啊!
白彥虎帳下,還有誰夠得上聶政、荊軻一流人物呢?袁升推斷來,推斷去,最後仍只能歸結到那一個人身上。
誰?余小虎。只有他才有如此狠毒,也只有他才有如此頑強與執著,能在大軍已陷滅頂之災、敗局再也無法挽回的情況下,敢一人而作此孤注。
可是,余小虎不是已俯首就擒,並懸首國門了嗎?
--袁升的思緒,一下回到了三年前。
三年前的冬天,南疆喀什噶爾上空的硝煙已開始飄散,這是收復南疆的最後一戰,是役結束,回民軍已在新疆無容身之地,元凶白彥虎、伯克胡里渡納林河逃往俄國。他們雖逃脫了生擒活捉之厄,可白彥虎的副手、義子余小虎卻落入了法網,這於劉錦棠面上真是增光不少。
余小虎本為「渭南四彥」之一余彥祿之子,「四彥」之首白彥虎之義子。所謂「渭南四彥」是指首先在陝西渭南造反的四個回民首領,即馬生彥、禹得彥、白彥虎、余彥祿。他們後來戰死的戰死,受撫的受撫,唯有白彥虎冥頑不化,拒不投降;余小虎追隨白彥虎,以他那年輕氣盛、血氣方剛的闖勁,與白彥虎並稱「大、小虎」,與官軍作對,屠戮官軍、團練及漢民無數,是一個十惡不赦的「渠匪」。
當聽到余小虎終於落入法網並被劉錦棠押赴喀什噶爾市曹處以極刑時,袁升當時不由在心中默誦了一句:菩薩保佑,此番總算去掉了一塊心病,了卻了一大心願。
現在想來,當初未免過於輕信。余小虎跟白彥虎一樣,是個出了名的「猾賊」,更何況他又年輕力壯,手段了得,與官軍糾纏十有餘年,好幾次都是在四面圍殲的天羅地網下逃脫了,這一回圍城之役,漏網而逃往俄國者頗多,他未必就「天數已滿」。
想到這裡,袁升不由疑竇大開,浮想聯翩……
刀下留人
同治七年冬,袁升奉令從山西渡黃河,護送營務處師爺何紹南去陝西綏德。
這年冬十一月,湘軍大將劉松山率老湘營全軍於古渡茅津過黃河,十二月軍次綏德,旋即指揮各軍攻擊活動於大、小理川的陝西回民軍,佔領堡寨百餘處,俘獲回民軍丁壯及家屬八千餘人。
此為左宗棠西征第一仗。
回民軍受此重創,主力漸向陝北及隴東轉移,劉松山也抓住戰機,緊追不捨,僅留侄子劉錦棠率後營在綏德善後,為此,左宗棠特委何紹南為辦案委員,前來協助劉錦棠辦理善後--無非是對被俘人員稍作甄別,即處決了事,只要求不留後患。
那一次殺人場面,其規模之大,連從軍多年的袁升也深感震駭。
在小理川的河灘上,河水早已凍結,大雪漫天,遍地皆白,河川雪地上,簇立著黑鴉鴉的一群蓬頭垢面的俘虜,他們一個個手腳被繩子捆著,像一串串玉米棒子,男女老少都有,但沒有一個求饒、叫屈,只瞪著一雙雙充滿仇恨的眼睛,注視著官軍。
官軍當眾活剮了十餘名頭目,霎時鮮血如菰漿茜汁,流滿了溝渠……
袁升一旁肅立,靜靜地注視著。
被俘的回民軍面對同類被戕,竟像是著了魔似的,巋然屹立,毫無戰慄、恐怖之態。有些大約是阿訇,他們念念有詞,在為死者祈誦。
這以前,袁升在他三爹身邊,常聽他叨念「治回」之艱難。三爹認為,「回逆」不比「髮逆」,「髮逆」受人鼓弄,輕信從「賊」,只要官長曉以大義,使之改惡從善,蓄髮後仍為朝廷子民;「回逆」則不然,他心裡只有真主,沒有皇上,縱使一時放下屠刀,日久仍不免反目,唯一之法,只是痛加懲創,毋令死灰復燃。
今天,面對這生死場上,眾回民那一雙雙噴出怒火的眼睛,袁升不得不承認「三爹」有先見之明。
殺完了頭目,凶狠的劊子手開始揮刀殺向密匝匝的群眾,這可沒什麼講究的,只一個勁亂砍,霎時之間,只見人頭滾滾,熱血橫流,眼前漸漸只剩下了兩種顏色--紅的血和白的雪,其餘雜色皆湮沒了。
突然,像有鬼似的,袁升的視線內出現了一個活的女人和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女人個頭很高大,樣子亦很強悍,袁升估計她大概是哪一個首犯的妻子--這一批死囚中,受株連的親屬不少。他們既已陷於漢回的仇殺中,平日結怨不少,對頭很多,一旦被俘,便有所謂「苦主」前來指認,所以,對他們一樣寬仁不得,袁升明白這一層,也絲毫不想憐憫這女人,可他卻對女人身邊的青年人發生了興趣,這娃娃又黑又瘦,顯然還未成人,一身衣褲也很破爛,在這大雪天,已有幾處露出了肉身,脖子上圍一條破圍巾,凍得直發抖……
袁升注視這青年,這青年也注視到了他。忽然,袁升發現他的臉龐和自己家中三弟很相像,特別是那雙眼睛,圓鼓鼓的,瞪著人時露出一種蔑視一切的神色,根本不在乎眼下的危險。
袁升想,他小小年紀,便如此癡迷,這態度,只能激起別人更大的瘋狂與殘忍。要不是自己想起了死去的親弟弟,他也根本不會從這樣的眼光中激發出憐憫心。
原來他三弟死時也是這麼狠狠地瞪著他的。
那時,袁升也才十三四歲,一天,他帶比自己小兩歲的三弟去後山栽竹子。三弟年紀小脾氣強,有些瞧不起比自己個頭大不了多少卻醜得多的哥哥,而袁升平日卻很寬容這個弟弟,當袁升把土坑挖好,準備把母竹放入坑中時,他把三弟招呼到面前,突然一反常態,虎下臉,「啪」地在三弟頭上狠狠敲了一記--這其實是根據一個古老的傳說行事,原來在流傳的《二十四孝》故事中,有「孟宗哭竹」一說,講古時孟宗母親患病,想吃鮮筍,時值隆冬無筍,孟宗撫竹根痛哭,孝心感動天地,致令冬竹也發嫩筍。沿襲下來,就成為定例,凡栽竹之際,身邊最好也有人痛哭,如此則竹子長勢必好。
兒時的袁升很迷信這一說法,這一回特地帶了弟弟來,且怕他不哭下手很重,不料三弟不但沒哭,反抱著頭,狠狠地瞪他一眼就衝下了山。這一跑終於造成了袁升的終身遺憾--他一人在塘邊洗腳,其時水滿池塘,腳下一石塊鬆動,不慎失足落水而死。
袁升記得很清楚,死後的小弟弟仍向他狠狠地瞪著眼,流露出一副桀驁不馴的神情。
後來,他從軍了,雖時隔多年,人世滄桑,可心中對小弟那一份自責自慚的心情從未淡化,他永遠記住了弟弟那滿是輕蔑的眼神。
今天,不知怎的,他一碰上這青年的眼光,馬上穿山渡水,引起聯想,心中那一份憐憫之情油然而生。
他終於猶豫著起身了。稍一打聽,立刻有參與定讞的幕僚告訴他,這個未長成的娃兒乃是聞名遐邇的余彥祿的兒子余小虎。據這幕僚講,余小虎這以前只是跟著流竄,並無罪孽,只是其父為罪大惡極的「四彥」之一,他受到株連。十六七歲的年紀,本在坎兒上,可輕也可重的,為斬草除根,故一併殺了算了。
袁升一聽,立即打定了主意。這時,劉錦棠指派的五百刀斧手已麻利地砍翻了東南角上一大片人犯,十幾名劊子手已連袂殺到了這一邊,眼看就要砍向這青年。袁升心一橫,上前揮手道:「慢來,此人留與老子試刀!」
以袁升的地位,劊子手趕緊收刀佇立,讓袁升把余小虎拉至一邊,袁升只用刀頭在他纏著厚圍巾的脖子上輕輕一抹,隨即一腳將他踢倒在死屍堆裡……
不久,袁升就把此事給忘了。不料一年之後,官軍在對流竄寧靈、金積堡一帶的白彥虎部清剿中,新發現一個厲害的對手,此人年輕力壯,與官軍作戰時勇猛異常;屠戮戰俘時,手段也非常殘忍。
左宗棠根據諜報核查,證實此人名余小虎,但是,案卷上注明,此人應當是早已被正法了的。
余小虎死而復活,成為官軍中一個謎,這個謎只有袁升心中明白,自己一時的惻隱,留下了一個心腹大患,他由此而想起了余小虎在刑場時那一副因仇恨而扭曲了的面孔及那一雙蔑視一切的眼睛。
他從此便一直記住了余小虎。
想起了這些前因後果,他對余小虎已伏法之說愈來愈懷疑,儘管他內心一百個願意,願意劉錦棠的報告是事實。
這些天,他隨左相東歸,途中聽到一個傳說,說流竄在俄國的陝西回民紛紛潛入了內地,他們欲趁中俄戰雲密布、官軍主力集中新疆邊界之際,聯絡內地已就撫的穆斯林,重扯綠旗又造反。余小虎的出現,難道是一個信號?
饑鷹餓虎,獵人難制。
袁升真有幾分擔心,幾分後怕。然而,當他來到左相房中,想將自己的擔憂稟告左相,以期引起他的警惕時,卻瞥見左相仍精神激昂,刺客的第二次出現所帶來的惱怒早又淡化了,載譽東歸,一路觸景生情,他完全陶醉在叱吒風雲的往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