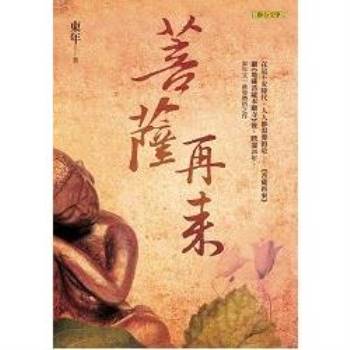1.
金教授再次表示自己確實看到護士推著病床在眼前跑過;林茉莉聽後,手上懸著的羊毫繼續落下觀音菩薩的臉,把剛染上的橘紅色洗平。
「妳佛畫還是唐卡,我看畫得很好。」金教授說:「不像一般畫成肖像,沒生氣。」
林茉莉不知道他是客氣話還是讚賞,只知道自己工筆畫,和一般把色彩拘泥在線型結構中的觀念不同,也清楚自己的線型鋪陳不能精準,所以隨類、隨情、隨意賦彩;就這點來看,她認為自己並沒完全獲得父親遺傳。她父親年輕時得過幾種獎,後來寧願枯站海邊或坐湖邊釣魚,偶而在畫本素描這些景色,說以後有空再來好好畫;釣到比較大的魚,他才會認真做魚身拓影。有一次她問他為何不再畫,他表示一個虛無和功利的社會只會對裝飾畫有興趣,這樣畫畫沒意思。他的漁拓起先只是一般拓法,後來認為嘉鱲應該有點紫紅,而黑鯛的黑色裡蘊含一點點墨藍,還有金線。這樣不從俗以及在黑白中賦彩,就是她後來畫工筆的想法。
「護士推病床在山上跑也奇怪──」金教授又說:「可惜妳沒看到。」
林茉莉把羊毫在筆洗中洗後擱上筆山,走近落地窗去探看。這樓房是老厝改建,保留有原來的三合院地。右廂樓頂斜面滾落雨水,有些瀑布段落在背襯的路燈下看起來縷脈分明。雨點喧嘩,錯亂閃爍,同樣剔透晶亮;光暈中還能看到豪雨自相摩擦,碰撞出氤氳。迷漫霧氣後的陰暗樹林和山徑,就是金教授說的,那裡剛有一個護士推著病床快步跑過。她才這樣想像,樹林下忽然照進一道手電筒光,晃動到處,能看到雨點紛紛打在潮濕葉片,或在流水路面濺起水花。
「好像有人來──」金教授說:「這樣大雨,又是晚上,啊,有一個晚上下雨,我看到兩個荷蘭士兵追一個西班牙士兵──」
林茉莉忍不住笑起來,終於說:「教授怎麼看出荷蘭兵和西班兵?」
「呃,這當然都很奇怪,我們這裡怎麼會跑出古代的荷蘭兵和西班牙兵,還騎馬──」金教授說:「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也到過美洲,我因為工作需要參考,讀科學史,順便把歷史文化也看了,收藏很多圖片──啊,希望沒嚇到妳。」
金教授經常會空望什麼地方發神或心不在焉,她不免就猜疑他是否神志有問題;「沒沒,我只是好奇──」她呼吸了一口氣說:「真是有點怪怪的。」他們以為來了一個人,卻是連續五把傘;其中三張傘面下露出赤色僧服下擺、白色布襪和土黃色僧鞋。有一個僧人腳下略跛,她想,他們的鞋、襪和褲腳,也許連衣服都溼透了。一會兒,王建仁上樓來站在門邊,說:「二伯,阿姨,我爸請你們半個鐘頭後下樓去和一位師父打招呼,他名號四指法師,呃,他有一隻手和一隻腳──總共只有四根指頭。」
「哇,有這樣的事?」林茉莉說:「你幹嘛站門邊不進來?」
「我襪子會把地板弄濕──」王建仁說:「我裡裡外外都淋濕了。」
「所以,就是董事長說的,這幾天會來一個聖僧。」林茉莉問:「是那一個山上來的?」
「這要問我爸,我是被叫去開車才知道──」王建仁說:「啊,阿姨要的綠色顏料,我放在車上忘了,對不起對不起。」
「沒關係,我明天──或者你要下山的時候,我和你一起去拿。」
「我今天不住這裡,我等等就要走了。」王建仁說:「雨這樣大,阿姨妳不好出去,我明天下午還會來,我等等上車就會放進包包,下次來就不會忘記。」
四指法師應是有點年紀,另兩位法師看似中壯,體態都堅實,林茉莉就看不出他們年紀。
他們換了輕鬆常服,白襪和僧鞋也都十分乾淨。襯著赤色上衣,她發覺他們的膚色出奇白皙,像是沒有血色;她這樣想,因為想像畫他們臉,幾乎只需勾描五官,不用染色。
「林茉莉小姐是我們基金會剛請來的秘書和畫師──」王董事長說:「菩薩嶺才興建不久,秘書工作是暫時的,以後啊,人漸漸多,就可以專心美術工作。」
「畫師不敢當。」林茉莉說:「我可以畫一點工筆畫,佛畫沒畫過,請大家多指教。」
王董事長繼續介紹自己的二哥金教授,由金教授說明自己怎麼由王教授變成金教授。他在美國大學教書,有外國學生問王這姓是什麼意思,台灣學生說是國王的king字;他追隨以前的指導教授在加速器實驗室找粒子,是一個工作小組召集人,他的同事也就同樣喊他Professor King,而華人學生和同事跟著諧音喊成金教授。
「基本上我是理論物理學家,業餘天文物理學家──」金教授說:「我很好奇,呃,四指法師──大師父,請教您怎樣看佛學。」
「啊,是不是改天再談佛學──」王董事長說。
「沒關係,我請法行法師和法眼法師隨意說一點。」四指法師攤開右手,向下坐的兩位法師致意。初次看到四指法師右手板的人難免大吃一驚,林茉莉卻緊盯著;那隻手板只有一支大拇指。她又低頭去看他腳;包覆在鞋襪裡,她看不出他的腳板有什麼異樣。
「我就跟著大家喊,金教授呵──在你們科學界,加速器實驗室的觀點,世界是由各種粒子、作用力,在各種場域構成和運作,是不是這樣?」法行法師說。
「呃,大概是這樣。」
「我們的世界,我師父的看法也是這樣,也是由一些基本元素,元件,構成世界的存在,這些基本元素就是我們佛法的法,法這個字原來梵語說的就是元素,它們是剎那間生滅的,但是,有些元素在生滅剎那間都會再發生,善啊,惡啊──」
「喔,也許說的是發生了別種粒子,而有的再重新組合──」金教授說:「這有意思。」
「無論如何,我們不找粒子,我們探究這些元素聚合、消滅的物質性、精神性,還有其中的作用力。」
「喔,這樣談佛法就很有意思。」金教授說:「聽起來很親切,很熟悉,很像我學生時代上物理課,還有以後在實驗室找粒子。」
法行法師沒再應答,法眼法師就說:「元素的概念──有些元素可以看成是恆常性的,就是剛才法行法師說的,它們永遠會出現在每一個生滅的剎那,而有些元素只會出現在特定情境,這是說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這些元素在自力和外力作用下,構成了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以及各種各自的可能,構成了宇宙萬物以及其中運行的原理和機運,構成三界二十八天,構成更高的天,所以我們的世界,天、神、人、阿修羅、畜生、鬼和地獄是同時間同空間存在的──喔,我們在這裡的期間,不會和所有的信眾這樣談佛法,只想談信眾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怎樣健康身心,認識和修習善緣。」
「同時間同空間──」金教授說:「如果是同時間不同空間,或者不同時間同空間,我們這個宇宙──」
「這,二弟,你自己再慢慢想呵,想到了給我們寫一篇文章看看。」王董事長說:「感謝感謝,感謝三位法師指點,那就不打擾師父休息了。」
林茉莉回到樓上,立刻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布包,把裡面一尊四、五十公分高佛像,立在桌上,說:「這是我兩個月前,在一個地攤買的,也是有一隻手只有大拇指,而有一隻腳只有三個指頭。」
「哇,這麼巧。」王董事長說:「四指法師的左腳,說是只有後面三個指頭。」「難怪,你們來的時候,我看有一個法師的腳步有點跛──」
「真巧真巧,這樣妳就不必藏起來。」王董事長說:「可以放在桌上。」
「如果四指法師喜歡,我可以送他。」林茉莉說。
「我明天問他看看,這麼巧,他一定會喜歡。」王董事長說:「賣給我轉送他好了。」
「沒多少錢。」林茉莉說:「我原來沒注意到,是走過地攤的時候,聽到老闆說,竟然連一百元也沒人買,這樟木雕就算買木材也要四五百元。」
「一定是看林茉莉有氣質,故意說來引她注意。」金教授說。
「是喔,我就回頭去看,彌勒佛傷了手腳還笑呵呵,我一看就喜歡,聞聞看,也還有樟木香氣。」林茉莉說:「可不可以請教董事長,是從哪裡找來這三位師父──」
「啊,這事也真巧,我去年在阿拉斯加機場轉機,在候機室打瞌睡,睡著了,就是他們把我及時喊醒,上了飛機,我又正好和他們坐一起──」王董事長說:「啊,如果妳是想知道他們來歷,我沒繼續請教,呃,好像是說出家後都在到處雲遊,看起來是富有人家出身或支持的,他們要去日本,我就給四指法師名片,歡迎他們隨時來台北。」
「也許是西藏那種什麼活佛,但是法號不像,而且──」金教授說:「你們不覺得他們的膚色,白得有點奇怪?」
「我也這麼想──」林茉莉說。
「呵呵,你又看到什麼──」王董事長說。
「看到什麼喔──」金教授說:「天剛暗的時候──今天,我又看到一個護士推著病床在路上跑。」
金教授再次表示自己確實看到護士推著病床在眼前跑過;林茉莉聽後,手上懸著的羊毫繼續落下觀音菩薩的臉,把剛染上的橘紅色洗平。
「妳佛畫還是唐卡,我看畫得很好。」金教授說:「不像一般畫成肖像,沒生氣。」
林茉莉不知道他是客氣話還是讚賞,只知道自己工筆畫,和一般把色彩拘泥在線型結構中的觀念不同,也清楚自己的線型鋪陳不能精準,所以隨類、隨情、隨意賦彩;就這點來看,她認為自己並沒完全獲得父親遺傳。她父親年輕時得過幾種獎,後來寧願枯站海邊或坐湖邊釣魚,偶而在畫本素描這些景色,說以後有空再來好好畫;釣到比較大的魚,他才會認真做魚身拓影。有一次她問他為何不再畫,他表示一個虛無和功利的社會只會對裝飾畫有興趣,這樣畫畫沒意思。他的漁拓起先只是一般拓法,後來認為嘉鱲應該有點紫紅,而黑鯛的黑色裡蘊含一點點墨藍,還有金線。這樣不從俗以及在黑白中賦彩,就是她後來畫工筆的想法。
「護士推病床在山上跑也奇怪──」金教授又說:「可惜妳沒看到。」
林茉莉把羊毫在筆洗中洗後擱上筆山,走近落地窗去探看。這樓房是老厝改建,保留有原來的三合院地。右廂樓頂斜面滾落雨水,有些瀑布段落在背襯的路燈下看起來縷脈分明。雨點喧嘩,錯亂閃爍,同樣剔透晶亮;光暈中還能看到豪雨自相摩擦,碰撞出氤氳。迷漫霧氣後的陰暗樹林和山徑,就是金教授說的,那裡剛有一個護士推著病床快步跑過。她才這樣想像,樹林下忽然照進一道手電筒光,晃動到處,能看到雨點紛紛打在潮濕葉片,或在流水路面濺起水花。
「好像有人來──」金教授說:「這樣大雨,又是晚上,啊,有一個晚上下雨,我看到兩個荷蘭士兵追一個西班牙士兵──」
林茉莉忍不住笑起來,終於說:「教授怎麼看出荷蘭兵和西班兵?」
「呃,這當然都很奇怪,我們這裡怎麼會跑出古代的荷蘭兵和西班牙兵,還騎馬──」金教授說:「荷蘭人和西班牙人也到過美洲,我因為工作需要參考,讀科學史,順便把歷史文化也看了,收藏很多圖片──啊,希望沒嚇到妳。」
金教授經常會空望什麼地方發神或心不在焉,她不免就猜疑他是否神志有問題;「沒沒,我只是好奇──」她呼吸了一口氣說:「真是有點怪怪的。」他們以為來了一個人,卻是連續五把傘;其中三張傘面下露出赤色僧服下擺、白色布襪和土黃色僧鞋。有一個僧人腳下略跛,她想,他們的鞋、襪和褲腳,也許連衣服都溼透了。一會兒,王建仁上樓來站在門邊,說:「二伯,阿姨,我爸請你們半個鐘頭後下樓去和一位師父打招呼,他名號四指法師,呃,他有一隻手和一隻腳──總共只有四根指頭。」
「哇,有這樣的事?」林茉莉說:「你幹嘛站門邊不進來?」
「我襪子會把地板弄濕──」王建仁說:「我裡裡外外都淋濕了。」
「所以,就是董事長說的,這幾天會來一個聖僧。」林茉莉問:「是那一個山上來的?」
「這要問我爸,我是被叫去開車才知道──」王建仁說:「啊,阿姨要的綠色顏料,我放在車上忘了,對不起對不起。」
「沒關係,我明天──或者你要下山的時候,我和你一起去拿。」
「我今天不住這裡,我等等就要走了。」王建仁說:「雨這樣大,阿姨妳不好出去,我明天下午還會來,我等等上車就會放進包包,下次來就不會忘記。」
四指法師應是有點年紀,另兩位法師看似中壯,體態都堅實,林茉莉就看不出他們年紀。
他們換了輕鬆常服,白襪和僧鞋也都十分乾淨。襯著赤色上衣,她發覺他們的膚色出奇白皙,像是沒有血色;她這樣想,因為想像畫他們臉,幾乎只需勾描五官,不用染色。
「林茉莉小姐是我們基金會剛請來的秘書和畫師──」王董事長說:「菩薩嶺才興建不久,秘書工作是暫時的,以後啊,人漸漸多,就可以專心美術工作。」
「畫師不敢當。」林茉莉說:「我可以畫一點工筆畫,佛畫沒畫過,請大家多指教。」
王董事長繼續介紹自己的二哥金教授,由金教授說明自己怎麼由王教授變成金教授。他在美國大學教書,有外國學生問王這姓是什麼意思,台灣學生說是國王的king字;他追隨以前的指導教授在加速器實驗室找粒子,是一個工作小組召集人,他的同事也就同樣喊他Professor King,而華人學生和同事跟著諧音喊成金教授。
「基本上我是理論物理學家,業餘天文物理學家──」金教授說:「我很好奇,呃,四指法師──大師父,請教您怎樣看佛學。」
「啊,是不是改天再談佛學──」王董事長說。
「沒關係,我請法行法師和法眼法師隨意說一點。」四指法師攤開右手,向下坐的兩位法師致意。初次看到四指法師右手板的人難免大吃一驚,林茉莉卻緊盯著;那隻手板只有一支大拇指。她又低頭去看他腳;包覆在鞋襪裡,她看不出他的腳板有什麼異樣。
「我就跟著大家喊,金教授呵──在你們科學界,加速器實驗室的觀點,世界是由各種粒子、作用力,在各種場域構成和運作,是不是這樣?」法行法師說。
「呃,大概是這樣。」
「我們的世界,我師父的看法也是這樣,也是由一些基本元素,元件,構成世界的存在,這些基本元素就是我們佛法的法,法這個字原來梵語說的就是元素,它們是剎那間生滅的,但是,有些元素在生滅剎那間都會再發生,善啊,惡啊──」
「喔,也許說的是發生了別種粒子,而有的再重新組合──」金教授說:「這有意思。」
「無論如何,我們不找粒子,我們探究這些元素聚合、消滅的物質性、精神性,還有其中的作用力。」
「喔,這樣談佛法就很有意思。」金教授說:「聽起來很親切,很熟悉,很像我學生時代上物理課,還有以後在實驗室找粒子。」
法行法師沒再應答,法眼法師就說:「元素的概念──有些元素可以看成是恆常性的,就是剛才法行法師說的,它們永遠會出現在每一個生滅的剎那,而有些元素只會出現在特定情境,這是說特定的時間和空間,這些元素在自力和外力作用下,構成了人的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以及各種各自的可能,構成了宇宙萬物以及其中運行的原理和機運,構成三界二十八天,構成更高的天,所以我們的世界,天、神、人、阿修羅、畜生、鬼和地獄是同時間同空間存在的──喔,我們在這裡的期間,不會和所有的信眾這樣談佛法,只想談信眾在日常生活中,能夠怎樣健康身心,認識和修習善緣。」
「同時間同空間──」金教授說:「如果是同時間不同空間,或者不同時間同空間,我們這個宇宙──」
「這,二弟,你自己再慢慢想呵,想到了給我們寫一篇文章看看。」王董事長說:「感謝感謝,感謝三位法師指點,那就不打擾師父休息了。」
林茉莉回到樓上,立刻打開抽屜,拿出一個布包,把裡面一尊四、五十公分高佛像,立在桌上,說:「這是我兩個月前,在一個地攤買的,也是有一隻手只有大拇指,而有一隻腳只有三個指頭。」
「哇,這麼巧。」王董事長說:「四指法師的左腳,說是只有後面三個指頭。」「難怪,你們來的時候,我看有一個法師的腳步有點跛──」
「真巧真巧,這樣妳就不必藏起來。」王董事長說:「可以放在桌上。」
「如果四指法師喜歡,我可以送他。」林茉莉說。
「我明天問他看看,這麼巧,他一定會喜歡。」王董事長說:「賣給我轉送他好了。」
「沒多少錢。」林茉莉說:「我原來沒注意到,是走過地攤的時候,聽到老闆說,竟然連一百元也沒人買,這樟木雕就算買木材也要四五百元。」
「一定是看林茉莉有氣質,故意說來引她注意。」金教授說。
「是喔,我就回頭去看,彌勒佛傷了手腳還笑呵呵,我一看就喜歡,聞聞看,也還有樟木香氣。」林茉莉說:「可不可以請教董事長,是從哪裡找來這三位師父──」
「啊,這事也真巧,我去年在阿拉斯加機場轉機,在候機室打瞌睡,睡著了,就是他們把我及時喊醒,上了飛機,我又正好和他們坐一起──」王董事長說:「啊,如果妳是想知道他們來歷,我沒繼續請教,呃,好像是說出家後都在到處雲遊,看起來是富有人家出身或支持的,他們要去日本,我就給四指法師名片,歡迎他們隨時來台北。」
「也許是西藏那種什麼活佛,但是法號不像,而且──」金教授說:「你們不覺得他們的膚色,白得有點奇怪?」
「我也這麼想──」林茉莉說。
「呵呵,你又看到什麼──」王董事長說。
「看到什麼喔──」金教授說:「天剛暗的時候──今天,我又看到一個護士推著病床在路上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