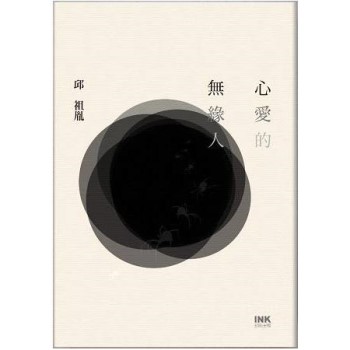產婆淑芬經常覺得這肉身不是自己的。回魂那年,她才十八歲,一切記憶都回來了,連關於之前接生出了意外的記憶也回來了,餘悸猶存,她害怕看到血,害怕看到女人陣痛,害怕看到女人哭,嬰兒剛出世的模樣,總是讓她想到那對死去的孩子。一開始她只敢跟著阿撿嬸出巡,當個助手,重回出師以前的日子,倒也落得輕鬆,但阿撿嬸年紀大了,又愛偷懶,才不到兩個月,就找種種藉口要淑芬獨自出任務。她很快克服了恐懼,熟門熟路,一樣的俐落手腳,一樣的火爆脾氣,她想起自己是有任務的,不容她怕事。
她想起自己的堅持,堅持沒卵脬的都得留下,誰都不准抱走,不過畢竟大病初癒,不似過往盛氣凌人,頭一次遇到生女兒的人家,她心懷忐忑,照例詢問:「孩子不會送走吧?」在場卻沒一個人說話,男人板著臉,女人垮著臉,淑芬傻眼,忘了下一步該怎麼做。她沒有罵人,沒有特別對誰下功夫,她不再像以前那樣精力十足,總是奮戰到底,不知是年紀到了、結過婚了,還是那次事件衝擊的結果。她沒繼續追問下去。她感到洩氣,魂魄若即若離,就算了吧!
出到門外,她深吸一口氣,不知何去何從,那戶人家的男人也跟出門來,沒理會她,自顧自的去張羅瑣事,淑芬沒好氣,往前走幾步路,走到村口,卻又停下腳步,不自覺回望,好巧不巧,那男人也望向她這邊來,兩人四目相接,有些尷尬,淑芬快步走開,要是讓這男人以為她在勾引他,那就糗了,真是臭美啊!我怎會看上這樣的男人。但她卻沒立即離開,她又回頭望,那男人正巧又回望。她竟看到自己的魂魄離開她的身體,不由自主的走向那個男人,去牽那男人的手,男人也不由自主的任由她的魂牽引,朝她的肉身走來,她的肉身還有一些知覺,覺得不妥,便動身起步,急著離開,這一來更像在勾引他了。
他們很快在林子裡交歡,草草結束,但男人神魂顛倒,力氣放盡,一年來未曾碰過女人,他的體內住著一頭猛獸,理應頑強蠻橫,不可理喻,但不知是淑芬更野,亦或誘人的女人總是讓男人沉淪得更快,這頭猛獸在她體內沒竄兩下,就一溜煙的跑開。
淑芬的身體沒有什麼感覺,倒是她的魂有些意猶未盡。她速速回魂,頭腦清醒而冷靜,就像做那回事的是別人,不是自己,也許是身體暢快了的結果。她記得要緊的事,對著男人嚴厲的說:「女兒不能送走,知道嗎?」男人愣了一下,緩緩點頭,像做錯事的孩子被抓個正著,「你要是敢把孩子送走,今天的事,所有人都會知道,我是不要臉的,如果你也不要臉,那就沒差,咱們走著瞧!」男人背脊發涼,涼到整個腳板,全身不能動彈,連褲子都忘了穿上。淑芬很快和衣起身,整理行囊,準備去另一戶人家走動,走沒幾步路,又回頭看,這次回頭,沒特別的意思,只是提醒那男人:「不要再來找我!」
這女孩果然沒被送走。但淑芬後悔自己的行為,這是出賣自己的身體,就算出發點再偉大、再高尚,也是出賣。她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心所愛的人,她有嗎?阿慶不會在乎吧?阿燦死了吧?就算沒死,此刻恐怕身邊還擁著別的女人,一個換過一個。阿榮不算個男人。此刻她是沒人愛的。但她是規矩人家的女孩,這樣做,別說自己不允許,別人也要看笑話,她會教那些沒把女兒送走的人家怨恨,還以為妳是多了不起的人,還以為妳的道德操守有多高,結果還不是個低三下四到處胡搞的女人,還有臉來說我們連骨肉都不要;那些早早把女兒送走的家庭,更要對她冷笑、狂笑,袂見笑,這女人,以為自己是聖女,還不是一天到晚等著被人幹,假仙假觸,卸世卸情。
怎麼辦?下次不可以再這樣了,一次也就算了,兩次、三次,事情就傳開了,還威脅人家不可說,真是不要臉。這事還怕人說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淑芬重重賞了自己兩個耳光,大聲喊:「下次不可以了!」像是在對自己的魂魄喊話。
卻一再身不由己。淑芬總是跟男人發生關係,之後再跟自己喊話,再傷害自己,還把自己打得鼻青臉腫。後來她放棄了,何苦呢,自己也想要不是嗎?就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吧,那畢竟還是自己,那是自己心底的聲音,她哪是什麼貞節烈女、少女媽祖婆,她骨子裡就是個不三不四的女人,就別裝了。她放開了。浪蕩度日,好不快活,每一次接生,都充滿期待,她幹得比以前更起勁。
往後一年,果真沒半個女孩被送走。淑芬不再疾言厲色,每次都只悄問:「女兒不會送走吧?」若答案是「不會」,她便放心走人;若不置可否,她通常不會猶豫太久,馬上故計重施,勾引男人,立下誓約,強加威逼,然後目的達成。屢試不爽。後來這件事逐漸傳開,男人們總是等著她來,等著她問,等著沉默不語,等著互相引誘,然後等著辦好事。這事之所以會傳開,起因於某個人食好鬥相報,「你就等她出門,你也跟著出門,不要跟喔,這女人不好惹,沒幾個男人打得過她,別討皮痛,她如果沒回看,你千萬別跟上去,她若回頭看你,你才可以跟上去,再來就有好康的了,包你卯死!」
她心甘情願。自此,若產婦生的是女的,她不再像過往那麼擔心,反而花更多時間照護這孩子,從剪完臍帶開始,把一個孩子從一個全身髒穢、擠眉弄眼、神情痛苦、驚惶失措的小野獸,擺弄成眼神清亮、滿身油光的紅麵龜,她就是有這本事。但這些女人卻開始變得不安,女人總是知道女人在想什麼,不必聽傳聞,就能嗅到某種不尋常的氣息,淑芬有時覺得是自己心裡有鬼,但這些剛生完孩子的女人,就是有股不一樣的生氣,眼睛就是能看穿妳心裡在想什麼,知道妳要來偷我的東西了,知道妳要來偷我的人。淑芬看女人的眼神總是閃爍,女人看她的眼神變得怨毒,逼得她只得草草了事,她想快點投到另一個男人的懷抱,把一日來的疲倦都拋去,哪管妳是誰的誰?妳就好好照看孩子就是了,這一趟,我保管妳母子平安,永不分離。她這麼一想,心情便輕鬆了。而這些剛生完孩子的女人,也的確不能拿她怎麼辦。
她想起自己的堅持,堅持沒卵脬的都得留下,誰都不准抱走,不過畢竟大病初癒,不似過往盛氣凌人,頭一次遇到生女兒的人家,她心懷忐忑,照例詢問:「孩子不會送走吧?」在場卻沒一個人說話,男人板著臉,女人垮著臉,淑芬傻眼,忘了下一步該怎麼做。她沒有罵人,沒有特別對誰下功夫,她不再像以前那樣精力十足,總是奮戰到底,不知是年紀到了、結過婚了,還是那次事件衝擊的結果。她沒繼續追問下去。她感到洩氣,魂魄若即若離,就算了吧!
出到門外,她深吸一口氣,不知何去何從,那戶人家的男人也跟出門來,沒理會她,自顧自的去張羅瑣事,淑芬沒好氣,往前走幾步路,走到村口,卻又停下腳步,不自覺回望,好巧不巧,那男人也望向她這邊來,兩人四目相接,有些尷尬,淑芬快步走開,要是讓這男人以為她在勾引他,那就糗了,真是臭美啊!我怎會看上這樣的男人。但她卻沒立即離開,她又回頭望,那男人正巧又回望。她竟看到自己的魂魄離開她的身體,不由自主的走向那個男人,去牽那男人的手,男人也不由自主的任由她的魂牽引,朝她的肉身走來,她的肉身還有一些知覺,覺得不妥,便動身起步,急著離開,這一來更像在勾引他了。
他們很快在林子裡交歡,草草結束,但男人神魂顛倒,力氣放盡,一年來未曾碰過女人,他的體內住著一頭猛獸,理應頑強蠻橫,不可理喻,但不知是淑芬更野,亦或誘人的女人總是讓男人沉淪得更快,這頭猛獸在她體內沒竄兩下,就一溜煙的跑開。
淑芬的身體沒有什麼感覺,倒是她的魂有些意猶未盡。她速速回魂,頭腦清醒而冷靜,就像做那回事的是別人,不是自己,也許是身體暢快了的結果。她記得要緊的事,對著男人嚴厲的說:「女兒不能送走,知道嗎?」男人愣了一下,緩緩點頭,像做錯事的孩子被抓個正著,「你要是敢把孩子送走,今天的事,所有人都會知道,我是不要臉的,如果你也不要臉,那就沒差,咱們走著瞧!」男人背脊發涼,涼到整個腳板,全身不能動彈,連褲子都忘了穿上。淑芬很快和衣起身,整理行囊,準備去另一戶人家走動,走沒幾步路,又回頭看,這次回頭,沒特別的意思,只是提醒那男人:「不要再來找我!」
這女孩果然沒被送走。但淑芬後悔自己的行為,這是出賣自己的身體,就算出發點再偉大、再高尚,也是出賣。她對不起自己,對不起父母,對不起心所愛的人,她有嗎?阿慶不會在乎吧?阿燦死了吧?就算沒死,此刻恐怕身邊還擁著別的女人,一個換過一個。阿榮不算個男人。此刻她是沒人愛的。但她是規矩人家的女孩,這樣做,別說自己不允許,別人也要看笑話,她會教那些沒把女兒送走的人家怨恨,還以為妳是多了不起的人,還以為妳的道德操守有多高,結果還不是個低三下四到處胡搞的女人,還有臉來說我們連骨肉都不要;那些早早把女兒送走的家庭,更要對她冷笑、狂笑,袂見笑,這女人,以為自己是聖女,還不是一天到晚等著被人幹,假仙假觸,卸世卸情。
怎麼辦?下次不可以再這樣了,一次也就算了,兩次、三次,事情就傳開了,還威脅人家不可說,真是不要臉。這事還怕人說嗎?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淑芬重重賞了自己兩個耳光,大聲喊:「下次不可以了!」像是在對自己的魂魄喊話。
卻一再身不由己。淑芬總是跟男人發生關係,之後再跟自己喊話,再傷害自己,還把自己打得鼻青臉腫。後來她放棄了,何苦呢,自己也想要不是嗎?就跟著自己的感覺走吧,那畢竟還是自己,那是自己心底的聲音,她哪是什麼貞節烈女、少女媽祖婆,她骨子裡就是個不三不四的女人,就別裝了。她放開了。浪蕩度日,好不快活,每一次接生,都充滿期待,她幹得比以前更起勁。
往後一年,果真沒半個女孩被送走。淑芬不再疾言厲色,每次都只悄問:「女兒不會送走吧?」若答案是「不會」,她便放心走人;若不置可否,她通常不會猶豫太久,馬上故計重施,勾引男人,立下誓約,強加威逼,然後目的達成。屢試不爽。後來這件事逐漸傳開,男人們總是等著她來,等著她問,等著沉默不語,等著互相引誘,然後等著辦好事。這事之所以會傳開,起因於某個人食好鬥相報,「你就等她出門,你也跟著出門,不要跟喔,這女人不好惹,沒幾個男人打得過她,別討皮痛,她如果沒回看,你千萬別跟上去,她若回頭看你,你才可以跟上去,再來就有好康的了,包你卯死!」
她心甘情願。自此,若產婦生的是女的,她不再像過往那麼擔心,反而花更多時間照護這孩子,從剪完臍帶開始,把一個孩子從一個全身髒穢、擠眉弄眼、神情痛苦、驚惶失措的小野獸,擺弄成眼神清亮、滿身油光的紅麵龜,她就是有這本事。但這些女人卻開始變得不安,女人總是知道女人在想什麼,不必聽傳聞,就能嗅到某種不尋常的氣息,淑芬有時覺得是自己心裡有鬼,但這些剛生完孩子的女人,就是有股不一樣的生氣,眼睛就是能看穿妳心裡在想什麼,知道妳要來偷我的東西了,知道妳要來偷我的人。淑芬看女人的眼神總是閃爍,女人看她的眼神變得怨毒,逼得她只得草草了事,她想快點投到另一個男人的懷抱,把一日來的疲倦都拋去,哪管妳是誰的誰?妳就好好照看孩子就是了,這一趟,我保管妳母子平安,永不分離。她這麼一想,心情便輕鬆了。而這些剛生完孩子的女人,也的確不能拿她怎麼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