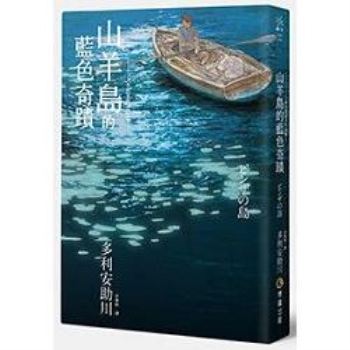若是沒死 我會活下去
即使死了 我仍會活下去
是的 不需要驚惶
在海洋的那一頭 大海鹿
正張開一朵朵色彩絢麗的傘
──來自遠方島嶼的阿萊基諾(註1)
1
雨後黃昏的天空,金黃色的陽光穿過雲層,水面滿布瀲灩波光;交錯飛過防波堤的海鷗、在貨櫃場工作的人們,都被陽光鍍上金邊。
開往安布里列島的渡輪剛離開R市港口的碼頭,正緩緩朝著港灣的灣口前進。
涼介坐在船內餐廳其中一桌,從他的位置不僅可以看到逐漸遠離的港灣風景,也能看見一部分甲板及船側的通道。甲板上的水窪因陽光照耀,彷彿灑落的碎片般閃閃發光;耀眼的光紋反射在駕駛艙上,隨著船身晃動,反覆聚攏,又迅速破碎離散。涼介的視線被光紋的節奏擄獲,剎那間,晃動的光影和誕生於海洋初始的生命印象重疊。
「你有在聽我說嗎?」
隔著桌子坐在涼介斜前方戴著眼鏡的男子,瞅著涼介的臉問。他是負責統籌島上工務的工頭。
「拜託,如果你在工地也心不在焉就完了。我跟你說話時,拜託你專心聽清楚。」
看起來四十五歲上下的工頭用手推了一下眼鏡後,撫著嘴邊稀疏的鬍鬚。船剛駛離港口,餐廳裡的客人寥寥可數。除了一個啜飲著燒酎(註2)、狀似漁民的男人,以及幾個上了年紀、正以島上方言熱絡交談的婦人之外,就只有涼介和工頭了。
「菊地涼介,二十八歲……」
由於引擎的震動,不僅桌子,連放在桌上涼介的履歷表都跟著晃動。工頭像是要壓住履歷表般,手指貼著涼介所寫的文字一行一行地確認。
「大學中輟。持有普通汽車駕照。前一個工作是餐廳廚師。對了!就是這個!打電話給你時想問你卻忘了。你是什麼廚師?中華料理?」
「不是,是……西式料理。」
「喔,那……我很愛吃鱈魚子義大利麵,你會做嗎?」
「會。」
「蛋包飯呢?」
「會。」
「唔。那,法國菜?嗯,一下子想不起來法國菜有什麼。呃……法式田螺?」
「那道菜必須使用法國特產的蝸牛才行。」
「咦?那,島上的蝸牛不行嗎?大概這麼小,島上很多。」
工頭用手指圈了個大小給涼介看。「不過,貝類比較好吃,畢竟是小島。」他彷彿自言自語般說完後,又把手放回履歷表上。
「另外,因為不確定工程什麼時候完成,所以沒有辦法馬上回來,你有先跟家人報備過嗎?」「沒有……」
「咦?」
「我沒有……家人。」
工頭把履歷表拿在手上,眼鏡後的目光飛快地掃視過一遍。
「這裡寫的緊急聯絡人呢?」
「那是我母親的電話,不過,她已經不在了。」
「過世了?」
「是的。」
「令尊呢?」
「他很早就……」
「兄弟姊妹呢?」
「沒有。」
工頭仰頭注視著餐廳的天花板,喉嚨發出呻吟般的聲音。涼介再度望向窗外,光紋依舊在駕駛艙同樣的位置躍動著。兩隻停在通道欄杆上的海鷗同時展開雙翼,往大海飛去。一個背著卡其色軍用背包、長髮隨風飛揚的男人,經過他們座位旁的窗前。
「菊地先生,那,有還不錯的人嗎?」
咦?涼介發出疑問。
工頭豎起小指,「女朋友?」
「沒有。」涼介搖頭。
工頭雙臂交叉環抱胸前,「這豈不是太孤單了嗎?」
涼介不置可否,只露出有點困窘的笑容。工頭可能懶得再找下一個話題,一逕眨著眼沉默不語。這時候,剛剛經過窗外的長髮男人進入餐廳。男人看了看四周,指著自己的鼻子便直直往涼介和工頭的桌子走過來。
「應該是這裡沒錯吧?」
「咦?」工頭半抬起身子,打開放有履歷表的資料夾。
「嗯……立川先生?要在安布里島打工的?」
「沒錯!」
男人放下軍用背包,以響遍整間餐廳的聲音打招呼:「你好!」工頭連連發出「欸?欸?」的聲音,詫異地比對履歷表和眼前的立川。
「我說立川先生,你給我的照片有點不同吧?你照片上的頭髮短多了。」
「啊,那是四年前拍的照片。」
「什麼?不是規定要用三個月內拍的照片嗎?」
「不好意思。不過,的確是我本人。」
「根本不同嘛!島上的人不知道會怎麼說……你那頭髮可以剪一剪嗎?」
「啥?要我剪?」
立川臉色大變,涼介彷彿聽到他在心裡咒罵「你這個死老頭講什麼屁話?」工頭雖然有一瞬間神色緊繃,卻連忙搖搖頭。
「不,算了,不剪也沒關係。雖然沒關係……不過……」
「怎樣?」
工頭本來似乎還想說什麼,可能看到立川粗暴地拉出椅子,因而中途打住了。
「你好,我叫吉米。」
立川很自然地向涼介伸出手。涼介雖然有些困惑仍然和他握了手。
「我是菊地涼介。」工頭再次核對了立川的履歷表。
「吉米?」
「這是我在夜店當牛郎時取的名字,本名超普通的。」
「立川一藏。」
可能沒想到工頭會立刻喊出他的本名,立川神情尷尬地笑了笑。
「呃,與其說普通,不如說是詭異。我的名字很怪吧?一藏,又不是落語家(註3)。」
對於初次見面的涼介,他仍然一股腦地問「很怪對吧?」
「唔……立川先生二十三歲,定時制高中(註4)肄業。對了!你們兩位都是中途輟學。還有,英文四級檢定……」
「喂!你搞什麼啊!不用連這些都唸出來吧?」
立川臉上的笑容消失,猛地抓住工頭的肩膀。「對不起!」工頭僵著脖子,拚命擠出聲音道歉。
「誰都有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耶。」
「真的很抱歉!」
工頭俯首道歉,但不知為何,他一低下頭瞄到立川的履歷表,又開始喃喃地唸了起來。
「八王子型男俱樂部、月光城男公關……」
「你這傢伙!」
在工頭一旁的立川嚷著,挑起一邊眉毛。
「哎呀,抱歉,不知不覺就……呃,不過,也真巧,你們兩個都是中途輟學,工作地點也是經常換……」
涼介和立川互看了一眼。
「總之我希望你們一直在島上待到工程結束,不要中途就不幹了。話說回來,定期往返的船只有星期一這班,就算想回也回不來,哈哈哈。」
工頭大笑著露出牙齦,接著突然站了起來。
「先不說這些,還有一個人沒到。究竟怎麼搞的?明明已經打電話跟我說收到船票了,應該上船了才對。」
「也就是說,這次總共有三個人來打工?」
立川不是問工頭,而是問涼介。「好像是。」涼介低聲回答。
「大概在船艙裡睡著了吧,雖然無所謂啦……算了,我們三個先乾杯吧!不照規矩來很傷腦筋耶。真是的!」
涼介覺得工頭故意嘆氣給他們聽,他的神情彷彿在宣告,事情從一開始就進行得不順利,一切都要怪沒來集合的那個人。
「搞什麼嘛!那傢伙!」
立川以不滿的眼神瞥了走向餐券販賣處的工頭一眼。涼介再度看向窗外。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到港灣,一眼望去,只見藍黑色的廣闊海洋以及橫向延伸出去的海岬輪廓。光線更加微弱,橙色的夕陽不見蹤影,反射在駕駛艙上的光紋也消失了,只留下大片藍灰色的天空。
「還是回去好了,如果那傢伙是工頭的話。」
涼介沒有附和立川。他繼續望著海岬,只應了一句:「是嗎?」「而且,日薪不是少得很嗎?」
「嗯,確實不多。」
涼介委婉地應答之際,工頭端著放有幾罐啤酒的托盤回來了。
「我們乾杯吧!」
三人把下酒菜擺到桌上,拿起啤酒,形式化地乾了杯。立川還是照樣不理會工頭,工頭沒轍,只好跟涼介攀談。只不過,涼介並不是愛說話的人。周圍的客人逐漸增多,餐廳裡開始熱鬧起來,只有他們這一桌始終瀰漫著一股拘束的氣氛。
「不過,也太奇怪了。該不會沒搭上船吧?」
工頭換了一下交疊的雙腳,看了好幾次手錶。立川拿出手機,開始按上面的按鍵,不知在操作什麼。涼介則完全被窗外的天空及大海的景色所吸引。工頭突然站起身來時,正好是三人已經完全無話可說的時候。
「啊,我們等妳好久了!」
聽到工頭這句話,涼介和立川跟著回頭看。
「不好意思,真抱歉。」
走近他們的,是一個留著短髮、穿皮夾克的女子。
「因為剛好看到夕陽,實在太美了,一不小心就在甲板上看得出神。」
「我還在擔心要是妳沒上船就完了。」
工頭一臉放心的神情,遞給她一罐啤酒。她伸手接過去,笑道:「遲到先罰一杯?」
「欸?」
立川開始坐立不安,帶著一臉五味雜陳的表情,像浮上水面的金魚一樣張著口,連連發出「欸?欸?」的疑問。
「為什麼是女的?」立川問。
涼介當然也沒想到會是這種狀況。他沒說話,只輕輕點了點頭打招呼。女子回給涼介一個微笑。五官很端正的女生,涼介心想。只不過,她的耳朵,以及稍微有點高的鼻子,各戴著稍嫌多了些的耳環和鼻環。
「你們好,我叫本宮薰。」
「喔──妳叫阿薰?鼻環還真勁爆。妳在玩樂團?」立川撥了撥頭髮,斜著肩前傾面對薰。薰搖頭否認,只簡單回了一句「請多指教」。
「這麼一來三個人都到齊了,太好了。」
「我太驚訝了,那個,阿薰也跟我們一起做土木嗎?土木耶。」
立川似乎忘了前一刻還很不愉快,嘻皮笑臉地問工頭。
「要做的事很多,除了土木還有其他工作。」
「沒錯沒錯,我本來就想問這件事。」
「有機會再說。反正,總有那麼一天。」
工頭露出「反正時間還多得是」的表情,用力點了點頭,接著把盛有炸雞的碟子推到薰的面前。薰回應了一聲「謝謝」,卻沒有伸手去拿,坐在隔壁桌開始喝起啤酒。「過來一起喝不好嗎?」
立川招了招手。薰皺皺鼻子,微笑地婉拒說:
「反正,總有那麼一天。」
工頭剛剛那句話,薰模仿得唯妙唯肖,惹得工頭撫著淡淡的鬍鬚哈哈大笑。立川看了工頭一眼,嘟噥著:「我完全被弄糊塗了。」
工頭似乎因此想起了什麼,原本打算攤開桌上一份文件,看樣子可能是薰的履歷表,不過,他看了看涼介和立川,卻中途打住了。
「對了,你們要吃什麼喝什麼都儘早結束,趕快睡覺比較好。」
「為什麼?」
薰一反問,工頭旋即看向開始變暗的大海。
「今晚浪似乎很高,出了海灣後,應該會搖晃得很厲害。」
涼介、立川和薰三人面面相覷。
「真討厭。我已經開始不舒服了。」
立川嘴角上揚,笑著說:「等一下我幫妳搓搓背放鬆一下吧!」
「真遺憾,我們不是同一個房間。」
工頭連忙解釋:「真抱歉,菊地和立川兩位在二等艙,和其他人睡大通鋪。本宮薰在頭等艙,睡單人房。」
瞧!我說的沒錯吧。薰和工頭互看了一眼。立川「嘖」了一聲,「什麼跟什麼嘛,真無趣。」然後誇張地聳了聳肩。涼介喝光啤酒,凝視著遠方岬角逐漸亮起的點點燈光。
三月的海上,覆蓋著更顯陰霾的天空。船朝著西南方往安布里列島前進。
註1:義大利的假面喜劇 (Commedia dell’arte)(十六世紀末流行於義大利的喜劇)中的經典丑角。阿萊基諾 (Arlecchino) 是劇中服侍二主的僕人。
註2:蒸餾酒的一種,以米、麥、芋頭、甘藷、黑糖等原料經酒精發酵後蒸餾而成。因酒精濃度高、價格便宜,在日本相當受到男性歡迎。
註3:「落語」是日本傳統表演藝術,類似單口相聲。「一藏」是落語家常用的藝名。
註4:日本高中按照不同的授課方式,分為全日制、定時制和函授制。定時制只有白天半天或夜間上課。
即使死了 我仍會活下去
是的 不需要驚惶
在海洋的那一頭 大海鹿
正張開一朵朵色彩絢麗的傘
──來自遠方島嶼的阿萊基諾(註1)
1
雨後黃昏的天空,金黃色的陽光穿過雲層,水面滿布瀲灩波光;交錯飛過防波堤的海鷗、在貨櫃場工作的人們,都被陽光鍍上金邊。
開往安布里列島的渡輪剛離開R市港口的碼頭,正緩緩朝著港灣的灣口前進。
涼介坐在船內餐廳其中一桌,從他的位置不僅可以看到逐漸遠離的港灣風景,也能看見一部分甲板及船側的通道。甲板上的水窪因陽光照耀,彷彿灑落的碎片般閃閃發光;耀眼的光紋反射在駕駛艙上,隨著船身晃動,反覆聚攏,又迅速破碎離散。涼介的視線被光紋的節奏擄獲,剎那間,晃動的光影和誕生於海洋初始的生命印象重疊。
「你有在聽我說嗎?」
隔著桌子坐在涼介斜前方戴著眼鏡的男子,瞅著涼介的臉問。他是負責統籌島上工務的工頭。
「拜託,如果你在工地也心不在焉就完了。我跟你說話時,拜託你專心聽清楚。」
看起來四十五歲上下的工頭用手推了一下眼鏡後,撫著嘴邊稀疏的鬍鬚。船剛駛離港口,餐廳裡的客人寥寥可數。除了一個啜飲著燒酎(註2)、狀似漁民的男人,以及幾個上了年紀、正以島上方言熱絡交談的婦人之外,就只有涼介和工頭了。
「菊地涼介,二十八歲……」
由於引擎的震動,不僅桌子,連放在桌上涼介的履歷表都跟著晃動。工頭像是要壓住履歷表般,手指貼著涼介所寫的文字一行一行地確認。
「大學中輟。持有普通汽車駕照。前一個工作是餐廳廚師。對了!就是這個!打電話給你時想問你卻忘了。你是什麼廚師?中華料理?」
「不是,是……西式料理。」
「喔,那……我很愛吃鱈魚子義大利麵,你會做嗎?」
「會。」
「蛋包飯呢?」
「會。」
「唔。那,法國菜?嗯,一下子想不起來法國菜有什麼。呃……法式田螺?」
「那道菜必須使用法國特產的蝸牛才行。」
「咦?那,島上的蝸牛不行嗎?大概這麼小,島上很多。」
工頭用手指圈了個大小給涼介看。「不過,貝類比較好吃,畢竟是小島。」他彷彿自言自語般說完後,又把手放回履歷表上。
「另外,因為不確定工程什麼時候完成,所以沒有辦法馬上回來,你有先跟家人報備過嗎?」「沒有……」
「咦?」
「我沒有……家人。」
工頭把履歷表拿在手上,眼鏡後的目光飛快地掃視過一遍。
「這裡寫的緊急聯絡人呢?」
「那是我母親的電話,不過,她已經不在了。」
「過世了?」
「是的。」
「令尊呢?」
「他很早就……」
「兄弟姊妹呢?」
「沒有。」
工頭仰頭注視著餐廳的天花板,喉嚨發出呻吟般的聲音。涼介再度望向窗外,光紋依舊在駕駛艙同樣的位置躍動著。兩隻停在通道欄杆上的海鷗同時展開雙翼,往大海飛去。一個背著卡其色軍用背包、長髮隨風飛揚的男人,經過他們座位旁的窗前。
「菊地先生,那,有還不錯的人嗎?」
咦?涼介發出疑問。
工頭豎起小指,「女朋友?」
「沒有。」涼介搖頭。
工頭雙臂交叉環抱胸前,「這豈不是太孤單了嗎?」
涼介不置可否,只露出有點困窘的笑容。工頭可能懶得再找下一個話題,一逕眨著眼沉默不語。這時候,剛剛經過窗外的長髮男人進入餐廳。男人看了看四周,指著自己的鼻子便直直往涼介和工頭的桌子走過來。
「應該是這裡沒錯吧?」
「咦?」工頭半抬起身子,打開放有履歷表的資料夾。
「嗯……立川先生?要在安布里島打工的?」
「沒錯!」
男人放下軍用背包,以響遍整間餐廳的聲音打招呼:「你好!」工頭連連發出「欸?欸?」的聲音,詫異地比對履歷表和眼前的立川。
「我說立川先生,你給我的照片有點不同吧?你照片上的頭髮短多了。」
「啊,那是四年前拍的照片。」
「什麼?不是規定要用三個月內拍的照片嗎?」
「不好意思。不過,的確是我本人。」
「根本不同嘛!島上的人不知道會怎麼說……你那頭髮可以剪一剪嗎?」
「啥?要我剪?」
立川臉色大變,涼介彷彿聽到他在心裡咒罵「你這個死老頭講什麼屁話?」工頭雖然有一瞬間神色緊繃,卻連忙搖搖頭。
「不,算了,不剪也沒關係。雖然沒關係……不過……」
「怎樣?」
工頭本來似乎還想說什麼,可能看到立川粗暴地拉出椅子,因而中途打住了。
「你好,我叫吉米。」
立川很自然地向涼介伸出手。涼介雖然有些困惑仍然和他握了手。
「我是菊地涼介。」工頭再次核對了立川的履歷表。
「吉米?」
「這是我在夜店當牛郎時取的名字,本名超普通的。」
「立川一藏。」
可能沒想到工頭會立刻喊出他的本名,立川神情尷尬地笑了笑。
「呃,與其說普通,不如說是詭異。我的名字很怪吧?一藏,又不是落語家(註3)。」
對於初次見面的涼介,他仍然一股腦地問「很怪對吧?」
「唔……立川先生二十三歲,定時制高中(註4)肄業。對了!你們兩位都是中途輟學。還有,英文四級檢定……」
「喂!你搞什麼啊!不用連這些都唸出來吧?」
立川臉上的笑容消失,猛地抓住工頭的肩膀。「對不起!」工頭僵著脖子,拚命擠出聲音道歉。
「誰都有不想讓別人知道的事耶。」
「真的很抱歉!」
工頭俯首道歉,但不知為何,他一低下頭瞄到立川的履歷表,又開始喃喃地唸了起來。
「八王子型男俱樂部、月光城男公關……」
「你這傢伙!」
在工頭一旁的立川嚷著,挑起一邊眉毛。
「哎呀,抱歉,不知不覺就……呃,不過,也真巧,你們兩個都是中途輟學,工作地點也是經常換……」
涼介和立川互看了一眼。
「總之我希望你們一直在島上待到工程結束,不要中途就不幹了。話說回來,定期往返的船只有星期一這班,就算想回也回不來,哈哈哈。」
工頭大笑著露出牙齦,接著突然站了起來。
「先不說這些,還有一個人沒到。究竟怎麼搞的?明明已經打電話跟我說收到船票了,應該上船了才對。」
「也就是說,這次總共有三個人來打工?」
立川不是問工頭,而是問涼介。「好像是。」涼介低聲回答。
「大概在船艙裡睡著了吧,雖然無所謂啦……算了,我們三個先乾杯吧!不照規矩來很傷腦筋耶。真是的!」
涼介覺得工頭故意嘆氣給他們聽,他的神情彷彿在宣告,事情從一開始就進行得不順利,一切都要怪沒來集合的那個人。
「搞什麼嘛!那傢伙!」
立川以不滿的眼神瞥了走向餐券販賣處的工頭一眼。涼介再度看向窗外。現在已經完全看不到港灣,一眼望去,只見藍黑色的廣闊海洋以及橫向延伸出去的海岬輪廓。光線更加微弱,橙色的夕陽不見蹤影,反射在駕駛艙上的光紋也消失了,只留下大片藍灰色的天空。
「還是回去好了,如果那傢伙是工頭的話。」
涼介沒有附和立川。他繼續望著海岬,只應了一句:「是嗎?」「而且,日薪不是少得很嗎?」
「嗯,確實不多。」
涼介委婉地應答之際,工頭端著放有幾罐啤酒的托盤回來了。
「我們乾杯吧!」
三人把下酒菜擺到桌上,拿起啤酒,形式化地乾了杯。立川還是照樣不理會工頭,工頭沒轍,只好跟涼介攀談。只不過,涼介並不是愛說話的人。周圍的客人逐漸增多,餐廳裡開始熱鬧起來,只有他們這一桌始終瀰漫著一股拘束的氣氛。
「不過,也太奇怪了。該不會沒搭上船吧?」
工頭換了一下交疊的雙腳,看了好幾次手錶。立川拿出手機,開始按上面的按鍵,不知在操作什麼。涼介則完全被窗外的天空及大海的景色所吸引。工頭突然站起身來時,正好是三人已經完全無話可說的時候。
「啊,我們等妳好久了!」
聽到工頭這句話,涼介和立川跟著回頭看。
「不好意思,真抱歉。」
走近他們的,是一個留著短髮、穿皮夾克的女子。
「因為剛好看到夕陽,實在太美了,一不小心就在甲板上看得出神。」
「我還在擔心要是妳沒上船就完了。」
工頭一臉放心的神情,遞給她一罐啤酒。她伸手接過去,笑道:「遲到先罰一杯?」
「欸?」
立川開始坐立不安,帶著一臉五味雜陳的表情,像浮上水面的金魚一樣張著口,連連發出「欸?欸?」的疑問。
「為什麼是女的?」立川問。
涼介當然也沒想到會是這種狀況。他沒說話,只輕輕點了點頭打招呼。女子回給涼介一個微笑。五官很端正的女生,涼介心想。只不過,她的耳朵,以及稍微有點高的鼻子,各戴著稍嫌多了些的耳環和鼻環。
「你們好,我叫本宮薰。」
「喔──妳叫阿薰?鼻環還真勁爆。妳在玩樂團?」立川撥了撥頭髮,斜著肩前傾面對薰。薰搖頭否認,只簡單回了一句「請多指教」。
「這麼一來三個人都到齊了,太好了。」
「我太驚訝了,那個,阿薰也跟我們一起做土木嗎?土木耶。」
立川似乎忘了前一刻還很不愉快,嘻皮笑臉地問工頭。
「要做的事很多,除了土木還有其他工作。」
「沒錯沒錯,我本來就想問這件事。」
「有機會再說。反正,總有那麼一天。」
工頭露出「反正時間還多得是」的表情,用力點了點頭,接著把盛有炸雞的碟子推到薰的面前。薰回應了一聲「謝謝」,卻沒有伸手去拿,坐在隔壁桌開始喝起啤酒。「過來一起喝不好嗎?」
立川招了招手。薰皺皺鼻子,微笑地婉拒說:
「反正,總有那麼一天。」
工頭剛剛那句話,薰模仿得唯妙唯肖,惹得工頭撫著淡淡的鬍鬚哈哈大笑。立川看了工頭一眼,嘟噥著:「我完全被弄糊塗了。」
工頭似乎因此想起了什麼,原本打算攤開桌上一份文件,看樣子可能是薰的履歷表,不過,他看了看涼介和立川,卻中途打住了。
「對了,你們要吃什麼喝什麼都儘早結束,趕快睡覺比較好。」
「為什麼?」
薰一反問,工頭旋即看向開始變暗的大海。
「今晚浪似乎很高,出了海灣後,應該會搖晃得很厲害。」
涼介、立川和薰三人面面相覷。
「真討厭。我已經開始不舒服了。」
立川嘴角上揚,笑著說:「等一下我幫妳搓搓背放鬆一下吧!」
「真遺憾,我們不是同一個房間。」
工頭連忙解釋:「真抱歉,菊地和立川兩位在二等艙,和其他人睡大通鋪。本宮薰在頭等艙,睡單人房。」
瞧!我說的沒錯吧。薰和工頭互看了一眼。立川「嘖」了一聲,「什麼跟什麼嘛,真無趣。」然後誇張地聳了聳肩。涼介喝光啤酒,凝視著遠方岬角逐漸亮起的點點燈光。
三月的海上,覆蓋著更顯陰霾的天空。船朝著西南方往安布里列島前進。
註1:義大利的假面喜劇 (Commedia dell’arte)(十六世紀末流行於義大利的喜劇)中的經典丑角。阿萊基諾 (Arlecchino) 是劇中服侍二主的僕人。
註2:蒸餾酒的一種,以米、麥、芋頭、甘藷、黑糖等原料經酒精發酵後蒸餾而成。因酒精濃度高、價格便宜,在日本相當受到男性歡迎。
註3:「落語」是日本傳統表演藝術,類似單口相聲。「一藏」是落語家常用的藝名。
註4:日本高中按照不同的授課方式,分為全日制、定時制和函授制。定時制只有白天半天或夜間上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