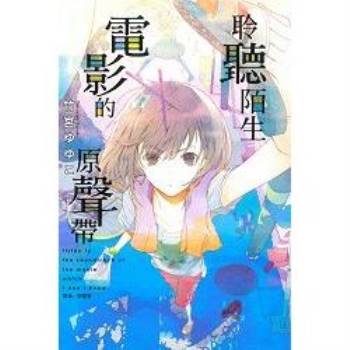腳踩廁所拖鞋奔跑於盛夏的鄉間小路上,斜揹著的小包包隨著步伐彈跳,不停拍打屁股。
旋轉吧──某個人曾這麼說過。
世間萬物都在無止境地循環,旋轉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動也不動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所以大家都轉呀轉、轉呀轉、轉呀轉地……枇杷覺得彷彿聽到有人在耳邊這麼溫柔低語。
(轉呀轉……說到旋轉……)
──啊!※拿破崙二人組。(譯註:由Bona植木與Parte小石所組成的魔術師組合,藝名取自拿破崙的姓Bonaparte。)
※Parte小石的頭部。(編註:拿破崙二人組的拿手魔術,將特殊道具裝於Parte小石的頭上,讓觀眾產生頭部能夠轉動三六○度的錯覺。)
(還有那個也是……)
放浪兄弟的Choo Choo TRAIN開頭舞蹈;「讀取中」的gif;黑天鵝奧吉莉雅的華麗鞭轉;※利普尼茨卡婭的貝爾曼旋轉;還有,過去的我們。(譯註:俄羅斯的年輕花式滑冰女選手。)
真的耶。
大家真的都在不停旋轉。
枇杷忘我地繼續往前奔跑,腦中接連不斷冒出旋轉的物體。
(迴轉壽司、龍捲風,以及陀螺、攪拌器,還有電動牙刷!)
想法接連浮現,一股股強烈的衝擊貫穿枇杷的心臟。真的,這個世界的一切全部都在轉動。既然如此,自己應該也是一樣。旋轉吧。旋轉著。
跑動著的雙腳再次提升速度,卯足全力衝過夏天。下巴跟著晃動不已,若不咬緊牙關,感覺好像會脫落。她已經停不下來了。這時,及膝的緊身裙襬發出「劈啪」的撕裂聲。真的假的啊?她遲疑了一瞬間,但沒空管這個了。於是枇杷假裝沒聽到,繼續往前奔去。
從天而降的毒辣陽光炙烤著頭頂,蟬鳴聲傾瀉而下,汗水如眼淚般沿著臉頰滑落。枇杷依舊埋頭猛衝,好似要一頭栽進未來。
兩旁裸露的岩壁逐漸逼近,道路愈來愈狹窄,前方是一條幽暗的隧道。只要鑽進那穿透碧綠山表的深黑,再自明亮的出口離開,便來到車站前的市區。可是,啊啊……
(沙拉脫水器、大迴旋、黑膠唱片、CD、DVD!)
──這個世界上充斥著各種轉來轉去的東西啊!
古今中外,現在、過去、未來,從人類誕生以來至此時此刻,所有瞬間都在不停轉動的事物啊!
從旋轉中誕生的這股力量!
(請務必也賜予我團團轉的力量,讓我踏上最終戰場!我無論如何都想贏!就算被打飛也無怨無悔!)
右眼從剛才就痛得厲害,枇杷一邊跑一邊用右手撫摸痛處。這股劇痛絕對是某種信號──告訴自己經過一年的等待,對決的時刻終於到來。
必須打倒的敵人,不久就會現身吧。他一定就在那個隧道裡,隱身於那個就連夏天都陰森潮濕的黑暗中,靜待自己的到來。
枇杷似乎可以想像對敵人的樣貌。
他應該穿著漆黑的水手服。
除了領口上點綴著的兩條白線外,他的打扮可說是全身黑,就連絲質領帶都是黑的。隨風飄揚的柔順長髮同樣烏黑,腳上穿著光可鑑人的黑皮鞋及黑色高筒襪。
平整的厚瀏海下有張下巴纖細、令人驚艷的美麗臉龐,看上去幾乎就像個雪白的倒三角形。
敵人大概正看著闖入隧道直奔而來的枇杷,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原本倚靠的牆壁。然後他會踏著悠閒的腳步,像要攔住去路似地擋在枇杷面前。那上翹的眼角鋒利如刃,危險得讓人笑不出來。
將閃耀著盛夏陽光的小小出口擋在身後,敵人渾身散發烈火般的黑色鬥氣,用清澈甜美的嗓音說出那句固定台詞。
「讓我來──」
對方以右手的球拍指向枇杷。
「制裁──」
接著輕輕扭腰,從下巴下方亮出左手握著的聖球。
「妳的罪行!」
總有一天,枇杷不得不與那傢伙正面對決。不和他戰鬥並打倒他,枇杷永遠無法向前邁進,無法繼續活下去。
而那個敵人名為──罪。
然而──就在枇杷為了取其性命而拚命奔走,準備衝進隧道時,她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她用腳蹬向地面,腦中沒來由地浮現朋友那天平靜的笑容。那顆聖球最終仍會無情地旋轉著襲來吧。
轉呀轉、轉呀轉……電風扇、洗衣機、呼拉圈、飛盤,還有地球和銀河,以及原子。全部,一切,大家,還有自己,都轉個不停。
旋轉正是世界的真理,是自然法則。只要存在於這世上,只要還活著,就不能夠停下來。
因旋轉而產生的離心力,將原本沉澱在意識最深處的回憶,從漩渦中心吸起並擴散開來,滿溢於枇杷的內部。不堪回首的往事有如暴風雨般四處灑落。
時間轉呀轉地回溯到過去,所有場景開始鮮明地浮現。
事情的開端始於那個夏天。
(當時我拚了命地想讓運轉停止。)
那個夏天的那個夜晚,枇杷把腳踏車放回家裡車庫的那個深夜,凌晨三點鐘。
立起腳架、上好鎖後,不知為何輪輻仍不厭其煩地發出聲響持續轉動著。那雜音讓枇杷打從心底感到厭煩,於是她踹了車輪一腳,想制止迴轉。結果大拇指指甲不敵橡膠的摩擦而造成撕裂傷,痛楚與懊悔讓枇杷忍不住咂了下舌。
──嘖!
(指甲你到底有多脆弱啊!)
枇杷在心裡暗自咒罵,躡手躡腳地爬上玄關前的台階。
她進入門廊屋簷下,悄悄打開門,從身體能通過的最低限度寬度迅速溜進家門。然後再以同樣謹慎的動作關上門,輕輕上鎖。
那一聲不響、不疾不徐的身手好似「女太極拳好手」或是「女竊賊」,也可能是「會使太極拳的女竊賊」,但以上皆非正確答案,因為這裡是她家。
凌晨三點,錦戶枇杷才返回家裡。
她輕聲脫掉愛用的褐色橡膠廁所拖鞋,踏上玄關。此時還不能掉以輕心,她得在不被熟睡的家人發現自己半夜偷溜出去的情況下,回到自己房間才行。
今晚的東京是個熱帶夜,悶熱到小籠包都能蒸熟的程度。在如此悶熱不適的三更半夜裡,枇杷獨自騎著腳踏車在街上繞來繞去,現在剛回到家。她自己也覺得這樣的行為很不正常,因此放輕手腳,不敢發出一點聲音,靜靜地穿過家裡的走廊。
她熱得要命,掛在脖子上用來擦汗的毛巾早已濕透,T恤也濕答答的,整個人上氣不接下氣、腳步蹣跚。
(慘了,頭昏眼花……)
不快點補充水分的話,說不定會筋疲力竭地直接倒下。
原本打算回房間的她改變了路線,在一片漆黑中鬼鬼祟祟地前進,從客廳往更裡頭的廚房走去。
打開冰箱候,她發現裡面有啤酒,雖然不是特別想攝取酒精,不過因為近在眼前而且冰得恰到好處,所以便順手拿起。
枇杷就這樣站在黑漆漆的廚房一隅,啜飲啤酒。冰涼的感覺幾乎沁入牙根,嘶嘶作響的碳酸刺激著喉嚨。看來枇杷似乎比自己想像中還要口乾舌燥,她忘我地一口接著一口,咕嘟咕嘟地將啤酒灌下肚。
她一口氣灌下半瓶左右的份量後,就這麼靠在牆上,抵著牆一屁股滑坐在廚房地板上。她差點就要打出嗝來,連忙用拳頭摀住嘴,熟練地讓啤酒的氣味無聲地從鼻子送出。
在這麼熱的天氣,全身汗水淋漓又口乾舌燥的狀態下,痛快地猛灌一瓶沁涼的啤酒。
即使如此,枇杷還是一點都高興不起來。她現在的心情完全無法發出「好喝!」「哇~讚啦!」「噗哈~!」諸如此類的讚嘆詞,一點也不覺得幸福。
她板著臉又喝了一口酒,然後將罐底的圓形凹陷處抵在膝頭。
問題在於今晚仍舊一無所獲。即使有啤酒也無法排解她心頭的鬱悶。枇杷在黑暗中縮起身子,腦袋垂靠於套著運動褲的兩膝間。
(又沒抓到……)
好似有一團比黑暗更加深沉的昏晦之物從頭上滴落般,苦澀的心情逐漸填滿胸口,讓枇杷更加鬱鬱寡歡。
事情是從四月底開始的,至今已過了三個月以上。我整整三個月都在做這種事嗎……?真的假的?
竟然如此虛度光陰,連枇杷自己都有些訝異。這麼做真的好嗎?只是不斷空轉、空轉再空轉,回過神來已經八月了!別說逮到人了,連個影子都沒看見,根本毫無成果可言。做這種事果然沒用嗎?太過有勇無謀,太沒計畫性了嗎?枇杷對此絕不放棄,但是又想不到其他方法。
明明想在八月十七號以前將這件事解決掉的。
她一直在找某個傢伙,一心想在那天之前把人找出來、逮住他,還要狠狠地教訓他一頓。
枇杷無論如何都想把被那傢伙搶走的東西拿回來。
和那傢伙相遇,是在春天快結束的時候。
櫻花早已散盡,種植於綿長的人行道兩側的樹木枝頭開始冒出鮮嫩綠葉。
時間大概是剛過深夜一點半,枇杷離開附近的家庭餐廳,一個人踩著腳踏車準備回家。
人煙稀少的住宅區裡,連一點微風吹拂的聲音都沒有,四周鴉雀無聲。肌膚接觸到的空氣溫熱得令人不舒服。一台紅綠燈上掛著「故障」的牌子,綠、黃、紅色的燈同時一閃一閃地發出刺眼光芒。枇杷抬頭仰望,內心只覺得這景象很少見,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搞不好其實是對即將來襲的事態的警告。可惜她當時沒有察覺,也完全沒有提防。
這裡是東京板橋區。
這塊幽靜到幾近無趣的住宅區,正是錦戶枇杷的家鄉。
她從出生就一直住在這裡。這一帶雖然也屬於東京都,卻有許多佔地廣大的獨門獨戶房屋林立。這裡對枇杷而言就像「後院」般,她熟知每一條小巷子。除了最近忽然開始興建的大樓區一帶,由於變化太大還來不及更新資訊外,這個不算大的市區的地理位置幾乎都儲存於枇杷的腦中。她於此土生土長,而且這裡又是她的後院──即使閉上眼睛她也能順利走回家。
這附近從以前起就是公認治安良好的區域,就算年輕女性半夜獨自在外行走,而且行動符合正常範圍(比如沒有喝得爛醉如泥,也沒有因為低頭玩手機或聽音樂而渾然忘我),基本上不會出什麼事──理應是這樣才對。至少在那個夜晚之前的二十三年來,身為當地居民的枇杷是這麼認為的。
那天枇杷並不急著趕路,只是悠哉地踩著腳踏車踏板。
忽然間,她的視線被閃著白光、佇立於人行道一角的自動販賣機吸引過去,嚇了一跳。
「哇啊!」
枇杷不小心驚叫出聲。因為貼在販賣機上的偶像海報幾乎跟真人一樣大,害她以為有個人站在那裡。
當然,枇杷馬上就發現是自己看錯了。她嘟噥了聲「搞什麼啊」便將視線從笑容滿面的偶像身上移開。竟然嚇我,害人家不小心叫出聲來了啦,真丟臉。好險沒人看見……
就在她微微鬆了口氣的瞬間──
有個人冷不防地伸出手,探向枇杷放在腳踏車置物籃裡的布製托特包。
枇杷沒有像剛才一樣發出單純感到訝異的驚呼聲,畢竟此刻的驚訝程度非同小可。
聽說人類這種生物一旦過度驚嚇,怦怦直跳的心臟就會通過脖子直竄腦門,撞擊頭蓋骨內部並在那裡劇烈跳動。枇杷還是第一次體會到這種事。不,可是,心臟?跳到頭裡?怎麼可能啊。當下,她連如此冷靜思考的能力都被突發事件給奪走,腦袋完全無法運轉。視野急遽縮小,控制臟器的管線像是斷掉般讓肺部停在膨脹的極限狀態,嘴巴也毫無意義地張著。她就是這麼震驚,只顧著震驚,震驚到忘記抓穩手把,連車帶人橫倒在地。
枇杷維持著跨在坐墊上的姿勢,雖然勉強用一隻腳踩地,但依舊失去平衡跌了一跤。托特包也從腳踏車籃裡飛了出去。
剛才伸手要拿枇杷包包的,是個留著一頭陰森長髮、穿得一身黑的女人,看上去就很危險。
凌亂的頭髮、質地單薄的黑衣、遮掩起來的臉孔、隨著喘息上下起伏的肩膀、格外高大的身軀──在在散發出令人不舒服的氣息。「不想與對方扯上關係」的指數瞬間破表。如果真的有測量這種情感數值的器具,指針應該會像下面的毛髮一樣捲曲起來才對。那女人一邊揮灑著極度「令人不想扯上關係」的氛圍,一邊用噁心的前屈小跑動作朝枇杷的包包直奔而來,活像隻習得了蟑螂高速移動技巧的蛞蝓。
飛揚的百褶裙底下露出了異常蒼白、光滑的小腿,讓人下意識冒出「好噁心!」的感想。雖然現在沒有閒工夫管這些,枇杷還是忍不住這麼想──噁心得讓人渾身打哆嗦,這感覺幾乎打破了自己心目中史上最噁心的紀錄,甚至噁心到令人心中升起一把無名火。這傢伙是怎樣?到底在搞什麼?愈看愈噁心耶!為什麼會噁到讓人作嘔?她還好吧?枇杷不由得像這樣替她擔心起來。
接著,枇杷看見那個噁心的傢伙用比一般女性還要大的手,一把抓住自己的包包。
那一剎那,她總算──
「……噫呀~啊啊啊啊~~~!」
發出有如吹壞的笛子般的尖叫。
包包雖然是雜誌附錄送的(而且還是去年的),不過裡面放了皮夾、智慧型手機和家裡鑰匙。枇杷不顧一切,擒抱似地縱身撲向犯人抓起的包包。
小偷!強盜!扒手!滿腔怒火和恐懼幾乎要炸裂開來,她早已失去了冷靜,只是卯足全力想搶回包包。無奈犯人也不肯放棄,兩人你拉我扯後,開始打轉,就這樣在自動販賣機的光源照映下旋轉著糾纏在一起。
兩人在氣息交織的極近距離無意間對上視線的瞬間,枇杷再次發出慘叫。
「啊呀啊啊啊~~~!」
這傢伙到底是怎樣──令人全身起雞皮疙瘩!毛骨悚然!此刻毛孔同心協力張開的程度教人嘆為觀止。因為、因為──
(這傢伙根本是個男的嘛!)
早知道對方是男性,自己就不會這麼頑強抵抗了。因為比力氣她贏不過對方,肯定會輸的。枇杷感到全身血液突然倒流。難怪我會覺得那麼噁心,因為這傢伙是個變態啊。
他的長髮異常蓬亂;仔細一看,身上穿的還是水手服!不管是臉的輪廓,還是搶包包的手,以及那大聲喘氣的聲音,都顯示他徹頭徹尾是個男的,是個不折不扣的變態。枇杷心想著剛才應該要逃跑才對,她不曾有過如此具體且強烈的後悔。她無法壓抑這股情緒,覺得好想哭。我可能會被強暴?不,更糟的情況還可能被殺掉。趕快逃吧,得逃走才行!但是被這種人搶走包含所有個人資料的皮夾、手機和鑰匙真的好嗎?這樣也不太好吧!
該怎麼辦才好?我要放開手?還是拚死不放?就在幾近狂亂的思緒使她出現猶豫的那一秒鐘,枇杷想起了自己不能放手的唯一理由。
皮夾裡有那個。
『我希望枇杷帶著這個。』
──對啊。
不行,我不可以放棄,千萬不能放開手,打死都不放開。
「……要、要錢的話──」
她以尖銳的哭聲說著。
「全、全部……都給你……!想要手機的話也可以拿去!」
枇杷拚命提出請求。她是真心這麼想。如果這樣能解決事情就該偷笑了。
「如果你要、要我不報警,我就不報警……!所以請還給我!把手放開!」
可惜對方似乎不領情。他以單手抓著包包,同時舉起另一隻手。枇杷半是放棄地看著他的動作,難看但奮力地縮起身子,以求就算被揍也能盡量減輕傷害。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沒有被揍飛,取而代之的是手肘附近被人抓住。男人的拇指就那樣按上枇杷的肘骨,輕柔的觸感甚至讓人感覺到一股不符合當下情況的溫柔。枇杷才察覺到不對勁,對方的拇指便用力一壓,一陣電擊般的尖銳疼痛從肩膀傳至胸骨正中央,眼前變得一片空白。枇杷不曉得對方做了什麼,但可以確定自己遭遇了令人恐懼的疼痛。
「噫──噫噫噫噫……!」
膝蓋無力地彎曲,枇杷即使整個人失去重心癱坐在地,依然沒有放開包包。接著,對方將手搭上她的肩膀──他要勒我的脖子嗎?死定了。枇杷害怕得死命甩頭,這次拇指深深地嵌入鎖骨上方的空隙,傳來了「啪唧、劈哩」宛如氣泡之類的物體爆開的清脆聲,但聲音來源不知為何並非鎖骨,而是來自眼睛深處。感覺就像從兩耳後方沿著頭皮被套上一條令人痛不欲生的帶子般,但對方明明沒有碰到那裡。
「噫──噫噫嗚嗚嗚啊啊……!」
枇杷再也撐不住,趴倒在路面上。屁股左邊大概被對方的膝蓋按住了,恐怕是拳骨的部位正緊貼著自己右腰上方。對方沒有再施加打擊而是觸摸,然後直接將全身的重量壓了上來。那一瞬間,枇杷在眼底看見了竄起的火柱,還浮現出「天誅!」這個詞彙,不過對方什麼都沒說就是了。
她已經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如奔流般從屁股往下竄的疼痛寒冷刺骨,由腰部往上攀升的疼痛則灼熱難耐,令人聯想到萬馬奔騰的畫面。氣勢磅礡的馬蹄從頭頂往腳尖踐踏而過,奪走了枇杷靈魂裡能夠繼續「努力」的東西。
她覺得渾身無力。那傢伙用膝蓋壓著枇杷的屁股,在她頭頂翻著包包。枇杷淚眼汪汪地拚命扭動身體,想要看清那傢伙的動作。對方打開了枇杷的皮夾,但卻看也不看放在裡面的幾張千元鈔票,也無視提款卡的存在。
「……只、只有那個……」
她沒辦法好好說話。
那傢伙從皮夾裡拿出的是收在夾層裡的一張照片。只有那個不行,只有那個東西不能再失去了,住手。是因為看穿枇杷的心思所以才要搶走嗎?對於枇杷之外的人而言,那東西明明毫無價值,但他偏偏要搶那個,只鎖定那個。
住手。
「……唔……!」
枇杷不顧幾乎要脫臼的肩膀,奮力伸出手,在空中徒然劃出一道有如漫畫中描繪的美麗弧線。乾脆俐落得教人絕望。照片被搶走了。
重量自枇杷的屁股上消失,皮夾和包包被扔在一旁;手機被拿走了──才這麼一想,便發現對方將手機丟向遠處。枇杷就這樣凝視沿著拋物線飛去的長方形精密機械,她甚至沒有餘力思考對方把手機丟遠的意圖,因為她光是用眼睛追逐掉落地點就已竭盡全力。
在這之後的幾分鐘內,枇杷犯了幾個錯誤。
手機這種東西其實怎樣都無所謂,她應該丟下一切,立刻去追那傢伙。
就算男性的腳程比較快,用腳踏車或許還追得上,但腳踏車的存在早被她拋到了九霄雲外。她腦中一片空白,竟然當場確認起皮夾裡的東西。照片果然被搶走了,她感到自己渾身顫抖,就連髮稍都抖動不已。然後枇杷撿起包包,驚慌失措地想往那傢伙跑走的方向追過去。不,還是要去報警?啊,手機……不對不對,怎麼辦才好──她猶豫不決地來回走動好幾趟之後,忽然想起倒在地上的腳踏車。於是枇杷扶起腳踏車,但因為用力過頭而使之倒向另一邊。她改變主意,先不管腳踏車,走向了手機掉落的樹叢。
枇杷在堆滿枯枝的杜鵑花叢深處根部找到了手機,她一把抓起,拍掉上頭的土後,才注意到自己的失態。周遭鴉雀無聲,連個腳步聲都聽不到。
這短短的幾分鐘,豈不是讓人溜得無影無蹤了嗎?
枇杷用微微顫抖的手抓住車把,匆忙騎向那傢伙可能離去的巷子。她使勁地踩著踏板,就算在這種緊急時刻她還是沒來由地想著「腳的動作真順暢啊?」這種事情。就像幫生鏽的零件上油一樣,有種關節轉動得比平常更為順暢的感覺。視野也更為清楚,寂靜無聲的深夜住宅區輪廓異常鮮明地躍入視野中。
結果她還是跟丟了那傢伙,變態的氣息消失無蹤。枇杷改變行進方向,死命騎向派出所。
她拉開玻璃門。
「我被搶了啊啊!」
她泫然欲泣地這麼控訴。
截至目前為止的遭遇已經夠慘了,之後卻更慘,實在慘不忍睹。
她被搶走的東西是一張相片。是張別人穿著套裝的求職用證件照。
那個東西對枇杷以外的人並無價值,所以不管她再怎麼說明,警察都無法明白被害的嚴重性,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是,就算如此──
「不是朋友在跟妳惡作劇嗎?就像是整人節目的升級版那樣。現在的瘋狂年輕人不是都會用『堆特』?投稿到電腦上嗎?」
警察叔叔這麼說道。對正在哭泣的被害者這樣說不會太過分了嗎?另外,雖然她不想提及,不過「堆特」是什麼鬼啊?她不想混淆話題所以才當作沒聽見,可是這也太扯了吧。枇杷氣不過,抓狂地說道:
「絕對不是!而且我沒有朋友!」
「欸,真可憐,為什麼啊?」
「這種事根本無所謂吧?」
枇杷生氣得太陽穴的血管不停抽動,只差沒噴出血來。她聲嘶力竭地喊著並傾身向前,幾乎從派出所的小椅子上跌落,她以雙手用力抓住辦公桌邊緣。儘管知道這種事不是大聲說就說得通,她還是無法控制自己不大吼大叫。
這可是一生一次的大事件,而且她許久沒跟家人以外的人講話了,現在又心服氣躁。不僅聲音格外尖銳,語尾還像個弱者似地發顫。都做到這個地步了,警察看起來依舊毫無緊張感。枇杷希望對方能以相同的幹勁質問自己,但他還是一副平靜溫和地說:「可是啊──」
「這件是很奇怪耶?那個陌生男子不搶皮夾也不搶手機,只抽走一張照片……喂,妳覺得這是為什麼啊?」
「不知道!所以我才要請你們調查啊!」
「……我再問一次,妳沒受傷吧?」
「沒有又怎樣?沒受傷就不行嗎?沒受傷不是比較好嗎?」
「話不是這麼……」
「腳踏車『喀鏘!』地倒下去!還被按到超痛的穴道,從眼睛裡發出奇怪的聲音!最不可思議的是現在肩膀、眼睛還有全身上下反而輕鬆得不得了,身體狀態絕佳,不過這只是碰巧啦!」
「哦──」
警察同意似地點了點頭,將一份文件挪到手邊。
「『反而狀態絕佳』……」
他特別強調那句話,以清晰的筆跡做起紀錄。從他的模樣可以明顯感受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企圖。開什麼玩笑。枇杷站起身,慌張地伸手張開五指。
「請、請等一下!我剛才說沒有受傷,身體狀態反而很好對吧?那個,其實呢……」
她擺出有如※金剛力士的阿形,又像是母親沉迷了一年以上的《所有運動都能透過DVD一看就懂!美木良介的深呼吸減肥法!一週見效呼吸課程》書籍封面那樣的姿勢,斬釘截鐵地開口。(譯註:佛教寺院常於山門兩側彩繪金剛力士,作為門神。右方的金剛力士為開口,代表阿形。)
「──是騙人的。」
「哦?騙人的?」
「其實……某個類似肋骨的地方?感覺好像處於一種斷了?的狀態?我有種……隱約的、預感……?也說不定?之類的。」
她揚起目光偷覷對方,以怯生生且惹人憐愛的姿勢用雙手按壓胸口部位。結果──
「那要叫救護車嗎?」
眼見警察伸手就要拿起電話,懂得察言觀色的枇杷立刻放棄作戰,死心地坐回椅子上。
「……沒事了。」
「我想也是。妳剛才說犯人穿著水手服?」
「對!沒錯!」
她重新振作起來,像搖滾樂團的樂手一樣瘋狂點頭。她轉念一想,與其控訴犯人施暴,強調變態的危險性還比較簡單明瞭。
「那件水手服布料很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很像Cosplay!超變態!那是赤裸裸的犯罪者啊!那傢伙看起來就很危險!」
「然後,對方還留著一頭長髮是嗎?」
「對!有如栗山千明的噁心版!有這麼長,這麼長喔!瀏海剪得齊齊的,像這樣『唰!』地直直留到腰部左右!我猜那八成是假髮!」
「然後,被他以指頭按壓後讓妳的身體變好了?」
「對!……個頭啦!」
她忍不住像舞獅般瘋狂扭動身體,搖頭否定。
「為什麼?為什麼說那是指壓?那是暴力行為吧?你快點派巡邏車出去,拉起警戒線抓人啦!對、對了,還得去現場才行!」
「會啦會啦,不過在那之前,來,這個文件。妳是錦戶枇杷小姐吧。枇杷……呃,二十三歲,沒錯吧?嗯,和父母住在一起?嗯,然後現在沒‧有‧工‧作。啊啊──待業中啊……」
「待業中又怎麼樣?對沒工作的人做什麼都沒關係嗎?因為沒有工作,所以在路上被人踩屁股、照片被搶就非得忍耐不可嗎?」
「加上沒有朋友……」
「那有什麼問題嗎?啊!你為什麼要補上一句『可憐人』?請你不要在筆錄加上個人主觀意見!」
「……」
「也請不要用那種看見可憐蟲的眼神看我!」
在那之後──
報案單正式提出,警察還送自己回家,並保證之後會加強附近巡邏,但──
枇杷在黑暗的廚房一角緊抱著膝蓋,思考報警之後徒勞無功的這三個月。
她沒接到犯人遭補的通知。不過她打從一開始就懷疑警察無意辦案,所以才會自己出門去找那傢伙。等找到人後,不論死活她都要把相片拿回來。
因為這樣,從那天開始枇杷就以那傢伙可能出現的地點為中心,騎著腳踏車於深夜的住宅區四處徘徊。
她的具體目標是要將對方輾過。
經過再三考慮,她認為即使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也能做到這點。反正也不想碰到他,乾脆心一橫全力輾過去。她要不停地來回輾壓,直到對方再也站不起來,然後再趁機把被搶走的東西拿回來。是個相當簡單明瞭的計畫。
可惜前景不太樂觀。她自行認定犯人是當地人,而且時常在附近街上走來走去,所以才會以事發現場為中心四處搜尋,但說不定這樣的假設是錯誤的。
如果那是一樁變態遠道而來享受女裝強盜樂趣的隨機犯案的話──可以想像那變態持著Suica輕巧地跳上電車,混入毫不在乎他人的乘客中,於月台上露出噁心微笑的身影……「今天要到哪條街上去欺負沒工作的人呢?」……這幅畫面清晰地浮現,令枇杷不禁打了個冷顫。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枇杷這幾個月就等於是白白浪費力氣和時間在錯誤的目標上了。
(距離十七號還有……咦!騙人,只剩下一個多禮拜了啦!)
──怎麼辦?
黑暗中,枇杷以腦海裡的日曆拚命重新數著日子。重新數一數或許就會增加幾天──這樣微小的期待在數到第三次時輕易破滅了。怎麼可能增加啊。
埋在兩膝間的腦袋垂得更低了。
(……話說回來,其實怎樣都好啦……)
就算放聲大叫,也不會有人出現。
枇杷維持著目不轉睛地凝視自己下半身的奇異姿勢,在一片淒黑中緩緩眨眼。現實中果然不存在正義英雄,這個世上根本沒有會前來拯救尖叫女性的人。
說得也是。在這種三更半夜裡聽到外面傳來尖叫聲,不管是誰都會當作沒聽見,然後迅速檢查家裡的門窗有沒有關好吧。大家都是這樣,自己也會這麼做。事實上枇杷過去一直都是這麼做的,也因為這樣她才會失去。
所以事到如今,不管她再怎麼大聲求救,也不會有人伸出援手,而她沒有資格對自己所處的現實怨天尤人。
就在這個時候──
「……」
天花板傳來了輕微的聲響,是從二樓發出的。枇杷抬起頭,像小動物一樣停止動作,側耳傾聽。還聽得見,並不是她的錯覺。
父母的寢室在一樓,所以製造聲響的不是哥哥,就是小天使櫻桃起來上廁所吧。
不管是誰,她都不想被發現自己都這幾點了還在外面遊蕩的事。枇杷拿起夾在膝蓋間的啤酒罐,悄然無聲地站起身,再次屏住氣息,小心翼翼地往自己位於一樓西側盡頭的房間前進。
旋轉吧──某個人曾這麼說過。
世間萬物都在無止境地循環,旋轉是天經地義的事,沒有一樣東西可以動也不動地存在於這個世界上。所以大家都轉呀轉、轉呀轉、轉呀轉地……枇杷覺得彷彿聽到有人在耳邊這麼溫柔低語。
(轉呀轉……說到旋轉……)
──啊!※拿破崙二人組。(譯註:由Bona植木與Parte小石所組成的魔術師組合,藝名取自拿破崙的姓Bonaparte。)
※Parte小石的頭部。(編註:拿破崙二人組的拿手魔術,將特殊道具裝於Parte小石的頭上,讓觀眾產生頭部能夠轉動三六○度的錯覺。)
(還有那個也是……)
放浪兄弟的Choo Choo TRAIN開頭舞蹈;「讀取中」的gif;黑天鵝奧吉莉雅的華麗鞭轉;※利普尼茨卡婭的貝爾曼旋轉;還有,過去的我們。(譯註:俄羅斯的年輕花式滑冰女選手。)
真的耶。
大家真的都在不停旋轉。
枇杷忘我地繼續往前奔跑,腦中接連不斷冒出旋轉的物體。
(迴轉壽司、龍捲風,以及陀螺、攪拌器,還有電動牙刷!)
想法接連浮現,一股股強烈的衝擊貫穿枇杷的心臟。真的,這個世界的一切全部都在轉動。既然如此,自己應該也是一樣。旋轉吧。旋轉著。
跑動著的雙腳再次提升速度,卯足全力衝過夏天。下巴跟著晃動不已,若不咬緊牙關,感覺好像會脫落。她已經停不下來了。這時,及膝的緊身裙襬發出「劈啪」的撕裂聲。真的假的啊?她遲疑了一瞬間,但沒空管這個了。於是枇杷假裝沒聽到,繼續往前奔去。
從天而降的毒辣陽光炙烤著頭頂,蟬鳴聲傾瀉而下,汗水如眼淚般沿著臉頰滑落。枇杷依舊埋頭猛衝,好似要一頭栽進未來。
兩旁裸露的岩壁逐漸逼近,道路愈來愈狹窄,前方是一條幽暗的隧道。只要鑽進那穿透碧綠山表的深黑,再自明亮的出口離開,便來到車站前的市區。可是,啊啊……
(沙拉脫水器、大迴旋、黑膠唱片、CD、DVD!)
──這個世界上充斥著各種轉來轉去的東西啊!
古今中外,現在、過去、未來,從人類誕生以來至此時此刻,所有瞬間都在不停轉動的事物啊!
從旋轉中誕生的這股力量!
(請務必也賜予我團團轉的力量,讓我踏上最終戰場!我無論如何都想贏!就算被打飛也無怨無悔!)
右眼從剛才就痛得厲害,枇杷一邊跑一邊用右手撫摸痛處。這股劇痛絕對是某種信號──告訴自己經過一年的等待,對決的時刻終於到來。
必須打倒的敵人,不久就會現身吧。他一定就在那個隧道裡,隱身於那個就連夏天都陰森潮濕的黑暗中,靜待自己的到來。
枇杷似乎可以想像對敵人的樣貌。
他應該穿著漆黑的水手服。
除了領口上點綴著的兩條白線外,他的打扮可說是全身黑,就連絲質領帶都是黑的。隨風飄揚的柔順長髮同樣烏黑,腳上穿著光可鑑人的黑皮鞋及黑色高筒襪。
平整的厚瀏海下有張下巴纖細、令人驚艷的美麗臉龐,看上去幾乎就像個雪白的倒三角形。
敵人大概正看著闖入隧道直奔而來的枇杷,一聲不響地離開了原本倚靠的牆壁。然後他會踏著悠閒的腳步,像要攔住去路似地擋在枇杷面前。那上翹的眼角鋒利如刃,危險得讓人笑不出來。
將閃耀著盛夏陽光的小小出口擋在身後,敵人渾身散發烈火般的黑色鬥氣,用清澈甜美的嗓音說出那句固定台詞。
「讓我來──」
對方以右手的球拍指向枇杷。
「制裁──」
接著輕輕扭腰,從下巴下方亮出左手握著的聖球。
「妳的罪行!」
總有一天,枇杷不得不與那傢伙正面對決。不和他戰鬥並打倒他,枇杷永遠無法向前邁進,無法繼續活下去。
而那個敵人名為──罪。
然而──就在枇杷為了取其性命而拚命奔走,準備衝進隧道時,她忽然想到一件事。
(我們為什麼會變成這樣?)
她用腳蹬向地面,腦中沒來由地浮現朋友那天平靜的笑容。那顆聖球最終仍會無情地旋轉著襲來吧。
轉呀轉、轉呀轉……電風扇、洗衣機、呼拉圈、飛盤,還有地球和銀河,以及原子。全部,一切,大家,還有自己,都轉個不停。
旋轉正是世界的真理,是自然法則。只要存在於這世上,只要還活著,就不能夠停下來。
因旋轉而產生的離心力,將原本沉澱在意識最深處的回憶,從漩渦中心吸起並擴散開來,滿溢於枇杷的內部。不堪回首的往事有如暴風雨般四處灑落。
時間轉呀轉地回溯到過去,所有場景開始鮮明地浮現。
事情的開端始於那個夏天。
(當時我拚了命地想讓運轉停止。)
那個夏天的那個夜晚,枇杷把腳踏車放回家裡車庫的那個深夜,凌晨三點鐘。
立起腳架、上好鎖後,不知為何輪輻仍不厭其煩地發出聲響持續轉動著。那雜音讓枇杷打從心底感到厭煩,於是她踹了車輪一腳,想制止迴轉。結果大拇指指甲不敵橡膠的摩擦而造成撕裂傷,痛楚與懊悔讓枇杷忍不住咂了下舌。
──嘖!
(指甲你到底有多脆弱啊!)
枇杷在心裡暗自咒罵,躡手躡腳地爬上玄關前的台階。
她進入門廊屋簷下,悄悄打開門,從身體能通過的最低限度寬度迅速溜進家門。然後再以同樣謹慎的動作關上門,輕輕上鎖。
那一聲不響、不疾不徐的身手好似「女太極拳好手」或是「女竊賊」,也可能是「會使太極拳的女竊賊」,但以上皆非正確答案,因為這裡是她家。
凌晨三點,錦戶枇杷才返回家裡。
她輕聲脫掉愛用的褐色橡膠廁所拖鞋,踏上玄關。此時還不能掉以輕心,她得在不被熟睡的家人發現自己半夜偷溜出去的情況下,回到自己房間才行。
今晚的東京是個熱帶夜,悶熱到小籠包都能蒸熟的程度。在如此悶熱不適的三更半夜裡,枇杷獨自騎著腳踏車在街上繞來繞去,現在剛回到家。她自己也覺得這樣的行為很不正常,因此放輕手腳,不敢發出一點聲音,靜靜地穿過家裡的走廊。
她熱得要命,掛在脖子上用來擦汗的毛巾早已濕透,T恤也濕答答的,整個人上氣不接下氣、腳步蹣跚。
(慘了,頭昏眼花……)
不快點補充水分的話,說不定會筋疲力竭地直接倒下。
原本打算回房間的她改變了路線,在一片漆黑中鬼鬼祟祟地前進,從客廳往更裡頭的廚房走去。
打開冰箱候,她發現裡面有啤酒,雖然不是特別想攝取酒精,不過因為近在眼前而且冰得恰到好處,所以便順手拿起。
枇杷就這樣站在黑漆漆的廚房一隅,啜飲啤酒。冰涼的感覺幾乎沁入牙根,嘶嘶作響的碳酸刺激著喉嚨。看來枇杷似乎比自己想像中還要口乾舌燥,她忘我地一口接著一口,咕嘟咕嘟地將啤酒灌下肚。
她一口氣灌下半瓶左右的份量後,就這麼靠在牆上,抵著牆一屁股滑坐在廚房地板上。她差點就要打出嗝來,連忙用拳頭摀住嘴,熟練地讓啤酒的氣味無聲地從鼻子送出。
在這麼熱的天氣,全身汗水淋漓又口乾舌燥的狀態下,痛快地猛灌一瓶沁涼的啤酒。
即使如此,枇杷還是一點都高興不起來。她現在的心情完全無法發出「好喝!」「哇~讚啦!」「噗哈~!」諸如此類的讚嘆詞,一點也不覺得幸福。
她板著臉又喝了一口酒,然後將罐底的圓形凹陷處抵在膝頭。
問題在於今晚仍舊一無所獲。即使有啤酒也無法排解她心頭的鬱悶。枇杷在黑暗中縮起身子,腦袋垂靠於套著運動褲的兩膝間。
(又沒抓到……)
好似有一團比黑暗更加深沉的昏晦之物從頭上滴落般,苦澀的心情逐漸填滿胸口,讓枇杷更加鬱鬱寡歡。
事情是從四月底開始的,至今已過了三個月以上。我整整三個月都在做這種事嗎……?真的假的?
竟然如此虛度光陰,連枇杷自己都有些訝異。這麼做真的好嗎?只是不斷空轉、空轉再空轉,回過神來已經八月了!別說逮到人了,連個影子都沒看見,根本毫無成果可言。做這種事果然沒用嗎?太過有勇無謀,太沒計畫性了嗎?枇杷對此絕不放棄,但是又想不到其他方法。
明明想在八月十七號以前將這件事解決掉的。
她一直在找某個傢伙,一心想在那天之前把人找出來、逮住他,還要狠狠地教訓他一頓。
枇杷無論如何都想把被那傢伙搶走的東西拿回來。
和那傢伙相遇,是在春天快結束的時候。
櫻花早已散盡,種植於綿長的人行道兩側的樹木枝頭開始冒出鮮嫩綠葉。
時間大概是剛過深夜一點半,枇杷離開附近的家庭餐廳,一個人踩著腳踏車準備回家。
人煙稀少的住宅區裡,連一點微風吹拂的聲音都沒有,四周鴉雀無聲。肌膚接觸到的空氣溫熱得令人不舒服。一台紅綠燈上掛著「故障」的牌子,綠、黃、紅色的燈同時一閃一閃地發出刺眼光芒。枇杷抬頭仰望,內心只覺得這景象很少見,但現在回想起來,那搞不好其實是對即將來襲的事態的警告。可惜她當時沒有察覺,也完全沒有提防。
這裡是東京板橋區。
這塊幽靜到幾近無趣的住宅區,正是錦戶枇杷的家鄉。
她從出生就一直住在這裡。這一帶雖然也屬於東京都,卻有許多佔地廣大的獨門獨戶房屋林立。這裡對枇杷而言就像「後院」般,她熟知每一條小巷子。除了最近忽然開始興建的大樓區一帶,由於變化太大還來不及更新資訊外,這個不算大的市區的地理位置幾乎都儲存於枇杷的腦中。她於此土生土長,而且這裡又是她的後院──即使閉上眼睛她也能順利走回家。
這附近從以前起就是公認治安良好的區域,就算年輕女性半夜獨自在外行走,而且行動符合正常範圍(比如沒有喝得爛醉如泥,也沒有因為低頭玩手機或聽音樂而渾然忘我),基本上不會出什麼事──理應是這樣才對。至少在那個夜晚之前的二十三年來,身為當地居民的枇杷是這麼認為的。
那天枇杷並不急著趕路,只是悠哉地踩著腳踏車踏板。
忽然間,她的視線被閃著白光、佇立於人行道一角的自動販賣機吸引過去,嚇了一跳。
「哇啊!」
枇杷不小心驚叫出聲。因為貼在販賣機上的偶像海報幾乎跟真人一樣大,害她以為有個人站在那裡。
當然,枇杷馬上就發現是自己看錯了。她嘟噥了聲「搞什麼啊」便將視線從笑容滿面的偶像身上移開。竟然嚇我,害人家不小心叫出聲來了啦,真丟臉。好險沒人看見……
就在她微微鬆了口氣的瞬間──
有個人冷不防地伸出手,探向枇杷放在腳踏車置物籃裡的布製托特包。
枇杷沒有像剛才一樣發出單純感到訝異的驚呼聲,畢竟此刻的驚訝程度非同小可。
聽說人類這種生物一旦過度驚嚇,怦怦直跳的心臟就會通過脖子直竄腦門,撞擊頭蓋骨內部並在那裡劇烈跳動。枇杷還是第一次體會到這種事。不,可是,心臟?跳到頭裡?怎麼可能啊。當下,她連如此冷靜思考的能力都被突發事件給奪走,腦袋完全無法運轉。視野急遽縮小,控制臟器的管線像是斷掉般讓肺部停在膨脹的極限狀態,嘴巴也毫無意義地張著。她就是這麼震驚,只顧著震驚,震驚到忘記抓穩手把,連車帶人橫倒在地。
枇杷維持著跨在坐墊上的姿勢,雖然勉強用一隻腳踩地,但依舊失去平衡跌了一跤。托特包也從腳踏車籃裡飛了出去。
剛才伸手要拿枇杷包包的,是個留著一頭陰森長髮、穿得一身黑的女人,看上去就很危險。
凌亂的頭髮、質地單薄的黑衣、遮掩起來的臉孔、隨著喘息上下起伏的肩膀、格外高大的身軀──在在散發出令人不舒服的氣息。「不想與對方扯上關係」的指數瞬間破表。如果真的有測量這種情感數值的器具,指針應該會像下面的毛髮一樣捲曲起來才對。那女人一邊揮灑著極度「令人不想扯上關係」的氛圍,一邊用噁心的前屈小跑動作朝枇杷的包包直奔而來,活像隻習得了蟑螂高速移動技巧的蛞蝓。
飛揚的百褶裙底下露出了異常蒼白、光滑的小腿,讓人下意識冒出「好噁心!」的感想。雖然現在沒有閒工夫管這些,枇杷還是忍不住這麼想──噁心得讓人渾身打哆嗦,這感覺幾乎打破了自己心目中史上最噁心的紀錄,甚至噁心到令人心中升起一把無名火。這傢伙是怎樣?到底在搞什麼?愈看愈噁心耶!為什麼會噁到讓人作嘔?她還好吧?枇杷不由得像這樣替她擔心起來。
接著,枇杷看見那個噁心的傢伙用比一般女性還要大的手,一把抓住自己的包包。
那一剎那,她總算──
「……噫呀~啊啊啊啊~~~!」
發出有如吹壞的笛子般的尖叫。
包包雖然是雜誌附錄送的(而且還是去年的),不過裡面放了皮夾、智慧型手機和家裡鑰匙。枇杷不顧一切,擒抱似地縱身撲向犯人抓起的包包。
小偷!強盜!扒手!滿腔怒火和恐懼幾乎要炸裂開來,她早已失去了冷靜,只是卯足全力想搶回包包。無奈犯人也不肯放棄,兩人你拉我扯後,開始打轉,就這樣在自動販賣機的光源照映下旋轉著糾纏在一起。
兩人在氣息交織的極近距離無意間對上視線的瞬間,枇杷再次發出慘叫。
「啊呀啊啊啊~~~!」
這傢伙到底是怎樣──令人全身起雞皮疙瘩!毛骨悚然!此刻毛孔同心協力張開的程度教人嘆為觀止。因為、因為──
(這傢伙根本是個男的嘛!)
早知道對方是男性,自己就不會這麼頑強抵抗了。因為比力氣她贏不過對方,肯定會輸的。枇杷感到全身血液突然倒流。難怪我會覺得那麼噁心,因為這傢伙是個變態啊。
他的長髮異常蓬亂;仔細一看,身上穿的還是水手服!不管是臉的輪廓,還是搶包包的手,以及那大聲喘氣的聲音,都顯示他徹頭徹尾是個男的,是個不折不扣的變態。枇杷心想著剛才應該要逃跑才對,她不曾有過如此具體且強烈的後悔。她無法壓抑這股情緒,覺得好想哭。我可能會被強暴?不,更糟的情況還可能被殺掉。趕快逃吧,得逃走才行!但是被這種人搶走包含所有個人資料的皮夾、手機和鑰匙真的好嗎?這樣也不太好吧!
該怎麼辦才好?我要放開手?還是拚死不放?就在幾近狂亂的思緒使她出現猶豫的那一秒鐘,枇杷想起了自己不能放手的唯一理由。
皮夾裡有那個。
『我希望枇杷帶著這個。』
──對啊。
不行,我不可以放棄,千萬不能放開手,打死都不放開。
「……要、要錢的話──」
她以尖銳的哭聲說著。
「全、全部……都給你……!想要手機的話也可以拿去!」
枇杷拚命提出請求。她是真心這麼想。如果這樣能解決事情就該偷笑了。
「如果你要、要我不報警,我就不報警……!所以請還給我!把手放開!」
可惜對方似乎不領情。他以單手抓著包包,同時舉起另一隻手。枇杷半是放棄地看著他的動作,難看但奮力地縮起身子,以求就算被揍也能盡量減輕傷害。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她沒有被揍飛,取而代之的是手肘附近被人抓住。男人的拇指就那樣按上枇杷的肘骨,輕柔的觸感甚至讓人感覺到一股不符合當下情況的溫柔。枇杷才察覺到不對勁,對方的拇指便用力一壓,一陣電擊般的尖銳疼痛從肩膀傳至胸骨正中央,眼前變得一片空白。枇杷不曉得對方做了什麼,但可以確定自己遭遇了令人恐懼的疼痛。
「噫──噫噫噫噫……!」
膝蓋無力地彎曲,枇杷即使整個人失去重心癱坐在地,依然沒有放開包包。接著,對方將手搭上她的肩膀──他要勒我的脖子嗎?死定了。枇杷害怕得死命甩頭,這次拇指深深地嵌入鎖骨上方的空隙,傳來了「啪唧、劈哩」宛如氣泡之類的物體爆開的清脆聲,但聲音來源不知為何並非鎖骨,而是來自眼睛深處。感覺就像從兩耳後方沿著頭皮被套上一條令人痛不欲生的帶子般,但對方明明沒有碰到那裡。
「噫──噫噫嗚嗚嗚啊啊……!」
枇杷再也撐不住,趴倒在路面上。屁股左邊大概被對方的膝蓋按住了,恐怕是拳骨的部位正緊貼著自己右腰上方。對方沒有再施加打擊而是觸摸,然後直接將全身的重量壓了上來。那一瞬間,枇杷在眼底看見了竄起的火柱,還浮現出「天誅!」這個詞彙,不過對方什麼都沒說就是了。
她已經連呻吟的力氣都沒有了。如奔流般從屁股往下竄的疼痛寒冷刺骨,由腰部往上攀升的疼痛則灼熱難耐,令人聯想到萬馬奔騰的畫面。氣勢磅礡的馬蹄從頭頂往腳尖踐踏而過,奪走了枇杷靈魂裡能夠繼續「努力」的東西。
她覺得渾身無力。那傢伙用膝蓋壓著枇杷的屁股,在她頭頂翻著包包。枇杷淚眼汪汪地拚命扭動身體,想要看清那傢伙的動作。對方打開了枇杷的皮夾,但卻看也不看放在裡面的幾張千元鈔票,也無視提款卡的存在。
「……只、只有那個……」
她沒辦法好好說話。
那傢伙從皮夾裡拿出的是收在夾層裡的一張照片。只有那個不行,只有那個東西不能再失去了,住手。是因為看穿枇杷的心思所以才要搶走嗎?對於枇杷之外的人而言,那東西明明毫無價值,但他偏偏要搶那個,只鎖定那個。
住手。
「……唔……!」
枇杷不顧幾乎要脫臼的肩膀,奮力伸出手,在空中徒然劃出一道有如漫畫中描繪的美麗弧線。乾脆俐落得教人絕望。照片被搶走了。
重量自枇杷的屁股上消失,皮夾和包包被扔在一旁;手機被拿走了──才這麼一想,便發現對方將手機丟向遠處。枇杷就這樣凝視沿著拋物線飛去的長方形精密機械,她甚至沒有餘力思考對方把手機丟遠的意圖,因為她光是用眼睛追逐掉落地點就已竭盡全力。
在這之後的幾分鐘內,枇杷犯了幾個錯誤。
手機這種東西其實怎樣都無所謂,她應該丟下一切,立刻去追那傢伙。
就算男性的腳程比較快,用腳踏車或許還追得上,但腳踏車的存在早被她拋到了九霄雲外。她腦中一片空白,竟然當場確認起皮夾裡的東西。照片果然被搶走了,她感到自己渾身顫抖,就連髮稍都抖動不已。然後枇杷撿起包包,驚慌失措地想往那傢伙跑走的方向追過去。不,還是要去報警?啊,手機……不對不對,怎麼辦才好──她猶豫不決地來回走動好幾趟之後,忽然想起倒在地上的腳踏車。於是枇杷扶起腳踏車,但因為用力過頭而使之倒向另一邊。她改變主意,先不管腳踏車,走向了手機掉落的樹叢。
枇杷在堆滿枯枝的杜鵑花叢深處根部找到了手機,她一把抓起,拍掉上頭的土後,才注意到自己的失態。周遭鴉雀無聲,連個腳步聲都聽不到。
這短短的幾分鐘,豈不是讓人溜得無影無蹤了嗎?
枇杷用微微顫抖的手抓住車把,匆忙騎向那傢伙可能離去的巷子。她使勁地踩著踏板,就算在這種緊急時刻她還是沒來由地想著「腳的動作真順暢啊?」這種事情。就像幫生鏽的零件上油一樣,有種關節轉動得比平常更為順暢的感覺。視野也更為清楚,寂靜無聲的深夜住宅區輪廓異常鮮明地躍入視野中。
結果她還是跟丟了那傢伙,變態的氣息消失無蹤。枇杷改變行進方向,死命騎向派出所。
她拉開玻璃門。
「我被搶了啊啊!」
她泫然欲泣地這麼控訴。
截至目前為止的遭遇已經夠慘了,之後卻更慘,實在慘不忍睹。
她被搶走的東西是一張相片。是張別人穿著套裝的求職用證件照。
那個東西對枇杷以外的人並無價值,所以不管她再怎麼說明,警察都無法明白被害的嚴重性,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但是,就算如此──
「不是朋友在跟妳惡作劇嗎?就像是整人節目的升級版那樣。現在的瘋狂年輕人不是都會用『堆特』?投稿到電腦上嗎?」
警察叔叔這麼說道。對正在哭泣的被害者這樣說不會太過分了嗎?另外,雖然她不想提及,不過「堆特」是什麼鬼啊?她不想混淆話題所以才當作沒聽見,可是這也太扯了吧。枇杷氣不過,抓狂地說道:
「絕對不是!而且我沒有朋友!」
「欸,真可憐,為什麼啊?」
「這種事根本無所謂吧?」
枇杷生氣得太陽穴的血管不停抽動,只差沒噴出血來。她聲嘶力竭地喊著並傾身向前,幾乎從派出所的小椅子上跌落,她以雙手用力抓住辦公桌邊緣。儘管知道這種事不是大聲說就說得通,她還是無法控制自己不大吼大叫。
這可是一生一次的大事件,而且她許久沒跟家人以外的人講話了,現在又心服氣躁。不僅聲音格外尖銳,語尾還像個弱者似地發顫。都做到這個地步了,警察看起來依舊毫無緊張感。枇杷希望對方能以相同的幹勁質問自己,但他還是一副平靜溫和地說:「可是啊──」
「這件是很奇怪耶?那個陌生男子不搶皮夾也不搶手機,只抽走一張照片……喂,妳覺得這是為什麼啊?」
「不知道!所以我才要請你們調查啊!」
「……我再問一次,妳沒受傷吧?」
「沒有又怎樣?沒受傷就不行嗎?沒受傷不是比較好嗎?」
「話不是這麼……」
「腳踏車『喀鏘!』地倒下去!還被按到超痛的穴道,從眼睛裡發出奇怪的聲音!最不可思議的是現在肩膀、眼睛還有全身上下反而輕鬆得不得了,身體狀態絕佳,不過這只是碰巧啦!」
「哦──」
警察同意似地點了點頭,將一份文件挪到手邊。
「『反而狀態絕佳』……」
他特別強調那句話,以清晰的筆跡做起紀錄。從他的模樣可以明顯感受到「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企圖。開什麼玩笑。枇杷站起身,慌張地伸手張開五指。
「請、請等一下!我剛才說沒有受傷,身體狀態反而很好對吧?那個,其實呢……」
她擺出有如※金剛力士的阿形,又像是母親沉迷了一年以上的《所有運動都能透過DVD一看就懂!美木良介的深呼吸減肥法!一週見效呼吸課程》書籍封面那樣的姿勢,斬釘截鐵地開口。(譯註:佛教寺院常於山門兩側彩繪金剛力士,作為門神。右方的金剛力士為開口,代表阿形。)
「──是騙人的。」
「哦?騙人的?」
「其實……某個類似肋骨的地方?感覺好像處於一種斷了?的狀態?我有種……隱約的、預感……?也說不定?之類的。」
她揚起目光偷覷對方,以怯生生且惹人憐愛的姿勢用雙手按壓胸口部位。結果──
「那要叫救護車嗎?」
眼見警察伸手就要拿起電話,懂得察言觀色的枇杷立刻放棄作戰,死心地坐回椅子上。
「……沒事了。」
「我想也是。妳剛才說犯人穿著水手服?」
「對!沒錯!」
她重新振作起來,像搖滾樂團的樂手一樣瘋狂點頭。她轉念一想,與其控訴犯人施暴,強調變態的危險性還比較簡單明瞭。
「那件水手服布料很薄,一看就知道是假的,很像Cosplay!超變態!那是赤裸裸的犯罪者啊!那傢伙看起來就很危險!」
「然後,對方還留著一頭長髮是嗎?」
「對!有如栗山千明的噁心版!有這麼長,這麼長喔!瀏海剪得齊齊的,像這樣『唰!』地直直留到腰部左右!我猜那八成是假髮!」
「然後,被他以指頭按壓後讓妳的身體變好了?」
「對!……個頭啦!」
她忍不住像舞獅般瘋狂扭動身體,搖頭否定。
「為什麼?為什麼說那是指壓?那是暴力行為吧?你快點派巡邏車出去,拉起警戒線抓人啦!對、對了,還得去現場才行!」
「會啦會啦,不過在那之前,來,這個文件。妳是錦戶枇杷小姐吧。枇杷……呃,二十三歲,沒錯吧?嗯,和父母住在一起?嗯,然後現在沒‧有‧工‧作。啊啊──待業中啊……」
「待業中又怎麼樣?對沒工作的人做什麼都沒關係嗎?因為沒有工作,所以在路上被人踩屁股、照片被搶就非得忍耐不可嗎?」
「加上沒有朋友……」
「那有什麼問題嗎?啊!你為什麼要補上一句『可憐人』?請你不要在筆錄加上個人主觀意見!」
「……」
「也請不要用那種看見可憐蟲的眼神看我!」
在那之後──
報案單正式提出,警察還送自己回家,並保證之後會加強附近巡邏,但──
枇杷在黑暗的廚房一角緊抱著膝蓋,思考報警之後徒勞無功的這三個月。
她沒接到犯人遭補的通知。不過她打從一開始就懷疑警察無意辦案,所以才會自己出門去找那傢伙。等找到人後,不論死活她都要把相片拿回來。
因為這樣,從那天開始枇杷就以那傢伙可能出現的地點為中心,騎著腳踏車於深夜的住宅區四處徘徊。
她的具體目標是要將對方輾過。
經過再三考慮,她認為即使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自己也能做到這點。反正也不想碰到他,乾脆心一橫全力輾過去。她要不停地來回輾壓,直到對方再也站不起來,然後再趁機把被搶走的東西拿回來。是個相當簡單明瞭的計畫。
可惜前景不太樂觀。她自行認定犯人是當地人,而且時常在附近街上走來走去,所以才會以事發現場為中心四處搜尋,但說不定這樣的假設是錯誤的。
如果那是一樁變態遠道而來享受女裝強盜樂趣的隨機犯案的話──可以想像那變態持著Suica輕巧地跳上電車,混入毫不在乎他人的乘客中,於月台上露出噁心微笑的身影……「今天要到哪條街上去欺負沒工作的人呢?」……這幅畫面清晰地浮現,令枇杷不禁打了個冷顫。如果事情真是如此,那枇杷這幾個月就等於是白白浪費力氣和時間在錯誤的目標上了。
(距離十七號還有……咦!騙人,只剩下一個多禮拜了啦!)
──怎麼辦?
黑暗中,枇杷以腦海裡的日曆拚命重新數著日子。重新數一數或許就會增加幾天──這樣微小的期待在數到第三次時輕易破滅了。怎麼可能增加啊。
埋在兩膝間的腦袋垂得更低了。
(……話說回來,其實怎樣都好啦……)
就算放聲大叫,也不會有人出現。
枇杷維持著目不轉睛地凝視自己下半身的奇異姿勢,在一片淒黑中緩緩眨眼。現實中果然不存在正義英雄,這個世上根本沒有會前來拯救尖叫女性的人。
說得也是。在這種三更半夜裡聽到外面傳來尖叫聲,不管是誰都會當作沒聽見,然後迅速檢查家裡的門窗有沒有關好吧。大家都是這樣,自己也會這麼做。事實上枇杷過去一直都是這麼做的,也因為這樣她才會失去。
所以事到如今,不管她再怎麼大聲求救,也不會有人伸出援手,而她沒有資格對自己所處的現實怨天尤人。
就在這個時候──
「……」
天花板傳來了輕微的聲響,是從二樓發出的。枇杷抬起頭,像小動物一樣停止動作,側耳傾聽。還聽得見,並不是她的錯覺。
父母的寢室在一樓,所以製造聲響的不是哥哥,就是小天使櫻桃起來上廁所吧。
不管是誰,她都不想被發現自己都這幾點了還在外面遊蕩的事。枇杷拿起夾在膝蓋間的啤酒罐,悄然無聲地站起身,再次屏住氣息,小心翼翼地往自己位於一樓西側盡頭的房間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