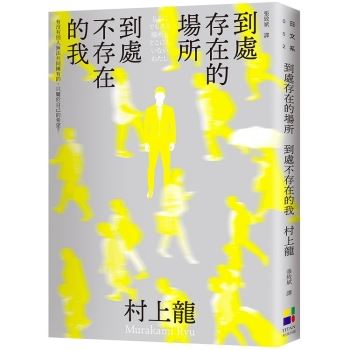居酒屋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八點多。我在居酒屋裡。坐在旁邊的是我的男朋友。男朋友的對面是他公司的人,我的對面則是我的公司同事。因為他公司的人想交女朋友,而我公司的同事則在找男朋友,於是我和我的他決定為兩人穿針引線。我的名字是水谷祐子,我的他名叫堺俊夫。我都喊他阿俊。
阿俊剛才介紹過他們公司那個人的名字。好像姓坂上,可是我沒聽清楚。因為後來一直沒有人喊那個人的名字,沒有辦法再次確認。或許是姓中上也不一定。阿俊與那個姓坂上還是中上的人的交情似乎並不是多麼好。我的公司同事名叫直美,二十五歲,比我小兩歲。
我們喝著生啤酒,吃著墨魚生魚片、炸雞、毛豆還有涼拌豆腐。姓坂上還是中上的那人,不知道為什麼帶了一個說是高中同學的女人同來。那女人穿著織有金銀絲線的粉紅色迷你洋裝,一副風塵味的打扮,而且還濃妝豔抹,那個女人的名字是吉本小夜子。直美雖然是來見未來男友人選的,卻因為害羞而帶了個游泳教室的男性友人一起來。他是小強,我之前並不認識。
我還是第一次光顧這家居酒屋。地點正好就位於JR東中野與中野的中間一帶。雖然這家店好像是阿俊選的,可是我並不清楚他以前是否來過這裡。櫃台裡有個看起來像是老闆的人,身穿和服頭上纏著布巾的打工女孩過來點菜。我們的隔壁是一桌上班族團體客。另外一邊的那一桌有七個人,正在聊著電影還是戲劇的話題,眾人都已經有了幾分醉意,講話的嗓門很大。他們之中有光頭族,也有長髮紮在腦後的人,七人中有兩名女性,兩人都穿著類似工作裝的黑色衣服。
牆邊的電視一直開著,可是沒有人在看。正在轉播職棒,在場上投球的是巨人隊的桑田,站在打擊區的則是橫濱的鈴木。恐怕只有坐在櫃台前一個人喝著酒的那些人才會看電視吧。櫃台在我的背後。有些什麼樣的人坐在櫃台,我並不知道。
我在品川一家配送公司負責內勤的工作,工作的時間朝九晚五。來這家公司上班之前,曾在西麻布的一家酒吧當服務生。阿俊在家具連鎖店工作。我們大約三個月前在淘兒唱片行挑選CD的時候認識的。雖然已經想不起來剛認識的時候聊了些什麼,可是並沒有聊到作畫的事情,到如今依然沒有談起過。就連直美,我也沒跟她提起過自己平常會作畫。直美好像是高中畢業之後就從山陰地方來到東京進入服裝設計的專門學校就讀,但是沒多久就休學了。聽說被男人騙過,但是詳細情形我並不清楚。
直美加入了網路的約會團體,曾經多次參加網友會以及紅娘派對,可是依然不停抱怨找不到好男人,所以我今天晚上才會安排介紹阿俊公司的人給直美認識。但不知道為什麼,她也帶了個男性友人一同前來。小強剛從大學畢業,好像是丸之內一家公司的職員。聽說這是兩人第一次在游泳教室之外的地方見面。
「所以人家才會說你沒有面對現實嘛!」
我聽到了這句話,可是不知道是從哪一桌傳來的聲音。這家店很吵,充滿了各種聲音。電視螢幕裡,桑田正準備投球,但不知為什麼還播放著音樂。好像是有線頻道,可是只知道正播放著音樂,不知道那是什麼曲子。四個頭上纏著布巾的打工女孩將食物與飲料送過來。剛才阿俊瞄了其中一個女孩一眼,大概是他中意的類型吧,我心裡想。是個大胸脯的女孩。與我交往之前,阿俊曾與一個名叫里美的大胸脯女孩交往,即使在與我交往之後,兩人依然藕斷絲連。
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如果行動電話響起,而阿俊回答說「我等一下再回撥」的時候,對方必定是里美。我並沒有和阿俊同居。因為里美的事情,阿俊似乎對我感到有些內疚。直美穿著涼鞋的腳邊出現了某種小蟲。直美的腳趾肉肉的。剛才,姓坂上還是中上的那人說了些什麼,可是誰也沒有反應。我正在吃炸雞,雖然蒜味滿重的,可是今天晚上就是想吃點富含蛋白質的食物。
我還在陪酒的年代有個朋友,一個花名叫做小楓的女孩,私底下會玩SM,好像是當女王。她確實個子很高,但是長相並不是多麼美。聽她說,常去看診的牙醫是個被虐待狂,所以自己才被帶進那個世界。他們會用牙科的治療器具來助興,可是我沒有問到底是什麼樣的性遊戲。
阿俊對我心懷歉疚,所以我一提直美的事情,他就表示要幫忙介紹公司的男同事。跟直美提起這件事之後她也表示非介紹不可,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安排,可是我其實有些話想單獨跟阿俊講。因為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想在這種居酒屋談。阿俊似乎有意跟我結婚。「雖然我還有其他女人,可是要結婚的話,還是要娶祐子。」阿俊說。這番話,是阿俊三個禮拜前說的。「那個女人只是胸部大而已,其他沒有任何優點,個性又不開朗。」阿俊這麼形容里美。里美好像是在特種營業工作。
「一想到她用含過其他男人那話兒的同一張嘴含著我的那話兒就覺得興奮不已,不過我可不希望討個那樣的老婆喔。」
「所以人家才會說你沒有面對現實嘛。所謂面對現實,就是要排除期待或是抱持希望的觀測這些先入之見,實事求是去看清楚現實,雖然並不是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可是卻沒有人發覺這一點。你那種作品論根本就沒有人要聽啦,而且,你首先就應該正視自己不被任何人期待的這個事實吧。不是嗎?」
說這番話的到底是什麼人呢?
機場
試著撥了電話給齊藤,一聽要進入語音信箱,我立刻就掛斷了。一群抱著滑雪板的人進來,從我的身旁經過。大玻璃門打開又關上。機場裡雖然明亮,可是在自動門的那一側更亮,抱著滑雪板的那群人起初看起來都成了剪影。一個中年男子坐在我的對面,正在看一本週刊雜誌。週刊的封面是一張女明星的臉,偶爾會在電視上看到的臉,可是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個姓氏中有個櫻字的女明星。我的手上並沒有機票。我正在全日空的登機櫃台前面等著與齊藤會合。齊藤會替我把機票帶來。
從剛才到現在,坐在對面拿著週刊的男子看了我兩次。年紀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身穿奶油色的長大衣,裡面是灰色西裝。全日空登機櫃台前面有好些面對面排放的椅子,妳就坐在那邊等我吧。我所等待的男子,齊藤,兩天前打電話來這麼說。我和齊藤是在四個月前認識的。全日空登機櫃台前面的椅子已經全部坐滿了。與來到機場的人相比,椅子的數量少得可憐。雖然不知道現在這個機場裡有多少人,而且有不少人是辦好登機手續便急忙衝向登機門,或許並不需要那麼多椅子也不一定,不過椅子的數量與想要坐下的人數相比確實是不夠的。有大批人正在等待別人從位子上站起來。那些人並沒有表現出正等待椅子空出來的神情態度,可是我就是知道那些人很想坐下來。因為,除了「想要找椅子坐下來」這種欲求之外,我並沒有接到那些人傳遞出其他任何訊息。
那個拿著週刊的男子與我四目相會。他的視線從我的眼睛移到肩膀,然後順著身體往下移到腳尖,短暫停留之後又回到週刊上。我穿了一件黑色洋裝,外面是駝色的毛外套,還圍了一條買了相當時日的名牌圍巾。手提包也是名牌貨,可是價格並不是多麼昂貴。因為不知道熊本會冷到什麼程度,所以我穿了與東京的冬季時相同的衣物前來。昨天晚上,原本打算在把孩子帶去託母親照顧之前先看看新聞的天氣預報了解一下熊本的氣溫,可是因為孩子有些撒賴,結果在天氣預報之前就出門了。
顯示出發航班狀況的電子告示板就在我的斜上方。全日空645往熊本的班機,上午十一點二十五分起飛,已經開始登機了。另外還有無數的航班狀況都顯示在告示板上。所顯示的航班一直排到下午三點十五分起飛的班機,而下一班往熊本的班機則是十三點四十分起飛。飛往福岡以及札幌的班機很多,到熊本的少。我看了看時間。飛熊本班機的登機手續,還剩幾分鐘就要截止辦理了呢?閱讀週刊的那個男人聽到飛福岡班機的登機說明廣播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男子站起來之前又看了我一眼。我不禁懷疑,或許可以從自己身上找到什麼那種女人的標誌也不一定。
我在兩年前離了婚,有個四歲的兒子。從結婚當時就一直和婆婆處不好,結果那就成了日後分手的直接原因。丈夫繼承了公公的機械零件工廠,可是在與我離異之後關廠了,好像是受主要客戶破產的連累。丈夫是個認真而個性溫和的人,對我很體貼,對婆婆更是體貼。婆婆的肩膀和背部出了問題,嘗試過以整脊、氣功、針灸以及其他各種古怪的民俗療法來治療,花了非常多錢。其實婆婆平常必須稍微活動活動才對,可是她幾乎都只是躺著,讓各種治療師在家裡進進出出。
閱讀週刊的男子站起來之後,兩個看起來像是一對夫妻的中年人,其中的男方在我的對面坐了下來。兩人的打扮,怎麼看都像是將要回鄉下去的樣子,臉和手都曬得黝黑。男方穿著起皺的白襯衫繫紅領帶,搭配袖子過短的焦茶色西裝。稀疏的頭髮抹了髮油往後梳得服貼,非常謹慎地抱著一個單肩大背包。女方的個子小,因為駝背的緣故,看起來就更小了。化了妝,只有臉部白得很不自然,白色女性襯衫外面穿了一件粗毛線編織成的橘色開襟毛衣,面無表情。
就算不認識那個人,也可以從對方的相貌、化妝、服裝以及態度上得知許多資訊。是住在都市裡呢,住在都市的近郊呢,還是住在非得搭飛機才到得了的鄉下,大概都可以看出來。從隨身的物品則可以看出對方的經濟狀況。從臉色和姿勢可以看出健康狀況,而年紀差不多一眼就可以判斷出來。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左手腕戴著卡地亞的手錶。這是我下海之後唯一買給自己的東西。別人看到這只手錶,是不是就會知道這個女人在風月場所上班呢?
離婚之後,我把兒子送到托兒所,自己在附近的加油站找了一份事務性的兼職。和一個名叫明美的女孩子一同當出納員,可是我不久便遭到解雇。當時明美二十二歲,我則是三十歲。加油站的獲利因為打價格戰而持續下滑,所以只想留下薪資較低的年輕人吧。離婚之後,我原本暫時住在丈夫的工廠作為員工宿舍的公寓裡,可是工廠倒閉之後,也非得搬出那裡不可了。聽說那間公寓後來也拿去抵了債。
隨著工廠關門,贍養費以及小孩的養育費也同時沒辦法付給我了。丈夫哭著向我道歉,可是我並沒有責怪他的意思。娘家在福島,雖然雙親叫我回去,可是哥哥嫂嫂住在那裡,根本不可能一起住。因為非得自己租房子不可,只好先去大崎找了間酒家上班,可是我的酒量很差,又不善於和陌生人交談,沒多久就因為胃出了問題而辭職。必須搬出宿舍的日子越來越接近,如果想找一間有衛浴和兩個房間的公寓來住,丈夫為我張羅的二十萬加上存款仍然不夠。一個月必須要有將近三十萬的收入才行。跟一個在大崎的酒家認識的不動產鑑定師商量之後,他介紹了一家可以信任的應召站給我。
《打工情報誌》上刊載了那家制服應召站的介紹,說是保證日入三萬五,每週一天亦可,來客經過該店嚴格篩選,均為具有社會信用的人士。撥了電話過去,對方要我直接到位於五反田西口的一棟住商混合大樓的店裡去。所謂的店面,也不過是一間套房而已。我獲得採用,拍了照片,登記了個花名叫做由依。店裡有各式各樣的道具服裝,而且,我當天就接了第一個客人。
這裡好像不能抽菸喔,坐在對面的中年男人這麼問同行的女性,可是女人依然面無表情,並沒有回答。中年男人講話帶著西部方言的口音。妳先過來佔一下位子。男人說著站起來換女人坐下,然後從胸前口袋掏出七星香菸,朝吸菸區走去。女人在我對面坐下之後,從布製的手提袋中拿出用玻璃紙包裝的點心,用雙手遮著取出裡面的東西慢條斯理送進口中,好像先用舌頭和牙齒弄散才吃下去。看起來像是餅乾還是冰糖栗子之類的點心,碎屑從女人的手邊掉落到深藍色的長褲上,她邊動著嘴巴邊用右手將那碎屑撢掉。
我的視野中滿是人。如果把移動的人們看作一整群的話,還真像是原始的動物或是洄游的魚群。已經撥了四次齊藤的行動電話的號碼。剛才撥電話給齊藤到現在還不到兩分鐘。難道他不會來嗎?齊藤比我小六歲,在一家顧問公司上班。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是在四個月前一個星期五的傍晚,地點是目黑的一家賓館。雖然我已經三十二歲,但是花名叫做由依的那個女人所登記的名字卻是二十五歲。就算填二十五歲也完全不會被懷疑喔,應召站負責人說。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接觸過將近兩百個女人了,女人的年齡啊,一般的男人可是看不出來的。
齊藤第一次買了我兩個鐘點。第一次接吻的時候,他撫著我的臉說,由依好美呀。第二次是在那三天後,同樣是兩個鐘點,然後隔天又買了三個鐘點,之後變成幾乎是天天來店裡報到。這種客人啊,一定要小心才行。
現在的時間是晚上八點多。我在居酒屋裡。坐在旁邊的是我的男朋友。男朋友的對面是他公司的人,我的對面則是我的公司同事。因為他公司的人想交女朋友,而我公司的同事則在找男朋友,於是我和我的他決定為兩人穿針引線。我的名字是水谷祐子,我的他名叫堺俊夫。我都喊他阿俊。
阿俊剛才介紹過他們公司那個人的名字。好像姓坂上,可是我沒聽清楚。因為後來一直沒有人喊那個人的名字,沒有辦法再次確認。或許是姓中上也不一定。阿俊與那個姓坂上還是中上的人的交情似乎並不是多麼好。我的公司同事名叫直美,二十五歲,比我小兩歲。
我們喝著生啤酒,吃著墨魚生魚片、炸雞、毛豆還有涼拌豆腐。姓坂上還是中上的那人,不知道為什麼帶了一個說是高中同學的女人同來。那女人穿著織有金銀絲線的粉紅色迷你洋裝,一副風塵味的打扮,而且還濃妝豔抹,那個女人的名字是吉本小夜子。直美雖然是來見未來男友人選的,卻因為害羞而帶了個游泳教室的男性友人一起來。他是小強,我之前並不認識。
我還是第一次光顧這家居酒屋。地點正好就位於JR東中野與中野的中間一帶。雖然這家店好像是阿俊選的,可是我並不清楚他以前是否來過這裡。櫃台裡有個看起來像是老闆的人,身穿和服頭上纏著布巾的打工女孩過來點菜。我們的隔壁是一桌上班族團體客。另外一邊的那一桌有七個人,正在聊著電影還是戲劇的話題,眾人都已經有了幾分醉意,講話的嗓門很大。他們之中有光頭族,也有長髮紮在腦後的人,七人中有兩名女性,兩人都穿著類似工作裝的黑色衣服。
牆邊的電視一直開著,可是沒有人在看。正在轉播職棒,在場上投球的是巨人隊的桑田,站在打擊區的則是橫濱的鈴木。恐怕只有坐在櫃台前一個人喝著酒的那些人才會看電視吧。櫃台在我的背後。有些什麼樣的人坐在櫃台,我並不知道。
我在品川一家配送公司負責內勤的工作,工作的時間朝九晚五。來這家公司上班之前,曾在西麻布的一家酒吧當服務生。阿俊在家具連鎖店工作。我們大約三個月前在淘兒唱片行挑選CD的時候認識的。雖然已經想不起來剛認識的時候聊了些什麼,可是並沒有聊到作畫的事情,到如今依然沒有談起過。就連直美,我也沒跟她提起過自己平常會作畫。直美好像是高中畢業之後就從山陰地方來到東京進入服裝設計的專門學校就讀,但是沒多久就休學了。聽說被男人騙過,但是詳細情形我並不清楚。
直美加入了網路的約會團體,曾經多次參加網友會以及紅娘派對,可是依然不停抱怨找不到好男人,所以我今天晚上才會安排介紹阿俊公司的人給直美認識。但不知道為什麼,她也帶了個男性友人一同前來。小強剛從大學畢業,好像是丸之內一家公司的職員。聽說這是兩人第一次在游泳教室之外的地方見面。
「所以人家才會說你沒有面對現實嘛!」
我聽到了這句話,可是不知道是從哪一桌傳來的聲音。這家店很吵,充滿了各種聲音。電視螢幕裡,桑田正準備投球,但不知為什麼還播放著音樂。好像是有線頻道,可是只知道正播放著音樂,不知道那是什麼曲子。四個頭上纏著布巾的打工女孩將食物與飲料送過來。剛才阿俊瞄了其中一個女孩一眼,大概是他中意的類型吧,我心裡想。是個大胸脯的女孩。與我交往之前,阿俊曾與一個名叫里美的大胸脯女孩交往,即使在與我交往之後,兩人依然藕斷絲連。
和我在一起的時候如果行動電話響起,而阿俊回答說「我等一下再回撥」的時候,對方必定是里美。我並沒有和阿俊同居。因為里美的事情,阿俊似乎對我感到有些內疚。直美穿著涼鞋的腳邊出現了某種小蟲。直美的腳趾肉肉的。剛才,姓坂上還是中上的那人說了些什麼,可是誰也沒有反應。我正在吃炸雞,雖然蒜味滿重的,可是今天晚上就是想吃點富含蛋白質的食物。
我還在陪酒的年代有個朋友,一個花名叫做小楓的女孩,私底下會玩SM,好像是當女王。她確實個子很高,但是長相並不是多麼美。聽她說,常去看診的牙醫是個被虐待狂,所以自己才被帶進那個世界。他們會用牙科的治療器具來助興,可是我沒有問到底是什麼樣的性遊戲。
阿俊對我心懷歉疚,所以我一提直美的事情,他就表示要幫忙介紹公司的男同事。跟直美提起這件事之後她也表示非介紹不可,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安排,可是我其實有些話想單獨跟阿俊講。因為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不想在這種居酒屋談。阿俊似乎有意跟我結婚。「雖然我還有其他女人,可是要結婚的話,還是要娶祐子。」阿俊說。這番話,是阿俊三個禮拜前說的。「那個女人只是胸部大而已,其他沒有任何優點,個性又不開朗。」阿俊這麼形容里美。里美好像是在特種營業工作。
「一想到她用含過其他男人那話兒的同一張嘴含著我的那話兒就覺得興奮不已,不過我可不希望討個那樣的老婆喔。」
「所以人家才會說你沒有面對現實嘛。所謂面對現實,就是要排除期待或是抱持希望的觀測這些先入之見,實事求是去看清楚現實,雖然並不是件多麼困難的事情,可是卻沒有人發覺這一點。你那種作品論根本就沒有人要聽啦,而且,你首先就應該正視自己不被任何人期待的這個事實吧。不是嗎?」
說這番話的到底是什麼人呢?
機場
試著撥了電話給齊藤,一聽要進入語音信箱,我立刻就掛斷了。一群抱著滑雪板的人進來,從我的身旁經過。大玻璃門打開又關上。機場裡雖然明亮,可是在自動門的那一側更亮,抱著滑雪板的那群人起初看起來都成了剪影。一個中年男子坐在我的對面,正在看一本週刊雜誌。週刊的封面是一張女明星的臉,偶爾會在電視上看到的臉,可是想不起她的名字,是個姓氏中有個櫻字的女明星。我的手上並沒有機票。我正在全日空的登機櫃台前面等著與齊藤會合。齊藤會替我把機票帶來。
從剛才到現在,坐在對面拿著週刊的男子看了我兩次。年紀大概還不到四十歲吧。身穿奶油色的長大衣,裡面是灰色西裝。全日空登機櫃台前面有好些面對面排放的椅子,妳就坐在那邊等我吧。我所等待的男子,齊藤,兩天前打電話來這麼說。我和齊藤是在四個月前認識的。全日空登機櫃台前面的椅子已經全部坐滿了。與來到機場的人相比,椅子的數量少得可憐。雖然不知道現在這個機場裡有多少人,而且有不少人是辦好登機手續便急忙衝向登機門,或許並不需要那麼多椅子也不一定,不過椅子的數量與想要坐下的人數相比確實是不夠的。有大批人正在等待別人從位子上站起來。那些人並沒有表現出正等待椅子空出來的神情態度,可是我就是知道那些人很想坐下來。因為,除了「想要找椅子坐下來」這種欲求之外,我並沒有接到那些人傳遞出其他任何訊息。
那個拿著週刊的男子與我四目相會。他的視線從我的眼睛移到肩膀,然後順著身體往下移到腳尖,短暫停留之後又回到週刊上。我穿了一件黑色洋裝,外面是駝色的毛外套,還圍了一條買了相當時日的名牌圍巾。手提包也是名牌貨,可是價格並不是多麼昂貴。因為不知道熊本會冷到什麼程度,所以我穿了與東京的冬季時相同的衣物前來。昨天晚上,原本打算在把孩子帶去託母親照顧之前先看看新聞的天氣預報了解一下熊本的氣溫,可是因為孩子有些撒賴,結果在天氣預報之前就出門了。
顯示出發航班狀況的電子告示板就在我的斜上方。全日空645往熊本的班機,上午十一點二十五分起飛,已經開始登機了。另外還有無數的航班狀況都顯示在告示板上。所顯示的航班一直排到下午三點十五分起飛的班機,而下一班往熊本的班機則是十三點四十分起飛。飛往福岡以及札幌的班機很多,到熊本的少。我看了看時間。飛熊本班機的登機手續,還剩幾分鐘就要截止辦理了呢?閱讀週刊的那個男人聽到飛福岡班機的登機說明廣播便從椅子上站了起來。男子站起來之前又看了我一眼。我不禁懷疑,或許可以從自己身上找到什麼那種女人的標誌也不一定。
我在兩年前離了婚,有個四歲的兒子。從結婚當時就一直和婆婆處不好,結果那就成了日後分手的直接原因。丈夫繼承了公公的機械零件工廠,可是在與我離異之後關廠了,好像是受主要客戶破產的連累。丈夫是個認真而個性溫和的人,對我很體貼,對婆婆更是體貼。婆婆的肩膀和背部出了問題,嘗試過以整脊、氣功、針灸以及其他各種古怪的民俗療法來治療,花了非常多錢。其實婆婆平常必須稍微活動活動才對,可是她幾乎都只是躺著,讓各種治療師在家裡進進出出。
閱讀週刊的男子站起來之後,兩個看起來像是一對夫妻的中年人,其中的男方在我的對面坐了下來。兩人的打扮,怎麼看都像是將要回鄉下去的樣子,臉和手都曬得黝黑。男方穿著起皺的白襯衫繫紅領帶,搭配袖子過短的焦茶色西裝。稀疏的頭髮抹了髮油往後梳得服貼,非常謹慎地抱著一個單肩大背包。女方的個子小,因為駝背的緣故,看起來就更小了。化了妝,只有臉部白得很不自然,白色女性襯衫外面穿了一件粗毛線編織成的橘色開襟毛衣,面無表情。
就算不認識那個人,也可以從對方的相貌、化妝、服裝以及態度上得知許多資訊。是住在都市裡呢,住在都市的近郊呢,還是住在非得搭飛機才到得了的鄉下,大概都可以看出來。從隨身的物品則可以看出對方的經濟狀況。從臉色和姿勢可以看出健康狀況,而年紀差不多一眼就可以判斷出來。我看了看自己的手。左手腕戴著卡地亞的手錶。這是我下海之後唯一買給自己的東西。別人看到這只手錶,是不是就會知道這個女人在風月場所上班呢?
離婚之後,我把兒子送到托兒所,自己在附近的加油站找了一份事務性的兼職。和一個名叫明美的女孩子一同當出納員,可是我不久便遭到解雇。當時明美二十二歲,我則是三十歲。加油站的獲利因為打價格戰而持續下滑,所以只想留下薪資較低的年輕人吧。離婚之後,我原本暫時住在丈夫的工廠作為員工宿舍的公寓裡,可是工廠倒閉之後,也非得搬出那裡不可了。聽說那間公寓後來也拿去抵了債。
隨著工廠關門,贍養費以及小孩的養育費也同時沒辦法付給我了。丈夫哭著向我道歉,可是我並沒有責怪他的意思。娘家在福島,雖然雙親叫我回去,可是哥哥嫂嫂住在那裡,根本不可能一起住。因為非得自己租房子不可,只好先去大崎找了間酒家上班,可是我的酒量很差,又不善於和陌生人交談,沒多久就因為胃出了問題而辭職。必須搬出宿舍的日子越來越接近,如果想找一間有衛浴和兩個房間的公寓來住,丈夫為我張羅的二十萬加上存款仍然不夠。一個月必須要有將近三十萬的收入才行。跟一個在大崎的酒家認識的不動產鑑定師商量之後,他介紹了一家可以信任的應召站給我。
《打工情報誌》上刊載了那家制服應召站的介紹,說是保證日入三萬五,每週一天亦可,來客經過該店嚴格篩選,均為具有社會信用的人士。撥了電話過去,對方要我直接到位於五反田西口的一棟住商混合大樓的店裡去。所謂的店面,也不過是一間套房而已。我獲得採用,拍了照片,登記了個花名叫做由依。店裡有各式各樣的道具服裝,而且,我當天就接了第一個客人。
這裡好像不能抽菸喔,坐在對面的中年男人這麼問同行的女性,可是女人依然面無表情,並沒有回答。中年男人講話帶著西部方言的口音。妳先過來佔一下位子。男人說著站起來換女人坐下,然後從胸前口袋掏出七星香菸,朝吸菸區走去。女人在我對面坐下之後,從布製的手提袋中拿出用玻璃紙包裝的點心,用雙手遮著取出裡面的東西慢條斯理送進口中,好像先用舌頭和牙齒弄散才吃下去。看起來像是餅乾還是冰糖栗子之類的點心,碎屑從女人的手邊掉落到深藍色的長褲上,她邊動著嘴巴邊用右手將那碎屑撢掉。
我的視野中滿是人。如果把移動的人們看作一整群的話,還真像是原始的動物或是洄游的魚群。已經撥了四次齊藤的行動電話的號碼。剛才撥電話給齊藤到現在還不到兩分鐘。難道他不會來嗎?齊藤比我小六歲,在一家顧問公司上班。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間是在四個月前一個星期五的傍晚,地點是目黑的一家賓館。雖然我已經三十二歲,但是花名叫做由依的那個女人所登記的名字卻是二十五歲。就算填二十五歲也完全不會被懷疑喔,應召站負責人說。到目前為止,我已經接觸過將近兩百個女人了,女人的年齡啊,一般的男人可是看不出來的。
齊藤第一次買了我兩個鐘點。第一次接吻的時候,他撫著我的臉說,由依好美呀。第二次是在那三天後,同樣是兩個鐘點,然後隔天又買了三個鐘點,之後變成幾乎是天天來店裡報到。這種客人啊,一定要小心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