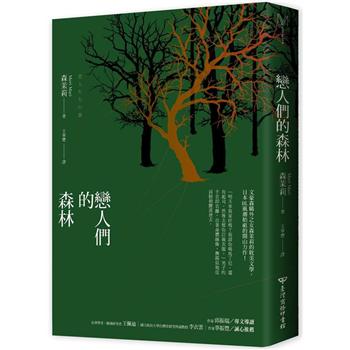選摘
<戀人們的森林>
從剛才開始,就有一名男子目不轉睛地觀察著巴羅的一舉一動,那就是義童。義童坐在巴羅正面深處的高腳椅上。他是位三十七、八歲的美男子,頸脖粗壯,帶有顯著的法國人特徵,但膚色黝黑,說一口道地的日語。他的額頭散發出豐富的學識氣息,但並不寬闊,頂著一頭濃密的黑髮。法國人常見的渾圓大眼帶著一點輕佻,同時又有種南洋島嶼毒蛇的味道。看著這名年輕人,就宛如疊影一般,浮現出一七七○、八○年代的法國書籍裡,蘋果樹枝纏繞著英文字母的插圖。讓人聯想起天鵝羽毛筆、羊皮紙書籍、一圈圈纏繞在脖子上繫成花朵狀的白絹領飾;或是巴士底監獄的床鋪、馬拉探出半裸上身的陶瓷浴缸;或穿著過短的長褲、頭戴徽章貝雷帽,高舉寫有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愛)標語旗幟的無套褲漢等民眾。看似具備智慧與睿智的年輕人,內在確實潛伏著法蘭西的榮光與法蘭西的淫蕩。粗頸上的衣領略髒,但似乎是這天午後新換上的,整體還算清潔。灰色毛呢背心與衣領之間探出的領帶,是深淺靛藍斜紋穿插著血紅色細絲的款式。年輕人則是一身黑西裝外套及深灰底配黑細紋貼身西褲。寬格圍巾從後頸覆蓋上來似地垂在胸前兩側,手肘撐在桌面,托著下巴,右手從剛才就一直插在口袋裡。年輕人似乎喝了不少,但看起來毫無醉意。唯一與平時不同的,僅有臉色略為蒼白,一雙黑眼顯得有些渙散而已。兩人之間有一名客人起身付帳時,望向那裡的巴羅目光正好對上了義童的。義童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浮現微笑。同時巴羅一驚,感覺到輕微的悸動。轉瞬之間,巴羅便悟出這名擁有深不可測迷人魅力的高大男子,從許久前便關注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巴羅的態度總有些僵硬起來,開始顯得矜持,令義童再次微笑。片刻之後,巴羅偷窺地將眼神朝義童一掃,隨即收回了視線。義童那雙有些駭人的黑眼睛溫柔地蕩漾開來。那種眼神,是已經嚐過那名女子的肉體,深知那具肉體的甜美,腦中浮現某種妄想而注視著女人時的眼神。肉慾的微笑在綻開的嘴唇抹上深濃的影子。
「琴費士。」
巴羅聽見這句話,目光再次飄了過去。這回男子看著服務生。巴羅那雙美麗的眼睛,眸子挑往斜上方,隔著眉毛望過去,隱藏著些許的不安和小小的恐懼,瞬間定在義童的側臉上。上唇起伏、下唇畫出美妙弧線的嘴唇緊抿,兩側擠出小窩,散發出冷峻的美。巴羅迅速地別開了目光。他有些難為情,想要離開,卻總捨不得這麼做。巴羅更頻繁地撩頭髮、東張西望、撈動鑰匙串了。同時他納悶那樣的男子會喝什麼琴費士嗎?這時,服務生的手倏地伸過來,放下琴費士的酒杯。巴羅的目光再次望向義童。
「喝吧,我請客。你喜歡琴費士吧?」
男子說。他那具備懾人力量,卻又輕佻戲謔的眸子,定在眼角,注視著巴羅。巴羅不自覺地微笑了。他很清楚自己這模樣有多可愛。天真無邪的微笑中,一雙眼眸湧出憧憬之色。巴羅欲言又止,抿起的嘴唇兩端羞怯地擠出酒窩。他珍惜地端起琴費士的酒杯,對燈端詳後挪到唇邊,對男子展現羞澀的微笑。領帶、背心、圍巾,那身服裝一望可知要價不菲。男子毫不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富裕。儘管巴羅看不出源於何處,但男子有種高級感,這家名為「茉莉」的小酒吧角落因為有了男子,變得彷彿別有城府。巴羅因醉意而濕潤的眼睛忽然嚴肅起來,嘴唇抿成孩子氣的形狀,目不轉睛地望向男子。在感到深受男子吸引的同時,巴羅想到了自己大學中輟,過著完全不讀書的生活,自慚形穢起來。
「你都來這裡?」
「嗯。」
巴羅把手放在偏褐色的亮澤頭髮的鬢角一帶,撩起了髮鬢。男子蒼白的臉緊繃著。那是陷入愛河的人有時會顯露的表情,彷彿承受著寒顫或苦澀,臉頰和嘴唇緊繃著。原本往下盯著鼻尖的眼睛忽然掃向牆邊,定在那裡。那眼神就像狙擊著麻雀的老鷹,彷彿發著高燒,黑眸的陰影甚至泛到眼白處。巴羅被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憧憬所驅動,陶然地望著那張側臉。那裡是一片暴風雨中的灰暗天空,傳來敏捷地掠過空中追逐雀鳥,並以尖銳的嘴喙撕裂空氣的老鷹的振翅聲。義童最後點了杯雙份高球雞尾酒,喝完後看了看身後的柱鐘,比對了一下腕錶,掀起外套摸索後口袋。他忘了帳單壓在手肘下,一邊摸口袋,目光一邊在桌上和腳邊逡巡。服務生把手伸到後頸,以眼神指示手肘下說:
「在那裡。」
「嗯。」
男子起身時,從斜上方俯視巴羅。
「再見……」
他微微舉手,指尖纖細而白皙。巴羅從剛才就知道帳單在哪裡,看見服務生以手繞頸提醒,這時他抬頭眨了眨眼,再次垂下目光。男子一離開,巴羅頓時覺得坐在那兒無趣極了。
「那個人是常客嗎?」
服務生須山眨起一眼:
「這陣子常來。是個怪傢伙,很厲害。」
「怪傢伙?」
「看就知道了吧?而且好像非常富有。你很有一手,要多常來啊。咱們不管是哪邊付錢都好,還請多多光臨。」
巴羅默默起身,手伸向後口袋。
「帳已經付清了。」
另一名服務生語氣輕佻地說。(沒見到他問,但我喝了幾杯他都看在眼裡。)巴羅頓時感到一股被盯上的羞恥。
「我會再來。」
巴羅說著,抓起掛在後方椅背的外套,迅速穿上,以纖細的雙手合攏前襟,踩著敏捷的腳步,一眨眼便消失在門外了。
巴羅走出只有模糊霓虹燈的巷弄,剛才的男子原本正在約十間 前方處緩步行走,這時突然回頭停步。他的下巴動了動,似在頷首,接著再次背過身往前走去,就像在叫他跟上去。巴羅腳步遲疑了一下,但隨即跑了過去。不知為何,一股宛如兄弟的懷念壓過了一切。巴羅追上以後,義童俯視著他微笑,是親近但祕密的微笑。巴羅感到安心極了,同時又有一種彷彿被喚醒的感覺。巴羅扭動了一下手插在後口袋的腰部,瞥了男子一眼,低頭繼續走。
「你住這附近?」
「更遠處……在松延寺那裡。」
巴羅低著頭說。
腳邊亮了起來,抬頭一看,兩人來到了路燈底下。義童停下腳步。巴羅抬頭仰望的眼睛帶著羞赧,與義童的眼神交纏在一起。巴羅雙眼皮的眼睛輪廓分明,宛如以銳利的雕刻刀所雕成,好似散發出淡紫色的火焰。義童把手搭到巴羅肩上。那動作極其自然,就像是兄弟,或高級裁縫師。
「明天來我家好嗎?我請你喝馬丁尼,還有起司。然後去幫你訂做衣服。」
男子的手若即若離,沿著身體線條,撫摸似地從肩膀朝腰部滑去。
巴羅沒喝過馬丁尼。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有如夢似幻的事情發生在身上了。
「你要來吧?」
「嗯。」
巴羅的聲音就像少女般輕柔。
*
自從北澤的酒吧那件事以後,巴羅的生活很快地變得與義童密不可分。只要是愉快的事,巴羅這個人就彷彿毫無意志一般,隨波逐流。義童本身以及他的生活,都充滿了吸引力。因此巴羅只是順著平時隨波逐流的作風行動罷了。然而巴羅逐漸被義童所吸引,除了無意識的功利想法外,亦開始真心仰慕起義童來了。
巴羅的父母還在世的時候,他上過一年大學,但他生性怠惰,對任何事都沒有動力,只能順從本能而活。巴羅會開車,因此靠著義童的門路,進入羅森斯坦當駕駛員。之前他在洗衣店送貨,但老闆娘開始對他拋媚眼、送秋波,害他被革職了。洗衣店有股怪味道,而且忙碌,但是在有許多公寓的北澤一帶,住在那裡的中年太太或年輕酒家女常會在門後塞給他百圓硬幣,甚至是五百圓鈔票,成了他的私房錢;因此離職那天下午,他為了洩憤,在隔簾後方摟抱住胖老闆娘的胸脯,與她接吻。老闆娘豐滿的胸脯激動起伏,突出的雙眼瞪著半空,氣喘吁吁,巴羅放開她,瞥了她一眼後,逃之夭夭地奔離現場,抓起鉤子上的手巾,將預藏的小費迅速塞進口袋,離開店裡。後來他向婚後住在函館的姊姊住子打秋風,用這筆錢在北澤一帶遊手好閒,差點加入不良集團。他對姊姊住子說,自己在義童那裡幫忙翻譯。從曉星中學畢業後,巴羅讀了一年法文系,但學業徹底荒廢,因此不可能幫得上義童,但由於義童是東大講師,住子儘管半信半疑,卻也覺得弟弟終於改邪歸正了。
月輪帶暈、徐風和暖的四月過去,樹木綻放綠意的五月也隨之離去,進入六月的某個午後,義童正坐在寢室,一旁,巴羅把身體折成L形,雙腳併攏伸出,柔情地依偎著他。巴羅的薄上衣是滴入咖啡般的牛奶色澤,臉上的雙眸黝黑晶亮。義童的手溫柔地撫弄著巴羅帶栗色的髮絲。
這裡是義童的工作室兼起居室。義童的本家在田園調布,住著寡母珠里,但義童自己蓋了棟僅有寬闊的房間、大廳、寢室、陽台和廚房的奢侈房屋而居,除了參加法事和雜務等難得回本家一趟以外,其餘時間都一個人生活。這棟屋子位在公車路旁巷道進去四、五町的地方。巴羅就在義童家附近租屋。
「蒙娜麗莎的臉真讓人不舒服。」
巴羅輕輕拂開義童的手,從一旁仰視義童說。
「你說樓梯的?」
義童的手往下滑,作勢要捧住巴羅小巧的臉龐。
田園調布的本家,在上去義童書房的內梯盡頭處的牆上,掛著蒙娜麗莎的複製畫,巴羅去辦事時看到了。
「那有什麼魅力嗎?聽說那是永遠的謎?」
「那是傳統的長相,有它獨特的趣味。」
「是嗎?你覺得她有魅力嗎?」
巴羅粗魯地拂開義童的手,離開去到窗邊的長椅,柔軟的身體趴在上頭,鑲嵌在形狀姣好而高挺的鼻子兩側的眼睛像寶石般閃閃發亮。義童放下懸在半空的手,上面還殘留著巴羅的髮絲觸感,右手朝巴羅伸去。巴羅立刻抓起桌上的Navy Cut菸草盒和火柴拋過去。義童視線緊盯著巴羅,接住之後,抽出雪茄點燃,望著天花板深深抽了一口。
「前天我遇到一個好厲害的人。第二次了。」
義童慢慢地將視線挪回到巴羅臉上,說:
「或許是我認識的人。」
「怎麼可能?我什麼都還沒說呢,你怎麼知道是誰?」
「稱得上厲害的傢伙可沒幾個。怎樣的人?」
「嗯,就像頭黑色的獅子。頭髮濃密,臉、額頭和兩頰都鬆垮垮的,膚色像印度人,嘴唇也是黑的。臉看起來頗油膩,脖子也是。然後他的眼睛……」
「那傢伙我見過。」
義童以帶著苦澀的表情微笑。
巴羅像隻靈巧的貓,觀望了義童的臉色後說:
「那傢伙很討厭,一直看我。」
巴羅沒有提到嶄新的施密特車。
下一瞬間,巴羅的表情就像忘了這回事,托著腮幫子,扭頭慵懶地望著天花板,噘起嘴唇,用口哨吹起向義童學來的曲子。(……)
選摘二 附錄
解說 富岡多惠子
(……)正如同唯有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才能是真正的浪漫主義者,森茉莉透過身為浪漫主義者,也是一名現實主義者。相對於一般人以看慣了現實的眼睛去看浪漫的世界,森茉莉卻是以注視浪漫世界的眼睛注視著現實,因此現實的虛假一眨眼便會被拆穿。真的是「某次」,我聽到森茉莉女士當著某個年輕女子的面大喊:啊,這個人有狐狸似的尾巴!她當時的眼神完全就是在該名女子身後看見了尾巴。她一定千真萬確地看見了尾巴吧!
對於無比敬愛的室生犀星,森茉莉女士曾在某處寫道,犀星是會從懷裡灑出星星的人。森茉莉說室生犀星的懷裡有許多小星星,會將這些星星灑在他欣賞的人身上,並說她親眼看過犀星一面把稿子交給報社派來取稿的小夥計,一面灑出小星星。這應該是事實。森茉莉一定在現實的世界看見了犀星將小星星灑在勤奮而禮貌的年輕人身上。這就是森茉莉對現實的認識。
室生犀星晚年將年輕時候開始寫的詩整理成一本全詩集時,從許多的詩篇拿掉了「永遠」兩個字,而西脇順三郎拾起犀星丟掉的這些「永遠」,完成了一部名叫《Aeternitas》(永遠)的詩集。愛好永恆之美的小說家森茉莉也隨著灑出的小星星,拾起了犀星的永遠嗎?
森茉莉女士花了八年或九年,最近完成了一部超過八百頁稿紙的長篇小說。脫稿之後,她說寫小說的期間,不管是吃是睡,心中都惦記著小說,很不快活,不過完成以後,所有的一切都好快樂,所以暫時也不想見人了。一陣子之後我倆碰面,她說她還要再寫長篇小說。開啟浪漫世界的門扉,活在其中,對森茉莉來說似乎不是未來式,而是Aeternitas的實踐。
(昭和五十年三月,作家)
<戀人們的森林>
從剛才開始,就有一名男子目不轉睛地觀察著巴羅的一舉一動,那就是義童。義童坐在巴羅正面深處的高腳椅上。他是位三十七、八歲的美男子,頸脖粗壯,帶有顯著的法國人特徵,但膚色黝黑,說一口道地的日語。他的額頭散發出豐富的學識氣息,但並不寬闊,頂著一頭濃密的黑髮。法國人常見的渾圓大眼帶著一點輕佻,同時又有種南洋島嶼毒蛇的味道。看著這名年輕人,就宛如疊影一般,浮現出一七七○、八○年代的法國書籍裡,蘋果樹枝纏繞著英文字母的插圖。讓人聯想起天鵝羽毛筆、羊皮紙書籍、一圈圈纏繞在脖子上繫成花朵狀的白絹領飾;或是巴士底監獄的床鋪、馬拉探出半裸上身的陶瓷浴缸;或穿著過短的長褲、頭戴徽章貝雷帽,高舉寫有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自由、平等、博愛)標語旗幟的無套褲漢等民眾。看似具備智慧與睿智的年輕人,內在確實潛伏著法蘭西的榮光與法蘭西的淫蕩。粗頸上的衣領略髒,但似乎是這天午後新換上的,整體還算清潔。灰色毛呢背心與衣領之間探出的領帶,是深淺靛藍斜紋穿插著血紅色細絲的款式。年輕人則是一身黑西裝外套及深灰底配黑細紋貼身西褲。寬格圍巾從後頸覆蓋上來似地垂在胸前兩側,手肘撐在桌面,托著下巴,右手從剛才就一直插在口袋裡。年輕人似乎喝了不少,但看起來毫無醉意。唯一與平時不同的,僅有臉色略為蒼白,一雙黑眼顯得有些渙散而已。兩人之間有一名客人起身付帳時,望向那裡的巴羅目光正好對上了義童的。義童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浮現微笑。同時巴羅一驚,感覺到輕微的悸動。轉瞬之間,巴羅便悟出這名擁有深不可測迷人魅力的高大男子,從許久前便關注著自己的一舉一動。巴羅的態度總有些僵硬起來,開始顯得矜持,令義童再次微笑。片刻之後,巴羅偷窺地將眼神朝義童一掃,隨即收回了視線。義童那雙有些駭人的黑眼睛溫柔地蕩漾開來。那種眼神,是已經嚐過那名女子的肉體,深知那具肉體的甜美,腦中浮現某種妄想而注視著女人時的眼神。肉慾的微笑在綻開的嘴唇抹上深濃的影子。
「琴費士。」
巴羅聽見這句話,目光再次飄了過去。這回男子看著服務生。巴羅那雙美麗的眼睛,眸子挑往斜上方,隔著眉毛望過去,隱藏著些許的不安和小小的恐懼,瞬間定在義童的側臉上。上唇起伏、下唇畫出美妙弧線的嘴唇緊抿,兩側擠出小窩,散發出冷峻的美。巴羅迅速地別開了目光。他有些難為情,想要離開,卻總捨不得這麼做。巴羅更頻繁地撩頭髮、東張西望、撈動鑰匙串了。同時他納悶那樣的男子會喝什麼琴費士嗎?這時,服務生的手倏地伸過來,放下琴費士的酒杯。巴羅的目光再次望向義童。
「喝吧,我請客。你喜歡琴費士吧?」
男子說。他那具備懾人力量,卻又輕佻戲謔的眸子,定在眼角,注視著巴羅。巴羅不自覺地微笑了。他很清楚自己這模樣有多可愛。天真無邪的微笑中,一雙眼眸湧出憧憬之色。巴羅欲言又止,抿起的嘴唇兩端羞怯地擠出酒窩。他珍惜地端起琴費士的酒杯,對燈端詳後挪到唇邊,對男子展現羞澀的微笑。領帶、背心、圍巾,那身服裝一望可知要價不菲。男子毫不保留地展示自己的富裕。儘管巴羅看不出源於何處,但男子有種高級感,這家名為「茉莉」的小酒吧角落因為有了男子,變得彷彿別有城府。巴羅因醉意而濕潤的眼睛忽然嚴肅起來,嘴唇抿成孩子氣的形狀,目不轉睛地望向男子。在感到深受男子吸引的同時,巴羅想到了自己大學中輟,過著完全不讀書的生活,自慚形穢起來。
「你都來這裡?」
「嗯。」
巴羅把手放在偏褐色的亮澤頭髮的鬢角一帶,撩起了髮鬢。男子蒼白的臉緊繃著。那是陷入愛河的人有時會顯露的表情,彷彿承受著寒顫或苦澀,臉頰和嘴唇緊繃著。原本往下盯著鼻尖的眼睛忽然掃向牆邊,定在那裡。那眼神就像狙擊著麻雀的老鷹,彷彿發著高燒,黑眸的陰影甚至泛到眼白處。巴羅被連自己都無法理解的憧憬所驅動,陶然地望著那張側臉。那裡是一片暴風雨中的灰暗天空,傳來敏捷地掠過空中追逐雀鳥,並以尖銳的嘴喙撕裂空氣的老鷹的振翅聲。義童最後點了杯雙份高球雞尾酒,喝完後看了看身後的柱鐘,比對了一下腕錶,掀起外套摸索後口袋。他忘了帳單壓在手肘下,一邊摸口袋,目光一邊在桌上和腳邊逡巡。服務生把手伸到後頸,以眼神指示手肘下說:
「在那裡。」
「嗯。」
男子起身時,從斜上方俯視巴羅。
「再見……」
他微微舉手,指尖纖細而白皙。巴羅從剛才就知道帳單在哪裡,看見服務生以手繞頸提醒,這時他抬頭眨了眨眼,再次垂下目光。男子一離開,巴羅頓時覺得坐在那兒無趣極了。
「那個人是常客嗎?」
服務生須山眨起一眼:
「這陣子常來。是個怪傢伙,很厲害。」
「怪傢伙?」
「看就知道了吧?而且好像非常富有。你很有一手,要多常來啊。咱們不管是哪邊付錢都好,還請多多光臨。」
巴羅默默起身,手伸向後口袋。
「帳已經付清了。」
另一名服務生語氣輕佻地說。(沒見到他問,但我喝了幾杯他都看在眼裡。)巴羅頓時感到一股被盯上的羞恥。
「我會再來。」
巴羅說著,抓起掛在後方椅背的外套,迅速穿上,以纖細的雙手合攏前襟,踩著敏捷的腳步,一眨眼便消失在門外了。
巴羅走出只有模糊霓虹燈的巷弄,剛才的男子原本正在約十間 前方處緩步行走,這時突然回頭停步。他的下巴動了動,似在頷首,接著再次背過身往前走去,就像在叫他跟上去。巴羅腳步遲疑了一下,但隨即跑了過去。不知為何,一股宛如兄弟的懷念壓過了一切。巴羅追上以後,義童俯視著他微笑,是親近但祕密的微笑。巴羅感到安心極了,同時又有一種彷彿被喚醒的感覺。巴羅扭動了一下手插在後口袋的腰部,瞥了男子一眼,低頭繼續走。
「你住這附近?」
「更遠處……在松延寺那裡。」
巴羅低著頭說。
腳邊亮了起來,抬頭一看,兩人來到了路燈底下。義童停下腳步。巴羅抬頭仰望的眼睛帶著羞赧,與義童的眼神交纏在一起。巴羅雙眼皮的眼睛輪廓分明,宛如以銳利的雕刻刀所雕成,好似散發出淡紫色的火焰。義童把手搭到巴羅肩上。那動作極其自然,就像是兄弟,或高級裁縫師。
「明天來我家好嗎?我請你喝馬丁尼,還有起司。然後去幫你訂做衣服。」
男子的手若即若離,沿著身體線條,撫摸似地從肩膀朝腰部滑去。
巴羅沒喝過馬丁尼。他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覺到有如夢似幻的事情發生在身上了。
「你要來吧?」
「嗯。」
巴羅的聲音就像少女般輕柔。
*
自從北澤的酒吧那件事以後,巴羅的生活很快地變得與義童密不可分。只要是愉快的事,巴羅這個人就彷彿毫無意志一般,隨波逐流。義童本身以及他的生活,都充滿了吸引力。因此巴羅只是順著平時隨波逐流的作風行動罷了。然而巴羅逐漸被義童所吸引,除了無意識的功利想法外,亦開始真心仰慕起義童來了。
巴羅的父母還在世的時候,他上過一年大學,但他生性怠惰,對任何事都沒有動力,只能順從本能而活。巴羅會開車,因此靠著義童的門路,進入羅森斯坦當駕駛員。之前他在洗衣店送貨,但老闆娘開始對他拋媚眼、送秋波,害他被革職了。洗衣店有股怪味道,而且忙碌,但是在有許多公寓的北澤一帶,住在那裡的中年太太或年輕酒家女常會在門後塞給他百圓硬幣,甚至是五百圓鈔票,成了他的私房錢;因此離職那天下午,他為了洩憤,在隔簾後方摟抱住胖老闆娘的胸脯,與她接吻。老闆娘豐滿的胸脯激動起伏,突出的雙眼瞪著半空,氣喘吁吁,巴羅放開她,瞥了她一眼後,逃之夭夭地奔離現場,抓起鉤子上的手巾,將預藏的小費迅速塞進口袋,離開店裡。後來他向婚後住在函館的姊姊住子打秋風,用這筆錢在北澤一帶遊手好閒,差點加入不良集團。他對姊姊住子說,自己在義童那裡幫忙翻譯。從曉星中學畢業後,巴羅讀了一年法文系,但學業徹底荒廢,因此不可能幫得上義童,但由於義童是東大講師,住子儘管半信半疑,卻也覺得弟弟終於改邪歸正了。
月輪帶暈、徐風和暖的四月過去,樹木綻放綠意的五月也隨之離去,進入六月的某個午後,義童正坐在寢室,一旁,巴羅把身體折成L形,雙腳併攏伸出,柔情地依偎著他。巴羅的薄上衣是滴入咖啡般的牛奶色澤,臉上的雙眸黝黑晶亮。義童的手溫柔地撫弄著巴羅帶栗色的髮絲。
這裡是義童的工作室兼起居室。義童的本家在田園調布,住著寡母珠里,但義童自己蓋了棟僅有寬闊的房間、大廳、寢室、陽台和廚房的奢侈房屋而居,除了參加法事和雜務等難得回本家一趟以外,其餘時間都一個人生活。這棟屋子位在公車路旁巷道進去四、五町的地方。巴羅就在義童家附近租屋。
「蒙娜麗莎的臉真讓人不舒服。」
巴羅輕輕拂開義童的手,從一旁仰視義童說。
「你說樓梯的?」
義童的手往下滑,作勢要捧住巴羅小巧的臉龐。
田園調布的本家,在上去義童書房的內梯盡頭處的牆上,掛著蒙娜麗莎的複製畫,巴羅去辦事時看到了。
「那有什麼魅力嗎?聽說那是永遠的謎?」
「那是傳統的長相,有它獨特的趣味。」
「是嗎?你覺得她有魅力嗎?」
巴羅粗魯地拂開義童的手,離開去到窗邊的長椅,柔軟的身體趴在上頭,鑲嵌在形狀姣好而高挺的鼻子兩側的眼睛像寶石般閃閃發亮。義童放下懸在半空的手,上面還殘留著巴羅的髮絲觸感,右手朝巴羅伸去。巴羅立刻抓起桌上的Navy Cut菸草盒和火柴拋過去。義童視線緊盯著巴羅,接住之後,抽出雪茄點燃,望著天花板深深抽了一口。
「前天我遇到一個好厲害的人。第二次了。」
義童慢慢地將視線挪回到巴羅臉上,說:
「或許是我認識的人。」
「怎麼可能?我什麼都還沒說呢,你怎麼知道是誰?」
「稱得上厲害的傢伙可沒幾個。怎樣的人?」
「嗯,就像頭黑色的獅子。頭髮濃密,臉、額頭和兩頰都鬆垮垮的,膚色像印度人,嘴唇也是黑的。臉看起來頗油膩,脖子也是。然後他的眼睛……」
「那傢伙我見過。」
義童以帶著苦澀的表情微笑。
巴羅像隻靈巧的貓,觀望了義童的臉色後說:
「那傢伙很討厭,一直看我。」
巴羅沒有提到嶄新的施密特車。
下一瞬間,巴羅的表情就像忘了這回事,托著腮幫子,扭頭慵懶地望著天花板,噘起嘴唇,用口哨吹起向義童學來的曲子。(……)
選摘二 附錄
解說 富岡多惠子
(……)正如同唯有真正的現實主義者,才能是真正的浪漫主義者,森茉莉透過身為浪漫主義者,也是一名現實主義者。相對於一般人以看慣了現實的眼睛去看浪漫的世界,森茉莉卻是以注視浪漫世界的眼睛注視著現實,因此現實的虛假一眨眼便會被拆穿。真的是「某次」,我聽到森茉莉女士當著某個年輕女子的面大喊:啊,這個人有狐狸似的尾巴!她當時的眼神完全就是在該名女子身後看見了尾巴。她一定千真萬確地看見了尾巴吧!
對於無比敬愛的室生犀星,森茉莉女士曾在某處寫道,犀星是會從懷裡灑出星星的人。森茉莉說室生犀星的懷裡有許多小星星,會將這些星星灑在他欣賞的人身上,並說她親眼看過犀星一面把稿子交給報社派來取稿的小夥計,一面灑出小星星。這應該是事實。森茉莉一定在現實的世界看見了犀星將小星星灑在勤奮而禮貌的年輕人身上。這就是森茉莉對現實的認識。
室生犀星晚年將年輕時候開始寫的詩整理成一本全詩集時,從許多的詩篇拿掉了「永遠」兩個字,而西脇順三郎拾起犀星丟掉的這些「永遠」,完成了一部名叫《Aeternitas》(永遠)的詩集。愛好永恆之美的小說家森茉莉也隨著灑出的小星星,拾起了犀星的永遠嗎?
森茉莉女士花了八年或九年,最近完成了一部超過八百頁稿紙的長篇小說。脫稿之後,她說寫小說的期間,不管是吃是睡,心中都惦記著小說,很不快活,不過完成以後,所有的一切都好快樂,所以暫時也不想見人了。一陣子之後我倆碰面,她說她還要再寫長篇小說。開啟浪漫世界的門扉,活在其中,對森茉莉來說似乎不是未來式,而是Aeternitas的實踐。
(昭和五十年三月,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