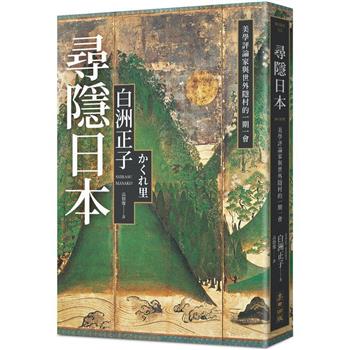宇陀的大藏寺
我不喜歡上電視。在那強烈的燈光照射下,接連接受提問,我連十分之一的內容都講不出來。當我在思考時,主持人馬上接話解危,話題就此被帶往意想不到的方向。這都是因為我自己腦筋轉得不夠快,沒資格抱怨,不過上完電視後總是感覺餘味頗糟。既然如此,推掉邀約不就得了,但有時會有一些有趣的節目,說要帶我到難得一去的地方,我也沒細想就這麼答應了,事後才感到後悔。宇陀的大藏寺就是這樣的節目之一。
順著大和平野南下,在櫻井轉乘,在榛原車站與工作人員會合。那天是梅雨季難得放晴的日子,一個悶熱的早晨。我們從這裡開車前往大宇陀一處叫栗野的地方,但因為路上都在說話,所以不清楚究竟花了多少時間。過了一會兒,我們在一處狹窄的山路下車。路旁立著石碑,寫著「元高野」。大藏寺是昔日弘法大師(※空海。)在開創高野山之前,四處找尋道場時,曾暫住過的地方,之所以叫「元高野」,似乎就是以這個緣由來命名。不過,聽說大藏寺創建的年代久遠,是聖德太子所創建,但此事真偽難定。
微微上坡的狹窄參道,行人稀少,地上覆滿夏草。下方可能有小溪流過,傳來輕快的澗澗水聲。我就喜歡這樣的小路。雖然不想說「還是保有古味好」,但確實是如此。例如要去法隆寺,得從王寺開始走,或是從郡山搭汽油火車,再走上一大段距離。沐浴在春陽下,順著油菜花燦放的鄉間小路往西行,遠方逐漸可以望見法輪寺的高塔。接著是法起寺,然後是法隆寺高大的五重塔,都在春霞中浮現。那種心情絕非搭汽車前往所能體會。走著走著,逐漸會興起一股到寺院參拜的氛圍,並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說得更誇張一點,可說是瀰漫在大和平原的推古、天平時代的空氣,滿滿充塞我的胸臆。
當然了,這座山寺沒有這樣的明亮氣息。話雖如此,它卻沒有密教寺院特有的陰鬱嚴肅,倒是給人一種雜樹山林裡健行般的感覺。走了將近一公里後,不知從哪兒飄來一陣甘甜的芳香。走近一看,原來是開滿白花的梔子樹,樹下建了一座小屋。他們告訴我「這是僧房」。我聽說這是一座氣派的寺院,但完全沒看到半點像樣的影子。連山門也沒有。此事姑且不談,眼前這棵高大的梔子樹令人驚訝。那是得抬頭仰望的大樹,可說是竭盡所能的開滿了花,花團錦簇,與一般我們所知道的灌木一點都不像。要長成這樣的大樹,至少也得花上近千年的時間吧。後方的山丘也種有足以雙手環抱的杜鵑,還開著殘存的花朵,確實是一座古寺,令人感佩。
大藏寺現在算是初瀨寺底下所屬的寺院,初瀨寺的事務長還特地前來接待。電視臺的威力果然不容小覷。休息片刻後,我們請他帶我們到正殿參觀。也難怪剛才看不到,寺院位在剛才提到的杜鵑山丘之上,拾級而上,眼前景色就此變得開闊,藥師堂、御影堂、十三重石塔等,都一一從聳立的高野金松間的縫隙現身。個個都是這一帶罕見的鎌倉時代建築,鋪上柔軟檜木皮的屋頂,彼此交疊錯落,就此融入周遭的山脊線中,美不勝收。西邊是區隔大和與宇陀的連峰,東邊則視野寬闊,不算太高的山脈和山丘蜿蜒並立,南方則可以遙望吉野的連山。昔日的寺院可能是因為懂得巧妙的善用自然,完全的融入周遭的景致中,讓人忘了它們是人工的建築。我所指的並非只限寺院。神社和房屋也都讓人覺得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這正是因為他們對所有事物都抱持一份敏銳的心。現代的生活讓人變得神經質,但絕不會讓人變得敏銳。我認為過度敏感是一種精神的麻痺狀態。
大藏寺正殿
如前所述,這裡的正殿和御影堂都是鎌倉時代的建築,整體呈現一種輕快感,連細部也看得出作工的細心。例如御影堂的蛙腿形裝飾,那明快的雕刻,很適合這座山寺,完全沒有刻意擺顯威儀的地方,令人心曠神怡。御影堂又稱作大師堂,供奉弘法大師的雕像,同樣是鎌倉時代的優秀雕刻,以大師像來說,算是頗有歷史。御影堂與正殿之間立著一座高大的十三重石塔,現在已失去其中三層,成了十重塔,不過這是當初重建東大寺時,從宋朝請來的伊行末(※南宋時代浙江省寧波人,於鎌倉時代赴日,投入重建東大寺的工程。是日本石匠集團「伊派」的創始者。)所打造,基壇的正面刻有銘文。我記得東大寺門前的狛犬以及般若寺的石塔,也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不過絲毫不帶中國風,是它的獨特之美,與周遭的景致以及建築也都充分融合。
這裡之所以會有這麼多鎌倉時代的建築,是因為當時寺院突然興盛,還是與東大寺有何關聯呢?它自古便是龍門七大寺之一,擁有許多所屬寺院和僧房,至今仍擁有數萬坪的廣大土地,可是卻鮮為人知,也沒有明確的歷史,當真令人費解。不過,或許就因為是這樣的地方,才有寺院的魅力。事物一旦變得過於清楚明白,反而引人懷疑,不如充滿謎團,這樣才讓人感興趣。至少對我來說,這麼美的寺院突然出現眼前,光是這樣,就覺得今天一天不算白活。
從大藏寺眺望烏之塒
可以望見一座很出色的高山與此寺相鄰。詢問後得知,此山名喚「烏之塒」。這一帶相當於神武天皇東征時的行經之路,所以可能是八咫烏之塒(※塒是鳥巢的意思。八咫烏是神武天皇東征時,受高皇產靈神和天照大神之命為天皇帶路的烏鴉,一般描繪為三隻腳的形象。),或是以烏鴉當圖騰的豪族居所,至今仍有許多烏鴉在此棲息。現在與大藏寺似乎已無直接關聯,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凡是古寺皆與古代信仰緊密結合,這是具有濃厚日本色彩,饒富趣味的存在方式。在神佛混淆的思想下,天竺諸佛為了度化眾生,以日本神明的形象現身,但事實卻與之相反,應該是為了宣揚佛教,而需要借助日本神明的力量吧。雖然只有些許差異,但意義卻大不相同。若換個說法,以日本神明當經線,以佛教當緯線,以此編織而成的,正是所謂的本地垂跡說(※日本佛教興盛時期的一種思想。指稱日本神道的八百萬神是佛菩薩的化身,稱為權現。理論上神佛具有同等地位。)。不過對象是不會說話的木石,無法加以證明,但日本的大自然向我說明了這一切。此事至今仍沒多大的不同。提出條理分明的理論,這是外國傳來的方式,日本人心中只能默默聆聽。然而,默不作聲不表示就此屈服。長期以來支撐起外來思想和技術的,一直都是沉默不語的日本諸神。
坦白說,我雖然對大藏寺的環境和建築感到佩服,但是對裡頭的佛像卻不抱持期待。藤原時代的佛像良莠不一。我心裡原本認為,在這種深山之地不會有什麼多像樣的雕刻,但是當正殿的大門開啟時,我的想法徹底被顛覆。那佛像真是美。不過,它並非是多特別的雕刻,明顯是地方上的作品,但這當中帶有言語難以形容的純真,感覺得出它已超越時代或技術。臉部尤其美。以類似推古時代佛像的表情,從它那八尺八寸的身高,心無雜念的俯視,看起來比藤原時代初期的佛像更有古味。這種情況也常見於敦煌的雕刻中,由於這是鄉間作品,反而傳達出古時候的樣式。或許專家不認同,但比起完美無缺的佛像,我覺得這種佛像更易親近。正殿內的擺設我也很欣賞。不同於一般的寺院正殿,這裡沒添加多餘的裝飾,佛龕也造型簡樸,使得佛像更顯高大。在一點都不像密教的開放氛圍下,給人一種直接膜拜神佛之感。
天部形立像(大藏寺珍藏)
據寺傳記載,這尊藥師佛是以境內的一株大樟樹雕刻而成,也算是一種「立木信仰」。關於立木觀音,前面也曾提過,不過當我望著這尊佛像時,看到的不是雕刻,而是樹木的自然樣貌。事實上,當初雕刻的人們肯定也從樹木中學習到不少。像是木材的處理方式、對木紋的細膩用心等,沒半點違逆自然之處。就這層意涵來看,在金銅打造的佛像方面,就算是藥師寺三尊這樣的名作,也還沒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作品。我們的祖先可說是在開始打造木雕後,才開始真正吸收了佛教思想。
正殿內供奉了同屬藤原時代的毘沙門天像。這又稱作兜跋毘沙門,聽說地方上的人們都稱呼它「神象先生」,我認為這才正確。佛像雖然右手托塔,但雙臂似乎都修補過,不論是臉部表情還是身體的僵硬模樣,都不太像佛像,反倒比較像神像。眾所皆知,不管再好的傑作,神像一定都會打造成僵硬的姿態,我向來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不過,在那雕刻興盛的時代,我不認為這是因為技術不夠純熟使然。也不可能是粗製濫造。若是如此,會不會打從一開始就是仿效樹木來打造呢?坐像就像樹根一樣,而立像看起來就像活生生的樹木。雙手都深藏在衣袖裡,不論臉部表情還是身體,都拒絕呈現任何「動作」。這尊神象先生和藥師如來之所以給人類似這樣的印象,想必是因為在這遠離都城的鄉村裡,古代的自然信仰已根深蒂固。雖然不清楚作者為何人,但肯定是同一個人,或同一流派的人,與神社關係深厚。
境內出乎意料的寬敞。處處都有高大的高野金松聳立,從樹木間的縫隙可以望見「烏之塒」。這座山就像在追著我們跑,不管我們去哪兒,都一樣看得到它。與弘法大師有關的事物,除了修行場外,只留下掛衣服的松樹或加持過的泉水,不過這雄偉的金松說明了它與高野山的深厚關係。正殿後方的小山丘上有一座墓地。這裡是視野開闊的高臺,當中地勢特別高的墳塚上立著一座漂亮的五輪塔。上面有正平六年(一三五一年)的銘文,但就只知道是「南朝某貴人」的墳墓,不清楚是何身分。因為這一帶是南朝的大本營,所以也許是在某地戰死的地方豪士,在故鄉的寺院下葬。或者是某位身分更高的「貴人」在此過世。墓地面朝吉野的方向而建,看起來宛如死者的情感至今仍飄蕩在布滿青苔的石面上。總之,這肯定是一方大將,如今雖已化為無名的石塔,卻仍持續凝望吉野的天空,那模樣深深打動我心。
岡倉天心捐贈的弁事堂和殿內的地藏菩薩
臨行時,我們在僧房接受熱茶款待。這段時間,住持讓我們見識寶物。裡頭是藤原時代的大般若經。八百卷中遺失了四十四卷,但令人吃驚的是,這大部分都是手抄經文,底頁寫道「仁安二年(一一六七)四月五日於仁和寺宿所書寫了」,那工整的字體保有天平時代的風格。說到字體,寫著「大藏寺」的匾額也很美。這匾額是出自藤原大人的草書,經淺雕後在上頭塗上顏色,但現在顏色幾乎都已褪盡。這匾額是嵯峨天皇行幸大藏寺時賜贈之勅額,上頭刻有銘文「保延六年(一一四○)庚申五月二十八日幸未書之 從五位上寺宮內權大輔藤原定信」,定信是知名的書法家。但與嵯峨天皇的時代不符。也許是一開始的匾額破損,請定信重新揮毫。天皇遠道而來,這點也啟人疑竇,不過主佛藥師佛建造完成,應該是在天皇在位期間,而寺院的創立也大約是在那時候。這座寺院寶物眾多,除了前面所列舉的之外,還有藤原時代的地藏菩薩、大黑天的木雕像、板繪的佛畫等,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上面刻有永正十一年(一五一四)銘文的一張經卷桌。這是俗稱的寺子屋桌,但正因為年代久遠,別具韻味。而不經意的保有這樣的古物,也是遠離塵囂的山寺可貴之處。
僧房旁有一座茅草屋頂的小佛堂,名叫「弁事堂」。是岡倉天心(※日本明治時期的美術家、思想家。)捐贈,聽說天心與這座寺院的前任住持交好,時常到此地留宿。佛堂裡祭祀鎌倉時代收集來的一尊地藏菩薩,最近從這尊菩薩體內發現摺佛(※將佛或菩薩的圖像印在紙或布面上。),上頭寫有延應元年(一二三九)僧人長信及其他多位結緣者的名字。由於此地藏菩薩無處安置,所以天心才會建造這座佛堂吧。大藏寺是他很喜愛的寺院,雖然就只是因為這樣,但這故事卻深植我心。
回程時,我們走另一條路。寺院後方是一片迷人的山白竹林,穿過竹林後,眼前是一處往下的陡坡,走不到三十分鐘便來到了幹道。
「要不要順便小逛一下」,導演K先生說道。我求之不得,這麼一來,我對討厭的電視演出也才能多點期待。這一帶有許多我想去的地方。「那麼,就交給我負責吧」,我聽從他的建議,也沒問他要去哪兒,就此坐上車。
我不喜歡上電視。在那強烈的燈光照射下,接連接受提問,我連十分之一的內容都講不出來。當我在思考時,主持人馬上接話解危,話題就此被帶往意想不到的方向。這都是因為我自己腦筋轉得不夠快,沒資格抱怨,不過上完電視後總是感覺餘味頗糟。既然如此,推掉邀約不就得了,但有時會有一些有趣的節目,說要帶我到難得一去的地方,我也沒細想就這麼答應了,事後才感到後悔。宇陀的大藏寺就是這樣的節目之一。
順著大和平野南下,在櫻井轉乘,在榛原車站與工作人員會合。那天是梅雨季難得放晴的日子,一個悶熱的早晨。我們從這裡開車前往大宇陀一處叫栗野的地方,但因為路上都在說話,所以不清楚究竟花了多少時間。過了一會兒,我們在一處狹窄的山路下車。路旁立著石碑,寫著「元高野」。大藏寺是昔日弘法大師(※空海。)在開創高野山之前,四處找尋道場時,曾暫住過的地方,之所以叫「元高野」,似乎就是以這個緣由來命名。不過,聽說大藏寺創建的年代久遠,是聖德太子所創建,但此事真偽難定。
微微上坡的狹窄參道,行人稀少,地上覆滿夏草。下方可能有小溪流過,傳來輕快的澗澗水聲。我就喜歡這樣的小路。雖然不想說「還是保有古味好」,但確實是如此。例如要去法隆寺,得從王寺開始走,或是從郡山搭汽油火車,再走上一大段距離。沐浴在春陽下,順著油菜花燦放的鄉間小路往西行,遠方逐漸可以望見法輪寺的高塔。接著是法起寺,然後是法隆寺高大的五重塔,都在春霞中浮現。那種心情絕非搭汽車前往所能體會。走著走著,逐漸會興起一股到寺院參拜的氛圍,並做好這樣的心理準備。說得更誇張一點,可說是瀰漫在大和平原的推古、天平時代的空氣,滿滿充塞我的胸臆。
當然了,這座山寺沒有這樣的明亮氣息。話雖如此,它卻沒有密教寺院特有的陰鬱嚴肅,倒是給人一種雜樹山林裡健行般的感覺。走了將近一公里後,不知從哪兒飄來一陣甘甜的芳香。走近一看,原來是開滿白花的梔子樹,樹下建了一座小屋。他們告訴我「這是僧房」。我聽說這是一座氣派的寺院,但完全沒看到半點像樣的影子。連山門也沒有。此事姑且不談,眼前這棵高大的梔子樹令人驚訝。那是得抬頭仰望的大樹,可說是竭盡所能的開滿了花,花團錦簇,與一般我們所知道的灌木一點都不像。要長成這樣的大樹,至少也得花上近千年的時間吧。後方的山丘也種有足以雙手環抱的杜鵑,還開著殘存的花朵,確實是一座古寺,令人感佩。
大藏寺現在算是初瀨寺底下所屬的寺院,初瀨寺的事務長還特地前來接待。電視臺的威力果然不容小覷。休息片刻後,我們請他帶我們到正殿參觀。也難怪剛才看不到,寺院位在剛才提到的杜鵑山丘之上,拾級而上,眼前景色就此變得開闊,藥師堂、御影堂、十三重石塔等,都一一從聳立的高野金松間的縫隙現身。個個都是這一帶罕見的鎌倉時代建築,鋪上柔軟檜木皮的屋頂,彼此交疊錯落,就此融入周遭的山脊線中,美不勝收。西邊是區隔大和與宇陀的連峰,東邊則視野寬闊,不算太高的山脈和山丘蜿蜒並立,南方則可以遙望吉野的連山。昔日的寺院可能是因為懂得巧妙的善用自然,完全的融入周遭的景致中,讓人忘了它們是人工的建築。我所指的並非只限寺院。神社和房屋也都讓人覺得像是大自然的一部分。這正是因為他們對所有事物都抱持一份敏銳的心。現代的生活讓人變得神經質,但絕不會讓人變得敏銳。我認為過度敏感是一種精神的麻痺狀態。
大藏寺正殿
如前所述,這裡的正殿和御影堂都是鎌倉時代的建築,整體呈現一種輕快感,連細部也看得出作工的細心。例如御影堂的蛙腿形裝飾,那明快的雕刻,很適合這座山寺,完全沒有刻意擺顯威儀的地方,令人心曠神怡。御影堂又稱作大師堂,供奉弘法大師的雕像,同樣是鎌倉時代的優秀雕刻,以大師像來說,算是頗有歷史。御影堂與正殿之間立著一座高大的十三重石塔,現在已失去其中三層,成了十重塔,不過這是當初重建東大寺時,從宋朝請來的伊行末(※南宋時代浙江省寧波人,於鎌倉時代赴日,投入重建東大寺的工程。是日本石匠集團「伊派」的創始者。)所打造,基壇的正面刻有銘文。我記得東大寺門前的狛犬以及般若寺的石塔,也都是出自同一人之手,不過絲毫不帶中國風,是它的獨特之美,與周遭的景致以及建築也都充分融合。
這裡之所以會有這麼多鎌倉時代的建築,是因為當時寺院突然興盛,還是與東大寺有何關聯呢?它自古便是龍門七大寺之一,擁有許多所屬寺院和僧房,至今仍擁有數萬坪的廣大土地,可是卻鮮為人知,也沒有明確的歷史,當真令人費解。不過,或許就因為是這樣的地方,才有寺院的魅力。事物一旦變得過於清楚明白,反而引人懷疑,不如充滿謎團,這樣才讓人感興趣。至少對我來說,這麼美的寺院突然出現眼前,光是這樣,就覺得今天一天不算白活。
從大藏寺眺望烏之塒
可以望見一座很出色的高山與此寺相鄰。詢問後得知,此山名喚「烏之塒」。這一帶相當於神武天皇東征時的行經之路,所以可能是八咫烏之塒(※塒是鳥巢的意思。八咫烏是神武天皇東征時,受高皇產靈神和天照大神之命為天皇帶路的烏鴉,一般描繪為三隻腳的形象。),或是以烏鴉當圖騰的豪族居所,至今仍有許多烏鴉在此棲息。現在與大藏寺似乎已無直接關聯,不過根據我的經驗,凡是古寺皆與古代信仰緊密結合,這是具有濃厚日本色彩,饒富趣味的存在方式。在神佛混淆的思想下,天竺諸佛為了度化眾生,以日本神明的形象現身,但事實卻與之相反,應該是為了宣揚佛教,而需要借助日本神明的力量吧。雖然只有些許差異,但意義卻大不相同。若換個說法,以日本神明當經線,以佛教當緯線,以此編織而成的,正是所謂的本地垂跡說(※日本佛教興盛時期的一種思想。指稱日本神道的八百萬神是佛菩薩的化身,稱為權現。理論上神佛具有同等地位。)。不過對象是不會說話的木石,無法加以證明,但日本的大自然向我說明了這一切。此事至今仍沒多大的不同。提出條理分明的理論,這是外國傳來的方式,日本人心中只能默默聆聽。然而,默不作聲不表示就此屈服。長期以來支撐起外來思想和技術的,一直都是沉默不語的日本諸神。
坦白說,我雖然對大藏寺的環境和建築感到佩服,但是對裡頭的佛像卻不抱持期待。藤原時代的佛像良莠不一。我心裡原本認為,在這種深山之地不會有什麼多像樣的雕刻,但是當正殿的大門開啟時,我的想法徹底被顛覆。那佛像真是美。不過,它並非是多特別的雕刻,明顯是地方上的作品,但這當中帶有言語難以形容的純真,感覺得出它已超越時代或技術。臉部尤其美。以類似推古時代佛像的表情,從它那八尺八寸的身高,心無雜念的俯視,看起來比藤原時代初期的佛像更有古味。這種情況也常見於敦煌的雕刻中,由於這是鄉間作品,反而傳達出古時候的樣式。或許專家不認同,但比起完美無缺的佛像,我覺得這種佛像更易親近。正殿內的擺設我也很欣賞。不同於一般的寺院正殿,這裡沒添加多餘的裝飾,佛龕也造型簡樸,使得佛像更顯高大。在一點都不像密教的開放氛圍下,給人一種直接膜拜神佛之感。
天部形立像(大藏寺珍藏)
據寺傳記載,這尊藥師佛是以境內的一株大樟樹雕刻而成,也算是一種「立木信仰」。關於立木觀音,前面也曾提過,不過當我望著這尊佛像時,看到的不是雕刻,而是樹木的自然樣貌。事實上,當初雕刻的人們肯定也從樹木中學習到不少。像是木材的處理方式、對木紋的細膩用心等,沒半點違逆自然之處。就這層意涵來看,在金銅打造的佛像方面,就算是藥師寺三尊這樣的名作,也還沒能成為真正的日本作品。我們的祖先可說是在開始打造木雕後,才開始真正吸收了佛教思想。
正殿內供奉了同屬藤原時代的毘沙門天像。這又稱作兜跋毘沙門,聽說地方上的人們都稱呼它「神象先生」,我認為這才正確。佛像雖然右手托塔,但雙臂似乎都修補過,不論是臉部表情還是身體的僵硬模樣,都不太像佛像,反倒比較像神像。眾所皆知,不管再好的傑作,神像一定都會打造成僵硬的姿態,我向來都覺得很不可思議,不過,在那雕刻興盛的時代,我不認為這是因為技術不夠純熟使然。也不可能是粗製濫造。若是如此,會不會打從一開始就是仿效樹木來打造呢?坐像就像樹根一樣,而立像看起來就像活生生的樹木。雙手都深藏在衣袖裡,不論臉部表情還是身體,都拒絕呈現任何「動作」。這尊神象先生和藥師如來之所以給人類似這樣的印象,想必是因為在這遠離都城的鄉村裡,古代的自然信仰已根深蒂固。雖然不清楚作者為何人,但肯定是同一個人,或同一流派的人,與神社關係深厚。
境內出乎意料的寬敞。處處都有高大的高野金松聳立,從樹木間的縫隙可以望見「烏之塒」。這座山就像在追著我們跑,不管我們去哪兒,都一樣看得到它。與弘法大師有關的事物,除了修行場外,只留下掛衣服的松樹或加持過的泉水,不過這雄偉的金松說明了它與高野山的深厚關係。正殿後方的小山丘上有一座墓地。這裡是視野開闊的高臺,當中地勢特別高的墳塚上立著一座漂亮的五輪塔。上面有正平六年(一三五一年)的銘文,但就只知道是「南朝某貴人」的墳墓,不清楚是何身分。因為這一帶是南朝的大本營,所以也許是在某地戰死的地方豪士,在故鄉的寺院下葬。或者是某位身分更高的「貴人」在此過世。墓地面朝吉野的方向而建,看起來宛如死者的情感至今仍飄蕩在布滿青苔的石面上。總之,這肯定是一方大將,如今雖已化為無名的石塔,卻仍持續凝望吉野的天空,那模樣深深打動我心。
岡倉天心捐贈的弁事堂和殿內的地藏菩薩
臨行時,我們在僧房接受熱茶款待。這段時間,住持讓我們見識寶物。裡頭是藤原時代的大般若經。八百卷中遺失了四十四卷,但令人吃驚的是,這大部分都是手抄經文,底頁寫道「仁安二年(一一六七)四月五日於仁和寺宿所書寫了」,那工整的字體保有天平時代的風格。說到字體,寫著「大藏寺」的匾額也很美。這匾額是出自藤原大人的草書,經淺雕後在上頭塗上顏色,但現在顏色幾乎都已褪盡。這匾額是嵯峨天皇行幸大藏寺時賜贈之勅額,上頭刻有銘文「保延六年(一一四○)庚申五月二十八日幸未書之 從五位上寺宮內權大輔藤原定信」,定信是知名的書法家。但與嵯峨天皇的時代不符。也許是一開始的匾額破損,請定信重新揮毫。天皇遠道而來,這點也啟人疑竇,不過主佛藥師佛建造完成,應該是在天皇在位期間,而寺院的創立也大約是在那時候。這座寺院寶物眾多,除了前面所列舉的之外,還有藤原時代的地藏菩薩、大黑天的木雕像、板繪的佛畫等,我特別感興趣的是上面刻有永正十一年(一五一四)銘文的一張經卷桌。這是俗稱的寺子屋桌,但正因為年代久遠,別具韻味。而不經意的保有這樣的古物,也是遠離塵囂的山寺可貴之處。
僧房旁有一座茅草屋頂的小佛堂,名叫「弁事堂」。是岡倉天心(※日本明治時期的美術家、思想家。)捐贈,聽說天心與這座寺院的前任住持交好,時常到此地留宿。佛堂裡祭祀鎌倉時代收集來的一尊地藏菩薩,最近從這尊菩薩體內發現摺佛(※將佛或菩薩的圖像印在紙或布面上。),上頭寫有延應元年(一二三九)僧人長信及其他多位結緣者的名字。由於此地藏菩薩無處安置,所以天心才會建造這座佛堂吧。大藏寺是他很喜愛的寺院,雖然就只是因為這樣,但這故事卻深植我心。
回程時,我們走另一條路。寺院後方是一片迷人的山白竹林,穿過竹林後,眼前是一處往下的陡坡,走不到三十分鐘便來到了幹道。
「要不要順便小逛一下」,導演K先生說道。我求之不得,這麼一來,我對討厭的電視演出也才能多點期待。這一帶有許多我想去的地方。「那麼,就交給我負責吧」,我聽從他的建議,也沒問他要去哪兒,就此坐上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