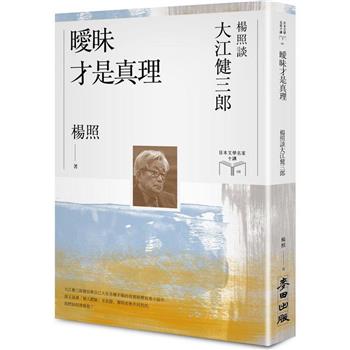走向漂浮靈魂的黑暗遠方
文/楊照
我知道伊丹十三早於閱讀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在美國留學時,校園裡有「卡本特電影中心」,在城裡有波士頓美術館的地下放映室,這兩地方的排片策展人中顯然有台灣新電影的影迷,幾年內我在那裡幾乎看完了侯孝賢、陳坤厚、楊德昌、萬仁等導演的主要作品。愛屋及烏,很自然地也對他們排出來的其他另類藝術電影有了信任與偏好。
就是在這兩個場地,接連先後看了伊丹十三執導的《葬禮》和《蒲公英》,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後誘發了好奇心,到「燕京圖書館」裡尋找相關資料,一下子找到了許多令我驚訝的日本現代歷史與文化線索。
知道了伊丹十三的父親是伊丹萬作,一位早在戰前就成名的日本導演,曾經被指派去協助拍攝和德國合作的電影。然而作為助導的伊丹萬作和德國導演意見不合、頻頻衝突,最後演變成「一部電影,各自表述」,拍出了兩個版本──德國版和日本版。這部奇特的電影其實是在時代風氣影響下,日本為了學習、模仿德國納粹式宣傳手法而安排的。這部電影的女主角是原節子。
連帶知道了,原節子在戰前崛起,和她的壯碩骨架外型有很大的關係。戰後經由小津安二郎的鏡頭畫面,原節子成了某種日本女性典型,然而剛跨入電影圈,原節子其實是以長得像西方人,尤其帶有德國風味美而受到重視的。還有,原節子和本名山口淑子的李香蘭同年出生,李香蘭同樣以不像日本人得到了銀幕上的獨特地位,她是日本人想像中的中國人形象代表。
類似的模稜、曖昧長相魅力,到了戰後,從不同方向又在伊丹十三身上發生過作用。在五十歲轉任導演之前,伊丹十三是國際名演員,出現在許多電影中。他是日本人,卻長得和西方人刻板印象中的日本人模樣大不相同,完全沒有那種矮小猥瑣的風格。伊丹十三俊美、大氣、開朗,卻又帶著明顯的東方輪廓,不會誤認為不純的混血來歷。劇本中如果有一個要讓西方觀眾立即留下正面第一印象的日本人角色,伊丹十三就是不二人選。甚至因為有伊丹十三,而使得西方電影擴大了對於日本人的想像發展空間,不再必然一出現就長得小鼻子小眼睛、矮個頭卻喜歡托大狂吼。
發現伊丹十三是一九八○年代後期,那時的台灣正從解嚴後掀動了一波又一波的「認同」爭議,「身分政治」成為最敏感也最激烈的社會動盪因素;而我所處的美國學院環境中,受到「後現代」文化思潮影響,多元身分同樣成為注目焦點,從種族、階級、宗教信仰等舊身分擴張到性別、性傾向、世代等新身分,每一項都存在著內外交煎的摩擦互動。如同滔滔洪流襲來的背景中,我很慶幸自己誤打誤撞進入一條很不一樣,密道般的路徑,探索、思考日本文化中的身分表現。
照道理說,日本是一個種族構成最單純的國家,而且還在政治傳統上建立了「萬世一系」的神話,在社會組織上長期保留嚴格的封建身分劃分,然而我卻發現了:即使是這樣的歷史構成都不可能沒有縫隙缺口,在日本的現代歷史中出現了多重多層次的縫隙缺口。
然後我讀到了大江健三郎的《聽雨樹的女人們》,被他迷宮般的日文眩惑,更對他的存在反思奇想感到佩服。於是開始追讀他的其他作品,讀到《個人的體驗》,還沒讀完前,已經覺得胸口彷彿被某種重物壓迫著,嚴重缺氧喘不過氣來。我原本不確定那種感覺從何而來,一度以為是自己的日文程度不夠,在他的語法語意間找不到路而產生的昏暈,但再繼續讀下去,隱約明白了真正的不適應是源自大江健三郎強調並實踐的「個人式體驗」寫法。
簡而言之,那是一種想盡辦法脫開身分,不依循任何身分規範行事,也就得不到任何身分屏障的思考與體驗,無法以常理描述形容的比赤裸裸更徹底的赤裸裸。裸露出孤伶伶擺盪漂浮靈魂的不堪樣貌。
不敢相信有人會用這種方式寫小說,用這種對自己最為殘忍不恤的方式運用虛構。然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明白放在眼前,不容不承認、不容不接受。
我必須承認,大江健三郎不是我特別喜歡的小說家,看到他明白地在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上唐突川端康成時,我毋寧是站在川端康成那一邊的。然而他卻是我認定非讀不可的小說家,至少我自己的態度很明確,即便預見讀他的作品會帶來什麼樣的不快不祥反應,我總是以近乎宿命、無從逃避的心情斷然翻開,用手指一行一行指著那絕不流暢的字句,專注地讀下去。
面對一位有勇氣寫出這種挑戰一切明晰答案,回歸真理曖昧性的作家,我們不能連閱讀與領受的勇氣都沒有。尤其當他挑戰的社會性答案,尤其是身分答案,其實帶有高度的普遍性,是我們共同的生活依據,那我們就更不該迴避他的痛切質疑了。
我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得知了大江健三郎和伊丹十三的情誼關係了,不過卻清楚記得二○○一年讀到《換取的孩子》原版書時,心中的糾結以及暗自決定。我決心拉著書中提供的思想線索,做好要走到漂浮靈魂黑暗遠方的準備,不懈地追蹤大江健三郎和伊丹十三的終極祕密,追到山窮水盡無路之處,並且將那裡最濛晦迷茫的身分曖昧狀況,盡可以記錄下來,讓更多人知道,引領更多人走這條路進入那個情境中。
而這本《曖昧才是真理》就是那份二十年前決心的遲來成果。
文/楊照
我知道伊丹十三早於閱讀大江健三郎的小說。在美國留學時,校園裡有「卡本特電影中心」,在城裡有波士頓美術館的地下放映室,這兩地方的排片策展人中顯然有台灣新電影的影迷,幾年內我在那裡幾乎看完了侯孝賢、陳坤厚、楊德昌、萬仁等導演的主要作品。愛屋及烏,很自然地也對他們排出來的其他另類藝術電影有了信任與偏好。
就是在這兩個場地,接連先後看了伊丹十三執導的《葬禮》和《蒲公英》,留下了深刻印象,然後誘發了好奇心,到「燕京圖書館」裡尋找相關資料,一下子找到了許多令我驚訝的日本現代歷史與文化線索。
知道了伊丹十三的父親是伊丹萬作,一位早在戰前就成名的日本導演,曾經被指派去協助拍攝和德國合作的電影。然而作為助導的伊丹萬作和德國導演意見不合、頻頻衝突,最後演變成「一部電影,各自表述」,拍出了兩個版本──德國版和日本版。這部奇特的電影其實是在時代風氣影響下,日本為了學習、模仿德國納粹式宣傳手法而安排的。這部電影的女主角是原節子。
連帶知道了,原節子在戰前崛起,和她的壯碩骨架外型有很大的關係。戰後經由小津安二郎的鏡頭畫面,原節子成了某種日本女性典型,然而剛跨入電影圈,原節子其實是以長得像西方人,尤其帶有德國風味美而受到重視的。還有,原節子和本名山口淑子的李香蘭同年出生,李香蘭同樣以不像日本人得到了銀幕上的獨特地位,她是日本人想像中的中國人形象代表。
類似的模稜、曖昧長相魅力,到了戰後,從不同方向又在伊丹十三身上發生過作用。在五十歲轉任導演之前,伊丹十三是國際名演員,出現在許多電影中。他是日本人,卻長得和西方人刻板印象中的日本人模樣大不相同,完全沒有那種矮小猥瑣的風格。伊丹十三俊美、大氣、開朗,卻又帶著明顯的東方輪廓,不會誤認為不純的混血來歷。劇本中如果有一個要讓西方觀眾立即留下正面第一印象的日本人角色,伊丹十三就是不二人選。甚至因為有伊丹十三,而使得西方電影擴大了對於日本人的想像發展空間,不再必然一出現就長得小鼻子小眼睛、矮個頭卻喜歡托大狂吼。
發現伊丹十三是一九八○年代後期,那時的台灣正從解嚴後掀動了一波又一波的「認同」爭議,「身分政治」成為最敏感也最激烈的社會動盪因素;而我所處的美國學院環境中,受到「後現代」文化思潮影響,多元身分同樣成為注目焦點,從種族、階級、宗教信仰等舊身分擴張到性別、性傾向、世代等新身分,每一項都存在著內外交煎的摩擦互動。如同滔滔洪流襲來的背景中,我很慶幸自己誤打誤撞進入一條很不一樣,密道般的路徑,探索、思考日本文化中的身分表現。
照道理說,日本是一個種族構成最單純的國家,而且還在政治傳統上建立了「萬世一系」的神話,在社會組織上長期保留嚴格的封建身分劃分,然而我卻發現了:即使是這樣的歷史構成都不可能沒有縫隙缺口,在日本的現代歷史中出現了多重多層次的縫隙缺口。
然後我讀到了大江健三郎的《聽雨樹的女人們》,被他迷宮般的日文眩惑,更對他的存在反思奇想感到佩服。於是開始追讀他的其他作品,讀到《個人的體驗》,還沒讀完前,已經覺得胸口彷彿被某種重物壓迫著,嚴重缺氧喘不過氣來。我原本不確定那種感覺從何而來,一度以為是自己的日文程度不夠,在他的語法語意間找不到路而產生的昏暈,但再繼續讀下去,隱約明白了真正的不適應是源自大江健三郎強調並實踐的「個人式體驗」寫法。
簡而言之,那是一種想盡辦法脫開身分,不依循任何身分規範行事,也就得不到任何身分屏障的思考與體驗,無法以常理描述形容的比赤裸裸更徹底的赤裸裸。裸露出孤伶伶擺盪漂浮靈魂的不堪樣貌。
不敢相信有人會用這種方式寫小說,用這種對自己最為殘忍不恤的方式運用虛構。然而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明白放在眼前,不容不承認、不容不接受。
我必須承認,大江健三郎不是我特別喜歡的小說家,看到他明白地在諾貝爾文學獎受獎演說上唐突川端康成時,我毋寧是站在川端康成那一邊的。然而他卻是我認定非讀不可的小說家,至少我自己的態度很明確,即便預見讀他的作品會帶來什麼樣的不快不祥反應,我總是以近乎宿命、無從逃避的心情斷然翻開,用手指一行一行指著那絕不流暢的字句,專注地讀下去。
面對一位有勇氣寫出這種挑戰一切明晰答案,回歸真理曖昧性的作家,我們不能連閱讀與領受的勇氣都沒有。尤其當他挑戰的社會性答案,尤其是身分答案,其實帶有高度的普遍性,是我們共同的生活依據,那我們就更不該迴避他的痛切質疑了。
我已經不記得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得知了大江健三郎和伊丹十三的情誼關係了,不過卻清楚記得二○○一年讀到《換取的孩子》原版書時,心中的糾結以及暗自決定。我決心拉著書中提供的思想線索,做好要走到漂浮靈魂黑暗遠方的準備,不懈地追蹤大江健三郎和伊丹十三的終極祕密,追到山窮水盡無路之處,並且將那裡最濛晦迷茫的身分曖昧狀況,盡可以記錄下來,讓更多人知道,引領更多人走這條路進入那個情境中。
而這本《曖昧才是真理》就是那份二十年前決心的遲來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