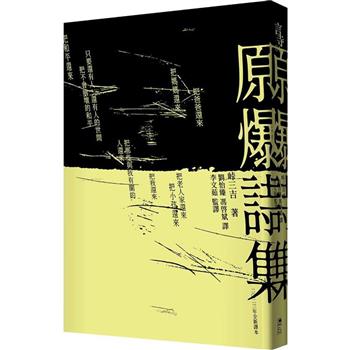〈序詩〉
把爸爸還來 把媽媽還來
把老人家還來
把小孩還來
把我還來 把那些與我有關的
人還來
只要還有人 還有人的世間
把不會崩壞的和平
把和平還來
〈八月六日〉
哪能忘得掉那道閃光
街頭三萬瞬間消失
在被壓碎的黑暗深淵裡
五萬悲鳴止息
黃色如漩渦般的煙淡去後
大樓崩裂、橋樑坍塌
滿員電車就那樣燒得焦黑
瓦礫與燼餘堆得無邊無際的廣島
未幾 皮膚如破布掛身
雙手抱胸
踩過迸裂的腦漿
腰間纏著燒焦布條的
一列裸身隊伍聚在一起邊哭邊走
練兵場的屍體像地藏石像般散亂
那為了從河岸爬向木筏而疊起的群體
在燒灼的日照下漸漸成為屍體
點亮黃昏的火光中
媽媽和弟弟被活埋的那一帶也
在延燒的火勢裡
兵工廠地板的屎尿裡
躺著逃難而來的女學生們
腹部腫脹的、單眼潰爛的、半身脫皮紅腫的、沒頭髮的
晨曦照著難以辨識誰是誰的群眾
四下已無動靜
彌漫的惡臭裡
只聞鐵盆附近徘徊的蒼蠅嗡嗡
哪能忘得掉那
遍佈在這三十萬的城市裡的寂靜
在那靜默之中
回不來的妻與子的白色眼窩
撕裂我們心神的
祈願
怎麼能忘得掉!?
〈死〉
!
耳朵深處號泣的聲音
默然變響
猛然撲來
在非比尋常的空間
煙塵彌漫
焦臭飄蕩間
狂奔的陰影
「啊
逃
得掉」
躍起的腰間
紅磚碎屑散落的
身體
正在燃燒
從背後推倒我的
熱風
在衣袖在肩頭
燃起火焰
在濃煙中抓住
水槽的混凝土邊緣
頭已經
在水裡
淋上水的衣服
沒有
燒焦破爛
電線木材鐵釘玻璃碎片
如浪的瓦牆
燃燒的指甲
腳踝脫落
鉛製的鈑金貼在背上
「嗚・嗚・嗚・嗚」
電線桿和土牆都
已被火
燻黑
火和煙的
漩渦
吹進破裂的頭殼
「小廣 小廣」
按住的乳房
啊 染血棉片的洞
倒地
──你、你、你、在哪
在匍匐前進的煙幕裡
會從哪裡出現啊
手牽手
轉啊轉啊跳著盂蘭盆舞的
裸身女孩們
在顛仆成一圈的
瓦片下
又是肩膀
沒有頭髮的老婦人
尖叫
像熱氣蒸騰噴出的痛苦高亢
路旁已是火焰搖曳
把肚子鼓得像太鼓
剝落到嘴脣的
紅色肉塊
抓住腳跟的手
滑溜地剝落
滾動的眼睛大叫
煮成白色的頭
手踏過的毛髮、腦漿
蒸騰的煙、撞擊的烈焰之風
在火花迸裂的黑暗裡
孩子的金色眼睛
燃燒的身體
燒灼的喉嚨
猛然折斷的
手臂
凹陷
肩
喔喔 再也
無法前進
在黑暗孤獨的深淵裡
太陽穴的巨響驟然遠去
啊啊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得
在路旁這種地方
也不在你身邊
為什麼
得死
在
這
?
把爸爸還來 把媽媽還來
把老人家還來
把小孩還來
把我還來 把那些與我有關的
人還來
只要還有人 還有人的世間
把不會崩壞的和平
把和平還來
〈八月六日〉
哪能忘得掉那道閃光
街頭三萬瞬間消失
在被壓碎的黑暗深淵裡
五萬悲鳴止息
黃色如漩渦般的煙淡去後
大樓崩裂、橋樑坍塌
滿員電車就那樣燒得焦黑
瓦礫與燼餘堆得無邊無際的廣島
未幾 皮膚如破布掛身
雙手抱胸
踩過迸裂的腦漿
腰間纏著燒焦布條的
一列裸身隊伍聚在一起邊哭邊走
練兵場的屍體像地藏石像般散亂
那為了從河岸爬向木筏而疊起的群體
在燒灼的日照下漸漸成為屍體
點亮黃昏的火光中
媽媽和弟弟被活埋的那一帶也
在延燒的火勢裡
兵工廠地板的屎尿裡
躺著逃難而來的女學生們
腹部腫脹的、單眼潰爛的、半身脫皮紅腫的、沒頭髮的
晨曦照著難以辨識誰是誰的群眾
四下已無動靜
彌漫的惡臭裡
只聞鐵盆附近徘徊的蒼蠅嗡嗡
哪能忘得掉那
遍佈在這三十萬的城市裡的寂靜
在那靜默之中
回不來的妻與子的白色眼窩
撕裂我們心神的
祈願
怎麼能忘得掉!?
〈死〉
!
耳朵深處號泣的聲音
默然變響
猛然撲來
在非比尋常的空間
煙塵彌漫
焦臭飄蕩間
狂奔的陰影
「啊
逃
得掉」
躍起的腰間
紅磚碎屑散落的
身體
正在燃燒
從背後推倒我的
熱風
在衣袖在肩頭
燃起火焰
在濃煙中抓住
水槽的混凝土邊緣
頭已經
在水裡
淋上水的衣服
沒有
燒焦破爛
電線木材鐵釘玻璃碎片
如浪的瓦牆
燃燒的指甲
腳踝脫落
鉛製的鈑金貼在背上
「嗚・嗚・嗚・嗚」
電線桿和土牆都
已被火
燻黑
火和煙的
漩渦
吹進破裂的頭殼
「小廣 小廣」
按住的乳房
啊 染血棉片的洞
倒地
──你、你、你、在哪
在匍匐前進的煙幕裡
會從哪裡出現啊
手牽手
轉啊轉啊跳著盂蘭盆舞的
裸身女孩們
在顛仆成一圈的
瓦片下
又是肩膀
沒有頭髮的老婦人
尖叫
像熱氣蒸騰噴出的痛苦高亢
路旁已是火焰搖曳
把肚子鼓得像太鼓
剝落到嘴脣的
紅色肉塊
抓住腳跟的手
滑溜地剝落
滾動的眼睛大叫
煮成白色的頭
手踏過的毛髮、腦漿
蒸騰的煙、撞擊的烈焰之風
在火花迸裂的黑暗裡
孩子的金色眼睛
燃燒的身體
燒灼的喉嚨
猛然折斷的
手臂
凹陷
肩
喔喔 再也
無法前進
在黑暗孤獨的深淵裡
太陽穴的巨響驟然遠去
啊啊
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我得
在路旁這種地方
也不在你身邊
為什麼
得死
在
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