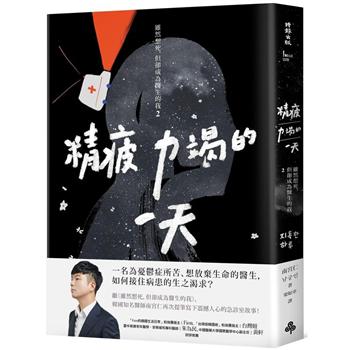劃出死亡瞬間的界線
醫學歸屬於科學的範疇,所謂科學大致上來說,就是描述特定的自然現象,並以客觀數值證明。因此,醫學院學生必讀的眾多教科書,大體上皆以下列方式進行陳述,「血壓的正常值收縮壓為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毫米汞柱(mmHg),舒張壓則為八十到九十毫米汞柱;如果比這數值低的話是低血壓,較高的話則為高血壓。」醫學以明確的方式將人體數值化,人類的血壓在一定的範圍之中,客觀地認定這些數值如何區分為正常與異常。
醫學院時期的學生必須背誦許多類似的理論內容,但當時的我總對其中一件事感到相當好奇。醫學終究是操縱人生死的一門學問,那麼在醫學上該怎麼用客觀的方式來陳述「死亡」或是「死亡的剎那」呢?人究竟在哪一個瞬間會被定義為「死亡」呢?我心中的疑問無法輕易地解開,那時的我仍不過是有很多東西要學習的學生,然而身為一個人,我所感受到對死亡根源性的好奇心絲毫沒有消失。當教科書裡提及「死亡」時,為了避免定義死亡,或是對死亡定義太過籠統的說明,通常以「死亡的可能性很高」或「也許會致死」的語言來表現,結果沒有任何一段文字可以痛快地消除我心中的疑問。我只能猜測成為醫生之後,才可能領悟到死亡的沉默真理吧。
曾經對死亡茫然的我成了在醫院工作的醫生,只要是有醫生執照的人,都可以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死亡宣告。不過,沒有經驗的人很難適切做出判斷,因此即使正式成為醫生,第一次遭遇病患的死亡仍須以旁觀者的身分,觀察其他有經驗的醫生進行宣告。第一次親眼目睹死亡的那一天,那時我才終於真正領悟「死亡瞬間」,也理解了為何教科書裡幾乎沒有提及「死亡瞬間」的理由。
那是一位接受腦部手術的重症患者,當他的心臟停止跳動之際,我馬上飛奔過去為他做心肺復甦術。我不停地反覆用力按壓他的胸口,沒有任何戲劇性的事情發生,時間只靜靜地流逝。負責指揮的住院醫生專注地看著監控螢幕,喃喃自語地說道:「兩次腦溢血手術,壓到了腦幹,一個月期間都沒有自主呼吸,心臟停止後二十六分鐘內都毫無反應。唉,現在看來已經不行了。」他皺著眉頭,突然抬起手看向手錶說:「死亡時間一點十八分。」就這樣,死亡的最初無法以任何明確界線劃分。一個人失去了意識與呼吸,心臟停止跳動,所有機能都停止了,在自然狀態下將這個人就這樣放置不管,不加以急救處置,也不會發生任何奇蹟,一定會死去。若沒有任何醫學上的幫助,心臟停止跳動與死亡其實是同義詞。如此,當失去生氣的心電圖顯示出水平直線的那一瞬間,就可說是人死亡的剎那;但在醫學上,並不會定義那一刻為死亡瞬間,因為透過醫學的努力與幫助,還是有可能把那個人救回來。
所謂的心肺復甦術,就是在體外對人的心臟反覆按壓的一種行為,即使心臟自主停止,若經由人為施予壓力反覆按壓,在某種程度上仍可以代替心臟功能。在勉強人體血液循環的狀況之下,如果可以找出心臟停止跳動的原因,並且予以矯正的話,就能讓患者的心臟重新自主跳動,這時我們會說這個人「活過來了」。
判斷死亡一個人與否,是綜合考慮患者心跳停止的狀態,斟酌目前所能採取的醫學處置與努力之後,確定這位接受心肺復甦術的患者絕對不可能有機會救回來的時候,所下的決定。救回來的可能性必須為零才行,若能毫不留戀地確信這一點,醫生即會停止所有的努力、宣告死亡。大致來說,心臟在停止跳動三十分鐘以上仍無法恢復自主心跳,同時處於無法恢復的無意識狀態,醫生就會出現放棄的念頭。有時明明就站在死亡的界線上,但過了一個小時的努力後,也可能再度回到他曾踩踏過的「生之地」;反之,當醫學上的努力完全停止的那一瞬間,希望回到了「無」,而患者必死無疑。所以在那一剎那,需要確信救回來的可能性為零才行,醫生經過如此苦思後,最終才能做出不治的宣告。
這判斷與宣告的職責交由最清楚這名患者的醫生全權決定,而死亡的那一瞬間也只限定由他一個人來判斷。甚至連正式的說法也沒有一定,「已經過世了」、「已經走了」、「死亡時間兩點二十三分」、「病人OOO現在已經過世了」、「雖然我們醫療團隊已經盡最大努力了,可是患者還是過世了。」這些全都是同樣的意思,只要聽這些話能夠理解,亡者現在已經永永遠遠離開自己身邊,不管說什麼都無濟於事。從不練唱的人
有一種人上KTV唱歌是抱著隨便唱唱的心態,別人要他唱他就唱,可是卻從來不練唱,即使唱得結結巴巴、節拍大亂他也不在乎。好玩的是,從不練唱的人幾乎做什麼事情都不太會自我要求,唱歌時他抱著歌有唱就好的心態,管他唱得好不好;上班時則抱著事情有做就好的心態,管他做得好不好。
做什麼事都不要求的人,在交朋友的時候自然也不會太過認真,除非別人主動跟他們連絡,否則他們就像斷了線的風箏般,輕飄飄地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
注重形象的人
有些人平日非常注重形象,然而,一旦碰到有表現的機會,就會不由自主地露出內在悶騷解放的一面。
有個朋友便是屬於悶騷解放型的人,每次剛開始唱歌的時候,他都會先找一大堆藉口說自己不會唱歌,譬如:「誰的歌唱得比我好多了,應該先請他獻聲才對。」
結果推來推去,好不容易說動他拿起麥克風,這下可不得了,他可以把周杰倫的歌從第一首唱到最後一首,嘴裡還不斷強調:「我今天喉嚨不舒服唱得不好。」言下之意是,如果他沒有身體微恙,表現會更加優異。
工作的時候也一樣,每次上司交付他一件新的任務,他都會先謙讓一番:「我何德何能可以擔任這麼重要的工作,某某某的能力比我強多了,他應該比我更適合這個任務。」
等到上司費盡唇舌證明他確實是負責這個任務的最佳人選,而他自己也決定好好表現一番時,那他便會把自己苦練多年的十八般武藝一樣一樣秀出來,而且邊秀還會邊說:「小弟在下不才我,做得不好請大家多多包涵。」
這種悶騷型的表現方式,可害苦了其他能力不及他的同事,試問:擁有十八般武藝的人都謙虛成這樣,那其他人該如何自處,無形中讓同仁陷入「表現焦慮」而不自知。
只唱某一類型歌的人
我認識一個朋友每次到KTV都只唱某種類型的歌,而且唱的時候全神投入,彷彿旁若無人,那種專注的模樣,真的讓人感動得想立刻頒一座最佳演唱獎給他。
通常,只唱自己喜歡的歌的人,工作時亦傾向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雖然唱歌時他們可以百分之百掌握主控權,愛唱誰的歌就唱誰的歌;不過,工作的時候可沒這麼自主,任他再堅持,依然得向現實妥協。專挑高難度歌唱的人
即使只是到KTV唱歌娛樂一下,也不是參加什麼唱歌比賽,他們也堅持要挑高難度或高水準的歌唱不可。
有一陣子有個很愛唱歌的朋友常常邀我去 PIANO BAR聽他唱歌,這個朋友不僅專挑高難度的歌唱,而且對唱歌的地點亦很挑剔。他覺得歌要唱得盡興,感覺要對才行,所以,他最痛恨在有人聊天、吃東西的KTV獻唱,那對他來說簡直是自找苦吃。
除此之外,這個朋友也很注意自己的台風,每次唱歌,他從咬字發音、臉部表情到肢體動作都配合得完美無缺,每每一曲唱罷,台下立刻響起如雷的掌聲。
專挑高難度歌唱的人,在做事的時候往往也喜歡挑困難度比較高的工作,他們最討厭做沒有表現空間的例行性公事。就像唱歌時,他們喜歡強調自己的品味出眾一樣,工作時他們也喜歡凸顯自己的能力,希望每完成一件工作都能獲得如雷的讚美聲,否則的話,他們就會覺得工作缺乏成就感,會越做越沒力氣。
選空檔唱歌的人
一大票人到KTV唱歌,有的人會緊握著麥克風不放,一曲接一曲,非唱到喉痛聲啞才肯放下麥克風;也有的人從不跟別人搶麥克風,只選在別人不唱的空檔唱首自己喜歡的歌,自得其樂一下。
通常會選在別人不唱的空檔唱歌的人,多半不擅於表現自己,唱歌的時候默默旁聽,工作的時候默默耕耘。這種型的人儘管做事腳踏實地,只可惜太過被動,萬一碰到大家興致高昂,完全沒有讓他表現的空檔,那他就只好從頭坐到底了。
覺得自己唱得最棒的人
有次應朋友之邀,擔任他們公司舉辦的KTV大賽的評審。原本我只是因為好玩而答應評分,不料到了現場,卻發現每個參賽者都全副武裝,每個人的臉上皆露出「我唱得最好」的表情。
其中有個自認長得很像某明星的帥哥,更在比賽前跑來跟我說「等下好好看我表現」我想,這麼有自信,大概有職業水準,沒想到他的歌聲只比我唱得好一點點。
比賽結束之後,這位帥哥的同事告訴我,不管做什麼事情他都認為「別人做得沒他好」,只有他最厲害,若事實如此那也就罷了,偏偏事與願違,這個自負的帥哥還好為人師,喜歡指導別人做這做那的,大家都很想知道,碰到這種自戀的人,要怎麼相處才不會被他搶光鋒頭。一開始決定要放棄急救這件事本身是相當困難辛苦的,因為這就像是在那一瞬間,我將這個人的全部希望統統都剝奪一般,即使腦海中已經將整個情況整理過後,確認在機率上不會發生的事情,也難以將這個想法從腦海裡抹去。這個人的死亡之中,難道沒有我的一丁點過失添加其中嗎?如果真是這樣,不管怎樣的努力都要再試試看不是嗎?難道奇蹟不會降臨在這人身上嗎?把這些可能成為變數的所有可能都想過了一遍,然後直到徹底絕望,判斷一個人死了,這件事本身就帶給人心理上極大的壓力。
戰勝這個想法與下定決心,醫生了解了不管自己開口做了死亡宣告前與後,亡者的狀態完全不會有所改變,但是這一切只是要有個人出面劃出這條界線,世界秩序才能正常運轉。這個人可能已經死了好一陣子了,但是必須得到醫生開口將放棄的話語吐出嘴的那一刻,這個人才能正式地成為死者。或許這條未知的界線,每次將人們劃分在生者與亡者的這條界線,最終是醫生必須要做的職責。
我至今仍然無法忘記自己第一次做出死亡宣告的那一瞬間,一位癌症患者在家中突然昏倒了,等到急救隊員趕到時心跳已停止了,當他被送到我面前時就是這樣的狀態。如家屬所言,他全身上下滿布著抗癌的各種痕跡,對一連串的醫療處置半點反應也沒有。我看著那一動也未動的僵直四肢,與這一片混亂中不停被按壓的胸口,第一次直覺該是宣判死亡宣告的時刻,但與此同時卻盈滿強烈的恐懼。
雖然身體忙碌又焦躁不停地動作,但第一次要下這樣的判斷,我仍在腦海中慎重再慎重地思考。心臟停止跳動,失去所有反應的狀態已過五十五分鐘了,不管期待奇蹟或是偶然,這個人要想重新返回這世界已經相當困難,即便如此,最後一刻我仍然猶豫不決。過了已經比一般心肺復甦術施行還要更長的時間、這一切我確定真的無法挽救的程度,但其實這個人好久之前就已死去了。
不過,清楚目睹所有過程的家屬們,絕對不會這樣想的。不久前仍一起聊天、深愛的人昏倒了,急救隊員疾速飛奔而來,毫不猶豫地施予心肺復甦術,馬上就送到醫院了,接手過後的醫護人員顯得苦惱,仍然繼續不停地按壓胸部,並且持續灌氣。對在一旁看著全部過程的人來說,內心抱持著期待是理所當然的。過了一會兒,我艱困地開了口,第一次宣告死亡。「兩點二十三分,我們醫療團隊盡了最大努力,但他仍然過世了。」在我說完話之前,他還是一個活人,但在我張嘴宣告他的死亡的那一瞬間,他成了死人。從家裡急急忙忙趕來的家屬們,由於那一瞬間降臨的死亡,全都感到極度悲傷,一下子嗚咽地痛哭失聲。
現在變成一具屍首的那個人,以及圍繞在他四周突然響起的哽咽哭聲,悲傷的冷空氣襲捲而來。在一群極度悲痛的人們之中,只有我要獨自裝作沒有任何情緒,很難撐過去。當死亡宣告從我口裡吐出,一吸氣,彷彿悲痛沉重的空氣充滿整個肺部,不知道怎麼回事,圍繞他的過去與現在,每一瞬間交織在腦海中,使我眼眶發熱、再也沒辦法說任何話了。從那時開始,無計可施的我只能努力讓自己變得遲鈍,但我也只不過是沒辦法忍受當下悲傷的一名凡人。那天我不自然地往房裡跑去,好一段時間沒辦法走出房門。
隨著時間流逝,我已經成為一個可以冷靜計算機率、對悲傷也有一套忍耐方法的平凡醫生。然而我仍本能地對宣告死亡的那瞬間感到恐懼,雖然是科學的瞬間,卻也是唯一無法交到科學手中負責的一刻:一個人由其他人在模糊不清的時間區塊裡,劃下的一條界線之下,成為了亡者。那毫無疑問必定使人沉浸於悲傷的一瞬間,往後的我仍會一直為這瞬間的命名繼續苦思煩惱著。
死亡是平等的嗎?
你問我,認為死亡是平等的嗎?……嗯,先分成兩個部分來談談吧。首先,醫學就是科學,所有的一切都得數值化、公式化、量化才行;死亡,也是如此。從非常時期開始就有許多科學家對死亡的過程與實際結果進行對照與研究,而現在透過醫學,我們獲得了預見死亡的驚人能力。醫院裡的醫生穿著白袍,成為了現代醫學的尖兵,放眼望去,死亡極其平等,我們就來談談這些吧。
某個像往常一樣在急診室工作的半夜,一位觀察死亡的學生問我:
「老師,人什麼時候會死呢?」
這是一個既常見、又概括而不具體、相當不怎麼樣的一個問題,就在我準備要開口責備這名學生的時候,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說真的,人,到底什麼時候才算死了?」
於是,我帶著這位學生到了安靜的醫務室,準備開始授課。在那之前,我已經做過無數次的死亡宣告,但卻從未對死亡做過概括性的整理。對於死亡,我以科學為立證,還有那些我個人做的死亡宣告,以及那時所感受到的瞬間,在腦海中一一展開,我開始對學生講起課來。
「基本上,休克的人就是死了,所有的休克定義,可以是下列五種型態之一:循環性休克、神經性休克、低血量性休克、過敏性休克(因為抗原─抗體免疫反應,而引發全身反應),還有敗血症。換句話說,如果發生了這五種不可逆的休克,人類一定會死去。當醫生遇上心臟停止跳動時,醫生必須要判斷患者的休克類型是哪一種,究竟是否存在可逆性?例如,頭部碎裂的人屬於神經性休克,大致來說是無法挽救的;四肢全部斷裂的人,屬於低血量性的休克,是有機會救回來的;心臟麻痺屬於循環性休克,也是有可能救回來的;而癌症末期雖然屬於複合性,但根據情況的不同,也有挽回生命的可能性。
包含上述在內,可逆性的心跳停止主要源自十一種可矯正因素(6H5T):缺氧、低溫、低血糖、低血容、高/低血鉀、酸中毒(人體血液呈現酸性狀態)、氣胸、心包填塞(心臟因外部因素而受到壓迫的狀態)、肺栓塞、冠狀動脈栓塞、毒素。這句話反過來說也代表著,這十一種因素能導致人類死亡,如果無法掌握心臟停止跳動的原因,醫生就需要將這十一種狀況全部納入考量範圍之中,尋求解決方法,如此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是,這不是單純在這十一種因素中尋找出一樣,就可以解決的事情,因為有可能同時存在兩、三種因素而引發狀況,所以必須找出造成現狀的根源才行。不過,到此為止仍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除了腦和心臟一旦受損,就會立即引發心臟停止跳動以外,人體中還有肝臟、腎臟、脾臟、胰臟、消化器官,與這些以外的其他附屬器官等所組成。醫學上也已清楚指出,當這些臟器一個個受損到某種程度而引發問題,也會進而造成生命危險。甚至當這些彼此密切關聯的內臟器官同時出現問題時,醫生可以預測這將會引發一連串相關的損傷,也能根據人體可承受的數值極限與綜合情況做出判斷,也可能與五種休克情況和十一種死亡因素相伴發生。對於這樣的情況,你還需要更多的學習與經驗,如此一來,你就會擁有一雙可以看見死亡的雙眼。」
這就是我講課的內容。學生聽著這突如其來、冗長煩悶的說明,顯得有些頭昏腦脹,但與其說是對學生講課,倒不如說是對我自己講課更貼近吧。總之,這可以說是身為早一步學習醫學的前輩所能做到、並且以極其科學性的科學家角度所發表的一堂講座吧。就連我自己也有些驚訝,因為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竟然已經處於一種以醫學方式、將死亡完美地整理妥當的狀態了。以這種方式在醫院工作的話,死亡在這樣的公式下將完全平等,不管是誰都無法脫離醫學學者所整理出來的經驗與公式,就算發生了例外,這也屬於醫學、科學可能發生的範疇裡。在這樣的公式中,沒有男女老幼之分,對於躺在醫院裡的人來說,適用的物理法則也只有醫學。不管是誰,只要踏出高高在上的神所規定的範圍之外,就只有死路一條。就連身為一名凡人的我都能預測的所謂「死亡」,還真是平等到令身為醫學學者的我不悅的程度。
不過令人感到羞愧的是,我同時也是一名寫作的人,如果我一直根深蒂固地認為「死亡是平等的」,也許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會提筆寫作了。醫生幾乎住在醫院裡,但患者的生活並非只在醫院,患者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外生活著,出了什麼意外才會來醫院就診。而由於職業的關係,每天看著蜂擁而入的患者們,醫生很容易就對死亡的偶然性感到麻痺,因為醫生們在一天之內,得以科學的方式重複不斷地對死亡做出解釋,機械般地處理好幾次的死亡。
我身處這個夾縫之中,或許自然而然地會想起那理所當然的法則。從地鐵上掉下來的老人,截斷了兩條腿而活了下來;從一樣高度跌下來的兄妹,結果一個死了,另一個卻活了下來;看起來可能立即就要死去的癌症末期患者,勉強地撐到明天才離世,面對這類例子,我們能只用物理法則來解釋人類史上最戲劇化的死亡嗎?死亡的橫行霸道與其殘忍的形象、驚人的突發性,以及緊密連結的悲傷特質,使得死亡自古以來總被戲劇化與神格化。死亡,從一開始就擁有著無法說是平等的性質。
「死亡,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平等的嗎?」一開始會想提出這樣的疑問,我認為是因為我們很容易只從側面角度去觀看死亡。就算人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也不會在同一個時間死去。關於死亡,討論仍然會繼續下去。如果死亡最終無法迴避、也無法預測的話,那麼一開始關於死亡是否平等的二分法問題,不就顯得沒有意義嗎?即使如此,在這理所當然的問題面前,我也只能低下頭來,於是直至今日,我仍提筆寫著關於死亡的思考。
醫學歸屬於科學的範疇,所謂科學大致上來說,就是描述特定的自然現象,並以客觀數值證明。因此,醫學院學生必讀的眾多教科書,大體上皆以下列方式進行陳述,「血壓的正常值收縮壓為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毫米汞柱(mmHg),舒張壓則為八十到九十毫米汞柱;如果比這數值低的話是低血壓,較高的話則為高血壓。」醫學以明確的方式將人體數值化,人類的血壓在一定的範圍之中,客觀地認定這些數值如何區分為正常與異常。
醫學院時期的學生必須背誦許多類似的理論內容,但當時的我總對其中一件事感到相當好奇。醫學終究是操縱人生死的一門學問,那麼在醫學上該怎麼用客觀的方式來陳述「死亡」或是「死亡的剎那」呢?人究竟在哪一個瞬間會被定義為「死亡」呢?我心中的疑問無法輕易地解開,那時的我仍不過是有很多東西要學習的學生,然而身為一個人,我所感受到對死亡根源性的好奇心絲毫沒有消失。當教科書裡提及「死亡」時,為了避免定義死亡,或是對死亡定義太過籠統的說明,通常以「死亡的可能性很高」或「也許會致死」的語言來表現,結果沒有任何一段文字可以痛快地消除我心中的疑問。我只能猜測成為醫生之後,才可能領悟到死亡的沉默真理吧。
曾經對死亡茫然的我成了在醫院工作的醫生,只要是有醫生執照的人,都可以做出具有法律效力的死亡宣告。不過,沒有經驗的人很難適切做出判斷,因此即使正式成為醫生,第一次遭遇病患的死亡仍須以旁觀者的身分,觀察其他有經驗的醫生進行宣告。第一次親眼目睹死亡的那一天,那時我才終於真正領悟「死亡瞬間」,也理解了為何教科書裡幾乎沒有提及「死亡瞬間」的理由。
那是一位接受腦部手術的重症患者,當他的心臟停止跳動之際,我馬上飛奔過去為他做心肺復甦術。我不停地反覆用力按壓他的胸口,沒有任何戲劇性的事情發生,時間只靜靜地流逝。負責指揮的住院醫生專注地看著監控螢幕,喃喃自語地說道:「兩次腦溢血手術,壓到了腦幹,一個月期間都沒有自主呼吸,心臟停止後二十六分鐘內都毫無反應。唉,現在看來已經不行了。」他皺著眉頭,突然抬起手看向手錶說:「死亡時間一點十八分。」就這樣,死亡的最初無法以任何明確界線劃分。一個人失去了意識與呼吸,心臟停止跳動,所有機能都停止了,在自然狀態下將這個人就這樣放置不管,不加以急救處置,也不會發生任何奇蹟,一定會死去。若沒有任何醫學上的幫助,心臟停止跳動與死亡其實是同義詞。如此,當失去生氣的心電圖顯示出水平直線的那一瞬間,就可說是人死亡的剎那;但在醫學上,並不會定義那一刻為死亡瞬間,因為透過醫學的努力與幫助,還是有可能把那個人救回來。
所謂的心肺復甦術,就是在體外對人的心臟反覆按壓的一種行為,即使心臟自主停止,若經由人為施予壓力反覆按壓,在某種程度上仍可以代替心臟功能。在勉強人體血液循環的狀況之下,如果可以找出心臟停止跳動的原因,並且予以矯正的話,就能讓患者的心臟重新自主跳動,這時我們會說這個人「活過來了」。
判斷死亡一個人與否,是綜合考慮患者心跳停止的狀態,斟酌目前所能採取的醫學處置與努力之後,確定這位接受心肺復甦術的患者絕對不可能有機會救回來的時候,所下的決定。救回來的可能性必須為零才行,若能毫不留戀地確信這一點,醫生即會停止所有的努力、宣告死亡。大致來說,心臟在停止跳動三十分鐘以上仍無法恢復自主心跳,同時處於無法恢復的無意識狀態,醫生就會出現放棄的念頭。有時明明就站在死亡的界線上,但過了一個小時的努力後,也可能再度回到他曾踩踏過的「生之地」;反之,當醫學上的努力完全停止的那一瞬間,希望回到了「無」,而患者必死無疑。所以在那一剎那,需要確信救回來的可能性為零才行,醫生經過如此苦思後,最終才能做出不治的宣告。
這判斷與宣告的職責交由最清楚這名患者的醫生全權決定,而死亡的那一瞬間也只限定由他一個人來判斷。甚至連正式的說法也沒有一定,「已經過世了」、「已經走了」、「死亡時間兩點二十三分」、「病人OOO現在已經過世了」、「雖然我們醫療團隊已經盡最大努力了,可是患者還是過世了。」這些全都是同樣的意思,只要聽這些話能夠理解,亡者現在已經永永遠遠離開自己身邊,不管說什麼都無濟於事。從不練唱的人
有一種人上KTV唱歌是抱著隨便唱唱的心態,別人要他唱他就唱,可是卻從來不練唱,即使唱得結結巴巴、節拍大亂他也不在乎。好玩的是,從不練唱的人幾乎做什麼事情都不太會自我要求,唱歌時他抱著歌有唱就好的心態,管他唱得好不好;上班時則抱著事情有做就好的心態,管他做得好不好。
做什麼事都不要求的人,在交朋友的時候自然也不會太過認真,除非別人主動跟他們連絡,否則他們就像斷了線的風箏般,輕飄飄地不知道飛到哪裡去了。
注重形象的人
有些人平日非常注重形象,然而,一旦碰到有表現的機會,就會不由自主地露出內在悶騷解放的一面。
有個朋友便是屬於悶騷解放型的人,每次剛開始唱歌的時候,他都會先找一大堆藉口說自己不會唱歌,譬如:「誰的歌唱得比我好多了,應該先請他獻聲才對。」
結果推來推去,好不容易說動他拿起麥克風,這下可不得了,他可以把周杰倫的歌從第一首唱到最後一首,嘴裡還不斷強調:「我今天喉嚨不舒服唱得不好。」言下之意是,如果他沒有身體微恙,表現會更加優異。
工作的時候也一樣,每次上司交付他一件新的任務,他都會先謙讓一番:「我何德何能可以擔任這麼重要的工作,某某某的能力比我強多了,他應該比我更適合這個任務。」
等到上司費盡唇舌證明他確實是負責這個任務的最佳人選,而他自己也決定好好表現一番時,那他便會把自己苦練多年的十八般武藝一樣一樣秀出來,而且邊秀還會邊說:「小弟在下不才我,做得不好請大家多多包涵。」
這種悶騷型的表現方式,可害苦了其他能力不及他的同事,試問:擁有十八般武藝的人都謙虛成這樣,那其他人該如何自處,無形中讓同仁陷入「表現焦慮」而不自知。
只唱某一類型歌的人
我認識一個朋友每次到KTV都只唱某種類型的歌,而且唱的時候全神投入,彷彿旁若無人,那種專注的模樣,真的讓人感動得想立刻頒一座最佳演唱獎給他。
通常,只唱自己喜歡的歌的人,工作時亦傾向做自己感興趣的事情。雖然唱歌時他們可以百分之百掌握主控權,愛唱誰的歌就唱誰的歌;不過,工作的時候可沒這麼自主,任他再堅持,依然得向現實妥協。專挑高難度歌唱的人
即使只是到KTV唱歌娛樂一下,也不是參加什麼唱歌比賽,他們也堅持要挑高難度或高水準的歌唱不可。
有一陣子有個很愛唱歌的朋友常常邀我去 PIANO BAR聽他唱歌,這個朋友不僅專挑高難度的歌唱,而且對唱歌的地點亦很挑剔。他覺得歌要唱得盡興,感覺要對才行,所以,他最痛恨在有人聊天、吃東西的KTV獻唱,那對他來說簡直是自找苦吃。
除此之外,這個朋友也很注意自己的台風,每次唱歌,他從咬字發音、臉部表情到肢體動作都配合得完美無缺,每每一曲唱罷,台下立刻響起如雷的掌聲。
專挑高難度歌唱的人,在做事的時候往往也喜歡挑困難度比較高的工作,他們最討厭做沒有表現空間的例行性公事。就像唱歌時,他們喜歡強調自己的品味出眾一樣,工作時他們也喜歡凸顯自己的能力,希望每完成一件工作都能獲得如雷的讚美聲,否則的話,他們就會覺得工作缺乏成就感,會越做越沒力氣。
選空檔唱歌的人
一大票人到KTV唱歌,有的人會緊握著麥克風不放,一曲接一曲,非唱到喉痛聲啞才肯放下麥克風;也有的人從不跟別人搶麥克風,只選在別人不唱的空檔唱首自己喜歡的歌,自得其樂一下。
通常會選在別人不唱的空檔唱歌的人,多半不擅於表現自己,唱歌的時候默默旁聽,工作的時候默默耕耘。這種型的人儘管做事腳踏實地,只可惜太過被動,萬一碰到大家興致高昂,完全沒有讓他表現的空檔,那他就只好從頭坐到底了。
覺得自己唱得最棒的人
有次應朋友之邀,擔任他們公司舉辦的KTV大賽的評審。原本我只是因為好玩而答應評分,不料到了現場,卻發現每個參賽者都全副武裝,每個人的臉上皆露出「我唱得最好」的表情。
其中有個自認長得很像某明星的帥哥,更在比賽前跑來跟我說「等下好好看我表現」我想,這麼有自信,大概有職業水準,沒想到他的歌聲只比我唱得好一點點。
比賽結束之後,這位帥哥的同事告訴我,不管做什麼事情他都認為「別人做得沒他好」,只有他最厲害,若事實如此那也就罷了,偏偏事與願違,這個自負的帥哥還好為人師,喜歡指導別人做這做那的,大家都很想知道,碰到這種自戀的人,要怎麼相處才不會被他搶光鋒頭。一開始決定要放棄急救這件事本身是相當困難辛苦的,因為這就像是在那一瞬間,我將這個人的全部希望統統都剝奪一般,即使腦海中已經將整個情況整理過後,確認在機率上不會發生的事情,也難以將這個想法從腦海裡抹去。這個人的死亡之中,難道沒有我的一丁點過失添加其中嗎?如果真是這樣,不管怎樣的努力都要再試試看不是嗎?難道奇蹟不會降臨在這人身上嗎?把這些可能成為變數的所有可能都想過了一遍,然後直到徹底絕望,判斷一個人死了,這件事本身就帶給人心理上極大的壓力。
戰勝這個想法與下定決心,醫生了解了不管自己開口做了死亡宣告前與後,亡者的狀態完全不會有所改變,但是這一切只是要有個人出面劃出這條界線,世界秩序才能正常運轉。這個人可能已經死了好一陣子了,但是必須得到醫生開口將放棄的話語吐出嘴的那一刻,這個人才能正式地成為死者。或許這條未知的界線,每次將人們劃分在生者與亡者的這條界線,最終是醫生必須要做的職責。
我至今仍然無法忘記自己第一次做出死亡宣告的那一瞬間,一位癌症患者在家中突然昏倒了,等到急救隊員趕到時心跳已停止了,當他被送到我面前時就是這樣的狀態。如家屬所言,他全身上下滿布著抗癌的各種痕跡,對一連串的醫療處置半點反應也沒有。我看著那一動也未動的僵直四肢,與這一片混亂中不停被按壓的胸口,第一次直覺該是宣判死亡宣告的時刻,但與此同時卻盈滿強烈的恐懼。
雖然身體忙碌又焦躁不停地動作,但第一次要下這樣的判斷,我仍在腦海中慎重再慎重地思考。心臟停止跳動,失去所有反應的狀態已過五十五分鐘了,不管期待奇蹟或是偶然,這個人要想重新返回這世界已經相當困難,即便如此,最後一刻我仍然猶豫不決。過了已經比一般心肺復甦術施行還要更長的時間、這一切我確定真的無法挽救的程度,但其實這個人好久之前就已死去了。
不過,清楚目睹所有過程的家屬們,絕對不會這樣想的。不久前仍一起聊天、深愛的人昏倒了,急救隊員疾速飛奔而來,毫不猶豫地施予心肺復甦術,馬上就送到醫院了,接手過後的醫護人員顯得苦惱,仍然繼續不停地按壓胸部,並且持續灌氣。對在一旁看著全部過程的人來說,內心抱持著期待是理所當然的。過了一會兒,我艱困地開了口,第一次宣告死亡。「兩點二十三分,我們醫療團隊盡了最大努力,但他仍然過世了。」在我說完話之前,他還是一個活人,但在我張嘴宣告他的死亡的那一瞬間,他成了死人。從家裡急急忙忙趕來的家屬們,由於那一瞬間降臨的死亡,全都感到極度悲傷,一下子嗚咽地痛哭失聲。
現在變成一具屍首的那個人,以及圍繞在他四周突然響起的哽咽哭聲,悲傷的冷空氣襲捲而來。在一群極度悲痛的人們之中,只有我要獨自裝作沒有任何情緒,很難撐過去。當死亡宣告從我口裡吐出,一吸氣,彷彿悲痛沉重的空氣充滿整個肺部,不知道怎麼回事,圍繞他的過去與現在,每一瞬間交織在腦海中,使我眼眶發熱、再也沒辦法說任何話了。從那時開始,無計可施的我只能努力讓自己變得遲鈍,但我也只不過是沒辦法忍受當下悲傷的一名凡人。那天我不自然地往房裡跑去,好一段時間沒辦法走出房門。
隨著時間流逝,我已經成為一個可以冷靜計算機率、對悲傷也有一套忍耐方法的平凡醫生。然而我仍本能地對宣告死亡的那瞬間感到恐懼,雖然是科學的瞬間,卻也是唯一無法交到科學手中負責的一刻:一個人由其他人在模糊不清的時間區塊裡,劃下的一條界線之下,成為了亡者。那毫無疑問必定使人沉浸於悲傷的一瞬間,往後的我仍會一直為這瞬間的命名繼續苦思煩惱著。
死亡是平等的嗎?
你問我,認為死亡是平等的嗎?……嗯,先分成兩個部分來談談吧。首先,醫學就是科學,所有的一切都得數值化、公式化、量化才行;死亡,也是如此。從非常時期開始就有許多科學家對死亡的過程與實際結果進行對照與研究,而現在透過醫學,我們獲得了預見死亡的驚人能力。醫院裡的醫生穿著白袍,成為了現代醫學的尖兵,放眼望去,死亡極其平等,我們就來談談這些吧。
某個像往常一樣在急診室工作的半夜,一位觀察死亡的學生問我:
「老師,人什麼時候會死呢?」
這是一個既常見、又概括而不具體、相當不怎麼樣的一個問題,就在我準備要開口責備這名學生的時候,腦中突然閃過一個念頭:「說真的,人,到底什麼時候才算死了?」
於是,我帶著這位學生到了安靜的醫務室,準備開始授課。在那之前,我已經做過無數次的死亡宣告,但卻從未對死亡做過概括性的整理。對於死亡,我以科學為立證,還有那些我個人做的死亡宣告,以及那時所感受到的瞬間,在腦海中一一展開,我開始對學生講起課來。
「基本上,休克的人就是死了,所有的休克定義,可以是下列五種型態之一:循環性休克、神經性休克、低血量性休克、過敏性休克(因為抗原─抗體免疫反應,而引發全身反應),還有敗血症。換句話說,如果發生了這五種不可逆的休克,人類一定會死去。當醫生遇上心臟停止跳動時,醫生必須要判斷患者的休克類型是哪一種,究竟是否存在可逆性?例如,頭部碎裂的人屬於神經性休克,大致來說是無法挽救的;四肢全部斷裂的人,屬於低血量性的休克,是有機會救回來的;心臟麻痺屬於循環性休克,也是有可能救回來的;而癌症末期雖然屬於複合性,但根據情況的不同,也有挽回生命的可能性。
包含上述在內,可逆性的心跳停止主要源自十一種可矯正因素(6H5T):缺氧、低溫、低血糖、低血容、高/低血鉀、酸中毒(人體血液呈現酸性狀態)、氣胸、心包填塞(心臟因外部因素而受到壓迫的狀態)、肺栓塞、冠狀動脈栓塞、毒素。這句話反過來說也代表著,這十一種因素能導致人類死亡,如果無法掌握心臟停止跳動的原因,醫生就需要將這十一種狀況全部納入考量範圍之中,尋求解決方法,如此才能挽救患者的生命。但是,這不是單純在這十一種因素中尋找出一樣,就可以解決的事情,因為有可能同時存在兩、三種因素而引發狀況,所以必須找出造成現狀的根源才行。不過,到此為止仍只不過是紙上談兵罷了。除了腦和心臟一旦受損,就會立即引發心臟停止跳動以外,人體中還有肝臟、腎臟、脾臟、胰臟、消化器官,與這些以外的其他附屬器官等所組成。醫學上也已清楚指出,當這些臟器一個個受損到某種程度而引發問題,也會進而造成生命危險。甚至當這些彼此密切關聯的內臟器官同時出現問題時,醫生可以預測這將會引發一連串相關的損傷,也能根據人體可承受的數值極限與綜合情況做出判斷,也可能與五種休克情況和十一種死亡因素相伴發生。對於這樣的情況,你還需要更多的學習與經驗,如此一來,你就會擁有一雙可以看見死亡的雙眼。」
這就是我講課的內容。學生聽著這突如其來、冗長煩悶的說明,顯得有些頭昏腦脹,但與其說是對學生講課,倒不如說是對我自己講課更貼近吧。總之,這可以說是身為早一步學習醫學的前輩所能做到、並且以極其科學性的科學家角度所發表的一堂講座吧。就連我自己也有些驚訝,因為在不知不覺之中,我竟然已經處於一種以醫學方式、將死亡完美地整理妥當的狀態了。以這種方式在醫院工作的話,死亡在這樣的公式下將完全平等,不管是誰都無法脫離醫學學者所整理出來的經驗與公式,就算發生了例外,這也屬於醫學、科學可能發生的範疇裡。在這樣的公式中,沒有男女老幼之分,對於躺在醫院裡的人來說,適用的物理法則也只有醫學。不管是誰,只要踏出高高在上的神所規定的範圍之外,就只有死路一條。就連身為一名凡人的我都能預測的所謂「死亡」,還真是平等到令身為醫學學者的我不悅的程度。
不過令人感到羞愧的是,我同時也是一名寫作的人,如果我一直根深蒂固地認為「死亡是平等的」,也許打從一開始我就不會提筆寫作了。醫生幾乎住在醫院裡,但患者的生活並非只在醫院,患者大部分時間都在醫院外生活著,出了什麼意外才會來醫院就診。而由於職業的關係,每天看著蜂擁而入的患者們,醫生很容易就對死亡的偶然性感到麻痺,因為醫生們在一天之內,得以科學的方式重複不斷地對死亡做出解釋,機械般地處理好幾次的死亡。
我身處這個夾縫之中,或許自然而然地會想起那理所當然的法則。從地鐵上掉下來的老人,截斷了兩條腿而活了下來;從一樣高度跌下來的兄妹,結果一個死了,另一個卻活了下來;看起來可能立即就要死去的癌症末期患者,勉強地撐到明天才離世,面對這類例子,我們能只用物理法則來解釋人類史上最戲劇化的死亡嗎?死亡的橫行霸道與其殘忍的形象、驚人的突發性,以及緊密連結的悲傷特質,使得死亡自古以來總被戲劇化與神格化。死亡,從一開始就擁有著無法說是平等的性質。
「死亡,對於任何人來說都是平等的嗎?」一開始會想提出這樣的疑問,我認為是因為我們很容易只從側面角度去觀看死亡。就算人在同年同月同日同時出生,也不會在同一個時間死去。關於死亡,討論仍然會繼續下去。如果死亡最終無法迴避、也無法預測的話,那麼一開始關於死亡是否平等的二分法問題,不就顯得沒有意義嗎?即使如此,在這理所當然的問題面前,我也只能低下頭來,於是直至今日,我仍提筆寫著關於死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