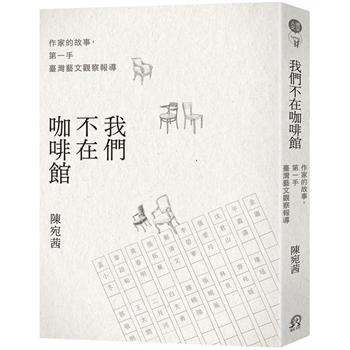金庸為什麼寫不出傳記
颱風前一天過境,香港維多利亞海港恢復風平浪靜,湛藍的海水裹著一層淡淡的薄霧,彷彿一面帶著滄桑的鏡子。八十多歲的金庸坐在明河社窗邊,一邊眺望波光中靜止的船帆,一邊意興遄飛地說起他創辦明報的經歷,跌宕起伏的故事不輸給他筆下的武俠小說。
文革初期,金庸白天寫社論批判翻江覆海的政治浪潮,晚上寫武俠小說「笑傲江湖」連載創造另一個江湖。金學專家說,「笑傲江湖」裡的人物都是兩岸政治人物的隱喻。但金庸不承認,只是笑呵呵地告訴我當年他行走江湖的凶險:「我在暗殺榜上排第二,第一名林彬已壯烈成仁。香港政府派警察在報館、家門前保護我,還給我十四個假車牌替換,讓歹徒跟蹤不到我的車。」
他說,這是一生中最懷念的時光。
我鼓起勇氣問他,這一生,你是否有過遺憾的時刻?
金庸辭世後,好友倪匡為他編了一本書,收錄親友談金庸的紀錄。書中,金庸幼女查傳納表示,父親不喜歡別人為他寫傳記,「他的小說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寫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經歷。」
關於金庸的傳記不少,卻沒一本獲得金庸授權或認可。金庸不寫傳記、也不僅不喜歡別人為他寫傳記、甚至差點把為他寫傳記的人告上公堂。像金庸這樣名動八方、走過大時代的作家與報人,卻沒留下一本官方認證的傳記或回憶錄,用自己的角度來看自己的一生和這個時代,在華人的文學史和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金庸為什麼不寫傳記?這在我心中是一個謎。
多年前,一個風狂雨驟的颱風夜,我接到了一通神秘的電話。電話中朋友說,一位朋友急需聯絡金庸,希望我代為幫忙。接著告訴我,一件現在想來仍覺不可思議之事。
朋友說,金庸大兒子查傳俠的前女友自殺了。這位女子卅年前和查傳俠在美國相戀,兩人爭吵後查傳俠跳樓身亡。她之後結婚生子,兒子跟當年自殺的查傳俠一樣,剛剛申請上一間美國長春藤名校。母親卻選在兒子金榜題名那一年自殺,離查傳俠辭世,足足過了卅年。
朋友希望我代為連絡金庸,告訴他兒子女友的消息。這位女子一直想告訴金庸,他的兒子不是為她而死;希望她離開人世後,這訊息能夠傳遞給金庸,了了她鬱結幾十年的心願。
在情人死後卅年殉情,這是甚麼樣的愛情?這卅年來,她又背負甚麼樣的心情,度過自己的人生?
我聽了震撼不已,立刻透過管道告知金庸此事,將朋友的聯絡電話轉了出去。
關於查傳俠之死,這是我第一次聽聞。我立刻上網,從零碎的網路八卦中一點一滴拼湊金庸的家庭故事。
網上說,查傳俠是金庸最引以為傲的兒子,和父親一樣從小展露傲人的寫作才華。他大學申請上美國常春藤名校,卻在上大學的第一年、人生最燦爛的青春年華,跟女友吵架後跳樓身亡。
他沒有留下遺書,自殺的原因成謎。一說是和女友吵架,負氣自殺;一說是憂憤父母離婚,以死明志。
我查不到金庸談兒子早夭的言論,但找到他在「倚天屠龍記」單行本的後記:
「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之情,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也太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那篇後記,正是查傳俠自殺後半年內所寫。
網上說,金庸在兒子自殺後,潛心研究佛經。
我又在網上查到關於查傳俠母親朱玫的八卦。朱玫是金庸第二任太太,和金庸都是記者出身,兩人一起打造明報報業王國,生了二子二女,卻不能白頭到老。
形容金庸每本小說都是人生經歷的么女查傳納,認為母親就是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的霍青桐:「我媽媽上街打扮得很漂亮,煮飯很好吃,工作能幹,但就是太叻(能幹)了。女人可以好叻,但在男人面前,都要留一留。」書劍恩仇錄裡的霍青桐,打仗勇智過人,談情說愛卻輸給香香公主。
現實中的霍青桐,晚年貧病交迫,死時身邊沒有親人,還是醫院工作人員為她申請死亡證,和金庸晚年的風光形成強烈對比。據說,金庸從記者口中得知此事後淚流滿面,悲嘆「我對不起我的家人」。
金庸未曾留下一本他認證的官方傳記,這些網路上流傳的八卦,缺乏金庸本人的說法,僅止於八卦。
關於這通颱風夜的奇異電話,我沒有進一步向金庸求證,也不打算將它寫成報導。我無法開口向一位年邁的父親詢問,愛子的自殺是不是他一手造成;也不願這塵封了卅年的往事,讓大俠到了暮年還要陷入世人的八卦陣。
這通電話成為我和金庸之間的一個秘密。
又過了一兩年,我得到金庸的允許,到香港採訪他。
那是一個颱風剛剛結束的晴天,我來到位於維多利亞港畔的明河社,拜訪剛完成三修作品壯舉的金庸。此時的金庸正準備全心投入劍橋大學的歷史碩士學位,當歷史學者,是他從小的心願。
或許是放下了長久懸在心頭的大石,又要開始追求年少的夢想,那一天,金庸對我敞開了心防,回憶起波瀾壯闊的一生。話題圍繞在他一生最懷念的時光、經營明報最艱困的時期。金庸興致勃勃地談起,他如何在詭譎肅殺的政治江湖中,執筆為劍,揮灑出自己的江山。
我想起那一通電話,鼓足勇氣問金庸:這一生,你是否有過遺憾的時刻?
金庸頓住了。他不置一詞,只是把眼光移向窗外,凝視著維多利亞港裡靜止的船帆,眼神神秘而深沉。那一整個下午,他始終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跟著金庸的目光望向遠處的維多利亞港。風雨已經過去,恢復平靜的海面,應當埋伏著深深的潛流吧。一生笑傲江湖的大俠、外人眼中功成名就的人生勝利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道靜靜的伏流,不容外人挖掘,甚至連自己都不敢碰觸。
金庸的傳記,始終沒寫出來。
隨著金庸的辭世,那一通神秘的電話,那一個下午金庸深沉的眼神,沉入如海水般幽深的時間之中。
關於那通電話的真相、世人的流言蜚語,關於愛情與親情,選擇與遺憾,金庸不曾留下任何一字一句。從此,我們只能從金庸的十五本小說中,從陳家洛、郭靖、楊過、張無忌、令狐沖等人的故事中,找到一點點,讀者自以為是的答案。
明星咖啡館裡的守護者
78歲的簡錦錐扶著欄杆、緩慢卻優雅地走上明星咖啡館二樓。他穿著整潔筆挺的黑色西裝,像是要赴一場盛宴。這段路燈光昏暗,牆上掛滿老照片,嘎吱嘎吱的木梯提醒訪客,每走一步,離歷史更近一步。
2003年明星咖啡館重新開幕,簡錦錐從埔里搬回明星第一代舊桌椅,找出藏在家中的俄羅斯杯盤,再找來老師傅用手工做出和當年一模一樣的鐵窗、木窗。這批桌椅經歷六十年風霜與九二一大地震,色澤質地卻一如當年,放上仿舊杯盤,彷彿未曾離開。
許多人以為,簡錦錐大費周章,為的是販賣明星咖啡館文學時代的氛圍。就像這一天的採訪,我以為他要告訴我明星和白先勇、黃春明等人的文學故事,沒想到,我得到的是另一個更遙遠的故事。
簡錦錐從口袋裡掏出一張黑白照片,裡頭坐滿一地西方人,「照片中的他們,剛在明星二樓開完俄國新年舞會。」我認出人群裡年輕的蔣經國和蔣方良,時光馬上啪啪啪倒退到一甲子前。
「照片洗出來後尼古拉(蔣經國俄文名)跟我說,不要留這一張啊,因為照中他的手像是要掐死芬娜(蔣方良)。」當時小蔣戀上顧正秋的緋聞鬧得滿城風雨,照片中蔣方良的笑容看得出勉強。簡錦錐形容為愛走天涯的她「很孤單,總想著回故鄉」。
來自俄羅斯的蔣方良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沉默的總統夫人。夾在中國、台灣和俄羅斯的政治夾縫中,她就像這張黑白照片扁平而暗淡,人們對她一無所知。但在明星咖啡館裡,蔣方良還原為愛跳舞嗜甜點的俄國年輕姑娘芬娜,熱情、浪漫,為了愛情放棄一切、來到遙遠的異鄉。
蔣方良的葬禮上,傷心的簡錦錐堅持女兒代表出席。他說,芬娜的家人早失去了蹤影,「明星就代表她的娘家。」
「你看,左邊第三個就是艾斯尼。」簡錦錐指著照片告訴我,那是一個有著憂鬱眼神的中年人。艾斯尼流著貴族血液的皇家侍衛軍,曾目賭沙皇全家屍體被淋上鹽酸的慘況。
一九一七年,俄共推翻沙皇政權,一群白俄人先後流亡到上海、台北。
簡錦錐認識艾斯尼時,艾斯尼已步入人生的黃昏,簡錦錐才十八歲。某日艾斯尼到簡家商店買拐杖,只有略通英語的簡錦錐可以跟他溝通,兩人結為忘年好友。簡錦錐為艾斯尼的外國朋友仲介房屋,發了一筆小財。
思念故鄉,艾斯尼和五位同鄉決定合夥開設專賣俄國食物的咖啡館,也拉了簡錦錐入股。一九四九年,明星在武昌街城隍廟對面掛起招牌,那時明星還不叫明星,只有一個英文名字Astoria。
「當時台灣的地板不是黃泥土就是水泥地板。Astoria卻是滿室木質地板,並以咖啡渣在地板上鋪出一個通道,一上樓梯就可以聞到濃濃的咖啡香」。簡錦錐閉上眼睛,彷彿聞到一甲子前飄出來的咖啡香。
合夥人之一伏爾林,曾在上海霞飛路開設Astoria咖啡館。據說台北的Astoria,完全按照上海的前世版本打造。明星咖啡館從誕生開始,便是一個懷舊和回憶的地方。
明星最有名的俄羅斯軟糖,由列比洛夫夫婦負責製作。列比洛夫曾在俄國王宮廚房裡工作,總是在自家秘密調製軟糖。
食物是治療鄉愁的靈藥,而明星就像一個時光隧道。流浪到台北的俄國人,包括總統夫人芬娜,總是把明星當成故鄉,到明星買羅宋湯、俄羅斯軟糖,舉行晚宴和舞會。當時在台灣的俄國人多是貴族出身,出現時總是西裝筆挺、衣服上一個皺褶都沒有,展現紳士在流亡生涯的從容與優雅。這習慣簡錦錐學了起來,一直保持到現在。
一九五0年代台海情勢緊張,伏爾林和列比洛夫陸續移民海外,艾斯尼留了下來。為了怕艾斯尼失去工作無法留在台灣,簡錦錐獨資把Astoria頂了下來,請艾斯尼當顧問。
換了老闆的Astoria重新開幕,掛上中文字「明星」。白俄時代落幕,明星的文學時代開啟,客人換成了黃春明、白先勇、陳映真、季季、林懷民……
黃春明代表作「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皆在明星咖啡館完成。黃春明談起這段日子時說,他經常坐一整天只點一杯咖啡,簡錦錐從不趕人,還交代員工不能打擾他。這種慷慨和包容,在錙銖必較的現代社會找不到了。
還沒到紐約習舞的林懷民,也是明星咖啡館的座上客、在這裡孵出了「蟬」。簡錦錐說,林懷民的父親林金生,曾到明星咖啡館找兒子,還開玩笑告訴他,懷著作家夢的兒子是「空ㄟ」。出身世家身居高官的林金生,對兒子的期望是當律師,違背父命的「作家」林懷民,在當時有著一副無法安定的靈魂。
不知道為什麼,明星咖啡館總是吸引漂泊的靈魂。被簡錦錐暱稱為「老周」的周夢蝶,在明星咖啡館騎樓下擺了幾十年的書攤。簡錦錐說,從大陸來台的老周一人獨居三重,一九五九年開始擺攤。簡錦錐擔心他搬書辛苦,邀他將書籍寄放在武昌街五號、簡錦錐租給茶莊使用的房產,晚上可至此地留宿。周夢蝶累了,也經常進明星小坐,每次都坐固定的位置。
周夢蝶辭世後,有人在昔年書攤位置的柱子上,貼上周夢蝶的詩篇。簡錦錐將這篇詩改貼到明星咖啡館內周夢蝶的「老位子」牆邊,桌上放上老周的照片,將這個位置永遠保留給周夢蝶。
簡錦錐又說起艾斯尼。他接手明星後,把艾斯尼接到家中照顧,一直到他過世。身體衰弱的艾斯尼堅持每天到明星,一個人喝咖啡、吃點心。艾斯尼過世後,明星依然保留他的位置,每天放上點心和咖啡。
人們驚嘆,明星為什麼可以容忍作家點一杯咖啡坐一整天?原來就算是靈魂,也可以在明星擁有一個永恆的位置。
俄國人走了,流亡的靈魂繼續流亡,故鄉的滋味卻在明星封存。這歸功於簡錦錐驚人的記憶力,列比洛夫曾讓他看過一次調製俄羅斯軟糖的過程,他走後簡憑記憶調配,味道被老顧客稱讚「一模一樣」。
從年輕到老,簡錦錐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到廚房監工,看師父有沒有按照配方調製軟糖,麵粉、糖的比例一點都不容更動。
簡錦錐知道故鄉滋味對遊子的重要。明星的俄羅斯軟糖,芬娜一直吃到八十八歲過世前。就像作家雖然離開了明星咖啡館,但只要喝一杯明星的咖啡,就會感覺自己回到了四十年前文學的明星年代。
曾有電影導演找上簡錦錐,說要拍「明星咖啡廳」,他看完劇本便拒絕了。為了戲劇效果,劇本變成「一個白俄人和中國人建立友誼、又互相背叛的故事。」簡錦錐說他不能忍受對歷史的虛構。
有段時間,每周二簡錦錐固定帶孫子到郊外騎馬,教導他「不能摘蘆葦」。艾斯尼曾告訴簡錦錐,從莫斯科一路騎馬逃到哈爾濱時,馬兒就靠蘆葦活了下來。
「明星」其實便是俄文Astoria的中文。「天上的星星,代表對故鄉的思念。」艾斯尼告訴簡錦錐,他騎馬逃亡的路上,一直看著天上的星星。
臨走前,簡錦錐堅持我帶走一盒俄羅斯軟糖。這款糖早因蔣方良聞名,然而到現在我才終於懂得它的滋味。
走出明星咖啡館,我抬頭往上看,發現昏黃的燈火中,簡錦錐的影子還映在二樓的窗口。六十多年來,明星咖啡館送走一批又一批漂泊的靈魂:游子、作家或異鄉客。每一場盛宴都有簡錦錐從開始守到最後,為他們開門、熄燈。
簡錦錐默默守著明星咖啡館,就像他守著那一段與俄國朋友的情誼。這世上總有不滅的星星,也許是友情,也許是回憶。也有像簡錦錐這樣永遠的守候者,只要有他們在,漂泊的靈魂就有暫歇的角落,而我們就有了文學。
書店的美好年代
煙火在深黑的夜色中炸開,將白天如此平淡的城市變得燦麗輝煌。人群拍手歡呼,燦爛的幸福彷彿觸手可及,卻轉瞬消逝。跨年夜的煙火總是予人一種奇異的幸福感,即將展開的新的一年如此光彩燦爛、卻又如此虛幻易逝;那是揉雜著淡淡哀傷的幸福感,在惘惘的威脅之下更顯強烈的幸福感。
千禧年後的台灣人,跨年夜總是在燦爛的101燈火中度過--不管是看電視、手機,或是擠在人群之中。這是一種極其神秘的經驗,人們透過煙火,一個在視覺與聽覺上兼具壯觀與虛幻的儀式,集體跨過某個看不見的界線,抵達新的一年的彼岸。
而我第一次的101煙火經驗,是在書店之中。
過完千禧年沒幾年,我在倫敦打開衛報,斗大標題讓我心頭一凜:「查令十字路書店寫下最後一頁。」報導的大意是,隨著連鎖咖啡館的攻城略池,屹立在書街查令十字路幾十年的書店,一間間熄了燈。
放下報紙我輕輕嘆息。不過是幾年前,電影「電子情書」還能將連鎖書店併吞獨立書店的商業戰,浪漫成湯姆漢克追求梅格萊恩的愛情故事;「新娘百分百」裡的諾丁丘獨立書店,也能創造大明星愛上書店老闆的當代童話。然而到了這臣屬於虛擬世界的新世紀,被連鎖咖啡館吃掉的連鎖書店、獨立書店,已然成為編不成好萊塢浪漫電影的殘酷現實。
帶著對逝去書店時代的感傷,我回到了台灣;沒想到此時的小島,正迎向書店的燦爛盛世。
20世紀的最後一年,台灣第一家24小時書店誠品敦南店開張,出乎意外的成功,吹響書店的號角。隔年走在潮流尖端的購物商場京華城,開起誠品第二家廿四小時不打烊書店;來自新加坡的連鎖書店page one,也在當時的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展開台灣的第一頁。
而最振奮人心的是誠品信義店。2005年六月,誠品打敗強敵SOGO,拿下信義計畫區統一國際大樓的經營權。誠品董事長吳清友躊躇滿志,宣布將在此地開設亞洲最大的書店。
誠品信義店擁有7500坪商場面積,其中2500坪販售書籍,藏書1百萬冊,預計一年吸引一千萬人次。吳清友形容它不僅是「百貨業的新模式」,更是「台灣望向世界的一個文化窗口」。
這三間開在商場中的大型書店,以壯觀的坪數、夢幻的設計,顛覆一般人對傳統書店的想像,多次贏得國際設計大獎。京華城的雙環狀圓形書店一旦連上城市夜晚的星空點點,讀者彷彿置身神秘宇宙;而Page one的書架如壯闊的山巒起伏,還打造讓讀者窩在裏頭讀書的「樹洞」;誠品信義店則放上百張設計師陳瑞憲從巴黎跳蚤市場找來的骨董椅,鼓勵讀者坐在上頭尋夢、作夢。
那真是一個勇於做夢的美好時代。明明同一時間台灣出版公會發表調查,台灣出版產值較兩年前掉了兩百多億。人們卻相信,可以和百貨公司、商場完美結合的書店,正要迎向最美好的年代。這些如宮殿似聖堂又彷彿宇宙的夢幻書店,正是書店美好年代的見證。
倫敦閱讀氛圍堪稱世界第一,但倫敦最大的書店也不會超過1000坪。我問吳清友,7500坪的書店,在台灣可以生存嗎?
「想像比知識重要。」吳清友沒有正面回答我,但堅定告訴我,誠品人都是勇於想像的人,而他心中的書店是「既能提供想像、又能滿足知識」的空間,這股想像的力量牽引他們完成美夢。吳清友為台灣人打造的夢幻書店,有講座、市集、演唱會、音樂會、畫廊…….集合生活中一切美好而理想的元素。
吳清友擁有激動人心的力量。誠品每隔幾年便會舉辦大型活動,吳清友總是站在台上,用簡潔感性的演講,勾勒書店的美好遠景,鼓勵台下的員工和讀者做夢、追夢。他經常穿著一身黑色衣服,梳著簡潔優雅的白髮,眼神堅定又溫暖,讓人想起佈道的牧師。誠品蟬聯了好多年社會新鮮人最愛的夢幻職業,即使起薪遠不及台積電等科技產業。
吳清友心臟病辭世後我才知道,原來他很年輕便知道,自己身體內裝了一個不定時炸彈;這些年來,他一直鼓起隨時可能爆光的生命能量,打造誠品足以照亮整個城市的燦爛夢想。
他的勇氣、想像力和創新,會不會來自於體內這顆炸彈?
飽滿的煙火炸開,在黑沉沉的天空噴出火樹銀花,城市在煙火的襯托下,顯得如此偉大輝煌。
2005年12月31日晚上11點半,亞洲最大的書店誠品信義店舉辦開幕派對,和隔鄰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的煙火,一起迎向2006年。
那天晚上不到9點,7500坪的信義店裡滿滿都是人。這是新世紀台北最盛大的一場藝文派對,我認識的台北藝文界人士,都說要來參加這場世紀派對。
我和朋友相約共赴這場派對,說好到了書店便打手機聯絡。但我一到書店,便發現人太多網路塞爆,手機根本不通。
那天夜裡,我狂打沒有反應的手機,努力在書店尋覓朋友的蹤跡,但多數時間只能被人群推擠著緩緩移動,哪裡都到不了。那些來自巴黎和世界各地的美麗的椅子,此刻坐滿歇腿的人,書和書之間也擠滿了人。
事後那位徹夜失聯的朋友告訴我,她在一台緩緩上升的電梯看到我,而我正坐著一台緩緩下降的電梯。我們曾在同一個高度對上,她向我揮手、大聲呼喚,但我渾然未覺、一臉茫然,逐漸消失在她的視野中。
那天我在書店看到的人群多數是這樣的表情,不知道是過度興奮還是疲憊。那些從我面前喧嘩流過的人潮,人人臉上掛著一抹茫然。嘉年華或演唱會那樣人山人海的超High氣氛,在象徵文明秩序的書店中,形成非常魔幻的畫面。
午夜12點,窗外爆出煙火,書店裡的人潮也達到頂點。我寸步難移,只能擠在書堆之中、人群之中,想像窗外的燦爛。書店裡人聲喧嘩,掩蓋了煙火的巨響。
那是我人生最魔幻的一刻,和一群陌生人擠在書與書之中,集體想像著煙火與即將到來的、充滿火光的新的一年,寫實又虛幻。
那一夜煙火燦爛,數萬人盤據在剛開幕的書店,想像窗外的煙火,未來在大家眼中閃耀燦爛的光芒。對於那個時代的我們,煙火和書,象徵生活中最燦爛美好的事物。
煙火散了,人們準備回家,又是一陣推擠混亂。我和一位朋友奇蹟般地遇上了,兩人一起在街上步行了幾小時,終於找到一台計程車順利回家。
過了彷彿一世紀的一夜,手機通了,失聯的朋友聯絡上了,大家談起這一夜的經歷都感到新奇。一位朋友一路被推擠進了捷運上,再從捷運口被推擠出來,他笑稱自己根本不需要移動雙腳,身上都是陌生人的汗水。有人把車子丟在停車場,獨自走了一夜的路回家。
「像不像一九四九大撤退?」一個朋友問,大家笑了。
「看到101煙火了嗎?」眾人紛紛搖頭。我們被擠在人群之中寸步難移,雖然煙火離我們只有咫尺之遙。
飽滿的煙火在黑夜中炸開,城市在煙火的襯托下,偉大而輝煌。我們沒能親眼見證這一幕,卻透過電視、手機等各種螢幕,以為自己親身經歷了這樣輝煌的一刻。
多年後回想這一幕,我的回憶動搖了,我是否曾在書店之中,親眼目睹窗外光彩流離的煙火呢?手機網路等虛擬世界的影像,已經自動幫我們填補創造了許多根本不曾存在的記憶。
在我對那一夜的記憶畫面之中,煙火逐漸模糊;逐漸清晰的是我和朋友走在城市空曠的街頭,那樣的清冷、那樣的茫然。
幾年後,京華城書店關了,page one收了。敵不過網路世界的威脅,實體書店的美好年代一去不復返。但誠品信義店還立在那裏,甚至成為廿四小時不打烊書店,整個城市都暗下去沉下去的時候書店亮著,那一點火光濃縮了那個時代所有美好的燦爛的想像。
現在想起來,那是一個浮躁的年代,好像有甚麼要發生,但其實甚麼也沒發生,就像看了一場轉瞬即逝的煙火。
那是一個人人愛看煙火的年代,世界第一高樓剛蓋好,隨之而來的101跨年煙火吸引了CNN等國際媒體的注意,「砰」一聲點燃台灣人的自信。大國崛起後,基於小島的邊緣感與不安全感,島民熱衷於最大與最多,用數字虛張聲勢。煙火成為一種儀式,我們透過世界第一高樓、規模最大與數量最多的煙火,相信自己站在世界的頂端、螢幕的中央,整個島國就沉浸在煙火般飽滿的自信之中。
那也是一個充滿激情與想像的年代。我們擁有世界最高的樓、最大與最美的書店,相信自己擁有最美好的一切。
現在想起來,那一場華麗的煙火,我們其實甚麼都沒見到,只是擠在人群中,一起度過了某個神祕的時刻。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個燦爛的輝煌的對未來充滿想像與激情的美好年代,就在那個我們什麼沒察覺到的時刻,靜靜消失了。
颱風前一天過境,香港維多利亞海港恢復風平浪靜,湛藍的海水裹著一層淡淡的薄霧,彷彿一面帶著滄桑的鏡子。八十多歲的金庸坐在明河社窗邊,一邊眺望波光中靜止的船帆,一邊意興遄飛地說起他創辦明報的經歷,跌宕起伏的故事不輸給他筆下的武俠小說。
文革初期,金庸白天寫社論批判翻江覆海的政治浪潮,晚上寫武俠小說「笑傲江湖」連載創造另一個江湖。金學專家說,「笑傲江湖」裡的人物都是兩岸政治人物的隱喻。但金庸不承認,只是笑呵呵地告訴我當年他行走江湖的凶險:「我在暗殺榜上排第二,第一名林彬已壯烈成仁。香港政府派警察在報館、家門前保護我,還給我十四個假車牌替換,讓歹徒跟蹤不到我的車。」
他說,這是一生中最懷念的時光。
我鼓起勇氣問他,這一生,你是否有過遺憾的時刻?
金庸辭世後,好友倪匡為他編了一本書,收錄親友談金庸的紀錄。書中,金庸幼女查傳納表示,父親不喜歡別人為他寫傳記,「他的小說就是他的平生。所以他寫完一本又一本,每本都是他的人生經歷。」
關於金庸的傳記不少,卻沒一本獲得金庸授權或認可。金庸不寫傳記、也不僅不喜歡別人為他寫傳記、甚至差點把為他寫傳記的人告上公堂。像金庸這樣名動八方、走過大時代的作家與報人,卻沒留下一本官方認證的傳記或回憶錄,用自己的角度來看自己的一生和這個時代,在華人的文學史和歷史上,不能不說是一個缺憾。
金庸為什麼不寫傳記?這在我心中是一個謎。
多年前,一個風狂雨驟的颱風夜,我接到了一通神秘的電話。電話中朋友說,一位朋友急需聯絡金庸,希望我代為幫忙。接著告訴我,一件現在想來仍覺不可思議之事。
朋友說,金庸大兒子查傳俠的前女友自殺了。這位女子卅年前和查傳俠在美國相戀,兩人爭吵後查傳俠跳樓身亡。她之後結婚生子,兒子跟當年自殺的查傳俠一樣,剛剛申請上一間美國長春藤名校。母親卻選在兒子金榜題名那一年自殺,離查傳俠辭世,足足過了卅年。
朋友希望我代為連絡金庸,告訴他兒子女友的消息。這位女子一直想告訴金庸,他的兒子不是為她而死;希望她離開人世後,這訊息能夠傳遞給金庸,了了她鬱結幾十年的心願。
在情人死後卅年殉情,這是甚麼樣的愛情?這卅年來,她又背負甚麼樣的心情,度過自己的人生?
我聽了震撼不已,立刻透過管道告知金庸此事,將朋友的聯絡電話轉了出去。
關於查傳俠之死,這是我第一次聽聞。我立刻上網,從零碎的網路八卦中一點一滴拼湊金庸的家庭故事。
網上說,查傳俠是金庸最引以為傲的兒子,和父親一樣從小展露傲人的寫作才華。他大學申請上美國常春藤名校,卻在上大學的第一年、人生最燦爛的青春年華,跟女友吵架後跳樓身亡。
他沒有留下遺書,自殺的原因成謎。一說是和女友吵架,負氣自殺;一說是憂憤父母離婚,以死明志。
我查不到金庸談兒子早夭的言論,但找到他在「倚天屠龍記」單行本的後記:
「然而,張三丰見到張翠山自刎時的悲痛之情,謝遜聽到張無忌死訊時的傷心,書中寫得也太膚淺了,真實人生中不是這樣的。因為那時候我還不明白。」
那篇後記,正是查傳俠自殺後半年內所寫。
網上說,金庸在兒子自殺後,潛心研究佛經。
我又在網上查到關於查傳俠母親朱玫的八卦。朱玫是金庸第二任太太,和金庸都是記者出身,兩人一起打造明報報業王國,生了二子二女,卻不能白頭到老。
形容金庸每本小說都是人生經歷的么女查傳納,認為母親就是金庸第一部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中的霍青桐:「我媽媽上街打扮得很漂亮,煮飯很好吃,工作能幹,但就是太叻(能幹)了。女人可以好叻,但在男人面前,都要留一留。」書劍恩仇錄裡的霍青桐,打仗勇智過人,談情說愛卻輸給香香公主。
現實中的霍青桐,晚年貧病交迫,死時身邊沒有親人,還是醫院工作人員為她申請死亡證,和金庸晚年的風光形成強烈對比。據說,金庸從記者口中得知此事後淚流滿面,悲嘆「我對不起我的家人」。
金庸未曾留下一本他認證的官方傳記,這些網路上流傳的八卦,缺乏金庸本人的說法,僅止於八卦。
關於這通颱風夜的奇異電話,我沒有進一步向金庸求證,也不打算將它寫成報導。我無法開口向一位年邁的父親詢問,愛子的自殺是不是他一手造成;也不願這塵封了卅年的往事,讓大俠到了暮年還要陷入世人的八卦陣。
這通電話成為我和金庸之間的一個秘密。
又過了一兩年,我得到金庸的允許,到香港採訪他。
那是一個颱風剛剛結束的晴天,我來到位於維多利亞港畔的明河社,拜訪剛完成三修作品壯舉的金庸。此時的金庸正準備全心投入劍橋大學的歷史碩士學位,當歷史學者,是他從小的心願。
或許是放下了長久懸在心頭的大石,又要開始追求年少的夢想,那一天,金庸對我敞開了心防,回憶起波瀾壯闊的一生。話題圍繞在他一生最懷念的時光、經營明報最艱困的時期。金庸興致勃勃地談起,他如何在詭譎肅殺的政治江湖中,執筆為劍,揮灑出自己的江山。
我想起那一通電話,鼓足勇氣問金庸:這一生,你是否有過遺憾的時刻?
金庸頓住了。他不置一詞,只是把眼光移向窗外,凝視著維多利亞港裡靜止的船帆,眼神神秘而深沉。那一整個下午,他始終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我跟著金庸的目光望向遠處的維多利亞港。風雨已經過去,恢復平靜的海面,應當埋伏著深深的潛流吧。一生笑傲江湖的大俠、外人眼中功成名就的人生勝利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道靜靜的伏流,不容外人挖掘,甚至連自己都不敢碰觸。
金庸的傳記,始終沒寫出來。
隨著金庸的辭世,那一通神秘的電話,那一個下午金庸深沉的眼神,沉入如海水般幽深的時間之中。
關於那通電話的真相、世人的流言蜚語,關於愛情與親情,選擇與遺憾,金庸不曾留下任何一字一句。從此,我們只能從金庸的十五本小說中,從陳家洛、郭靖、楊過、張無忌、令狐沖等人的故事中,找到一點點,讀者自以為是的答案。
明星咖啡館裡的守護者
78歲的簡錦錐扶著欄杆、緩慢卻優雅地走上明星咖啡館二樓。他穿著整潔筆挺的黑色西裝,像是要赴一場盛宴。這段路燈光昏暗,牆上掛滿老照片,嘎吱嘎吱的木梯提醒訪客,每走一步,離歷史更近一步。
2003年明星咖啡館重新開幕,簡錦錐從埔里搬回明星第一代舊桌椅,找出藏在家中的俄羅斯杯盤,再找來老師傅用手工做出和當年一模一樣的鐵窗、木窗。這批桌椅經歷六十年風霜與九二一大地震,色澤質地卻一如當年,放上仿舊杯盤,彷彿未曾離開。
許多人以為,簡錦錐大費周章,為的是販賣明星咖啡館文學時代的氛圍。就像這一天的採訪,我以為他要告訴我明星和白先勇、黃春明等人的文學故事,沒想到,我得到的是另一個更遙遠的故事。
簡錦錐從口袋裡掏出一張黑白照片,裡頭坐滿一地西方人,「照片中的他們,剛在明星二樓開完俄國新年舞會。」我認出人群裡年輕的蔣經國和蔣方良,時光馬上啪啪啪倒退到一甲子前。
「照片洗出來後尼古拉(蔣經國俄文名)跟我說,不要留這一張啊,因為照中他的手像是要掐死芬娜(蔣方良)。」當時小蔣戀上顧正秋的緋聞鬧得滿城風雨,照片中蔣方良的笑容看得出勉強。簡錦錐形容為愛走天涯的她「很孤單,總想著回故鄉」。
來自俄羅斯的蔣方良是中華民國有史以來最沉默的總統夫人。夾在中國、台灣和俄羅斯的政治夾縫中,她就像這張黑白照片扁平而暗淡,人們對她一無所知。但在明星咖啡館裡,蔣方良還原為愛跳舞嗜甜點的俄國年輕姑娘芬娜,熱情、浪漫,為了愛情放棄一切、來到遙遠的異鄉。
蔣方良的葬禮上,傷心的簡錦錐堅持女兒代表出席。他說,芬娜的家人早失去了蹤影,「明星就代表她的娘家。」
「你看,左邊第三個就是艾斯尼。」簡錦錐指著照片告訴我,那是一個有著憂鬱眼神的中年人。艾斯尼流著貴族血液的皇家侍衛軍,曾目賭沙皇全家屍體被淋上鹽酸的慘況。
一九一七年,俄共推翻沙皇政權,一群白俄人先後流亡到上海、台北。
簡錦錐認識艾斯尼時,艾斯尼已步入人生的黃昏,簡錦錐才十八歲。某日艾斯尼到簡家商店買拐杖,只有略通英語的簡錦錐可以跟他溝通,兩人結為忘年好友。簡錦錐為艾斯尼的外國朋友仲介房屋,發了一筆小財。
思念故鄉,艾斯尼和五位同鄉決定合夥開設專賣俄國食物的咖啡館,也拉了簡錦錐入股。一九四九年,明星在武昌街城隍廟對面掛起招牌,那時明星還不叫明星,只有一個英文名字Astoria。
「當時台灣的地板不是黃泥土就是水泥地板。Astoria卻是滿室木質地板,並以咖啡渣在地板上鋪出一個通道,一上樓梯就可以聞到濃濃的咖啡香」。簡錦錐閉上眼睛,彷彿聞到一甲子前飄出來的咖啡香。
合夥人之一伏爾林,曾在上海霞飛路開設Astoria咖啡館。據說台北的Astoria,完全按照上海的前世版本打造。明星咖啡館從誕生開始,便是一個懷舊和回憶的地方。
明星最有名的俄羅斯軟糖,由列比洛夫夫婦負責製作。列比洛夫曾在俄國王宮廚房裡工作,總是在自家秘密調製軟糖。
食物是治療鄉愁的靈藥,而明星就像一個時光隧道。流浪到台北的俄國人,包括總統夫人芬娜,總是把明星當成故鄉,到明星買羅宋湯、俄羅斯軟糖,舉行晚宴和舞會。當時在台灣的俄國人多是貴族出身,出現時總是西裝筆挺、衣服上一個皺褶都沒有,展現紳士在流亡生涯的從容與優雅。這習慣簡錦錐學了起來,一直保持到現在。
一九五0年代台海情勢緊張,伏爾林和列比洛夫陸續移民海外,艾斯尼留了下來。為了怕艾斯尼失去工作無法留在台灣,簡錦錐獨資把Astoria頂了下來,請艾斯尼當顧問。
換了老闆的Astoria重新開幕,掛上中文字「明星」。白俄時代落幕,明星的文學時代開啟,客人換成了黃春明、白先勇、陳映真、季季、林懷民……
黃春明代表作「看海的日子」、「兒子的大玩偶」,皆在明星咖啡館完成。黃春明談起這段日子時說,他經常坐一整天只點一杯咖啡,簡錦錐從不趕人,還交代員工不能打擾他。這種慷慨和包容,在錙銖必較的現代社會找不到了。
還沒到紐約習舞的林懷民,也是明星咖啡館的座上客、在這裡孵出了「蟬」。簡錦錐說,林懷民的父親林金生,曾到明星咖啡館找兒子,還開玩笑告訴他,懷著作家夢的兒子是「空ㄟ」。出身世家身居高官的林金生,對兒子的期望是當律師,違背父命的「作家」林懷民,在當時有著一副無法安定的靈魂。
不知道為什麼,明星咖啡館總是吸引漂泊的靈魂。被簡錦錐暱稱為「老周」的周夢蝶,在明星咖啡館騎樓下擺了幾十年的書攤。簡錦錐說,從大陸來台的老周一人獨居三重,一九五九年開始擺攤。簡錦錐擔心他搬書辛苦,邀他將書籍寄放在武昌街五號、簡錦錐租給茶莊使用的房產,晚上可至此地留宿。周夢蝶累了,也經常進明星小坐,每次都坐固定的位置。
周夢蝶辭世後,有人在昔年書攤位置的柱子上,貼上周夢蝶的詩篇。簡錦錐將這篇詩改貼到明星咖啡館內周夢蝶的「老位子」牆邊,桌上放上老周的照片,將這個位置永遠保留給周夢蝶。
簡錦錐又說起艾斯尼。他接手明星後,把艾斯尼接到家中照顧,一直到他過世。身體衰弱的艾斯尼堅持每天到明星,一個人喝咖啡、吃點心。艾斯尼過世後,明星依然保留他的位置,每天放上點心和咖啡。
人們驚嘆,明星為什麼可以容忍作家點一杯咖啡坐一整天?原來就算是靈魂,也可以在明星擁有一個永恆的位置。
俄國人走了,流亡的靈魂繼續流亡,故鄉的滋味卻在明星封存。這歸功於簡錦錐驚人的記憶力,列比洛夫曾讓他看過一次調製俄羅斯軟糖的過程,他走後簡憑記憶調配,味道被老顧客稱讚「一模一樣」。
從年輕到老,簡錦錐每天醒來第一件事就是到廚房監工,看師父有沒有按照配方調製軟糖,麵粉、糖的比例一點都不容更動。
簡錦錐知道故鄉滋味對遊子的重要。明星的俄羅斯軟糖,芬娜一直吃到八十八歲過世前。就像作家雖然離開了明星咖啡館,但只要喝一杯明星的咖啡,就會感覺自己回到了四十年前文學的明星年代。
曾有電影導演找上簡錦錐,說要拍「明星咖啡廳」,他看完劇本便拒絕了。為了戲劇效果,劇本變成「一個白俄人和中國人建立友誼、又互相背叛的故事。」簡錦錐說他不能忍受對歷史的虛構。
有段時間,每周二簡錦錐固定帶孫子到郊外騎馬,教導他「不能摘蘆葦」。艾斯尼曾告訴簡錦錐,從莫斯科一路騎馬逃到哈爾濱時,馬兒就靠蘆葦活了下來。
「明星」其實便是俄文Astoria的中文。「天上的星星,代表對故鄉的思念。」艾斯尼告訴簡錦錐,他騎馬逃亡的路上,一直看著天上的星星。
臨走前,簡錦錐堅持我帶走一盒俄羅斯軟糖。這款糖早因蔣方良聞名,然而到現在我才終於懂得它的滋味。
走出明星咖啡館,我抬頭往上看,發現昏黃的燈火中,簡錦錐的影子還映在二樓的窗口。六十多年來,明星咖啡館送走一批又一批漂泊的靈魂:游子、作家或異鄉客。每一場盛宴都有簡錦錐從開始守到最後,為他們開門、熄燈。
簡錦錐默默守著明星咖啡館,就像他守著那一段與俄國朋友的情誼。這世上總有不滅的星星,也許是友情,也許是回憶。也有像簡錦錐這樣永遠的守候者,只要有他們在,漂泊的靈魂就有暫歇的角落,而我們就有了文學。
書店的美好年代
煙火在深黑的夜色中炸開,將白天如此平淡的城市變得燦麗輝煌。人群拍手歡呼,燦爛的幸福彷彿觸手可及,卻轉瞬消逝。跨年夜的煙火總是予人一種奇異的幸福感,即將展開的新的一年如此光彩燦爛、卻又如此虛幻易逝;那是揉雜著淡淡哀傷的幸福感,在惘惘的威脅之下更顯強烈的幸福感。
千禧年後的台灣人,跨年夜總是在燦爛的101燈火中度過--不管是看電視、手機,或是擠在人群之中。這是一種極其神秘的經驗,人們透過煙火,一個在視覺與聽覺上兼具壯觀與虛幻的儀式,集體跨過某個看不見的界線,抵達新的一年的彼岸。
而我第一次的101煙火經驗,是在書店之中。
過完千禧年沒幾年,我在倫敦打開衛報,斗大標題讓我心頭一凜:「查令十字路書店寫下最後一頁。」報導的大意是,隨著連鎖咖啡館的攻城略池,屹立在書街查令十字路幾十年的書店,一間間熄了燈。
放下報紙我輕輕嘆息。不過是幾年前,電影「電子情書」還能將連鎖書店併吞獨立書店的商業戰,浪漫成湯姆漢克追求梅格萊恩的愛情故事;「新娘百分百」裡的諾丁丘獨立書店,也能創造大明星愛上書店老闆的當代童話。然而到了這臣屬於虛擬世界的新世紀,被連鎖咖啡館吃掉的連鎖書店、獨立書店,已然成為編不成好萊塢浪漫電影的殘酷現實。
帶著對逝去書店時代的感傷,我回到了台灣;沒想到此時的小島,正迎向書店的燦爛盛世。
20世紀的最後一年,台灣第一家24小時書店誠品敦南店開張,出乎意外的成功,吹響書店的號角。隔年走在潮流尖端的購物商場京華城,開起誠品第二家廿四小時不打烊書店;來自新加坡的連鎖書店page one,也在當時的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展開台灣的第一頁。
而最振奮人心的是誠品信義店。2005年六月,誠品打敗強敵SOGO,拿下信義計畫區統一國際大樓的經營權。誠品董事長吳清友躊躇滿志,宣布將在此地開設亞洲最大的書店。
誠品信義店擁有7500坪商場面積,其中2500坪販售書籍,藏書1百萬冊,預計一年吸引一千萬人次。吳清友形容它不僅是「百貨業的新模式」,更是「台灣望向世界的一個文化窗口」。
這三間開在商場中的大型書店,以壯觀的坪數、夢幻的設計,顛覆一般人對傳統書店的想像,多次贏得國際設計大獎。京華城的雙環狀圓形書店一旦連上城市夜晚的星空點點,讀者彷彿置身神秘宇宙;而Page one的書架如壯闊的山巒起伏,還打造讓讀者窩在裏頭讀書的「樹洞」;誠品信義店則放上百張設計師陳瑞憲從巴黎跳蚤市場找來的骨董椅,鼓勵讀者坐在上頭尋夢、作夢。
那真是一個勇於做夢的美好時代。明明同一時間台灣出版公會發表調查,台灣出版產值較兩年前掉了兩百多億。人們卻相信,可以和百貨公司、商場完美結合的書店,正要迎向最美好的年代。這些如宮殿似聖堂又彷彿宇宙的夢幻書店,正是書店美好年代的見證。
倫敦閱讀氛圍堪稱世界第一,但倫敦最大的書店也不會超過1000坪。我問吳清友,7500坪的書店,在台灣可以生存嗎?
「想像比知識重要。」吳清友沒有正面回答我,但堅定告訴我,誠品人都是勇於想像的人,而他心中的書店是「既能提供想像、又能滿足知識」的空間,這股想像的力量牽引他們完成美夢。吳清友為台灣人打造的夢幻書店,有講座、市集、演唱會、音樂會、畫廊…….集合生活中一切美好而理想的元素。
吳清友擁有激動人心的力量。誠品每隔幾年便會舉辦大型活動,吳清友總是站在台上,用簡潔感性的演講,勾勒書店的美好遠景,鼓勵台下的員工和讀者做夢、追夢。他經常穿著一身黑色衣服,梳著簡潔優雅的白髮,眼神堅定又溫暖,讓人想起佈道的牧師。誠品蟬聯了好多年社會新鮮人最愛的夢幻職業,即使起薪遠不及台積電等科技產業。
吳清友心臟病辭世後我才知道,原來他很年輕便知道,自己身體內裝了一個不定時炸彈;這些年來,他一直鼓起隨時可能爆光的生命能量,打造誠品足以照亮整個城市的燦爛夢想。
他的勇氣、想像力和創新,會不會來自於體內這顆炸彈?
飽滿的煙火炸開,在黑沉沉的天空噴出火樹銀花,城市在煙火的襯托下,顯得如此偉大輝煌。
2005年12月31日晚上11點半,亞洲最大的書店誠品信義店舉辦開幕派對,和隔鄰世界第一高樓台北101的煙火,一起迎向2006年。
那天晚上不到9點,7500坪的信義店裡滿滿都是人。這是新世紀台北最盛大的一場藝文派對,我認識的台北藝文界人士,都說要來參加這場世紀派對。
我和朋友相約共赴這場派對,說好到了書店便打手機聯絡。但我一到書店,便發現人太多網路塞爆,手機根本不通。
那天夜裡,我狂打沒有反應的手機,努力在書店尋覓朋友的蹤跡,但多數時間只能被人群推擠著緩緩移動,哪裡都到不了。那些來自巴黎和世界各地的美麗的椅子,此刻坐滿歇腿的人,書和書之間也擠滿了人。
事後那位徹夜失聯的朋友告訴我,她在一台緩緩上升的電梯看到我,而我正坐著一台緩緩下降的電梯。我們曾在同一個高度對上,她向我揮手、大聲呼喚,但我渾然未覺、一臉茫然,逐漸消失在她的視野中。
那天我在書店看到的人群多數是這樣的表情,不知道是過度興奮還是疲憊。那些從我面前喧嘩流過的人潮,人人臉上掛著一抹茫然。嘉年華或演唱會那樣人山人海的超High氣氛,在象徵文明秩序的書店中,形成非常魔幻的畫面。
午夜12點,窗外爆出煙火,書店裡的人潮也達到頂點。我寸步難移,只能擠在書堆之中、人群之中,想像窗外的燦爛。書店裡人聲喧嘩,掩蓋了煙火的巨響。
那是我人生最魔幻的一刻,和一群陌生人擠在書與書之中,集體想像著煙火與即將到來的、充滿火光的新的一年,寫實又虛幻。
那一夜煙火燦爛,數萬人盤據在剛開幕的書店,想像窗外的煙火,未來在大家眼中閃耀燦爛的光芒。對於那個時代的我們,煙火和書,象徵生活中最燦爛美好的事物。
煙火散了,人們準備回家,又是一陣推擠混亂。我和一位朋友奇蹟般地遇上了,兩人一起在街上步行了幾小時,終於找到一台計程車順利回家。
過了彷彿一世紀的一夜,手機通了,失聯的朋友聯絡上了,大家談起這一夜的經歷都感到新奇。一位朋友一路被推擠進了捷運上,再從捷運口被推擠出來,他笑稱自己根本不需要移動雙腳,身上都是陌生人的汗水。有人把車子丟在停車場,獨自走了一夜的路回家。
「像不像一九四九大撤退?」一個朋友問,大家笑了。
「看到101煙火了嗎?」眾人紛紛搖頭。我們被擠在人群之中寸步難移,雖然煙火離我們只有咫尺之遙。
飽滿的煙火在黑夜中炸開,城市在煙火的襯托下,偉大而輝煌。我們沒能親眼見證這一幕,卻透過電視、手機等各種螢幕,以為自己親身經歷了這樣輝煌的一刻。
多年後回想這一幕,我的回憶動搖了,我是否曾在書店之中,親眼目睹窗外光彩流離的煙火呢?手機網路等虛擬世界的影像,已經自動幫我們填補創造了許多根本不曾存在的記憶。
在我對那一夜的記憶畫面之中,煙火逐漸模糊;逐漸清晰的是我和朋友走在城市空曠的街頭,那樣的清冷、那樣的茫然。
幾年後,京華城書店關了,page one收了。敵不過網路世界的威脅,實體書店的美好年代一去不復返。但誠品信義店還立在那裏,甚至成為廿四小時不打烊書店,整個城市都暗下去沉下去的時候書店亮著,那一點火光濃縮了那個時代所有美好的燦爛的想像。
現在想起來,那是一個浮躁的年代,好像有甚麼要發生,但其實甚麼也沒發生,就像看了一場轉瞬即逝的煙火。
那是一個人人愛看煙火的年代,世界第一高樓剛蓋好,隨之而來的101跨年煙火吸引了CNN等國際媒體的注意,「砰」一聲點燃台灣人的自信。大國崛起後,基於小島的邊緣感與不安全感,島民熱衷於最大與最多,用數字虛張聲勢。煙火成為一種儀式,我們透過世界第一高樓、規模最大與數量最多的煙火,相信自己站在世界的頂端、螢幕的中央,整個島國就沉浸在煙火般飽滿的自信之中。
那也是一個充滿激情與想像的年代。我們擁有世界最高的樓、最大與最美的書店,相信自己擁有最美好的一切。
現在想起來,那一場華麗的煙火,我們其實甚麼都沒見到,只是擠在人群中,一起度過了某個神祕的時刻。
很久以後我才明白,那個燦爛的輝煌的對未來充滿想像與激情的美好年代,就在那個我們什麼沒察覺到的時刻,靜靜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