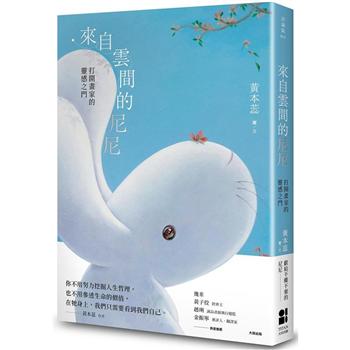一個落幕式和一個開場白——從插畫創作到純藝術創作
故事發生在那年三月一個無聊的午後……
我坐在畫桌前,百無聊賴地盯著那張畫了塗、塗了擦的畫紙,明知交稿日期在即,內在的我卻只想把這份責任心丟出去,跟它說「拜拜」!我真心只想打混,只想塗鴉……
三月下旬在西方文化裡,正值正復活節的前夕。不論走過店家或是打開電視,最不容易忽視的,就是代表春天即將降臨的復活節兔子。是不是這個肇因,至今也無從考起。總之,那個片刻,不知哪兒乍現的靈光,在我手下出現了一隻奇怪的動物,那是個造型頗為詭異的兔子!說不出喜歡或不喜歡,但是那整個下午,我竟然忙著與這隻小動物互動:「有事嗎?」我好像問。「沒事,有點話。」牠好像回答。之後十幾、二十個與當時工作全然不相關的兔子前仆後繼地在畫紙上出現:穿雨衣的兔子、跟大兔子對話的小兔子、跟影子牽手的兔子、夢遊兔子、美容院燙髮的兔子、碗中的兔子、雕塑與兔子……好像牠們在我體內沈潛了好久好久,終於在那個下午像決堤似的一個緊接一個流瀉了出來,來不及似的!好像牠們有話要說,是我有話要說嗎?我像個長久不曾開口的人,終於張了口,話語像是滾出來似的,生澀又不穩定,不但跳動還彼此歪斜碰撞……
之後,為了確認那是我的原創,而非在哪兒被哪張圖畫影響,我還特地上網請問了谷哥大神,等確認了那是絕無僅有的首創之後,我頒給了這隻小兔子牠的首張身分證:尼尼。隨後幾個月,第一、二、三、四張等等的尼尼繪畫相繼問世……
現在回想,怎麼也無法想像,當年那個神奇的午後,開啟了我人生的下一個起點。雖然至此,我的插畫工作好像也順道落下了幕,但事實真是如此?我從插畫工作,走到純藝術創作,一個落幕式和一個開場白之間,真能以一線隔之?它們之間的切換,看似是出版業和畫廊業的差別;作品的呈現,也是在紙本書上和在畫布上的區分,之間講的是不相關的兩回事。這麼多年來我不斷回望,今日終於明白了,這不是同一個創作者的前後兩個人生,而是隨著年歲漸增,所知所感來回擺盪,此消彼長後而組織起來的一條長橋。我從橋的這一頭,慢慢走著到達了另一頭,不管之前我做什麼開始,其間轉折做了什麼,最終又以什麼結束,每一段經歷加起來的林林總總,營造出來的就是今日的我這個獨一無二的創作者,創作著現在這樣的作品。之間每個經歷都是必然的存在,似乎不存在著偶然。一直以來,每當有人問我為什麼畫兔子?我的回答常常是各種的——直接的、間接的、潛意識、顯意識……現在,這些意外闖入我畫布上的兔子已逾十年,我看著牠們安適地坐著看著我,其實,我最無法否認的是自己過去二十多年的插畫經驗,使我選擇了兔子這具有插畫氣質的形象,作為藝術創作的開始。一個人若決定開始創作,即便是抽象創作,這創作必有其源自何處,怎能僅因為想要創作,作品就誕生了?我在無聊乏悶時塗鴉的各種兔子中,還有比大家現在看過的更為詭異的造型,我在大量的塗鴉中,挑選出較能適任於繪畫中的兔子們,讓牠們用身體、眼神、動作,擔當我的繪畫中的主角、配角,或是路人甲乙丙……當時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情創作,沒想到牠們艱鉅的任務就此開始,而且到今天已經邁入第二個十年了!
共鳴的開始——為何兔子?為何尼尼?
自從我的第一張兔子繪畫問世,這個問題就不停地被提出,多半是閒聊間好奇的問題。但是有一次,竟然是一位韓國的藝術策展人金先生提問的:「Why bunnies?」好了!我得要慎重地回答了。
有三組答覆,你可以選擇滿足自己的答案來聽,而它們都在我繪畫過程的某一時刻發散過或輕或重的影響力。
我可以既人文又懷舊地回答道:我父親生長在蘇州,中年來台,受到母親這個道地台北姑娘的吸引,成立了新的家庭,生下了我、以及姐姐、哥哥、和妹妹。選擇名為尼尼(nini)的兔子為主角,因為母親姓倪,屬兔。又曾經,一個愛爾蘭朋友說,nini在愛爾蘭語是妹妹之意(此語尚待查證,因為此兄當時正值酒醉酩酊之際),「妹妹」又是我兒時的小名,綜合這些小因緣,都令我對兔子,對尼尼這名字有一份來自前世的親切感。
另外,我也可以就心理層面上來分析「為何兔子?」兔子外型脆弱、面部鮮有表情,你同情牠,所以認同牠,讓牠領你進入牠的世界,也就是畫裡。在畫面上,牠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有時主觀,有時旁觀,你擔心牠身處大海、暗夜的柔弱,又怕牠迷航、失落;但有時又懾於牠毫不以為意的安適態度,「Why not? Why not bunnies?」縱使以上種種,我想,比較偏向我個人的答案則是:因為長期與雕塑家先生一起生活,共用畫室,又好像是創作道路上的夥伴一樣,不停地對話。如此數十年的經驗,不難想像,我筆下畫的,不再只是兔子而已,也可以是一個個造型極簡、酷似兔子的白或黑色的抽象雕塑吧!而我更無法否認的,是過去長年研究插畫藝術又從事插畫家一職,一種對於外來的刺激能敏感接收立論,加上「傳播訊息」的使命感與執著已經深植我的內在,如影隨形,而且大到想放棄都難,於是漸漸地,黑白兔子有了動作,也有了情感,透過畫面的色彩、造型等等元素,又藉著一個個或常或短的標題,牠自己成就了一張張與觀賞者之間的對話,有人說,這種形式的對話,像是心弦上的共鳴,所以就稱它作「共鳴的開始」吧!
待續……
故事發生在那年三月一個無聊的午後……
我坐在畫桌前,百無聊賴地盯著那張畫了塗、塗了擦的畫紙,明知交稿日期在即,內在的我卻只想把這份責任心丟出去,跟它說「拜拜」!我真心只想打混,只想塗鴉……
三月下旬在西方文化裡,正值正復活節的前夕。不論走過店家或是打開電視,最不容易忽視的,就是代表春天即將降臨的復活節兔子。是不是這個肇因,至今也無從考起。總之,那個片刻,不知哪兒乍現的靈光,在我手下出現了一隻奇怪的動物,那是個造型頗為詭異的兔子!說不出喜歡或不喜歡,但是那整個下午,我竟然忙著與這隻小動物互動:「有事嗎?」我好像問。「沒事,有點話。」牠好像回答。之後十幾、二十個與當時工作全然不相關的兔子前仆後繼地在畫紙上出現:穿雨衣的兔子、跟大兔子對話的小兔子、跟影子牽手的兔子、夢遊兔子、美容院燙髮的兔子、碗中的兔子、雕塑與兔子……好像牠們在我體內沈潛了好久好久,終於在那個下午像決堤似的一個緊接一個流瀉了出來,來不及似的!好像牠們有話要說,是我有話要說嗎?我像個長久不曾開口的人,終於張了口,話語像是滾出來似的,生澀又不穩定,不但跳動還彼此歪斜碰撞……
之後,為了確認那是我的原創,而非在哪兒被哪張圖畫影響,我還特地上網請問了谷哥大神,等確認了那是絕無僅有的首創之後,我頒給了這隻小兔子牠的首張身分證:尼尼。隨後幾個月,第一、二、三、四張等等的尼尼繪畫相繼問世……
現在回想,怎麼也無法想像,當年那個神奇的午後,開啟了我人生的下一個起點。雖然至此,我的插畫工作好像也順道落下了幕,但事實真是如此?我從插畫工作,走到純藝術創作,一個落幕式和一個開場白之間,真能以一線隔之?它們之間的切換,看似是出版業和畫廊業的差別;作品的呈現,也是在紙本書上和在畫布上的區分,之間講的是不相關的兩回事。這麼多年來我不斷回望,今日終於明白了,這不是同一個創作者的前後兩個人生,而是隨著年歲漸增,所知所感來回擺盪,此消彼長後而組織起來的一條長橋。我從橋的這一頭,慢慢走著到達了另一頭,不管之前我做什麼開始,其間轉折做了什麼,最終又以什麼結束,每一段經歷加起來的林林總總,營造出來的就是今日的我這個獨一無二的創作者,創作著現在這樣的作品。之間每個經歷都是必然的存在,似乎不存在著偶然。一直以來,每當有人問我為什麼畫兔子?我的回答常常是各種的——直接的、間接的、潛意識、顯意識……現在,這些意外闖入我畫布上的兔子已逾十年,我看著牠們安適地坐著看著我,其實,我最無法否認的是自己過去二十多年的插畫經驗,使我選擇了兔子這具有插畫氣質的形象,作為藝術創作的開始。一個人若決定開始創作,即便是抽象創作,這創作必有其源自何處,怎能僅因為想要創作,作品就誕生了?我在無聊乏悶時塗鴉的各種兔子中,還有比大家現在看過的更為詭異的造型,我在大量的塗鴉中,挑選出較能適任於繪畫中的兔子們,讓牠們用身體、眼神、動作,擔當我的繪畫中的主角、配角,或是路人甲乙丙……當時只是抱著好玩的心情創作,沒想到牠們艱鉅的任務就此開始,而且到今天已經邁入第二個十年了!
共鳴的開始——為何兔子?為何尼尼?
自從我的第一張兔子繪畫問世,這個問題就不停地被提出,多半是閒聊間好奇的問題。但是有一次,竟然是一位韓國的藝術策展人金先生提問的:「Why bunnies?」好了!我得要慎重地回答了。
有三組答覆,你可以選擇滿足自己的答案來聽,而它們都在我繪畫過程的某一時刻發散過或輕或重的影響力。
我可以既人文又懷舊地回答道:我父親生長在蘇州,中年來台,受到母親這個道地台北姑娘的吸引,成立了新的家庭,生下了我、以及姐姐、哥哥、和妹妹。選擇名為尼尼(nini)的兔子為主角,因為母親姓倪,屬兔。又曾經,一個愛爾蘭朋友說,nini在愛爾蘭語是妹妹之意(此語尚待查證,因為此兄當時正值酒醉酩酊之際),「妹妹」又是我兒時的小名,綜合這些小因緣,都令我對兔子,對尼尼這名字有一份來自前世的親切感。
另外,我也可以就心理層面上來分析「為何兔子?」兔子外型脆弱、面部鮮有表情,你同情牠,所以認同牠,讓牠領你進入牠的世界,也就是畫裡。在畫面上,牠既是主角,又是配角;有時主觀,有時旁觀,你擔心牠身處大海、暗夜的柔弱,又怕牠迷航、失落;但有時又懾於牠毫不以為意的安適態度,「Why not? Why not bunnies?」縱使以上種種,我想,比較偏向我個人的答案則是:因為長期與雕塑家先生一起生活,共用畫室,又好像是創作道路上的夥伴一樣,不停地對話。如此數十年的經驗,不難想像,我筆下畫的,不再只是兔子而已,也可以是一個個造型極簡、酷似兔子的白或黑色的抽象雕塑吧!而我更無法否認的,是過去長年研究插畫藝術又從事插畫家一職,一種對於外來的刺激能敏感接收立論,加上「傳播訊息」的使命感與執著已經深植我的內在,如影隨形,而且大到想放棄都難,於是漸漸地,黑白兔子有了動作,也有了情感,透過畫面的色彩、造型等等元素,又藉著一個個或常或短的標題,牠自己成就了一張張與觀賞者之間的對話,有人說,這種形式的對話,像是心弦上的共鳴,所以就稱它作「共鳴的開始」吧!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