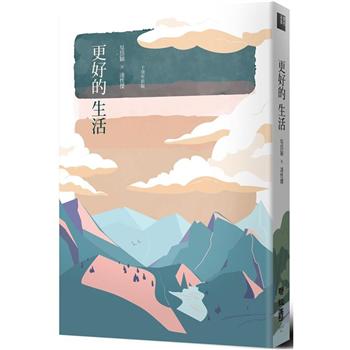序文節選
詩與思的高度結合── 序《更好的生活》隱地
詩是一切藝術的精華。讀詩、寫詩、朗誦詩或是賞析詩,都是優質生活、更好的生活,甚至是最好的生活。有一天,如果連商人和政治人物也肯接近詩,說話的時候能引用一兩行詩句,均屬加分行為;而戀人的生活裡若加了詩,更是集美好生活之大成,讓人覺得這世界美如月光燦爛如朝陽。
賞析一首詩,評介一首詩,類似詩導讀的詩評詩論集,在台灣,早年蕭蕭、張漢良、羅青、張默、向明、白靈、陳義芝、陳幸蕙⋯⋯許許多多詩人、教授都曾寫過編過類似的詩選和詩評集,但像凌性傑和吳岱穎這樣由兩人合寫合編的書並不多,更特別的是,兩人的文筆調性類似,若不看書末兩人分別撰寫的篇目,一時還真不容易分辨何篇由何人執筆。
凌性傑和吳岱穎都是年輕詩人中的閃亮矚目之星,前途未可限量,兩人都在建國中學擔任國文老師,年齡相仿、興趣相同,兩人都熱愛文學,如今合寫一冊賞詩讀本,卻更超越賞詩讀本的範圍,解析一首詩的結構和美學之外,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本身就是篇篇質地精美的敘情散文,全書充滿睿智的思維,也是他倆自我成長的心路歷程。讀此書,彷彿在詩園散步,不但思考詩的問題,同時也思考人的問題。透過此書,我們不但跟隨兩位詩人進入奼紫嫣紅的詩花園,而且他倆把每一首詩分析得神韻分明,譬如凌性傑〈事物的相關〉一文,論及馮至十四行詩,他幾乎讓詩人馮至復活在我們眼前,把五四年代拉成一條線,宛若接上電源,讓我們清清楚楚和現代詩劃上等號,真的是將一個「看似毫無相關的一切,在一個光影幽微的午後兜攏在一起,充滿了神祕與趣味」。何況還讓我們懂得十四行詩的來源,結構和韻式作法。
吳岱穎也是一位優質的詩評家,他能把一首好詩好在哪裡說得透透徹徹明明白白,譬如在分析陳義芝的〈手稿〉一詩之前,他先寫出自己和建中學生之間的一段師生情誼,紅樓少年的青春心念和肉身,他全了然於心,並自比是動物園的飼育員和馬戲團的馴獸師。至此,點出作者開首兩句:「生活就是一場儀式,生命本身就是一種獻祭」引言的意義和源由,並帶出陳義芝「溫暖中暗藏寒涼,熱情裡透露冷靜」的詩篇,接著像說明書般的,將〈手稿〉的地基和高度,從各個角落闡釋,讓讀者終於了解經過古文經典薰陶從中文系出身的詩人畢竟和自學自練者有所不同。
吳岱穎生命裡第一個接觸的詩人是楊牧。那時他就讀花蓮中學,原名王靖獻的老學長楊牧隨著老校長在走廊上走過⋯⋯升高三的暑假,吳岱穎又偶然地在公共電視頻道看到楊牧的身影,詩人在螢光幕上一筆一畫寫著自己的詩句「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就是這一行詩,引發吳岱穎寫下生平第一首名為〈雪止〉的詩。等到高三準備考試的艱難時光裡,吳岱穎在花蓮唯一一家大型書局(書局如今還在嗎?)裡買下楊牧的詩集《有人》,而這也是吳岱穎所購買的第一本詩集。
其餘諸篇,也均有勝場,將各個詩人的特質均能娓娓道來,凌性傑和吳岱穎共選了卞之琳、余光中、商禽、鄭愁予、吳晟、陳育虹、陳黎、羅智成、莫那能、焦桐、顧城、瓦歷斯.諾幹、海子、許悔之、林婉瑜、羅毓嘉等二十五家詩作討論,從徐志摩到林育德,時間縱橫七、八十年,空間更是自台灣綿亙至整個中國大陸,可謂是一本全方位頗具代表性的抽樣性詩評和詩賞析選集。
可見只要有心努力,任何年輕的文學種子,將來都有開花結果,成為一棵大樹的可能。
內文選摘
偶然與巧合
徐志摩〈偶然〉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失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在午後的陽光中,把《慈悲情人》讀完了,心頭惻惻。鍾文音還是那麼勇敢,那麼野性,在文字裡帶出愛的存在與毀滅。小說中的女主角浪跡天涯,在遠走佛國時發展出短暫的情緣,仍然不斷懷想最初的戀人︱︱ 遙遠的昔日,童男童女走進一家廉價旅館,想要用最純潔的肉身作為愛的報償,他們「還沒被哀傷毒素感染,不知人生是有過去有未來。」而這一段愛欲劫毀,要用一生來記憶與贖救,代價是何其沉重。「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是張愛玲對胡蘭成說過的話。若不是因為明白了,我想鍾文音大概寫不出這麼憂傷的作品。因緣聚散,好像雲迷霧繞,讓人身在其中卻怎麼也看不清自己。
每到六月我都會嗅到校園裡告別的氣味,年復一年的熟悉它,看著生命中的來來去去不斷發生。即將走出這個校園的青春身影來到我面前,問說可不可以在畢業冊上留幾句話給他們。彷彿有了一些勉勵祝福的話語,以及許多別具個性的簽名,就可以毫不猶豫的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了。幫幾個畢業生題辭後,在二樓走廊上俯瞰著操場,舞台架設好了,畢業典禮再過一天就要舉行⋯⋯前一天整個城市被雷雨胞籠罩,大家都擔心雨勢會持續多久。不過一夜之間,雨就停了,然後天空裡看不見半片雲。靜靜的站著,我不由得又想起D︱︱ 那個聰慧早熟的學生,把自己的青春獻祭給愛情,一再迷路。我打電話探問,想要知道他的近況。我以為他已經好好的了,卻只能在欷吁中掛斷電話。暗自揣想,如果能夠逆迴時光,D會不會希望那個美麗的盛夏不曾發生,沒有買摩托車,也沒有遇見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女孩。
幾年過去了,我卻感覺這些似乎都是昨天的事。只是那些昨天,實際上已經非常遙遠了。我告訴D,愛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與愛的輕重無關,而是取決於命運的干涉有多深。
電影《偶然與巧合》裡,皮耶對梅莉安說:「越大的不幸越值得去經歷。」竟然一語成讖,人的意志再怎麼大,也大不過命運。梅莉安與男舞者相戀結婚生下塞吉,後因理念不合分手。梅莉安帶八歲的塞吉來到威尼斯,遇見了賣假畫的皮耶。皮耶將梅莉安母子畫入作品中,進而展開一場熱戀。然而在度假期間,皮耶帶著塞吉乘帆船出海時發生意外,攝影機記錄了他們生前的最後影像。傷心的梅莉安便帶著這部攝影機走訪世界,拍攝塞吉未完的心願︱︱ 去加拿大哈德遜灣看北極熊、訪問冰上曲棍球員柏諾姆、到阿卡波柯看死亡之躍的高空跳水。在這趟旅程中,梅莉安的攝影機失而復得,她也從企圖尋死的悲痛中找到活下去的希望。皮耶生前曾說:「死亡是人類的摯友,人生最大的謊言。」梅莉安的身影在真實與謊言之間擺盪,終於安頓了自己。
不可避免的,任何一場感情風暴,來去之間令人猝不及防。徐志摩(一八九 七︱︱一九三一)的愛情遭遇大抵也是如此,簡短的〈偶然〉詩中,似乎藏了一則跟遺憾有關的人生故事。這首詩寫於一九二六年,刊載於五月二十七日《晨報副刊.詩鐫》第九期,署名志摩。這也是後來徐志摩和陸小曼合寫的劇本《卞昆岡》(一九二八年發表)裡老瞎子的唱詞。現代詩創作藉由鋪陳意象來表情達意,徐志摩可說是箇中高手。〈再別康橋〉如此,〈偶然〉也不例外。看似隨機選取的意象,其實都有著本質上的相關,構成完整的意義體系。詩句中的每一物像,都關涉到最內裡、最細緻的感情,不能以割裂、孤立的方式來看待。
這首詩結構齊整,兩小節互為對應,除了是音樂性的安排,也是情感的推衍使然。第一小節從開頭的兩行可以發現,「天空裡的一片雲」與「波心」相映照,代表我與你彼此相遇的偶然。一旦雲移影逝,或是驟起波瀾,相對應的關係就會消失無痕跡。而詩人故作豁達的說:「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刻意淡化情緒︱︱「不必訝異」、「無須歡喜」,適足以說明因為巧合際會而產生的心理變化。可惜的是,不過一瞬之間,美好的遇合消失無蹤,彷若未曾發生。用這樣的形象語言來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情愛的聚散,尤其具有說服力。徐志摩崇拜的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漂鳥集》中是這麼講 的:「生命有如渡過一重大海,我們相遇在這同一的狹船裡。死時我們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短短幾行話,便把生命歷程中的所有遭逢,寫得既輕盈又透徹。
第二小節則把場景帶到黑夜的海上,景象更為壯闊。如果聯繫著前一節來看,雲影與水波各有去向,而天空突來的閃光,見證了一切。詩人的口氣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而不是「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一方面避免了重複與囉唆,一方面也把「方向」特別標舉出來,句子寫得相當漂亮。「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把忘卻與記取講得何其輕易,然而情緒又是何其沉重。我相信這是一種故作瀟灑,否則不會在結尾點出這場交會是「互放的光亮」。他在日記裡說過:「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又說:「我唯一的靠傍是剎那間的靈通。」徐志摩人生與詩藝的美感,就在這首詩裡融為一體了。
徐志摩在中國現代詩史上的重要意義,在於他的書寫出乎至情至性、唯美浪漫,以及對新格律的追求。這首詩在格律上頗見功力,徐志摩匠心獨運,在重複中設計了變化。於是原本可能流於呆板的韻律,變得靈動起來。全詩前後兩節的格律對稱,每一節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五句安排了相似的音步。中間的三、四句則插入了較短的音步,每句五個字。句子的長短調節得宜,嚴謹之中亦見灑脫。卞之琳說:「這首詩在作者詩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陳夢家則表示,徐志摩從〈偶然〉諸作之後,畫開了前後兩期的鴻溝,「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氣,用整齊柔麗清爽的詩句,來寫那微妙的靈魂的祕密。」
當時的徐志摩,靈魂的祕密究竟是什麼呢?或許又是跟愛情有關的事。我一直相信,愛情是一種美麗的交換︱︱ 換我心為你心,消弭了存在的界線,獲得一種真實活著的整體感。只要擁有這樣的體驗,剎那即可是永恆。所以當時光一點一滴流逝,生命變得平淡枯寂的時候,總喜歡惦記那些恍若煙花燦爛的愛。一切都是偶然與巧合,教人不得不相信。某些偶然中的偶然、巧合中的巧合,讓我知道了,什麼叫作至死方休。
愛與不愛的問題,不也是偶然與巧合的問題嗎?當下的明白,往往不是真正的明白。總是要事過境遷之後才漸漸看清楚,那許多的理所當然。D對我說,很可能又要放棄了。眼前的一切,好像不再具有吸引力,點不燃他的熱情。我沒再問,上回他說到的那個女孩。我歎了一口氣說,或許所有的相遇,都是某種形式的錯過。也不敢問D,還寫不寫詩?還相不相信自己有追求美好的天分?仔細算來,已經是三年過去了。生活在同一個城市,我與D幾度約著要一起痛飲,卻又屢屢無法踐約。這次如果再聚不成,D可能就要休學去當兵,離開這個城市很長一段時間了。生命裡有這樣一段停頓,或者說是暫時離開軌道的時光,想必也是好的。不能重來的人生,最好能夠因此變得可信一些。
鍾文音說:「光是相信的本身就有力量了,甚至無需任何的儀式。」我很想告訴D,互放的光亮暗下以後,這世界仍有其他的光亮可以相信。
因為慈悲,因為懂得,因為那是我們相信的。
詩與思的高度結合── 序《更好的生活》隱地
詩是一切藝術的精華。讀詩、寫詩、朗誦詩或是賞析詩,都是優質生活、更好的生活,甚至是最好的生活。有一天,如果連商人和政治人物也肯接近詩,說話的時候能引用一兩行詩句,均屬加分行為;而戀人的生活裡若加了詩,更是集美好生活之大成,讓人覺得這世界美如月光燦爛如朝陽。
賞析一首詩,評介一首詩,類似詩導讀的詩評詩論集,在台灣,早年蕭蕭、張漢良、羅青、張默、向明、白靈、陳義芝、陳幸蕙⋯⋯許許多多詩人、教授都曾寫過編過類似的詩選和詩評集,但像凌性傑和吳岱穎這樣由兩人合寫合編的書並不多,更特別的是,兩人的文筆調性類似,若不看書末兩人分別撰寫的篇目,一時還真不容易分辨何篇由何人執筆。
凌性傑和吳岱穎都是年輕詩人中的閃亮矚目之星,前途未可限量,兩人都在建國中學擔任國文老師,年齡相仿、興趣相同,兩人都熱愛文學,如今合寫一冊賞詩讀本,卻更超越賞詩讀本的範圍,解析一首詩的結構和美學之外,這本書最大的特點在於本身就是篇篇質地精美的敘情散文,全書充滿睿智的思維,也是他倆自我成長的心路歷程。讀此書,彷彿在詩園散步,不但思考詩的問題,同時也思考人的問題。透過此書,我們不但跟隨兩位詩人進入奼紫嫣紅的詩花園,而且他倆把每一首詩分析得神韻分明,譬如凌性傑〈事物的相關〉一文,論及馮至十四行詩,他幾乎讓詩人馮至復活在我們眼前,把五四年代拉成一條線,宛若接上電源,讓我們清清楚楚和現代詩劃上等號,真的是將一個「看似毫無相關的一切,在一個光影幽微的午後兜攏在一起,充滿了神祕與趣味」。何況還讓我們懂得十四行詩的來源,結構和韻式作法。
吳岱穎也是一位優質的詩評家,他能把一首好詩好在哪裡說得透透徹徹明明白白,譬如在分析陳義芝的〈手稿〉一詩之前,他先寫出自己和建中學生之間的一段師生情誼,紅樓少年的青春心念和肉身,他全了然於心,並自比是動物園的飼育員和馬戲團的馴獸師。至此,點出作者開首兩句:「生活就是一場儀式,生命本身就是一種獻祭」引言的意義和源由,並帶出陳義芝「溫暖中暗藏寒涼,熱情裡透露冷靜」的詩篇,接著像說明書般的,將〈手稿〉的地基和高度,從各個角落闡釋,讓讀者終於了解經過古文經典薰陶從中文系出身的詩人畢竟和自學自練者有所不同。
吳岱穎生命裡第一個接觸的詩人是楊牧。那時他就讀花蓮中學,原名王靖獻的老學長楊牧隨著老校長在走廊上走過⋯⋯升高三的暑假,吳岱穎又偶然地在公共電視頻道看到楊牧的身影,詩人在螢光幕上一筆一畫寫著自己的詩句「但知每一片波浪/都從花蓮開始⋯⋯」,就是這一行詩,引發吳岱穎寫下生平第一首名為〈雪止〉的詩。等到高三準備考試的艱難時光裡,吳岱穎在花蓮唯一一家大型書局(書局如今還在嗎?)裡買下楊牧的詩集《有人》,而這也是吳岱穎所購買的第一本詩集。
其餘諸篇,也均有勝場,將各個詩人的特質均能娓娓道來,凌性傑和吳岱穎共選了卞之琳、余光中、商禽、鄭愁予、吳晟、陳育虹、陳黎、羅智成、莫那能、焦桐、顧城、瓦歷斯.諾幹、海子、許悔之、林婉瑜、羅毓嘉等二十五家詩作討論,從徐志摩到林育德,時間縱橫七、八十年,空間更是自台灣綿亙至整個中國大陸,可謂是一本全方位頗具代表性的抽樣性詩評和詩賞析選集。
可見只要有心努力,任何年輕的文學種子,將來都有開花結果,成為一棵大樹的可能。
內文選摘
偶然與巧合
徐志摩〈偶然〉
我是天空裡的一片雲,
偶爾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訝異,
更無須歡喜——
在轉瞬間消失了蹤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記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這交會時互放的光亮!
在午後的陽光中,把《慈悲情人》讀完了,心頭惻惻。鍾文音還是那麼勇敢,那麼野性,在文字裡帶出愛的存在與毀滅。小說中的女主角浪跡天涯,在遠走佛國時發展出短暫的情緣,仍然不斷懷想最初的戀人︱︱ 遙遠的昔日,童男童女走進一家廉價旅館,想要用最純潔的肉身作為愛的報償,他們「還沒被哀傷毒素感染,不知人生是有過去有未來。」而這一段愛欲劫毀,要用一生來記憶與贖救,代價是何其沉重。「因為懂得,所以慈悲。」這是張愛玲對胡蘭成說過的話。若不是因為明白了,我想鍾文音大概寫不出這麼憂傷的作品。因緣聚散,好像雲迷霧繞,讓人身在其中卻怎麼也看不清自己。
每到六月我都會嗅到校園裡告別的氣味,年復一年的熟悉它,看著生命中的來來去去不斷發生。即將走出這個校園的青春身影來到我面前,問說可不可以在畢業冊上留幾句話給他們。彷彿有了一些勉勵祝福的話語,以及許多別具個性的簽名,就可以毫不猶豫的走向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了。幫幾個畢業生題辭後,在二樓走廊上俯瞰著操場,舞台架設好了,畢業典禮再過一天就要舉行⋯⋯前一天整個城市被雷雨胞籠罩,大家都擔心雨勢會持續多久。不過一夜之間,雨就停了,然後天空裡看不見半片雲。靜靜的站著,我不由得又想起D︱︱ 那個聰慧早熟的學生,把自己的青春獻祭給愛情,一再迷路。我打電話探問,想要知道他的近況。我以為他已經好好的了,卻只能在欷吁中掛斷電話。暗自揣想,如果能夠逆迴時光,D會不會希望那個美麗的盛夏不曾發生,沒有買摩托車,也沒有遇見一個正當最好年齡的女孩。
幾年過去了,我卻感覺這些似乎都是昨天的事。只是那些昨天,實際上已經非常遙遠了。我告訴D,愛是要付出代價的。這代價,與愛的輕重無關,而是取決於命運的干涉有多深。
電影《偶然與巧合》裡,皮耶對梅莉安說:「越大的不幸越值得去經歷。」竟然一語成讖,人的意志再怎麼大,也大不過命運。梅莉安與男舞者相戀結婚生下塞吉,後因理念不合分手。梅莉安帶八歲的塞吉來到威尼斯,遇見了賣假畫的皮耶。皮耶將梅莉安母子畫入作品中,進而展開一場熱戀。然而在度假期間,皮耶帶著塞吉乘帆船出海時發生意外,攝影機記錄了他們生前的最後影像。傷心的梅莉安便帶著這部攝影機走訪世界,拍攝塞吉未完的心願︱︱ 去加拿大哈德遜灣看北極熊、訪問冰上曲棍球員柏諾姆、到阿卡波柯看死亡之躍的高空跳水。在這趟旅程中,梅莉安的攝影機失而復得,她也從企圖尋死的悲痛中找到活下去的希望。皮耶生前曾說:「死亡是人類的摯友,人生最大的謊言。」梅莉安的身影在真實與謊言之間擺盪,終於安頓了自己。
不可避免的,任何一場感情風暴,來去之間令人猝不及防。徐志摩(一八九 七︱︱一九三一)的愛情遭遇大抵也是如此,簡短的〈偶然〉詩中,似乎藏了一則跟遺憾有關的人生故事。這首詩寫於一九二六年,刊載於五月二十七日《晨報副刊.詩鐫》第九期,署名志摩。這也是後來徐志摩和陸小曼合寫的劇本《卞昆岡》(一九二八年發表)裡老瞎子的唱詞。現代詩創作藉由鋪陳意象來表情達意,徐志摩可說是箇中高手。〈再別康橋〉如此,〈偶然〉也不例外。看似隨機選取的意象,其實都有著本質上的相關,構成完整的意義體系。詩句中的每一物像,都關涉到最內裡、最細緻的感情,不能以割裂、孤立的方式來看待。
這首詩結構齊整,兩小節互為對應,除了是音樂性的安排,也是情感的推衍使然。第一小節從開頭的兩行可以發現,「天空裡的一片雲」與「波心」相映照,代表我與你彼此相遇的偶然。一旦雲移影逝,或是驟起波瀾,相對應的關係就會消失無痕跡。而詩人故作豁達的說:「你不必訝異,更無須歡喜,在轉瞬間消滅了蹤影。」刻意淡化情緒︱︱「不必訝異」、「無須歡喜」,適足以說明因為巧合際會而產生的心理變化。可惜的是,不過一瞬之間,美好的遇合消失無蹤,彷若未曾發生。用這樣的形象語言來談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特別是情愛的聚散,尤其具有說服力。徐志摩崇拜的印度詩人泰戈爾的《新月漂鳥集》中是這麼講 的:「生命有如渡過一重大海,我們相遇在這同一的狹船裡。死時我們同登彼岸,又向不同的世界各奔前程。」短短幾行話,便把生命歷程中的所有遭逢,寫得既輕盈又透徹。
第二小節則把場景帶到黑夜的海上,景象更為壯闊。如果聯繫著前一節來看,雲影與水波各有去向,而天空突來的閃光,見證了一切。詩人的口氣是「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而不是「你有你的方向,我有我的方向」,一方面避免了重複與囉唆,一方面也把「方向」特別標舉出來,句子寫得相當漂亮。「你記得也好,最好你忘掉」,把忘卻與記取講得何其輕易,然而情緒又是何其沉重。我相信這是一種故作瀟灑,否則不會在結尾點出這場交會是「互放的光亮」。他在日記裡說過:「戀愛是生命的中心與精華,戀愛的成功是生命的成功,戀愛的失敗是生命的失敗,這是不容疑義的。」又說:「我唯一的靠傍是剎那間的靈通。」徐志摩人生與詩藝的美感,就在這首詩裡融為一體了。
徐志摩在中國現代詩史上的重要意義,在於他的書寫出乎至情至性、唯美浪漫,以及對新格律的追求。這首詩在格律上頗見功力,徐志摩匠心獨運,在重複中設計了變化。於是原本可能流於呆板的韻律,變得靈動起來。全詩前後兩節的格律對稱,每一節的第一句、第二句、第五句安排了相似的音步。中間的三、四句則插入了較短的音步,每句五個字。句子的長短調節得宜,嚴謹之中亦見灑脫。卞之琳說:「這首詩在作者詩中是在形式上最完美的一首。」陳夢家則表示,徐志摩從〈偶然〉諸作之後,畫開了前後兩期的鴻溝,「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氣,用整齊柔麗清爽的詩句,來寫那微妙的靈魂的祕密。」
當時的徐志摩,靈魂的祕密究竟是什麼呢?或許又是跟愛情有關的事。我一直相信,愛情是一種美麗的交換︱︱ 換我心為你心,消弭了存在的界線,獲得一種真實活著的整體感。只要擁有這樣的體驗,剎那即可是永恆。所以當時光一點一滴流逝,生命變得平淡枯寂的時候,總喜歡惦記那些恍若煙花燦爛的愛。一切都是偶然與巧合,教人不得不相信。某些偶然中的偶然、巧合中的巧合,讓我知道了,什麼叫作至死方休。
愛與不愛的問題,不也是偶然與巧合的問題嗎?當下的明白,往往不是真正的明白。總是要事過境遷之後才漸漸看清楚,那許多的理所當然。D對我說,很可能又要放棄了。眼前的一切,好像不再具有吸引力,點不燃他的熱情。我沒再問,上回他說到的那個女孩。我歎了一口氣說,或許所有的相遇,都是某種形式的錯過。也不敢問D,還寫不寫詩?還相不相信自己有追求美好的天分?仔細算來,已經是三年過去了。生活在同一個城市,我與D幾度約著要一起痛飲,卻又屢屢無法踐約。這次如果再聚不成,D可能就要休學去當兵,離開這個城市很長一段時間了。生命裡有這樣一段停頓,或者說是暫時離開軌道的時光,想必也是好的。不能重來的人生,最好能夠因此變得可信一些。
鍾文音說:「光是相信的本身就有力量了,甚至無需任何的儀式。」我很想告訴D,互放的光亮暗下以後,這世界仍有其他的光亮可以相信。
因為慈悲,因為懂得,因為那是我們相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