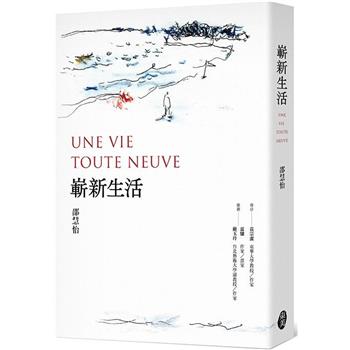推薦序 片斷的生活:讀《嶄新生活》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黃宗潔
多年前某次去日本旅行,在天守閣的觀景台不免俗地進行著觀光客常見的行為:用投幣式望遠鏡胡亂對焦。結果,我看見了遠方某個辦公大樓裡還未下班的人影。當時的心情有點微妙,像是不慎窺見了別人不欲公開的私隱,但另一種心情則是,身為觀光客的我,與這位永遠也不會知道是誰的上班族,在一瞬之間產生了(儘管只有我知道的)交集,我揣想著他下班之後會像個普通白領離開辦公室、然後回到自己的生活,除了那一瞬之外,這個人的人生以及其他世界上某個角落發生的,他人的人生,都在我所看不見之處繼續著。
我有時會被這樣的心思糾纏,想像著視野所不能及之處的,他人的生活,卻很難具體說出那抽象又隱微的心緒,究竟是被什麼所牽動。直到閱讀岸政彥的《片斷人間》,看到他提及某次出差那霸市的經驗,在深夜途經某間度假飯店時,下意識盯著飯店窗戶的他,偶然看見電梯停了下來,他稍稍瞥見走進電梯的人的後腦勺,電梯門隨即關上。在那一瞬間,岸政彥說:
當下我卻覺得,自己和這個不知名的某人,『一起搭上了』這間飯店的電梯。既不知長相、姓名、性別和年齡,也不知前來沖繩的理由或搭電梯的目的—一個我一無所知的陌生人,正好在某間飯店的某層樓走進電梯,那瞬間的景象,恰巧被夜晚走在路上的我瞧見。而這件事除了我,沒人知道。
看到這段話的時候,我內心「啊」了一聲,就是這樣的感受!竟然有人如此具體地寫出了我內心那無以名之的悸動。一個過去與未來我們都將一無所知的人,但他的生命有非常短暫的瞬間,與你發生微不足道的,甚且無意義的交集。當然還有更多,是連交集也不存在的,獨一無二、無窮無盡地散落的片斷。這個世界,是由無數這樣散落的片斷集結而成。
閱讀邵慧怡的時候,我想起了天守閣的望遠鏡,想起了《片斷人間》,因為在她的作品中,我同樣讀到、感受到此種,對無窮無盡地散落在世上的片斷深深著迷,被其中的意義與無意義吸引的特質。這個特色,在前作《遊蕩的廓線》中已清楚得見。她的人物速寫與其畫風頗為近似:簡筆勾勒輪廓,形象精神亦隨之浮現。但細讀之後就會發現,她筆下紀錄的多數人物,無論是房東、同學、司機或其他旅途中偶遇的人,與她之間的交集,有時未必比「一起搭上」飯店電梯的陌生人多出太多。但重要的是,她仍記得他們。
因為記得,所以她寫下法國南部短暫旅行時,遇見的以色列女士。當時她買了薰衣草茶包給這位有睡眠障礙的女士,「至今我偶爾會想起她,但我想就算再見面,恐怕我們也認不出彼此了。」她說。在清晨五點多的史特拉斯堡,一對老夫妻指引她正確的方向後,她寫下:「之後,他們道別與祝福。這輩子他們不可能再相遇了,但這也無妨,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都被這一刻影響了。他們說不出來那是什麼,但他們隱隱約約知道。」這隱隱約約的感受,在書末〈夢之旅〉一篇中,有了更為明顯的輪廓:
不知道明天的史特拉斯堡還下雨嗎?電影明星有沒有找到他的行李房鑰匙?車站的女服務生,仍戴著她的草帽煮咖啡?
我想我永遠不會知道了。我只知道他們留在我的記憶中,然後,可能的話,他們會在我的想像中繼續活下去,就此和真實的人生分道揚鑣。
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接下來的「如常」,或是未必如常。但他們留在我的記憶中,在我的想像中,擁有了延續的,嶄新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同樣以異國生活、移動之憶記為主要內容的《嶄新生活》,或可視為《遊蕩的廓線》之某種延續。《嶄新生活》置於書末的〈12/24/2011〉一篇,與前述〈夢之旅〉甚至具有某種遙相呼應的互文效果。
文中憶述十多年前的越南之行,邵慧怡這麼形容:「十多年前的行程,本該忘去的景與事,萍水相逢的剎那。他們。似乎靜候在角落,等待著。就像被我留在抽屜底層,那些染上淡淡顏色的相片。」她已想不起當年相遇的阿玉的臉,但仍不時想起這趟旅程,偶然也會想著,「他們現在如何了呢?」
本該忘去但未曾忘卻的萍水相逢,無須刻意渲染其中的意義及影響,但那些有意義或無意義的斷片,就是被記住了。而無數的斷片之積累,也能勾勒出形形色色的,人生風景。邵慧怡作品的好看之處,其實正在其淡筆文字的線條輪廓,就像她對記憶中阿玉的形容:「相貌早已模糊難辨,但她那開朗而舒坦的笑容,留住了。」她筆下人物形象生動,卻未必個個具體,顯然是因為她也清楚意識到岸政彥所提醒的:「記錄這種片斷性邂逅中所談到的片斷性人生,然後將其普遍性地、整體性地視為對方的人生,或詮釋為對方所屬的族群的命運,這其實是一種暴力。」因此,她對片斷的記述,以其碎片化特質而展現出某種必然的視野局限,但此種局限的視野,正是移動與行旅的必然。
正因為旅居時的相遇都是片斷性邂逅,邂逅對象既是一無所知之人,反應難以預期,自然不乏「情理及意料之外」的互動:幫朋友代購精品包時,帶著職業化笑容的優雅女售貨員,突然在遇到中國顧客時,無視其問題直接用中文大聲喊著:「沒有啦!沒—有—了—啦—!」;喜劇演員般口若懸河精力旺盛的導覽員「喬派西」,卻在第二次相遇時,無視自己的微笑與招呼,頭也不抬地說:「參加導覽的人那麼多,我哪記得誰是誰啊。」;龐畢度書店裡,要求自己幫忙挑張生日卡給小孫女的老先生,在喝咖啡的邀約被回絕後,突然表示要回家下廚而匆忙離開......
但伴隨這些意料之外的事件與互動而生的心情,無論是擔憂、偏見、不滿、好奇、驚喜、感慨或失望,邵慧怡都點到即止,有時甚至僅停留在事件本身,心情與想法則付之闕如。這讓她的文字語言具有強烈的鏡頭感,又帶有相當的疏離感。我們看見發生了些什麼,但主角為什麼來到此地?她的種種經歷帶來的所思所感、影響與改變是什麼?讀者卻未必能掌握充分的線索。這讓我想起攝影師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的一系列《無題》自拍照,每張照片都宛如劇照,能召喚觀者的熟悉感,卻不指向任何實際的電影作品。邵慧怡的散文曾被論者形容為「像看一場歐洲電影」,或許正在於她的文字所召喚的閱讀感受,同樣帶有這種由光影、氛圍、人物組成一幅幅立體畫面,指向某種似曾相識的情境之特質。
這樣的特質,也讓邵慧怡的旅行文字,未必符合一般讀者對「旅行文學」的印象,就算將這些篇章拼湊起來看,也是對話比事件多、「路上」比定點多的日常風景。但在一個全球化移動已如此普遍的年代,我們早已不需要透過他人的旅遊經驗「增廣」己身之見聞。我們需要增加的,是對這變動不居又複雜多元的世界,更細膩的理解。透過邵慧怡版的「片斷人間」,我們反倒能將這些未必依照時序地點,有些隨性的散落碎片,疊加在我們自身的碎片上,想起那些我們曾經遇過的人與事。並且像她一樣,在看盡各種碎片之後安慰自己,就算天氣與身體有時都令人感到疲憊而難以忍受,就算身上背著過大的背包、腦中有關不掉的自我貶抑,莫名其妙地帶著一條穿不上的牛仔褲,還是可以感受到:「幸運的是,竟有些糖果在褲子口袋。」
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教授 黃宗潔
多年前某次去日本旅行,在天守閣的觀景台不免俗地進行著觀光客常見的行為:用投幣式望遠鏡胡亂對焦。結果,我看見了遠方某個辦公大樓裡還未下班的人影。當時的心情有點微妙,像是不慎窺見了別人不欲公開的私隱,但另一種心情則是,身為觀光客的我,與這位永遠也不會知道是誰的上班族,在一瞬之間產生了(儘管只有我知道的)交集,我揣想著他下班之後會像個普通白領離開辦公室、然後回到自己的生活,除了那一瞬之外,這個人的人生以及其他世界上某個角落發生的,他人的人生,都在我所看不見之處繼續著。
我有時會被這樣的心思糾纏,想像著視野所不能及之處的,他人的生活,卻很難具體說出那抽象又隱微的心緒,究竟是被什麼所牽動。直到閱讀岸政彥的《片斷人間》,看到他提及某次出差那霸市的經驗,在深夜途經某間度假飯店時,下意識盯著飯店窗戶的他,偶然看見電梯停了下來,他稍稍瞥見走進電梯的人的後腦勺,電梯門隨即關上。在那一瞬間,岸政彥說:
當下我卻覺得,自己和這個不知名的某人,『一起搭上了』這間飯店的電梯。既不知長相、姓名、性別和年齡,也不知前來沖繩的理由或搭電梯的目的—一個我一無所知的陌生人,正好在某間飯店的某層樓走進電梯,那瞬間的景象,恰巧被夜晚走在路上的我瞧見。而這件事除了我,沒人知道。
看到這段話的時候,我內心「啊」了一聲,就是這樣的感受!竟然有人如此具體地寫出了我內心那無以名之的悸動。一個過去與未來我們都將一無所知的人,但他的生命有非常短暫的瞬間,與你發生微不足道的,甚且無意義的交集。當然還有更多,是連交集也不存在的,獨一無二、無窮無盡地散落的片斷。這個世界,是由無數這樣散落的片斷集結而成。
閱讀邵慧怡的時候,我想起了天守閣的望遠鏡,想起了《片斷人間》,因為在她的作品中,我同樣讀到、感受到此種,對無窮無盡地散落在世上的片斷深深著迷,被其中的意義與無意義吸引的特質。這個特色,在前作《遊蕩的廓線》中已清楚得見。她的人物速寫與其畫風頗為近似:簡筆勾勒輪廓,形象精神亦隨之浮現。但細讀之後就會發現,她筆下紀錄的多數人物,無論是房東、同學、司機或其他旅途中偶遇的人,與她之間的交集,有時未必比「一起搭上」飯店電梯的陌生人多出太多。但重要的是,她仍記得他們。
因為記得,所以她寫下法國南部短暫旅行時,遇見的以色列女士。當時她買了薰衣草茶包給這位有睡眠障礙的女士,「至今我偶爾會想起她,但我想就算再見面,恐怕我們也認不出彼此了。」她說。在清晨五點多的史特拉斯堡,一對老夫妻指引她正確的方向後,她寫下:「之後,他們道別與祝福。這輩子他們不可能再相遇了,但這也無妨,因為他們知道,他們都被這一刻影響了。他們說不出來那是什麼,但他們隱隱約約知道。」這隱隱約約的感受,在書末〈夢之旅〉一篇中,有了更為明顯的輪廓:
不知道明天的史特拉斯堡還下雨嗎?電影明星有沒有找到他的行李房鑰匙?車站的女服務生,仍戴著她的草帽煮咖啡?
我想我永遠不會知道了。我只知道他們留在我的記憶中,然後,可能的話,他們會在我的想像中繼續活下去,就此和真實的人生分道揚鑣。
我永遠不會知道他們接下來的「如常」,或是未必如常。但他們留在我的記憶中,在我的想像中,擁有了延續的,嶄新生活。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同樣以異國生活、移動之憶記為主要內容的《嶄新生活》,或可視為《遊蕩的廓線》之某種延續。《嶄新生活》置於書末的〈12/24/2011〉一篇,與前述〈夢之旅〉甚至具有某種遙相呼應的互文效果。
文中憶述十多年前的越南之行,邵慧怡這麼形容:「十多年前的行程,本該忘去的景與事,萍水相逢的剎那。他們。似乎靜候在角落,等待著。就像被我留在抽屜底層,那些染上淡淡顏色的相片。」她已想不起當年相遇的阿玉的臉,但仍不時想起這趟旅程,偶然也會想著,「他們現在如何了呢?」
本該忘去但未曾忘卻的萍水相逢,無須刻意渲染其中的意義及影響,但那些有意義或無意義的斷片,就是被記住了。而無數的斷片之積累,也能勾勒出形形色色的,人生風景。邵慧怡作品的好看之處,其實正在其淡筆文字的線條輪廓,就像她對記憶中阿玉的形容:「相貌早已模糊難辨,但她那開朗而舒坦的笑容,留住了。」她筆下人物形象生動,卻未必個個具體,顯然是因為她也清楚意識到岸政彥所提醒的:「記錄這種片斷性邂逅中所談到的片斷性人生,然後將其普遍性地、整體性地視為對方的人生,或詮釋為對方所屬的族群的命運,這其實是一種暴力。」因此,她對片斷的記述,以其碎片化特質而展現出某種必然的視野局限,但此種局限的視野,正是移動與行旅的必然。
正因為旅居時的相遇都是片斷性邂逅,邂逅對象既是一無所知之人,反應難以預期,自然不乏「情理及意料之外」的互動:幫朋友代購精品包時,帶著職業化笑容的優雅女售貨員,突然在遇到中國顧客時,無視其問題直接用中文大聲喊著:「沒有啦!沒—有—了—啦—!」;喜劇演員般口若懸河精力旺盛的導覽員「喬派西」,卻在第二次相遇時,無視自己的微笑與招呼,頭也不抬地說:「參加導覽的人那麼多,我哪記得誰是誰啊。」;龐畢度書店裡,要求自己幫忙挑張生日卡給小孫女的老先生,在喝咖啡的邀約被回絕後,突然表示要回家下廚而匆忙離開......
但伴隨這些意料之外的事件與互動而生的心情,無論是擔憂、偏見、不滿、好奇、驚喜、感慨或失望,邵慧怡都點到即止,有時甚至僅停留在事件本身,心情與想法則付之闕如。這讓她的文字語言具有強烈的鏡頭感,又帶有相當的疏離感。我們看見發生了些什麼,但主角為什麼來到此地?她的種種經歷帶來的所思所感、影響與改變是什麼?讀者卻未必能掌握充分的線索。這讓我想起攝影師辛蒂•雪曼(Cindy Sherman)的一系列《無題》自拍照,每張照片都宛如劇照,能召喚觀者的熟悉感,卻不指向任何實際的電影作品。邵慧怡的散文曾被論者形容為「像看一場歐洲電影」,或許正在於她的文字所召喚的閱讀感受,同樣帶有這種由光影、氛圍、人物組成一幅幅立體畫面,指向某種似曾相識的情境之特質。
這樣的特質,也讓邵慧怡的旅行文字,未必符合一般讀者對「旅行文學」的印象,就算將這些篇章拼湊起來看,也是對話比事件多、「路上」比定點多的日常風景。但在一個全球化移動已如此普遍的年代,我們早已不需要透過他人的旅遊經驗「增廣」己身之見聞。我們需要增加的,是對這變動不居又複雜多元的世界,更細膩的理解。透過邵慧怡版的「片斷人間」,我們反倒能將這些未必依照時序地點,有些隨性的散落碎片,疊加在我們自身的碎片上,想起那些我們曾經遇過的人與事。並且像她一樣,在看盡各種碎片之後安慰自己,就算天氣與身體有時都令人感到疲憊而難以忍受,就算身上背著過大的背包、腦中有關不掉的自我貶抑,莫名其妙地帶著一條穿不上的牛仔褲,還是可以感受到:「幸運的是,竟有些糖果在褲子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