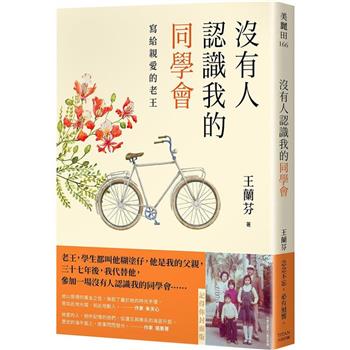〈俺不逮〉
我問爸爸:「爸,人家山東人都說『俺』,我怎麼沒聽你說過這個字?」
爸爸:「是啊,我沒這樣說過,但我們那裡確實也有這麼說的。」
爸爸突然想起什麼繼續說:「有一次回老家,在我表哥屋裡,到了晚飯時間他那個小孫子回家。奇怪啦,給他吃這個他不要,給他吃那個,那個也不要,就是一直地哭,一直地說,俺不逮,俺不逮。」
我:「蛤?什麼是俺不逮?」
爸爸:「老家的話就是我不吃、我不吃。」
我:「俺不逮呀……」
爸爸:「後來,噯,還是他媽媽聰明。走到水缸前面舀了一大瓢的水,讓他喝,喝完他就高興了。原來是口渴,小孩子又不懂得表達。」
我:「高興了然後呢?」
「然後他就什麼都逮了。」爸爸呵呵地笑起來。
〈酸餃子〉
今天我過生日,過生日就是要吃餃子。
現在大家都說水餃,但真正懂得吃餃子的北方人就是叫餃子餃子。不然怎麼有句話說「好吃不過餃子,好玩不過嫂子」(喂)呢?
以前我們家包餃子,回想起來像永恆的總是在陽光燦爛的日子,全家聚在明亮的廚房裡。我爸揉麵,搓成條狀,再切成小塊,每一小塊用手掌壓扁,再拿艀麵棍順時鐘靈巧出中心厚邊緣薄的餃子皮。好輕輕拋在旁邊預先撒好的麵粉堆裡,揚起小小一陣白色粉塵,我爸對自己的生產品老是得意,說:「看看我的,又快又好。」
等餃子皮堆出高度,我們便去拿來餐桌上。那裡有一大盆媽媽剛剛用刀反覆剁到成泥的豬絞肉、切碎的高麗菜或韭菜或胡瓜、薑末、碎蔥、麻油、醬油、鹽和一點水調出來的餡。
包餃子講究手勢,得兩手虎口同時一捏,一個半月形肚子飽滿的餃子瞬間成形,既有漂亮的荷葉邊還能嚴絲合縫不露餡。我爸我媽跟我妹都有這工夫,就我怎麼練都不成,老是得多捏個五六七八下。我餃子包得不好,但眼睛很尖,一大盤熱呼呼的餃子上桌,馬上能認得出哪些是我包的,千萬別去夾。
下餃子也有學問,我爸站在鍋邊教:「剛下時要拿漏勺這樣划,餃子才不會沉到底下去黏鍋,黏鍋就破了。然後得滾三次,每次滾了就得加涼水,一點一點加,有時得蓋鍋蓋,有時得把鍋蓋揭開。」
餃子當然要趁熱吃,熱呼呼地夾起來直接塞嘴裡,或是蘸點醬油加醋,再來顆現剝大蒜,那美味直接升級到頭等艙啊。
如果沒有馬上吃,我爸都會從位子上站起來,伸手提起那些盤子,輕輕晃一晃,讓餃子不黏在盤子上,非常堅持,簡直像個儀式似的,搆不著的他喊我們:「動一動,把盤子動一動。欸對,動一動就好。」
到現在我煮好餃子放進盤裡端上桌,也會提起盤子的一邊,輕輕來回滑動餃子,老爸像是在白色熱騰水氣的那一頭笑著:「欸對,就是這樣。」
〈老家都是這樣子〉
然後吃餃子配什麼呢?
酸辣湯?
喔喔,答錯出局。
吃餃子當然是配餃子湯。我爸樂呵呵地吸啜著燙得要命,從鍋裡舀出來白白的煮餃子水:「欸,這個好,這叫原湯化原食。」
舅舅當年第一次從台北到我們高雄家玩,回去後氣呼呼地說:「王老師太不夠意思了,我大老遠去,他只請我吃水餃配水餃湯。」
每年除夕夜,吃過晚餐爸媽便開始包餃子,包好滿滿擺一整個餐桌,就那麼到隔天,一早放完鞭炮後再煮來吃。因此每個大年初一,我們都吃酸掉的餃子。
我們抱怨,餃子放過夜都壞了。老爸這時會繃緊臉,現在想起來,他不是生氣,可能只是想掩蓋住快哭的表情。「你們懂什麼,老家都是這樣子的。」
等我們大一點,會反抗了,頂嘴說:「你們老家過年會下雪,包了丟哪裡都馬上結凍,這裡是台灣耶,而且高雄熱得要命,放一晚就壞了,我才不想吃了肚子痛。」摔筷子離席。爸爸就自己一個人坐在桌邊,默默地把所有酸餃子吃掉。
第二年除夕,爸爸包好餃子,一盤盤放進冷凍庫裡。
妥協的還有,過年時要寫的紅紙。
爸爸會把我們平常用來寫功課的書桌收乾淨,靠在陽光照得到的牆邊。然後裁出一張紅紙,要我們幫忙磨墨,恭恭敬敬用毛筆在紅紙上寫出「王氏歷代祖先牌位」,端端正正貼在牆上。桌子則擺出四樣水果或點心,拿個裝滿米的飯碗,插上三枝點燃的香。
一開始要三個小孩早晚點,後來只要求我弟做這件事,再後來連我弟也不聽話,就只有老爸自己慢慢爬到三樓,慢慢點香,慢慢插在碗裡。我們嫌這樣沒書桌寫功課,點燃的香老是害我們咳嗽。爸爸先是取消了點香,等我們都離家去念書,爸爸漸漸地也不寫紅紙不擺香桌了。
今天我過生日,當然要吃餃子,餃子好吃,一點也不酸。
但今天的生日就像老爸的酸餃子,充滿了對過去的懷念,對現今的無奈承受,和對未來悲觀的想像呢。
原來我爸那時包的不是餃子,而是一封封他走後才會寄到我手中的家書。
〈很久很久以前的愛情故事〉
我:「爸,媽媽是不是你的初戀情人啊?」
爸(停頓很久):「不是……」
我:「哇!爸你另外有初戀情人喔?是誰呀?」
爸(又想很久):「我不能說。」
我:「為什麼?」
爸:「講了妳媽媽會不樂意。」
我(小聲):「反正媽媽現在又不在這裡,爸爸你可以講啦!是誰啊?」
爸(害羞):「……是我的表姐。」
我(驚):「表兄弟姐妹不能結婚吧?」
爸:「那時候沒有關係的。」
我:「所以如果當年你沒有跑出來,就會跟你表姐結婚嗎?」
爸(堅決):「對!」
我:「哇!爸,你們以前是怎麼談戀愛的啊?」
爸:「沒有談戀愛。」
我:「啊?你剛不是說你表姐是你的初戀情人嗎?」
爸:「是啊。」
我:「沒有談戀愛怎麼算是初戀啊?」
爸:「怎麼不算呢?我喜歡她,她也喜歡我!」
我:「爸爸,你怎麼知道她喜歡你呀?她跟你說的喔?」
爸(笑):「她沒有跟我說,我也沒有跟她說,我們就是知道。」
我:「因為常常相處有默契嗎?」
爸:「也不是。我大姨跟我們不住一個村子,他們離我們還有十幾里路遠,走路的話,得走個大半天。」
我:「所以爸你根本沒有跟你表姐相處過嘛!」
爸:「有!十七歲那年,我大姨跟我表姐來我們家住了一個多月。」
我:「啊,原來是這樣,那你們都聊些什麼啊?」
爸:「我們沒說過話。」
我:「蛤?!沒說過話?!真的假的?一句話都沒說過嗎?」
爸:「嗯。」
我:「這樣怎麼知道你喜歡她、她喜歡你?」
爸:「就是知道!」
我:「那爸爸,你表姐長什麼樣子啊?」
爸:「高高的,細細的,像柳枝兒。」
我:「臉呢?臉長怎樣?」
爸(笑):「長相想不起來了。」
我:「你喜歡你表姐什麼啊?」
爸:「我也不知道,就是喜歡。」
我:「後來呢?」
爸:「後來我就跑出來了。」
我:「她現在變成怎樣了啊?」
爸:「我也不知道。」
我:「你後來回去也沒見到她嗎?」
爸:「沒有……再也沒看見過。」
【後記】漫長的等待
爸爸第一次住進台大醫院,把肝硬化造成的腹水抽掉後,馬上胃口跟精神都變得不錯,只是腦子有點糊裡糊塗,實習醫生常常來聊天測試他衰退的程度。
那天又有穿著短版白袍的年輕男生客氣地大聲跟他打招呼,然後指著我問他:
「北北,這個是誰你知道嗎?」
我爸抬頭看了半天,說:「她是網ㄌㄢ粉(山東腔的王蘭芬)。」
「那她呢?」醫生指指外籍看護。
「麗莎。」爸爸又答對了。大家都給他拍拍手。
「北北,還有一個啊,那位是誰你認識嗎?」醫生要我爸看向坐在他對面沙發上的我媽。
他點點頭說:「認識。」
「哇!你認識耶,好棒,那她是誰呢?」
老先生被問累了,把垂著的頭再抬起來一次,盯著老太太看了看,手臂舉起兩秒接著重重放下,努力打起精神回答:
「她是印尼國國王!」
嚴重的肝硬化不僅讓老爸的身體極度虛弱,併發的器官病變也使得腦部萎縮,不知道是不是這個緣故,過去十分內斂寡言、習慣憋著心事的大男人,突然不斷冒出許多我們聽來莫名其妙的言語。
例如在安寧病房時,某個早上醒來,吃過早餐,他突然心事重重地說:「哎,既然某某某都這樣說了,我們也只能照辦,這樣大家都好吧。」看似神志十分清楚地再三重複。
我問:「爸,你說的那個某某某是誰呀?」
他呵呵笑起來:「妳問我他是誰,我也記不得了。」
下午弟弟來病房,我提起這件事,他馬上說:「某某某是我高中教官啊!幾百年沒聽過這名字了,爸爸是哪根筋突然想到?」
本來以為那不過是退化過程中的某種錯亂現象罷了,轉身一忙便忘記。
我爸過世快一年,前幾天跟我妹在春水堂吃完牛肉麵,然後一邊喝著白毫烏龍一邊隨便聊天時,想起這件事,就跟當時不在場的她描述了一下,「好妙,到底是什麼讓爸爸突然想起弟弟高中教官的名字?」
我妹若有所思地說:「我記得……弟弟那時候發生過一件事,這個教官的名字我聽過。」
原來我弟高三畢業那天參與一場群架,有學弟受傷,所有人都被抓到訓導處,事情鬧得很大,教官打了好幾次電話來家裡,連大學放暑假回高雄家的她都接到過。
我跟我妹坐在春水堂裡,兩個人都哭起來。
因為那個瞬間,我們同時明白了,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我爸,腦中那些因為關心、因為忍耐、因為無法表達的愛而被鎖在意識抽屜深處的一切在大火即將燒毀整個海馬迴前,一頁頁被熱與光掀出照亮,他只是看見了並讀出那泛黃紙頁上的字句,就這樣洩露他過去難以用言語表達的對我們三個小孩那麼深的情感。
二十幾年前,我爸接到教官的電話時,一定非常非常擔心憂慮吧。
面對已經十八歲、脾氣暴躁的王家唯一的兒子,當老師的爸爸除了一如既往地諄諄教誨,並眼看著他聽完一臉不耐甩頭離去外,還能做什麼呢?
他只能忍耐,只能等待。
等待我弟有長大懂事的一天,就像我爸八十七年的人生中永遠在等待的一切那樣。
〈我帶你去〉
民國二十年出生於山東棲霞的父親,三十八年隨著山東聯中逃難到澎湖。被時代巨浪衝擊得頭昏眼花的農村小孩好不容易可以鬆口氣時,才發現自己舉目無親,還跟著其他同學一起,被違背當初國民政府所承諾會讓他們繼續就學決議的軍人將領,強迫當兵。
忍耐著,等待著,只求能活下去並期待有一天可以繼續念書。拚了命地努力及奮鬥二十年後,他才終於念完大學、謀得教職,並娶妻生子。
幾年前開始爸爸不再每天早上去小公園運動,也不再一有空就去掃爺爺奶奶的墓,只是搬著一張老藤椅坐在門口曬太陽。那時我們居然一點也沒警覺到他身體出問題。一年只回去高雄一次的我,每次打電話回家,我爸都樂呵呵扯著大嗓門喊:「都挺好的啊,人老了都這樣,腿腳不行了,走起路來頭昏眼花,哎,這是自然的退化,只要躺在床上就跟好人似的,也不痛也不癢。」
沒注意到,爸爸這樣大聲說話是因為耳朵逐漸聽不見。更沒發現他連最喜歡的饅頭都不吃,是因為牙齒都掉光光,媽媽每天把麵條煮得軟爛,讓他用牙齦慢慢磨著吞下去。幾十年來每天必讀的報紙不看了,他眼睛根本半瞎我也完全不知道。
直到走前一年,某個晚上醒來突然分不清東西南北,沒力氣下床,驚嚇得大小便失禁,我們才終於第一次醒悟,那個在我們印象中總是高大強壯、一肩扛起整個家的老爸,正在垮下去。
過往雖然知道爸爸年紀大了,但我總是想,再等一陣子吧,等雙胞胎再大一點……等他們上小學……等他們上國中……等可以放心脫手我就可以多回家陪爸媽,帶他們去檢查身體,帶他們去大陸玩,或者至少讓老爸再回一次老家。
自從我爺爺在台灣過世、我爸去老家把奶奶骨灰帶來合葬後,就再也沒回去過。我每次問:「爸,你有沒有想去哪裡玩?我帶你去!」
「大陸的大好河山倒是值得去看看啊……不過我在家裡也可環遊全世界,我把你們以前的地理課本都找出來,重新複習,搭配妳給我買的大陸地圖,就可以沿著長江、沿著黃河,一個地方一個地方遊覽,我這叫臥遊啊,也不用搭飛機也不用搭船的,妳看看多好。」
印象裡只有一次,我又問我爸要不要去哪裡走走,他不太好意思地小聲說:「三峽大壩要動工了,我還真是想趁景觀還沒有改變前去看看。」然而那時我報社工作忙,壓力很大,不知不覺就拖過了時間,後來三峽的居民開始搬家,再後來大壩完工放水,李白「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情景,終於沒被老爸等到就再也無緣相見。
爸爸生病,媽媽也因意外行動不便,我強迫著把深怕拖累子女的兩個老人搬到台北來。開始帶爸爸去動白內障手術、去裝假牙跟助聽器,爸爸那時身體還沒那麼虛弱,聽到我們要幫他做這些,氣半天,最後不得不妥協時嘆氣:「花那麼多錢幹什麼呢?萬一做好了我就死了,這些東西也沒人可以再用,不是浪費了嗎?」
而果然,等這一切都弄好,爸爸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