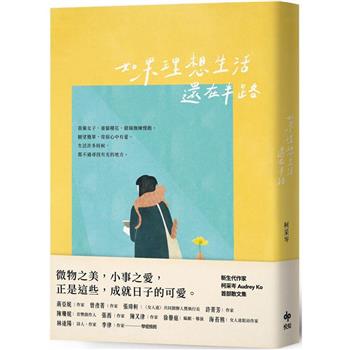三十而立
做內容很長一段時間,三十歲一直是常熱主題,為著是,人人都可能即將三十歲,人人都想像過三十歲,人人都擁有過三十歲。人總會長大,而下一代,也會即將三十。
三十歲主題翻身轉世,推陳出新,像書店暢銷排行榜,經典歷久不衰,諸如《祕密》一類,有百刷本事,人人都需要,像順路拜佛,必須求個安慰。昔有臺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的程又青談初老,洋洋灑灑寫下五十條初老症狀,從小腹多出一攤肉,再到對完美起疑,對不完美深信不疑;今有中劇《三十而已》,開場即是,三個即將三十歲的女人迎來各自一天——其中有對三十而立的抵抗,誰說三十必須而立,不過是三十而已。
於是我驚覺,《我可能不會愛你》已是將近十年前的電視劇,現在的三十不再是女子的初老焦慮,兼且要被毛茸茸的怪物追趕在後(現在回頭看,那怪物不很明擺著影射婚姻嗎),而是而立的重新想像——我要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理解這一點以後,我要成為什麼樣的自己。視角已然不同。
回想二十幾歲,剛做編輯,寫過許多揣測三十歲的文章,當年雖無經驗,起碼還能訪談周遭友人,好險想像人設也並不困難。我發現三十普遍追求的,實與二十幾歲無太大差異,不過是要到更進階的東西——說實話,已過了願意將就,或是甘願普通的年紀,無論生活、交友、關係、事業、家庭,總之就是要好,還要更好一點,並且理解,自己已有能力做到。
曾浪漫想過,要在三十歲到來之前,給自己寫封文情並茂的信,畢竟人一生只有一次三十。信是沒寫成,三十就匆匆報到。
怎麼說,這倒是也很三十歲。
當時想寫下的東西,更接近儀式性的祝禱吧——三十歲以後,無論如何,去做理想中的大人。不再害怕長大,並且明白長大的意義,其實不過是更有意願去承擔,去解難題。Problem-solving,不再只是數學算式,而有其生活意義。
總之是,事事奮力而為,但也要越來越尊重並接納自己的狀態,理解自己在乎什麼,什麼會讓自己真正快樂。身體的狀態能負荷到哪裡,什麼東西要,什麼東西不要,辨別什麼是「挑戰」,而什麼叫做「受傷」。全心全意地,去把自己給照顧好。在每個關於自己的節點之上,都更細緻處理,再往下鑽得更深一些。
而在往後的每一天裡,試圖去過如常可愛的一天。這是心願,也是實踐——在看似平凡的每一天,每一個當下,告訴自己,我想要,也能夠創造我真正喜歡的日子。
凡事奮力,在奮力中理解與觀照自己,去養成一種對事物理解的清明,去當一個願意創造,也有能力給予愛的人。把每一天活出可愛,我要當成是給三十歲的祝福與啟示。
* * *
而三十歲,能算上一句老了吧。
年老色衰、老氣橫秋、老態龍鐘、老驥伏櫪、老調重彈、老之將至、倚老賣老、老大無成。
有次我無聊,查閱與老相關成語,整排點開,所有都指涉著同樣的,經過淡淡粉飾的,殘酷結果——青年的不再、舞臺的遺失、內在的離散。老,是失去與不再擁有,是歲月在身上不願停留。至少,我們是被這樣告訴的。
老,好老。
「老」,也是這樣。當褐髮冒出細細白線,緩慢增生直至白雪整片;當肌膚出現內凹褶邊,褶內還有無數皺褶爬上滿臉;要用更多時間換一次安詳睡眠,更多金錢追求青春重現。老是無從議價的交換,我真以為過,有那樣詛咒,名為變老。
於是,當後浪滾向前浪,九零後從初出社會爛草莓,成為職場中堅分子;同儕話題從租屋好難變成哪個地段買房划算;我於是意識到,我也已經要是,即將變老的那一群。
我正在變老,正要長得超過,能夠想像得了的歲數。一個人若無法想像,是有辦法成為的嗎?
可奇妙的,更多時候,除了我們亟欲逃離的變老與成熟的框架——諸如,成家立業、早生貴子、大富大貴等照樣造句的成語之外,更多時候,我感覺到的是變老有祝福。
無論是外在樣態或內在肌理,我是從未想過,三十歲後的生活能這樣的好。這是認真實話,二十幾歲時,大概讀過太多三十歲以後的恐嚇——新陳代謝下降、賀爾蒙劇烈變化、易胖再也難瘦、色弛愛衰、列入大齡之列。內外夾攻,雙管齊下的寓言。
我沒想過我變老以後,感受到更多的是經歷過時間的僥倖——清楚自己是誰或是想成為誰,清楚自己要的與不要的是什麼,於是選擇變得比較容易,自己願意與不願追求或忍受的是什麼,也知道怎麼從內在驅動,從這裡的A點去到那個B點。
若沒有二十歲的磕絆,大抵沒有三十歲的灑脫自在。或許我也可以,將老,寫成一個中氣十足的大字。
尤其,三十歲以後,我常感覺「創造」這個詞對我的意義深重。創造是找到一個方法,一種角度,由自己起始,去學習、去理解、去給予、去參與,每一刻未來的積極發生——如果你想要的並不存在,那麼就去創造。創造是件讓人感到幸福,也特別紮實的一件事。
二十幾歲的我,有許多逞強的時候。多數時候悶頭努力,對自己多有責難,也對很多自己其實在乎的事情不夠上心,有時候甚至也懶得理會自己的心情。
而我在這陣子回頭看,越發感覺我是個非常幸運的孩子。二十多歲的我,雖有許多不成熟與磨難,但幸運是千真萬確,是有這麼多人的愛與祝福,那麼多人的支持與照顧,我才得以穩穩地走到今天。
謝謝有這麼多人,參與我這三十年的生命。
人說三十而立,我認為那意思其實是,三十歲是另一次的出生。你把自己拉出來看一看,你真的看到,過去你的每一步,都有人支持與照看著你,你是一個被愛的孩子;接著你要站起來了,你為自己負責,你為自己決定要往哪走去,同時你也要去支持其他人,把路走得自在遼闊,把世界變得如你希冀。
也有三十歲,生日的真人真事一則。
當作故事讀,而某種程度,我認為適合總結三十歲後的多數發生——務虛也務實,出手大氣,敢拿敢要,已經沒什麼好抱歉或糾結的了,有意願,就去出力,不再猶豫愛情與麵包的選擇,不是的,我想要兩個都要,我可以兩個都要。
是這樣的。
* * *
這幾年生日,多是颱風,我是夏日正午生,常感覺自己未免風暴降生,而今年三十歲的生日夜晚,晚風吹來,身體涼爽,難得風平浪靜。
晚餐吃海產火鍋,我心裡暗自決定要連續慶生三天,接著突然很想吃麵包,而且是預約明日早餐的那種——麵包、牛奶、蛋、太陽光。我對G說,「欸我們去買陳耀訓麵包埠。」搬來中山國中附近,常常想買,每一次都錯過,快快查了Google map,依然明日請早。
想吃麵包的心意很堅定,於是想,那買善菓屋,九點打烊,還有十五分鐘,騎車去松江南京。一路飆車,抵達關鍵的交叉路口,八點五十三分,等紅燈,要五十秒,開始開玩笑,說還是我在這邊跳車,跑過兩個十字路口,奔跑過去。兩個人亂笑一陣,定格五秒。我說,欸我真的要跳車,我真的覺得一定要買到麵包。
放下安全帽,開始奔跑,跑百米姿勢,連跑兩個紅綠燈,壓線衝進麵包店,八點五十五分——我想買的法國奶油卷已經賣完了。於是帶一包吐司、兩個卡士達,又被店員推坑買了芒果捲捲。「很好吃哦,這個可以放冰箱,芒果捲捲。」好,我要,而且名字聽起來很可愛,熱血的少女容易勸敗。
買完麵包,一邊想剛剛好青春啊。G說,他坐在摩托車上看我奔跑時,開始想些無聊的文案,比方說:
三十歲,放下羞恥,為愛而跑。
我說好爛,而且買麵包有什麼好羞恥,應該是放下無謂矜持吧。三十歲,放下矜持,也放下頭髮,用跑的也要買到麵包。我說你的文案不夠詩意,只能印在早餐飲料杯緣,或像靜思文體。
然後繼續亂想,「Run for thirty」,副標「30 is the new 20」,還是「running is the new sexy」,是不是很適合辦成年馬拉松大賽?壓線的時候人人有麵包,帶回家當隔日早餐。意思是說,喂,除了有獎牌的精神鼓舞以外,也請給我真材實料的實際獎品。
如果拍成微電影,慢動作播放,大標大字放好放滿,三十歲,還有心跳,為自己找一個奔跑的理由。女子再也不是為了失戀在街頭狂奔,而是為了要買麵包。對,買麵包,給明天,給後天,以及給未來的自己,豈不是很激勵人心,希望麵包店都可以來找我下廣告。
或許曾經有一度,人們想像,所有讓女孩子困擾的全是愛情,於是畫面裡,女子哭笑均是為情愛糾纏,愛情是有可煩惱也有可愛之處。不過更多時間,我想我們花心思的,是怎麼樣輕輕扯開旁人包裝精美的期待,從盒裝的美好,或甚至量身訂製的精良人生規畫簿裡,掙脫出來,真正地去處理——自己的生活想要怎麼過。
總要有一次,邁開腳步,奔跑著,去追求自己。
有光的地方
「其實人跟樹是一樣的,越是嚮往高處的陽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偶然在書店看到這段話,聽見心裡傳來很深的嘆息。
光亮與黑暗,常被看作光譜兩端,矛盾對立,但其實光亮與黑暗,有時候是同件事的兩面,互為滋養。一個光亮的人,勢必懂得深深的黑暗;一個黑暗的時刻,則會有很強動力想要趨光;全然光亮,或全然黑暗,都不是人的真實,亮面與暗面,早都是我們一部分。
今年在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家庭系統排列」;家族排列是由德國心理學家海寧格(Bert Hellinger)開發的心理治療方法。我感覺家族排列,就是類似的作用,因為見識黑暗,懂得黑暗,接納黑暗,於是才能抵達有光的地方。
家族排列實在神妙,卻並不是胡說八道,家排系統,是藉由集體的智慧與能量,往自己的內心深處工作。家族排列場上,能量流動,相信每個位置均該有人,人需要適得其所——小孩有小孩的位置,父母有父母的位置,一旦錯置,就有亂套,就有情緒與業力需要處理。
家族排列,透過處理能量的失衡與位置的失序,得到一種回歸正位的通透,可是說到頭來,處理的不是別人,而都是自己的問題。
「你在這個畫面看到了什麼?」這是老師很常問的問題。
許多時候,家族排列是看他人故事,想自己人生,進而發現生命橫向的相似性,誰都也有黑暗面,誰都有一碰就疼的議題,誰都曾經逃避自身責任而推託是他人毛病,誰都會有不想面對、轉身逃跑的時刻,進而感覺一種蔓生寬慰——人就是這樣,因為充滿著諸多瑕疵與缺陷,因而為人。人不是完美的,從來也都不是。人正是因為沒有逃避去看見,去接納自己的種種不堪,方能成人。而若身邊無友伴,可能早已在半路放棄。
我在家排經驗裡獲得許多,更多時候,是感覺到每個位置都有它的祝福與課題,也沒有什麼位置比較輕鬆容易,不要輕易踩上他人位置。苦難無從比較,幸福大概也是,排列場上處理的不是優劣好壞問題,而是觀察問題——你看到越多,就能往下切得越深。往下切深,那說明了,你有很深的向內動力,要去回答自己生命裡的問題。
說到底,家族排列,是一個痛的過程。愛與痛有時候也是一樣的,正如光明與黑暗,其實是的,真正的療癒,就是痛的。
療癒不是呼呼、拍拍,或是愛的抱抱,而是要把傷口剜出來,要揭露不堪與黑暗,要凝視自己體內漫無邊界的欲望或脆弱,要去看見,那樣的自己確實存在。當你真正地接納這樣的自己存在,那就是療癒。
好療癒,這樣的我,也是可以的。
往內工作,是一種意願,家族排列之於我,解放了這個意願。而從家族排列老師口中得到的提醒,往往是痛得不得了,有時候,希望老師下手務必留情,卻又總是在深深看見與理解之後,感覺自己整個人變得輕盈許多。
帶領我們的家族排列老師,姓樓,長著雙入世的,慈愛的,毫不尖銳的眼睛,被她盯著,並不叫人緊張。可在關鍵時刻,那雙無爭的眼常雪亮起來,目光如雷,點醒我們一些必要事情,告訴我們她都看見。
不僅只是我們經驗著赤裸,家排老師也是,現場的所有人,越是敞開自己,越是有力量鑽到更深之處。
想起某次家族排列經驗,我寫下的筆記——嚮往有光的地方,就不能不經過黑暗。自此以後,我常感覺到這個詞彙召喚:有光的地方。
創世紀如是說,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光,而有光的地方自此以後還在哪裡?那筆記我是這樣寫給自己看的——你嚮往有光的地方,可你不想經過黑暗。對,你害怕黑暗,害怕黑暗的長度未知,害怕黑暗的傷害難測,所以你轉身逃跑,改去要一個,看來比較容易的經過。當然,你可以說服自己,那看上去很像的東西,也是光,可實際上是,那並不真實,不持久,充其量,不過是你為自己打的舞臺燈光。
人偶爾為自己搭建一幅場景,是為了讓自己能夠繞道真實的崎嶇。就算別人看不清楚,你心裡明白,那樣的東西仍然是虛的。你騙得過別人,不要也騙過自己。
想做一個有光的人,就要放下對其他人光照的依賴;你想去有光的地方,就要先經歷過黑暗。痛裡生出氣力,因為黑暗是你的根基,你明白著黑暗存在,並且願意向光,那樣的氣力,就是實實在在的。
自此以後,我不再這麼害怕黑暗。黑暗是光的前夕,抵達之前的黎明。
* * *
還有一次家排場子,我也跟著家排樓老師,全場皆陌生,我們排與母親的關係。我心想先前已經排過了,我跟媽媽就是相安無事,快樂嬉遊的友伴,不以為意,心無負擔。
通常這樣的排練練習,兩人一組,先是一人當自己,一人當其母,接著反轉角色,對方做他自己,另一人當其母。先閉眼睛,接著睜開眼,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母親。我跟母親一向很親的,在排列場上也如此,並肩站在一起,我是忍不住想黏著媽媽,時而也想支持媽媽,於是伸手摟著媽媽的肩。
而排列後彼此交換心得,對方跟我說,確實感覺到很親密與貼近,可是心裡也有一點負擔存在,感覺失去自由,很擔心稍有離開或搖擺,女兒就會傷心或失控。
在那一刻我照見自己問題,我以為自己做女兒,比較有能耐,比較有見識,有時也忍不住要越界奪位,想指點媽媽的問題。殊不知,真正的支持,不是指導,不是指示,只不過是讓其是其所是。
我向我媽媽要自由與寬容,卻連自由與寬容也無法給自己母親。當下能做的,也是深深反省。
家排經常就是如此,看見內心清澈河流裡有淤泥垃圾,過往會選擇遮眼不看,繞道而行,現在可以選擇把淤泥清一清,把垃圾掃一掃,做垃圾分類,拿去好好丟掉。家排是個系統方法,讓自己不再關上心裡的門。
而我這麼想,若有一天,當我們能深深看見自己的心,並且在自己的心裡頭深深休息,接納那樣的自己。
或許我們也會看見,原來我們自己的身體裡,就有一處,有光的地方。
做內容很長一段時間,三十歲一直是常熱主題,為著是,人人都可能即將三十歲,人人都想像過三十歲,人人都擁有過三十歲。人總會長大,而下一代,也會即將三十。
三十歲主題翻身轉世,推陳出新,像書店暢銷排行榜,經典歷久不衰,諸如《祕密》一類,有百刷本事,人人都需要,像順路拜佛,必須求個安慰。昔有臺劇《我可能不會愛你》的程又青談初老,洋洋灑灑寫下五十條初老症狀,從小腹多出一攤肉,再到對完美起疑,對不完美深信不疑;今有中劇《三十而已》,開場即是,三個即將三十歲的女人迎來各自一天——其中有對三十而立的抵抗,誰說三十必須而立,不過是三十而已。
於是我驚覺,《我可能不會愛你》已是將近十年前的電視劇,現在的三十不再是女子的初老焦慮,兼且要被毛茸茸的怪物追趕在後(現在回頭看,那怪物不很明擺著影射婚姻嗎),而是而立的重新想像——我要立的究竟是什麼東西?
理解這一點以後,我要成為什麼樣的自己。視角已然不同。
回想二十幾歲,剛做編輯,寫過許多揣測三十歲的文章,當年雖無經驗,起碼還能訪談周遭友人,好險想像人設也並不困難。我發現三十普遍追求的,實與二十幾歲無太大差異,不過是要到更進階的東西——說實話,已過了願意將就,或是甘願普通的年紀,無論生活、交友、關係、事業、家庭,總之就是要好,還要更好一點,並且理解,自己已有能力做到。
曾浪漫想過,要在三十歲到來之前,給自己寫封文情並茂的信,畢竟人一生只有一次三十。信是沒寫成,三十就匆匆報到。
怎麼說,這倒是也很三十歲。
當時想寫下的東西,更接近儀式性的祝禱吧——三十歲以後,無論如何,去做理想中的大人。不再害怕長大,並且明白長大的意義,其實不過是更有意願去承擔,去解難題。Problem-solving,不再只是數學算式,而有其生活意義。
總之是,事事奮力而為,但也要越來越尊重並接納自己的狀態,理解自己在乎什麼,什麼會讓自己真正快樂。身體的狀態能負荷到哪裡,什麼東西要,什麼東西不要,辨別什麼是「挑戰」,而什麼叫做「受傷」。全心全意地,去把自己給照顧好。在每個關於自己的節點之上,都更細緻處理,再往下鑽得更深一些。
而在往後的每一天裡,試圖去過如常可愛的一天。這是心願,也是實踐——在看似平凡的每一天,每一個當下,告訴自己,我想要,也能夠創造我真正喜歡的日子。
凡事奮力,在奮力中理解與觀照自己,去養成一種對事物理解的清明,去當一個願意創造,也有能力給予愛的人。把每一天活出可愛,我要當成是給三十歲的祝福與啟示。
* * *
而三十歲,能算上一句老了吧。
年老色衰、老氣橫秋、老態龍鐘、老驥伏櫪、老調重彈、老之將至、倚老賣老、老大無成。
有次我無聊,查閱與老相關成語,整排點開,所有都指涉著同樣的,經過淡淡粉飾的,殘酷結果——青年的不再、舞臺的遺失、內在的離散。老,是失去與不再擁有,是歲月在身上不願停留。至少,我們是被這樣告訴的。
老,好老。
「老」,也是這樣。當褐髮冒出細細白線,緩慢增生直至白雪整片;當肌膚出現內凹褶邊,褶內還有無數皺褶爬上滿臉;要用更多時間換一次安詳睡眠,更多金錢追求青春重現。老是無從議價的交換,我真以為過,有那樣詛咒,名為變老。
於是,當後浪滾向前浪,九零後從初出社會爛草莓,成為職場中堅分子;同儕話題從租屋好難變成哪個地段買房划算;我於是意識到,我也已經要是,即將變老的那一群。
我正在變老,正要長得超過,能夠想像得了的歲數。一個人若無法想像,是有辦法成為的嗎?
可奇妙的,更多時候,除了我們亟欲逃離的變老與成熟的框架——諸如,成家立業、早生貴子、大富大貴等照樣造句的成語之外,更多時候,我感覺到的是變老有祝福。
無論是外在樣態或內在肌理,我是從未想過,三十歲後的生活能這樣的好。這是認真實話,二十幾歲時,大概讀過太多三十歲以後的恐嚇——新陳代謝下降、賀爾蒙劇烈變化、易胖再也難瘦、色弛愛衰、列入大齡之列。內外夾攻,雙管齊下的寓言。
我沒想過我變老以後,感受到更多的是經歷過時間的僥倖——清楚自己是誰或是想成為誰,清楚自己要的與不要的是什麼,於是選擇變得比較容易,自己願意與不願追求或忍受的是什麼,也知道怎麼從內在驅動,從這裡的A點去到那個B點。
若沒有二十歲的磕絆,大抵沒有三十歲的灑脫自在。或許我也可以,將老,寫成一個中氣十足的大字。
尤其,三十歲以後,我常感覺「創造」這個詞對我的意義深重。創造是找到一個方法,一種角度,由自己起始,去學習、去理解、去給予、去參與,每一刻未來的積極發生——如果你想要的並不存在,那麼就去創造。創造是件讓人感到幸福,也特別紮實的一件事。
二十幾歲的我,有許多逞強的時候。多數時候悶頭努力,對自己多有責難,也對很多自己其實在乎的事情不夠上心,有時候甚至也懶得理會自己的心情。
而我在這陣子回頭看,越發感覺我是個非常幸運的孩子。二十多歲的我,雖有許多不成熟與磨難,但幸運是千真萬確,是有這麼多人的愛與祝福,那麼多人的支持與照顧,我才得以穩穩地走到今天。
謝謝有這麼多人,參與我這三十年的生命。
人說三十而立,我認為那意思其實是,三十歲是另一次的出生。你把自己拉出來看一看,你真的看到,過去你的每一步,都有人支持與照看著你,你是一個被愛的孩子;接著你要站起來了,你為自己負責,你為自己決定要往哪走去,同時你也要去支持其他人,把路走得自在遼闊,把世界變得如你希冀。
也有三十歲,生日的真人真事一則。
當作故事讀,而某種程度,我認為適合總結三十歲後的多數發生——務虛也務實,出手大氣,敢拿敢要,已經沒什麼好抱歉或糾結的了,有意願,就去出力,不再猶豫愛情與麵包的選擇,不是的,我想要兩個都要,我可以兩個都要。
是這樣的。
* * *
這幾年生日,多是颱風,我是夏日正午生,常感覺自己未免風暴降生,而今年三十歲的生日夜晚,晚風吹來,身體涼爽,難得風平浪靜。
晚餐吃海產火鍋,我心裡暗自決定要連續慶生三天,接著突然很想吃麵包,而且是預約明日早餐的那種——麵包、牛奶、蛋、太陽光。我對G說,「欸我們去買陳耀訓麵包埠。」搬來中山國中附近,常常想買,每一次都錯過,快快查了Google map,依然明日請早。
想吃麵包的心意很堅定,於是想,那買善菓屋,九點打烊,還有十五分鐘,騎車去松江南京。一路飆車,抵達關鍵的交叉路口,八點五十三分,等紅燈,要五十秒,開始開玩笑,說還是我在這邊跳車,跑過兩個十字路口,奔跑過去。兩個人亂笑一陣,定格五秒。我說,欸我真的要跳車,我真的覺得一定要買到麵包。
放下安全帽,開始奔跑,跑百米姿勢,連跑兩個紅綠燈,壓線衝進麵包店,八點五十五分——我想買的法國奶油卷已經賣完了。於是帶一包吐司、兩個卡士達,又被店員推坑買了芒果捲捲。「很好吃哦,這個可以放冰箱,芒果捲捲。」好,我要,而且名字聽起來很可愛,熱血的少女容易勸敗。
買完麵包,一邊想剛剛好青春啊。G說,他坐在摩托車上看我奔跑時,開始想些無聊的文案,比方說:
三十歲,放下羞恥,為愛而跑。
我說好爛,而且買麵包有什麼好羞恥,應該是放下無謂矜持吧。三十歲,放下矜持,也放下頭髮,用跑的也要買到麵包。我說你的文案不夠詩意,只能印在早餐飲料杯緣,或像靜思文體。
然後繼續亂想,「Run for thirty」,副標「30 is the new 20」,還是「running is the new sexy」,是不是很適合辦成年馬拉松大賽?壓線的時候人人有麵包,帶回家當隔日早餐。意思是說,喂,除了有獎牌的精神鼓舞以外,也請給我真材實料的實際獎品。
如果拍成微電影,慢動作播放,大標大字放好放滿,三十歲,還有心跳,為自己找一個奔跑的理由。女子再也不是為了失戀在街頭狂奔,而是為了要買麵包。對,買麵包,給明天,給後天,以及給未來的自己,豈不是很激勵人心,希望麵包店都可以來找我下廣告。
或許曾經有一度,人們想像,所有讓女孩子困擾的全是愛情,於是畫面裡,女子哭笑均是為情愛糾纏,愛情是有可煩惱也有可愛之處。不過更多時間,我想我們花心思的,是怎麼樣輕輕扯開旁人包裝精美的期待,從盒裝的美好,或甚至量身訂製的精良人生規畫簿裡,掙脫出來,真正地去處理——自己的生活想要怎麼過。
總要有一次,邁開腳步,奔跑著,去追求自己。
有光的地方
「其實人跟樹是一樣的,越是嚮往高處的陽光,它的根就越要伸向黑暗的地底。」——《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
偶然在書店看到這段話,聽見心裡傳來很深的嘆息。
光亮與黑暗,常被看作光譜兩端,矛盾對立,但其實光亮與黑暗,有時候是同件事的兩面,互為滋養。一個光亮的人,勢必懂得深深的黑暗;一個黑暗的時刻,則會有很強動力想要趨光;全然光亮,或全然黑暗,都不是人的真實,亮面與暗面,早都是我們一部分。
今年在因緣際會之下,認識了「家庭系統排列」;家族排列是由德國心理學家海寧格(Bert Hellinger)開發的心理治療方法。我感覺家族排列,就是類似的作用,因為見識黑暗,懂得黑暗,接納黑暗,於是才能抵達有光的地方。
家族排列實在神妙,卻並不是胡說八道,家排系統,是藉由集體的智慧與能量,往自己的內心深處工作。家族排列場上,能量流動,相信每個位置均該有人,人需要適得其所——小孩有小孩的位置,父母有父母的位置,一旦錯置,就有亂套,就有情緒與業力需要處理。
家族排列,透過處理能量的失衡與位置的失序,得到一種回歸正位的通透,可是說到頭來,處理的不是別人,而都是自己的問題。
「你在這個畫面看到了什麼?」這是老師很常問的問題。
許多時候,家族排列是看他人故事,想自己人生,進而發現生命橫向的相似性,誰都也有黑暗面,誰都有一碰就疼的議題,誰都曾經逃避自身責任而推託是他人毛病,誰都會有不想面對、轉身逃跑的時刻,進而感覺一種蔓生寬慰——人就是這樣,因為充滿著諸多瑕疵與缺陷,因而為人。人不是完美的,從來也都不是。人正是因為沒有逃避去看見,去接納自己的種種不堪,方能成人。而若身邊無友伴,可能早已在半路放棄。
我在家排經驗裡獲得許多,更多時候,是感覺到每個位置都有它的祝福與課題,也沒有什麼位置比較輕鬆容易,不要輕易踩上他人位置。苦難無從比較,幸福大概也是,排列場上處理的不是優劣好壞問題,而是觀察問題——你看到越多,就能往下切得越深。往下切深,那說明了,你有很深的向內動力,要去回答自己生命裡的問題。
說到底,家族排列,是一個痛的過程。愛與痛有時候也是一樣的,正如光明與黑暗,其實是的,真正的療癒,就是痛的。
療癒不是呼呼、拍拍,或是愛的抱抱,而是要把傷口剜出來,要揭露不堪與黑暗,要凝視自己體內漫無邊界的欲望或脆弱,要去看見,那樣的自己確實存在。當你真正地接納這樣的自己存在,那就是療癒。
好療癒,這樣的我,也是可以的。
往內工作,是一種意願,家族排列之於我,解放了這個意願。而從家族排列老師口中得到的提醒,往往是痛得不得了,有時候,希望老師下手務必留情,卻又總是在深深看見與理解之後,感覺自己整個人變得輕盈許多。
帶領我們的家族排列老師,姓樓,長著雙入世的,慈愛的,毫不尖銳的眼睛,被她盯著,並不叫人緊張。可在關鍵時刻,那雙無爭的眼常雪亮起來,目光如雷,點醒我們一些必要事情,告訴我們她都看見。
不僅只是我們經驗著赤裸,家排老師也是,現場的所有人,越是敞開自己,越是有力量鑽到更深之處。
想起某次家族排列經驗,我寫下的筆記——嚮往有光的地方,就不能不經過黑暗。自此以後,我常感覺到這個詞彙召喚:有光的地方。
創世紀如是說,神說要有光,於是就有光,而有光的地方自此以後還在哪裡?那筆記我是這樣寫給自己看的——你嚮往有光的地方,可你不想經過黑暗。對,你害怕黑暗,害怕黑暗的長度未知,害怕黑暗的傷害難測,所以你轉身逃跑,改去要一個,看來比較容易的經過。當然,你可以說服自己,那看上去很像的東西,也是光,可實際上是,那並不真實,不持久,充其量,不過是你為自己打的舞臺燈光。
人偶爾為自己搭建一幅場景,是為了讓自己能夠繞道真實的崎嶇。就算別人看不清楚,你心裡明白,那樣的東西仍然是虛的。你騙得過別人,不要也騙過自己。
想做一個有光的人,就要放下對其他人光照的依賴;你想去有光的地方,就要先經歷過黑暗。痛裡生出氣力,因為黑暗是你的根基,你明白著黑暗存在,並且願意向光,那樣的氣力,就是實實在在的。
自此以後,我不再這麼害怕黑暗。黑暗是光的前夕,抵達之前的黎明。
* * *
還有一次家排場子,我也跟著家排樓老師,全場皆陌生,我們排與母親的關係。我心想先前已經排過了,我跟媽媽就是相安無事,快樂嬉遊的友伴,不以為意,心無負擔。
通常這樣的排練練習,兩人一組,先是一人當自己,一人當其母,接著反轉角色,對方做他自己,另一人當其母。先閉眼睛,接著睜開眼,在對方身上看見自己母親。我跟母親一向很親的,在排列場上也如此,並肩站在一起,我是忍不住想黏著媽媽,時而也想支持媽媽,於是伸手摟著媽媽的肩。
而排列後彼此交換心得,對方跟我說,確實感覺到很親密與貼近,可是心裡也有一點負擔存在,感覺失去自由,很擔心稍有離開或搖擺,女兒就會傷心或失控。
在那一刻我照見自己問題,我以為自己做女兒,比較有能耐,比較有見識,有時也忍不住要越界奪位,想指點媽媽的問題。殊不知,真正的支持,不是指導,不是指示,只不過是讓其是其所是。
我向我媽媽要自由與寬容,卻連自由與寬容也無法給自己母親。當下能做的,也是深深反省。
家排經常就是如此,看見內心清澈河流裡有淤泥垃圾,過往會選擇遮眼不看,繞道而行,現在可以選擇把淤泥清一清,把垃圾掃一掃,做垃圾分類,拿去好好丟掉。家排是個系統方法,讓自己不再關上心裡的門。
而我這麼想,若有一天,當我們能深深看見自己的心,並且在自己的心裡頭深深休息,接納那樣的自己。
或許我們也會看見,原來我們自己的身體裡,就有一處,有光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