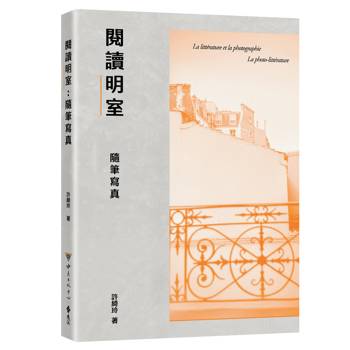糖衣與木乃伊
「很多人說糖甘甜,可是我呢,我覺得暴力,糖。」
糖很暴力?對於羅蘭.巴特在 《明室》中這句奇怪且看似反常理的話,也許有人立即能體會其中的愛恨交加,深表贊同:憑著味覺經驗與記憶,直覺地認定糖的甜味的確甜中帶狠,帶了點猛烈迫人的傷害力。可不是嗎?剛嚐過了甜頭,留在口中那不再純粹、逐漸沉膩而黏黏不散的感覺,「無一可迴拒,無一可轉化」⋯⋯也不是滋味!
如果換個角度,擴展時空視野,回溯一下糖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便可發現糖所涉及的另一種暴力,創痛更深:探究兩三百年來在地球上糖的生產與消費,以及帝國主義殖民地時代蔗糖的開發經營與運銷,可知其中包含了多少利益爭鬥,多少黑奴或殖民地人民的辛酸血淚,多少土地被偏執利用,只為了滿足帝國主義者的欲求!當又乾又瘦的農奴頂著大太陽在蔗田裡辛苦工作,不時還得忍受工頭的怒斥鞭打時,歐洲的王公貴族卻在奢華豔麗的沙龍裡,以肥嫩的手指優雅地拎起在精美銀器中的一顆咖啡色方糖往嘴裡一扔(「嗯⋯⋯!再來一顆?」),男男女女,狂笑諷語不斷,淹過一旁演奏的樂音;仔細看看,個個因甜品(特別是巧克力)嗜食過多,滿口蛀牙,黑黑爛爛的,不比端上甜點來的鄉下女僕,輕露一口潔白美齒(隨著時代,總有某些病症成為特定社會階級的身體符號。現今,蛀牙的毛病事小,且不提糖引起的其他各種疾病:肥胖症、糖尿病等,都相當難纏)1。如此,人類因糖的文化,的確自作自受,承受了不少暴力。
不過,一向也關注社會,關注歷史與人類命運的巴特在此會提到糖的暴力,想到的可能不是糖的社會經濟史。「我覺得暴力,糖。」這句引言是出自《明室》第二篇第37章:〈停滯〉。巴特正哀慟無比地看著已逝母親年幼時拍的一張相片,即「冬園相片」,他感嘆攝影「沒有未來」,沒有現象學所言的「前瞻性」。他寫道:「攝影——我的相片——沒有文化修養:傷心時,它不知轉化悲慟為哀悼服喪。如果有這樣的辨證思想,即克服墮落,化死亡的負面性為工作的力量,那麼,攝影就是非辨證的:因為攝影正如變質的戲劇,死亡在其中無法
『自我觀照』,自我反照,自我內向化⋯⋯。」相中人有如希臘正教禮拜堂裡的聖像,保存隔離在冰冷的玻璃內。時間,在相片裡已「梗塞不通」,處於停滯狀態;最有甚者是這種停滯性更挫止了觀相片者喚起回憶的希望:因此,照片的暴力並不在於拍照內容為何,而是因其本身「死亡」的本質,使得看似栩栩如生的相中之物,卻已真真無可奈何地永遠停息在內。雖死寂卻又鮮明歷歷的相片「一次一次地強迫塞滿視界,照片裡頭,無一可回拒,無一可轉化」。最後,巴特在括弧內又加上暴力的糖這句奇怪的聯想作結,未再多作解釋。
照文章如此的推演過程,從攝影的暴力連接糖的暴力,如何將停滯、無可轉化、冷冰冰的玻璃、強迫塞滿視界等等這些死死的攝影絕望,借著甘甜的糖來譬喻?糖亦會有同等性質的暴力?換言之,糖如何可以就近參與死亡?
法國美食學專家布希亞-撒瓦涵(Anthelme Brillat-Savarin, 1755-1862),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可靠而有趣的答案。布希亞-撒瓦涵是美食家,也是飲食文化研究者,寫過一本有關美食品味面面觀的經典著作傳世(Physiologie du goût, 1826)。他大概也常有機會品嚐來自亞熱帶的巧克力與方糖,一邊思考著吃的藝術與哲學,然後擦淨手指、專心寫作。
二十世紀以來,在各種意識形態之學術研究都有意忽略「感官享樂」的時代,布希亞-撒瓦涵著作的題材原本處於正典文學主流的邊緣,可是他那有時充滿機智又故作嚴肅的奇想卻頗能吸引羅蘭.巴特(自言有他享樂主義者的一面)。1975年,巴特便曾撰寫序文評述這本名著2,其中有短短的一段,提到了「死亡」與糖出人意料的某種關聯:
那麼死亡呢?死亡如何進入一位其題材與風格都堪稱「美好生活」(bon vivant)典範的作家文章裡?沒錯,死亡僅僅以微不足道的形式出現在其文中。B.-S.(布希亞-撒瓦涵)從糖可以用來保存食物,罐裝久存的家常事例,推想自問:何以人們沒有想到利用糖來作為保存屍體的防腐香料:美味的屍體、糖漬蜜餞、裹上糖衣、作成糖葫蘆!(好個離奇古怪的想像,不禁令人想起了傅立葉〔Joseph Fourier〕。)
(愛情之歡享總不斷地——經由多少神話故事——與死亡相連,可是食之豐饗卻沒有這等文學待遇;就形上學來講——或就人類學來講——食之豐饗是一種沉濁無光澤的享受。)
巴特寫這段文字顯得冷靜理智,還作了互文本與不同領域學門的參照思考。是否日後他在喪母的不尋常心境裡,突然悟得攝影豈不正如糖衣那般,活活地裹住相中人,那糖衣木乃伊有點令人毛骨悚然的想像才在巴特的心中發酵起來,忽而深感其暴力恐怖,我們便不得而知了。而巴特在《明室》這個表達悼念卻無以釋懷的章節裡,只簡言地(「微不足道」地)影射「糖很暴力」而不去解穿源由,也許是為了保持該章節一貫的憂傷悲憤口吻,不願讓糖衣木乃伊之喻一旦明言,忽然迸發黑色幽默的詭異語調吧?
「很多人說糖甘甜,可是我呢,我覺得暴力,糖。」
糖很暴力?對於羅蘭.巴特在 《明室》中這句奇怪且看似反常理的話,也許有人立即能體會其中的愛恨交加,深表贊同:憑著味覺經驗與記憶,直覺地認定糖的甜味的確甜中帶狠,帶了點猛烈迫人的傷害力。可不是嗎?剛嚐過了甜頭,留在口中那不再純粹、逐漸沉膩而黏黏不散的感覺,「無一可迴拒,無一可轉化」⋯⋯也不是滋味!
如果換個角度,擴展時空視野,回溯一下糖在人類歷史中的角色,便可發現糖所涉及的另一種暴力,創痛更深:探究兩三百年來在地球上糖的生產與消費,以及帝國主義殖民地時代蔗糖的開發經營與運銷,可知其中包含了多少利益爭鬥,多少黑奴或殖民地人民的辛酸血淚,多少土地被偏執利用,只為了滿足帝國主義者的欲求!當又乾又瘦的農奴頂著大太陽在蔗田裡辛苦工作,不時還得忍受工頭的怒斥鞭打時,歐洲的王公貴族卻在奢華豔麗的沙龍裡,以肥嫩的手指優雅地拎起在精美銀器中的一顆咖啡色方糖往嘴裡一扔(「嗯⋯⋯!再來一顆?」),男男女女,狂笑諷語不斷,淹過一旁演奏的樂音;仔細看看,個個因甜品(特別是巧克力)嗜食過多,滿口蛀牙,黑黑爛爛的,不比端上甜點來的鄉下女僕,輕露一口潔白美齒(隨著時代,總有某些病症成為特定社會階級的身體符號。現今,蛀牙的毛病事小,且不提糖引起的其他各種疾病:肥胖症、糖尿病等,都相當難纏)1。如此,人類因糖的文化,的確自作自受,承受了不少暴力。
不過,一向也關注社會,關注歷史與人類命運的巴特在此會提到糖的暴力,想到的可能不是糖的社會經濟史。「我覺得暴力,糖。」這句引言是出自《明室》第二篇第37章:〈停滯〉。巴特正哀慟無比地看著已逝母親年幼時拍的一張相片,即「冬園相片」,他感嘆攝影「沒有未來」,沒有現象學所言的「前瞻性」。他寫道:「攝影——我的相片——沒有文化修養:傷心時,它不知轉化悲慟為哀悼服喪。如果有這樣的辨證思想,即克服墮落,化死亡的負面性為工作的力量,那麼,攝影就是非辨證的:因為攝影正如變質的戲劇,死亡在其中無法
『自我觀照』,自我反照,自我內向化⋯⋯。」相中人有如希臘正教禮拜堂裡的聖像,保存隔離在冰冷的玻璃內。時間,在相片裡已「梗塞不通」,處於停滯狀態;最有甚者是這種停滯性更挫止了觀相片者喚起回憶的希望:因此,照片的暴力並不在於拍照內容為何,而是因其本身「死亡」的本質,使得看似栩栩如生的相中之物,卻已真真無可奈何地永遠停息在內。雖死寂卻又鮮明歷歷的相片「一次一次地強迫塞滿視界,照片裡頭,無一可回拒,無一可轉化」。最後,巴特在括弧內又加上暴力的糖這句奇怪的聯想作結,未再多作解釋。
照文章如此的推演過程,從攝影的暴力連接糖的暴力,如何將停滯、無可轉化、冷冰冰的玻璃、強迫塞滿視界等等這些死死的攝影絕望,借著甘甜的糖來譬喻?糖亦會有同等性質的暴力?換言之,糖如何可以就近參與死亡?
法國美食學專家布希亞-撒瓦涵(Anthelme Brillat-Savarin, 1755-1862),也許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個可靠而有趣的答案。布希亞-撒瓦涵是美食家,也是飲食文化研究者,寫過一本有關美食品味面面觀的經典著作傳世(Physiologie du goût, 1826)。他大概也常有機會品嚐來自亞熱帶的巧克力與方糖,一邊思考著吃的藝術與哲學,然後擦淨手指、專心寫作。
二十世紀以來,在各種意識形態之學術研究都有意忽略「感官享樂」的時代,布希亞-撒瓦涵著作的題材原本處於正典文學主流的邊緣,可是他那有時充滿機智又故作嚴肅的奇想卻頗能吸引羅蘭.巴特(自言有他享樂主義者的一面)。1975年,巴特便曾撰寫序文評述這本名著2,其中有短短的一段,提到了「死亡」與糖出人意料的某種關聯:
那麼死亡呢?死亡如何進入一位其題材與風格都堪稱「美好生活」(bon vivant)典範的作家文章裡?沒錯,死亡僅僅以微不足道的形式出現在其文中。B.-S.(布希亞-撒瓦涵)從糖可以用來保存食物,罐裝久存的家常事例,推想自問:何以人們沒有想到利用糖來作為保存屍體的防腐香料:美味的屍體、糖漬蜜餞、裹上糖衣、作成糖葫蘆!(好個離奇古怪的想像,不禁令人想起了傅立葉〔Joseph Fourier〕。)
(愛情之歡享總不斷地——經由多少神話故事——與死亡相連,可是食之豐饗卻沒有這等文學待遇;就形上學來講——或就人類學來講——食之豐饗是一種沉濁無光澤的享受。)
巴特寫這段文字顯得冷靜理智,還作了互文本與不同領域學門的參照思考。是否日後他在喪母的不尋常心境裡,突然悟得攝影豈不正如糖衣那般,活活地裹住相中人,那糖衣木乃伊有點令人毛骨悚然的想像才在巴特的心中發酵起來,忽而深感其暴力恐怖,我們便不得而知了。而巴特在《明室》這個表達悼念卻無以釋懷的章節裡,只簡言地(「微不足道」地)影射「糖很暴力」而不去解穿源由,也許是為了保持該章節一貫的憂傷悲憤口吻,不願讓糖衣木乃伊之喻一旦明言,忽然迸發黑色幽默的詭異語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