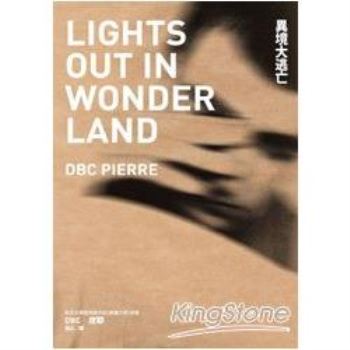倫敦
十月
沒有詞彙可以形容我的處境。首先,我決定殺了我自己。接著,則是因為這個構想:我並不需要馬上執行。
呼嘶──通過一道小門。就是混沌邊境了。
我再也不必接起電話,或是支付帳單。我的信用評分也無所謂了。恐懼和義務無所謂、襪子無所謂,因為我就快要死了。至於我會帶著什麼身分死去呢?微波爐大廚、在小冊子上書寫的作家、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被當掉的學生、有缺陷的男人、拙劣的詩人、雙重思想的激進分子、愛喝巧克力牛奶的人,沒有巧克力牛奶的時候,就喝草莓牛奶。
適者生存的道理隨著時代調整──而不是隨著適者調整。
啊,好吧。我一向會避開鏡子,不過這會兒,我在房間裡裸著身體面對一個水槽和一面鏡子,我偷瞄了一眼。呼嘶──狡猾的人不見了。剎那之間,我變成了讓人猜不透、擁有合唱團男孩雙眼的人,猶如腐朽的人像油畫般散發光芒和自然粗糙。
因為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如果你可以掌控的話,戒毒中心並不是一個適合鼓舞人心的地方。
我在水槽裡小便以示慶祝──畢竟,我覺得小便順著瓷器設備流入水管──然後用水龍頭的水沖洗掉,那樣表現出精緻優雅。合理和優雅在我存活的最後時刻顯現。證明我不是瘋了,我是優良人種的一分子。或者至少,是來自優良人種的傳奇。
迅速地穿上衣服,我懶得洗澡,那並不重要。我只是停在窗邊舒展著身體並且感到相當驚奇。我的沮喪消失了。呼嘶──掉進兔子洞裡消失了。一切都是呼嘶。這就是混沌邊境的衝擊。當然,唯有自殺是最終的決定,這一切才有意義。而且那正是我的決定。
理由很簡單:不管我如何嘗試,反正我從來學不會好好活著。而且在我們這個時代,活得不好等同於沒有活著。我也沒有一整個網絡的心靈摯友幫我指點迷津,畢竟現今人人為己。所以我淹沒在現代人的夢想壓力之下,聽起來也許很可悲,除了一件事:我並非缺乏可供耗費的力量,我內心充滿力量,簡直滿溢。然而它們不曾找到發洩管道,它們是無處發洩的力量,激昂沸騰得到了極點。
力量無處發洩比毫無力量可言還要沒有意義。
我所書寫的內容也許就像是我在建議你走上這條絕命小徑。嗯我的確是這麼建議。根據你看見的、下定決心,不過同時之間,我將你視為最後一個朋友和同伴。而且我要告訴你:每個人都會在聆聽他身後的社交聚會發出笑鬧聲之際,後悔提早離開聚會。死亡肯定也是同樣的感受。但是我一點兒也感覺不到;因為這場聚會已經結束,早已人去樓空,酒桶裡徒留泡沫,我們身後的商業帝國正在做最後的抽搐陣痛。拜拜,自由市場。再見,條款及細則。告辭,假笑。哈哈,呼噗,哇嘿。它最終的縱酒狂歡徒留我們在免費活動上常見的廢物殘渣,現在只剩嘔吐而出的薯條和葡萄酒。我察覺到現況的時候,我感覺到的並非遺憾而是自傲,而且在絕佳的時機退出。
再見,「現代社會」,再見了。這是另一個證明我們擁有自我掌控能力的機會,從此刻起,自由的價值已經逝去了。我們的內心深處都非常明白。十幾年來我們只是將過去重新加熱,不斷地因為我們過去的數百個精采時刻而洋洋得意,就像活在歡樂時光中的老者,在毫無自覺之下道別。
現在,望著異境裡的朦朧微光。
呼嘶,真是墮落啊。
外面某處有一顆球在球拍之間彈跳著,對我來說那是時鐘的滴答聲,和自然界的真實時間一樣不平均。我得從這裡消失了──快一點,在任何人玩弄我心智之前。我要去多活一、兩個小時了,因為我值得一活,哈哈。正如我的混沌邊境所暗示的行為態度,我只是隨處看看。如果我們追隨著地位同等之人,那麼想必不需要比他們更偉大的道德規範。
這意味著加布列爾‧柏克威徹底自由了。(待續)首先第一件事是──我要追尋我所認識最成功的放蕩者:我的老朋友尼爾森‧斯穆茲,一個離不開葡萄酒和誘惑的男人。和他在一起可以讓我最後的幾小時成為即將拋棄的歲月中最完美的縮影,沒什麼比最後的肆意狂歡更容易遺忘。
啊墮落,我對著窗外微笑。改過向善的能力和位在北倫敦鄉間的家族祕密般潰爛,那裡有石窟、灌木、以及覆蓋軟泥的池塘,收容者──所謂的客戶──到處遊盪吸食著腐葉土──所謂的新鮮空氣──並且身穿無法接觸雙腿的褲子,褲子在出錯的鞋子上方空空蕩蕩的。
我的房間沒有上鎖。外頭的走道飄散著吸塵器運作時機械管道的陳年氣味。我穿過灑進這棟建築物的暮光,一道金黃色風暴挾帶著銀河系塵埃映照著漆黑的門廊。呼嘶。古人會稱此現象為好預兆。看來這項重大決定召喚出熱心神靈的天蹟,也許我們做出重要行為的時候,便會出現象徵點頭的光照或是皺眉的陰影。那些冷嘲熱諷和異想天開的神靈一定就像我們周遭的液體。混沌邊境絕對會吸引他們──而且死亡之前的混沌邊境就像漩渦的捲流。如果他們會在冒險的旅途上給予預兆、或者為死亡保留他們的訓誡,誰知道他們到底是不是喜歡生命多過於死亡。
還是來吧──我們拭目以待。
有著長臉的女孩在櫃檯後方一個踉蹌,她看著我、希望我不要靠近。呼嘶──我穿過光線迷亂地走向她。我的害羞不見了,我快要死掉的祕密讓害羞變得很不恰當,所以我不斷往前,一直到她的臉籠罩在陰影之下,然後我跟她要了一枝筆和一張紙。我們來做筆記──是的!──就在一切都如此清晰的這一刻。女孩正在翻找的時候,我發現櫃檯後方的退房表格,並且伸手拿了一張。她往後彈了一步,彷彿我的手臂擁有強大的力場。不過後來我才明白她是個對所有事物畏懼退縮的人,所有動作對她而言都是輕微地驚嚇。她放下一本筆記、在旁邊準備一枝筆,我在櫃檯上摺著退房表格的時候,她往後退了一步。我虛張聲勢地拿起了筆。
「非酒精麻醉而衍生的快樂,」我寫著,「──都是假的。」
她緩慢地張開了嘴巴:「好──吧。我還是找大衛來好了,或是蘿絲瑪麗──和你接洽的人是誰──大衛還是蘿絲瑪麗?」
她的臉愈拉愈長,每說一個字都像是要融化在櫃檯之上。這是一名薩爾瓦多‧達利畫筆下的女孩,就是那個畫出樹枝上掛著對摺懷錶的人。
「都不是。」我說,然後繼續寫下去:
「所有非酒精麻醉而流洩的自我認知、勇氣和決心──都是假的。」
「我會傳話給大衛。」她正搜尋著電話筒。
我一屁股坐下、以導師評語的口吻填寫著退房原因那一欄。「想法不會挺身而出,」我寫著,「社會裡那些少數感受劇烈的離經叛道者對財富的敏感性將他們壓垮,而其敏感正使他們擁有人性、特性以及受到同儕頌揚的激情──」
「大衛‧威斯特,大衛請到櫃檯來。」
「應該,藉由平庸與自律將他們的失敗加以調和,卻避開了被動而具侵略性的投機分子,那些投機分子用盡全力於逞兇好鬥、人為操控和武斷教條,他們將其視為某種治病療法。」
「大衛請到接待處。」
「各種新加州人和極端分子所渴求的金援贊助、掌權能力以及對其他人的虛偽同情心是一種更加驚人而且險惡無比的性格,比任何事都讓我熱切嚮往。如果說有一件事能說服我留下來,那正是這個令人驚駭的事實:不是因為如此欺瞞愚弄能找到盟友──而是因為找來的盟友應該相當來勢洶洶。」
達利女孩一陣抽搐,她將小冊子攤平。「只有老天才知道大衛在哪裡吧。我們到休息室幫你找個位子坐下如何?在我們把事情──解決之前?」
「不要。」我說。
她眨了眨眼睛,遲緩地點了點頭:「事情是這樣的──你填的不是你的表格,你的表格在我們的檔案夾裡,所以我們得把那些內容再謄寫出來。」
我站起身看著她好一會兒。「那為什麼不把你們手上那張表格上字數比較少的登記資料複製到這張上面來呢?」
「呃,不行,不過──這張表格不是我們歸檔的那一份啊,你懂嗎?總之你真的不能填這張表格。」
我移開我的目光。
「而且你的表格上會有評語和──」
「不會有的,我什麼都沒參加啊。」
「嗯,是沒錯,不過還是會有評語,因為──那就是你的表格。」
「那妳為什麼不去把表格拿來?」
「很遺憾,那是機密文件。」
「嗯。」我頓失力氣。
「我很抱歉──就是這樣,詳細費用也會在上面──」
「你們真的會收半個晚上的停留費嗎?」
女孩一陣僵硬。「嗯,課程是預先付費的。你知道吧?條款及細則──」
「不對不對──條款及細則只存在於我昨晚抵達這裡時的世界,現在我要離開了。」我客氣地說,甚至張著嘴巴微笑著。我下巴的鬍髭像松鼠一樣竄了出來。
達利女孩坐立難安。(待續)啊很好、很好。在屍骸墜落的這個關頭,我們依然能夠從中挖取利益。我飄忽著後退了一步。就在我試圖接受這個事實的時候,達利女孩胡亂地翻著紙張。「我不知道大衛究竟在哪裡。」說這句話的同時她蹙緊眉頭。
「嗯,那真是太可惡了。」我冷靜地將筆記本和筆放入口袋。
「大衛‧威斯特,請立即到櫃檯報到。」
我注視的目光越過桌子旁邊的棕櫚盆栽,然後停留在後方的幾個字上:「希望。」我思考著,上面的字如果是「傑出非凡」肯定會好看得多,甚至是中國超市的某個招牌,「優秀農作物」或者「處女膜新品」。
「重點是,」達利女孩得意地想出新點子,「你想取回私人物品吧?你的錢包、手機,你還有帶什麼嗎?我需要請高階職員簽署文件將它們領出來,我不能直接拿出來。事情就是這樣。」
「聽著:在這三分鐘的空白裡,妳幫不上忙的理由盡是些:我必須在不同的表格上填寫啦;我不能任意填寫表格啦;我不准看到表格啦;還有妳要找專業的來打開櫃子。」
「正是如此。」她說,因為轉移了話題而高興不已。「我去幫你拿礦泉水好嗎?一邊等大衛?」
正是如此。我看見她臉上散發著權威呼喚那些比大衛更快趕到的人們,而且他們正接受藥物治療。呼嘶。我剛拿到礦泉水,坦白地說,水裡的檸檬片周圍滋滋地冒著泡泡,我悶悶不樂地沿著走道往休息室去。這是一個俯瞰莊園領土的空虛靈魂,一處你被安排等待大衛的地方,聞起來是油漆和潮溼的氣息。我發現這裡很空洞,我坐在一張正對窗戶的濃皰色沙發上,窗戶外面的樹隨著風搖曳著濃密的枝幹。
我應該直接走出去的,接待處是一個錯誤。
茶几上擺了一張西洋棋盤以及幾本與休閒和呼吸有關的雜誌,桌燈的光線映照著封面。我沉思著,需要學習呼吸方法的生物應該可以獲准去死吧。而且我很好奇光線是否也會從《貝肯巴斯特》或《手交人妻》之中蹦跳而出,我們永遠無從得知,這就是為什麼這些農村復興會造成疑慮。因為一幢跳著華爾滋、空氣中攪動著馨香以及受寵的家犬和孩童發出咆哮吵鬧聲的縱慾豪宅,現在只是一處充滿羞恥、毫無價值的地方──而且可能有一本《手交人妻》或者家庭菜園下會埋著屍體。
不會兩者都存在。
我關掉桌燈並且沐浴在紫羅蘭的光暈裡。西洋棋擺在那裡等待著一場對奕,我檢視著擺成一列的旗子,兵排隊等死、騎士走斜線、城堡估算峽灣。基於一種蠻橫的偷竊行為,我拿起了白后,並且將兩方陣營鏟過一遍、將黑王打到地板上去。這就是我們今晚需要的態度,不管我們過的是何種冒險生活──而且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冒險,儘管很簡短──應該能對生活和自然表現相同的漠然,那正是它們顯露出來的。我們即將無所克制地尋求愉悅。
以資本家的身分!像動物般出走吧!(待續)啊,死亡之前的時刻是一場處女秀。我不是第一個發明自殺的人,甚至你一定也懷抱過這個想法,解除一段黑暗時光的皮膜,聞聞它、掌握它。不是說你曾經像我這樣計畫過;只是你一定感受過,各種命運組合已經在你周遭活躍著,至少其中一個結果會以你的死亡作為代價。我很想知道那是否就是我們體悟出幸運的地方,看著命運的手指劃過我們的板機、看著其他人扣下板機。這肯定是萬中選一的機會。
總之,我的命運出擊了。
我的理智逐漸漂向尼爾森‧斯穆茲。我們即將擁有什麼樣的放蕩啊,真是一場飲酒作樂。最近一次我知道他剛從布魯塞爾回來,待在一間位於南方的私人廚房裡。好一陣子了,一年前吧,也許。啊斯穆茲。
在這段深思自省的過程中,休息室的門是開著的。一名瘦削的年輕男子往裡面看,他身穿合身毛衣而且擁有蒼白、不成熟的臉,像是馬的胎兒。他就站在那裡看著,過了一會兒之後他指著我的鞋子。
「那是皮革製的。」他說。
不太確定他哪來的想法,我回望著他片刻,他卻不再提供進一步的線索。我伸出一根手指指著他的上衣說:「那是羊毛製的。」
「沒錯,但是綿羊還活著。」他說。
我轉過頭,眨了眨眼。
在一陣靜默之後,他說:「你不一起來嗎?」
「不要。」我說。
又過了好半晌。他走出去並且關上身後的門。一陣碎碎念在走廊上迴盪,就在聲音消逝之際,一連串的腳步聲接近。
「加布列爾‧柏克威?」一名男子在門口喚道。他的語氣輕巧不費力,就算無人回應也不會顯得太愚蠢。
我忽略他。我要在這裡等到大家都安靜的時候,然後逃跑。我感覺到他愚蠢地回望著門外,但是對於忽略他這個行為我毫不擔心、也毫不在乎。那些緊張現在全都不見了,因為我隨時都能殺了自己。
「加布列爾?」
他喊我名字的時候,我在筆記本上寫著字。
一道標題顯現:《加布列爾的書》。
接著是一道副標:任何生物──獻給猴子、狗和詩人。
我使用的詞是任何生物而非所有生物,這是因為所有生物皆以同樣的方式成形。為了支持大量的偽工業,市場誘使我們相信生活的每一碎片都是專業分工的,因此需要商品和服務加以控制;然而事實上所有生物都擁有無趣並且顯而易見的性格,無論你是甲蟲或是X光師、正在躲避小鳥或是幻想著乳房。正如同標題上提及的動物,我覺得牠們是人類靈魂的使者、來自媚惑和自我厭惡誕生之處的中心思想。牠們說不定擁有自己的天堂──有何不可?──既然史威登堡都說過土耳其人和荷蘭人擁有專屬的天堂了。
筆記本正式地開啟了混沌邊境裡針對靈魂研究的普遍性。而且也是一層珍貴的外皮,得以和企業家匹配,甚至是政府官員;突然之間我們的任務不是放肆享樂而是科學,一個拓展人類認知大膽、而無私的行為。因此我們的筆記應該要很清晰,而且只要用語看似合乎規範,你便會原諒我──當然我們必須暫時拋棄艱澀難懂的文字才能清楚地闡述墮落,就像屈服於獲得批准的惡行。因為語言不正支持著文明?以一種微妙而且不會出錯或遺漏的方式不斷磨練解釋藉口和罪行的能力?
在這段決定性的靈光乍現之後,我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我的私人物品就留在接待處吧,反正斯穆茲還是有錢,斯穆茲會有食物和美酒的。
一名男子的頭探入休息室。「啊,你在這裡啊。」他說。(待續)2
大衛‧威斯特是個面黃肌瘦而且似乎很容易受傷的男人。他的雙眼像是沒有光澤的水煮蛋,蛋白中間甚至還有隱約難辨的混濁蛋黃,眼窩像是裝蛋的杯子將其牢牢托住,我對它們沒有好感。
「要找到你還真難啊。」他說。「講習開始了,你不加入我們嗎?」
「不要。」我說。
他領著我離開休息室,一邊皺眉一邊微笑著:「你看起來糟透了,我們還猜想你是不是根本還沒醒呢。」
「還好吧,我只是想要吃蛋糕。」
「啊,大衛。」達利女孩從接待處探出頭來,非常開心他終於現身了:「柏克威先生需要一些協助。」然後無聲地說:「他好像很激動。」
這是一個警報代號。他們看著對方,並且停頓了一會兒。達利女孩眨著眼睛暗示大衛櫃檯上有我的表格,並將其抬高角度方便大衛留意。他閱讀表格的同時握緊了我的肩膀,一種虛假的友好動作、某種人類碰觸的嘲諷技巧。然而就在他邁出步伐之時,他開始像發現距離比他想像得還遠的漫步者般一陣頹喪。
終於他轉向了女孩:「可以請妳提取加布列爾的檔案嗎?」之後對我說:「加布列爾、加布列爾──多麼巴洛克啊,我真不知道該獎勵你還是發表你的文章!」
現在他是個聰明機伶的男子,不過和我沒關係。「唔,」我左顧右盼。「可以的話,我只想拿回我的東西。」
他又挨近了一點、咬著嘴脣。「你知道我很失望吧,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可是你自己必須先邁出一步才行。對我們敞開心胸,加布列爾。這是合約──而且雙方要互相合作。我不能讓你像這樣把自己隱藏起來。」
我輕輕地抓了一下我的鬈髮。「威斯特先生──只待一個晚上就要收兩個星期的費用,並沒有建構在互相合作之上噢。」
「聽著,」他說,「我知道你並非最滿意的顧客,這沒關係。但是你來自同一個星球,你明白事情的運作方式。這裡不是旅館,如果我們認真地要幫助你,那麼你的房間就得全程受到保護。對於條款與細則我和你有同樣的感受,但是──」
「那你為什麼不做你認為公平的事?」
「加布列爾,這同時也是我們的事業、是我們生存的方式。在任何制度下,都不會有人能在預期之中放棄他們的生計。求生並非只存在於資本主義概念裡。」
「不好意思──資本主義概念帶來的是附屬細則裡百分之一千的罰款。比生存條件要多出太多了。」
「但是那不是罰款;你訂了一份為期兩週的產品,合約上已經闡明你接受與否──條款很清楚啊。」
「沒錯,說得非常好,唯獨一件事實──我本人並未在任何合約之下訂任何為期兩週的產品噢。」
大衛停頓了一會兒,查看自己的手錶。接著他嘆了一口氣:「不管訂購者是你父親或是你自己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而且事實上,正因為確認訂購者是你父親,我們應該和他討論一下你私自毀約的情況吧?這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你的權益喪失不也能解釋為某種剽竊?竊取自你父親?」
「他帶我來的時候我睡著了。」
「睡著了,」他伴隨一絲靈光:「還是失去意識?」
我的表情提醒了他,不管是哪一種狀態很顯然地都是在睡覺。不過他繼續說下去:「你明白的,加布列爾,課程為期兩星期是因為必須花這麼長的時間才能有所成效。這是很複雜的,你很複雜的。你不能只在這裡待一晚就抱怨錢花得沒有價值。四十二堂療程──每天都有一堂個人、一堂團體和一堂特別課程──以我們的收費,你在倫敦是找不到這種服務的。」(待續)達利女孩帶著一份淡紫色的文件夾回來並且交給大衛,她接近的時候,我緊靠著她說:「妳可不可以去把我的東西拿來!」然後她跳開了。
「好了,好了。」大衛舉起一隻手說:「蘇珊娜有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
他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皮膚像紙一樣既乾燥且蒼白。如此外型搭配他憔悴的臉龐,使我意識到熱忱所傳遞出的徵兆:大衛‧威斯特是個日式摺紙型的人。文化將他攤平、皺摺、對摺,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名聰明的男子,如同在摺痕之下毫無思想的餐巾紙,他將別人攤開以後再摺成和他相同的形象。他從文件夾中抬起頭的時候一定看見我目光裡的恐懼了,因為他的臉變得益發冷峻。
「你快要惹我生氣了。」他說。「我一直對你保持著耐性,儘管你害我面對其他客戶的時候遲到了。他們的問題難道不比你的重要嗎?每個人都必須因為你的行為而喪失權益嗎?」
他靈魂裡的糞便滑溜而出的時刻,我等待著。現在我們也發現了他最喜歡警察過度解讀的伎倆。,另一種則是貪腐的警察,尤其各州的最大犯罪組織在定義上正是它們的警力。因為他會活在一個熱情的熔爐之中;風險、機密和不定性都需要大膽的即性創作,以及與放縱財富的密切聯繫──而這至少提供了我們一些讓人得以理解的平凡生物。)唯有警察和八歲小女孩會以這麼空洞的問題展現自身的行為態度:「你會把車子留在大馬路中央嗎,先生?我猜你會認為那是合理的行為吧?如果有人對你這麼做你會作何感想?」之類的。在表達與生俱來的自以為是之際,過度解讀也將迫使你投降;因為誠實的答案會讓你像個白痴一樣──至於合理的反駁則會使你成為囚徒。
我高估了大衛‧威斯特。
我從口袋裡抽出一根菸。
「這裡不准抽菸,搞什麼。」他壓低嗓音:「我們不能首開惡例。你經歷了生命中艱難的時刻,我很遺憾。你失去女友、失去工作,失去所有與之相關的一切。你失去──」
「那是檔案裡寫的,對吧?」
「別忘了,是我從你父親那幫你簽到的。我的重點是,加布列爾:事情一向都很艱難,我感同身受,但是你不必單打獨鬥,不需要這麼痛苦的。給我一點耐心,和我一起坐下來好好地聊一聊。我們可以聊任何話題──像是我在你的留言裡看到的躁鬱症問題。」
「我當時很憂鬱。」我摸索著我的打火機。「現在我沒事了。」
他闔上文件夾。「嗯,我擔心的是,躁鬱症並不只是在憂鬱和沒事之間擺盪。否則應該叫沒事憂鬱症,你不覺得嗎?」
我點燃了香菸。
「你真的要惹我生氣了。」
我抬高目光,我吸足了一大口菸並且看著房間裡的挑高門楣,典雅的纏繞藤蔓、喇叭狀的花朵與葉片、少許水滴緊偎其上,全部都漆上無趣的乳白色。我幻想著它們鍍上黃金、藍寶石鑲滿樹梢和天際,就像從墳墓裡往上望的光景。
「加布列爾,你觸犯法律了。」
達利女孩咳了一聲。真是太不具說服力了,她應該要召喚出癌症的,卻出現像是家庭主婦暗示某人鼻涕流到嘴脣上的聲音。我默默地加速重建這令人喪氣的建築結構,地板鋪上義大利大理石、在休息室豎立起一座長滿神聖蓮花和水罌粟的弗拉斯卡帝式莊園噴泉。
「加布列爾,你褻瀆了這裡而且觸犯了法律。」
這地方還真是個心靈下水道,多麼腐敗而空洞啊。在經過一陣吞雲吐霧的沉思之後,我終於轉向大衛。
「你竟然敢褻瀆這裡,」我說:「你這個混蛋。」(待續)3
大錯特錯,我應該直接走出去的。逐漸昏黃的日光讓休息室的沙發呈現傷口感染的色澤。護士走了出來。
他身後的門上了鎖。
女人是對的:混蛋原本是個很難聽的詞。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身上穿著小熊維尼的睡衣,那是個一切開始趨近惡化的夜晚。我說了晚安──那是一位操控自己生命終結時刻的成人認定為夜晚的傍晚。前一分鐘我才跳上了走廊,剛泡完澡全身蓬鬆柔軟,像個傻瓜一樣哼著歌。接著我被一個突如其來的浮誇炫耀心態攻占,足以從年幼的軀體之中噴發而出的小小狂亂,猶如從蠕蟲身上浮現而出的泡沫:「哇──哇噢,」我唱著,「拿了錢走人!」我不懂那是什麼意思,我只是很喜歡它的旋律。而且身在走廊上的那一刻,從來不曾想過要猜測其含意。
之後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父親對著我在玻璃門外猛拍著:
「混蛋,」他噓聲說。「你這個小混蛋!」
我也不懂那是什麼意思,但是聽起來尖酸刻薄,透過玻璃傳達而出的驚嚇與震撼倒是融合得很好。之後我躺在走廊的地毯上,像一枝被瓶罐流洩而出的血泊靜靜包圍的湯杓。而且我記得當時心想混蛋真是適合此姿態的聲音。
我試圖重新站起來的時候心裡想著這件事。
然而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再也站不起來了。
那個小傢伙從此只能躺在那裡流著鮮血。
我的朋友尼爾森‧斯穆茲當時來我家過夜,他穿著牛仔睡衣、帶著來自開普敦的清新氣息跑過我身邊。在猛烈撞擊之後,他走出了門、撿拾著玻璃的碎片,然後莊重地將它們擺放在我的胸口上。那是它們應該待的地方吧,我猜測著,和其他碎片待在一起。
玻璃門事件對我來說是個轉捩點。為了要牢牢鎖住這個教訓,聽見女友腳步聲的父親站在我上方對著我吼:「我告訴過你幾次不要在室內奔跑!」她抵達之後父親補充:「不要在室內!」父親在她面前扮演歐洲男人。蓋伊‧柏克威是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前往西柏林的蓄鬍男人之一。他用一隻鞋打破一座廢棄工廠的窗戶,並且開設了一家有汽車音響和一瓶薑酒的俱樂部。玻璃門事件發生時,我們才剛從他瘦削的青少年時期歸來。他所需要證明的只是一些糟糕的褲子和一些他可以在女人面前使用的德語字彙。就我自己而言,時至今日我依然會用德語思考某些事情,甚至是過了這麼多年以後。幼兒的大腦和麥片粥一樣柔軟,粥裡的那些葡萄乾只能直接向下沉。
另外,我帶了一本叫做《菲德列克》的書回來,作者是李奧‧利歐尼。菲德列克是一隻在夏天儲存顏色的老鼠,所以當其他老鼠同伴在冬天只有晦暗的事情可以思考的時候,他便再次喚回他所儲存的顏色。最後老鼠們都歡欣鼓舞地說:「菲德列克,你真是個詩人啊!」
我知道菲德列克就是我,我甚至長得和他很像。我以前常常在我們位於普倫茲勞爾堡彈痕累累的住處裡拉來一張椅子,然後站在上面朗誦詩篇。我從來不看著任何人,我隱身於詩韻背後。但是我總是以菲德列克的方式開始朗誦:「Ihr lieben Mausegesichter──我親愛的老鼠朋友們
。」
共產政權垮臺之後的東柏林就像一座兒童沙池,沒有人知道誰擁有什麼東西,沒有人需要金錢或是證明其計畫的文件,他們只需要一個垃圾袋、一些情慾音樂或是一只漆上眼球的灑水壺,西德人爭先恐後地穿上破爛的衣服,像來自東德的陰鬱工人四處遊盪。對東德的懷舊之情成為全新的身分。
我不是躺在英格蘭地板上淌著鮮血的那晚回想起這件事的。父親在廚房餐桌上,賞我碘酒和OK繃,他咬牙切齒地試圖冷靜說話,廚房有著診所的氣味。斯穆茲眼裡的光芒自漆黑的門口閃現,我們都很害怕,和經歷過暴力的動物一樣。
我父親很憂心金錢問題,那正是他如此積極進取的原因。平心而論,他甚至根本不打算找出憂心的癥結──就像大多數的人一樣,他只是在某一天突然鬆懈了下來,然後簽署了某樣東西好提昇他自以為的身分。一些悠閒的音樂、一些活潑的色調、一些年輕女人的照片,然後他就簽署了某樣東西。導尿管滑進了他的銀行帳戶,於是他的錢就一點一滴地溜走了,隨著經濟的水龍頭流洩或噴湧而出。他逐漸遭遇麻煩,我看著他轉變,他全然地仰賴商品和存款來意識自己的存在。
是利益將我摔出玻璃門的,不是他。
而且感染很快地使他處於衰弱的狀態。多年後當他看見那本菲德列克的書並且加以嘲笑的時候,我證實了這點。無足輕重的老鼠在市場上發現了一個契機,並且製造了一個產品好填補之──然後免費放送。
我父親稱其為一本「輸家指南」。
我父親像個戀童癖般懷抱著資本主義。當犯錯對他而言仍舊像是自我探索之旅般有趣的時候,當發展仍舊意味著尋找新方法推卸責任的時候。他那一世代決定要成為孩子的好夥伴,現在那一世代很想知道事情會如何演變。事情的演變就是三十年之後父母的角色將不復存在。
唯有遊手好閒的朋友你不能信任。
總而言之,我不會受過去的事物煩擾,現在一點兒都不重要了。我聽見休息室門的後方大衛‧威斯特的聲音逐漸接近。從停頓和語調之中我馬上感覺到我父親,下一個阻礙。
「技術上來說他或許可以,」大衛說:「讓你短期照顧。不過我建議在我們依據法案對他加以評估之前不要這麼做。」
我的眉毛垮了下來,他指的一定是心理健康法案。我躲回窗口望著秋意侵襲著室外的黑夜。所有的夏日都在某個時間點結束了,外面的景色似乎這麼吶喊著。而我是否享受過剛剛離去的夏日呢?我有將它的汁液榨得一滴不剩嗎?沒有。因為我不曉得那會是這一刻的前一刻啊,如果我知道的話,或許就可以蹦蹦跳跳地穿越陽光滿布的原野、將鞋子拋向天空。不過誰能預知哪一刻會是前一刻呢?而且就算有人能預知,又該如何保存那一刻呢?真是安穩人生中的謎題啊。
一堆堆的謎題真是塞爆了我的人生啊。
混沌邊境下沉了,這使我一心求死。於是激起了這樣的構想:我並不需要馬上執行。然而這又使我陷於地獄邊境。好個循環。
而且第一個壓力率先出現了:萬一我的決心減弱了呢?我絕對不能冒著失去氣勢的風險。如果我要去死,那麼我就應該處於隨時備戰的狀態。在每一個新地點、每一個新房間,我都應該擁有偵測到死亡的潛在工具。
就從這裡開始吧,我猜,如果我對這一切是認真的話。
十月
沒有詞彙可以形容我的處境。首先,我決定殺了我自己。接著,則是因為這個構想:我並不需要馬上執行。
呼嘶──通過一道小門。就是混沌邊境了。
我再也不必接起電話,或是支付帳單。我的信用評分也無所謂了。恐懼和義務無所謂、襪子無所謂,因為我就快要死了。至於我會帶著什麼身分死去呢?微波爐大廚、在小冊子上書寫的作家、我們這個時代的產物、被當掉的學生、有缺陷的男人、拙劣的詩人、雙重思想的激進分子、愛喝巧克力牛奶的人,沒有巧克力牛奶的時候,就喝草莓牛奶。
適者生存的道理隨著時代調整──而不是隨著適者調整。
啊,好吧。我一向會避開鏡子,不過這會兒,我在房間裡裸著身體面對一個水槽和一面鏡子,我偷瞄了一眼。呼嘶──狡猾的人不見了。剎那之間,我變成了讓人猜不透、擁有合唱團男孩雙眼的人,猶如腐朽的人像油畫般散發光芒和自然粗糙。
因為一切都不再重要了。
如果你可以掌控的話,戒毒中心並不是一個適合鼓舞人心的地方。
我在水槽裡小便以示慶祝──畢竟,我覺得小便順著瓷器設備流入水管──然後用水龍頭的水沖洗掉,那樣表現出精緻優雅。合理和優雅在我存活的最後時刻顯現。證明我不是瘋了,我是優良人種的一分子。或者至少,是來自優良人種的傳奇。
迅速地穿上衣服,我懶得洗澡,那並不重要。我只是停在窗邊舒展著身體並且感到相當驚奇。我的沮喪消失了。呼嘶──掉進兔子洞裡消失了。一切都是呼嘶。這就是混沌邊境的衝擊。當然,唯有自殺是最終的決定,這一切才有意義。而且那正是我的決定。
理由很簡單:不管我如何嘗試,反正我從來學不會好好活著。而且在我們這個時代,活得不好等同於沒有活著。我也沒有一整個網絡的心靈摯友幫我指點迷津,畢竟現今人人為己。所以我淹沒在現代人的夢想壓力之下,聽起來也許很可悲,除了一件事:我並非缺乏可供耗費的力量,我內心充滿力量,簡直滿溢。然而它們不曾找到發洩管道,它們是無處發洩的力量,激昂沸騰得到了極點。
力量無處發洩比毫無力量可言還要沒有意義。
我所書寫的內容也許就像是我在建議你走上這條絕命小徑。嗯我的確是這麼建議。根據你看見的、下定決心,不過同時之間,我將你視為最後一個朋友和同伴。而且我要告訴你:每個人都會在聆聽他身後的社交聚會發出笑鬧聲之際,後悔提早離開聚會。死亡肯定也是同樣的感受。但是我一點兒也感覺不到;因為這場聚會已經結束,早已人去樓空,酒桶裡徒留泡沫,我們身後的商業帝國正在做最後的抽搐陣痛。拜拜,自由市場。再見,條款及細則。告辭,假笑。哈哈,呼噗,哇嘿。它最終的縱酒狂歡徒留我們在免費活動上常見的廢物殘渣,現在只剩嘔吐而出的薯條和葡萄酒。我察覺到現況的時候,我感覺到的並非遺憾而是自傲,而且在絕佳的時機退出。
再見,「現代社會」,再見了。這是另一個證明我們擁有自我掌控能力的機會,從此刻起,自由的價值已經逝去了。我們的內心深處都非常明白。十幾年來我們只是將過去重新加熱,不斷地因為我們過去的數百個精采時刻而洋洋得意,就像活在歡樂時光中的老者,在毫無自覺之下道別。
現在,望著異境裡的朦朧微光。
呼嘶,真是墮落啊。
外面某處有一顆球在球拍之間彈跳著,對我來說那是時鐘的滴答聲,和自然界的真實時間一樣不平均。我得從這裡消失了──快一點,在任何人玩弄我心智之前。我要去多活一、兩個小時了,因為我值得一活,哈哈。正如我的混沌邊境所暗示的行為態度,我只是隨處看看。如果我們追隨著地位同等之人,那麼想必不需要比他們更偉大的道德規範。
這意味著加布列爾‧柏克威徹底自由了。(待續)首先第一件事是──我要追尋我所認識最成功的放蕩者:我的老朋友尼爾森‧斯穆茲,一個離不開葡萄酒和誘惑的男人。和他在一起可以讓我最後的幾小時成為即將拋棄的歲月中最完美的縮影,沒什麼比最後的肆意狂歡更容易遺忘。
啊墮落,我對著窗外微笑。改過向善的能力和位在北倫敦鄉間的家族祕密般潰爛,那裡有石窟、灌木、以及覆蓋軟泥的池塘,收容者──所謂的客戶──到處遊盪吸食著腐葉土──所謂的新鮮空氣──並且身穿無法接觸雙腿的褲子,褲子在出錯的鞋子上方空空蕩蕩的。
我的房間沒有上鎖。外頭的走道飄散著吸塵器運作時機械管道的陳年氣味。我穿過灑進這棟建築物的暮光,一道金黃色風暴挾帶著銀河系塵埃映照著漆黑的門廊。呼嘶。古人會稱此現象為好預兆。看來這項重大決定召喚出熱心神靈的天蹟,也許我們做出重要行為的時候,便會出現象徵點頭的光照或是皺眉的陰影。那些冷嘲熱諷和異想天開的神靈一定就像我們周遭的液體。混沌邊境絕對會吸引他們──而且死亡之前的混沌邊境就像漩渦的捲流。如果他們會在冒險的旅途上給予預兆、或者為死亡保留他們的訓誡,誰知道他們到底是不是喜歡生命多過於死亡。
還是來吧──我們拭目以待。
有著長臉的女孩在櫃檯後方一個踉蹌,她看著我、希望我不要靠近。呼嘶──我穿過光線迷亂地走向她。我的害羞不見了,我快要死掉的祕密讓害羞變得很不恰當,所以我不斷往前,一直到她的臉籠罩在陰影之下,然後我跟她要了一枝筆和一張紙。我們來做筆記──是的!──就在一切都如此清晰的這一刻。女孩正在翻找的時候,我發現櫃檯後方的退房表格,並且伸手拿了一張。她往後彈了一步,彷彿我的手臂擁有強大的力場。不過後來我才明白她是個對所有事物畏懼退縮的人,所有動作對她而言都是輕微地驚嚇。她放下一本筆記、在旁邊準備一枝筆,我在櫃檯上摺著退房表格的時候,她往後退了一步。我虛張聲勢地拿起了筆。
「非酒精麻醉而衍生的快樂,」我寫著,「──都是假的。」
她緩慢地張開了嘴巴:「好──吧。我還是找大衛來好了,或是蘿絲瑪麗──和你接洽的人是誰──大衛還是蘿絲瑪麗?」
她的臉愈拉愈長,每說一個字都像是要融化在櫃檯之上。這是一名薩爾瓦多‧達利畫筆下的女孩,就是那個畫出樹枝上掛著對摺懷錶的人。
「都不是。」我說,然後繼續寫下去:
「所有非酒精麻醉而流洩的自我認知、勇氣和決心──都是假的。」
「我會傳話給大衛。」她正搜尋著電話筒。
我一屁股坐下、以導師評語的口吻填寫著退房原因那一欄。「想法不會挺身而出,」我寫著,「社會裡那些少數感受劇烈的離經叛道者對財富的敏感性將他們壓垮,而其敏感正使他們擁有人性、特性以及受到同儕頌揚的激情──」
「大衛‧威斯特,大衛請到櫃檯來。」
「應該,藉由平庸與自律將他們的失敗加以調和,卻避開了被動而具侵略性的投機分子,那些投機分子用盡全力於逞兇好鬥、人為操控和武斷教條,他們將其視為某種治病療法。」
「大衛請到接待處。」
「各種新加州人和極端分子所渴求的金援贊助、掌權能力以及對其他人的虛偽同情心是一種更加驚人而且險惡無比的性格,比任何事都讓我熱切嚮往。如果說有一件事能說服我留下來,那正是這個令人驚駭的事實:不是因為如此欺瞞愚弄能找到盟友──而是因為找來的盟友應該相當來勢洶洶。」
達利女孩一陣抽搐,她將小冊子攤平。「只有老天才知道大衛在哪裡吧。我們到休息室幫你找個位子坐下如何?在我們把事情──解決之前?」
「不要。」我說。
她眨了眨眼睛,遲緩地點了點頭:「事情是這樣的──你填的不是你的表格,你的表格在我們的檔案夾裡,所以我們得把那些內容再謄寫出來。」
我站起身看著她好一會兒。「那為什麼不把你們手上那張表格上字數比較少的登記資料複製到這張上面來呢?」
「呃,不行,不過──這張表格不是我們歸檔的那一份啊,你懂嗎?總之你真的不能填這張表格。」
我移開我的目光。
「而且你的表格上會有評語和──」
「不會有的,我什麼都沒參加啊。」
「嗯,是沒錯,不過還是會有評語,因為──那就是你的表格。」
「那妳為什麼不去把表格拿來?」
「很遺憾,那是機密文件。」
「嗯。」我頓失力氣。
「我很抱歉──就是這樣,詳細費用也會在上面──」
「你們真的會收半個晚上的停留費嗎?」
女孩一陣僵硬。「嗯,課程是預先付費的。你知道吧?條款及細則──」
「不對不對──條款及細則只存在於我昨晚抵達這裡時的世界,現在我要離開了。」我客氣地說,甚至張著嘴巴微笑著。我下巴的鬍髭像松鼠一樣竄了出來。
達利女孩坐立難安。(待續)啊很好、很好。在屍骸墜落的這個關頭,我們依然能夠從中挖取利益。我飄忽著後退了一步。就在我試圖接受這個事實的時候,達利女孩胡亂地翻著紙張。「我不知道大衛究竟在哪裡。」說這句話的同時她蹙緊眉頭。
「嗯,那真是太可惡了。」我冷靜地將筆記本和筆放入口袋。
「大衛‧威斯特,請立即到櫃檯報到。」
我注視的目光越過桌子旁邊的棕櫚盆栽,然後停留在後方的幾個字上:「希望。」我思考著,上面的字如果是「傑出非凡」肯定會好看得多,甚至是中國超市的某個招牌,「優秀農作物」或者「處女膜新品」。
「重點是,」達利女孩得意地想出新點子,「你想取回私人物品吧?你的錢包、手機,你還有帶什麼嗎?我需要請高階職員簽署文件將它們領出來,我不能直接拿出來。事情就是這樣。」
「聽著:在這三分鐘的空白裡,妳幫不上忙的理由盡是些:我必須在不同的表格上填寫啦;我不能任意填寫表格啦;我不准看到表格啦;還有妳要找專業的來打開櫃子。」
「正是如此。」她說,因為轉移了話題而高興不已。「我去幫你拿礦泉水好嗎?一邊等大衛?」
正是如此。我看見她臉上散發著權威呼喚那些比大衛更快趕到的人們,而且他們正接受藥物治療。呼嘶。我剛拿到礦泉水,坦白地說,水裡的檸檬片周圍滋滋地冒著泡泡,我悶悶不樂地沿著走道往休息室去。這是一個俯瞰莊園領土的空虛靈魂,一處你被安排等待大衛的地方,聞起來是油漆和潮溼的氣息。我發現這裡很空洞,我坐在一張正對窗戶的濃皰色沙發上,窗戶外面的樹隨著風搖曳著濃密的枝幹。
我應該直接走出去的,接待處是一個錯誤。
茶几上擺了一張西洋棋盤以及幾本與休閒和呼吸有關的雜誌,桌燈的光線映照著封面。我沉思著,需要學習呼吸方法的生物應該可以獲准去死吧。而且我很好奇光線是否也會從《貝肯巴斯特》或《手交人妻》之中蹦跳而出,我們永遠無從得知,這就是為什麼這些農村復興會造成疑慮。因為一幢跳著華爾滋、空氣中攪動著馨香以及受寵的家犬和孩童發出咆哮吵鬧聲的縱慾豪宅,現在只是一處充滿羞恥、毫無價值的地方──而且可能有一本《手交人妻》或者家庭菜園下會埋著屍體。
不會兩者都存在。
我關掉桌燈並且沐浴在紫羅蘭的光暈裡。西洋棋擺在那裡等待著一場對奕,我檢視著擺成一列的旗子,兵排隊等死、騎士走斜線、城堡估算峽灣。基於一種蠻橫的偷竊行為,我拿起了白后,並且將兩方陣營鏟過一遍、將黑王打到地板上去。這就是我們今晚需要的態度,不管我們過的是何種冒險生活──而且我認為這就是一種冒險,儘管很簡短──應該能對生活和自然表現相同的漠然,那正是它們顯露出來的。我們即將無所克制地尋求愉悅。
以資本家的身分!像動物般出走吧!(待續)啊,死亡之前的時刻是一場處女秀。我不是第一個發明自殺的人,甚至你一定也懷抱過這個想法,解除一段黑暗時光的皮膜,聞聞它、掌握它。不是說你曾經像我這樣計畫過;只是你一定感受過,各種命運組合已經在你周遭活躍著,至少其中一個結果會以你的死亡作為代價。我很想知道那是否就是我們體悟出幸運的地方,看著命運的手指劃過我們的板機、看著其他人扣下板機。這肯定是萬中選一的機會。
總之,我的命運出擊了。
我的理智逐漸漂向尼爾森‧斯穆茲。我們即將擁有什麼樣的放蕩啊,真是一場飲酒作樂。最近一次我知道他剛從布魯塞爾回來,待在一間位於南方的私人廚房裡。好一陣子了,一年前吧,也許。啊斯穆茲。
在這段深思自省的過程中,休息室的門是開著的。一名瘦削的年輕男子往裡面看,他身穿合身毛衣而且擁有蒼白、不成熟的臉,像是馬的胎兒。他就站在那裡看著,過了一會兒之後他指著我的鞋子。
「那是皮革製的。」他說。
不太確定他哪來的想法,我回望著他片刻,他卻不再提供進一步的線索。我伸出一根手指指著他的上衣說:「那是羊毛製的。」
「沒錯,但是綿羊還活著。」他說。
我轉過頭,眨了眨眼。
在一陣靜默之後,他說:「你不一起來嗎?」
「不要。」我說。
又過了好半晌。他走出去並且關上身後的門。一陣碎碎念在走廊上迴盪,就在聲音消逝之際,一連串的腳步聲接近。
「加布列爾‧柏克威?」一名男子在門口喚道。他的語氣輕巧不費力,就算無人回應也不會顯得太愚蠢。
我忽略他。我要在這裡等到大家都安靜的時候,然後逃跑。我感覺到他愚蠢地回望著門外,但是對於忽略他這個行為我毫不擔心、也毫不在乎。那些緊張現在全都不見了,因為我隨時都能殺了自己。
「加布列爾?」
他喊我名字的時候,我在筆記本上寫著字。
一道標題顯現:《加布列爾的書》。
接著是一道副標:任何生物──獻給猴子、狗和詩人。
我使用的詞是任何生物而非所有生物,這是因為所有生物皆以同樣的方式成形。為了支持大量的偽工業,市場誘使我們相信生活的每一碎片都是專業分工的,因此需要商品和服務加以控制;然而事實上所有生物都擁有無趣並且顯而易見的性格,無論你是甲蟲或是X光師、正在躲避小鳥或是幻想著乳房。正如同標題上提及的動物,我覺得牠們是人類靈魂的使者、來自媚惑和自我厭惡誕生之處的中心思想。牠們說不定擁有自己的天堂──有何不可?──既然史威登堡都說過土耳其人和荷蘭人擁有專屬的天堂了。
筆記本正式地開啟了混沌邊境裡針對靈魂研究的普遍性。而且也是一層珍貴的外皮,得以和企業家匹配,甚至是政府官員;突然之間我們的任務不是放肆享樂而是科學,一個拓展人類認知大膽、而無私的行為。因此我們的筆記應該要很清晰,而且只要用語看似合乎規範,你便會原諒我──當然我們必須暫時拋棄艱澀難懂的文字才能清楚地闡述墮落,就像屈服於獲得批准的惡行。因為語言不正支持著文明?以一種微妙而且不會出錯或遺漏的方式不斷磨練解釋藉口和罪行的能力?
在這段決定性的靈光乍現之後,我從沙發上站了起來。我的私人物品就留在接待處吧,反正斯穆茲還是有錢,斯穆茲會有食物和美酒的。
一名男子的頭探入休息室。「啊,你在這裡啊。」他說。(待續)2
大衛‧威斯特是個面黃肌瘦而且似乎很容易受傷的男人。他的雙眼像是沒有光澤的水煮蛋,蛋白中間甚至還有隱約難辨的混濁蛋黃,眼窩像是裝蛋的杯子將其牢牢托住,我對它們沒有好感。
「要找到你還真難啊。」他說。「講習開始了,你不加入我們嗎?」
「不要。」我說。
他領著我離開休息室,一邊皺眉一邊微笑著:「你看起來糟透了,我們還猜想你是不是根本還沒醒呢。」
「還好吧,我只是想要吃蛋糕。」
「啊,大衛。」達利女孩從接待處探出頭來,非常開心他終於現身了:「柏克威先生需要一些協助。」然後無聲地說:「他好像很激動。」
這是一個警報代號。他們看著對方,並且停頓了一會兒。達利女孩眨著眼睛暗示大衛櫃檯上有我的表格,並將其抬高角度方便大衛留意。他閱讀表格的同時握緊了我的肩膀,一種虛假的友好動作、某種人類碰觸的嘲諷技巧。然而就在他邁出步伐之時,他開始像發現距離比他想像得還遠的漫步者般一陣頹喪。
終於他轉向了女孩:「可以請妳提取加布列爾的檔案嗎?」之後對我說:「加布列爾、加布列爾──多麼巴洛克啊,我真不知道該獎勵你還是發表你的文章!」
現在他是個聰明機伶的男子,不過和我沒關係。「唔,」我左顧右盼。「可以的話,我只想拿回我的東西。」
他又挨近了一點、咬著嘴脣。「你知道我很失望吧,我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可是你自己必須先邁出一步才行。對我們敞開心胸,加布列爾。這是合約──而且雙方要互相合作。我不能讓你像這樣把自己隱藏起來。」
我輕輕地抓了一下我的鬈髮。「威斯特先生──只待一個晚上就要收兩個星期的費用,並沒有建構在互相合作之上噢。」
「聽著,」他說,「我知道你並非最滿意的顧客,這沒關係。但是你來自同一個星球,你明白事情的運作方式。這裡不是旅館,如果我們認真地要幫助你,那麼你的房間就得全程受到保護。對於條款與細則我和你有同樣的感受,但是──」
「那你為什麼不做你認為公平的事?」
「加布列爾,這同時也是我們的事業、是我們生存的方式。在任何制度下,都不會有人能在預期之中放棄他們的生計。求生並非只存在於資本主義概念裡。」
「不好意思──資本主義概念帶來的是附屬細則裡百分之一千的罰款。比生存條件要多出太多了。」
「但是那不是罰款;你訂了一份為期兩週的產品,合約上已經闡明你接受與否──條款很清楚啊。」
「沒錯,說得非常好,唯獨一件事實──我本人並未在任何合約之下訂任何為期兩週的產品噢。」
大衛停頓了一會兒,查看自己的手錶。接著他嘆了一口氣:「不管訂購者是你父親或是你自己都不會改變這個事實。而且事實上,正因為確認訂購者是你父親,我們應該和他討論一下你私自毀約的情況吧?這才是迫在眉睫的事情?你的權益喪失不也能解釋為某種剽竊?竊取自你父親?」
「他帶我來的時候我睡著了。」
「睡著了,」他伴隨一絲靈光:「還是失去意識?」
我的表情提醒了他,不管是哪一種狀態很顯然地都是在睡覺。不過他繼續說下去:「你明白的,加布列爾,課程為期兩星期是因為必須花這麼長的時間才能有所成效。這是很複雜的,你很複雜的。你不能只在這裡待一晚就抱怨錢花得沒有價值。四十二堂療程──每天都有一堂個人、一堂團體和一堂特別課程──以我們的收費,你在倫敦是找不到這種服務的。」(待續)達利女孩帶著一份淡紫色的文件夾回來並且交給大衛,她接近的時候,我緊靠著她說:「妳可不可以去把我的東西拿來!」然後她跳開了。
「好了,好了。」大衛舉起一隻手說:「蘇珊娜有權利得到應有的尊重。」
他說話的時候,我注意到他的皮膚像紙一樣既乾燥且蒼白。如此外型搭配他憔悴的臉龐,使我意識到熱忱所傳遞出的徵兆:大衛‧威斯特是個日式摺紙型的人。文化將他攤平、皺摺、對摺,讓他看起來像是一名聰明的男子,如同在摺痕之下毫無思想的餐巾紙,他將別人攤開以後再摺成和他相同的形象。他從文件夾中抬起頭的時候一定看見我目光裡的恐懼了,因為他的臉變得益發冷峻。
「你快要惹我生氣了。」他說。「我一直對你保持著耐性,儘管你害我面對其他客戶的時候遲到了。他們的問題難道不比你的重要嗎?每個人都必須因為你的行為而喪失權益嗎?」
他靈魂裡的糞便滑溜而出的時刻,我等待著。現在我們也發現了他最喜歡警察過度解讀的伎倆。,另一種則是貪腐的警察,尤其各州的最大犯罪組織在定義上正是它們的警力。因為他會活在一個熱情的熔爐之中;風險、機密和不定性都需要大膽的即性創作,以及與放縱財富的密切聯繫──而這至少提供了我們一些讓人得以理解的平凡生物。)唯有警察和八歲小女孩會以這麼空洞的問題展現自身的行為態度:「你會把車子留在大馬路中央嗎,先生?我猜你會認為那是合理的行為吧?如果有人對你這麼做你會作何感想?」之類的。在表達與生俱來的自以為是之際,過度解讀也將迫使你投降;因為誠實的答案會讓你像個白痴一樣──至於合理的反駁則會使你成為囚徒。
我高估了大衛‧威斯特。
我從口袋裡抽出一根菸。
「這裡不准抽菸,搞什麼。」他壓低嗓音:「我們不能首開惡例。你經歷了生命中艱難的時刻,我很遺憾。你失去女友、失去工作,失去所有與之相關的一切。你失去──」
「那是檔案裡寫的,對吧?」
「別忘了,是我從你父親那幫你簽到的。我的重點是,加布列爾:事情一向都很艱難,我感同身受,但是你不必單打獨鬥,不需要這麼痛苦的。給我一點耐心,和我一起坐下來好好地聊一聊。我們可以聊任何話題──像是我在你的留言裡看到的躁鬱症問題。」
「我當時很憂鬱。」我摸索著我的打火機。「現在我沒事了。」
他闔上文件夾。「嗯,我擔心的是,躁鬱症並不只是在憂鬱和沒事之間擺盪。否則應該叫沒事憂鬱症,你不覺得嗎?」
我點燃了香菸。
「你真的要惹我生氣了。」
我抬高目光,我吸足了一大口菸並且看著房間裡的挑高門楣,典雅的纏繞藤蔓、喇叭狀的花朵與葉片、少許水滴緊偎其上,全部都漆上無趣的乳白色。我幻想著它們鍍上黃金、藍寶石鑲滿樹梢和天際,就像從墳墓裡往上望的光景。
「加布列爾,你觸犯法律了。」
達利女孩咳了一聲。真是太不具說服力了,她應該要召喚出癌症的,卻出現像是家庭主婦暗示某人鼻涕流到嘴脣上的聲音。我默默地加速重建這令人喪氣的建築結構,地板鋪上義大利大理石、在休息室豎立起一座長滿神聖蓮花和水罌粟的弗拉斯卡帝式莊園噴泉。
「加布列爾,你褻瀆了這裡而且觸犯了法律。」
這地方還真是個心靈下水道,多麼腐敗而空洞啊。在經過一陣吞雲吐霧的沉思之後,我終於轉向大衛。
「你竟然敢褻瀆這裡,」我說:「你這個混蛋。」(待續)3
大錯特錯,我應該直接走出去的。逐漸昏黃的日光讓休息室的沙發呈現傷口感染的色澤。護士走了出來。
他身後的門上了鎖。
女人是對的:混蛋原本是個很難聽的詞。我第一次聽到這句話的時候,身上穿著小熊維尼的睡衣,那是個一切開始趨近惡化的夜晚。我說了晚安──那是一位操控自己生命終結時刻的成人認定為夜晚的傍晚。前一分鐘我才跳上了走廊,剛泡完澡全身蓬鬆柔軟,像個傻瓜一樣哼著歌。接著我被一個突如其來的浮誇炫耀心態攻占,足以從年幼的軀體之中噴發而出的小小狂亂,猶如從蠕蟲身上浮現而出的泡沫:「哇──哇噢,」我唱著,「拿了錢走人!」我不懂那是什麼意思,我只是很喜歡它的旋律。而且身在走廊上的那一刻,從來不曾想過要猜測其含意。
之後我所知道的,就是我父親對著我在玻璃門外猛拍著:
「混蛋,」他噓聲說。「你這個小混蛋!」
我也不懂那是什麼意思,但是聽起來尖酸刻薄,透過玻璃傳達而出的驚嚇與震撼倒是融合得很好。之後我躺在走廊的地毯上,像一枝被瓶罐流洩而出的血泊靜靜包圍的湯杓。而且我記得當時心想混蛋真是適合此姿態的聲音。
我試圖重新站起來的時候心裡想著這件事。
然而就某種程度而言,我再也站不起來了。
那個小傢伙從此只能躺在那裡流著鮮血。
我的朋友尼爾森‧斯穆茲當時來我家過夜,他穿著牛仔睡衣、帶著來自開普敦的清新氣息跑過我身邊。在猛烈撞擊之後,他走出了門、撿拾著玻璃的碎片,然後莊重地將它們擺放在我的胸口上。那是它們應該待的地方吧,我猜測著,和其他碎片待在一起。
玻璃門事件對我來說是個轉捩點。為了要牢牢鎖住這個教訓,聽見女友腳步聲的父親站在我上方對著我吼:「我告訴過你幾次不要在室內奔跑!」她抵達之後父親補充:「不要在室內!」父親在她面前扮演歐洲男人。蓋伊‧柏克威是柏林圍牆倒塌之後前往西柏林的蓄鬍男人之一。他用一隻鞋打破一座廢棄工廠的窗戶,並且開設了一家有汽車音響和一瓶薑酒的俱樂部。玻璃門事件發生時,我們才剛從他瘦削的青少年時期歸來。他所需要證明的只是一些糟糕的褲子和一些他可以在女人面前使用的德語字彙。就我自己而言,時至今日我依然會用德語思考某些事情,甚至是過了這麼多年以後。幼兒的大腦和麥片粥一樣柔軟,粥裡的那些葡萄乾只能直接向下沉。
另外,我帶了一本叫做《菲德列克》的書回來,作者是李奧‧利歐尼。菲德列克是一隻在夏天儲存顏色的老鼠,所以當其他老鼠同伴在冬天只有晦暗的事情可以思考的時候,他便再次喚回他所儲存的顏色。最後老鼠們都歡欣鼓舞地說:「菲德列克,你真是個詩人啊!」
我知道菲德列克就是我,我甚至長得和他很像。我以前常常在我們位於普倫茲勞爾堡彈痕累累的住處裡拉來一張椅子,然後站在上面朗誦詩篇。我從來不看著任何人,我隱身於詩韻背後。但是我總是以菲德列克的方式開始朗誦:「Ihr lieben Mausegesichter──我親愛的老鼠朋友們
。」
共產政權垮臺之後的東柏林就像一座兒童沙池,沒有人知道誰擁有什麼東西,沒有人需要金錢或是證明其計畫的文件,他們只需要一個垃圾袋、一些情慾音樂或是一只漆上眼球的灑水壺,西德人爭先恐後地穿上破爛的衣服,像來自東德的陰鬱工人四處遊盪。對東德的懷舊之情成為全新的身分。
我不是躺在英格蘭地板上淌著鮮血的那晚回想起這件事的。父親在廚房餐桌上,賞我碘酒和OK繃,他咬牙切齒地試圖冷靜說話,廚房有著診所的氣味。斯穆茲眼裡的光芒自漆黑的門口閃現,我們都很害怕,和經歷過暴力的動物一樣。
我父親很憂心金錢問題,那正是他如此積極進取的原因。平心而論,他甚至根本不打算找出憂心的癥結──就像大多數的人一樣,他只是在某一天突然鬆懈了下來,然後簽署了某樣東西好提昇他自以為的身分。一些悠閒的音樂、一些活潑的色調、一些年輕女人的照片,然後他就簽署了某樣東西。導尿管滑進了他的銀行帳戶,於是他的錢就一點一滴地溜走了,隨著經濟的水龍頭流洩或噴湧而出。他逐漸遭遇麻煩,我看著他轉變,他全然地仰賴商品和存款來意識自己的存在。
是利益將我摔出玻璃門的,不是他。
而且感染很快地使他處於衰弱的狀態。多年後當他看見那本菲德列克的書並且加以嘲笑的時候,我證實了這點。無足輕重的老鼠在市場上發現了一個契機,並且製造了一個產品好填補之──然後免費放送。
我父親稱其為一本「輸家指南」。
我父親像個戀童癖般懷抱著資本主義。當犯錯對他而言仍舊像是自我探索之旅般有趣的時候,當發展仍舊意味著尋找新方法推卸責任的時候。他那一世代決定要成為孩子的好夥伴,現在那一世代很想知道事情會如何演變。事情的演變就是三十年之後父母的角色將不復存在。
唯有遊手好閒的朋友你不能信任。
總而言之,我不會受過去的事物煩擾,現在一點兒都不重要了。我聽見休息室門的後方大衛‧威斯特的聲音逐漸接近。從停頓和語調之中我馬上感覺到我父親,下一個阻礙。
「技術上來說他或許可以,」大衛說:「讓你短期照顧。不過我建議在我們依據法案對他加以評估之前不要這麼做。」
我的眉毛垮了下來,他指的一定是心理健康法案。我躲回窗口望著秋意侵襲著室外的黑夜。所有的夏日都在某個時間點結束了,外面的景色似乎這麼吶喊著。而我是否享受過剛剛離去的夏日呢?我有將它的汁液榨得一滴不剩嗎?沒有。因為我不曉得那會是這一刻的前一刻啊,如果我知道的話,或許就可以蹦蹦跳跳地穿越陽光滿布的原野、將鞋子拋向天空。不過誰能預知哪一刻會是前一刻呢?而且就算有人能預知,又該如何保存那一刻呢?真是安穩人生中的謎題啊。
一堆堆的謎題真是塞爆了我的人生啊。
混沌邊境下沉了,這使我一心求死。於是激起了這樣的構想:我並不需要馬上執行。然而這又使我陷於地獄邊境。好個循環。
而且第一個壓力率先出現了:萬一我的決心減弱了呢?我絕對不能冒著失去氣勢的風險。如果我要去死,那麼我就應該處於隨時備戰的狀態。在每一個新地點、每一個新房間,我都應該擁有偵測到死亡的潛在工具。
就從這裡開始吧,我猜,如果我對這一切是認真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