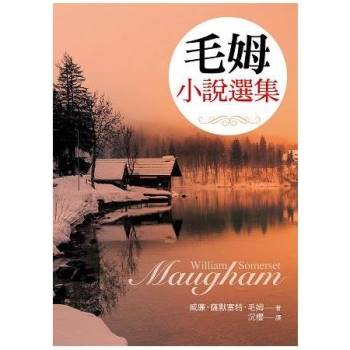療養院裡
奧桑汀住進療養院的前六星期,一直是躺在床上,除了早晚來診視的醫生,照拂他的護士和送飯的女僕之外,別的什麼人也看不到。他患了肺結核症,因為種種關係未能到瑞士去療養,那在倫敦為他治病的醫生便把他送到這個蘇格蘭北部的療養院來。他耐心等待著的日子終於到來,醫生說他可以起床了。下午護士幫他穿好衣服,帶他到走廊上,給他背後放了好些靠墊,身上蓋了毯子,讓他躺在那裡享受那晴朗天空射下來的陽光。這是仲冬的時候,療養院在一個山頂上,可以一覽無遺地望見那遍地是雪的村景。整個廊子上全坐滿了人,有的在和身旁的人聊天,有的在看書。不時有人發出一陣咳嗽,咳嗽完了之後,你如果注意的話,可以看見他焦急地去看他的手帕。護士把奧桑汀安置好要離去的時候,她用一種職務上的活潑態度對旁邊躺椅上的人說:
「讓我來把奧桑汀先生介紹給你。」她說著又轉向奧桑汀說:「這位是麥克雷先生。他和康伯爾先生是在這裡住得最久的。」
在奧桑汀另一邊躺著一位漂亮的少女,紅頭髮藍眼睛,臉上沒有化妝,但嘴唇很紅,腮上也有兩片紅暈,這更顯出了她皮膚的白皙,儘管你知道這種美麗的臉色是病態的,還是覺得非常可愛。她穿著皮外套,蓋著毯子,看不到她的身體,但她的臉非常瘦,瘦到使她那實際上並不算大的鼻子看起來有點突出。她對奧桑汀和藹地望了一眼,但是沒有說話,而奧桑汀呢,在這許多陌生人中間覺得有點侷促不安,總想別人先來對他開口。
「你是第一次起床吧,是不是?」麥克雷說。
「是的。」
「你的房間在那裡?」
奧桑汀告訴了他。
「那間小得很。這裡每一間屋子我都知道。我在這裡已經住了十七年。我現在住著最好的一間,我認為我應該住的。康伯爾曾經想把我擠出去,他自己來住,但是我不肯搬,我有權利住,我比他早六個月來到這裡的。」
麥克雷躺在那裡,給人的印象是個子非常之高,他的皮緊貼著骨頭,腮和額角凹陷進去,頭骨的形狀明顯地露出來,在那憔悴的臉上長著一個露骨的大鼻子和一對大得出奇的眼睛。
「十七年可算是一段長時間了。」奧桑汀想不出什麼話來,只好這樣說著。「時間倒也過得快。我很喜歡這裡。最初的一、二年,一到夏天我便出院,但後來不想離開了。現在這裡已成了我的家。我本來有一個兄弟兩個姊妹,但現在他們已經結婚,各自成家立業,都不要我了。你在這裡住上幾年之後,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會覺得有點格格不入的,你知道嗎?因為你的同伴都各奔前程了,你和他們完全失去聯繫。那一切好像是一條可怕的急流。無事自擾是最好的形容,到處都顯得吵鬧擁擠,還是住在這裡好點。總之,在他們用棺材抬我出去之前,我是再也不想出去了。」
醫生曾對奧桑汀說過,如果他注意調養,過一個時間就會痊癒的。現在他好奇地望著麥克雷問道:
「你一天到晚都在做些什麼呢?」
「做什麼?生了肺病有的是事做。量體溫稱體重,不慌不忙地穿衣服。吃早飯,看報紙,去散步。然後休息。吃午飯,玩橋牌,然後再休息。又吃晚飯,再玩一會橋牌,上床睡覺。這裡有個相當可觀的圖書館,可以看到一切新出版的書籍,不過,我實在沒有時間看書,我常同人談話。你在這裡可以遇見各式各樣的人。來的去的,他們出去,有時候是自以為病好了,但出去不久又轉回來,有時候是死了。我曾看見不少人出去,希望在我死前還能看見更多的人出去。」
那位坐在奧桑汀另一邊的女孩子忽然說話了。
「我告訴你,從來沒有人能對著柩車,比麥克雷先生笑得更開心的。」
麥克雷格格地笑起來。
「這我倒不知道呢。不過,如果我不在心裡想著:『我真高興柩車載走的是他不是我』,那也未免太違反人性了。」
他忽然想起奧桑汀還不認識這女孩,於是便介紹說:
「我想你們以前沒有見過吧。這位是奧桑汀先生,這位是琵少芙小姐。她是英國人,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你在這裡多久了?」奧桑汀問。
「才兩年,這是最後的一個冬天了。林諾克司大夫說再過幾個月我就要完全好了,不必再留在這裡了。」
「我看這才叫傻呢,」麥克雷說:「聽我的話,還是住在這養好了你的病的地方吧。」
這時候有個男人拄著手杖,慢慢地從走廊那一頭走過來了。
「呵,你看譚萊登來了。」琵少芙滿臉微笑,藍眼睛更明亮起來;他走近來的時候,她說:「真高興看見你又起來了。」
「呵,沒有什麼,不過是受了一點涼,現在完全好了。」話剛剛說出口,又咳嗽起來,身體沉重地靠在手杖上。但咳嗽過去後,他高興地笑著說:
「總擺脫不了這討厭的咳嗽,這是因為吸煙太多的緣故,林諾克司大夫說我應該戒掉才好,但是有什麼用,我做不到……」
他個子很高,樣子很好看,就是稍微有點矯揉造作,臉色蒼白灰暗,眼睛卻又黑又美,還留著一撮很整齊的黑鬍子,穿著一件有羊皮翻領的皮外套。他給人的印象是漂亮之中稍帶炫耀。琵少芙小姐把奧桑汀介紹給他,他隨便而又親切地說了幾句客氣話,接著就請琵少芙小姐一同去散步,因為大夫吩咐過,叫他到療養院後面的一個地方去走一個來回。
麥克雷望著他倆一同走去的背影說:
「他倆中間,恐怕有點什麼呢。譚萊登沒有得病之前,是個最會勾引女孩子的傢伙。」
「現在總該不會那樣子了。」奧桑汀說。
「這難講得很。這些年來我在這裡見過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我高興起來可以有無窮無盡的故事說給你聽呢。」
「你當然知道很多,為什麼不現在就說點。」
麥克雷咧嘴笑了笑。
「好,我先講一個給你聽。三、四年前這裡住過一位女人,又漂亮又風騷,她的丈夫總是每隔一周的周末就來看她,是從倫敦乘飛機來的,發瘋般地愛她。但林諾克司大夫很肯定地認為她和這裡的一個人有勾搭,可是又找不出是誰。有一天晚上我們大家都上床睡覺的時候,他在那女人的房門口鋪上一張薄薄的塗著油漆的布,第二天一早他把所有住院人的便鞋都收去檢查。你說妙不妙?那位在布上留有鞋印的人就強迫出院了。你知道嗎?林諾克司大夫這人很特別,他不願意讓這地方有個難聽的名聲。」
「譚萊登在這裡多久了?」
「才三、四個月。他大部分時間是躺在床上的,病勢很重。琵少芙小姐如果愛上他,那才是傻透了呢,因為她自己很有好起來的希望。我見的病人太多了,我能看出來的。我只要對一個人望望,立刻便能斷定他能不能好起來,如果是不能好的,他還能活多久,我也看得出,很少有錯誤。我看譚萊登也不過還有兩年的壽命。」
麥克雷推測地望了奧桑汀一眼,奧桑汀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自己竭力想一笑置之,但又總不由得有點掛念不安。麥克雷擠動著眼睛,很明顯地知道奧桑汀心中的念頭。
「你會好起來的。我不十分確定是不肯說的,因為我不想叫林諾克司大夫為了我用預言嚇了他的病人而趕我出去。」這時奧桑汀的護士走來,又把他帶回到床上去了。雖然他才不過坐了一個鐘頭的工夫,已經覺得很累,很高興又回到被單之間。晚上林諾克司大夫來看他的時候,望了望那體溫紀錄表,說:
「情形還不錯。」
林諾克司大夫是個矮小、活潑而又溫和的人。是一位很好的醫生,能幹的事業家,同時又是熱狂的釣魚者。漁季開始的時候,他簡直有點想把病人交給助手不管了的樣子,病人對這自然不免口出怨言,可是每餐都能吃到他釣的嫩鮭魚時又很喜歡。他很愛談話。這時站在奧桑汀床頭,便用他那蘇格蘭口音問他今天下午可曾和別的病人聊天嗎?奧桑汀告訴他,護士曾把他介紹給麥克雷。林諾克司大夫笑了。
「這位最老的住客,他對於這療養院和這裡面的人知道得比我都清楚。真不知道他從那裡得來的那麼多消息,總之,這裡的任何人的私生活他沒有不知道的。這裡的老小姐也沒有比他對於謠言更敏感的。他曾對你談起康伯爾嗎?」
「談起的。」
「他恨康伯爾,康伯爾恨他。想想也有趣,他們在這裡休養了十七年了,而兩人合起來還沒有一個完整的肺。他們彼此憎恨到簡直誰也見不得誰。我已經拒絕聽他們互相的控訴。康伯爾的房間剛巧是在麥克雷的房間下面,康伯爾是愛吹笛的,吵得麥克雷受不了。他說他聽同一個調子已經聽了十五年了,而康伯爾便說麥克雷根本分不出這一個調和那一個調的不同。麥克雷要阻止康伯爾吹笛,而我怎麼能做到,在規定要安靜的時間之外,他是有權利愛吹多久就吹多久的。我提議過麥克雷換房間,可是他又不肯換,他說康伯爾吹笛子就是為了逼他離開那房間,因為那是這地方最好的一個房間,他自己想住。你說奇怪不奇怪,這兩個中年人竟彼此情願把生活弄得像在地獄裡一般。誰也不讓誰,他們在一張桌上吃飯,一塊玩橋牌,沒有一天可以不吵架過去的。有時候我用趕他們出院嚇他們,還能使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怕出去,因為在這裡住了這麼久了,已經再沒有什麼人關懷他們,而他們也不能適應外面的世界了。幾年前的時候,康伯爾出院去要在外面住兩個月,但是,住了一星期便回來了,說他受不了那種嘈雜,並且街上擁擠的情形也使他驚慌。」這時奧桑汀的護士走來,又把他帶回到床上去了。雖然他才不過坐了一個鐘頭的工夫,已經覺得很累,很高興又回到被單之間。晚上林諾克司大夫來看他的時候,望了望那體溫紀錄表,說:
「情形還不錯。」
林諾克司大夫是個矮小、活潑而又溫和的人。是一位很好的醫生,能幹的事業家,同時又是熱狂的釣魚者。漁季開始的時候,他簡直有點想把病人交給助手不管了的樣子,病人對這自然不免口出怨言,可是每餐都能吃到他釣的嫩鮭魚時又很喜歡。他很愛談話。這時站在奧桑汀床頭,便用他那蘇格蘭口音問他今天下午可曾和別的病人聊天嗎?奧桑汀告訴他,護士曾把他介紹給麥克雷。林諾克司大夫笑了。
「這位最老的住客,他對於這療養院和這裡面的人知道得比我都清楚。真不知道他從那裡得來的那麼多消息,總之,這裡的任何人的私生活他沒有不知道的。這裡的老小姐也沒有比他對於謠言更敏感的。他曾對你談起康伯爾嗎?」
「談起的。」
「他恨康伯爾,康伯爾恨他。想想也有趣,他們在這裡休養了十七年了,而兩人合起來還沒有一個完整的肺。他們彼此憎恨到簡直誰也見不得誰。我已經拒絕聽他們互相的控訴。康伯爾的房間剛巧是在麥克雷的房間下面,康伯爾是愛吹笛的,吵得麥克雷受不了。他說他聽同一個調子已經聽了十五年了,而康伯爾便說麥克雷根本分不出這一個調和那一個調的不同。麥克雷要阻止康伯爾吹笛,而我怎麼能做到,在規定要安靜的時間之外,他是有權利愛吹多久就吹多久的。我提議過麥克雷換房間,可是他又不肯換,他說康伯爾吹笛子就是為了逼他離開那房間,因為那是這地方最好的一個房間,他自己想住。你說奇怪不奇怪,這兩個中年人竟彼此情願把生活弄得像在地獄裡一般。誰也不讓誰,他們在一張桌上吃飯,一塊玩橋牌,沒有一天可以不吵架過去的。有時候我用趕他們出院嚇他們,還能使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怕出去,因為在這裡住了這麼久了,已經再沒有什麼人關懷他們,而他們也不能適應外面的世界了。幾年前的時候,康伯爾出院去要在外面住兩個月,但是,住了一星期便回來了,說他受不了那種嘈雜,並且街上擁擠的情形也使他驚慌。」奧桑汀發覺他住進來的這地方,實在是個奇怪的世界。後來他的健康慢慢進步,和同住的病人也就混在一起了。有一天早晨林諾克司大夫告訴他說,他可以到飯廳和大家一起吃飯了。那是一間很大很低的房子,有很大的窗子。那些窗子總是大開著,晴天的時候,陽光滿屋照耀著。那裡面好像擠滿了人,使他很久才能把他們分辨清楚,有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形形色色都有,有些人像麥克雷和康伯爾,是已經住了許多年並且準備死在這裡的,還有些人是剛住進來幾個月的。有一位叫阿蒂根的中年老小姐,她是每年冬天便住進來,夏天便出去和親戚朋友一塊過,這樣子已經很多年了。她的病實在已經無關緊要,就是冬天不住進來也是一樣不會發的,但是她喜歡這種生活。她的住院資格使她有了一種地位,她成了圖書館的名譽館長,並且和護士長成了知交。她好像隨時都願意和別人聊天,可是別人對她說的話不一會就又傳到其他人的耳朵裡。在林諾克司大夫方面,能知道病人們相處得很好並且聽他的話沒有什麼放蕩行為,這是很有用處的。這院裡沒有一點事能逃過阿蒂根小姐的眼,並且總是從她傳到護士長,從護士長又傳到林諾克司大夫那裡。因為她住院的資格也相當老了,所以和麥克雷、康伯爾在一張桌上用餐,那桌上另外還有一位老將軍,是因為階級高而排在那裡的。這張餐桌和別的餐桌沒有絲毫的不同,安放的地位也並不優越,只是因為資格最老的病人坐在那裡,就被大家仰慕成誰都想坐的地方。有幾位年紀較大的女人對阿蒂根小姐非常氣憤,因為她每年夏天要出去住四五個月,竟有資格坐那張桌子,而她們是長年住在這裡的,反被安排在別的桌上。還有一位年紀很大的印度人,他在這療養院內住的時間,除麥克雷和康伯爾之外,是比任何人都長久,他過去的職位很高,曾統治過一個省分,現在也是氣憤不平地在等著麥克雷和康伯爾死去一個的時候,他好遞補上去坐那一張餐桌。奧桑汀和康伯爾也認識了。他是一個高個禿頂的人,身體瘦到使你納悶他那四肢怎麼連在一起的,當他折疊著身子坐到安樂椅上的時候,給人一種很不自然的印象,不由得想起傀儡戲中人物的動作。他很直爽急躁,脾氣很壞。他問奧桑汀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喜歡音樂嗎?」
「喜歡的。」「這鬼地方沒有一個懂的人。我愛拉小提琴,哪天你到我房裡來,我拉給你聽。」
「你可別去。」麥克雷在旁邊聽見了插嘴說,「那簡直是受罪。」
「你怎麼能這樣沒有禮貌?」阿蒂根小姐喝止著說,「康伯爾先生拉得很好的。」
「這個鬼地方簡直沒有人能分得清調子。」康伯爾說。
麥克雷嘲弄地笑著走開了,阿蒂根小姐想把事情平息下來,就說:
「你千萬不要把麥克雷先生的話放在心上。」
「呵,我不會的。不過我有辦法對付他。」
那天整個下午,他反覆不停地把同一個調子拉了又拉,使得麥克雷在樓上直敲地板。但他在樓下還是照舊地繼續拉。麥克雷叫女僕送信說他有點頭痛,請康伯爾先生不要再拉琴了好不好;康伯爾回答說他有充分的拉琴自由,如果麥克雷先生不願意聽,可以塞起耳朵來。第二天他們遇見的時候,自然又是一場大吵。
奧桑汀是和琵少芙小姐、譚萊登以及一位叫亨利‧蔡斯特做會計員的倫敦人在一張餐桌上。那位會計員是個矮粗、寬肩、很強壯的人,別人看了他那樣子,總會認為那是最不容易染上肺病的。這病到了他的身上也確乎是樁突然意外的打擊。他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物,三四十歲的年紀,已經結了婚,有兩個孩子,他住在近郊的地方,每天早晨進城工作,看晨報;每天傍晚下鄉回家,看晚報。除了職務和家庭對別的都不感興趣,他喜歡他的工作,掙的錢也足夠維持舒適的生活,每年還總有相當的積蓄。每逢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他便打高爾夫球,每到八月,便往本郡海邊去度三星期的假期。將來他的兒子長大結婚之後,他要把業務交給他,而自己便和老妻隱居到鄉下一所小房子裡,在那裡悠閒度日,以終天年。除此之外,他對於生活再無所求,而且這種生活也正是千千萬萬的人曾經滿意度過的。他就是一個這樣平凡的人物,然而意外的事情竟發生了。他在打高爾夫球的時候,受了點涼,就此咳嗽起來,並且總好不了。他因為一向強壯健康,從沒有想到過要找醫生,最後還是他的妻子再三勸說,他才同意去看一次醫生。當他聽說兩個肺上都有了結核病並且只有立刻進療養院還有治癒希望的時候,那真是一個大打擊,一個可怕的大打擊。當時給他看病的醫生告訴他說:只要兩年之後就可照常工作了。但是現在兩年已經過去了,而林諾克司大夫卻勸他一年之內最好別做這打算,曾叫他看他痰內的細菌和他肺部的X光照片,這使他的心完全沉下去了。他覺得命運對他的作弄實在太不公平太過殘忍了。如果他曾過一種放蕩的生活,喝酒、遲睡、玩女人……,那麼得這種病也還不算意外,不算冤枉。但那些事情,他是一樣也不做的,所以這真是出奇地不公平。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修養,對書籍又不感興趣,所以除了想著自己的健康之外,再也無事可做。這又造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病態,時刻焦急地注意著自己的病狀。他自己每天要量十二次體溫,並且有種成見,認為醫生對於他的病太不關心,為了引起注意,他想盡方法使體溫增到驚人的程度,要是做不到,便變得抑鬱不歡。但本質上他是個樂觀隨和的人,當他忘記自己的時候,他會很開心地談笑,只是一想起自己是個病人的時候,眼裡立刻就現出死亡的恐怖來。
每月的月尾,他的妻子總會到這裡來,在附近的旅館裡住上一兩天。林諾克司大夫是不大喜歡這些病人家屬來探望的,因為這會使病人的情緒激動不安,可是看了蔡斯特盼著他妻子到來的熱切,誰都會感動的,不過注意去看的話,很奇怪的是,她每來一次,他的熱切便低落一點。蔡斯特太太是一位很討人喜歡的有說有笑的女人,說不上漂亮,但打扮得很整潔,像她丈夫一樣平庸,一望便知是位賢妻良母,溫和安靜,善於持家,盡職安分,與人無爭。她對於過了那麼許多年的呆板家庭生活非常滿意,她的唯一的生活調劑是看電影,最大的興奮是倫敦那些商店的大減價,而且這一切從未使她覺得單調,絕對地心滿意足。奧桑汀很喜歡她,當她談著她的孩子,她的房子,她的鄰居和她的平淡無奇的工作時,他很感興趣地去聽著。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見了她,那時蔡斯特正在院中接受治療試驗,所以只她一個人在走著,奧桑汀便提議一同去散步,他們談了一會閒話之後,她忽然問他對她丈夫的病覺得怎樣?
「我想他會完全好起來的。」
「我真是心煩得要命呢。」
「你要記著這是需要長期慢慢治療的,一個人要有耐性才行。」
他們又走了一會,他看見她哭了。
「不要這麼為他擔憂吧。」他溫和地說。「呵,你不知道我每次來這裡所忍受的滋味。也許我不應該說的,但我要說說,我可以信任你的,是不是?」
「當然可以。」
「我愛他,我非常崇拜他。我願意為他做世界上任何的事。我們從來沒有吵過架,從來沒有對一點小事意見不同。現在他竟開始恨我,這太使我傷心了。」
「呵,這我不相信。你不在的時候,他總是在談你,談得再好沒有了,他也是崇拜你的。」
奧桑汀住進療養院的前六星期,一直是躺在床上,除了早晚來診視的醫生,照拂他的護士和送飯的女僕之外,別的什麼人也看不到。他患了肺結核症,因為種種關係未能到瑞士去療養,那在倫敦為他治病的醫生便把他送到這個蘇格蘭北部的療養院來。他耐心等待著的日子終於到來,醫生說他可以起床了。下午護士幫他穿好衣服,帶他到走廊上,給他背後放了好些靠墊,身上蓋了毯子,讓他躺在那裡享受那晴朗天空射下來的陽光。這是仲冬的時候,療養院在一個山頂上,可以一覽無遺地望見那遍地是雪的村景。整個廊子上全坐滿了人,有的在和身旁的人聊天,有的在看書。不時有人發出一陣咳嗽,咳嗽完了之後,你如果注意的話,可以看見他焦急地去看他的手帕。護士把奧桑汀安置好要離去的時候,她用一種職務上的活潑態度對旁邊躺椅上的人說:
「讓我來把奧桑汀先生介紹給你。」她說著又轉向奧桑汀說:「這位是麥克雷先生。他和康伯爾先生是在這裡住得最久的。」
在奧桑汀另一邊躺著一位漂亮的少女,紅頭髮藍眼睛,臉上沒有化妝,但嘴唇很紅,腮上也有兩片紅暈,這更顯出了她皮膚的白皙,儘管你知道這種美麗的臉色是病態的,還是覺得非常可愛。她穿著皮外套,蓋著毯子,看不到她的身體,但她的臉非常瘦,瘦到使她那實際上並不算大的鼻子看起來有點突出。她對奧桑汀和藹地望了一眼,但是沒有說話,而奧桑汀呢,在這許多陌生人中間覺得有點侷促不安,總想別人先來對他開口。
「你是第一次起床吧,是不是?」麥克雷說。
「是的。」
「你的房間在那裡?」
奧桑汀告訴了他。
「那間小得很。這裡每一間屋子我都知道。我在這裡已經住了十七年。我現在住著最好的一間,我認為我應該住的。康伯爾曾經想把我擠出去,他自己來住,但是我不肯搬,我有權利住,我比他早六個月來到這裡的。」
麥克雷躺在那裡,給人的印象是個子非常之高,他的皮緊貼著骨頭,腮和額角凹陷進去,頭骨的形狀明顯地露出來,在那憔悴的臉上長著一個露骨的大鼻子和一對大得出奇的眼睛。
「十七年可算是一段長時間了。」奧桑汀想不出什麼話來,只好這樣說著。「時間倒也過得快。我很喜歡這裡。最初的一、二年,一到夏天我便出院,但後來不想離開了。現在這裡已成了我的家。我本來有一個兄弟兩個姊妹,但現在他們已經結婚,各自成家立業,都不要我了。你在這裡住上幾年之後,再回到正常的生活中,會覺得有點格格不入的,你知道嗎?因為你的同伴都各奔前程了,你和他們完全失去聯繫。那一切好像是一條可怕的急流。無事自擾是最好的形容,到處都顯得吵鬧擁擠,還是住在這裡好點。總之,在他們用棺材抬我出去之前,我是再也不想出去了。」
醫生曾對奧桑汀說過,如果他注意調養,過一個時間就會痊癒的。現在他好奇地望著麥克雷問道:
「你一天到晚都在做些什麼呢?」
「做什麼?生了肺病有的是事做。量體溫稱體重,不慌不忙地穿衣服。吃早飯,看報紙,去散步。然後休息。吃午飯,玩橋牌,然後再休息。又吃晚飯,再玩一會橋牌,上床睡覺。這裡有個相當可觀的圖書館,可以看到一切新出版的書籍,不過,我實在沒有時間看書,我常同人談話。你在這裡可以遇見各式各樣的人。來的去的,他們出去,有時候是自以為病好了,但出去不久又轉回來,有時候是死了。我曾看見不少人出去,希望在我死前還能看見更多的人出去。」
那位坐在奧桑汀另一邊的女孩子忽然說話了。
「我告訴你,從來沒有人能對著柩車,比麥克雷先生笑得更開心的。」
麥克雷格格地笑起來。
「這我倒不知道呢。不過,如果我不在心裡想著:『我真高興柩車載走的是他不是我』,那也未免太違反人性了。」
他忽然想起奧桑汀還不認識這女孩,於是便介紹說:
「我想你們以前沒有見過吧。這位是奧桑汀先生,這位是琵少芙小姐。她是英國人,一個很可愛的女孩子。」
「你在這裡多久了?」奧桑汀問。
「才兩年,這是最後的一個冬天了。林諾克司大夫說再過幾個月我就要完全好了,不必再留在這裡了。」
「我看這才叫傻呢,」麥克雷說:「聽我的話,還是住在這養好了你的病的地方吧。」
這時候有個男人拄著手杖,慢慢地從走廊那一頭走過來了。
「呵,你看譚萊登來了。」琵少芙滿臉微笑,藍眼睛更明亮起來;他走近來的時候,她說:「真高興看見你又起來了。」
「呵,沒有什麼,不過是受了一點涼,現在完全好了。」話剛剛說出口,又咳嗽起來,身體沉重地靠在手杖上。但咳嗽過去後,他高興地笑著說:
「總擺脫不了這討厭的咳嗽,這是因為吸煙太多的緣故,林諾克司大夫說我應該戒掉才好,但是有什麼用,我做不到……」
他個子很高,樣子很好看,就是稍微有點矯揉造作,臉色蒼白灰暗,眼睛卻又黑又美,還留著一撮很整齊的黑鬍子,穿著一件有羊皮翻領的皮外套。他給人的印象是漂亮之中稍帶炫耀。琵少芙小姐把奧桑汀介紹給他,他隨便而又親切地說了幾句客氣話,接著就請琵少芙小姐一同去散步,因為大夫吩咐過,叫他到療養院後面的一個地方去走一個來回。
麥克雷望著他倆一同走去的背影說:
「他倆中間,恐怕有點什麼呢。譚萊登沒有得病之前,是個最會勾引女孩子的傢伙。」
「現在總該不會那樣子了。」奧桑汀說。
「這難講得很。這些年來我在這裡見過不少稀奇古怪的事,我高興起來可以有無窮無盡的故事說給你聽呢。」
「你當然知道很多,為什麼不現在就說點。」
麥克雷咧嘴笑了笑。
「好,我先講一個給你聽。三、四年前這裡住過一位女人,又漂亮又風騷,她的丈夫總是每隔一周的周末就來看她,是從倫敦乘飛機來的,發瘋般地愛她。但林諾克司大夫很肯定地認為她和這裡的一個人有勾搭,可是又找不出是誰。有一天晚上我們大家都上床睡覺的時候,他在那女人的房門口鋪上一張薄薄的塗著油漆的布,第二天一早他把所有住院人的便鞋都收去檢查。你說妙不妙?那位在布上留有鞋印的人就強迫出院了。你知道嗎?林諾克司大夫這人很特別,他不願意讓這地方有個難聽的名聲。」
「譚萊登在這裡多久了?」
「才三、四個月。他大部分時間是躺在床上的,病勢很重。琵少芙小姐如果愛上他,那才是傻透了呢,因為她自己很有好起來的希望。我見的病人太多了,我能看出來的。我只要對一個人望望,立刻便能斷定他能不能好起來,如果是不能好的,他還能活多久,我也看得出,很少有錯誤。我看譚萊登也不過還有兩年的壽命。」
麥克雷推測地望了奧桑汀一眼,奧桑汀知道他心裡在想什麼,自己竭力想一笑置之,但又總不由得有點掛念不安。麥克雷擠動著眼睛,很明顯地知道奧桑汀心中的念頭。
「你會好起來的。我不十分確定是不肯說的,因為我不想叫林諾克司大夫為了我用預言嚇了他的病人而趕我出去。」這時奧桑汀的護士走來,又把他帶回到床上去了。雖然他才不過坐了一個鐘頭的工夫,已經覺得很累,很高興又回到被單之間。晚上林諾克司大夫來看他的時候,望了望那體溫紀錄表,說:
「情形還不錯。」
林諾克司大夫是個矮小、活潑而又溫和的人。是一位很好的醫生,能幹的事業家,同時又是熱狂的釣魚者。漁季開始的時候,他簡直有點想把病人交給助手不管了的樣子,病人對這自然不免口出怨言,可是每餐都能吃到他釣的嫩鮭魚時又很喜歡。他很愛談話。這時站在奧桑汀床頭,便用他那蘇格蘭口音問他今天下午可曾和別的病人聊天嗎?奧桑汀告訴他,護士曾把他介紹給麥克雷。林諾克司大夫笑了。
「這位最老的住客,他對於這療養院和這裡面的人知道得比我都清楚。真不知道他從那裡得來的那麼多消息,總之,這裡的任何人的私生活他沒有不知道的。這裡的老小姐也沒有比他對於謠言更敏感的。他曾對你談起康伯爾嗎?」
「談起的。」
「他恨康伯爾,康伯爾恨他。想想也有趣,他們在這裡休養了十七年了,而兩人合起來還沒有一個完整的肺。他們彼此憎恨到簡直誰也見不得誰。我已經拒絕聽他們互相的控訴。康伯爾的房間剛巧是在麥克雷的房間下面,康伯爾是愛吹笛的,吵得麥克雷受不了。他說他聽同一個調子已經聽了十五年了,而康伯爾便說麥克雷根本分不出這一個調和那一個調的不同。麥克雷要阻止康伯爾吹笛,而我怎麼能做到,在規定要安靜的時間之外,他是有權利愛吹多久就吹多久的。我提議過麥克雷換房間,可是他又不肯換,他說康伯爾吹笛子就是為了逼他離開那房間,因為那是這地方最好的一個房間,他自己想住。你說奇怪不奇怪,這兩個中年人竟彼此情願把生活弄得像在地獄裡一般。誰也不讓誰,他們在一張桌上吃飯,一塊玩橋牌,沒有一天可以不吵架過去的。有時候我用趕他們出院嚇他們,還能使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怕出去,因為在這裡住了這麼久了,已經再沒有什麼人關懷他們,而他們也不能適應外面的世界了。幾年前的時候,康伯爾出院去要在外面住兩個月,但是,住了一星期便回來了,說他受不了那種嘈雜,並且街上擁擠的情形也使他驚慌。」這時奧桑汀的護士走來,又把他帶回到床上去了。雖然他才不過坐了一個鐘頭的工夫,已經覺得很累,很高興又回到被單之間。晚上林諾克司大夫來看他的時候,望了望那體溫紀錄表,說:
「情形還不錯。」
林諾克司大夫是個矮小、活潑而又溫和的人。是一位很好的醫生,能幹的事業家,同時又是熱狂的釣魚者。漁季開始的時候,他簡直有點想把病人交給助手不管了的樣子,病人對這自然不免口出怨言,可是每餐都能吃到他釣的嫩鮭魚時又很喜歡。他很愛談話。這時站在奧桑汀床頭,便用他那蘇格蘭口音問他今天下午可曾和別的病人聊天嗎?奧桑汀告訴他,護士曾把他介紹給麥克雷。林諾克司大夫笑了。
「這位最老的住客,他對於這療養院和這裡面的人知道得比我都清楚。真不知道他從那裡得來的那麼多消息,總之,這裡的任何人的私生活他沒有不知道的。這裡的老小姐也沒有比他對於謠言更敏感的。他曾對你談起康伯爾嗎?」
「談起的。」
「他恨康伯爾,康伯爾恨他。想想也有趣,他們在這裡休養了十七年了,而兩人合起來還沒有一個完整的肺。他們彼此憎恨到簡直誰也見不得誰。我已經拒絕聽他們互相的控訴。康伯爾的房間剛巧是在麥克雷的房間下面,康伯爾是愛吹笛的,吵得麥克雷受不了。他說他聽同一個調子已經聽了十五年了,而康伯爾便說麥克雷根本分不出這一個調和那一個調的不同。麥克雷要阻止康伯爾吹笛,而我怎麼能做到,在規定要安靜的時間之外,他是有權利愛吹多久就吹多久的。我提議過麥克雷換房間,可是他又不肯換,他說康伯爾吹笛子就是為了逼他離開那房間,因為那是這地方最好的一個房間,他自己想住。你說奇怪不奇怪,這兩個中年人竟彼此情願把生活弄得像在地獄裡一般。誰也不讓誰,他們在一張桌上吃飯,一塊玩橋牌,沒有一天可以不吵架過去的。有時候我用趕他們出院嚇他們,還能使他們安靜一點。他們都怕出去,因為在這裡住了這麼久了,已經再沒有什麼人關懷他們,而他們也不能適應外面的世界了。幾年前的時候,康伯爾出院去要在外面住兩個月,但是,住了一星期便回來了,說他受不了那種嘈雜,並且街上擁擠的情形也使他驚慌。」奧桑汀發覺他住進來的這地方,實在是個奇怪的世界。後來他的健康慢慢進步,和同住的病人也就混在一起了。有一天早晨林諾克司大夫告訴他說,他可以到飯廳和大家一起吃飯了。那是一間很大很低的房子,有很大的窗子。那些窗子總是大開著,晴天的時候,陽光滿屋照耀著。那裡面好像擠滿了人,使他很久才能把他們分辨清楚,有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形形色色都有,有些人像麥克雷和康伯爾,是已經住了許多年並且準備死在這裡的,還有些人是剛住進來幾個月的。有一位叫阿蒂根的中年老小姐,她是每年冬天便住進來,夏天便出去和親戚朋友一塊過,這樣子已經很多年了。她的病實在已經無關緊要,就是冬天不住進來也是一樣不會發的,但是她喜歡這種生活。她的住院資格使她有了一種地位,她成了圖書館的名譽館長,並且和護士長成了知交。她好像隨時都願意和別人聊天,可是別人對她說的話不一會就又傳到其他人的耳朵裡。在林諾克司大夫方面,能知道病人們相處得很好並且聽他的話沒有什麼放蕩行為,這是很有用處的。這院裡沒有一點事能逃過阿蒂根小姐的眼,並且總是從她傳到護士長,從護士長又傳到林諾克司大夫那裡。因為她住院的資格也相當老了,所以和麥克雷、康伯爾在一張桌上用餐,那桌上另外還有一位老將軍,是因為階級高而排在那裡的。這張餐桌和別的餐桌沒有絲毫的不同,安放的地位也並不優越,只是因為資格最老的病人坐在那裡,就被大家仰慕成誰都想坐的地方。有幾位年紀較大的女人對阿蒂根小姐非常氣憤,因為她每年夏天要出去住四五個月,竟有資格坐那張桌子,而她們是長年住在這裡的,反被安排在別的桌上。還有一位年紀很大的印度人,他在這療養院內住的時間,除麥克雷和康伯爾之外,是比任何人都長久,他過去的職位很高,曾統治過一個省分,現在也是氣憤不平地在等著麥克雷和康伯爾死去一個的時候,他好遞補上去坐那一張餐桌。奧桑汀和康伯爾也認識了。他是一個高個禿頂的人,身體瘦到使你納悶他那四肢怎麼連在一起的,當他折疊著身子坐到安樂椅上的時候,給人一種很不自然的印象,不由得想起傀儡戲中人物的動作。他很直爽急躁,脾氣很壞。他問奧桑汀的第一件事就是:
「你喜歡音樂嗎?」
「喜歡的。」「這鬼地方沒有一個懂的人。我愛拉小提琴,哪天你到我房裡來,我拉給你聽。」
「你可別去。」麥克雷在旁邊聽見了插嘴說,「那簡直是受罪。」
「你怎麼能這樣沒有禮貌?」阿蒂根小姐喝止著說,「康伯爾先生拉得很好的。」
「這個鬼地方簡直沒有人能分得清調子。」康伯爾說。
麥克雷嘲弄地笑著走開了,阿蒂根小姐想把事情平息下來,就說:
「你千萬不要把麥克雷先生的話放在心上。」
「呵,我不會的。不過我有辦法對付他。」
那天整個下午,他反覆不停地把同一個調子拉了又拉,使得麥克雷在樓上直敲地板。但他在樓下還是照舊地繼續拉。麥克雷叫女僕送信說他有點頭痛,請康伯爾先生不要再拉琴了好不好;康伯爾回答說他有充分的拉琴自由,如果麥克雷先生不願意聽,可以塞起耳朵來。第二天他們遇見的時候,自然又是一場大吵。
奧桑汀是和琵少芙小姐、譚萊登以及一位叫亨利‧蔡斯特做會計員的倫敦人在一張餐桌上。那位會計員是個矮粗、寬肩、很強壯的人,別人看了他那樣子,總會認為那是最不容易染上肺病的。這病到了他的身上也確乎是樁突然意外的打擊。他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物,三四十歲的年紀,已經結了婚,有兩個孩子,他住在近郊的地方,每天早晨進城工作,看晨報;每天傍晚下鄉回家,看晚報。除了職務和家庭對別的都不感興趣,他喜歡他的工作,掙的錢也足夠維持舒適的生活,每年還總有相當的積蓄。每逢星期六下午及星期日,他便打高爾夫球,每到八月,便往本郡海邊去度三星期的假期。將來他的兒子長大結婚之後,他要把業務交給他,而自己便和老妻隱居到鄉下一所小房子裡,在那裡悠閒度日,以終天年。除此之外,他對於生活再無所求,而且這種生活也正是千千萬萬的人曾經滿意度過的。他就是一個這樣平凡的人物,然而意外的事情竟發生了。他在打高爾夫球的時候,受了點涼,就此咳嗽起來,並且總好不了。他因為一向強壯健康,從沒有想到過要找醫生,最後還是他的妻子再三勸說,他才同意去看一次醫生。當他聽說兩個肺上都有了結核病並且只有立刻進療養院還有治癒希望的時候,那真是一個大打擊,一個可怕的大打擊。當時給他看病的醫生告訴他說:只要兩年之後就可照常工作了。但是現在兩年已經過去了,而林諾克司大夫卻勸他一年之內最好別做這打算,曾叫他看他痰內的細菌和他肺部的X光照片,這使他的心完全沉下去了。他覺得命運對他的作弄實在太不公平太過殘忍了。如果他曾過一種放蕩的生活,喝酒、遲睡、玩女人……,那麼得這種病也還不算意外,不算冤枉。但那些事情,他是一樣也不做的,所以這真是出奇地不公平。因為他本身沒有什麼修養,對書籍又不感興趣,所以除了想著自己的健康之外,再也無事可做。這又造成了一種精神上的病態,時刻焦急地注意著自己的病狀。他自己每天要量十二次體溫,並且有種成見,認為醫生對於他的病太不關心,為了引起注意,他想盡方法使體溫增到驚人的程度,要是做不到,便變得抑鬱不歡。但本質上他是個樂觀隨和的人,當他忘記自己的時候,他會很開心地談笑,只是一想起自己是個病人的時候,眼裡立刻就現出死亡的恐怖來。
每月的月尾,他的妻子總會到這裡來,在附近的旅館裡住上一兩天。林諾克司大夫是不大喜歡這些病人家屬來探望的,因為這會使病人的情緒激動不安,可是看了蔡斯特盼著他妻子到來的熱切,誰都會感動的,不過注意去看的話,很奇怪的是,她每來一次,他的熱切便低落一點。蔡斯特太太是一位很討人喜歡的有說有笑的女人,說不上漂亮,但打扮得很整潔,像她丈夫一樣平庸,一望便知是位賢妻良母,溫和安靜,善於持家,盡職安分,與人無爭。她對於過了那麼許多年的呆板家庭生活非常滿意,她的唯一的生活調劑是看電影,最大的興奮是倫敦那些商店的大減價,而且這一切從未使她覺得單調,絕對地心滿意足。奧桑汀很喜歡她,當她談著她的孩子,她的房子,她的鄰居和她的平淡無奇的工作時,他很感興趣地去聽著。有一次他在路上遇見了她,那時蔡斯特正在院中接受治療試驗,所以只她一個人在走著,奧桑汀便提議一同去散步,他們談了一會閒話之後,她忽然問他對她丈夫的病覺得怎樣?
「我想他會完全好起來的。」
「我真是心煩得要命呢。」
「你要記著這是需要長期慢慢治療的,一個人要有耐性才行。」
他們又走了一會,他看見她哭了。
「不要這麼為他擔憂吧。」他溫和地說。「呵,你不知道我每次來這裡所忍受的滋味。也許我不應該說的,但我要說說,我可以信任你的,是不是?」
「當然可以。」
「我愛他,我非常崇拜他。我願意為他做世界上任何的事。我們從來沒有吵過架,從來沒有對一點小事意見不同。現在他竟開始恨我,這太使我傷心了。」
「呵,這我不相信。你不在的時候,他總是在談你,談得再好沒有了,他也是崇拜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