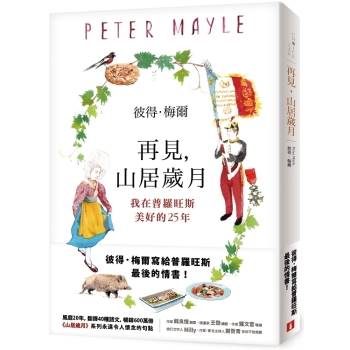一切始於天氣忽然變好。我和妻子珍妮為了躲避英國夏季的爛天氣,來到蔚藍海岸,想在風光優美如詩之地,好好地度假,為期兩週。眾口皆云那裡一年當中足足有三百天陽光普照,我們去的那一年偏偏就不是這麼回事,老天動不動就下起滂沱大雨。海灘上的遮陽傘濕透,傘布扁扁的,變成一團團;那些一身古銅色肌膚、負責巡邏海灘的年輕人擠在沙灘小屋中,泳褲濕答答。尼斯海濱英國人漫步道邊上的咖啡館裡,坐滿悲慘的父母和耍性子的孩子,大人原本答應小孩可以弄潮戲水一整天。《國際前鋒論壇報》上有條消息說,熱浪正襲擊英格蘭。我們準備離開尼斯,希望熱浪能延續到我們返家時。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需要得到某種慰藉。我們考慮越過邊界到義大利,要麼跳上航向科西嘉的渡輪,要不就開一大段路,南下巴塞隆納,趕過去吃晚飯。不過我們後來決定探索法國,不走高速公路,轉而行駛沒那麼寬廣的次級道路。我們心想,就算下著雨,沿路風光也會美麗一點、有趣一點,勝過加入主要幹道上由卡車和露營拖車形成的北上車流。再說,我們對法國的印象始終局限於巴黎和蔚藍海岸,接下來所到之處將是全新且未知的領域。
***
我們一邊喝著粉紅酒,一邊又瞧了瞧地圖,發覺呂貝宏山脈北側散落著好些村落。看來大有可為,而且從那裡回英國多少算是順路。我們吃了一頓恰到好處的普羅旺斯午餐,菜色有芥末兔肉和味道特別細緻的蘋果塔,送餐給我們的侍者簡直像樣版人物── 白圍裙、大肚腩,那一把八字鬍更是濃密得教人過目不忘── 我們蓄勢待發,不論迎面而來是什麼樣的崇山峻嶺,我們都作好準備。
我們駛離艾克斯,天空漸漸雲開日出,我們越往前走就看見越益大片的藍天。太陽依舊未露臉,但是下午的天氣越來越舒服。當我們遠離艾克斯,來到鄉間時,景色的轉換讓這個午後更顯宜人,風光優美而遼闊,常是一片又一片的荒野。葡萄園和向日葵花田遠遠多於房屋,眼前所見的房舍屋宇又是那麼迷人──石塊飽經風霜,屋瓦褪色,綠蔭蔥蘢,屋旁不是有兩三棵古老的梧桐樹,就是有兩排夾道的絲柏。我們後來才發覺,這正是典型的普羅旺斯鄉間風景,而我們當場愛上這般情景,且深愛至今。
空曠的田野間或變成一座座村莊,村中教堂的尖塔居高臨下,統領著塔底那一堆零亂分布的石屋。有幾幢屋子樓上的窗口晾曬著當天清洗的衣物,在我們看來,那是一個徵兆,顯示村民正等著陽光照耀,而在氣象預報這件事上,當地人始終是專家。果然,當我們駛入地圖上的「呂貝宏自然區公園」時,太陽出來了,陽光燦爛又歡暢,令萬事萬物看來鮮明而潔淨,大地景觀如蝕刻畫一般鑲在天邊,在尼斯度過的那些灰暗的雨天簡直像出現於另一個星球。
這會兒,我們可以遠遠地往呂貝宏山瞧上兩眼。山脈走向長而低矮,山勢看來並不崎嶇險峻,是讓人看著舒服的山。呂貝宏山甚至有條馬路看似從南到北,穿山越嶺,而我們正要往北走。我們在盧瑪杭(Lourmarin)村外選了這條路,朝向北方,可是這條路只有頭幾公里是平直的瀝青路,跟著就變得七彎八拐,那是我頭一回坐在車裡卻覺得暈船。雪上加霜的是,路面狹窄,往往一側是陡峭的岩壁,另一側為千丈懸崖,還有對向來車。來的若是機車,倒也不難閃躲,雖說有些騎士可真是把馬路當賽車道;若是汽車,倘若我們緊挨著岩壁,就勉強仍可通行。拖車和露營車則構成挑戰,尤其在轉彎處,我們拚命靠向一側,差一點就要擦上岩壁。我們提心吊膽,屏住呼吸,珍妮非常明智地閉上眼睛。
馬路總算逐漸變平變寬,我倆鬆了一口氣。路標指向文明的前哨 ── 奔牛村(Bonnieux),這村子美如風景明信片,地勢居高臨下,屹立於山頭,山谷風光一覽無遺。我們在地圖上查找下一站,目光被「波希村」(Village des Bories)這一行粗體字吸引。我們心裡直納悶,波希是什麼啊?是享有特權的小部落成員,可以建立自己的村落嗎?也或許是稀有高山動物的庇護區?還是說,這年頭人心如此開放、愛自由,那裡搞不好是天體村?我們決定去瞧瞧。
我們好不容易來到那村落,一個天體人士也沒見著,眼前是一幢幢非凡獨特的小屋,由採自當地的六吋厚石岩板堆砌而成,完全沒有水泥。這二十八幢波希小石屋的外觀有點像巨大的蜂巢,建於十八、十九世紀。有羊圈、烤窯、一間養蠶室、牲口棚和穀倉,想當年可都是符合生活所需的現代化設施,且都保存良好。
沉浸於歷史後,難免需要吃點、喝點什麼,好提神醒腦一下。幸好再往前走一會兒,勾德(Gordes)村裡就有。勾德如今已成典範,兼具田園之趣和世故老練之妙,有好旅館、餐廳和精品店,夏季時有絡繹不絕的遊客,然而彼時它還是個寂靜、幾乎無人居住卻美得驚人的小村,有如石頭搭建的電影場景。
勾德歷史可追溯至公元一○三一年,我們橫越主廣場時,一邊走一邊不難想像,此地自開村以來並未改變多少。村屋的外觀呈現著淡淡的蜂蜜色澤,那是千百年來的陽光留下的痕跡。多年來,不時有密斯脫拉風吹颳過整個普羅旺斯,石塊的表面皆因風化作用而變得光滑。廣場邊上有家咖啡館,更給這個下午增添樂趣。
我們坐在露天座位上眺望周遭的鄉野,說不定就是在那一刻,夫妻倆起心動念,想要改變生活。我們都覺得,要是能居住在此地,豈不妙哉。我們在職場打滾已久,在倫敦和紐約工作多年,已準備好要過簡單一點、陽光多一點的生活了。
***
坐在豔陽下的露天咖啡座盤算著易國而居是一回事,待回歸現實世界時,卻是另一回事。我們回到英格蘭以後,日子一天天過去,普羅旺斯就一天天顯得更加遙遠,也更令人嚮往。在那個階段,我們連想要住在普羅旺斯的哪個角落,都沒有一點概念。倘若把蔚藍海岸也算在內(我們可不會這麼算,因為那裡和真正的普羅旺斯根本是兩碼子事),這整個地區從北部山區到南部卡西斯(Cassis)和馬賽的海濱,總面積超過三萬平方公里。由於我們對未來的家園所知甚寡,一開始的時候就只能作作白日夢、讀讀旅遊書,這更加讓我們失去耐心。
珍妮起碼做了件有用的事:報名學法文,班上同學全是十幾歲的孩子。我本來就很熱中於講學生式的法語,我的口音曾讓勾德村一位女士開口說道:「可是,先生,您說的法語好像是西班牙牛在講話。」我起先以為這是在讚美我法語流利,可她真的是將我的口音比擬為西班牙牛在哞哞叫。
冬天帶著泥濘的腳步逐漸席捲英格蘭鄉間,我們藉由看地圖、閱讀《米其林指南》來自我安慰,打算初夏重返普羅旺斯。這一次,我們的行動會更周密,且完全講求實效。在那裡生活的開支需要多少?英國難民受人歡迎嗎?我們是否需要正式的居留許可?我們的兩條狗需要護照嗎?法國稅制到底有多麼可怕?我們討論許久,談話的基調在大部分時候都是樂天又無知,那是記憶當中最漫長的一個冬季,不過總歸還是結束了,我們至少在精神上又可以穿上短褲、戴上太陽眼鏡,準備好出發了。
我們時常注意到,英國人開車出國時,很愛往車裡塞進英國東西,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好比說,充足的茶葉、鍾愛的茶壺、巧克力甜餅、管它什麼季節也要帶著以防萬一的冬季毛衣、兩把小型摺疊躺椅、雨傘,還有非得帶上不可的腸胃藥,眾所周知外國人老愛把奇奇怪怪的玩意擱進菜裡。
我們則盡量清空車內,好騰出空間裝載我們打算帶回家的橄欖油和葡萄酒。駕車周遊普羅旺斯時,有一樁讓人分心的樂事,那就是沿途有不計其數的酒莊邀請口渴的過客順道拜訪,喝個一兩杯,而這難免會讓人順便就買上一兩瓶。如此這般地採買葡萄酒,格外令人心曠神怡,而且文明。停車的地方不論是古老的農舍,還是屋前有兩百公尺林蔭車道的小型凡爾賽宮,你都會受到溫暖的歡迎,對方既樂於幫忙,酒更往往美味。
不過,我們首先得到達那裡。我們需連人帶車搭渡輪前往卡萊港,然而穿越寬廣的法國鄉間。法國的人口數字和不列顛差不多,國土面積卻將近三倍大。當你駕車從法國的一端前往另一端,狀況更是明顯,遼闊的大地綿延不絕,看來宛若大批造景園藝工匠的心血結晶:田地和樹籬工整,柵欄維修完好,拖拉機在田裡留下的犁溝筆直到不行,放眼望去卻一片空曠,沒有房子,沒有人。
有句諺語說,「普羅旺斯始於瓦朗斯」。誠然,車子一過瓦朗斯,我們就看見天空逐漸換了顏色,建築物也從磚牆、石板瓦,變成石牆、陶瓦。陽光普照,氣溫慢慢上升,目的地快到了。
我們有位朋友在普羅旺斯已定居數年,拜其之助,我們在勾德村主廣場邊上租了一間小公寓,離咖啡館一百公尺,至麵包店只要兩分鐘腳程,隔壁還有家看來甚有可為的小餐館。另外,還裝了電話,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咱倆夫復何求?
我們成為勾德村民(雖然僅僅兩週)的第一個全天,有兩項重責要務:備妥糧草── 液體和固體都要,還有找到本地的房地產仲介。這兩件事只需要兩三小時就可以辦妥,我們當時這麼以為。
想當年,只有在大城和小鎮才有那種能夠讓人一次購足所需的超級市場。在普羅旺斯鄉下,想要買麵包就得上麵包店;買肉,去肉店;蔬果、乳酪、葡萄酒、洗衣粉、曬衣夾,各有各的專門店,店主往往是各自專門行業的行家,總是樂於將所知傾囊相授。還有當地顧客,絕大多數是凡事多疑的女士。她們下定決心絕不肯上當,誤買到被掐壞的蜜桃或外皮起縐的番茄,店老闆則自然而然會起而捍衛自家商品。於是這裡捏捏,那裡嗅嗅,倘若這樣無法奏效,那就試吃吧。老闆趁此時大力推銷,到末了,多疑的女士掏出腰包,雙方銀貨兩訖。這過程旁觀起來真是有意思,卻太花時間,買兩顆甜瓜一般得耗掉十分鐘,因之到了正午,我們還有數樣東西沒買齊。唉,偏偏店家一律午休,我們從而習得普羅旺斯購物學的第一堂課:早點上門、保持耐心、午餐不可遲到。
尋覓房地產仲介有點困難,不是因為缺乏,恰恰相反,幾乎每個村莊都找得到至少一處美得如詩如畫的小角落,開著一家不動產仲介公司,店外的木頭遮陽窗板上面掛著待售房屋的照片。這些鄉屋一律配上「機會不再、及早把握」的形容文字。問題在於,我們經驗不足,又容易受到左右,於是在我們看來,每幢建築都還可以:屋頂快垮下來的破爛穀倉;已有二十五年無人居住的可愛小村屋,之所以沒人住,想必有其原因;破舊到連鴿子都棄之不顧的鴿舍── 每一幢都似乎準備妥當,就等著人發揮想像力,大事翻修。
仲介當然跟我們一樣,也是摩拳擦掌、興致勃勃,他們的措詞用語足以令中古車銷售員臉紅。我們看到的每一張照片都配上圖說註釋── 潛力無窮的珍寶、夢幻一般、罕見且寶貴的機會。事情還不僅限於此,有好幾回,仲介對我們使出秘密武器,那就是,算我們走運,只要若干報酬,大夥都很樂於對我們伸出援手。仲介人脈廣,有一位連襟是建築師,一位表兄弟當電工,還有位阿姨是卓越的造景園藝師。
幸好,常識上場幫了忙,我們沒有被甜言蜜語沖昏頭。我們提醒自己,要找的是可以住的房子,而非需費時五年的計畫,所以我們繼續尋尋覓覓。
在此同時,我們也體會到小村生活的若干樂趣和值得玩味之處,很快便發覺,咱倆可是地方上的小小話題人物。素昧平生的人會在街上攔下我們,問我們找到房子了沒有。有天傍晚,我們發現有位和氣的老先生坐在我們的居處門前,他問清楚我們確是「英國佬」後,說明來訪的原因。
「聽說兩位有電話,這在村子裡非常少有。」
我們是有電話沒錯。「啊,那好,」他說,「我有個兒子,他太太懷孕了,可是我沒有收到消息,我想打電話給他。」
我們帶著他到電話機旁,讓他獨自在那裡打電話,心想他也就講個兩三分鐘吧。過了一刻鐘,他才又現身,一臉笑呵呵。
「我有孫子了,三公斤。」
我們恭喜他,他謝了我們,並且說他電話機旁留了一點東西。果然,桌上擺了一枚兩毛硬幣。直到我們收到電話費帳單,這才發現他的兒子住在加勒比海的馬丁尼克島。
日子過得有趣、美妙,偶爾讓人感到洩氣。主要是由於我們再怎麼拚命,語言溝通仍有問題,普羅旺斯人講話往往如連珠炮一般,而且不時會把擠眉弄眼和比手勢當成某種視覺性的標點符號,凡此種種更使得溝通難上加難。比方說,他們會以一派莊重的模樣點一點鼻子,表示此事需要謹慎處理;輕輕搖晃雙手,暗示著方才說的話不盡然正確;咬一咬拇指、拍一拍二頭肌、拉一拉耳垂、誇張地挑一挑眉頭。這還是雙方客客氣氣地在交談的情景,要是雙方一言不合吵了起來,天知道會有何等激烈的肢體動作。
剛進入第二個星期,我們在找房子這件事上時來運轉,在奔牛村的一間小辦公室裡認識莎賓娜。她不同於我們先前接觸過的房地產仲介,會傾聽我們述說心中想法,而不是想方設法向我們推銷她手裡已有的房產。她嬌小迷人,從左鄰右舍的噪音到種種謎樣的夙怨世仇,一一向我們提醒小村生活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頓時贏得我們對她的信心。她說,我們身為外來者,尤其還是外來的外國人,會勾起鄉親強烈的好奇心,成為蜚短流長的焦點,最好找個僻靜的所在,遠離窺探的目光和說三道四的嘴巴,不知我們意下如何?
她欣然得知我們同意她的看法,接著好像靈光一閃,拍了自己的腦門一下,說:「誒,當然如此!」她說明道,當天早上才收到剛上市求售的一幢房產照片,說不定正合乎理想。
她拿出照片,是一幢形狀不規則的穀倉兼農莊,色調柔和的石頭立面浴在陽光中,有條狗在梧桐樹蔭裡呼呼大睡。你幾乎聽得見蟋蟀在唧唧叫,其情其景如詩如畫,而且還不只這樣而已。
莎賓娜說明,這幢房子蓋在山坡上,俯瞰著無人居住的山谷── 她稱之為「私人景觀」。那會兒,我們早已準備好搬進去住了,就連屋價也未能令我們卻步。東挪西湊,總是能籌到款項的。我們和莎賓娜約好次日下午去看屋。
房屋一如照片所示,私人景觀美如風景明信片。屋主是位藝術家,人很親切,請我們自己隨意走走看看,他則坐在陰涼處和莎賓娜聊天。我們四處遊走、拍照、寫筆記、為我們的家具找擺設的地方、商量且決定相當簡單的廚房該如何裝潢。至於錢的問題,日後還有充足的時間可以討論,那會兒我們樂昏了頭。
屋主樂康特先生必然已將這一切收於眼底,意識到會很快成交,拿出一瓶粉紅酒,對我們一一道出這房子比較不是那麼一目瞭然的魅力。他說,在房屋下方的山谷裡有一片櫟樹木,每年冬天盛產滋味妙不可言的松露。屋後的山坡保護房子不受密斯脫拉風侵襲,此烈風來自西伯利亞,從吹掀了屋頂到逼人自殺,種種壞事都可以怪它。私人水源供應充足,對我家的狗兒來講可謂完美國度,而且沒有煩人的鄰居會來打擾我們。他娓娓道來,我們還沒有聽他講完,就已經買定了這房子。
當天晚上為表示慶祝,我們到小村畢歐(Buoux)吃飯,館子是莎賓娜推薦的,她認得店主兼大廚莫理斯,說我們不會失望。我們果然沒有失望,其後多年,我們時常在此愉快地用餐,夏季坐在戶外吃午餐和晚餐,冬天則坐在大壁爐前。這麼多年下來,我可以公道地說,在那兒吃到的每一口飯菜都讓我齒頰留芳。
頭一回造訪的那一天,我們陶醉在幸福的感覺中,無法相信咱倆竟如此好運,一切都好得簡直不像是真的。
當然,世上哪有此等好事。
【試讀內容摘錄自《再見,山居歲月:我在普羅旺斯美好的25年》】
在這種情況之下,我們需要得到某種慰藉。我們考慮越過邊界到義大利,要麼跳上航向科西嘉的渡輪,要不就開一大段路,南下巴塞隆納,趕過去吃晚飯。不過我們後來決定探索法國,不走高速公路,轉而行駛沒那麼寬廣的次級道路。我們心想,就算下著雨,沿路風光也會美麗一點、有趣一點,勝過加入主要幹道上由卡車和露營拖車形成的北上車流。再說,我們對法國的印象始終局限於巴黎和蔚藍海岸,接下來所到之處將是全新且未知的領域。
***
我們一邊喝著粉紅酒,一邊又瞧了瞧地圖,發覺呂貝宏山脈北側散落著好些村落。看來大有可為,而且從那裡回英國多少算是順路。我們吃了一頓恰到好處的普羅旺斯午餐,菜色有芥末兔肉和味道特別細緻的蘋果塔,送餐給我們的侍者簡直像樣版人物── 白圍裙、大肚腩,那一把八字鬍更是濃密得教人過目不忘── 我們蓄勢待發,不論迎面而來是什麼樣的崇山峻嶺,我們都作好準備。
我們駛離艾克斯,天空漸漸雲開日出,我們越往前走就看見越益大片的藍天。太陽依舊未露臉,但是下午的天氣越來越舒服。當我們遠離艾克斯,來到鄉間時,景色的轉換讓這個午後更顯宜人,風光優美而遼闊,常是一片又一片的荒野。葡萄園和向日葵花田遠遠多於房屋,眼前所見的房舍屋宇又是那麼迷人──石塊飽經風霜,屋瓦褪色,綠蔭蔥蘢,屋旁不是有兩三棵古老的梧桐樹,就是有兩排夾道的絲柏。我們後來才發覺,這正是典型的普羅旺斯鄉間風景,而我們當場愛上這般情景,且深愛至今。
空曠的田野間或變成一座座村莊,村中教堂的尖塔居高臨下,統領著塔底那一堆零亂分布的石屋。有幾幢屋子樓上的窗口晾曬著當天清洗的衣物,在我們看來,那是一個徵兆,顯示村民正等著陽光照耀,而在氣象預報這件事上,當地人始終是專家。果然,當我們駛入地圖上的「呂貝宏自然區公園」時,太陽出來了,陽光燦爛又歡暢,令萬事萬物看來鮮明而潔淨,大地景觀如蝕刻畫一般鑲在天邊,在尼斯度過的那些灰暗的雨天簡直像出現於另一個星球。
這會兒,我們可以遠遠地往呂貝宏山瞧上兩眼。山脈走向長而低矮,山勢看來並不崎嶇險峻,是讓人看著舒服的山。呂貝宏山甚至有條馬路看似從南到北,穿山越嶺,而我們正要往北走。我們在盧瑪杭(Lourmarin)村外選了這條路,朝向北方,可是這條路只有頭幾公里是平直的瀝青路,跟著就變得七彎八拐,那是我頭一回坐在車裡卻覺得暈船。雪上加霜的是,路面狹窄,往往一側是陡峭的岩壁,另一側為千丈懸崖,還有對向來車。來的若是機車,倒也不難閃躲,雖說有些騎士可真是把馬路當賽車道;若是汽車,倘若我們緊挨著岩壁,就勉強仍可通行。拖車和露營車則構成挑戰,尤其在轉彎處,我們拚命靠向一側,差一點就要擦上岩壁。我們提心吊膽,屏住呼吸,珍妮非常明智地閉上眼睛。
馬路總算逐漸變平變寬,我倆鬆了一口氣。路標指向文明的前哨 ── 奔牛村(Bonnieux),這村子美如風景明信片,地勢居高臨下,屹立於山頭,山谷風光一覽無遺。我們在地圖上查找下一站,目光被「波希村」(Village des Bories)這一行粗體字吸引。我們心裡直納悶,波希是什麼啊?是享有特權的小部落成員,可以建立自己的村落嗎?也或許是稀有高山動物的庇護區?還是說,這年頭人心如此開放、愛自由,那裡搞不好是天體村?我們決定去瞧瞧。
我們好不容易來到那村落,一個天體人士也沒見著,眼前是一幢幢非凡獨特的小屋,由採自當地的六吋厚石岩板堆砌而成,完全沒有水泥。這二十八幢波希小石屋的外觀有點像巨大的蜂巢,建於十八、十九世紀。有羊圈、烤窯、一間養蠶室、牲口棚和穀倉,想當年可都是符合生活所需的現代化設施,且都保存良好。
沉浸於歷史後,難免需要吃點、喝點什麼,好提神醒腦一下。幸好再往前走一會兒,勾德(Gordes)村裡就有。勾德如今已成典範,兼具田園之趣和世故老練之妙,有好旅館、餐廳和精品店,夏季時有絡繹不絕的遊客,然而彼時它還是個寂靜、幾乎無人居住卻美得驚人的小村,有如石頭搭建的電影場景。
勾德歷史可追溯至公元一○三一年,我們橫越主廣場時,一邊走一邊不難想像,此地自開村以來並未改變多少。村屋的外觀呈現著淡淡的蜂蜜色澤,那是千百年來的陽光留下的痕跡。多年來,不時有密斯脫拉風吹颳過整個普羅旺斯,石塊的表面皆因風化作用而變得光滑。廣場邊上有家咖啡館,更給這個下午增添樂趣。
我們坐在露天座位上眺望周遭的鄉野,說不定就是在那一刻,夫妻倆起心動念,想要改變生活。我們都覺得,要是能居住在此地,豈不妙哉。我們在職場打滾已久,在倫敦和紐約工作多年,已準備好要過簡單一點、陽光多一點的生活了。
***
坐在豔陽下的露天咖啡座盤算著易國而居是一回事,待回歸現實世界時,卻是另一回事。我們回到英格蘭以後,日子一天天過去,普羅旺斯就一天天顯得更加遙遠,也更令人嚮往。在那個階段,我們連想要住在普羅旺斯的哪個角落,都沒有一點概念。倘若把蔚藍海岸也算在內(我們可不會這麼算,因為那裡和真正的普羅旺斯根本是兩碼子事),這整個地區從北部山區到南部卡西斯(Cassis)和馬賽的海濱,總面積超過三萬平方公里。由於我們對未來的家園所知甚寡,一開始的時候就只能作作白日夢、讀讀旅遊書,這更加讓我們失去耐心。
珍妮起碼做了件有用的事:報名學法文,班上同學全是十幾歲的孩子。我本來就很熱中於講學生式的法語,我的口音曾讓勾德村一位女士開口說道:「可是,先生,您說的法語好像是西班牙牛在講話。」我起先以為這是在讚美我法語流利,可她真的是將我的口音比擬為西班牙牛在哞哞叫。
冬天帶著泥濘的腳步逐漸席捲英格蘭鄉間,我們藉由看地圖、閱讀《米其林指南》來自我安慰,打算初夏重返普羅旺斯。這一次,我們的行動會更周密,且完全講求實效。在那裡生活的開支需要多少?英國難民受人歡迎嗎?我們是否需要正式的居留許可?我們的兩條狗需要護照嗎?法國稅制到底有多麼可怕?我們討論許久,談話的基調在大部分時候都是樂天又無知,那是記憶當中最漫長的一個冬季,不過總歸還是結束了,我們至少在精神上又可以穿上短褲、戴上太陽眼鏡,準備好出發了。
我們時常注意到,英國人開車出國時,很愛往車裡塞進英國東西,越多越好,多多益善。好比說,充足的茶葉、鍾愛的茶壺、巧克力甜餅、管它什麼季節也要帶著以防萬一的冬季毛衣、兩把小型摺疊躺椅、雨傘,還有非得帶上不可的腸胃藥,眾所周知外國人老愛把奇奇怪怪的玩意擱進菜裡。
我們則盡量清空車內,好騰出空間裝載我們打算帶回家的橄欖油和葡萄酒。駕車周遊普羅旺斯時,有一樁讓人分心的樂事,那就是沿途有不計其數的酒莊邀請口渴的過客順道拜訪,喝個一兩杯,而這難免會讓人順便就買上一兩瓶。如此這般地採買葡萄酒,格外令人心曠神怡,而且文明。停車的地方不論是古老的農舍,還是屋前有兩百公尺林蔭車道的小型凡爾賽宮,你都會受到溫暖的歡迎,對方既樂於幫忙,酒更往往美味。
不過,我們首先得到達那裡。我們需連人帶車搭渡輪前往卡萊港,然而穿越寬廣的法國鄉間。法國的人口數字和不列顛差不多,國土面積卻將近三倍大。當你駕車從法國的一端前往另一端,狀況更是明顯,遼闊的大地綿延不絕,看來宛若大批造景園藝工匠的心血結晶:田地和樹籬工整,柵欄維修完好,拖拉機在田裡留下的犁溝筆直到不行,放眼望去卻一片空曠,沒有房子,沒有人。
有句諺語說,「普羅旺斯始於瓦朗斯」。誠然,車子一過瓦朗斯,我們就看見天空逐漸換了顏色,建築物也從磚牆、石板瓦,變成石牆、陶瓦。陽光普照,氣溫慢慢上升,目的地快到了。
我們有位朋友在普羅旺斯已定居數年,拜其之助,我們在勾德村主廣場邊上租了一間小公寓,離咖啡館一百公尺,至麵包店只要兩分鐘腳程,隔壁還有家看來甚有可為的小餐館。另外,還裝了電話,這在當時是很罕見的。咱倆夫復何求?
我們成為勾德村民(雖然僅僅兩週)的第一個全天,有兩項重責要務:備妥糧草── 液體和固體都要,還有找到本地的房地產仲介。這兩件事只需要兩三小時就可以辦妥,我們當時這麼以為。
想當年,只有在大城和小鎮才有那種能夠讓人一次購足所需的超級市場。在普羅旺斯鄉下,想要買麵包就得上麵包店;買肉,去肉店;蔬果、乳酪、葡萄酒、洗衣粉、曬衣夾,各有各的專門店,店主往往是各自專門行業的行家,總是樂於將所知傾囊相授。還有當地顧客,絕大多數是凡事多疑的女士。她們下定決心絕不肯上當,誤買到被掐壞的蜜桃或外皮起縐的番茄,店老闆則自然而然會起而捍衛自家商品。於是這裡捏捏,那裡嗅嗅,倘若這樣無法奏效,那就試吃吧。老闆趁此時大力推銷,到末了,多疑的女士掏出腰包,雙方銀貨兩訖。這過程旁觀起來真是有意思,卻太花時間,買兩顆甜瓜一般得耗掉十分鐘,因之到了正午,我們還有數樣東西沒買齊。唉,偏偏店家一律午休,我們從而習得普羅旺斯購物學的第一堂課:早點上門、保持耐心、午餐不可遲到。
尋覓房地產仲介有點困難,不是因為缺乏,恰恰相反,幾乎每個村莊都找得到至少一處美得如詩如畫的小角落,開著一家不動產仲介公司,店外的木頭遮陽窗板上面掛著待售房屋的照片。這些鄉屋一律配上「機會不再、及早把握」的形容文字。問題在於,我們經驗不足,又容易受到左右,於是在我們看來,每幢建築都還可以:屋頂快垮下來的破爛穀倉;已有二十五年無人居住的可愛小村屋,之所以沒人住,想必有其原因;破舊到連鴿子都棄之不顧的鴿舍── 每一幢都似乎準備妥當,就等著人發揮想像力,大事翻修。
仲介當然跟我們一樣,也是摩拳擦掌、興致勃勃,他們的措詞用語足以令中古車銷售員臉紅。我們看到的每一張照片都配上圖說註釋── 潛力無窮的珍寶、夢幻一般、罕見且寶貴的機會。事情還不僅限於此,有好幾回,仲介對我們使出秘密武器,那就是,算我們走運,只要若干報酬,大夥都很樂於對我們伸出援手。仲介人脈廣,有一位連襟是建築師,一位表兄弟當電工,還有位阿姨是卓越的造景園藝師。
幸好,常識上場幫了忙,我們沒有被甜言蜜語沖昏頭。我們提醒自己,要找的是可以住的房子,而非需費時五年的計畫,所以我們繼續尋尋覓覓。
在此同時,我們也體會到小村生活的若干樂趣和值得玩味之處,很快便發覺,咱倆可是地方上的小小話題人物。素昧平生的人會在街上攔下我們,問我們找到房子了沒有。有天傍晚,我們發現有位和氣的老先生坐在我們的居處門前,他問清楚我們確是「英國佬」後,說明來訪的原因。
「聽說兩位有電話,這在村子裡非常少有。」
我們是有電話沒錯。「啊,那好,」他說,「我有個兒子,他太太懷孕了,可是我沒有收到消息,我想打電話給他。」
我們帶著他到電話機旁,讓他獨自在那裡打電話,心想他也就講個兩三分鐘吧。過了一刻鐘,他才又現身,一臉笑呵呵。
「我有孫子了,三公斤。」
我們恭喜他,他謝了我們,並且說他電話機旁留了一點東西。果然,桌上擺了一枚兩毛硬幣。直到我們收到電話費帳單,這才發現他的兒子住在加勒比海的馬丁尼克島。
日子過得有趣、美妙,偶爾讓人感到洩氣。主要是由於我們再怎麼拚命,語言溝通仍有問題,普羅旺斯人講話往往如連珠炮一般,而且不時會把擠眉弄眼和比手勢當成某種視覺性的標點符號,凡此種種更使得溝通難上加難。比方說,他們會以一派莊重的模樣點一點鼻子,表示此事需要謹慎處理;輕輕搖晃雙手,暗示著方才說的話不盡然正確;咬一咬拇指、拍一拍二頭肌、拉一拉耳垂、誇張地挑一挑眉頭。這還是雙方客客氣氣地在交談的情景,要是雙方一言不合吵了起來,天知道會有何等激烈的肢體動作。
剛進入第二個星期,我們在找房子這件事上時來運轉,在奔牛村的一間小辦公室裡認識莎賓娜。她不同於我們先前接觸過的房地產仲介,會傾聽我們述說心中想法,而不是想方設法向我們推銷她手裡已有的房產。她嬌小迷人,從左鄰右舍的噪音到種種謎樣的夙怨世仇,一一向我們提醒小村生活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頓時贏得我們對她的信心。她說,我們身為外來者,尤其還是外來的外國人,會勾起鄉親強烈的好奇心,成為蜚短流長的焦點,最好找個僻靜的所在,遠離窺探的目光和說三道四的嘴巴,不知我們意下如何?
她欣然得知我們同意她的看法,接著好像靈光一閃,拍了自己的腦門一下,說:「誒,當然如此!」她說明道,當天早上才收到剛上市求售的一幢房產照片,說不定正合乎理想。
她拿出照片,是一幢形狀不規則的穀倉兼農莊,色調柔和的石頭立面浴在陽光中,有條狗在梧桐樹蔭裡呼呼大睡。你幾乎聽得見蟋蟀在唧唧叫,其情其景如詩如畫,而且還不只這樣而已。
莎賓娜說明,這幢房子蓋在山坡上,俯瞰著無人居住的山谷── 她稱之為「私人景觀」。那會兒,我們早已準備好搬進去住了,就連屋價也未能令我們卻步。東挪西湊,總是能籌到款項的。我們和莎賓娜約好次日下午去看屋。
房屋一如照片所示,私人景觀美如風景明信片。屋主是位藝術家,人很親切,請我們自己隨意走走看看,他則坐在陰涼處和莎賓娜聊天。我們四處遊走、拍照、寫筆記、為我們的家具找擺設的地方、商量且決定相當簡單的廚房該如何裝潢。至於錢的問題,日後還有充足的時間可以討論,那會兒我們樂昏了頭。
屋主樂康特先生必然已將這一切收於眼底,意識到會很快成交,拿出一瓶粉紅酒,對我們一一道出這房子比較不是那麼一目瞭然的魅力。他說,在房屋下方的山谷裡有一片櫟樹木,每年冬天盛產滋味妙不可言的松露。屋後的山坡保護房子不受密斯脫拉風侵襲,此烈風來自西伯利亞,從吹掀了屋頂到逼人自殺,種種壞事都可以怪它。私人水源供應充足,對我家的狗兒來講可謂完美國度,而且沒有煩人的鄰居會來打擾我們。他娓娓道來,我們還沒有聽他講完,就已經買定了這房子。
當天晚上為表示慶祝,我們到小村畢歐(Buoux)吃飯,館子是莎賓娜推薦的,她認得店主兼大廚莫理斯,說我們不會失望。我們果然沒有失望,其後多年,我們時常在此愉快地用餐,夏季坐在戶外吃午餐和晚餐,冬天則坐在大壁爐前。這麼多年下來,我可以公道地說,在那兒吃到的每一口飯菜都讓我齒頰留芳。
頭一回造訪的那一天,我們陶醉在幸福的感覺中,無法相信咱倆竟如此好運,一切都好得簡直不像是真的。
當然,世上哪有此等好事。
【試讀內容摘錄自《再見,山居歲月:我在普羅旺斯美好的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