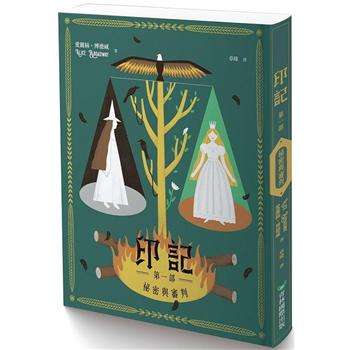第二十九章
我到工作室的時候,歐貝爾已經在了,看得出來他已經待上好一段時間。他看起來很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這睡了一晚。我很訝異他看到我的時候,臉上浮現鬆一口氣的表情,我以為自己不會被歡迎;說真的,我原本以為自己必須努力贏回這份工作。
「你不知道看到你我有多開心。」歐貝爾很快站起來,從我手中接過外套,幫我掛好,「我知道昨天一團糟,我說的一些話……」
「我們說的一些話。」我懊惱地說。
「萊歐拉,我們現在就同意各持己見吧。不可否認的是,你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印記師,不管我們抱持的信念是否相同,我都想要繼續培訓你。你覺得怎麼樣?」
我猶豫一下,然後點頭,腦子裡千頭萬緒,根本做不出決定。現在,我就先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
「太好了!我今天很需要你。」歐貝爾說,遞給我一封信,「昨天發生卡爾的事情之後,官員要過來調查。這小子留了一堆爛攤子讓我收拾。」他對我無奈地笑。
我很快掃過信件,信裡提到一名叫傑克.明饒的人今天會來工作室。信上說,他會幫助歐貝爾準備需要的文件,記錄卡爾在沒有歐貝爾監督下,幫客人刻劃印記的過程。
「動作真快。」我皺起眉頭。
「對啊,我昨晚才舉報。要嘛是他們真的很閒,要嘛就是真的非常想來調查我。」歐貝爾嚥了一口口水,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緊張。
我們核對彼此對事發經過的描述,確定故事吻合。歐貝爾開店時,我負責打掃、整頓工作室,讓一切就緒;因為不確定政府的調查員何時會來,我們決定不如就照常工作。
工作室來了幾個人,我替一位女士在接近週末的時候預約諮詢,我坐在接待區,在預約簿上填寫資料的時候,聽到門鈴叮咚作響。我抬頭看,一位穿著政府高官正式黑色制服的高大男人,正任憑身後的門重重關上。
「傑克.明饒。」他說,「我找歐貝爾.維特沃斯。」
他剃了個光頭、皮膚晒得黝黑,高高站在我面前,他肯定比歐貝爾還高大。剃光的頭上有著細緻的印記,我瞬間解讀了瞄到的印記:都和獵食動物有關,意義清晰明瞭。他的頭皮上刻劃著一群鬣狗,我讀到那是為了慶祝成功驅逐空白人而刻劃的印記,所有的暴力和殘酷都還留在印記上。我讀到他對血腥的喜愛,不禁打起冷顫,但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平靜鎮定。
「明饒先生,請坐,我去請歐貝爾過來。您要喝點什麼嗎?」我的聲音太高亢了,他一定聽出我有多緊張。
傑克.明饒閉上眼睛、搖搖頭,當他睜開雙眼的時候,露出有點得意的笑,「請維特沃斯先生過來就行了。」
我才要離開,歐貝爾就剛好走進工作室,用抹布擦著雙手。他伸出一隻手來和明饒打招呼,明饒握了他的手,因為歐貝爾還濕濕的手而皺眉。
「維特沃斯先生,我們就開始吧?」他一邊在褲子上擦手,一邊看著歐貝爾,毫不掩飾他的敵意,「有人最近很調皮,對吧?我聽說是未在你的監督之下,擅自刻劃印記?」他放縱地咯咯笑,「我相信那位當事人很有野心。我得承認,我欣賞這樣的特質。」
歐貝爾要我去休息室練習畫畫,但明饒制止了他。
「我想跟你們兩人說話。弗林特小姐,請坐。」
他要我們告訴他事情發生的經過,且由我先開始。我開始說著事情始末,一邊分神注意傑克.明饒,一邊又看著歐貝爾,擔心說錯話會害他遭殃。這一次的來訪只是為了卡爾的事嗎?
明饒一直在做筆記,並問一些小問題好釐清細節。過程都非常有禮,但我感覺他是在等我說溜嘴。他的印記炯炯閃耀、栩栩如生,我根本沒辦法好好思考;他也問了歐貝爾相同的問題,質問他為什麼離開我和卡爾、逼問他在開除卡爾的時候,對他說的話等種種細節。他一言不發地記錄,幾分鐘後,遞給我一張紙。
「麻煩你看過一遍。若是同意我的紀錄,就請簽名。」重讀事件的經過,就好像再經歷一次昨天一樣,我心不在焉地揉著頭。
「看起來可以。」我說,把紙推還給桌子對面的他。
「可以還是正確,弗林特小姐?這兩者可不一樣。」他說的時候雖然帶著微笑,但我覺得那是惡魔才會有的微笑。
「正確無誤,跟我說的一樣,也是事實。」他遞給我一支筆;簽好名後,我很快瞄了歐貝爾一眼,確定自己做的事沒錯。
「謝謝。」明饒把筆交給歐貝爾,他在我的簽名上方簽下自己的名字。明饒把我們的供詞放進他的袋子裡,開始環顧四周。他往後靠上椅背,伸展一下身體,「弗林特小姐,你覺得這裡怎麼樣?目前為止一切都順利嗎?」
「一切都很好!當然,除了那個以外,」我以下巴示意他的袋子和裡面的供詞,「其他我都很喜歡。」
「那維特沃斯先生呢?」他看著歐貝爾,「你對他滿意嗎?他有沒有好好訓練你?」
歐貝爾就站在旁邊,我卻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雖然覺得很怪,但我試著表現鎮定,「他非常好,我在這裡很開心。」我不要再說更多話了。
「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維特沃斯先生,不如你帶我參觀一下吧?」明饒拿起袋子,和歐貝爾走到接待區,邊走邊聊天。我讓他們兩個單獨聊,正想自己回休息室的時候,卻聽到明饒的聲音愈來愈清楚。我抬頭看,發現他正往回走,一邊解開背心的扣子,一邊走往歐貝爾的工作區。
明饒放鬆地坐在椅子上,好像那是他自己的椅子一樣。他把袋子放在地上,朝我這邊看。
「我看你們現在都不忙,所以你的導師剛剛說可以幫我刻劃印記,你說是吧,維特沃斯?」我看見歐貝爾整個人都僵掉了,很顯然這不是一個疑問句。明饒解開一顆顆的釦子、脫去背心和短袖汗衫。隨著衣服被脫去,我看見他身上的印記;那是以前解讀印記時,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感受。他印記裡的暴力和憤怒十分猛烈,讓人無法承受。我想逃跑、我想大哭、我想告訴他,我可以看穿他,但我只是保持沉默,看著他和歐貝爾之間的詭譎互動。
歐貝爾打破沉默,「明饒先生,一般我們不會這麼做。通常,我們會先和您諮詢,再請您回來刻劃印記;但如果是您的話,我們當然很樂意,這是我們的榮幸。」歐貝爾看著我,「萊歐拉,明饒先生想要……一隻貓頭鷹。對嗎,明饒先生?」
明饒魯莽地點點頭,他的肩膀魁梧,「對,一隻大鵰鴞。」他附和。我知道他在講哪一種貓頭鷹,歐貝爾叫我練習畫了千百種生物。
歐貝爾開始問他通常詢問客人的制式問題,就跟平常一樣冷靜。我離開去準備工具,當我帶著裝滿工具的托盤回來時,聽見歐貝爾和明饒對話的結尾。
「……是的,傑出的獵食者,視覺和聽覺都無以倫比。獵物以為牠們已經跑得夠快夠遠,隱密地藏身在貓頭鷹看不見的地方,結果牠咻地俯衝而下,獵物都還沒聽到牠的聲音,就已經被抓到了,無法阻擋、令人生畏。」
歐貝爾吞了一口口水,轉向我,「萊歐拉,謝謝,接下來的就交給我。」
我轉身要離開,明饒卻在這時說:「我們何不把這當作一個訓練的機會?我想請萊歐拉幫我刻劃印記。」
我的震驚顯露無遺。
「你之前刻劃過印記了,對嗎?」我虛弱地點點頭。「那就沒問題了,至少維特沃斯先生會在一旁協助你。我想把印記刻劃在這裡,在我的肩膀上方,牠可以看守我的家人。」
我用顫抖的雙手擦拭工作檯,仔細消毒每個地方,再將工具依照我習慣的順序擺放好。我向明饒說明即將使用的器具都乾淨嶄新,並詢問他想要什麼樣子的貓頭鷹。我給他看一些我畫的草圖,心裡很感謝歐貝爾叫我練習畫這麼多圖。我開始清潔明饒的皮膚、剃掉細小的黑色汗毛。每碰到他的皮膚一次,他的印記便對我咆哮一次;這和替上次那位女士刻劃印記時,所感受到的愉悅電流完全不同,現在的感覺像是有一群謀殺犯大聲渴求鮮血。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夠再和他多相處一秒,更別說得花上好幾個小時完成他的印記。為了拖延時間,我給他看轉印紙上的圖案,以確認我已完全了解他想要的印記。我對歐貝爾眨眼;很少見地,他看起來很擔心,但當他注意到我時,他用微笑表示肯定。
「妹妹,你沒問題的。你天生就是印記師,記得嗎?」他輕聲說。
我把畫好的圖騰轉印到明饒的皮膚上,讓圖案留下清楚的輪廓痕跡。每一次接觸到他的皮膚,我都要鼓起勇氣、試著不讓他印記中的暴戾之氣干擾我。我用鏡子反射圖騰的線條給明饒看,他點點頭。
開始刻劃後,我聽著工具熟悉的聲響,任由機器引領我的思緒。但只要我一開始覺得安全自在的時候,明饒就會開口說話,就好像在快要睡著的時候,被人一把從床上抓起來一樣,每一次我都因為被打斷而驚嚇不已。這讓我更沒辦法專注聽他說話,以及構思我的回答。
「萊歐拉,你刻劃的第一個印記是什麼?」他問。
「是一片樹葉。」我渙散地回應。
「樹葉?刻在哪裡?」我正在刻劃貓頭鷹的爪子,心裡想著那位心碎的女士,於是脫口而出:「在她的家庭樹下,她的寶寶過世了。」
我發現他的肌肉緊繃了起來,這已足夠讓我清醒一點,提起警戒。
「喔,她想要一個紀念寶寶的印記?」
我還記得那位女士說的話,彷彿她正說著那些字句:「如果他在刻劃出生印記之前就過世的話,我知道自己應該要忘記他……他才兩天大。」接著,我想起歐貝爾的警告。我不能讓他失望,我得想辦法讓明饒不再發問。
我給自己一點時間深呼吸,故意在明饒一塊已經紅腫的皮膚上,隨意拖著針頭。我聽到他倒抽一口氣。
「啊,對不起!」我說,「我需要更專心一點,你知道我還在學。顯然我還沒辦法一邊聊天一邊刻劃。」
歐貝爾注意到了,他在明饒沒在看的時候,迅速笑了一下。那之後,唯一的聲音就是刺青機器的聲響、明饒忍受疼痛時發出的喘氣聲,還有他的印記張狂對我嘶吼祕密的喊叫聲。
在輪廓終於完成之後,明饒的皮膚已經因為太過紅腫,而沒辦法再繼續刻劃印記。
「明饒先生,我想我們得等傷口稍微復原一點,才能繼續進行。」我對他說,幫他擦拭血跡,並包紮我在他肩膀上刻劃的美麗又駭人的印記。我迫不及待他趕快離開,「印記很好看,」我邊說邊脫手套,「看起來就像貓頭鷹準備好要俯衝而下、捕抓獵物。」我用盡全力讓自己聽起來輕鬆隨意,「不曉得大鵰鴞都抓什麼樣的獵物。」
「任何微小又不重要的生物,我想牠幾乎都抓。」明饒說,「不過,牠們捕抓的其中一種獵物,我認為非常特別,顯示了貓頭鷹有多勇敢和強壯。」
「喔,是嗎?」我爽朗地問,「是什麼?」
我的手忙著整理工作檯、拆除椅子上的塑膠套。
「烏鴉。大鵰鴞獵捕烏鴉。深夜時分,當烏鴉棲息、以為安全無虞的時候,貓頭鷹就會來抓牠們。」
我把塑膠套丟掉,擦了擦雙手,把襯衫拿給明饒,確保他在穿上襯衫時,不拉扯到包裹傷口的繃帶,同時試著對他彬彬有禮地微笑。他也是獵食者。
我在幫忙的時候,他抓住我的手,皺眉看著我仍在痊癒的傷口,「割到手了?你可得小心點,弗林特小姐。」
他放開我的手,我一句話也沒說。他沒有預約下一次的時間,但說會再找時間過來。他正要離開時,突然停下腳步、轉向我,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事似地從口袋拿出某樣東西。他把東西拿到我面前。
「有沒有看過像這樣的東西?」我看著那張皺巴巴的紙,嚥下一口口水—那是羽毛的圖騰,跟關店後來訪的那位女士遞給歐貝爾的紙條一模一樣。我搖搖頭。
「沒有,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我輕描淡寫地說,努力讓臉不要漲紅。他把紙張收回口袋,沉默地盯著我看。我目送明饒走出門,看到他忘記肩上的印記、逕自把背帶掛上肩膀,因疼痛而抽動時,那一刻,我感到非常開心。
他頭也不回地向前走。當他完全走出視線時,我關門,並上了鎖。我回到休息室去,一遍又一遍地刷洗自己的手,直到雙手發紅刺痛。歐貝爾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把水龍頭關上,我沒有阻止他。我擦乾顫抖的雙手。
「歐貝爾,我很害怕。」
而最糟糕的是,歐貝爾也回說:「我也是,萊歐拉,我也是。」
第三十章
那天下午,歐貝爾正跟客人在一起,而我安靜工作的時候,工作室的後門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開門,發現是薇瑞蒂。她上氣不接下氣,雙眼瞪大、充滿恐懼。我走到門外,站在街道上。
「他們找到了。」薇瑞蒂低聲地說,「所有康納.卓隱藏的證據,都藏在他工場裡的一個祕密空間內。現在是休息時間,我不能離開辦公室太久。但是,萊歐拉,」她停頓一下,調整呼吸,「他們沒收了所有東西,證據都在政府大樓裡,明天就要被逐一歸檔記錄。沒剩多少時間了,你得在他們之前找到你爸爸的皮膚。」我點點頭。薇瑞蒂給我一張對折的紙條和一把鑰匙,「這會幫得上忙,你今晚就要行動。」她瞪大雙眼,眼神十分害怕,「千萬要小心,萊歐拉,這風險太大了。」
我還沒來得及道別或道謝,她就離開了。
我祈禱奧斯卡有收到我留的訊息,我祈禱他會赴約。我提議約在博物館,因為裡面既溫暖又不收費,加上又是公共場所,所以人多且忙碌,沒人會懷疑我們在密謀什麼不宜的事。我根本沒想到會需要策畫潛入政府大樓,但反正這裡是個絕佳的討論地點。
我看到奧斯卡在接待區等我的時候,整個人如釋重負地差點哭出來。我平復情緒,兩人一言不發地走過存放歷代領導者生命之書的中庭;偶爾停下腳步,欣賞某件藝術品或考古文物,但大多時間我們就這麼走著。
我邊走邊把薇瑞蒂給我的紙張遞給奧斯卡,那是政府大樓的地圖,上面指示著如何前往存放被沒收證據的地方。我低聲告訴奧斯卡薇瑞蒂跟我說的事,他沉重地點點頭,沒有我想像得那麼震驚,他肯定知道這一刻總有一天會來臨,或至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他把紙塞進外套口袋,我們沉默地盯著玻璃看了一會。他轉向我,非常溫柔地把我的頭髮從眼前撥開,我額頭上的瘀青露了出來。看到我頭上又紅又紫的瘀青,他皺起眉頭。
「你還好嗎?」他問我,聲音低沉,「我每次看到你,你就多一道傷痕。」他抓起我的手,仔細看著結痂的傷口。我突然意識到他的手有多溫暖厚實;他的手指劃過我的年齡印記時,我能感受到他粗糙的皮膚。
「你需不需要保鑣?」
我笑了出來,把手抽開,「你想當我的保鑣嗎?」
「裝訂師的體格可是很出名的。」他也笑起來,而我繼續對著他傻笑。
「萊歐拉,你希望大家記起你的時候,會想到什麼?」他突然問,「你一定會刻劃在皮膚上的,會是什麼樣的印記?」
我微微皺眉,這個問題讓我措手不及,感覺好奇怪,還有點嚇人;但當我抬頭看他的臉時,我知道他是認真的。我閉上眼睛思考:我的第一個印記會是什麼樣子?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我的印記中讀到什麼?大家想起我的時候,我想要他們記得什麼?什麼東西重要到能夠永久流傳?
我什麼都想不到。
我想著所有想做的事:當一流的印記師,結婚,生子。但這些事情值得被記得嗎?我的生命不過是熊熊烈火中的一抹火花,在我逝世後,真的需要有人記得我嗎?從皮膚的印記上看,我的生命和其他人大同小異。
我腦海裡突然閃過一個危險的想法:或許閱讀生命之書並沒有辦法讓你認識一個人。沒有辦法真正認識他們。
我抹去這個念頭,試著將注意力放回奧斯卡身上。
「我不知道,」我說,「我猜我大概還沒認真想過,你呢?」
奧斯卡不可置信地笑,「真的假的?你還沒認真想過?這可是我們人生的目的,你卻還沒認真想過?」
我聳聳肩,換來他不悅地搖頭。我們在館內繼續慢慢地走,試圖讓自己看起來跟一般的訪客沒兩樣。
「我有一個印記,是為了紀念我完成第一年的裝訂師培訓而刻劃的;還有一個是在家庭樹上移除爸爸的印記。」他聳聳肩,「我只希望能活得夠久,所以皮膚上不會只有這些印記……」他的聲音漸漸消失。
「我懂。」我說。
「或許這就是我想要的。」他靜靜說,「有機會能讓爸爸的回憶發光發熱,讓我們兩個都能夠被記得。」
我們看著彼此,就在那一刻,我知道大家在記起我的時候,我會希望他們想到什麼,我想要他們記得我曾為爸爸而戰。奧斯卡和我的眼中都帶著淚水,他的額頭靠著我的額頭。
「會沒事的,萊歐拉。」我抬頭看他,呼吸斷斷續續。
導覽員經過我們身旁,帶著一群人參觀中央的展覽。導覽員朝我們的方向皺眉,我們連忙分開。奧斯卡牽起我的手,快速穿過最近的一扇門,忍著不在經過警衛時笑出聲。我站著不動,等眼睛重新適應環境的黯淡光線;奧斯卡往後退了一步,撞到了某樣東西,發出沉悶的聲響。我們停住不動,當視線逐漸清楚後,我看到奧斯卡的笑容漸漸消失,我們這才發現自己身在何處。我們走進了綠色的門,裝著漂浮空白人的水缸因為被奧斯卡撞到,正微微搖晃著,液體輕輕地起伏,空白人的手肘擠壓著玻璃。我們被包圍了。
四周都是空白人的圖片。這裡是雪白的墓地,埋葬皮膚一片空白的人們,和他們的祕密。有些圖片呈現他們突起的腹部,好似他們隱藏的謊言和邪惡已經將他們填滿,隨時可能爆炸。他們都有一雙看了太多、知道太多,也隱藏太多的眼睛。
看著一張描繪空白人切下印記人的手的圖片—奪走年華、奪走印記、奪走生命,這讓我顫抖。從圖片和文字滲透出的邪惡,讓這間展廳沉重無比。身受空白人折磨的家庭,寫下他們恐怖的經歷。假裝這些都只是童話故事的一部分,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這些都真正發生過,而且不應被遺忘。
他們看起來像骷髏—不對,像幽靈。現在,我們揮之不去的只是他們的回憶。我提醒自己,他們已經不在了,我們很安全;但我覺得自己的恐懼好真實,他們的力量好強大。
我轉向奧斯卡,向他低語:「我好討厭這裡。」
他抓緊我的手,含糊不清地說了一些話,再拍了拍裝著薇瑞蒂寫的紙條的口袋。我不太確定他說了什麼,但聽起來像是:「但我們都有祕密。」
我到家的時間比平常晚一點,媽媽從樓上叫我。「萊歐拉,你回來了嗎?我要下去了!」
媽媽走下樓,腳步聲砰砰作響,手上握著一張紙。她臉上的表情很怪異,混合著害怕和欣慰,「今天收到這封信,靈魂秤重儀式的日子決定了。」
她遞給我那封厚實的官方信件。我讀了信,爸爸的靈魂秤重儀式將在幾個星期後舉行。
沒剩下多少時間了……
第三十一章
我七歲的時候,偷了一塊餅乾。
是從麵包店偷來的—就是賽巴現在工作的麵包店。我知道如果問媽媽的話,她一定會說不行,她每次都不准我吃。餅乾就擺在和我視線一樣高的位置,誘惑、逗弄著我。我等到麵包師背對我,還有媽媽往前靠、請師傅切麵包的時候,把一片上面撒著糖粉的淺色圓餅乾塞進外套口袋。
我那時還沒想好要怎麼吃到餅乾又不被爸媽發現。接下來的一整天,我都在想該怎麼接近掛在門口掛鉤上的外套,而不讓爸媽起疑心。我被罪惡感加上強烈的渴望籠罩,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在半夜偷偷下樓。我摸黑找到外套,在黑暗中冷得發抖,心臟狂跳,同時恐懼被抓到又太期待吃到餅乾。但口袋裡只剩餅乾屑。
第二天早上,我太害怕又羞恥得不敢問媽媽。她發現餅乾了嗎?或者,餅乾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掉出來了。我確定媽媽看得出來我的罪惡感,可能還聞得到我身上散發著甜甜香草味的恐懼,不管走到哪它都跟著我。我一直沒有勇氣問那片餅乾到底去哪了,但我從此再也沒偷過東西。
直到今晚。
或許,這也不算偷。畢竟他是我爸爸,他的故事屬於我。不過在晚上潛入政府大樓,還是讓我覺得極度不妥;薇瑞蒂和奧斯卡也可能會因為我而惹上麻煩。如果被發現,我們可能統統都會被遺忘。但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如果現在不試著拯救爸爸的生命之書,我以後一定會常常猜想自己當初是不是做得到。我在政府大樓和奧斯卡碰面,善良又貼心的薇瑞蒂已經幫我們把大樓內部的地圖和路線都詳細畫好。我們需要從大樓南側的一扇窗戶進入,爬過窗之後,就會到一間上鎖的儲藏室。薇瑞蒂在紙上標示出放在櫃子上的備份鑰匙,她給我的那把鑰匙則是用來通往存放從康納.卓的工場所沒收物品的房間。我不知道她怎麼得到這些資訊的,只希望她夠小心,別讓矛頭指向她。
深夜時分,我準備偷溜出家門;七歲時,摸黑下樓拿偷來的餅乾的那股罪惡和恐懼又湧上來。外面好冷,我只想鑽回被窩,假裝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套上我最深色的衣服時,身上的紋路卻讓我分了心。在微亮的燈光下,胸口的生長紋看起來顏色更深、更參差不齊,肩膀前方還有塊被卡爾指甲弄傷而留下的疤。再這樣下去,我身上的生長紋和傷疤會比印記還多。我繫好軟靴的鞋帶、悄悄走過媽媽的房門,輕輕地關上身後的大門。薇瑞蒂給我的鑰匙沉甸甸地放在口袋裡。
晚上的廣場點滿燈籠,所以奧斯卡和我約在政府大樓的後方,那裡漆黑一片、沒有人會經過。我走過路口要轉彎的時候,差點撞到其中一個垃圾桶。我聽到一陣模糊的笑聲。
「很靈巧嘛。」奧斯卡低聲地說。我在黑暗中朝前凝視,只看到他眼鏡的反光。
「噓!」我慢慢向前,伸出一隻手摸索,擔心被絆倒。直到摸到奧斯卡外套的粗粗觸感,我才往前走向他,他把我拉得更靠近。我們兩個都在發抖,我踮起腳尖在他耳邊低語:「那,我們要爬的窗戶在哪裡?」
奧斯卡對我微笑;在黑暗中只看得到他潔白發亮的牙齒,讓我想到了他的酒窩。大腦,專注點。他用手示意我跟上,帶我沿著大樓側邊往前走。
「我想應該是這扇窗戶。」他在一扇結冰的窗前停下,裡面的燈光剛好夠亮,能讓我們看到薇瑞蒂提到的窗鉤。
「如果我們能用刀或什麼東西滑過這兩扇窗框的中間,我們就可以打開窗鉤、爬進去。」我說。
奧斯卡伸手進包包,拿出一把金屬製的尺。「我才不要在被抓到時帶有武器。」他對我笑,把尺卡在兩扇窗戶的交接處,再用力從窗縫往上推。他在狹小的縫隙中左右移動尺,油漆像雪花般片片掉落。我緊張地環顧四周,窗鉤有幾次幾乎就要掉了,但又啪噠一聲地彈回關上。尺還卡在窗戶的縫隙中,奧斯卡在褲子上來回擦手,繼續嘗試。最後,窗鉤終於開了,奧斯卡把尺拉出來,輕輕推開窗戶,窗戶發出微微的吱嘎聲響、前後不穩地搖擺。奧斯卡推我爬過窗戶,我安穩踩上地板,卻絆到一個水桶,聲音鏗鏘作響。我希望薇瑞蒂說得沒錯,今天晚上不會有任何警衛,要不然我剛剛就會驚動他們了。我挪出位置,好讓奧斯卡爬進來,接著伸手到窗戶旁的櫃子頂端,找到了鑰匙。我試著開門,鑰匙完全吻合,輕輕鬆鬆便打開通向走廊的門,一點聲響也沒有。我鬆了一口氣。自從進來政府大樓後,我的心臟跳得太快,試圖回想薇瑞蒂的指示時,腦中只剩一片空白。我閉上眼睛,深呼吸,仔細端詳又空曠又詭異的走廊,我想起來了。
「薇瑞蒂在地圖上說,先右轉,到底的時候再左轉,左手邊的第三扇門。」奧斯卡對我點頭,斜揹起包包,我們安靜又緩慢地沿著走廊走。厚重木門和亮光漆的味道,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學校裡面;走廊上昏暗的燈光讓所有東西都染上了一層綠色。
我不斷往後看,覺得一定會有人來抓我們。
但一切都跟薇瑞蒂說得一樣,似乎太過容易了。門雖然關上,卻沒有上鎖。奧斯卡推開門時,門嘎吱作響,房間裡沒有窗戶—以避免溫度變化太大。一個個箱子整齊地推放在小房間裡。
「看來他們還沒開始清點證據。」我們小心地移開一個個箱子,「記好箱子原本的位子,我們最後得恢復原樣。」奧斯卡點點頭,打開離他最近的箱子,裡面的東西比我想得還要多。
「這些都是你爸爸……割除的皮膚?」我低聲地問。
「大多數是。」奧斯卡靜靜地回答。
「他為什麼要全部留著?」過去幾天,我一直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不把證據丟掉或是燒掉之類的?」
奧斯卡斜眼看著我,「萊歐拉,這些依然是人們的皮膚,」他在箱子裡翻找,動作十分小心翼翼,「你不能就這樣丟掉,這是他們的一部分。」
我思考著他說的話,他說得對,就算爸爸的印記如此令人反感,但如果印記真的永遠消失了,我會更加心碎。皮膚太重要了。奧斯卡走到房間的另一端,我們沉默地尋找,只剩呼吸、翻閱資料夾、紙張和皮膚的聲音。
「找到了!」奧斯卡說,從箱子裡拿出一個資料夾,輕輕地拍了拍,「這是他的名字,對嗎?」他把資料夾拿給我,我看到爸爸的名字工整地寫在封面上:喬爾.弗林特。我慢慢打開資料夾,大頭針將一小片皮膚小心又仔細地固定在一張厚紙片上。我拿起那片皮膚,像是它有生命一樣。我顫抖地深吸一口氣,很高興看到爸爸,但心情跟我們上次看到他生命之書的時候大不相同。當時的那股期待和欣喜,已經被再次看到烏鴉印記的緊張和恐懼所取代。看得出來頭皮上的頭髮已被剃掉,但還剩下一些細小的頭髮;薇瑞蒂的媽媽幫他縫合的傷口所留下的疤痕,現在是一條蒼白的線—而烏鴉印記就在那裡,黑色羽毛的翅膀清晰可見。
奧斯卡跨過打開的各個箱子,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讓我帶走嗎?」
他伸出手來,我把裝著爸爸皮膚的資料夾給他,我們說好由他保管爸爸的皮膚。奧斯卡說他們已經去他家搜了好多次,他很清楚哪些地方絕對不會被搜查到。
「萊歐拉,他值得被記住。」奧斯卡把資料夾塞進包包,「我們把這些箱子放回原位吧?」我點點頭,開始幫他一起收箱子。
我們一語不發地收拾,一切很快物歸原位,和我們剛進來時一模一樣。我相信不會有人懷疑我們到過這裡。
除非有人知道爸爸的印記。邪惡的聲音在我耳邊說,我不理它。
「好了嗎?」我轉向奧斯卡,他正關上包包。同時,我看到包包裡還有一個資料夾。我很確定他在包包裡放了其他東西,奧斯卡發現我在看他。
「這不在計畫之中。」我的聲音在一片寂靜中聽起來很大聲。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我伸手想拿他的包包,他用力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強硬地制止我。所有的溫柔都不見了,他的眼神冰冷。我正想爭辯,卻聽到門被小心翼翼關上的聲音—顯然有人不想被發現。
我們一句話都沒說,迅速溜出房間,半跑半走地穿過一片漆黑的走廊。當我們抵達儲藏室時,我把門鎖上,看到窗鉤還開著,心裡鬆了一口氣。奧斯卡打開窗戶,讓我踩在他手上,就在我抓著窗臺的同時,我們聽到儲藏室門把轉動的聲音。
我們僵止不動,我閉上雙眼—這是源自小時候的直覺反應:想要讓自己消失不見。我的心跳加劇,覺得自己就要昏倒了。
「快爬!」奧斯卡催促。我用力把自己扔出窗外,自己都不知道原來我力氣可以這麼大。我絆了一跤、膝蓋撞到地上。奧斯卡在我身旁輕盈落地、關上窗戶,並俐落地重新拴好。
我們沿著小巷跑,到廣場的時候,奧斯卡停了下來,抓住我的手臂,「如果有人在政府大樓裡,他們會看見我們在廣場奔跑。」
「那你說要怎麼辦?」我無助地問。
「脫下帽子,試著正常呼吸,跟我一起走。假裝我們是在月光下散步。」奧斯卡脫下他的帽子、弄亂頭髮、解開外套,一派輕鬆地往前走。他轉身向我伸出一隻手,我搖搖頭,無法相信他居然可以如此冷靜,然後牽住他的手。
當我們走到廣場中央時,我往後瞄了政府大樓一眼。一個蒼白的身影站在大樓正面的一扇窗戶前,盯著我們看。看著他寬闊的輪廓,我想我認出他是誰。
我們被他追捕。
但有些獵物會逃跑,不是嗎?
我到工作室的時候,歐貝爾已經在了,看得出來他已經待上好一段時間。他看起來很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這睡了一晚。我很訝異他看到我的時候,臉上浮現鬆一口氣的表情,我以為自己不會被歡迎;說真的,我原本以為自己必須努力贏回這份工作。
「你不知道看到你我有多開心。」歐貝爾很快站起來,從我手中接過外套,幫我掛好,「我知道昨天一團糟,我說的一些話……」
「我們說的一些話。」我懊惱地說。
「萊歐拉,我們現在就同意各持己見吧。不可否認的是,你是一位非常優秀的印記師,不管我們抱持的信念是否相同,我都想要繼續培訓你。你覺得怎麼樣?」
我猶豫一下,然後點頭,腦子裡千頭萬緒,根本做不出決定。現在,我就先繼續做自己喜歡的事。
「太好了!我今天很需要你。」歐貝爾說,遞給我一封信,「昨天發生卡爾的事情之後,官員要過來調查。這小子留了一堆爛攤子讓我收拾。」他對我無奈地笑。
我很快掃過信件,信裡提到一名叫傑克.明饒的人今天會來工作室。信上說,他會幫助歐貝爾準備需要的文件,記錄卡爾在沒有歐貝爾監督下,幫客人刻劃印記的過程。
「動作真快。」我皺起眉頭。
「對啊,我昨晚才舉報。要嘛是他們真的很閒,要嘛就是真的非常想來調查我。」歐貝爾嚥了一口口水,我能感受到他內心的緊張。
我們核對彼此對事發經過的描述,確定故事吻合。歐貝爾開店時,我負責打掃、整頓工作室,讓一切就緒;因為不確定政府的調查員何時會來,我們決定不如就照常工作。
工作室來了幾個人,我替一位女士在接近週末的時候預約諮詢,我坐在接待區,在預約簿上填寫資料的時候,聽到門鈴叮咚作響。我抬頭看,一位穿著政府高官正式黑色制服的高大男人,正任憑身後的門重重關上。
「傑克.明饒。」他說,「我找歐貝爾.維特沃斯。」
他剃了個光頭、皮膚晒得黝黑,高高站在我面前,他肯定比歐貝爾還高大。剃光的頭上有著細緻的印記,我瞬間解讀了瞄到的印記:都和獵食動物有關,意義清晰明瞭。他的頭皮上刻劃著一群鬣狗,我讀到那是為了慶祝成功驅逐空白人而刻劃的印記,所有的暴力和殘酷都還留在印記上。我讀到他對血腥的喜愛,不禁打起冷顫,但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平靜鎮定。
「明饒先生,請坐,我去請歐貝爾過來。您要喝點什麼嗎?」我的聲音太高亢了,他一定聽出我有多緊張。
傑克.明饒閉上眼睛、搖搖頭,當他睜開雙眼的時候,露出有點得意的笑,「請維特沃斯先生過來就行了。」
我才要離開,歐貝爾就剛好走進工作室,用抹布擦著雙手。他伸出一隻手來和明饒打招呼,明饒握了他的手,因為歐貝爾還濕濕的手而皺眉。
「維特沃斯先生,我們就開始吧?」他一邊在褲子上擦手,一邊看著歐貝爾,毫不掩飾他的敵意,「有人最近很調皮,對吧?我聽說是未在你的監督之下,擅自刻劃印記?」他放縱地咯咯笑,「我相信那位當事人很有野心。我得承認,我欣賞這樣的特質。」
歐貝爾要我去休息室練習畫畫,但明饒制止了他。
「我想跟你們兩人說話。弗林特小姐,請坐。」
他要我們告訴他事情發生的經過,且由我先開始。我開始說著事情始末,一邊分神注意傑克.明饒,一邊又看著歐貝爾,擔心說錯話會害他遭殃。這一次的來訪只是為了卡爾的事嗎?
明饒一直在做筆記,並問一些小問題好釐清細節。過程都非常有禮,但我感覺他是在等我說溜嘴。他的印記炯炯閃耀、栩栩如生,我根本沒辦法好好思考;他也問了歐貝爾相同的問題,質問他為什麼離開我和卡爾、逼問他在開除卡爾的時候,對他說的話等種種細節。他一言不發地記錄,幾分鐘後,遞給我一張紙。
「麻煩你看過一遍。若是同意我的紀錄,就請簽名。」重讀事件的經過,就好像再經歷一次昨天一樣,我心不在焉地揉著頭。
「看起來可以。」我說,把紙推還給桌子對面的他。
「可以還是正確,弗林特小姐?這兩者可不一樣。」他說的時候雖然帶著微笑,但我覺得那是惡魔才會有的微笑。
「正確無誤,跟我說的一樣,也是事實。」他遞給我一支筆;簽好名後,我很快瞄了歐貝爾一眼,確定自己做的事沒錯。
「謝謝。」明饒把筆交給歐貝爾,他在我的簽名上方簽下自己的名字。明饒把我們的供詞放進他的袋子裡,開始環顧四周。他往後靠上椅背,伸展一下身體,「弗林特小姐,你覺得這裡怎麼樣?目前為止一切都順利嗎?」
「一切都很好!當然,除了那個以外,」我以下巴示意他的袋子和裡面的供詞,「其他我都很喜歡。」
「那維特沃斯先生呢?」他看著歐貝爾,「你對他滿意嗎?他有沒有好好訓練你?」
歐貝爾就站在旁邊,我卻要回答這樣的問題;雖然覺得很怪,但我試著表現鎮定,「他非常好,我在這裡很開心。」我不要再說更多話了。
「很高興聽到你這麼說。維特沃斯先生,不如你帶我參觀一下吧?」明饒拿起袋子,和歐貝爾走到接待區,邊走邊聊天。我讓他們兩個單獨聊,正想自己回休息室的時候,卻聽到明饒的聲音愈來愈清楚。我抬頭看,發現他正往回走,一邊解開背心的扣子,一邊走往歐貝爾的工作區。
明饒放鬆地坐在椅子上,好像那是他自己的椅子一樣。他把袋子放在地上,朝我這邊看。
「我看你們現在都不忙,所以你的導師剛剛說可以幫我刻劃印記,你說是吧,維特沃斯?」我看見歐貝爾整個人都僵掉了,很顯然這不是一個疑問句。明饒解開一顆顆的釦子、脫去背心和短袖汗衫。隨著衣服被脫去,我看見他身上的印記;那是以前解讀印記時,從來沒有經歷過的感受。他印記裡的暴力和憤怒十分猛烈,讓人無法承受。我想逃跑、我想大哭、我想告訴他,我可以看穿他,但我只是保持沉默,看著他和歐貝爾之間的詭譎互動。
歐貝爾打破沉默,「明饒先生,一般我們不會這麼做。通常,我們會先和您諮詢,再請您回來刻劃印記;但如果是您的話,我們當然很樂意,這是我們的榮幸。」歐貝爾看著我,「萊歐拉,明饒先生想要……一隻貓頭鷹。對嗎,明饒先生?」
明饒魯莽地點點頭,他的肩膀魁梧,「對,一隻大鵰鴞。」他附和。我知道他在講哪一種貓頭鷹,歐貝爾叫我練習畫了千百種生物。
歐貝爾開始問他通常詢問客人的制式問題,就跟平常一樣冷靜。我離開去準備工具,當我帶著裝滿工具的托盤回來時,聽見歐貝爾和明饒對話的結尾。
「……是的,傑出的獵食者,視覺和聽覺都無以倫比。獵物以為牠們已經跑得夠快夠遠,隱密地藏身在貓頭鷹看不見的地方,結果牠咻地俯衝而下,獵物都還沒聽到牠的聲音,就已經被抓到了,無法阻擋、令人生畏。」
歐貝爾吞了一口口水,轉向我,「萊歐拉,謝謝,接下來的就交給我。」
我轉身要離開,明饒卻在這時說:「我們何不把這當作一個訓練的機會?我想請萊歐拉幫我刻劃印記。」
我的震驚顯露無遺。
「你之前刻劃過印記了,對嗎?」我虛弱地點點頭。「那就沒問題了,至少維特沃斯先生會在一旁協助你。我想把印記刻劃在這裡,在我的肩膀上方,牠可以看守我的家人。」
我用顫抖的雙手擦拭工作檯,仔細消毒每個地方,再將工具依照我習慣的順序擺放好。我向明饒說明即將使用的器具都乾淨嶄新,並詢問他想要什麼樣子的貓頭鷹。我給他看一些我畫的草圖,心裡很感謝歐貝爾叫我練習畫這麼多圖。我開始清潔明饒的皮膚、剃掉細小的黑色汗毛。每碰到他的皮膚一次,他的印記便對我咆哮一次;這和替上次那位女士刻劃印記時,所感受到的愉悅電流完全不同,現在的感覺像是有一群謀殺犯大聲渴求鮮血。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夠再和他多相處一秒,更別說得花上好幾個小時完成他的印記。為了拖延時間,我給他看轉印紙上的圖案,以確認我已完全了解他想要的印記。我對歐貝爾眨眼;很少見地,他看起來很擔心,但當他注意到我時,他用微笑表示肯定。
「妹妹,你沒問題的。你天生就是印記師,記得嗎?」他輕聲說。
我把畫好的圖騰轉印到明饒的皮膚上,讓圖案留下清楚的輪廓痕跡。每一次接觸到他的皮膚,我都要鼓起勇氣、試著不讓他印記中的暴戾之氣干擾我。我用鏡子反射圖騰的線條給明饒看,他點點頭。
開始刻劃後,我聽著工具熟悉的聲響,任由機器引領我的思緒。但只要我一開始覺得安全自在的時候,明饒就會開口說話,就好像在快要睡著的時候,被人一把從床上抓起來一樣,每一次我都因為被打斷而驚嚇不已。這讓我更沒辦法專注聽他說話,以及構思我的回答。
「萊歐拉,你刻劃的第一個印記是什麼?」他問。
「是一片樹葉。」我渙散地回應。
「樹葉?刻在哪裡?」我正在刻劃貓頭鷹的爪子,心裡想著那位心碎的女士,於是脫口而出:「在她的家庭樹下,她的寶寶過世了。」
我發現他的肌肉緊繃了起來,這已足夠讓我清醒一點,提起警戒。
「喔,她想要一個紀念寶寶的印記?」
我還記得那位女士說的話,彷彿她正說著那些字句:「如果他在刻劃出生印記之前就過世的話,我知道自己應該要忘記他……他才兩天大。」接著,我想起歐貝爾的警告。我不能讓他失望,我得想辦法讓明饒不再發問。
我給自己一點時間深呼吸,故意在明饒一塊已經紅腫的皮膚上,隨意拖著針頭。我聽到他倒抽一口氣。
「啊,對不起!」我說,「我需要更專心一點,你知道我還在學。顯然我還沒辦法一邊聊天一邊刻劃。」
歐貝爾注意到了,他在明饒沒在看的時候,迅速笑了一下。那之後,唯一的聲音就是刺青機器的聲響、明饒忍受疼痛時發出的喘氣聲,還有他的印記張狂對我嘶吼祕密的喊叫聲。
在輪廓終於完成之後,明饒的皮膚已經因為太過紅腫,而沒辦法再繼續刻劃印記。
「明饒先生,我想我們得等傷口稍微復原一點,才能繼續進行。」我對他說,幫他擦拭血跡,並包紮我在他肩膀上刻劃的美麗又駭人的印記。我迫不及待他趕快離開,「印記很好看,」我邊說邊脫手套,「看起來就像貓頭鷹準備好要俯衝而下、捕抓獵物。」我用盡全力讓自己聽起來輕鬆隨意,「不曉得大鵰鴞都抓什麼樣的獵物。」
「任何微小又不重要的生物,我想牠幾乎都抓。」明饒說,「不過,牠們捕抓的其中一種獵物,我認為非常特別,顯示了貓頭鷹有多勇敢和強壯。」
「喔,是嗎?」我爽朗地問,「是什麼?」
我的手忙著整理工作檯、拆除椅子上的塑膠套。
「烏鴉。大鵰鴞獵捕烏鴉。深夜時分,當烏鴉棲息、以為安全無虞的時候,貓頭鷹就會來抓牠們。」
我把塑膠套丟掉,擦了擦雙手,把襯衫拿給明饒,確保他在穿上襯衫時,不拉扯到包裹傷口的繃帶,同時試著對他彬彬有禮地微笑。他也是獵食者。
我在幫忙的時候,他抓住我的手,皺眉看著我仍在痊癒的傷口,「割到手了?你可得小心點,弗林特小姐。」
他放開我的手,我一句話也沒說。他沒有預約下一次的時間,但說會再找時間過來。他正要離開時,突然停下腳步、轉向我,好像忽然想起什麼事似地從口袋拿出某樣東西。他把東西拿到我面前。
「有沒有看過像這樣的東西?」我看著那張皺巴巴的紙,嚥下一口口水—那是羽毛的圖騰,跟關店後來訪的那位女士遞給歐貝爾的紙條一模一樣。我搖搖頭。
「沒有,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我輕描淡寫地說,努力讓臉不要漲紅。他把紙張收回口袋,沉默地盯著我看。我目送明饒走出門,看到他忘記肩上的印記、逕自把背帶掛上肩膀,因疼痛而抽動時,那一刻,我感到非常開心。
他頭也不回地向前走。當他完全走出視線時,我關門,並上了鎖。我回到休息室去,一遍又一遍地刷洗自己的手,直到雙手發紅刺痛。歐貝爾把手放在我的肩上,把水龍頭關上,我沒有阻止他。我擦乾顫抖的雙手。
「歐貝爾,我很害怕。」
而最糟糕的是,歐貝爾也回說:「我也是,萊歐拉,我也是。」
第三十章
那天下午,歐貝爾正跟客人在一起,而我安靜工作的時候,工作室的後門傳來一陣急促的敲門聲。我開門,發現是薇瑞蒂。她上氣不接下氣,雙眼瞪大、充滿恐懼。我走到門外,站在街道上。
「他們找到了。」薇瑞蒂低聲地說,「所有康納.卓隱藏的證據,都藏在他工場裡的一個祕密空間內。現在是休息時間,我不能離開辦公室太久。但是,萊歐拉,」她停頓一下,調整呼吸,「他們沒收了所有東西,證據都在政府大樓裡,明天就要被逐一歸檔記錄。沒剩多少時間了,你得在他們之前找到你爸爸的皮膚。」我點點頭。薇瑞蒂給我一張對折的紙條和一把鑰匙,「這會幫得上忙,你今晚就要行動。」她瞪大雙眼,眼神十分害怕,「千萬要小心,萊歐拉,這風險太大了。」
我還沒來得及道別或道謝,她就離開了。
我祈禱奧斯卡有收到我留的訊息,我祈禱他會赴約。我提議約在博物館,因為裡面既溫暖又不收費,加上又是公共場所,所以人多且忙碌,沒人會懷疑我們在密謀什麼不宜的事。我根本沒想到會需要策畫潛入政府大樓,但反正這裡是個絕佳的討論地點。
我看到奧斯卡在接待區等我的時候,整個人如釋重負地差點哭出來。我平復情緒,兩人一言不發地走過存放歷代領導者生命之書的中庭;偶爾停下腳步,欣賞某件藝術品或考古文物,但大多時間我們就這麼走著。
我邊走邊把薇瑞蒂給我的紙張遞給奧斯卡,那是政府大樓的地圖,上面指示著如何前往存放被沒收證據的地方。我低聲告訴奧斯卡薇瑞蒂跟我說的事,他沉重地點點頭,沒有我想像得那麼震驚,他肯定知道這一刻總有一天會來臨,或至少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他把紙塞進外套口袋,我們沉默地盯著玻璃看了一會。他轉向我,非常溫柔地把我的頭髮從眼前撥開,我額頭上的瘀青露了出來。看到我頭上又紅又紫的瘀青,他皺起眉頭。
「你還好嗎?」他問我,聲音低沉,「我每次看到你,你就多一道傷痕。」他抓起我的手,仔細看著結痂的傷口。我突然意識到他的手有多溫暖厚實;他的手指劃過我的年齡印記時,我能感受到他粗糙的皮膚。
「你需不需要保鑣?」
我笑了出來,把手抽開,「你想當我的保鑣嗎?」
「裝訂師的體格可是很出名的。」他也笑起來,而我繼續對著他傻笑。
「萊歐拉,你希望大家記起你的時候,會想到什麼?」他突然問,「你一定會刻劃在皮膚上的,會是什麼樣的印記?」
我微微皺眉,這個問題讓我措手不及,感覺好奇怪,還有點嚇人;但當我抬頭看他的臉時,我知道他是認真的。我閉上眼睛思考:我的第一個印記會是什麼樣子?我希望自己的孩子在我的印記中讀到什麼?大家想起我的時候,我想要他們記得什麼?什麼東西重要到能夠永久流傳?
我什麼都想不到。
我想著所有想做的事:當一流的印記師,結婚,生子。但這些事情值得被記得嗎?我的生命不過是熊熊烈火中的一抹火花,在我逝世後,真的需要有人記得我嗎?從皮膚的印記上看,我的生命和其他人大同小異。
我腦海裡突然閃過一個危險的想法:或許閱讀生命之書並沒有辦法讓你認識一個人。沒有辦法真正認識他們。
我抹去這個念頭,試著將注意力放回奧斯卡身上。
「我不知道,」我說,「我猜我大概還沒認真想過,你呢?」
奧斯卡不可置信地笑,「真的假的?你還沒認真想過?這可是我們人生的目的,你卻還沒認真想過?」
我聳聳肩,換來他不悅地搖頭。我們在館內繼續慢慢地走,試圖讓自己看起來跟一般的訪客沒兩樣。
「我有一個印記,是為了紀念我完成第一年的裝訂師培訓而刻劃的;還有一個是在家庭樹上移除爸爸的印記。」他聳聳肩,「我只希望能活得夠久,所以皮膚上不會只有這些印記……」他的聲音漸漸消失。
「我懂。」我說。
「或許這就是我想要的。」他靜靜說,「有機會能讓爸爸的回憶發光發熱,讓我們兩個都能夠被記得。」
我們看著彼此,就在那一刻,我知道大家在記起我的時候,我會希望他們想到什麼,我想要他們記得我曾為爸爸而戰。奧斯卡和我的眼中都帶著淚水,他的額頭靠著我的額頭。
「會沒事的,萊歐拉。」我抬頭看他,呼吸斷斷續續。
導覽員經過我們身旁,帶著一群人參觀中央的展覽。導覽員朝我們的方向皺眉,我們連忙分開。奧斯卡牽起我的手,快速穿過最近的一扇門,忍著不在經過警衛時笑出聲。我站著不動,等眼睛重新適應環境的黯淡光線;奧斯卡往後退了一步,撞到了某樣東西,發出沉悶的聲響。我們停住不動,當視線逐漸清楚後,我看到奧斯卡的笑容漸漸消失,我們這才發現自己身在何處。我們走進了綠色的門,裝著漂浮空白人的水缸因為被奧斯卡撞到,正微微搖晃著,液體輕輕地起伏,空白人的手肘擠壓著玻璃。我們被包圍了。
四周都是空白人的圖片。這裡是雪白的墓地,埋葬皮膚一片空白的人們,和他們的祕密。有些圖片呈現他們突起的腹部,好似他們隱藏的謊言和邪惡已經將他們填滿,隨時可能爆炸。他們都有一雙看了太多、知道太多,也隱藏太多的眼睛。
看著一張描繪空白人切下印記人的手的圖片—奪走年華、奪走印記、奪走生命,這讓我顫抖。從圖片和文字滲透出的邪惡,讓這間展廳沉重無比。身受空白人折磨的家庭,寫下他們恐怖的經歷。假裝這些都只是童話故事的一部分,是再簡單不過的事;但這些都真正發生過,而且不應被遺忘。
他們看起來像骷髏—不對,像幽靈。現在,我們揮之不去的只是他們的回憶。我提醒自己,他們已經不在了,我們很安全;但我覺得自己的恐懼好真實,他們的力量好強大。
我轉向奧斯卡,向他低語:「我好討厭這裡。」
他抓緊我的手,含糊不清地說了一些話,再拍了拍裝著薇瑞蒂寫的紙條的口袋。我不太確定他說了什麼,但聽起來像是:「但我們都有祕密。」
我到家的時間比平常晚一點,媽媽從樓上叫我。「萊歐拉,你回來了嗎?我要下去了!」
媽媽走下樓,腳步聲砰砰作響,手上握著一張紙。她臉上的表情很怪異,混合著害怕和欣慰,「今天收到這封信,靈魂秤重儀式的日子決定了。」
她遞給我那封厚實的官方信件。我讀了信,爸爸的靈魂秤重儀式將在幾個星期後舉行。
沒剩下多少時間了……
第三十一章
我七歲的時候,偷了一塊餅乾。
是從麵包店偷來的—就是賽巴現在工作的麵包店。我知道如果問媽媽的話,她一定會說不行,她每次都不准我吃。餅乾就擺在和我視線一樣高的位置,誘惑、逗弄著我。我等到麵包師背對我,還有媽媽往前靠、請師傅切麵包的時候,把一片上面撒著糖粉的淺色圓餅乾塞進外套口袋。
我那時還沒想好要怎麼吃到餅乾又不被爸媽發現。接下來的一整天,我都在想該怎麼接近掛在門口掛鉤上的外套,而不讓爸媽起疑心。我被罪惡感加上強烈的渴望籠罩,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在半夜偷偷下樓。我摸黑找到外套,在黑暗中冷得發抖,心臟狂跳,同時恐懼被抓到又太期待吃到餅乾。但口袋裡只剩餅乾屑。
第二天早上,我太害怕又羞恥得不敢問媽媽。她發現餅乾了嗎?或者,餅乾可能在回家的路上掉出來了。我確定媽媽看得出來我的罪惡感,可能還聞得到我身上散發著甜甜香草味的恐懼,不管走到哪它都跟著我。我一直沒有勇氣問那片餅乾到底去哪了,但我從此再也沒偷過東西。
直到今晚。
或許,這也不算偷。畢竟他是我爸爸,他的故事屬於我。不過在晚上潛入政府大樓,還是讓我覺得極度不妥;薇瑞蒂和奧斯卡也可能會因為我而惹上麻煩。如果被發現,我們可能統統都會被遺忘。但我只有這條路可以走了,如果現在不試著拯救爸爸的生命之書,我以後一定會常常猜想自己當初是不是做得到。我在政府大樓和奧斯卡碰面,善良又貼心的薇瑞蒂已經幫我們把大樓內部的地圖和路線都詳細畫好。我們需要從大樓南側的一扇窗戶進入,爬過窗之後,就會到一間上鎖的儲藏室。薇瑞蒂在紙上標示出放在櫃子上的備份鑰匙,她給我的那把鑰匙則是用來通往存放從康納.卓的工場所沒收物品的房間。我不知道她怎麼得到這些資訊的,只希望她夠小心,別讓矛頭指向她。
深夜時分,我準備偷溜出家門;七歲時,摸黑下樓拿偷來的餅乾的那股罪惡和恐懼又湧上來。外面好冷,我只想鑽回被窩,假裝這一切都不是真的。套上我最深色的衣服時,身上的紋路卻讓我分了心。在微亮的燈光下,胸口的生長紋看起來顏色更深、更參差不齊,肩膀前方還有塊被卡爾指甲弄傷而留下的疤。再這樣下去,我身上的生長紋和傷疤會比印記還多。我繫好軟靴的鞋帶、悄悄走過媽媽的房門,輕輕地關上身後的大門。薇瑞蒂給我的鑰匙沉甸甸地放在口袋裡。
晚上的廣場點滿燈籠,所以奧斯卡和我約在政府大樓的後方,那裡漆黑一片、沒有人會經過。我走過路口要轉彎的時候,差點撞到其中一個垃圾桶。我聽到一陣模糊的笑聲。
「很靈巧嘛。」奧斯卡低聲地說。我在黑暗中朝前凝視,只看到他眼鏡的反光。
「噓!」我慢慢向前,伸出一隻手摸索,擔心被絆倒。直到摸到奧斯卡外套的粗粗觸感,我才往前走向他,他把我拉得更靠近。我們兩個都在發抖,我踮起腳尖在他耳邊低語:「那,我們要爬的窗戶在哪裡?」
奧斯卡對我微笑;在黑暗中只看得到他潔白發亮的牙齒,讓我想到了他的酒窩。大腦,專注點。他用手示意我跟上,帶我沿著大樓側邊往前走。
「我想應該是這扇窗戶。」他在一扇結冰的窗前停下,裡面的燈光剛好夠亮,能讓我們看到薇瑞蒂提到的窗鉤。
「如果我們能用刀或什麼東西滑過這兩扇窗框的中間,我們就可以打開窗鉤、爬進去。」我說。
奧斯卡伸手進包包,拿出一把金屬製的尺。「我才不要在被抓到時帶有武器。」他對我笑,把尺卡在兩扇窗戶的交接處,再用力從窗縫往上推。他在狹小的縫隙中左右移動尺,油漆像雪花般片片掉落。我緊張地環顧四周,窗鉤有幾次幾乎就要掉了,但又啪噠一聲地彈回關上。尺還卡在窗戶的縫隙中,奧斯卡在褲子上來回擦手,繼續嘗試。最後,窗鉤終於開了,奧斯卡把尺拉出來,輕輕推開窗戶,窗戶發出微微的吱嘎聲響、前後不穩地搖擺。奧斯卡推我爬過窗戶,我安穩踩上地板,卻絆到一個水桶,聲音鏗鏘作響。我希望薇瑞蒂說得沒錯,今天晚上不會有任何警衛,要不然我剛剛就會驚動他們了。我挪出位置,好讓奧斯卡爬進來,接著伸手到窗戶旁的櫃子頂端,找到了鑰匙。我試著開門,鑰匙完全吻合,輕輕鬆鬆便打開通向走廊的門,一點聲響也沒有。我鬆了一口氣。自從進來政府大樓後,我的心臟跳得太快,試圖回想薇瑞蒂的指示時,腦中只剩一片空白。我閉上眼睛,深呼吸,仔細端詳又空曠又詭異的走廊,我想起來了。
「薇瑞蒂在地圖上說,先右轉,到底的時候再左轉,左手邊的第三扇門。」奧斯卡對我點頭,斜揹起包包,我們安靜又緩慢地沿著走廊走。厚重木門和亮光漆的味道,讓我覺得自己好像在學校裡面;走廊上昏暗的燈光讓所有東西都染上了一層綠色。
我不斷往後看,覺得一定會有人來抓我們。
但一切都跟薇瑞蒂說得一樣,似乎太過容易了。門雖然關上,卻沒有上鎖。奧斯卡推開門時,門嘎吱作響,房間裡沒有窗戶—以避免溫度變化太大。一個個箱子整齊地推放在小房間裡。
「看來他們還沒開始清點證據。」我們小心地移開一個個箱子,「記好箱子原本的位子,我們最後得恢復原樣。」奧斯卡點點頭,打開離他最近的箱子,裡面的東西比我想得還要多。
「這些都是你爸爸……割除的皮膚?」我低聲地問。
「大多數是。」奧斯卡靜靜地回答。
「他為什麼要全部留著?」過去幾天,我一直都在想這個問題,「為什麼不把證據丟掉或是燒掉之類的?」
奧斯卡斜眼看著我,「萊歐拉,這些依然是人們的皮膚,」他在箱子裡翻找,動作十分小心翼翼,「你不能就這樣丟掉,這是他們的一部分。」
我思考著他說的話,他說得對,就算爸爸的印記如此令人反感,但如果印記真的永遠消失了,我會更加心碎。皮膚太重要了。奧斯卡走到房間的另一端,我們沉默地尋找,只剩呼吸、翻閱資料夾、紙張和皮膚的聲音。
「找到了!」奧斯卡說,從箱子裡拿出一個資料夾,輕輕地拍了拍,「這是他的名字,對嗎?」他把資料夾拿給我,我看到爸爸的名字工整地寫在封面上:喬爾.弗林特。我慢慢打開資料夾,大頭針將一小片皮膚小心又仔細地固定在一張厚紙片上。我拿起那片皮膚,像是它有生命一樣。我顫抖地深吸一口氣,很高興看到爸爸,但心情跟我們上次看到他生命之書的時候大不相同。當時的那股期待和欣喜,已經被再次看到烏鴉印記的緊張和恐懼所取代。看得出來頭皮上的頭髮已被剃掉,但還剩下一些細小的頭髮;薇瑞蒂的媽媽幫他縫合的傷口所留下的疤痕,現在是一條蒼白的線—而烏鴉印記就在那裡,黑色羽毛的翅膀清晰可見。
奧斯卡跨過打開的各個箱子,一隻手放在我的肩膀上,「讓我帶走嗎?」
他伸出手來,我把裝著爸爸皮膚的資料夾給他,我們說好由他保管爸爸的皮膚。奧斯卡說他們已經去他家搜了好多次,他很清楚哪些地方絕對不會被搜查到。
「萊歐拉,他值得被記住。」奧斯卡把資料夾塞進包包,「我們把這些箱子放回原位吧?」我點點頭,開始幫他一起收箱子。
我們一語不發地收拾,一切很快物歸原位,和我們剛進來時一模一樣。我相信不會有人懷疑我們到過這裡。
除非有人知道爸爸的印記。邪惡的聲音在我耳邊說,我不理它。
「好了嗎?」我轉向奧斯卡,他正關上包包。同時,我看到包包裡還有一個資料夾。我很確定他在包包裡放了其他東西,奧斯卡發現我在看他。
「這不在計畫之中。」我的聲音在一片寂靜中聽起來很大聲。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東西。」
我伸手想拿他的包包,他用力地一把抓住我的手臂,強硬地制止我。所有的溫柔都不見了,他的眼神冰冷。我正想爭辯,卻聽到門被小心翼翼關上的聲音—顯然有人不想被發現。
我們一句話都沒說,迅速溜出房間,半跑半走地穿過一片漆黑的走廊。當我們抵達儲藏室時,我把門鎖上,看到窗鉤還開著,心裡鬆了一口氣。奧斯卡打開窗戶,讓我踩在他手上,就在我抓著窗臺的同時,我們聽到儲藏室門把轉動的聲音。
我們僵止不動,我閉上雙眼—這是源自小時候的直覺反應:想要讓自己消失不見。我的心跳加劇,覺得自己就要昏倒了。
「快爬!」奧斯卡催促。我用力把自己扔出窗外,自己都不知道原來我力氣可以這麼大。我絆了一跤、膝蓋撞到地上。奧斯卡在我身旁輕盈落地、關上窗戶,並俐落地重新拴好。
我們沿著小巷跑,到廣場的時候,奧斯卡停了下來,抓住我的手臂,「如果有人在政府大樓裡,他們會看見我們在廣場奔跑。」
「那你說要怎麼辦?」我無助地問。
「脫下帽子,試著正常呼吸,跟我一起走。假裝我們是在月光下散步。」奧斯卡脫下他的帽子、弄亂頭髮、解開外套,一派輕鬆地往前走。他轉身向我伸出一隻手,我搖搖頭,無法相信他居然可以如此冷靜,然後牽住他的手。
當我們走到廣場中央時,我往後瞄了政府大樓一眼。一個蒼白的身影站在大樓正面的一扇窗戶前,盯著我們看。看著他寬闊的輪廓,我想我認出他是誰。
我們被他追捕。
但有些獵物會逃跑,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