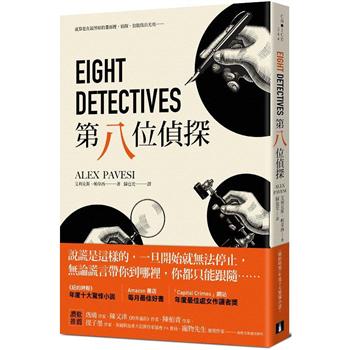1 一九三○,西班牙
幾無特色的白色起居室裡,兩名嫌疑犯坐在不成套的座椅上,正等待著某事發生。在他們的座位之間有一道拱門,通往狹窄無窗的樓梯間──一個存在感似乎主宰這空間的陰暗凹處,彷彿像一座大得不成比例的壁爐。樓梯在中途轉彎,上層遭遮蔽,令人感覺往上除了黑暗,便再無其他。
「在這乾等真像置身地獄。」梅根坐在拱門右側。「話說回來,西班牙人午睡一般都睡多久啊?」
她起身走到窗前。外面的西班牙鄉間是一片朦朧的橘色,在這熱度下看似不宜居住。
「一兩個小時,不過他剛剛喝酒喝個不停。」亨利側坐在椅子上,雙腿懸在一邊扶手,一把吉他擱在腿上。「我了解邦尼,他會一路睡到晚餐時間。」
梅根走到酒櫃前檢視裡面的酒瓶,小心地一一轉動,直到所有酒標都朝外。亨利將口中的菸拿到右眼前,假裝正拿著假的望遠鏡看她。「妳又在用鞋子呼吸了。」
她大半個下午都不停地在來回踱步。這個會客室的白地磚和擦得乾乾淨淨的每個表面都讓她想起某醫生的候診室──他們彷彿身在家鄉的某紅磚醫院,而非崎嶇紅丘頂的一座古怪西班牙別墅。「如果我是在用鞋子呼吸,」她咕噥,「那你就是在用嘴巴走路。」
數小時前,他們在鄰近村落的一家小酒館用午餐,那裡距離邦尼家只需穿過三十分鐘的樹林。用餐結束時邦尼站起,他們雙雙注意到他有多醉。
「我們得談談。」他含糊地說。「你們多半在納悶我為什麼請你們來。有一件事我一直想找人聊,已經很久了。」對他的兩位客人說這話並不吉利,因為他們從沒來過這個國家,事事都得仰仗他。「等回別墅後,就我們三個。」
他們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才走回別墅──邦尼像頭老驢般辛苦地爬上山丘,他的灰色西裝和紅色大地形成對比。此刻令人回想起他們三個曾在多年前一起去過牛津,這感覺頗為荒謬,因為邦尼看起來比他們老了十歲。
「我需要休息。」帶他們進屋後他慢聲慢氣地說道。「先讓我睡一會兒,然後我們才能談。」於是邦尼上樓睡掉這個炎熱的午後,梅根和亨利則癱進樓梯兩側的扶手椅。「簡短的午睡。」
那差不多是三小時前的事了。
梅根在眺望窗外。亨利傾身計算他們之間的方格,她站在他對角,距離七塊白地磚。「感覺像一盤西洋棋。」他說。「所以妳才一直移動,想把妳的棋子放到最佳攻擊位置嗎?」
她轉身面對他,雙眼瞇起。「西洋棋是拙劣的隱喻。任何男人想用浮誇的方式談論衝突時都會用上。」
自從邦尼突然結束午餐,整個下午他們之間都醞釀著一股殺氣。我們三個得談談,避開西班牙的耳目。梅根又眺望窗外,那場即將爆發的爭執就像天氣變化那般無可避免,有如堆積在藍天中的黑影。
「西洋棋講究規則和對稱,」她接著說,「衝突卻總只是殘酷與齷齪。」
亨利隨手撥弦,藉此改變話題。「妳知道怎麼調音嗎?」他剛剛發現這把吉他掛在他椅子上方的牆上。「調好音的話我可以來彈彈。」
「不知道。」她說完後走出起居室。
他看著她走進房子的深處,她的身影逐漸縮小,被走廊上一道道門漸次框住。他往後靠,點燃另一根菸。
「你覺得他什麼時候會醒?我需要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她回來了,最大版本的她站在離亨利最近的門框下。
「天知道。」亨利說。「他剛吃過午餐又去睡了。」她沒笑。「妳可以離開。無論他想說什麼,我應該都能等。」
梅根停頓,她的臉就像她在宣傳照裡時那樣清新、難以捉摸。她的職業是演員。「你知道他要跟我們說什麼嗎?」
亨利猶豫。「我不覺得我知道。」
「好。那我要出去了。」
他點頭,看著她離開。走廊沿著他面對的方向通往起居室外面,他看見她穿過走廊,走出盡頭的一扇門,而樓梯在他左方。
他繼續漫不經心地撥動吉他弦,直到其中一條突然斷掉,彈開的金屬絲割傷了他的手背。
就在此時,起居室轉暗,他無意識地將頭轉向右邊。梅根正從窗外朝內看,她身後的紅色山丘為她的輪廓圈上一輪惡魔般的光輝。或許是白日太熾,她似乎看不見他。無論如何,他還是感覺自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他將手背湊在嘴邊,吸吮著那道輕微割傷,手指則垂在頦前。
梅根在房子的陰影下躲太陽。
她站在一叢野花中,背靠屋牆,閉上雙眼。近處傳來「滴滴滴」的輕柔叩擊聲,聲音似乎來自她身後。剛開始她以為是遠方穿牆而出的吉他聲,卻又不具備旋律。聲音非常微弱,幾不可聞,但她還是能聽見,就像鞋裡的一顆石頭,令人無法錯認。
滴滴滴。
她轉身抬頭看。透過精緻的鐵窗可以看見一隻蒼蠅一再撞擊邦尼臥室關起的窗戶。邦尼睡在她隔壁的房間,位於頂樓。起初看起來只是一隻想逃跑的小蒼蠅,然後她發現其實有兩隻。事實上是三隻。現在變成四隻了。一整群試圖逃出來的蒼蠅,在窗戶角落形成黑糊糊的一片,她可以想像那些死蒼蠅逐漸堆積在窗臺上的畫面。她從地上撿起一顆小石頭朝窗戶丟去,那片黑雲在清楚可聞的碰撞聲之下散開,然而裡面沒傳出聲音。她又試了一次,還是吵不醒沉睡的東道主。
她耐性漸失,抓起滿滿一把石頭一顆一顆丟出去,直到雙手轉空。她繞著屋子往回走,進門後沿著走廊來到樓梯旁,仍坐在那兒的亨利被突然現身的她嚇了一跳,吉他哐啷掉落冰冷潔白的地板。
「我覺得我們應該叫醒邦尼。」
他看出她的憂慮。「妳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而事實上她是生氣。「我覺得我們該看看。」
她拾級而上,因眼前所見而停步驚叫時,他正緊跟在她身後,隨即伸臂摟住她。他的用意是讓她冷靜下來,卻做得太笨拙,弄得兩人卡在那兒動彈不得。
「放手。」她用手肘架開他後往前跑,而隨著她的肩膀不再擋住前方,他也看見她方才所見:邦尼臥室的門縫下漫出細細一道血流,直直地指向他的屍體。
他們都不曾見過這麼多血。邦尼俯臥床單,一根刀柄從他背上冒出來,一道蜿蜒紅跡一路蔓延到床的最低處。刀身幾乎完全沒入,他們只看得見他的身體和黑色刀柄間的一絲銀色細線,彷彿一瞥從窗簾縫隙透入的月光。「那是心臟的位置。」梅根說。刀柄本身可能成了日晷的一部分,屍體則無心插柳地標記出時間的流逝。
她繞過地板上的血窪走近床邊,距離屍體剩一呎時,亨利阻止她。「妳覺得我們該這樣嗎?」
「我必須檢查一下。」她荒唐地用兩根手指貼住他的頸側。沒有脈搏。她搖頭,「這不可能。」
亨利震驚地在床墊邊緣坐下,重量壓得血跡朝他擴散,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般一躍而起。他看著門,接著又回頭看梅根。
「兇手一定還在這裡。」他低聲說。「我去搜其他房間。」
「好。」梅根也低聲說,而因為她是演員,就算壓低音量仍清楚如平常說話。這幾乎稱得上是種諷刺了。「順便檢查是不是所有窗戶都鎖上了。」
「妳在這裡等。」他隨即離開。
她試著深呼吸,但房內已有腐爛的味道,那幾隻八卦的蒼蠅仍在輕拍窗外的酷暑,想必是對屍體厭倦了吧。她走過去將窗戶抬起打開幾吋,蒼蠅疾射而出,消失在藍空中,彷彿攪入湯中的鹽粒。她站在窗邊,仍因震驚而發冷,同時可聽見亨利在附近房間搜索,打開一個個衣櫃、查看床底。
他又出現在門口,這次一臉失望。「樓上沒人。」
「窗戶都鎖上了嗎?」
「對,我檢查了。」
「我想也是。去吃午餐前,我親眼看著邦尼偏執地把所有東西都上了鎖。」
「那門呢?也都鎖上了嗎?」他手指她身後通往陽臺的兩扇門。她走過去拉了拉門把。門的上中下都以門栓拴起。
「對。」她在床緣坐下,忽略蔓延的血跡。「亨利,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他皺眉。「這代表他們一定是從樓梯離開的。我去鎖上樓下的所有門窗,妳在這裡等。」
「等等。」她才開口,但他已經離開。她聽見他赤腳踩在堅硬潔白有如琴鍵的階梯,發出絲毫不具音樂性的沉重腳步聲,走到轉彎處時稍停,接著一掌啪地平貼著牆,以穩住身子,最後是在樓下到處走動的聲音。
她拉開邦尼床邊櫃的抽屜,裡面只有內衣和一只金錶,而另一個抽屜裡裝有一本日記和他的睡衣。當然了,他是穿著他原本的衣服入睡。她拿出日記一頁頁翻過,最後一篇寫於幾乎一年前。她將日記放回去,接著看了看自己的錶。
她要在這裡等多久,容忍亨利裝模作樣地掌控大局,然後才能下去和他對質?
隨著亨利關起一扇扇門,屋子裡變得愈來愈熱,因此他雖然在倉促中開始檢查,現在卻改為緩慢但有系統地行動。他的呼吸沉重,多次進出各個房間,以確保沒有任何遺漏。這裡的格局令人困惑,他納悶邦尼為何會落得獨居於如此偌大的房子。似乎沒有任何房間是相同的形狀或大小,許多還連一扇窗都沒有。「無光,只可見黑暗。」1他暗想,人有錢了就是會做這種事。
他回到起居室,發現她也在這,坐在他剛剛坐的那張椅子上,抽著他的菸。他覺得自己該說些笑話,延緩面對現實,就算幾秒也好。「妳只欠把吉他,再剪個頭髮,我就會像看著鏡子一樣了。」
梅根沒回應。
「他們離開了。當然,樓下有這麼多門窗,他們想怎麼出去都可以。」
她緩緩地將菸丟進菸灰缸,拿起她剛剛放在旁邊的一把小刀。那只是另一個融入這簡樸空間的細長物品,他甚至沒注意到小刀在那。她起身,對他舉刀,刀尖對準他的胸膛。
「別動。」她輕聲說。「停在那兒就好,我們需要聊聊。」
亨利往後退,跌坐在她對面的那張椅子上。她被這突然的動作嚇了一跳,而他開始覺得自己毫無力量,只能絕望地緊抓扶手,但她仍停留在原地。「妳要殺我嗎,梅根?」
「除非你逼我。」
「我永遠不會逼妳做任何事。」他嘆氣。「可以給我一根菸嗎?我怕要是我自己伸手拿,說不定會掉一兩根手指。我可能得像抽小雪茄一樣抽我自己的拇指。」
她從菸盒裡抽出一根菸朝他扔去。他撿起後小心地點燃。「好啦。妳今天下午一直想找架吵,我原本以為會比較文明一點。現在是怎樣?」
梅根以一種智勝敵方的自信說話。「你嘗試故作鎮定,亨利,但是你的手在發抖。」
「說不定是因為我覺得冷。是只有我嗎?還是今年西班牙的夏天有點冷?」
「但你汗如雨下。」
「妳還指望我怎樣?妳用刀對準我的臉耶。」
「這只是把小刀,而你是個高大的男人,且我根本離你的臉很遠。你發抖是因為擔心東窗事發,才不是怕我傷害你。」
「妳想說什麼?」
「嗯,以下是幾個事實。樓上有五個房間,都有裝鐵窗,跟卡通一樣的那種黑色粗鐵條。兩個房間有通往陽臺的門,門都上了鎖,窗戶也是,你剛剛自己檢查過。只有一道階梯通往頂樓,也就是這裡這道。我說的都對嗎?」
他點頭。
「那麼無論是誰謀殺了邦尼,那人一定都是從那道樓梯上去的。」她手指著籠罩在陰影中的樓梯中軸,樓梯在此處轉彎,短暫失去所有光線。「然後再從這裡下來。而我們吃完午餐回來後,你從頭到尾都坐在樓梯底這兒。」
他聳肩。「那又如何?妳的意思該不會是我跟這件事有任何關係吧?」
「我正是這個意思。你要不看見兇手上樓,要不就是你自己上去,這樣一來,你不是兇手就是幫兇。而我不認為你待在這裡的時間有長到足以交任何朋友。」
他閉上眼專心聽她說話。「胡扯。可能有人從我旁邊溜過去。我幾乎沒在注意。」
「有人在一個寂靜、潔白的房間從你旁邊溜過去?那會是什麼,亨利?老鼠還是芭蕾舞者?」
「所以妳真認為是我殺了他?」她的整個論述突然變得清晰明瞭,他起身抗議。「但是梅根,妳漏了一件事。我或許從午餐後就坐在這兒專心消化,但妳自己也跟我一起坐在這裡啊。」
她的頭歪向一邊。「沒錯,但我記得我至少出去透氣了三次。不知道你是不是因此才抽這麼多菸,好逼我出去?我不知道一把刀捅進某人的背要花多少時間,但我想應該可以很快得手吧,完事後的洗手可能還會占用更多時間。」
亨利又坐下。「天啊,」他努力坐得舒服點,「妳居然是認真的,對吧?我們才剛發現我們的朋友死在樓上,而妳居然說是我做的?基於什麼?只因為我就坐在樓梯旁?我們認識彼此幾乎十年了耶?」
「人會改變。」
「嗯,那倒是。最近我覺得大家都謬讚莎士比亞,而我也不再上教堂。但如果我沒帶道德感出門,我希望有人能夠知會我一聲。」
「我不是針對你,只是把線索串起來而已。你從頭到尾都在這,不是嗎?」
「不是針對我?」他難以置信地搖頭。「妳有讀過偵探故事嗎,梅根?有上百種方式可以殺他,說不定有條上樓的秘密通道。」
「這是現實世界,亨利。真實人生中,如果只有一個人具備動機與機會,那他通常有罪。」
「動機?我的動機又是什麼了?」
「邦尼為何找我們來?」
「我不知道。」
「我認為你知道。沉默五年後,他寫信邀請我們來他西班牙的家,而我們就眼巴巴地跑來。為什麼?因為他打算勒索我們。這你一定知道吧?」
「勒索我們?因為牛津發生的事嗎?」亨利揮開這想法。「開車的是邦尼耶。」
「我們也不全然是無辜的,對吧?」
「胡扯。我來是因為他跟我說妳也會在,他還說妳想見我。跟勒索一點關係也沒有。」
「你有帶著他寫給你的信嗎?」
「沒有。」
「那就只有你的一面之詞囉?」
他茫然地盯著地板。「我還愛妳,梅根,所以我才會來。邦尼完全知道說什麼能把我引來。真不敢相信妳居然認為我會做出像這樣的事。」
她不為所動。「我希望我能活在你的世界裡,亨利。你多半在幻想著我們會隨時唱起歌來吧。」
「我只是把我的感覺跟妳說而已。」
「而如我剛剛所說,我只是把線索串起來而已。」
「除了……」
「什麼?」她懷疑地看著他,刀子在手中抽動。「除了什麼,亨利?」
他又起身,一手放在頭上,一手撐著紮實的白牆,接著開始來回踱步。「甭擔心,我會保持距離。」她緊張起來,刀尖追著他的動作。「如果妳出去透氣後我也離開,那該怎麼說?我真有可能離開,而妳不會知道。兇手可能趁這時候出擊。」
「那你有離開嗎?」
「有。」他又坐下。「我回房間拿了本書,兇手一定趁機溜過。」
「你說謊。」
「我沒有。」
「有,你有。如果是真的,你會更早說出來。」
「我忘了,就是這樣。」
「亨利,算了吧。」她朝他走近一步。「我沒興趣被騙。」
他伸出一隻手,沒發抖。「喂,妳看,我說的是真話。」
她踢他的椅腳,他撐著扶手穩住自己,那隻手勾起成爪狀。「說得夠多了,我只想知道你接下來打算怎麼樣。」
「嗯,這裡沒電話,所以我要跑到村裡帶警察和醫師過來。但若妳打算跟他們說人是我殺的,那我就難辦了,對吧?」
「我們可以晚點再來擔心警察。現在我只想確定如果我放下刀,我不會落得躺在邦尼旁邊的下場。你為什麼殺他?」
「我沒有。」
「那是誰殺的?」
「一定是陌生人闖入殺了他。」
「為了什麼?」
「我怎麼知道。」
她坐下。「聽著,我會幫你脫身,亨利。不難想像你一定有什麼合理的理由殺他。我們都知道,邦尼可以很殘酷,而且魯莽。搞不好最後我甚至能夠原諒你,但如果你想要我為你說謊,你就不該測試我的耐性。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用這種手法?」
「梅根,這太瘋狂了。」亨利閉上眼。所有門窗皆被關上,這熱度令人難以忍受。他覺得他們像兩個懸浮在油中的樣本,有人正研究著他們。
「所以你還是堅持你是無辜的囉?天啊,我們已經走過一輪了,亨利,你努力過,但排在走廊的十二盆植物陪審團已判定你有罪。你從頭到尾都在這,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把頭埋入雙掌中。「再讓我想想。」他複習著她的指控,嘴脣無聲蠕動。「快被妳煩死了。」他突兀地伸手從旁邊的地上拿起吉他,撥動剩下的五根弦。「會不會我們吃完午餐回來時他們就躲在樓上了?」他的額頭滿是汗水。「除非是就在我們回來的那個當下,否則他們沒有機會離開。事實上、事實上,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他又起身。「我想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梅根。」
她朝他仰起頭──一個表示鼓勵的倒轉點頭。
「梅根,妳這小蜘蛛、妳這不懷好意的蛇。是妳殺死了他。」
梅根看起來完全不為所動。「別傻了。」
「看得出來妳經過一番思考。我們來了,具有相同機會、動機也廣泛得足以涵蓋雙方的兩名嫌疑犯,所以妳只要否認一切,罪責就會歸咎於我。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我們之中誰比較會演戲,而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如我方才所指出,亨利,你整個下午都坐在這裡看守你的殺戮,所以我怎樣才下得了手?」
「妳只要否認一切,講到喉嚨乾掉就好,沒必要陷害我、假造證據。妳從頭到尾就是打這如意算盤,對吧?警察來了後會發現這裡有兩個外國人跟一具屍體,其中之一是我,既挫敗又講不清楚,試圖主張可能有人頭下腳上爬過天花板以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上樓。另一個則是妳,完美自制,否認一切──一朵英國玫瑰奮起對抗粗野男子。我們都知道他們會相信誰,而我還能怎麼說服他們?我在這天殺的國家裡甚至點不了一杯咖啡。」
「這是你的理論,是吧?那我怎麼從你旁邊溜過去,亨利?像你說的在天花板爬行嗎?還是你在剛剛這二十秒內又想出了什麼更具說服力的說法?」
「我沒必要。這問題不對。」他起身走到窗戶旁,這會兒不怕她了。「頂樓確實牢牢上鎖,只能從樓梯出入,也確實我自從午餐後,也自從邦尼上去他房間後整個下午都坐在這,連廁所都沒去上。不過也確實我們剛回來時我走得又熱又一身髒,曾經去梳洗一番。我留下妳獨自在這,就是這裡。我回來時妳不曾移動。我清洗臉、脖子和雙手花了九到十分鐘,這時間太短暫,我幾乎完全忘記。但話說回來,把小刀捅進某人背上要花多長時間?」
「那是幾小時前的事了。」
「三小時前。那妳覺得他死了多久?血都流到整條走廊了。」
「那時候我們才剛進屋,他剛上樓,甚至還沒睡著吧。」
「對,但他很醉,睡不睡根本沒差。他一趴上床就完全無法防備了。」
「所以就這樣,是吧?你指控我謀殺他?」
亨利微笑,為自己的邏輯感到驕傲。「沒錯,我就是。」
「你這可悲、幸災樂禍的傻瓜。他死了,而你想拿來當遊戲?我知道是你幹的,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也可以問妳相同問題。」
梅根停下,把整件事想過一遍,拿刀的手放鬆了。亨利眺望窗外,透過髒玻璃看見泛著光暈的山丘。他正以他的無畏嘲弄她,這是一種主張他權威的方式。
「我懂你在做什麼了,我現在看得一清二楚。這事關名聲,對吧?我是演員,像這樣的醜聞會毀掉我。就算只是再雞毛蒜皮的懷疑,我的名聲都將破滅。你覺得我的損失會比你大,所以不得不配合?」
他旋過身,被身後的明亮日光晒紅。「妳以為跟妳的職業名聲有關?並不是什麼都跟妳的演藝生涯有關好嗎,梅根。」
她咬住下脣。「不,我也不覺得你會承認,對吧。你首先讓我見識你可以多頑強,然後呢?當你讓我相信我贏不了、我如果不配合就會毀掉我的演藝生涯後,你再提出你的計畫。你會想出某種故事再要求我替你佐證。如果真是這樣,你還是直接跟我說實話比較明智。」
他嘆氣,搖了搖頭。「真不知道妳為什麼一直說這些。跟妳解釋過這場犯罪的各種情況了,但就算是最棒的偵探,面對徹底否認也沒轍。我煩得都快扯光我的頭髮了,事情就是這樣了,不過我不覺得光頭適合我。」
她盯著他。大約有一分鐘的時間兩人都不發一語。最後她終於把刀放在身旁的桌上,刀尖轉到一旁不再對準他。
「好吧。拿起你的吉他接著彈吧。我指控你,你也指控我,顯然我們就是置身這種處境。但如果你以為我是那種會屈服、只因為一個男人說天空是綠色就被說服的女人,那你可是低估我了。」
「如果妳以為妳只要站穩立場、搧搧睫毛,我就會像隻鳥兒般唱歌,妳才是高估了妳自己的魅力。」
「噢,」梅根眨眼,「但我以為你還愛我?」
亨利在她對面的椅子坐下。「我是,所以這才如此令人瘋狂。只要妳承認是妳殺的,我不管如何都會原諒妳。」
「那我們來談談以前沒談過的事。」她又拿起小刀,而他眼中閃過一絲真實的恐懼。「你擁有狂暴的一面,亨利。我看過你喝醉,也看過你只是不喜歡陌生人看我的方式就跟他們打起來,還看過你呼喊、尖叫、砸玻璃。這些你也一概否認嗎?」
他注視地板。「不,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有見過我那樣嗎?」
「或許沒有,但妳也可以很殘酷。」
「尖牙利嘴殺不了人的。」
他聳肩。「所以我脾氣暴躁。這是妳不想嫁給我的原因嗎?」
「不盡然,但也不算加分就是了。」
「我那時喝了很多酒。」
「你午餐時也喝了很多。」
「不多。沒以前多。」
「顯然夠多了。」
亨利嘆氣。「如果我想殺邦尼,我會用更好的方法。」
「亨利,我知道是你,我們都知道。你到底想說服我相信什麼?我發瘋了?」
「我也可以說一樣的話,不是嗎?」
「不,你不能。」她揮刀刺入她的椅子扶手,刀刺穿墊襯卡在木頭裡。「邦尼在樓上像個水龍頭般滴滴答答,我們卻只是在這裡吵架。要是警察發現我們整個下午在做什麼,他們會怎麼想?」
「真是場惡夢。」
梅根翻白眼。「另一個爛譬喻。」
「好吧,如果我們要這樣度過這下午,那我想要手上有杯酒。想加入嗎?」
「你有病。」
他幫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半小時過去,什麼也沒改變,他們反覆著這個情況數次,每次都沒有結果。
亨利喝完酒,把空杯捧在眼前,透過酒杯凝視變形、空洞的起居室,手一面左右移動。梅根看著他,不知道他的注意力怎麼會這麼容易分散。
亨利回頭看她。「我要再來一杯然後就結束,妳想加入嗎?」
門窗依然緊閉,起居室內令人窒息,彷彿是一項他們彼此都同意的自我懲罰。
她點頭。「我跟你喝一杯。」
他哼了一聲,走到酒櫃旁,從威士忌長頸瓶倒出兩大杯酒。當然了,酒是溫的。他一手拿起一杯,有節奏地旋了旋,將另一杯遞給她。她看見這分量瞪大了眼,三分之二滿。「最後一杯酒。」他說。
「如果我們都沒有要認罪,」梅根說,「我們應該要討論一下接下來該做什麼。是不是根本沒必要牽扯上警察?沒人知道我們在這,或許我們乾脆趁夜離開就好。」
亨利靜靜啜飲他的酒。他們就這樣在那兒坐了幾分鐘。梅根一手掩著她的杯子,終於舉到嘴邊時,她在酒杯碰到嘴脣前停住。「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下毒?」
「我們可以交換。」
她聳肩。這段對話似乎並不值得接續下去。她啜了一小口,「味道不錯。」而他只是用一種令她不安的方式靜靜注視著她。「換個角度來說,為了避免疑慮。」他嘆氣,將自己的酒杯交給她;她接下,也把自己的酒杯給他。
他氣力用盡地坐回椅子上,舉杯。「敬邦尼。」
「敬邦尼。」
威士忌如即將到來的落日那樣橘紅熱烈。亨利又拿起吉他,重新彈起先前那個笨拙的調子。「我們回到起點了。」他嘆氣。
「如我所說,我們需要討論接下來該怎麼辦。」
「妳要我說我們可以就這樣逃跑,假裝自己沒來過?跟上次一樣。那自始至終就是妳的計畫,對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梅根放下酒杯,搖了搖頭。「是因為我取消我們的訂婚嗎?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啜飲酒漿已成為亨利用來拖延對話的主要手段,然而面對這個問題,他卻認真相對,並點燃一根菸。「那我就再說一次吧,梅根,我還愛妳。」
「很高興知道你還愛我。」她期待地看著他。「你開始覺得頭暈了嗎,亨利?」
剛開始他困惑不解,接著瞥了一眼他的酒杯。他已幾乎喝乾,只剩下最後半吋高度。他伸手想要拿杯子,卻發現左臂幾乎麻痺,姿態詭異又笨拙的手將杯子打落地面,酒杯隨即破碎,在白地磚留下一個棕色圓圈。「妳做了什麼?」
菸從他口中掉落,墜入吉他琴身內,一縷盤繞的煙從琴弦間裊裊上升。她的臉除了些微擔心外不露情感。
「梅根。」
他往前滾下椅子,半邊身體麻痺,吉他彈到一旁。他俯臥白地板,毫無節奏地顫抖,唾液在他下巴前方的地磚上聚積。
「說謊是這樣的,亨利。」她起身聳立他身旁。「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無論謊言帶你到哪,你都只能跟隨。」
幾無特色的白色起居室裡,兩名嫌疑犯坐在不成套的座椅上,正等待著某事發生。在他們的座位之間有一道拱門,通往狹窄無窗的樓梯間──一個存在感似乎主宰這空間的陰暗凹處,彷彿像一座大得不成比例的壁爐。樓梯在中途轉彎,上層遭遮蔽,令人感覺往上除了黑暗,便再無其他。
「在這乾等真像置身地獄。」梅根坐在拱門右側。「話說回來,西班牙人午睡一般都睡多久啊?」
她起身走到窗前。外面的西班牙鄉間是一片朦朧的橘色,在這熱度下看似不宜居住。
「一兩個小時,不過他剛剛喝酒喝個不停。」亨利側坐在椅子上,雙腿懸在一邊扶手,一把吉他擱在腿上。「我了解邦尼,他會一路睡到晚餐時間。」
梅根走到酒櫃前檢視裡面的酒瓶,小心地一一轉動,直到所有酒標都朝外。亨利將口中的菸拿到右眼前,假裝正拿著假的望遠鏡看她。「妳又在用鞋子呼吸了。」
她大半個下午都不停地在來回踱步。這個會客室的白地磚和擦得乾乾淨淨的每個表面都讓她想起某醫生的候診室──他們彷彿身在家鄉的某紅磚醫院,而非崎嶇紅丘頂的一座古怪西班牙別墅。「如果我是在用鞋子呼吸,」她咕噥,「那你就是在用嘴巴走路。」
數小時前,他們在鄰近村落的一家小酒館用午餐,那裡距離邦尼家只需穿過三十分鐘的樹林。用餐結束時邦尼站起,他們雙雙注意到他有多醉。
「我們得談談。」他含糊地說。「你們多半在納悶我為什麼請你們來。有一件事我一直想找人聊,已經很久了。」對他的兩位客人說這話並不吉利,因為他們從沒來過這個國家,事事都得仰仗他。「等回別墅後,就我們三個。」
他們花了將近一個小時才走回別墅──邦尼像頭老驢般辛苦地爬上山丘,他的灰色西裝和紅色大地形成對比。此刻令人回想起他們三個曾在多年前一起去過牛津,這感覺頗為荒謬,因為邦尼看起來比他們老了十歲。
「我需要休息。」帶他們進屋後他慢聲慢氣地說道。「先讓我睡一會兒,然後我們才能談。」於是邦尼上樓睡掉這個炎熱的午後,梅根和亨利則癱進樓梯兩側的扶手椅。「簡短的午睡。」
那差不多是三小時前的事了。
梅根在眺望窗外。亨利傾身計算他們之間的方格,她站在他對角,距離七塊白地磚。「感覺像一盤西洋棋。」他說。「所以妳才一直移動,想把妳的棋子放到最佳攻擊位置嗎?」
她轉身面對他,雙眼瞇起。「西洋棋是拙劣的隱喻。任何男人想用浮誇的方式談論衝突時都會用上。」
自從邦尼突然結束午餐,整個下午他們之間都醞釀著一股殺氣。我們三個得談談,避開西班牙的耳目。梅根又眺望窗外,那場即將爆發的爭執就像天氣變化那般無可避免,有如堆積在藍天中的黑影。
「西洋棋講究規則和對稱,」她接著說,「衝突卻總只是殘酷與齷齪。」
亨利隨手撥弦,藉此改變話題。「妳知道怎麼調音嗎?」他剛剛發現這把吉他掛在他椅子上方的牆上。「調好音的話我可以來彈彈。」
「不知道。」她說完後走出起居室。
他看著她走進房子的深處,她的身影逐漸縮小,被走廊上一道道門漸次框住。他往後靠,點燃另一根菸。
「你覺得他什麼時候會醒?我需要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她回來了,最大版本的她站在離亨利最近的門框下。
「天知道。」亨利說。「他剛吃過午餐又去睡了。」她沒笑。「妳可以離開。無論他想說什麼,我應該都能等。」
梅根停頓,她的臉就像她在宣傳照裡時那樣清新、難以捉摸。她的職業是演員。「你知道他要跟我們說什麼嗎?」
亨利猶豫。「我不覺得我知道。」
「好。那我要出去了。」
他點頭,看著她離開。走廊沿著他面對的方向通往起居室外面,他看見她穿過走廊,走出盡頭的一扇門,而樓梯在他左方。
他繼續漫不經心地撥動吉他弦,直到其中一條突然斷掉,彈開的金屬絲割傷了他的手背。
就在此時,起居室轉暗,他無意識地將頭轉向右邊。梅根正從窗外朝內看,她身後的紅色山丘為她的輪廓圈上一輪惡魔般的光輝。或許是白日太熾,她似乎看不見他。無論如何,他還是感覺自己像動物園裡的動物,他將手背湊在嘴邊,吸吮著那道輕微割傷,手指則垂在頦前。
梅根在房子的陰影下躲太陽。
她站在一叢野花中,背靠屋牆,閉上雙眼。近處傳來「滴滴滴」的輕柔叩擊聲,聲音似乎來自她身後。剛開始她以為是遠方穿牆而出的吉他聲,卻又不具備旋律。聲音非常微弱,幾不可聞,但她還是能聽見,就像鞋裡的一顆石頭,令人無法錯認。
滴滴滴。
她轉身抬頭看。透過精緻的鐵窗可以看見一隻蒼蠅一再撞擊邦尼臥室關起的窗戶。邦尼睡在她隔壁的房間,位於頂樓。起初看起來只是一隻想逃跑的小蒼蠅,然後她發現其實有兩隻。事實上是三隻。現在變成四隻了。一整群試圖逃出來的蒼蠅,在窗戶角落形成黑糊糊的一片,她可以想像那些死蒼蠅逐漸堆積在窗臺上的畫面。她從地上撿起一顆小石頭朝窗戶丟去,那片黑雲在清楚可聞的碰撞聲之下散開,然而裡面沒傳出聲音。她又試了一次,還是吵不醒沉睡的東道主。
她耐性漸失,抓起滿滿一把石頭一顆一顆丟出去,直到雙手轉空。她繞著屋子往回走,進門後沿著走廊來到樓梯旁,仍坐在那兒的亨利被突然現身的她嚇了一跳,吉他哐啷掉落冰冷潔白的地板。
「我覺得我們應該叫醒邦尼。」
他看出她的憂慮。「妳覺得有什麼不對嗎?」
而事實上她是生氣。「我覺得我們該看看。」
她拾級而上,因眼前所見而停步驚叫時,他正緊跟在她身後,隨即伸臂摟住她。他的用意是讓她冷靜下來,卻做得太笨拙,弄得兩人卡在那兒動彈不得。
「放手。」她用手肘架開他後往前跑,而隨著她的肩膀不再擋住前方,他也看見她方才所見:邦尼臥室的門縫下漫出細細一道血流,直直地指向他的屍體。
他們都不曾見過這麼多血。邦尼俯臥床單,一根刀柄從他背上冒出來,一道蜿蜒紅跡一路蔓延到床的最低處。刀身幾乎完全沒入,他們只看得見他的身體和黑色刀柄間的一絲銀色細線,彷彿一瞥從窗簾縫隙透入的月光。「那是心臟的位置。」梅根說。刀柄本身可能成了日晷的一部分,屍體則無心插柳地標記出時間的流逝。
她繞過地板上的血窪走近床邊,距離屍體剩一呎時,亨利阻止她。「妳覺得我們該這樣嗎?」
「我必須檢查一下。」她荒唐地用兩根手指貼住他的頸側。沒有脈搏。她搖頭,「這不可能。」
亨利震驚地在床墊邊緣坐下,重量壓得血跡朝他擴散,他彷彿從噩夢中驚醒般一躍而起。他看著門,接著又回頭看梅根。
「兇手一定還在這裡。」他低聲說。「我去搜其他房間。」
「好。」梅根也低聲說,而因為她是演員,就算壓低音量仍清楚如平常說話。這幾乎稱得上是種諷刺了。「順便檢查是不是所有窗戶都鎖上了。」
「妳在這裡等。」他隨即離開。
她試著深呼吸,但房內已有腐爛的味道,那幾隻八卦的蒼蠅仍在輕拍窗外的酷暑,想必是對屍體厭倦了吧。她走過去將窗戶抬起打開幾吋,蒼蠅疾射而出,消失在藍空中,彷彿攪入湯中的鹽粒。她站在窗邊,仍因震驚而發冷,同時可聽見亨利在附近房間搜索,打開一個個衣櫃、查看床底。
他又出現在門口,這次一臉失望。「樓上沒人。」
「窗戶都鎖上了嗎?」
「對,我檢查了。」
「我想也是。去吃午餐前,我親眼看著邦尼偏執地把所有東西都上了鎖。」
「那門呢?也都鎖上了嗎?」他手指她身後通往陽臺的兩扇門。她走過去拉了拉門把。門的上中下都以門栓拴起。
「對。」她在床緣坐下,忽略蔓延的血跡。「亨利,你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
他皺眉。「這代表他們一定是從樓梯離開的。我去鎖上樓下的所有門窗,妳在這裡等。」
「等等。」她才開口,但他已經離開。她聽見他赤腳踩在堅硬潔白有如琴鍵的階梯,發出絲毫不具音樂性的沉重腳步聲,走到轉彎處時稍停,接著一掌啪地平貼著牆,以穩住身子,最後是在樓下到處走動的聲音。
她拉開邦尼床邊櫃的抽屜,裡面只有內衣和一只金錶,而另一個抽屜裡裝有一本日記和他的睡衣。當然了,他是穿著他原本的衣服入睡。她拿出日記一頁頁翻過,最後一篇寫於幾乎一年前。她將日記放回去,接著看了看自己的錶。
她要在這裡等多久,容忍亨利裝模作樣地掌控大局,然後才能下去和他對質?
隨著亨利關起一扇扇門,屋子裡變得愈來愈熱,因此他雖然在倉促中開始檢查,現在卻改為緩慢但有系統地行動。他的呼吸沉重,多次進出各個房間,以確保沒有任何遺漏。這裡的格局令人困惑,他納悶邦尼為何會落得獨居於如此偌大的房子。似乎沒有任何房間是相同的形狀或大小,許多還連一扇窗都沒有。「無光,只可見黑暗。」1他暗想,人有錢了就是會做這種事。
他回到起居室,發現她也在這,坐在他剛剛坐的那張椅子上,抽著他的菸。他覺得自己該說些笑話,延緩面對現實,就算幾秒也好。「妳只欠把吉他,再剪個頭髮,我就會像看著鏡子一樣了。」
梅根沒回應。
「他們離開了。當然,樓下有這麼多門窗,他們想怎麼出去都可以。」
她緩緩地將菸丟進菸灰缸,拿起她剛剛放在旁邊的一把小刀。那只是另一個融入這簡樸空間的細長物品,他甚至沒注意到小刀在那。她起身,對他舉刀,刀尖對準他的胸膛。
「別動。」她輕聲說。「停在那兒就好,我們需要聊聊。」
亨利往後退,跌坐在她對面的那張椅子上。她被這突然的動作嚇了一跳,而他開始覺得自己毫無力量,只能絕望地緊抓扶手,但她仍停留在原地。「妳要殺我嗎,梅根?」
「除非你逼我。」
「我永遠不會逼妳做任何事。」他嘆氣。「可以給我一根菸嗎?我怕要是我自己伸手拿,說不定會掉一兩根手指。我可能得像抽小雪茄一樣抽我自己的拇指。」
她從菸盒裡抽出一根菸朝他扔去。他撿起後小心地點燃。「好啦。妳今天下午一直想找架吵,我原本以為會比較文明一點。現在是怎樣?」
梅根以一種智勝敵方的自信說話。「你嘗試故作鎮定,亨利,但是你的手在發抖。」
「說不定是因為我覺得冷。是只有我嗎?還是今年西班牙的夏天有點冷?」
「但你汗如雨下。」
「妳還指望我怎樣?妳用刀對準我的臉耶。」
「這只是把小刀,而你是個高大的男人,且我根本離你的臉很遠。你發抖是因為擔心東窗事發,才不是怕我傷害你。」
「妳想說什麼?」
「嗯,以下是幾個事實。樓上有五個房間,都有裝鐵窗,跟卡通一樣的那種黑色粗鐵條。兩個房間有通往陽臺的門,門都上了鎖,窗戶也是,你剛剛自己檢查過。只有一道階梯通往頂樓,也就是這裡這道。我說的都對嗎?」
他點頭。
「那麼無論是誰謀殺了邦尼,那人一定都是從那道樓梯上去的。」她手指著籠罩在陰影中的樓梯中軸,樓梯在此處轉彎,短暫失去所有光線。「然後再從這裡下來。而我們吃完午餐回來後,你從頭到尾都坐在樓梯底這兒。」
他聳肩。「那又如何?妳的意思該不會是我跟這件事有任何關係吧?」
「我正是這個意思。你要不看見兇手上樓,要不就是你自己上去,這樣一來,你不是兇手就是幫兇。而我不認為你待在這裡的時間有長到足以交任何朋友。」
他閉上眼專心聽她說話。「胡扯。可能有人從我旁邊溜過去。我幾乎沒在注意。」
「有人在一個寂靜、潔白的房間從你旁邊溜過去?那會是什麼,亨利?老鼠還是芭蕾舞者?」
「所以妳真認為是我殺了他?」她的整個論述突然變得清晰明瞭,他起身抗議。「但是梅根,妳漏了一件事。我或許從午餐後就坐在這兒專心消化,但妳自己也跟我一起坐在這裡啊。」
她的頭歪向一邊。「沒錯,但我記得我至少出去透氣了三次。不知道你是不是因此才抽這麼多菸,好逼我出去?我不知道一把刀捅進某人的背要花多少時間,但我想應該可以很快得手吧,完事後的洗手可能還會占用更多時間。」
亨利又坐下。「天啊,」他努力坐得舒服點,「妳居然是認真的,對吧?我們才剛發現我們的朋友死在樓上,而妳居然說是我做的?基於什麼?只因為我就坐在樓梯旁?我們認識彼此幾乎十年了耶?」
「人會改變。」
「嗯,那倒是。最近我覺得大家都謬讚莎士比亞,而我也不再上教堂。但如果我沒帶道德感出門,我希望有人能夠知會我一聲。」
「我不是針對你,只是把線索串起來而已。你從頭到尾都在這,不是嗎?」
「不是針對我?」他難以置信地搖頭。「妳有讀過偵探故事嗎,梅根?有上百種方式可以殺他,說不定有條上樓的秘密通道。」
「這是現實世界,亨利。真實人生中,如果只有一個人具備動機與機會,那他通常有罪。」
「動機?我的動機又是什麼了?」
「邦尼為何找我們來?」
「我不知道。」
「我認為你知道。沉默五年後,他寫信邀請我們來他西班牙的家,而我們就眼巴巴地跑來。為什麼?因為他打算勒索我們。這你一定知道吧?」
「勒索我們?因為牛津發生的事嗎?」亨利揮開這想法。「開車的是邦尼耶。」
「我們也不全然是無辜的,對吧?」
「胡扯。我來是因為他跟我說妳也會在,他還說妳想見我。跟勒索一點關係也沒有。」
「你有帶著他寫給你的信嗎?」
「沒有。」
「那就只有你的一面之詞囉?」
他茫然地盯著地板。「我還愛妳,梅根,所以我才會來。邦尼完全知道說什麼能把我引來。真不敢相信妳居然認為我會做出像這樣的事。」
她不為所動。「我希望我能活在你的世界裡,亨利。你多半在幻想著我們會隨時唱起歌來吧。」
「我只是把我的感覺跟妳說而已。」
「而如我剛剛所說,我只是把線索串起來而已。」
「除了……」
「什麼?」她懷疑地看著他,刀子在手中抽動。「除了什麼,亨利?」
他又起身,一手放在頭上,一手撐著紮實的白牆,接著開始來回踱步。「甭擔心,我會保持距離。」她緊張起來,刀尖追著他的動作。「如果妳出去透氣後我也離開,那該怎麼說?我真有可能離開,而妳不會知道。兇手可能趁這時候出擊。」
「那你有離開嗎?」
「有。」他又坐下。「我回房間拿了本書,兇手一定趁機溜過。」
「你說謊。」
「我沒有。」
「有,你有。如果是真的,你會更早說出來。」
「我忘了,就是這樣。」
「亨利,算了吧。」她朝他走近一步。「我沒興趣被騙。」
他伸出一隻手,沒發抖。「喂,妳看,我說的是真話。」
她踢他的椅腳,他撐著扶手穩住自己,那隻手勾起成爪狀。「說得夠多了,我只想知道你接下來打算怎麼樣。」
「嗯,這裡沒電話,所以我要跑到村裡帶警察和醫師過來。但若妳打算跟他們說人是我殺的,那我就難辦了,對吧?」
「我們可以晚點再來擔心警察。現在我只想確定如果我放下刀,我不會落得躺在邦尼旁邊的下場。你為什麼殺他?」
「我沒有。」
「那是誰殺的?」
「一定是陌生人闖入殺了他。」
「為了什麼?」
「我怎麼知道。」
她坐下。「聽著,我會幫你脫身,亨利。不難想像你一定有什麼合理的理由殺他。我們都知道,邦尼可以很殘酷,而且魯莽。搞不好最後我甚至能夠原諒你,但如果你想要我為你說謊,你就不該測試我的耐性。為什麼是現在?為什麼用這種手法?」
「梅根,這太瘋狂了。」亨利閉上眼。所有門窗皆被關上,這熱度令人難以忍受。他覺得他們像兩個懸浮在油中的樣本,有人正研究著他們。
「所以你還是堅持你是無辜的囉?天啊,我們已經走過一輪了,亨利,你努力過,但排在走廊的十二盆植物陪審團已判定你有罪。你從頭到尾都在這,你還有什麼好說的?」
他把頭埋入雙掌中。「再讓我想想。」他複習著她的指控,嘴脣無聲蠕動。「快被妳煩死了。」他突兀地伸手從旁邊的地上拿起吉他,撥動剩下的五根弦。「會不會我們吃完午餐回來時他們就躲在樓上了?」他的額頭滿是汗水。「除非是就在我們回來的那個當下,否則他們沒有機會離開。事實上、事實上,我想我找到答案了。」
他又起身。「我想我知道發生什麼事了,梅根。」
她朝他仰起頭──一個表示鼓勵的倒轉點頭。
「梅根,妳這小蜘蛛、妳這不懷好意的蛇。是妳殺死了他。」
梅根看起來完全不為所動。「別傻了。」
「看得出來妳經過一番思考。我們來了,具有相同機會、動機也廣泛得足以涵蓋雙方的兩名嫌疑犯,所以妳只要否認一切,罪責就會歸咎於我。問題的癥結就在於我們之中誰比較會演戲,而我們都知道答案是什麼。」
「如我方才所指出,亨利,你整個下午都坐在這裡看守你的殺戮,所以我怎樣才下得了手?」
「妳只要否認一切,講到喉嚨乾掉就好,沒必要陷害我、假造證據。妳從頭到尾就是打這如意算盤,對吧?警察來了後會發現這裡有兩個外國人跟一具屍體,其中之一是我,既挫敗又講不清楚,試圖主張可能有人頭下腳上爬過天花板以在不被發現的情況下上樓。另一個則是妳,完美自制,否認一切──一朵英國玫瑰奮起對抗粗野男子。我們都知道他們會相信誰,而我還能怎麼說服他們?我在這天殺的國家裡甚至點不了一杯咖啡。」
「這是你的理論,是吧?那我怎麼從你旁邊溜過去,亨利?像你說的在天花板爬行嗎?還是你在剛剛這二十秒內又想出了什麼更具說服力的說法?」
「我沒必要。這問題不對。」他起身走到窗戶旁,這會兒不怕她了。「頂樓確實牢牢上鎖,只能從樓梯出入,也確實我自從午餐後,也自從邦尼上去他房間後整個下午都坐在這,連廁所都沒去上。不過也確實我們剛回來時我走得又熱又一身髒,曾經去梳洗一番。我留下妳獨自在這,就是這裡。我回來時妳不曾移動。我清洗臉、脖子和雙手花了九到十分鐘,這時間太短暫,我幾乎完全忘記。但話說回來,把小刀捅進某人背上要花多長時間?」
「那是幾小時前的事了。」
「三小時前。那妳覺得他死了多久?血都流到整條走廊了。」
「那時候我們才剛進屋,他剛上樓,甚至還沒睡著吧。」
「對,但他很醉,睡不睡根本沒差。他一趴上床就完全無法防備了。」
「所以就這樣,是吧?你指控我謀殺他?」
亨利微笑,為自己的邏輯感到驕傲。「沒錯,我就是。」
「你這可悲、幸災樂禍的傻瓜。他死了,而你想拿來當遊戲?我知道是你幹的,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也可以問妳相同問題。」
梅根停下,把整件事想過一遍,拿刀的手放鬆了。亨利眺望窗外,透過髒玻璃看見泛著光暈的山丘。他正以他的無畏嘲弄她,這是一種主張他權威的方式。
「我懂你在做什麼了,我現在看得一清二楚。這事關名聲,對吧?我是演員,像這樣的醜聞會毀掉我。就算只是再雞毛蒜皮的懷疑,我的名聲都將破滅。你覺得我的損失會比你大,所以不得不配合?」
他旋過身,被身後的明亮日光晒紅。「妳以為跟妳的職業名聲有關?並不是什麼都跟妳的演藝生涯有關好嗎,梅根。」
她咬住下脣。「不,我也不覺得你會承認,對吧。你首先讓我見識你可以多頑強,然後呢?當你讓我相信我贏不了、我如果不配合就會毀掉我的演藝生涯後,你再提出你的計畫。你會想出某種故事再要求我替你佐證。如果真是這樣,你還是直接跟我說實話比較明智。」
他嘆氣,搖了搖頭。「真不知道妳為什麼一直說這些。跟妳解釋過這場犯罪的各種情況了,但就算是最棒的偵探,面對徹底否認也沒轍。我煩得都快扯光我的頭髮了,事情就是這樣了,不過我不覺得光頭適合我。」
她盯著他。大約有一分鐘的時間兩人都不發一語。最後她終於把刀放在身旁的桌上,刀尖轉到一旁不再對準他。
「好吧。拿起你的吉他接著彈吧。我指控你,你也指控我,顯然我們就是置身這種處境。但如果你以為我是那種會屈服、只因為一個男人說天空是綠色就被說服的女人,那你可是低估我了。」
「如果妳以為妳只要站穩立場、搧搧睫毛,我就會像隻鳥兒般唱歌,妳才是高估了妳自己的魅力。」
「噢,」梅根眨眼,「但我以為你還愛我?」
亨利在她對面的椅子坐下。「我是,所以這才如此令人瘋狂。只要妳承認是妳殺的,我不管如何都會原諒妳。」
「那我們來談談以前沒談過的事。」她又拿起小刀,而他眼中閃過一絲真實的恐懼。「你擁有狂暴的一面,亨利。我看過你喝醉,也看過你只是不喜歡陌生人看我的方式就跟他們打起來,還看過你呼喊、尖叫、砸玻璃。這些你也一概否認嗎?」
他注視地板。「不,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那你有見過我那樣嗎?」
「或許沒有,但妳也可以很殘酷。」
「尖牙利嘴殺不了人的。」
他聳肩。「所以我脾氣暴躁。這是妳不想嫁給我的原因嗎?」
「不盡然,但也不算加分就是了。」
「我那時喝了很多酒。」
「你午餐時也喝了很多。」
「不多。沒以前多。」
「顯然夠多了。」
亨利嘆氣。「如果我想殺邦尼,我會用更好的方法。」
「亨利,我知道是你,我們都知道。你到底想說服我相信什麼?我發瘋了?」
「我也可以說一樣的話,不是嗎?」
「不,你不能。」她揮刀刺入她的椅子扶手,刀刺穿墊襯卡在木頭裡。「邦尼在樓上像個水龍頭般滴滴答答,我們卻只是在這裡吵架。要是警察發現我們整個下午在做什麼,他們會怎麼想?」
「真是場惡夢。」
梅根翻白眼。「另一個爛譬喻。」
「好吧,如果我們要這樣度過這下午,那我想要手上有杯酒。想加入嗎?」
「你有病。」
他幫自己倒了一杯威士忌。
半小時過去,什麼也沒改變,他們反覆著這個情況數次,每次都沒有結果。
亨利喝完酒,把空杯捧在眼前,透過酒杯凝視變形、空洞的起居室,手一面左右移動。梅根看著他,不知道他的注意力怎麼會這麼容易分散。
亨利回頭看她。「我要再來一杯然後就結束,妳想加入嗎?」
門窗依然緊閉,起居室內令人窒息,彷彿是一項他們彼此都同意的自我懲罰。
她點頭。「我跟你喝一杯。」
他哼了一聲,走到酒櫃旁,從威士忌長頸瓶倒出兩大杯酒。當然了,酒是溫的。他一手拿起一杯,有節奏地旋了旋,將另一杯遞給她。她看見這分量瞪大了眼,三分之二滿。「最後一杯酒。」他說。
「如果我們都沒有要認罪,」梅根說,「我們應該要討論一下接下來該做什麼。是不是根本沒必要牽扯上警察?沒人知道我們在這,或許我們乾脆趁夜離開就好。」
亨利靜靜啜飲他的酒。他們就這樣在那兒坐了幾分鐘。梅根一手掩著她的杯子,終於舉到嘴邊時,她在酒杯碰到嘴脣前停住。「我怎麼知道你有沒有下毒?」
「我們可以交換。」
她聳肩。這段對話似乎並不值得接續下去。她啜了一小口,「味道不錯。」而他只是用一種令她不安的方式靜靜注視著她。「換個角度來說,為了避免疑慮。」他嘆氣,將自己的酒杯交給她;她接下,也把自己的酒杯給他。
他氣力用盡地坐回椅子上,舉杯。「敬邦尼。」
「敬邦尼。」
威士忌如即將到來的落日那樣橘紅熱烈。亨利又拿起吉他,重新彈起先前那個笨拙的調子。「我們回到起點了。」他嘆氣。
「如我所說,我們需要討論接下來該怎麼辦。」
「妳要我說我們可以就這樣逃跑,假裝自己沒來過?跟上次一樣。那自始至終就是妳的計畫,對吧?」
「你為什麼要這樣對我?」梅根放下酒杯,搖了搖頭。「是因為我取消我們的訂婚嗎?但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
啜飲酒漿已成為亨利用來拖延對話的主要手段,然而面對這個問題,他卻認真相對,並點燃一根菸。「那我就再說一次吧,梅根,我還愛妳。」
「很高興知道你還愛我。」她期待地看著他。「你開始覺得頭暈了嗎,亨利?」
剛開始他困惑不解,接著瞥了一眼他的酒杯。他已幾乎喝乾,只剩下最後半吋高度。他伸手想要拿杯子,卻發現左臂幾乎麻痺,姿態詭異又笨拙的手將杯子打落地面,酒杯隨即破碎,在白地磚留下一個棕色圓圈。「妳做了什麼?」
菸從他口中掉落,墜入吉他琴身內,一縷盤繞的煙從琴弦間裊裊上升。她的臉除了些微擔心外不露情感。
「梅根。」
他往前滾下椅子,半邊身體麻痺,吉他彈到一旁。他俯臥白地板,毫無節奏地顫抖,唾液在他下巴前方的地磚上聚積。
「說謊是這樣的,亨利。」她起身聳立他身旁。「一旦開始就無法停止,無論謊言帶你到哪,你都只能跟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