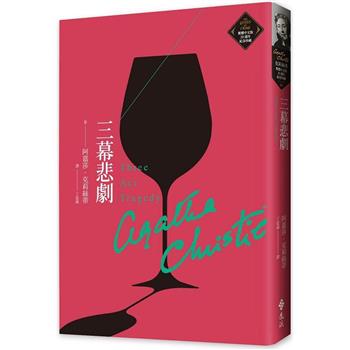01鴉巢屋
沙特衛先生坐在鴉巢屋的露台上,看著屋主查爾斯.卡萊特爵士從海邊爬上小路。
鴉巢屋是一幢漂亮的現代平房,木質結構不到一半,沒有三角牆,沒有三流建築師愛不釋手的累贅設計。這幢簡潔而堅固的白色建築物,看起來比實際體積小。這房子得名於它的位置,居高臨下,可俯瞰整個魯茅斯海港。露台由結實的圍欄保護著,從露台一角望去,有一堵懸崖峭壁直落海底。鴉巢屋離城裡有一英里路程,這條路從內地過來,之後在海岸高處迂迴盤旋。如果徒步跋涉,七分鐘就可走完查爾斯爵士此刻正在攀登的陡峭漁夫小徑。
查爾斯爵士是個體格健壯、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他穿著一條灰色的法蘭絨舊褲,上身套著白色毛衣。他走起路來有點兒左右搖擺,常常把雙手半插在口袋裡。每次他一出現,十個人中便有九個會說:「真像個退役的海軍軍官。絕對錯不了。」只有目光敏銳的最後那一位,會稍有保留,對某種模糊的假想心存質疑。旋及,一個畫面便會陡然在他們心中浮起:一個舞台上船的甲板,懸掛著厚實豪華的帷幕,將船的一部分遮蓋。有一個人站在甲板上,那就是查爾斯.卡萊特。代表陽光的燈照射在他的身上,他雙手半握,步履輕盈,說話時聲音爽朗宏亮,帶有英國水兵和紳士的腔調。
「不,先生,」查爾斯.卡萊特說道,「恐怕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沉重的帷幕唰的一聲落了下來,燈光突然向上直射,管弦樂隊奏起了最新式的切分音曲調。已到後台的女孩們頭上紮著大蝴蝶結,她們說著:「有巧克力嗎?有檸檬嗎?」《大海的呼喚》第一幕就這樣結束。
查爾斯.卡萊特在劇中扮演副艦長范史東。
沙特衛先生微笑著,從他所站的有利位置向下俯視。
沙特衛先生是一個乾瘦的小個子男人,就像個小瓦罐。他是位美術和戲劇的贊助人,脾氣固執但好相處,挺愛充紳士派頭。凡是重要一點的私人宴會和社交場合,總會有他的身影;「還有沙特衛先生」這一段字,總是名列在來賓名單的末尾。他還是一個智慧過人、看待人和事物目光銳利的觀察家。
只見他自言自語道:「完全想不到。是呀,真的完全想不到。」
露台上響起了腳步聲,沙特衛先生轉過頭去。是那位灰白頭髮的大個子。他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他歲值中年,嚴肅又慈祥的臉清楚地表明他的職業,他就是哈利大街的醫生巴塞羅繆.史全奇爵士。他是個著名的精神病專家,最近在英國女王誕辰時榮獲爵士頭銜。
他把椅子拉到沙特衛先生旁邊說:「你想不到什麼啊?說出來聽聽。」
沙特衛報之一笑,一心注視著正從下面的小徑往上爬的那個人。
「想不到查爾斯爵士竟能耐得住這種──呃,放逐生涯。」
「哎呀,我也沒有想到!」醫生把頭朝後一仰,大笑起來。「我從小就認識查爾斯。我們一起進牛津大學。他從來不改本色──在私下的生活中,他是一個比在舞台上還要出色的演員!查爾斯總是在演戲,而且已到不能自拔的程度,這是他的第二天性。他不是走出一間屋子,而是在『退場』。他辦事常常遵循著已經擬定的計畫,還有,他喜歡變換角色,這誰也沒有他在行。兩年前,他從戲劇界退休,說是希望過一種簡樸的鄉間生活,遠離塵囂,沉溺於往昔對大海的夢幻。於是他來到這兒,修建了這幢房子,亦即他理想中的鄉間小屋─浴室就有三間,還有一大堆時髦的裝潢!沙特衛,我和你一樣,認為他的這種生活持續不了多久。畢竟查爾斯是個凡人,他需要觀眾。兩三個退職船長,一票女人,再加上一個牧師,那可玩不出什麼好戲來。我想,這位『對大海懷有深情的簡樸紳士』,頂多在這兒待上六個月,隨後,他就會開始厭惡這個角色。我看,下一個角色會是一個厭世的蒙地卡羅旅人,或是一位蘇格蘭高地的地主。總之,他是一名演技高超的演員。」
醫生停了下來。他的話猶如一篇冗長的演講,說話時眼睛充滿激情和喜悅,並望著從下面小徑上來的那位主角,只是那位仁兄對此絲毫未察覺。再過幾分鐘,他就要到他們身邊。
巴塞羅繆爵士繼續說:「不管怎麼說,我們似乎錯了。簡樸生活自有它的魅力。」
「一個戲劇化的人,有時會讓人家誤解。」沙特衛先生指出,「人們很難相信他的所作所為出自真心。」
醫生點了點頭。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說,「完全正確。」
當查爾斯.卡萊特爬上露台前的階梯時,人們發出一陣歡呼聲。
「『米拉貝爾』超乎想像的好。」他說,「沙特衛先生,你也應該來試一試。」
沙特衛搖搖頭。每每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時,他的胃總不聽使喚,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今天早晨,他從臥房的窗口遠望米拉貝爾號輪船,看到它航行時刮起了一陣大風,沙特衛先生不禁打心底感謝著上帝。
查爾斯爵士走到客廳的窗口,要僕人給他送杯酒來。
「你應當加入我們的行列,托利。」他對老朋友巴塞羅繆爵士說,「難道你準備消磨半輩子,淨坐在哈利大街告訴你的病人說,生活在大海波濤之上對他們的身體會有多好?」
「當醫生的最大好處是,」巴塞羅繆爵士說,「他不必遵循自己的忠告。」
查爾斯爵士大笑起來。他仍然在不知不覺地扮演某種角色──一個屹立在船頭、海風撲面的海軍軍官。他是個儀表堂堂、體格勻稱健美的男子,一張瘦削的臉,兩鬢的幾根灰髮使他更加與眾不同。一看就會知道他是個紳士,其次你會猜他是演員。
「你是一個人去的嗎?」醫生問道。
「不。」查爾斯爵士轉身,從一個衣著整潔的接待女僕的托盤裡,拿了一杯酒。「我有個幫手。具體地說,是蛋蛋小姐。」
他的聲音裡隱約流露著不自在。這使得沙特衛先生猛然抬起頭來。
「是蛋蛋.莉頓.戈爾小姐嗎?她對航行略知一二,是吧?」
查爾斯爵士懊悔地苦笑了起來。
「她讓我感到自己是個徹底的大笨蛋。但是我有進步了──多虧有了她。」
沙特衛思緒萬端。「真讓人納悶……也許,戈爾小姐就是使他不知疲倦的因素……那個年齡啊,危險的年齡。女孩子在那種年紀……」
查爾斯爵士繼續說:「世上無論什麼都比不上大海,比不上陽光、風和海洋,還有一間可以像家一樣居住的簡樸茅舍。」
他滿懷喜悅地看著身後那幢白屋。裡面有三間浴室,所有的臥房都有冷、熱水供應,有最新式的中央暖氣系統,有最時髦的電器,有一群接待女僕、打掃的傭人、司機和廚娘。查爾斯爵士對簡樸生活的解釋,似乎言過其實了。
這時,一個其醜無比的高個兒女人從房裡出來,走到他們身邊。
「早安,查爾斯爵士。」她又朝另外兩位輕輕點頭。「早安。這是晚餐的菜單,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想換換口味。」
查爾斯爵士接過菜單咕噥說:「我來瞧瞧……甜瓜、俄式菜湯、新鮮鯖魚、松雞、幸運蛋奶酥、黛安娜乳酪麵包……夠了,這很好,米蕾小姐。客人們會搭四點半的火車到達。」
「我已讓霍蓋特安排了。對了,查爾斯爵士,如果可以,今晚我最好一起用餐。」
查爾斯爵士顯得有點驚訝,但還是客氣地說:「我很樂意,米蕾小姐。但是,呃……」
米蕾小姐平靜地搶先解釋道:「查爾斯爵士,如果我不跟你們一起吃飯,餐桌上就正好是十三個人。這兒有很多人都很迷信。」
她說話的語氣讓人覺得,若要她一輩子的每個晚上都與十二個人共餐,她也無所懼。她繼續說:「一切已安排妥當。我要霍蓋特駕車去接瑪麗夫人和巴賓頓一家。沒問題吧?」
「當然,我才要交代你這件事呢。」
米蕾小姐退了出去,她那張凸眉凹眼的臉上,帶著一絲得意的微笑。
查爾斯爵士恭敬地說:「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常常擔心她會把我給慣壞了。」
「是個高效率的模範。」史全奇說。
「她跟了我六年。」查爾斯爵士說,「她原是我在倫敦的祕書。到了這兒,她則成了一位頂瓜瓜的管家,像時鐘走針一樣有效率地管理這地方。現在,她就要離開了。」
「為什麼?」
「她說,」查爾斯爵士含糊地摸摸鼻子。「她說她有個病弱的母親。我不相信,她那樣的女人根本不會有什麼母親。她可以像發電機一樣自動產生能量。不,一定有別的原因。」
「絕對有可能。」巴塞羅繆爵士說,「人們一直在議論她。」
「議論她?」那演員睜大眼睛說,「議論什麼?」
「親愛的查爾斯,你知道『議論』指的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她……跟我?我跟那種長相的女人?她年齡也不小了吧?」
「她也許還不到五十歲。」
「我想她有五十歲了。」查爾斯爵士思忖道,「老實說,托利,你注意過她的臉嗎?同樣是一雙眼睛、一個鼻子和一張嘴巴,可是這不是一張臉,不是一張女性的臉。就算是街坊裡最愛造謠生事的老貓,也絕不會將風流韻事與這樣一張臉聯繫在一起。」
「你太小看我們這位英國老處女了。」
查爾斯爵士搖了搖頭。
「我才不相信哩。米蕾小姐身上蘊藏著某種威嚴,就算她是個老處女也不能否認這點。她是貞潔和尊嚴的化身,是個絕頂能幹的女人。我選擇祕書向來都是很挑剔的。」
「聰明的人。」
查爾斯爵士沉思了一會兒。巴塞羅繆爵士改變話題問道:「今天下午來了什麼客人?」
「第一位,安琪。」
「是安琪拉.薩克利夫嗎?太好了。」
沙特衛先生饒有興趣地側過身去。他極想知道這次宴會的成員。安琪拉.薩克利夫是個著名女演員,不年輕了,但仍然受觀眾喜愛。人們讚揚她的聰慧和魅力,甚至,還稱她為愛倫.泰瑞的接班人。
「還有戴克斯一家。」
沙特衛又一次點了點頭。戴克斯太太是安博森有限公司的設計師。那是個生意興隆的時裝公司,你常可在演出節目表上看到「布蘭克小姐的首演服裝是由安博森公司所承製」這類說明。她的丈夫是戴克斯船長,用他自己的賽馬行話來說,他是一匹黑馬。他花了大把時間在賽馬場上。這幾年來,他一頭栽進大英野外障礙賽馬會。他曾經惹過一些麻煩,但儘管謠言四起,誰也不清楚內情,沒有人問過他──公開問過他,但是,總之一提到佛萊迪.戴克斯,人們就會揚起眉頭。
「還有安東尼.亞斯特,那個劇作家。」
「沒錯。」沙特衛先生說,「她寫過《單行道》。我看了兩遍。劇本很具震撼力。」
他頗得意地展現自己知道安東尼.亞斯特是個女人。
「就是呀。」查爾斯爵士說,「我忘了她的真名。大概姓威爾斯吧。我只見過她一面。我請她來,好讓安琪拉高興高興。大概就是這些人了──我是指這次的晚宴。」
「本地人有邀請嗎?」醫生問道。
「哦,對,本地人!有啊,巴賓頓夫婦。他是個牧師,一位好人,不太像個牧師。他的妻子是個不錯的女人,常教導我一些園藝知識。還有瑪麗夫人和蛋蛋要來。哦,還有一位叫曼德斯的小夥子,是個記者還是什麼的,這年輕人長得滿帥的。這就是宴會的全班人馬。」
沙特衛是個辦事井井有條的人。他正在數人數。
「薩克利夫小姐,一個;戴克斯夫婦,三個;安東尼.亞斯特,四個;瑪麗夫人和她女兒,六個;牧師和他的妻子,八個;那年輕人,九個;加上我們幾個,共十二個人。查爾斯爵士,不是你就是米蕾小姐數錯了。」
「米蕾小姐不可能弄錯。」查爾斯爵士肯定地說,「那個女人永遠都不會出差錯的。讓我來算一算……是的,你是對的,我漏了一位客人,剛好一下子想不起他來了。」他噗嗤一聲笑了起來。「這位先生似乎不是很受歡迎,他是我所見過最自負的人,鬼靈精一個。」
沙特衛眨了眨眼睛。他一直秉持一個觀點:演員是世界上最最虛榮的人,他認為查爾斯爵士也不例外。所以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使他感到好笑。
「誰是這個自以為是的人?」他問道。
「是個古怪的矮冬瓜。」查爾斯爵士說,「但也是個大大有名的矮冬瓜。你們可能聽說過他:赫丘勒.白羅,一個比利時人。」
「是那位偵探吧?」沙特衛說,「我見過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確是號人物。」查爾斯爵士說。
「我還沒見過他。」巴塞羅繆爵士說,「不過經常聽到他的傳聞。不久前他退休了,是吧?也許我聽到的多是謠傳。嗨,查爾斯,我希望這個週末我們這兒不會發生什麼案件。」
「怎麼會呢?就因為有位偵探要來?托利,你可別胡說。」
「嗯,只是這正好符合我的觀點。」
「你的觀點是什麼,醫生?」沙特衛問道。
「案件找人,不是人找案件。為什麼有的人生活精采刺激,而有的人卻平淡無奇?這是因為環境的不同嗎?完全不是。有人可以遊遍天涯海角而平安無事,可是在他到達某地的前一週,當地才發生過大屠殺;而或許在他離開後的第二天,又突然爆發地震,或是他差一點要去乘坐的小船會遭到船難。可是,另外一個住巴爾罕的男人,每天都在城裡進進出出,卻不幸大難臨頭,他可能被捲進勒索、桃色糾紛或飛車黨搶劫的事端之中。還有一些人,即使乘坐設施完備的湖上小船,還是難逃翻船的厄運。同樣的道理,像赫丘勒.白羅那樣的人,他不必去尋找犯罪案件,案件就會自己找上門來。」
「照你這麼說,」沙特衛說道,「米蕾小姐最好是來參加我們的宴會,這麼一來,就不會變成十三個人同桌吃飯。」
「好吧。」查爾斯爵士灑脫地說,「托利,如果你熱中於此,你就儘管去設想你的凶殺案吧。反正我只下一個結論:我自己不會成為那具屍體。」
三個人都笑了起來,邁步走進屋裡。
02飯前意外
沙特衛生活中的主要興趣是人。總括言之,他對女人比對男人更感興趣。以一個男人而言,沙特衛對女人知之頗深。在他的性格裡有一種女性氣質,這使他能夠更深入地觀察女性的內心世界。他身邊的女人都十分信賴他,但也不是很看重他。對此,他有時會感到不是滋味。他總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小包廂裡看戲,而不是在劇中親自扮演一個角色。然而,旁觀者的角色實際上最適合他不過了。
這天晚上,他坐在一間面對露台的大房間裡──一家現代裝潢公司精巧地將它裝飾成宛若船上特等艙的氣派─他最感興趣的是辛西亞.戴克斯頭上那染髮劑的顏色。那是一種全新的顏色,他猜想那必定是直接從巴黎進口的,那銅綠色能製造一種俏皮討喜的效果。要描述戴克斯太太的相貌簡直不可能。她是個高個子女人,絕對符合當下時興的形象。她的脖子和手臂有著夏天鄉間女人們那種黝黑的膚色,誰也不知道這是天然生成,還是人工所造。她的銅綠色頭髮梳理成優雅而新穎的樣式,只有倫敦第一流的理髮師才有這種技藝。她的眉毛向上彎曲,睫毛畫黑,臉部經過精心修飾,原來平平的嘴形變得輪廓鮮明,彎曲可人。這一切都映襯著她身上那件美妙絕倫、高雅脫俗的深藍色晚裝。那衣服剪裁得簡單大方(儘管與這種場合格格不入),布料質地也非同一般,色澤淡雅,卻有暗光閃爍。
「靈巧的女人。」沙特衛說著,眼睛凝視著她,流露出讚賞的神情。「真想知道她的真實樣貌。」
他指的是心裡的想法,而不是外貌。
她談話時總拖長聲調,這種語氣時下最為流行。
「我親愛的,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事好像可能又好像不可能。這件事可不是如此,這事滲透得很。」
這是目前的一個新詞。什麼事都「滲透得很」。
查爾斯爵士興致勃勃地搖著雞尾酒,一邊與安琪拉.薩克利夫交談。她是高個的灰髮女人,有一張頑皮的嘴和一雙漂亮的眼睛。
戴克斯對著巴塞羅繆.史全奇說:「人人都知道老拉迪斯伯恩出了什麼錯。整個賽馬場都清楚。」
他說話時把嗓門提高,聲音短促。他是個小個頭男人,皮膚發紅,有褐斑,嘴上留一小撮短鬚,還有一雙不安分的眼睛。
沙特衛旁邊坐著威爾斯小姐。她的劇本《單行道》被譽為近年倫敦戲劇界最詼諧機智、最震撼人心的劇目之一。威爾斯小姐身材修長瘦削,下巴後縮,頭髮蓬鬆凌亂。她臉上架著夾鼻眼鏡,身穿極其柔軟的雪紡綢洋裝,嗓門很高,卻缺乏抑揚頓挫。
「我去了法國南方。」她說,「但是說真的,我不太喜歡那兒。這麼說似乎很不友善。當然啦,你知道,這對我的寫作很有好處─去看看正在流行的事物。」
沙特衛心想:「真是個可憐的人!事業的成功使她不得不遠離她精神的歸宿─伯恩茅斯的寓所。那才是她喜歡居住的地方。」對於作品和作者之間的明顯反差,他很感驚奇。安東尼.亞斯特在劇本裡體現了一種「當代男性」的風格,但你在威爾斯小姐的身上能感覺到它絲毫的展現嗎?他注意到夾鼻眼鏡後面的那雙淡藍色眼睛異常機敏聰慧,而此時,這雙眼睛也以一種明察秋毫的目光投向他,使他有點心神不安。威爾斯小姐像是在用心觀察他。
查爾斯爵士正在倒雞尾酒。
「讓我幫您弄一杯吧。」沙特衛突然縱身而起。
威爾斯小姐咯咯咯地笑了。
「我倒樂意為你調製一杯。」她說。
門開了,達珮宣布瑪麗.莉頓.戈爾夫人、巴賓頓夫婦和莉頓.戈爾小姐到達。
沙特衛給威爾斯小姐送去一杯雞尾酒。然後悄悄溜到瑪麗.莉頓.戈爾夫人身邊。正如前面所述,他對名銜有特殊的興趣。
然而,撇開他喜愛趨附名流的習性不談,他倒是真心喜歡某位高尚的女士。不消說,那就是瑪麗夫人。
她只是個寡婦,丈夫拋下她離世而去時,留下了一個三歲小女孩。此後,她來到魯茅斯,住進一幢小平房,一個忠實的女僕一直陪伴著她。她是個高䠷清瘦的女人,看上去比她五十五歲的年紀還要老。她談吐溫柔,略帶羞怯,十分溺愛女兒,常為她擔憂害怕。
不知為什麼,人們通常把赫米歐妮.莉頓.戈爾叫做「蛋蛋」。她與母親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她屬於比較熱情開朗的類型。在沙特衛先生看來,她並不漂亮,但毫無疑問有一種魅力。他想,這種魅力在於她那朝氣蓬勃的活力。她比屋子裡所有的人都要活潑得多。她有一頭黑髮,灰色眼睛,中等身材。也許是她那鬈曲齊頸的短髮、灰色眼珠直勾勾看人的目光、曲線柔美的臉頰和具有感染力的笑聲,令她全身散發著一種奔放不羈的青春活力。
她站著與剛剛到達的奧利佛.曼德斯說話。
「真難想像你為什麼會覺得航海很無聊。你以前很喜歡航海啊。」
「蛋蛋,我親愛的,人是會長大的!」他慢吞吞地說著,並揚起眉頭。
這是個挺帥的年輕人,大約有二十五歲。在他俊俏的臉上,有點世故的表情,還有某種……是一種異國的味道吧?某種非英國的氣質。
還有一個人在看著奧利佛.曼德斯。是位小個子的男人,蛋形頭,留著很特殊的鬍鬚。沙特衛喚起自己對赫丘勒.白羅先生的記憶。這位矮個子男人總是笑容可掬。沙特衛懷疑他總刻意誇大他的異國氣質。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要說:「你們把我當成滑稽戲裡的小丑嗎?以為我會為你們演齣喜劇嗎?那好,就讓你們如願以償!」
但是,赫丘勒.白羅的眼睛此刻已不再閃閃發光。他顯得有些不快和憂傷。
魯茅斯的教區牧師史蒂芬.巴賓頓走過來與瑪麗夫人和沙特衛談話。他已六十開外,一雙仁慈的眼睛暗淡無光。言談舉止已缺乏銳氣和自信。他對沙特衛先生說:「能與查爾斯爵士為伍,我們實在很幸運。他非常仁慈、慷慨,真是個好鄰居。相信瑪麗夫人也有同感。」
瑪麗夫人微笑道:「我非常喜歡他。他的成功沒有寵壞了他。」她笑得更開心了。「他在很多方面還像個孩子。」
這時女僕端著一盤雞尾酒走了過來。沙特衛想道,女人的母性多麼的永無止境啊!由於他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對這種性格很是讚賞。
「喝杯雞尾酒吧,媽媽們。」蛋蛋小姐舉著酒杯對她們揮一揮手說,「只限一杯。」
「謝謝你,親愛的。」瑪麗夫人溫柔地說。
「我想,」巴賓頓先生說,「我妻子應該會允許我喝一杯。」
接著他發出慈祥牧師特有的笑聲。
沙特衛從遠處凝望著巴賓頓太太,她正和查爾斯爵士認真地談著種花施肥的事。
「她的眼力很好。」他想。
巴賓頓太太是個高大的女人。她穿著隨性,精力充沛,不拘小節。正如查爾斯.卡萊特曾經說過的,她是個好女人。
「告訴我,」瑪麗夫人將身子朝前傾了傾說,「那位年輕女子是誰?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在跟她說話;就是穿綠衣服那一位。」
「她是個劇作家,安東尼.亞斯特。」
「什麼?就是那個看上去像是患了貧血症的小姐嗎?哦!」她控制住自己。「我太沒眼光了。這可真是令人吃驚。她的樣子不像──我是說,她看上去倒像一個笨手笨腳的托兒所保母。」
她對威爾斯小姐這種恰如其分的描述,使得沙特衛笑了起來。此刻巴賓頓先生那雙溫和的近視眼在屋裡四處探望。他啜了一口雞尾酒,在嘴裡品嘗著酒的滋味。沙特衛饒富興味地想著,巴賓頓一定不常喝雞尾酒,在他看來,也許喝雞尾酒是一種時髦玩意兒……他看來不喜歡喝。巴賓頓先生勉強又喝了一口,臉上的肌肉開始有點扭曲了。他說:「是那邊那位女士嗎?哦,我的天……」
他伸手放在喉嚨上。
蛋蛋小姐的聲音響了起來。「奧利佛,你這個狡猾的夏洛克……」
沙特衛想道:「當然,正是如此,他可不是什麼異鄉人,而是個猶太人!」
他們是很相配的一對,兩人都這麼年輕漂亮……當然也容易吵嘴──總之,是很健康的象徵。
旁邊的聲響突然打斷他的思緒。巴賓頓先生剛從座位上站起來,正在前後搖晃。他的面部出現了痙攣。
蛋蛋小姐清脆的尖叫驚動了全屋子的人。在這之前,瑪麗夫人已經站起身來,焦急地伸出了手。
「哎呀!」蛋蛋叫道,「巴賓頓先生不好了。」
巴塞羅繆.史全奇爵士連忙跑過來,一把扶住這突然發病的人,並將他攙扶到客廳一側的長沙發上。其他人也圍了上來,緊張地幫著醫生。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
兩分鐘之後,史全奇醫生站直身子,搖了搖頭。他知道此時不宜拐彎抹角,於是他直截了當地說:「很遺憾,他死了……」
沙特衛先生坐在鴉巢屋的露台上,看著屋主查爾斯.卡萊特爵士從海邊爬上小路。
鴉巢屋是一幢漂亮的現代平房,木質結構不到一半,沒有三角牆,沒有三流建築師愛不釋手的累贅設計。這幢簡潔而堅固的白色建築物,看起來比實際體積小。這房子得名於它的位置,居高臨下,可俯瞰整個魯茅斯海港。露台由結實的圍欄保護著,從露台一角望去,有一堵懸崖峭壁直落海底。鴉巢屋離城裡有一英里路程,這條路從內地過來,之後在海岸高處迂迴盤旋。如果徒步跋涉,七分鐘就可走完查爾斯爵士此刻正在攀登的陡峭漁夫小徑。
查爾斯爵士是個體格健壯、皮膚黝黑的中年男子。他穿著一條灰色的法蘭絨舊褲,上身套著白色毛衣。他走起路來有點兒左右搖擺,常常把雙手半插在口袋裡。每次他一出現,十個人中便有九個會說:「真像個退役的海軍軍官。絕對錯不了。」只有目光敏銳的最後那一位,會稍有保留,對某種模糊的假想心存質疑。旋及,一個畫面便會陡然在他們心中浮起:一個舞台上船的甲板,懸掛著厚實豪華的帷幕,將船的一部分遮蓋。有一個人站在甲板上,那就是查爾斯.卡萊特。代表陽光的燈照射在他的身上,他雙手半握,步履輕盈,說話時聲音爽朗宏亮,帶有英國水兵和紳士的腔調。
「不,先生,」查爾斯.卡萊特說道,「恐怕我不能回答你的問題。」
沉重的帷幕唰的一聲落了下來,燈光突然向上直射,管弦樂隊奏起了最新式的切分音曲調。已到後台的女孩們頭上紮著大蝴蝶結,她們說著:「有巧克力嗎?有檸檬嗎?」《大海的呼喚》第一幕就這樣結束。
查爾斯.卡萊特在劇中扮演副艦長范史東。
沙特衛先生微笑著,從他所站的有利位置向下俯視。
沙特衛先生是一個乾瘦的小個子男人,就像個小瓦罐。他是位美術和戲劇的贊助人,脾氣固執但好相處,挺愛充紳士派頭。凡是重要一點的私人宴會和社交場合,總會有他的身影;「還有沙特衛先生」這一段字,總是名列在來賓名單的末尾。他還是一個智慧過人、看待人和事物目光銳利的觀察家。
只見他自言自語道:「完全想不到。是呀,真的完全想不到。」
露台上響起了腳步聲,沙特衛先生轉過頭去。是那位灰白頭髮的大個子。他拉了一張椅子坐下。他歲值中年,嚴肅又慈祥的臉清楚地表明他的職業,他就是哈利大街的醫生巴塞羅繆.史全奇爵士。他是個著名的精神病專家,最近在英國女王誕辰時榮獲爵士頭銜。
他把椅子拉到沙特衛先生旁邊說:「你想不到什麼啊?說出來聽聽。」
沙特衛報之一笑,一心注視著正從下面的小徑往上爬的那個人。
「想不到查爾斯爵士竟能耐得住這種──呃,放逐生涯。」
「哎呀,我也沒有想到!」醫生把頭朝後一仰,大笑起來。「我從小就認識查爾斯。我們一起進牛津大學。他從來不改本色──在私下的生活中,他是一個比在舞台上還要出色的演員!查爾斯總是在演戲,而且已到不能自拔的程度,這是他的第二天性。他不是走出一間屋子,而是在『退場』。他辦事常常遵循著已經擬定的計畫,還有,他喜歡變換角色,這誰也沒有他在行。兩年前,他從戲劇界退休,說是希望過一種簡樸的鄉間生活,遠離塵囂,沉溺於往昔對大海的夢幻。於是他來到這兒,修建了這幢房子,亦即他理想中的鄉間小屋─浴室就有三間,還有一大堆時髦的裝潢!沙特衛,我和你一樣,認為他的這種生活持續不了多久。畢竟查爾斯是個凡人,他需要觀眾。兩三個退職船長,一票女人,再加上一個牧師,那可玩不出什麼好戲來。我想,這位『對大海懷有深情的簡樸紳士』,頂多在這兒待上六個月,隨後,他就會開始厭惡這個角色。我看,下一個角色會是一個厭世的蒙地卡羅旅人,或是一位蘇格蘭高地的地主。總之,他是一名演技高超的演員。」
醫生停了下來。他的話猶如一篇冗長的演講,說話時眼睛充滿激情和喜悅,並望著從下面小徑上來的那位主角,只是那位仁兄對此絲毫未察覺。再過幾分鐘,他就要到他們身邊。
巴塞羅繆爵士繼續說:「不管怎麼說,我們似乎錯了。簡樸生活自有它的魅力。」
「一個戲劇化的人,有時會讓人家誤解。」沙特衛先生指出,「人們很難相信他的所作所為出自真心。」
醫生點了點頭。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說,「完全正確。」
當查爾斯.卡萊特爬上露台前的階梯時,人們發出一陣歡呼聲。
「『米拉貝爾』超乎想像的好。」他說,「沙特衛先生,你也應該來試一試。」
沙特衛搖搖頭。每每乘船渡過英吉利海峽時,他的胃總不聽使喚,讓他吃了不少苦頭。今天早晨,他從臥房的窗口遠望米拉貝爾號輪船,看到它航行時刮起了一陣大風,沙特衛先生不禁打心底感謝著上帝。
查爾斯爵士走到客廳的窗口,要僕人給他送杯酒來。
「你應當加入我們的行列,托利。」他對老朋友巴塞羅繆爵士說,「難道你準備消磨半輩子,淨坐在哈利大街告訴你的病人說,生活在大海波濤之上對他們的身體會有多好?」
「當醫生的最大好處是,」巴塞羅繆爵士說,「他不必遵循自己的忠告。」
查爾斯爵士大笑起來。他仍然在不知不覺地扮演某種角色──一個屹立在船頭、海風撲面的海軍軍官。他是個儀表堂堂、體格勻稱健美的男子,一張瘦削的臉,兩鬢的幾根灰髮使他更加與眾不同。一看就會知道他是個紳士,其次你會猜他是演員。
「你是一個人去的嗎?」醫生問道。
「不。」查爾斯爵士轉身,從一個衣著整潔的接待女僕的托盤裡,拿了一杯酒。「我有個幫手。具體地說,是蛋蛋小姐。」
他的聲音裡隱約流露著不自在。這使得沙特衛先生猛然抬起頭來。
「是蛋蛋.莉頓.戈爾小姐嗎?她對航行略知一二,是吧?」
查爾斯爵士懊悔地苦笑了起來。
「她讓我感到自己是個徹底的大笨蛋。但是我有進步了──多虧有了她。」
沙特衛思緒萬端。「真讓人納悶……也許,戈爾小姐就是使他不知疲倦的因素……那個年齡啊,危險的年齡。女孩子在那種年紀……」
查爾斯爵士繼續說:「世上無論什麼都比不上大海,比不上陽光、風和海洋,還有一間可以像家一樣居住的簡樸茅舍。」
他滿懷喜悅地看著身後那幢白屋。裡面有三間浴室,所有的臥房都有冷、熱水供應,有最新式的中央暖氣系統,有最時髦的電器,有一群接待女僕、打掃的傭人、司機和廚娘。查爾斯爵士對簡樸生活的解釋,似乎言過其實了。
這時,一個其醜無比的高個兒女人從房裡出來,走到他們身邊。
「早安,查爾斯爵士。」她又朝另外兩位輕輕點頭。「早安。這是晚餐的菜單,不知道你們是不是想換換口味。」
查爾斯爵士接過菜單咕噥說:「我來瞧瞧……甜瓜、俄式菜湯、新鮮鯖魚、松雞、幸運蛋奶酥、黛安娜乳酪麵包……夠了,這很好,米蕾小姐。客人們會搭四點半的火車到達。」
「我已讓霍蓋特安排了。對了,查爾斯爵士,如果可以,今晚我最好一起用餐。」
查爾斯爵士顯得有點驚訝,但還是客氣地說:「我很樂意,米蕾小姐。但是,呃……」
米蕾小姐平靜地搶先解釋道:「查爾斯爵士,如果我不跟你們一起吃飯,餐桌上就正好是十三個人。這兒有很多人都很迷信。」
她說話的語氣讓人覺得,若要她一輩子的每個晚上都與十二個人共餐,她也無所懼。她繼續說:「一切已安排妥當。我要霍蓋特駕車去接瑪麗夫人和巴賓頓一家。沒問題吧?」
「當然,我才要交代你這件事呢。」
米蕾小姐退了出去,她那張凸眉凹眼的臉上,帶著一絲得意的微笑。
查爾斯爵士恭敬地說:「她是個了不起的女人。我常常擔心她會把我給慣壞了。」
「是個高效率的模範。」史全奇說。
「她跟了我六年。」查爾斯爵士說,「她原是我在倫敦的祕書。到了這兒,她則成了一位頂瓜瓜的管家,像時鐘走針一樣有效率地管理這地方。現在,她就要離開了。」
「為什麼?」
「她說,」查爾斯爵士含糊地摸摸鼻子。「她說她有個病弱的母親。我不相信,她那樣的女人根本不會有什麼母親。她可以像發電機一樣自動產生能量。不,一定有別的原因。」
「絕對有可能。」巴塞羅繆爵士說,「人們一直在議論她。」
「議論她?」那演員睜大眼睛說,「議論什麼?」
「親愛的查爾斯,你知道『議論』指的是什麼。」
「你的意思是說她……跟我?我跟那種長相的女人?她年齡也不小了吧?」
「她也許還不到五十歲。」
「我想她有五十歲了。」查爾斯爵士思忖道,「老實說,托利,你注意過她的臉嗎?同樣是一雙眼睛、一個鼻子和一張嘴巴,可是這不是一張臉,不是一張女性的臉。就算是街坊裡最愛造謠生事的老貓,也絕不會將風流韻事與這樣一張臉聯繫在一起。」
「你太小看我們這位英國老處女了。」
查爾斯爵士搖了搖頭。
「我才不相信哩。米蕾小姐身上蘊藏著某種威嚴,就算她是個老處女也不能否認這點。她是貞潔和尊嚴的化身,是個絕頂能幹的女人。我選擇祕書向來都是很挑剔的。」
「聰明的人。」
查爾斯爵士沉思了一會兒。巴塞羅繆爵士改變話題問道:「今天下午來了什麼客人?」
「第一位,安琪。」
「是安琪拉.薩克利夫嗎?太好了。」
沙特衛先生饒有興趣地側過身去。他極想知道這次宴會的成員。安琪拉.薩克利夫是個著名女演員,不年輕了,但仍然受觀眾喜愛。人們讚揚她的聰慧和魅力,甚至,還稱她為愛倫.泰瑞的接班人。
「還有戴克斯一家。」
沙特衛又一次點了點頭。戴克斯太太是安博森有限公司的設計師。那是個生意興隆的時裝公司,你常可在演出節目表上看到「布蘭克小姐的首演服裝是由安博森公司所承製」這類說明。她的丈夫是戴克斯船長,用他自己的賽馬行話來說,他是一匹黑馬。他花了大把時間在賽馬場上。這幾年來,他一頭栽進大英野外障礙賽馬會。他曾經惹過一些麻煩,但儘管謠言四起,誰也不清楚內情,沒有人問過他──公開問過他,但是,總之一提到佛萊迪.戴克斯,人們就會揚起眉頭。
「還有安東尼.亞斯特,那個劇作家。」
「沒錯。」沙特衛先生說,「她寫過《單行道》。我看了兩遍。劇本很具震撼力。」
他頗得意地展現自己知道安東尼.亞斯特是個女人。
「就是呀。」查爾斯爵士說,「我忘了她的真名。大概姓威爾斯吧。我只見過她一面。我請她來,好讓安琪拉高興高興。大概就是這些人了──我是指這次的晚宴。」
「本地人有邀請嗎?」醫生問道。
「哦,對,本地人!有啊,巴賓頓夫婦。他是個牧師,一位好人,不太像個牧師。他的妻子是個不錯的女人,常教導我一些園藝知識。還有瑪麗夫人和蛋蛋要來。哦,還有一位叫曼德斯的小夥子,是個記者還是什麼的,這年輕人長得滿帥的。這就是宴會的全班人馬。」
沙特衛是個辦事井井有條的人。他正在數人數。
「薩克利夫小姐,一個;戴克斯夫婦,三個;安東尼.亞斯特,四個;瑪麗夫人和她女兒,六個;牧師和他的妻子,八個;那年輕人,九個;加上我們幾個,共十二個人。查爾斯爵士,不是你就是米蕾小姐數錯了。」
「米蕾小姐不可能弄錯。」查爾斯爵士肯定地說,「那個女人永遠都不會出差錯的。讓我來算一算……是的,你是對的,我漏了一位客人,剛好一下子想不起他來了。」他噗嗤一聲笑了起來。「這位先生似乎不是很受歡迎,他是我所見過最自負的人,鬼靈精一個。」
沙特衛眨了眨眼睛。他一直秉持一個觀點:演員是世界上最最虛榮的人,他認為查爾斯爵士也不例外。所以這種五十步笑百步的情形使他感到好笑。
「誰是這個自以為是的人?」他問道。
「是個古怪的矮冬瓜。」查爾斯爵士說,「但也是個大大有名的矮冬瓜。你們可能聽說過他:赫丘勒.白羅,一個比利時人。」
「是那位偵探吧?」沙特衛說,「我見過他,是個了不起的人物。」
「他的確是號人物。」查爾斯爵士說。
「我還沒見過他。」巴塞羅繆爵士說,「不過經常聽到他的傳聞。不久前他退休了,是吧?也許我聽到的多是謠傳。嗨,查爾斯,我希望這個週末我們這兒不會發生什麼案件。」
「怎麼會呢?就因為有位偵探要來?托利,你可別胡說。」
「嗯,只是這正好符合我的觀點。」
「你的觀點是什麼,醫生?」沙特衛問道。
「案件找人,不是人找案件。為什麼有的人生活精采刺激,而有的人卻平淡無奇?這是因為環境的不同嗎?完全不是。有人可以遊遍天涯海角而平安無事,可是在他到達某地的前一週,當地才發生過大屠殺;而或許在他離開後的第二天,又突然爆發地震,或是他差一點要去乘坐的小船會遭到船難。可是,另外一個住巴爾罕的男人,每天都在城裡進進出出,卻不幸大難臨頭,他可能被捲進勒索、桃色糾紛或飛車黨搶劫的事端之中。還有一些人,即使乘坐設施完備的湖上小船,還是難逃翻船的厄運。同樣的道理,像赫丘勒.白羅那樣的人,他不必去尋找犯罪案件,案件就會自己找上門來。」
「照你這麼說,」沙特衛說道,「米蕾小姐最好是來參加我們的宴會,這麼一來,就不會變成十三個人同桌吃飯。」
「好吧。」查爾斯爵士灑脫地說,「托利,如果你熱中於此,你就儘管去設想你的凶殺案吧。反正我只下一個結論:我自己不會成為那具屍體。」
三個人都笑了起來,邁步走進屋裡。
02飯前意外
沙特衛生活中的主要興趣是人。總括言之,他對女人比對男人更感興趣。以一個男人而言,沙特衛對女人知之頗深。在他的性格裡有一種女性氣質,這使他能夠更深入地觀察女性的內心世界。他身邊的女人都十分信賴他,但也不是很看重他。對此,他有時會感到不是滋味。他總覺得自己好像只是在小包廂裡看戲,而不是在劇中親自扮演一個角色。然而,旁觀者的角色實際上最適合他不過了。
這天晚上,他坐在一間面對露台的大房間裡──一家現代裝潢公司精巧地將它裝飾成宛若船上特等艙的氣派─他最感興趣的是辛西亞.戴克斯頭上那染髮劑的顏色。那是一種全新的顏色,他猜想那必定是直接從巴黎進口的,那銅綠色能製造一種俏皮討喜的效果。要描述戴克斯太太的相貌簡直不可能。她是個高個子女人,絕對符合當下時興的形象。她的脖子和手臂有著夏天鄉間女人們那種黝黑的膚色,誰也不知道這是天然生成,還是人工所造。她的銅綠色頭髮梳理成優雅而新穎的樣式,只有倫敦第一流的理髮師才有這種技藝。她的眉毛向上彎曲,睫毛畫黑,臉部經過精心修飾,原來平平的嘴形變得輪廓鮮明,彎曲可人。這一切都映襯著她身上那件美妙絕倫、高雅脫俗的深藍色晚裝。那衣服剪裁得簡單大方(儘管與這種場合格格不入),布料質地也非同一般,色澤淡雅,卻有暗光閃爍。
「靈巧的女人。」沙特衛說著,眼睛凝視著她,流露出讚賞的神情。「真想知道她的真實樣貌。」
他指的是心裡的想法,而不是外貌。
她談話時總拖長聲調,這種語氣時下最為流行。
「我親愛的,這是不可能的。我的意思是,有些事好像可能又好像不可能。這件事可不是如此,這事滲透得很。」
這是目前的一個新詞。什麼事都「滲透得很」。
查爾斯爵士興致勃勃地搖著雞尾酒,一邊與安琪拉.薩克利夫交談。她是高個的灰髮女人,有一張頑皮的嘴和一雙漂亮的眼睛。
戴克斯對著巴塞羅繆.史全奇說:「人人都知道老拉迪斯伯恩出了什麼錯。整個賽馬場都清楚。」
他說話時把嗓門提高,聲音短促。他是個小個頭男人,皮膚發紅,有褐斑,嘴上留一小撮短鬚,還有一雙不安分的眼睛。
沙特衛旁邊坐著威爾斯小姐。她的劇本《單行道》被譽為近年倫敦戲劇界最詼諧機智、最震撼人心的劇目之一。威爾斯小姐身材修長瘦削,下巴後縮,頭髮蓬鬆凌亂。她臉上架著夾鼻眼鏡,身穿極其柔軟的雪紡綢洋裝,嗓門很高,卻缺乏抑揚頓挫。
「我去了法國南方。」她說,「但是說真的,我不太喜歡那兒。這麼說似乎很不友善。當然啦,你知道,這對我的寫作很有好處─去看看正在流行的事物。」
沙特衛心想:「真是個可憐的人!事業的成功使她不得不遠離她精神的歸宿─伯恩茅斯的寓所。那才是她喜歡居住的地方。」對於作品和作者之間的明顯反差,他很感驚奇。安東尼.亞斯特在劇本裡體現了一種「當代男性」的風格,但你在威爾斯小姐的身上能感覺到它絲毫的展現嗎?他注意到夾鼻眼鏡後面的那雙淡藍色眼睛異常機敏聰慧,而此時,這雙眼睛也以一種明察秋毫的目光投向他,使他有點心神不安。威爾斯小姐像是在用心觀察他。
查爾斯爵士正在倒雞尾酒。
「讓我幫您弄一杯吧。」沙特衛突然縱身而起。
威爾斯小姐咯咯咯地笑了。
「我倒樂意為你調製一杯。」她說。
門開了,達珮宣布瑪麗.莉頓.戈爾夫人、巴賓頓夫婦和莉頓.戈爾小姐到達。
沙特衛給威爾斯小姐送去一杯雞尾酒。然後悄悄溜到瑪麗.莉頓.戈爾夫人身邊。正如前面所述,他對名銜有特殊的興趣。
然而,撇開他喜愛趨附名流的習性不談,他倒是真心喜歡某位高尚的女士。不消說,那就是瑪麗夫人。
她只是個寡婦,丈夫拋下她離世而去時,留下了一個三歲小女孩。此後,她來到魯茅斯,住進一幢小平房,一個忠實的女僕一直陪伴著她。她是個高䠷清瘦的女人,看上去比她五十五歲的年紀還要老。她談吐溫柔,略帶羞怯,十分溺愛女兒,常為她擔憂害怕。
不知為什麼,人們通常把赫米歐妮.莉頓.戈爾叫做「蛋蛋」。她與母親幾乎沒有相似之處。她屬於比較熱情開朗的類型。在沙特衛先生看來,她並不漂亮,但毫無疑問有一種魅力。他想,這種魅力在於她那朝氣蓬勃的活力。她比屋子裡所有的人都要活潑得多。她有一頭黑髮,灰色眼睛,中等身材。也許是她那鬈曲齊頸的短髮、灰色眼珠直勾勾看人的目光、曲線柔美的臉頰和具有感染力的笑聲,令她全身散發著一種奔放不羈的青春活力。
她站著與剛剛到達的奧利佛.曼德斯說話。
「真難想像你為什麼會覺得航海很無聊。你以前很喜歡航海啊。」
「蛋蛋,我親愛的,人是會長大的!」他慢吞吞地說著,並揚起眉頭。
這是個挺帥的年輕人,大約有二十五歲。在他俊俏的臉上,有點世故的表情,還有某種……是一種異國的味道吧?某種非英國的氣質。
還有一個人在看著奧利佛.曼德斯。是位小個子的男人,蛋形頭,留著很特殊的鬍鬚。沙特衛喚起自己對赫丘勒.白羅先生的記憶。這位矮個子男人總是笑容可掬。沙特衛懷疑他總刻意誇大他的異國氣質。他那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要說:「你們把我當成滑稽戲裡的小丑嗎?以為我會為你們演齣喜劇嗎?那好,就讓你們如願以償!」
但是,赫丘勒.白羅的眼睛此刻已不再閃閃發光。他顯得有些不快和憂傷。
魯茅斯的教區牧師史蒂芬.巴賓頓走過來與瑪麗夫人和沙特衛談話。他已六十開外,一雙仁慈的眼睛暗淡無光。言談舉止已缺乏銳氣和自信。他對沙特衛先生說:「能與查爾斯爵士為伍,我們實在很幸運。他非常仁慈、慷慨,真是個好鄰居。相信瑪麗夫人也有同感。」
瑪麗夫人微笑道:「我非常喜歡他。他的成功沒有寵壞了他。」她笑得更開心了。「他在很多方面還像個孩子。」
這時女僕端著一盤雞尾酒走了過來。沙特衛想道,女人的母性多麼的永無止境啊!由於他屬於維多利亞時代的人,對這種性格很是讚賞。
「喝杯雞尾酒吧,媽媽們。」蛋蛋小姐舉著酒杯對她們揮一揮手說,「只限一杯。」
「謝謝你,親愛的。」瑪麗夫人溫柔地說。
「我想,」巴賓頓先生說,「我妻子應該會允許我喝一杯。」
接著他發出慈祥牧師特有的笑聲。
沙特衛從遠處凝望著巴賓頓太太,她正和查爾斯爵士認真地談著種花施肥的事。
「她的眼力很好。」他想。
巴賓頓太太是個高大的女人。她穿著隨性,精力充沛,不拘小節。正如查爾斯.卡萊特曾經說過的,她是個好女人。
「告訴我,」瑪麗夫人將身子朝前傾了傾說,「那位年輕女子是誰?我們進來的時候,你在跟她說話;就是穿綠衣服那一位。」
「她是個劇作家,安東尼.亞斯特。」
「什麼?就是那個看上去像是患了貧血症的小姐嗎?哦!」她控制住自己。「我太沒眼光了。這可真是令人吃驚。她的樣子不像──我是說,她看上去倒像一個笨手笨腳的托兒所保母。」
她對威爾斯小姐這種恰如其分的描述,使得沙特衛笑了起來。此刻巴賓頓先生那雙溫和的近視眼在屋裡四處探望。他啜了一口雞尾酒,在嘴裡品嘗著酒的滋味。沙特衛饒富興味地想著,巴賓頓一定不常喝雞尾酒,在他看來,也許喝雞尾酒是一種時髦玩意兒……他看來不喜歡喝。巴賓頓先生勉強又喝了一口,臉上的肌肉開始有點扭曲了。他說:「是那邊那位女士嗎?哦,我的天……」
他伸手放在喉嚨上。
蛋蛋小姐的聲音響了起來。「奧利佛,你這個狡猾的夏洛克……」
沙特衛想道:「當然,正是如此,他可不是什麼異鄉人,而是個猶太人!」
他們是很相配的一對,兩人都這麼年輕漂亮……當然也容易吵嘴──總之,是很健康的象徵。
旁邊的聲響突然打斷他的思緒。巴賓頓先生剛從座位上站起來,正在前後搖晃。他的面部出現了痙攣。
蛋蛋小姐清脆的尖叫驚動了全屋子的人。在這之前,瑪麗夫人已經站起身來,焦急地伸出了手。
「哎呀!」蛋蛋叫道,「巴賓頓先生不好了。」
巴塞羅繆.史全奇爵士連忙跑過來,一把扶住這突然發病的人,並將他攙扶到客廳一側的長沙發上。其他人也圍了上來,緊張地幫著醫生。然而,一切都無濟於事……
兩分鐘之後,史全奇醫生站直身子,搖了搖頭。他知道此時不宜拐彎抹角,於是他直截了當地說:「很遺憾,他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