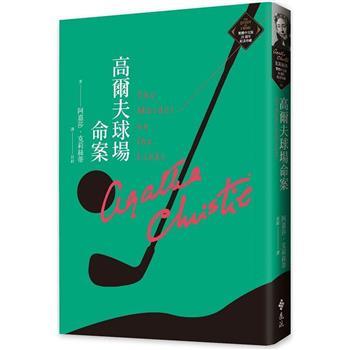01灰姑娘
我知道有這麼一則為人共知的軼事,它的內容大概是:一位年輕作家為了把自己的故事開頭寫得獨具一格、具說服力些,以吸引那些全然麻痺的編輯注意,便寫了如下的句子:「『該死!』公爵夫人說道。」
剛好,我這故事的開頭也是一樣,只不過說這句話的不是一位公爵夫人罷了。
那是六月初的某一天,我在巴黎辦完一些事,正乘著早車回倫敦去。在倫敦,我仍跟我的老朋友──前比利時警探赫丘勒.白羅──賃屋合住。
開往加來的特快車空得出奇,在我乘坐的這節車廂中,只有我與另外一位旅客。我離開旅館時是急匆匆的,所以在好不容易趕上火車、正忙著清點行李是否齊全的時候,火車就開動了。在此之前,我幾乎不曾去注意另外一位同車乘客,直到此刻,我才忽然想起還有這麼個人和我在同一車廂裡。
她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放下車窗,把頭探了出去,一會兒又縮回頭,短促但很使勁地喊了一聲:「該死!」
我是個保守的人,認為女人就該有女人的樣子!時下那些神經質的女孩子,從早到晚跳著爵士舞,嘴上抽根煙囪似的香菸,用的語言連比林斯蓋漁市的女人聽了也會感到害臊,我一向看不慣這種人。
我微微皺著眉,一抬頭,看到了一張俏麗、任性的臉,她頭上戴著一頂小巧的紅帽,濃密又烏溜溜的鬈髮蓋住了耳朵。我推測她最多不過十七歲,但是她臉上搽著粉,嘴上的口紅塗得不能再紅了。
她一點也不感到窘迫,反而回頭看著我,還做了一個表情十足的鬼臉。
「哎喲,可把這位善良的紳士嚇壞了!」她假裝對著眼前想像中的觀眾說,「很抱歉,我言語粗魯,太不像個小姐樣。不過,啊,上帝,這是有原因的!你可知道我唯一的妹妹不見了?」
「真的?」我客氣地說,「好不幸啊!」
「這個人看我們不順眼!」女孩自言自語地說,「他……不僅對我完全看不順眼,對我妹妹也是這樣……這太不公平,他連她的人影都還沒見過呢!」
我剛張開嘴,她卻先開了口。「別說了!誰也不愛我!我只好到花園裡去找小蟲吃。嗚嗚,我這下子可完啦!」
她把自己藏在一份法文報紙的後面。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她兩隻眼睛偷偷越過報紙上方窺視著我,我忍不住微微一笑。她馬上就把報紙扔在一邊,愉快地縱情大笑了起來。
「我就知道你不像看起來的那樣傻。」她喊叫著說。
她的笑聲富有感染力,我也不禁笑了起來,儘管我對「傻」這個用詞頗不以為然。
「嗨!這下我們算是朋友啦,」那女孩說,「好,說你對我妹妹的事感到難過……」
「我好難過啊!」
「那才是個好孩子!」
「讓我把話說完。我還要補一句:雖然我好難過,不過沒有她我還能忍受。」我微微地行了一個禮。
可是這個令人無法捉摸的小女孩蹙起眉頭,搖了搖頭。
「別說啦!我倒寧願瞧你那副自以為是、看不順眼的樣子。看你的表情就好像在說:『這人不是和我們同一類的。』這點你倒是猜對了。不過,當心點兒,現在還很難說呢!不是每個人都能辨別出誰是真公爵夫人,誰是假公爵夫人。瞧,我想我又把你嚇唬住了!說你是個老古板,可一點都不假,我也不在乎,就算再多幾個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也還受得了。我恨的是那種粗魯蠻橫的人,那簡直會使我發瘋。」
她使勁搖著頭。
「你發瘋是什麼樣子?」我帶著笑問。
「一個如假包換的小魔鬼!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或做什麼!有一次我差點兒把一個傢伙殺了,不過他也是活該嘛!」
「哎,」我央求說,「你可別跟我生氣呀。」
「我不會跟你生氣。我第一眼見到你就喜歡你了。但你這麼一副看人不順眼的態度,我想我們是永遠也不會成為朋友。」
「嗯,我們已經是朋友了。說說你自己吧。」
「我是個演員,不……可不是你所想的那種。從我還是六歲小女孩時,就在木板上翻筋斗了。」
「你的意思是──」我感到迷惑不解。
「你從沒看過馬戲團的童星表演嗎?」
「哦,我懂了!」
「我出生在美國,可是大部分時間是在英國度過的。現在我們有一檔新節目……」
「我們?」
「我妹妹和我。有歌唱有舞蹈,還有繞口令,再穿插些老把戲,整個節目精采別致,每次演出都很成功,很有賺頭喔……」
我這位新朋友探著身子,滔滔不絕地講著,她的好多用語對我來說簡直是不知所云。但我發現自己對她愈來愈感興趣。她像個好奇寶寶及成年女性的綜合體,讓人難以理解。她就如她自己所說的能言善道,很能幹,又可以照顧自己,然而她那誠實的生活態度,及立定目標要「出人頭地」的決心,又帶著一種純真無邪。
火車過了亞眠,這個地名勾起了我許多回憶,而我的同伴好像也感受到我心中在想著什麼似的。
「想起戰爭了嗎?」
我點點頭。
「我想,你已經走過來了?」
「還算好,我受過一次傷。索姆戰役後,我因傷遣返,現在是一位議員的私人祕書。」
「哇,那可是要花心思的工作!」
「不,才沒有。實際上,沒有什麼工作可做。通常每天只要花兩小時就處理好了,而且十分枯燥乏味。說實在的,要不是我還有別的嗜好可以寄託,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別告訴我你在收集昆蟲!」
「不是,我跟一個非常有趣的人合住。他是比利時人,曾是一名警探。現在他在倫敦定居,當私人偵探,他辦案非常出色。這小個子非常了不起,已經多次證明凡是警察解決不了的事情,總是難不倒他。」
我的同伴睜大了眼睛聽著。
「這真有趣,不是嗎?我好喜歡犯罪的故事,只要有偵探電影,我一定去看;若是報上有刊登謀殺案,那我簡直要把報紙吞了下去。」
「你記得『史岱爾莊謀殺案』嗎?」
「我想想……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被下毒的那起案件?在艾塞克斯的某個地方發生?」
我點點頭。
「那是白羅偵辦的第一個重大案件。要不是他,那凶手早就逍遙法外了。那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破案行動!」
我愈談愈起勁,乾脆把案件從頭到尾講了一遍,最後還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凱旋式收場。那女孩聽得著了迷。事實上我們聊得太專心,以致連火車進了加來站都差點不知道呢!
我找了兩個腳夫,我們一起走下月台,我的同伴伸出她的手。
「再見,以後我一定會多注意自己的言行。」
「唔,讓我在船上照顧你吧?」
「我也許不上船了,因我還得看看我妹妹到底有沒有上火車。總之,謝謝你了。」
「呃,不過我們應該還有見面的機會吧?難道你連你的姓名也不告訴我?」當她轉身離去時,我喊道。
她回過頭來望著我。
「灰姑娘。」她說著笑了。
我根本想不出會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再看到這位灰姑娘。
02一封求救信
第二天早上九點零五分,我走進我們共用的客廳吃早餐。我的朋友白羅跟往常一樣,分秒不差,正在輕輕敲他的第二顆雞蛋。
我進來時,他微笑著向我打招呼。
「你睡得還不錯吧?從可怕的跨海之旅恢復過來啦!今天早晨你幾乎如往常般準時。恕我冒犯──你的領帶打歪了,讓我把它調整一下。」
白羅這個人,我在別處已經描繪過:他的個子非常矮小,五呎四吋高,蛋形頭微微偏向一邊,興奮時兩眼閃耀著綠光,兩道整齊略帶僵硬的軍人式髭鬚,讓人印象深刻。他外表整潔,注重穿著。對於任何東西都非常講究整潔,只要看到有件飾品擺偏了,或是哪兒有那麼一點點灰塵,甚至誰的衣服稍欠整齊,這小個兒簡直就像活受罪般地痛苦,非得調整一番,心裡才舒坦。講究條理、方法是他的信條。他對諸如腳印、菸灰等這些看得見的證據是相當蔑視的,總認為光憑這些東西永遠也不可能幫偵探解決問題。每當他發表見解後,往往會輕叩自己的蛋形腦袋,那洋洋自得的樣子頗為可笑,接著還會再自鳴得意地歸功於:「真本事是在這裡面的這些小小灰色腦細胞,mon ami,永遠別忘記這些小小灰色腦細胞。」
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懶懶地回答白羅說,從加來到多佛那種一小時的渡海航程,可不是用「可怕」二字可一語帶過的。
「有什麼有趣的信件嗎?」我問道。
白羅搖搖頭,看起來不太滿意。
「我還沒看,可是這年頭已沒有什麼有趣的事了。那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智慧型犯罪,現在可找不到啦。」
他失望地搖晃著腦袋,我哈哈大笑起來。
「振作起來吧,白羅,時運會改變的。把信拆開看看,說不定有一起重大案件正在地平線上浮現呢。」
白羅微笑著,拿起他那把乾淨的拆信刀,裁開放在他餐盤旁的幾枚信封。
「帳單,又是一張帳單,看來我年紀愈大,卻變得愈揮霍無度了。啊哈!傑派寄來的一張字條。」
「是嗎?」我豎起耳朵,這位蘇格蘭警場的警探,曾經不止一次介紹給我們一些有趣的案件。
「他只是(按照他的方式)向我道謝,因為我在『艾比士威案』上曾經給了他一些小小的指點,讓他找到正確方向,我很高興那對他有幫助。」
白羅繼續平靜地讀信。
「有人建議我對本地的童子軍做一次演講;弗法諾伯爵夫人說,如果我去看她,她將非常感激──不用懷疑,八成又要送我一隻小狗。現在是最後的一封信了,啊……」
我警覺到他的聲調有變化,抬頭望了一眼。白羅正在仔細讀著信,沒多久他就把信拿給了我。
「我的朋友,這信有點不尋常,你自己讀吧。」
信是寫在一張外國信箋上,字跡粗大又頗有特色。
法國梅蘭維鎮索爾梅村熱內維芙別墅
親愛的先生:
我需要偵探的幫助,而且基於某些原因(以後將奉告),我並不想求助於當地警察。我曾多次聽說過你,公眾的評價也足以證明先生你不僅才智卓越,而且是個謹慎從事的人。關於細節,我不準備在信中多談。
由於我手中掌握某項祕密,因此終日惶惶不安,我深信危險已迫在眉睫,因此我懇求你火速渡海前來法國。如蒙告知抵達時間,我將派車前往加來迎接。先生若將手頭各項案件暫時擱下,以我的委託為優先,我將感激不盡,並願付出相當的補償金額。我或許需要你一段時間的協助,必要時可能還得有勞先生去聖地牙哥一趟,我曾在該地住過多年,先生所需的一切費用,我將樂意照付。
情況緊急,再次強調。
P.T.雷諾謹上
在簽名下面有一行潦草得幾乎難以辨認的字跡:「看在上帝的份上,速來!」
我把信遞還給他,心裡興奮得心跳也加快了。
「總算出現不尋常的事情了。」
「是呀,的確如此。」白羅沉思地說。
「你當然會去囉。」我接著說。
白羅點點頭,仍沉思著。最後他似乎打定了主意,望了一下鐘,表情顯得很嚴肅。
「我的朋友,看來我們得快點了。去歐陸的特快車十一點在維多利亞車站開出。不過別激動,還有時間呢,我們還可以討論十分鐘。你要跟我一起去,nest-ce pas?」
「呃……」
「你自己跟我說過,接下來幾個星期你的老闆用不著你。」
「噢,那倒不成問題,只是這位雷諾先生明顯暗示這是件私事啊!」
「謝啦,雷諾先生那裡我會應付的。仔細想想,這個姓氏好像挺耳熟的。」
「有位大名鼎鼎的南美百萬富翁,名字就叫雷諾,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一定是他沒錯,這就可以解釋信中為什麼會提到聖地牙哥了。聖地牙哥在智利,智利又在南美。啊,我們進展得不錯嘛!那行附言你注意到沒有?你的感覺如何?」
我思索著。
「很明顯,他寫信時,盡量克制著情感,可是到最後他的自制力崩潰了,衝動之下,草草寫下了這些絕望的字眼。」
可是我的朋友卻用力地搖著頭。
「你錯了。你沒有看見簽名的墨跡是黑的,那附言的顏色卻很淡?」
「是嗎?」我疑惑地問。
「Mon Dieu,我的朋友,用用你小小的灰色腦細胞吧,那不是再明顯不過的嗎?雷諾先生寫了信後,他沒有使用吸墨紙,就仔細地再讀了一遍。接著,不是出於一時衝動,而是經過謹慎考慮後,加上了最後幾個字,然後再用吸墨紙吸的。」
「那又是為什麼?」
「當然是為了讓我以為情況是如你所說的那樣。」
「什麼?」
「總之,就是要我非去法國不可。他重新讀過信後感到不滿意,因為語氣不夠有力。」
他停了一下,兩眼閃耀著內心激動時常發出的綠色光芒,接著又輕聲說:「我的朋友,既然附言是經過冷靜思考後鄭重加上去的,而不是出於一時衝動,情況一定很緊急,那我們得盡快趕到他那裡去。」
「梅蘭維鎮,」我沉思低語著,「我想,我聽說過這個地方。」
白羅點點頭。
「那是個安靜而別致的小地方,就在布洛涅到加來的中間,我猜雷諾在英國有別墅。」
「是啊,如果我沒記錯,他有一座別墅在拉特蘭門;在赫特福德郡的某處鄉村也有一所大豪宅。可是我對他所知不多,因為他在社交圈中並不活躍。我相信他在倫敦股市控有大量的南美股份,而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智利和阿根廷。」
「呃,反正我們等著聽他本人詳述始末就是了。來,我們收拾行李吧!各人帶個小手提箱,叫輛計程車到維多利亞車站。」
十一點鐘,我們從維多利亞出發前往多佛。啟程前,白羅給雷諾發了一封電報,告訴他我們抵達加來的時間。
在船上,我知道此時最好不要去打擾我的朋友。天氣真好,海面正如成語所說的「風平浪靜」,因此當白羅竟面帶微笑的和我在加來一起下船時,我並不感到意外。可是隨即而來的情況卻令人大失所望,因為沒有汽車來接我們。白羅認為這是電報傳遞延誤所致。
「我們就雇輛車吧。」他興致勃勃地說。
幾分鐘後,我們就坐著一輛破舊不堪的計程車,嘎吱嘎吱地一路顛簸著朝梅蘭維的方向駛去。
我興致很好,可是我那小個子朋友卻嚴肅地望著我。
「你這興奮的模樣就像蘇格蘭人所謂的『回光返照』,海斯汀,這是災禍的預兆!」
「胡扯,不過看來,你的感覺與我的不同。」
「是不同,我感到害怕。」
「害怕什麼?」
「我說不上來,但是我有預感……je ne sais quoi!」
他說話的態度凝重,我不由自主地也受到了影響。
「我有一種感覺,」他慢條斯理地說道,「這將是一起重大事件─一個不易解決、耗費時間的棘手問題。」
我本來還要追問下去,就在此時我們駛入了梅蘭維小鎮。我們放慢了車速,詢問去熱內維芙別墅的方向。
「穿過小鎮,先生,筆直地往前走。熱內維芙別墅離馬路的另一邊大約還有半哩路。那是一座面海的大別墅,不會找不到的。」
我們向指路人道過謝,就離鎮往前駛去,在路邊的岔道那兒我們又停下了。一個農夫正向我們走來,我們準備等他靠近些再問路。在路旁有一座小小的別墅,但看起來太小、太破舊,不像是我們要找的那座。在我們等候時,小別墅的門開了,一個女孩走了出來。
那農夫正要走過我們身旁時,司機從座位上探身問路。
「熱內維芙別墅嗎?就在這條路右邊沒幾步,先生。要不是這彎道,你就看見它了。」
司機向他道了謝,再次開動車子。女孩仍站在那兒,一隻手按在門上,望著我們。我的眼睛被她吸引住了。凡是美的事物我總是非常愛慕欣賞,這女孩是這麼美,不論誰看見她都會想和她說話。她身材修長,有如天仙般的姿態,一頭金髮在陽光中熠熠發光。我自忖著,這是我所見過最美的女孩了。當車子搖晃著駛上崎嶇不平的道路時,我還回過頭去望著她。
「啊,白羅,」我驚呼道,「你看見那位年輕的美仙子了吧?」
白羅揚起了雙眉。
「Ça commence!」他低聲說,「你已經認定那是一位仙子!」
「別開玩笑了,難道她不是嗎?」
「也許吧,但我沒注意。」
「你不是也有看到她嗎?」
「我的朋友,很少有兩個人看到同一事物的感受會是相同的。比方說,你看到的是位仙子,可是我……」他吞吞吐吐地說。
「嗯?」
「我看到的只不過是個眼神慌張的女孩。」白羅沉重地說道。
這時車子靠近了一扇綠色大門,我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驚呼。門前站著一個嚴肅的警官,他舉起手來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先生們,你們不能過去。」
「可是我們是來見雷諾先生的,」我喊道,「我們與他有約,這不是他的住宅嗎?」
「是,先生,不過……」
白羅探身向前。
「不過什麼?」
「雷諾先生今天早晨被謀殺了。」
我知道有這麼一則為人共知的軼事,它的內容大概是:一位年輕作家為了把自己的故事開頭寫得獨具一格、具說服力些,以吸引那些全然麻痺的編輯注意,便寫了如下的句子:「『該死!』公爵夫人說道。」
剛好,我這故事的開頭也是一樣,只不過說這句話的不是一位公爵夫人罷了。
那是六月初的某一天,我在巴黎辦完一些事,正乘著早車回倫敦去。在倫敦,我仍跟我的老朋友──前比利時警探赫丘勒.白羅──賃屋合住。
開往加來的特快車空得出奇,在我乘坐的這節車廂中,只有我與另外一位旅客。我離開旅館時是急匆匆的,所以在好不容易趕上火車、正忙著清點行李是否齊全的時候,火車就開動了。在此之前,我幾乎不曾去注意另外一位同車乘客,直到此刻,我才忽然想起還有這麼個人和我在同一車廂裡。
她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放下車窗,把頭探了出去,一會兒又縮回頭,短促但很使勁地喊了一聲:「該死!」
我是個保守的人,認為女人就該有女人的樣子!時下那些神經質的女孩子,從早到晚跳著爵士舞,嘴上抽根煙囪似的香菸,用的語言連比林斯蓋漁市的女人聽了也會感到害臊,我一向看不慣這種人。
我微微皺著眉,一抬頭,看到了一張俏麗、任性的臉,她頭上戴著一頂小巧的紅帽,濃密又烏溜溜的鬈髮蓋住了耳朵。我推測她最多不過十七歲,但是她臉上搽著粉,嘴上的口紅塗得不能再紅了。
她一點也不感到窘迫,反而回頭看著我,還做了一個表情十足的鬼臉。
「哎喲,可把這位善良的紳士嚇壞了!」她假裝對著眼前想像中的觀眾說,「很抱歉,我言語粗魯,太不像個小姐樣。不過,啊,上帝,這是有原因的!你可知道我唯一的妹妹不見了?」
「真的?」我客氣地說,「好不幸啊!」
「這個人看我們不順眼!」女孩自言自語地說,「他……不僅對我完全看不順眼,對我妹妹也是這樣……這太不公平,他連她的人影都還沒見過呢!」
我剛張開嘴,她卻先開了口。「別說了!誰也不愛我!我只好到花園裡去找小蟲吃。嗚嗚,我這下子可完啦!」
她把自己藏在一份法文報紙的後面。過了一會兒,我看到她兩隻眼睛偷偷越過報紙上方窺視著我,我忍不住微微一笑。她馬上就把報紙扔在一邊,愉快地縱情大笑了起來。
「我就知道你不像看起來的那樣傻。」她喊叫著說。
她的笑聲富有感染力,我也不禁笑了起來,儘管我對「傻」這個用詞頗不以為然。
「嗨!這下我們算是朋友啦,」那女孩說,「好,說你對我妹妹的事感到難過……」
「我好難過啊!」
「那才是個好孩子!」
「讓我把話說完。我還要補一句:雖然我好難過,不過沒有她我還能忍受。」我微微地行了一個禮。
可是這個令人無法捉摸的小女孩蹙起眉頭,搖了搖頭。
「別說啦!我倒寧願瞧你那副自以為是、看不順眼的樣子。看你的表情就好像在說:『這人不是和我們同一類的。』這點你倒是猜對了。不過,當心點兒,現在還很難說呢!不是每個人都能辨別出誰是真公爵夫人,誰是假公爵夫人。瞧,我想我又把你嚇唬住了!說你是個老古板,可一點都不假,我也不在乎,就算再多幾個像你這樣的人,我們也還受得了。我恨的是那種粗魯蠻橫的人,那簡直會使我發瘋。」
她使勁搖著頭。
「你發瘋是什麼樣子?」我帶著笑問。
「一個如假包換的小魔鬼!完全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或做什麼!有一次我差點兒把一個傢伙殺了,不過他也是活該嘛!」
「哎,」我央求說,「你可別跟我生氣呀。」
「我不會跟你生氣。我第一眼見到你就喜歡你了。但你這麼一副看人不順眼的態度,我想我們是永遠也不會成為朋友。」
「嗯,我們已經是朋友了。說說你自己吧。」
「我是個演員,不……可不是你所想的那種。從我還是六歲小女孩時,就在木板上翻筋斗了。」
「你的意思是──」我感到迷惑不解。
「你從沒看過馬戲團的童星表演嗎?」
「哦,我懂了!」
「我出生在美國,可是大部分時間是在英國度過的。現在我們有一檔新節目……」
「我們?」
「我妹妹和我。有歌唱有舞蹈,還有繞口令,再穿插些老把戲,整個節目精采別致,每次演出都很成功,很有賺頭喔……」
我這位新朋友探著身子,滔滔不絕地講著,她的好多用語對我來說簡直是不知所云。但我發現自己對她愈來愈感興趣。她像個好奇寶寶及成年女性的綜合體,讓人難以理解。她就如她自己所說的能言善道,很能幹,又可以照顧自己,然而她那誠實的生活態度,及立定目標要「出人頭地」的決心,又帶著一種純真無邪。
火車過了亞眠,這個地名勾起了我許多回憶,而我的同伴好像也感受到我心中在想著什麼似的。
「想起戰爭了嗎?」
我點點頭。
「我想,你已經走過來了?」
「還算好,我受過一次傷。索姆戰役後,我因傷遣返,現在是一位議員的私人祕書。」
「哇,那可是要花心思的工作!」
「不,才沒有。實際上,沒有什麼工作可做。通常每天只要花兩小時就處理好了,而且十分枯燥乏味。說實在的,要不是我還有別的嗜好可以寄託,我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別告訴我你在收集昆蟲!」
「不是,我跟一個非常有趣的人合住。他是比利時人,曾是一名警探。現在他在倫敦定居,當私人偵探,他辦案非常出色。這小個子非常了不起,已經多次證明凡是警察解決不了的事情,總是難不倒他。」
我的同伴睜大了眼睛聽著。
「這真有趣,不是嗎?我好喜歡犯罪的故事,只要有偵探電影,我一定去看;若是報上有刊登謀殺案,那我簡直要把報紙吞了下去。」
「你記得『史岱爾莊謀殺案』嗎?」
「我想想……是不是一位老太太被下毒的那起案件?在艾塞克斯的某個地方發生?」
我點點頭。
「那是白羅偵辦的第一個重大案件。要不是他,那凶手早就逍遙法外了。那可真是一件了不起的破案行動!」
我愈談愈起勁,乾脆把案件從頭到尾講了一遍,最後還來了一個意想不到的凱旋式收場。那女孩聽得著了迷。事實上我們聊得太專心,以致連火車進了加來站都差點不知道呢!
我找了兩個腳夫,我們一起走下月台,我的同伴伸出她的手。
「再見,以後我一定會多注意自己的言行。」
「唔,讓我在船上照顧你吧?」
「我也許不上船了,因我還得看看我妹妹到底有沒有上火車。總之,謝謝你了。」
「呃,不過我們應該還有見面的機會吧?難道你連你的姓名也不告訴我?」當她轉身離去時,我喊道。
她回過頭來望著我。
「灰姑娘。」她說著笑了。
我根本想不出會在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再看到這位灰姑娘。
02一封求救信
第二天早上九點零五分,我走進我們共用的客廳吃早餐。我的朋友白羅跟往常一樣,分秒不差,正在輕輕敲他的第二顆雞蛋。
我進來時,他微笑著向我打招呼。
「你睡得還不錯吧?從可怕的跨海之旅恢復過來啦!今天早晨你幾乎如往常般準時。恕我冒犯──你的領帶打歪了,讓我把它調整一下。」
白羅這個人,我在別處已經描繪過:他的個子非常矮小,五呎四吋高,蛋形頭微微偏向一邊,興奮時兩眼閃耀著綠光,兩道整齊略帶僵硬的軍人式髭鬚,讓人印象深刻。他外表整潔,注重穿著。對於任何東西都非常講究整潔,只要看到有件飾品擺偏了,或是哪兒有那麼一點點灰塵,甚至誰的衣服稍欠整齊,這小個兒簡直就像活受罪般地痛苦,非得調整一番,心裡才舒坦。講究條理、方法是他的信條。他對諸如腳印、菸灰等這些看得見的證據是相當蔑視的,總認為光憑這些東西永遠也不可能幫偵探解決問題。每當他發表見解後,往往會輕叩自己的蛋形腦袋,那洋洋自得的樣子頗為可笑,接著還會再自鳴得意地歸功於:「真本事是在這裡面的這些小小灰色腦細胞,mon ami,永遠別忘記這些小小灰色腦細胞。」
我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來,懶懶地回答白羅說,從加來到多佛那種一小時的渡海航程,可不是用「可怕」二字可一語帶過的。
「有什麼有趣的信件嗎?」我問道。
白羅搖搖頭,看起來不太滿意。
「我還沒看,可是這年頭已沒有什麼有趣的事了。那些重大的刑事案件、智慧型犯罪,現在可找不到啦。」
他失望地搖晃著腦袋,我哈哈大笑起來。
「振作起來吧,白羅,時運會改變的。把信拆開看看,說不定有一起重大案件正在地平線上浮現呢。」
白羅微笑著,拿起他那把乾淨的拆信刀,裁開放在他餐盤旁的幾枚信封。
「帳單,又是一張帳單,看來我年紀愈大,卻變得愈揮霍無度了。啊哈!傑派寄來的一張字條。」
「是嗎?」我豎起耳朵,這位蘇格蘭警場的警探,曾經不止一次介紹給我們一些有趣的案件。
「他只是(按照他的方式)向我道謝,因為我在『艾比士威案』上曾經給了他一些小小的指點,讓他找到正確方向,我很高興那對他有幫助。」
白羅繼續平靜地讀信。
「有人建議我對本地的童子軍做一次演講;弗法諾伯爵夫人說,如果我去看她,她將非常感激──不用懷疑,八成又要送我一隻小狗。現在是最後的一封信了,啊……」
我警覺到他的聲調有變化,抬頭望了一眼。白羅正在仔細讀著信,沒多久他就把信拿給了我。
「我的朋友,這信有點不尋常,你自己讀吧。」
信是寫在一張外國信箋上,字跡粗大又頗有特色。
法國梅蘭維鎮索爾梅村熱內維芙別墅
親愛的先生:
我需要偵探的幫助,而且基於某些原因(以後將奉告),我並不想求助於當地警察。我曾多次聽說過你,公眾的評價也足以證明先生你不僅才智卓越,而且是個謹慎從事的人。關於細節,我不準備在信中多談。
由於我手中掌握某項祕密,因此終日惶惶不安,我深信危險已迫在眉睫,因此我懇求你火速渡海前來法國。如蒙告知抵達時間,我將派車前往加來迎接。先生若將手頭各項案件暫時擱下,以我的委託為優先,我將感激不盡,並願付出相當的補償金額。我或許需要你一段時間的協助,必要時可能還得有勞先生去聖地牙哥一趟,我曾在該地住過多年,先生所需的一切費用,我將樂意照付。
情況緊急,再次強調。
P.T.雷諾謹上
在簽名下面有一行潦草得幾乎難以辨認的字跡:「看在上帝的份上,速來!」
我把信遞還給他,心裡興奮得心跳也加快了。
「總算出現不尋常的事情了。」
「是呀,的確如此。」白羅沉思地說。
「你當然會去囉。」我接著說。
白羅點點頭,仍沉思著。最後他似乎打定了主意,望了一下鐘,表情顯得很嚴肅。
「我的朋友,看來我們得快點了。去歐陸的特快車十一點在維多利亞車站開出。不過別激動,還有時間呢,我們還可以討論十分鐘。你要跟我一起去,nest-ce pas?」
「呃……」
「你自己跟我說過,接下來幾個星期你的老闆用不著你。」
「噢,那倒不成問題,只是這位雷諾先生明顯暗示這是件私事啊!」
「謝啦,雷諾先生那裡我會應付的。仔細想想,這個姓氏好像挺耳熟的。」
「有位大名鼎鼎的南美百萬富翁,名字就叫雷諾,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個人。」
「一定是他沒錯,這就可以解釋信中為什麼會提到聖地牙哥了。聖地牙哥在智利,智利又在南美。啊,我們進展得不錯嘛!那行附言你注意到沒有?你的感覺如何?」
我思索著。
「很明顯,他寫信時,盡量克制著情感,可是到最後他的自制力崩潰了,衝動之下,草草寫下了這些絕望的字眼。」
可是我的朋友卻用力地搖著頭。
「你錯了。你沒有看見簽名的墨跡是黑的,那附言的顏色卻很淡?」
「是嗎?」我疑惑地問。
「Mon Dieu,我的朋友,用用你小小的灰色腦細胞吧,那不是再明顯不過的嗎?雷諾先生寫了信後,他沒有使用吸墨紙,就仔細地再讀了一遍。接著,不是出於一時衝動,而是經過謹慎考慮後,加上了最後幾個字,然後再用吸墨紙吸的。」
「那又是為什麼?」
「當然是為了讓我以為情況是如你所說的那樣。」
「什麼?」
「總之,就是要我非去法國不可。他重新讀過信後感到不滿意,因為語氣不夠有力。」
他停了一下,兩眼閃耀著內心激動時常發出的綠色光芒,接著又輕聲說:「我的朋友,既然附言是經過冷靜思考後鄭重加上去的,而不是出於一時衝動,情況一定很緊急,那我們得盡快趕到他那裡去。」
「梅蘭維鎮,」我沉思低語著,「我想,我聽說過這個地方。」
白羅點點頭。
「那是個安靜而別致的小地方,就在布洛涅到加來的中間,我猜雷諾在英國有別墅。」
「是啊,如果我沒記錯,他有一座別墅在拉特蘭門;在赫特福德郡的某處鄉村也有一所大豪宅。可是我對他所知不多,因為他在社交圈中並不活躍。我相信他在倫敦股市控有大量的南美股份,而大部分時間他都待在智利和阿根廷。」
「呃,反正我們等著聽他本人詳述始末就是了。來,我們收拾行李吧!各人帶個小手提箱,叫輛計程車到維多利亞車站。」
十一點鐘,我們從維多利亞出發前往多佛。啟程前,白羅給雷諾發了一封電報,告訴他我們抵達加來的時間。
在船上,我知道此時最好不要去打擾我的朋友。天氣真好,海面正如成語所說的「風平浪靜」,因此當白羅竟面帶微笑的和我在加來一起下船時,我並不感到意外。可是隨即而來的情況卻令人大失所望,因為沒有汽車來接我們。白羅認為這是電報傳遞延誤所致。
「我們就雇輛車吧。」他興致勃勃地說。
幾分鐘後,我們就坐著一輛破舊不堪的計程車,嘎吱嘎吱地一路顛簸著朝梅蘭維的方向駛去。
我興致很好,可是我那小個子朋友卻嚴肅地望著我。
「你這興奮的模樣就像蘇格蘭人所謂的『回光返照』,海斯汀,這是災禍的預兆!」
「胡扯,不過看來,你的感覺與我的不同。」
「是不同,我感到害怕。」
「害怕什麼?」
「我說不上來,但是我有預感……je ne sais quoi!」
他說話的態度凝重,我不由自主地也受到了影響。
「我有一種感覺,」他慢條斯理地說道,「這將是一起重大事件─一個不易解決、耗費時間的棘手問題。」
我本來還要追問下去,就在此時我們駛入了梅蘭維小鎮。我們放慢了車速,詢問去熱內維芙別墅的方向。
「穿過小鎮,先生,筆直地往前走。熱內維芙別墅離馬路的另一邊大約還有半哩路。那是一座面海的大別墅,不會找不到的。」
我們向指路人道過謝,就離鎮往前駛去,在路邊的岔道那兒我們又停下了。一個農夫正向我們走來,我們準備等他靠近些再問路。在路旁有一座小小的別墅,但看起來太小、太破舊,不像是我們要找的那座。在我們等候時,小別墅的門開了,一個女孩走了出來。
那農夫正要走過我們身旁時,司機從座位上探身問路。
「熱內維芙別墅嗎?就在這條路右邊沒幾步,先生。要不是這彎道,你就看見它了。」
司機向他道了謝,再次開動車子。女孩仍站在那兒,一隻手按在門上,望著我們。我的眼睛被她吸引住了。凡是美的事物我總是非常愛慕欣賞,這女孩是這麼美,不論誰看見她都會想和她說話。她身材修長,有如天仙般的姿態,一頭金髮在陽光中熠熠發光。我自忖著,這是我所見過最美的女孩了。當車子搖晃著駛上崎嶇不平的道路時,我還回過頭去望著她。
「啊,白羅,」我驚呼道,「你看見那位年輕的美仙子了吧?」
白羅揚起了雙眉。
「Ça commence!」他低聲說,「你已經認定那是一位仙子!」
「別開玩笑了,難道她不是嗎?」
「也許吧,但我沒注意。」
「你不是也有看到她嗎?」
「我的朋友,很少有兩個人看到同一事物的感受會是相同的。比方說,你看到的是位仙子,可是我……」他吞吞吐吐地說。
「嗯?」
「我看到的只不過是個眼神慌張的女孩。」白羅沉重地說道。
這時車子靠近了一扇綠色大門,我們不約而同地發出一聲驚呼。門前站著一個嚴肅的警官,他舉起手來擋住了我們的去路。
「先生們,你們不能過去。」
「可是我們是來見雷諾先生的,」我喊道,「我們與他有約,這不是他的住宅嗎?」
「是,先生,不過……」
白羅探身向前。
「不過什麼?」
「雷諾先生今天早晨被謀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