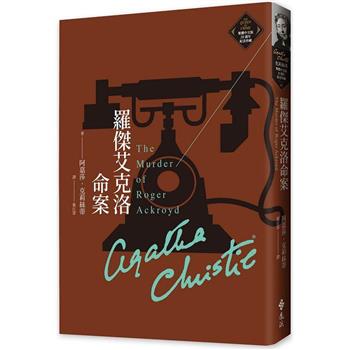01夏波醫生的早餐談話
弗拉爾太太於十六日晚(星期四)離世而去了。十七日(星期五)早晨八點就有人來請我過去。其實我已幫不了什麼忙,因為她已死了好幾個小時。
九點過幾分我就回到家。我取出鑰匙打開前門,故意在大廳裡磨蹭一會,不慌不忙地把帽子和風衣掛好,這些都是我用來抵禦初秋晨寒的東西。老實說,當時我的心情非常沮喪憂愁,並不想假裝自己能夠預料今後幾週將要發生的事。我確實無法預料,但我有一種預感,有段雞犬不寧的時期即將到來。
左邊的餐廳傳來了叮叮噹噹的杯子聲,以及我姐姐卡羅琳的乾咳聲。
「是你嗎,詹姆斯?」她大聲地叫喊著。
這話問得有點多餘,還有可能是誰呢?老實說,就是因為我的姐姐卡羅琳,我才在大廳裡磨蹭了幾分鐘。要說貓鼬這種動物的座右銘,吉卜林先生可是說過了,那就是:「出去挖!」而如果卡羅琳想要選用一種彰顯個人特質的紋章,那我一定極力推薦她採用貓鼬躍立撲擊的圖案;而且對卡羅琳來說,那句座右銘的前兩個字還可省去──卡羅琳只需靜靜地坐在家中就能挖到許多消息。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這一點,但事實卻是如此。我猜想,可能是家中的僕人和做買賣的小販都充當了她的智囊團。她外出並不是為了去挖掘消息,而是去傳播消息。就傳播消息這一點來說,她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專家。
就是因為她的這一特點,才使我感到猶豫不決。如果把弗拉爾太太死亡之事告訴卡羅琳,不出一個半小時,全村的人都會知道。作為一個專業醫務人員,我說話本應特別謹慎,所以久而久之,我便養成了一個習慣──盡可能瞞住消息,不讓姐姐知道。當然,她還是能像平常一樣打聽到這件消息,但至少我自認沒有誤失,對得起良心。
弗拉爾太太的丈夫已去世一年。卡羅琳始終認為他是被妻子毒死的,但她又拿不出什麼確鑿證據。
我跟她說,弗拉爾先生死於習慣性過量飲用含酒精的飲料,導致急性胃炎;而她對我的這一說法總是加以嘲笑。我同意胃炎的症狀與砷中毒有相同之處,但卡羅琳對弗拉爾太太的指控,是基於與此完全不相干的理由。
「你只需要看看她的模樣就知道了。」我曾聽她這麼說過。
弗拉爾太太雖算不上年輕,但丰姿仍然十分迷人。她身上穿的巴黎時裝雖談不上華麗,但看上去非常自然、合適。不管怎麼說,很多婦女都愛去巴黎買衣服,但她們可沒個個都把丈夫給毒死啊!
我躊躇不定地站在大廳裡,腦海裡浮現著所有這一切。這時卡羅琳又叫喊起來,嗓門比前一次還要大。
「詹姆斯,你到底在磨蹭些什麼?為什麼還不來吃早餐?」
「馬上就來,親愛的。」我急急忙忙地應了一聲,「我在掛風衣。」
「這麼長的時間,掛五、六件都可以了。」
她說得一點沒錯。我走進餐廳,習慣性地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然後坐下來吃雞蛋和鹹肉。鹹肉是冷的。
「你這麼早就去串門?」卡羅琳說。
「是的,我去了金帕達克,到弗拉爾太太家跑了一趟。」
「我知道。」姐姐說。
「你怎麼知道?」
「安妮告訴我的。」
安妮是接待女僕,一個挺可愛的女孩,但她有一個難改的習性,愛多嘴。
沉默了片刻,我繼續吃著雞蛋和鹹肉。這時,姐姐瘦長的鼻子抽動了一下。每當她對某件事感興趣或興奮時,就會出現這個動作。
「然後呢?」她追問道。
「悲劇收場。已經回天乏術了,她大概是昨晚睡覺時死的。」
「我知道。」姐姐又說。
這下可把我惹火了。
「你不可能知道,」我厲聲說道,「我也是到了那裡才知道的,我還沒跟任何人講過這件事。如果安妮連這個都曉得的話,她簡直就是活神仙了。」
「不是安妮,是那個送牛奶的人告訴我的,他是從弗拉爾家的廚師那裡聽來的。」
正如我前面所說,卡羅琳沒有必要出去探聽消息,她只需坐在家中,消息自然會傳到她的耳中。
姐姐繼續問道:「她是怎麼死的?是不是心臟病發作?」
「難道送牛奶的人沒有告訴你嗎?」我譏諷地反問道。
譏諷對卡羅琳不起作用,她還以為我是真的在問她問題。
「他也不知道。」她解釋道。
不管怎樣,卡羅琳遲早會知道的,還不如我告訴她算了。
「她因服用過量安眠藥而死。她最近失眠,一直在服這種藥,大概是吃得太多了。」
「胡說,」卡羅琳馬上反駁說,「她是自殺,你不要為她辯解。」
很奇怪,當一個人心中不願承認的想法被別人揭穿時,他往往會惱羞成怒,竭力否認。我當下感到非常氣憤,衝口說了一番氣話。
「你又跟我來這一套了,」我說,「沒有根據的亂說一通。弗拉爾太太究竟有什麼理由要自殺?她雖是個寡婦,但那麼年輕,那麼有錢,而且身體又棒,每天等著享福就夠了。你的話實在太荒唐了。」
「一點都不荒唐。她最近有點反常,這一點你應該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已有六個月,她一定是被妖魔纏住了。你剛才也說她一直睡不好覺。」
「那你的診斷是什麼呢?」我冷冷地問道,「一場不幸的戀愛,我猜?」
我姐姐搖搖頭。
「自責。」她津津樂道地說。
「自責?」
「是的。我一直跟你說,是她毒死了丈夫,但你就是不信。我現在更確信無疑。」
「你這番話不合情理,」我反駁說,「一個婦道人家如果有膽量殺人,她一定是個冷酷無情的人,絕對會心安理得地享受成果。才不會像意志薄弱的人那樣感到自責。」
卡羅琳搖搖頭。
「可能有些婦女會像你說的那樣,但弗拉爾太太並非如此。她很有膽量,一股無法抑制的衝動驅使她害死丈夫,因為她這個人無法忍受任何形式的痛苦。毫無疑問,身為阿什利.弗拉爾這種男人的妻子,必定飽受不少痛苦……」
我點點頭。
「自從害死丈夫後,她一直在煩憂中過日子。這一點我很同情她。」她說。
弗拉爾太太活著的時候,我可沒見過卡羅琳對她表示同情。現在既然她已遠去那不能再穿巴黎時裝(我猜)的地方,卡羅琳倒準備要盡情發揮她的同情和同理心了。
我堅決地告訴她,她的這個想法純屬無稽。而我之所以格外堅決,是因為我心中其實贊成她某部分──極少部分──的說法。但卡羅琳畢竟只是通過猜測來得到事實真相,這種做法可說是完全錯誤,我絕不能鼓勵這種行為。不然的話,她會走遍整個村子,傳播她對弗拉爾太太死亡的看法。人們必定會認為,那是得自於我所提供的醫學判斷。生活中糾纏不清的事真是太多了。
「胡說八道,」面對我那尖刻的言語,卡羅琳並不示弱,「你等著瞧,十有八九她留有一封懺悔信,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寫在上面。」
「她什麼信都沒留下。」我嚴厲地駁斥道,不知這麼說會陷自己於何種境地。
「哦!」卡羅琳說,「這麼說你也打聽過信的事情了。我相信,詹姆斯,你內心深處思忖的事,跟我完全一樣。你真是一個可愛的老騙子。」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自殺的可能性。」我強調道。
「要驗屍嗎?」
「可能會,這要看情況。如果我能絕對有把握地說,她是不小心服用了過量安眠藥,那麼驗屍可能會取消。」
「你有絕對的把握嗎?」姐姐非常奸巧地問道。
我起身離開餐桌,沒有回答她的問題。
02金艾博特村的名流
在我繼續陳述我和卡羅琳的談話內容之前,我不妨先把我們這個村子的地理位置介紹一下。這個村子的名字叫金艾博特,與其他村子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最近的大城鎮是克蘭切斯特,離這兒有九英里。本村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火車站,一個小小的郵電所,兩家相互對峙的「百貨商店」。有才幹的男人,大多在年輕時就離開了這裡,留下來的大多是未婚女子和退伍軍官。因此大家的嗜好和娛樂可用一個詞來歸納:「嚼舌根」。
在金艾博特村,像樣的房子只有兩幢。一幢是金帕達克,弗拉爾太太的丈夫留給她的。另一幢是弗恩利莊,主人是羅傑.艾克洛。我對他很感興趣,因為他一點都不像一個鄉紳。一見到他,我就會聯想到老式音樂喜劇中,第一幕就登場的那位紅臉冒險家。這類喜劇大都以鄉村綠野做背景,而這個角色最喜歡哼著上倫敦城的小調。我們現在演出的都是時事諷刺劇,鄉紳已從音樂形式中消失。
其實,艾克洛並不是一位真正的鄉紳,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車輪製造商。他年近五十,臉色紅潤,待人和藹。他與教區牧師的關係很密切,常常大把大把的捐獻金錢給教會,作為教區救濟金(儘管外面謠傳,說他在個人花費上非常吝嗇)。他還慷慨地資助板球比賽、少年俱樂部、殘廢軍人療養所。事實上,他是金艾博特這個寧靜村子的靈魂人物。
羅傑.艾克洛二十一歲時,就愛上了一個比他大五、六歲的漂亮少婦,並與她結了婚。她是生有一個孩子的寡婦,亡夫姓佩頓。她與艾克洛的婚姻維持並不長,生活充滿了不幸。直率一點說,艾克洛太太是一個酗酒者,婚後四年因長期酗酒而命歸黃泉。
妻子死後多年,艾克洛一直沒有考慮再娶。妻子與前夫生的孩子拉爾夫.佩頓,七歲就失去了母親,他現在已有二十五歲。艾克洛一直把他當作自己的親生兒子來養育,但這個孩子非常難管教,總是惹事生非,讓繼父為他操心不已。儘管如此,金艾博特這裡的人都喜歡拉爾夫。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位小夥子長得英俊瀟灑。
正如前述,在我們這個村子裡,人人喜歡說長道短,因此,艾克洛先生與弗拉爾太太的曖昧關係,一開始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自從弗拉爾太太的丈夫死後,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更加明顯。人們總是看見他們倆在一起。有人甚至大膽地猜測,哀悼期一過,弗拉爾太太就會變成羅傑.艾克洛太太。的確,人們都感到事情有點巧合。大家都知道,羅傑.艾克洛的妻子死於酗酒,而阿什利.弗拉爾生前也是一個酒鬼。這兩個嗜酒如命的死者所留下的未亡人,心理上可以相互撫慰對方,彌補死者給他們帶來的痛苦。
弗拉爾來這兒居住的時間並不長,只不過一年多一點,但有關艾克洛的閒言閒語已流傳多年。在拉爾夫.佩頓的成長過程中,先後有好幾位女管家管理過艾克洛的宅邸,而每個人都受過卡羅琳和她的那夥朋友的懷疑。至少有十五年時間,村子裡的人都確信艾克洛會娶某個女管家為妻,這種看法並非全無道理。最後一個女管家叫拉瑟兒小姐,她最引起人們的懷疑。她整整主持了艾克洛家五年的家務,比以前任何一位女管家任職的時間要長上一倍多。人們都認為要不是弗拉爾太太的出現,艾克洛是無法擺脫拉瑟兒小姐的。當然還有另一個意料之外的原因。他那死了丈夫的弟媳,帶著女兒從加拿大回來了。塞西爾.艾克洛太太是艾克洛那個窩囊弟弟的遺孀,她回來後就住在弗恩利莊。據卡羅琳說,她非常成功地讓拉瑟兒小姐知守分寸。
我不知道「知守分寸」的確切含義─聽起來有點令人不寒而慄、不太愉快─我只知道拉瑟兒小姐總是噘著嘴,而我也只能把這看成是一種苦笑。她對可憐的艾克洛太太深表同情,她曾說:「靠大伯的施捨過日子,太可憐了。施捨的麵包是苦澀的,不是嗎?如果我不是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那就淒慘了。」
談到弗拉爾太太,我不知道塞西爾.艾克洛太太是怎麼想,如果艾克洛先生不再結婚,這對她無疑是有好處的。但每次遇到弗拉爾太太,她總要向她獻一番殷勤,熱情招呼就更不消說了──但卡羅琳說,她這麼做是沒有用的。
這就是過去幾年金艾博特這個地方的重要大事。我們從各個角度談論了艾克洛以及與他有關的一些事情,當然弗拉爾太太也是談論的中心人物。
現在,萬花筒的角度得重新調整一下了,人們對這樁未來婚禮的討論,已驟然被這件悲劇所取代。
我把所有這一切翻來覆去地想一遍後,按慣例外出巡診。我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病人需要診斷治療,所以腦海裡一遍又一遍地浮現出弗拉爾太太的猝死之謎。她是自殺嗎?確定無疑。而如果是自殺的話,她必定會留下遺言,告訴人們為何這麼做。按我的經驗,女人一旦下決心要自殺,通常會把自殺的原因講出來。她們一心巴望聚光燈聚焦在她們身上。
我最後一次是何時見到她?還不到一個星期前。那時,她的舉止行為看來還很正常──嗯,有看仔細的話。
這時我突然想起,我昨天還見過她,但沒與她講話。她正和拉爾夫.佩頓走在一起,我感到很吃驚,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想到,他會在金艾博特村出現。我一直以為他與他的繼父鬧翻了。他有將近六個月沒在這兒露面了。他們肩並肩地走在一起,頭挨得非常近。她說話時的態度一臉嚴肅。
可以確定地說,就在這時,我的心中產生了不祥之兆。雖然目前還沒發生什麼事,但我有一種模糊的預感。回想起昨天拉爾夫.佩頓和弗拉爾太太兩人熱切交頭接耳的情景,我升起一股厭惡之感。
正想著這件事時,我和羅傑.艾克洛在街上面對面地相遇了。
「夏波!」他大聲喊著,「我正想找你,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你已經聽說了?」
他點點頭。可以看得出,他經受了沉重的打擊,臉上紅暈消失,往常愉悅、活力十足的精神不再,全然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事情比你知道的更糟糕,」他平靜地說,「夏波,我有話要跟你說。你現在能不能跟我一起回家?」
「恐怕不行,我還有三個病人等著出診,而且我必須在十二點以前趕回去診所看診。」
「那麼今天下午─不,晚上一起來吃飯吧。七點半怎麼樣?」
「好吧,我一定準時到。出了什麼事?是不是拉爾夫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問,可能是因為以前常常都是為了拉爾夫吧。
艾克洛茫然地盯著我,好像什麼也沒聽明白。我開始意識到,一定是出了嚴重的問題。我以前從未見他這麼心煩意亂過。
「拉爾夫?」他含糊不清地說,「哦,不是為了他,拉爾夫在倫敦─見鬼,甘尼特小姐過來了,我可沒興致跟她聊這種可怕的事。晚上見,夏波,七點半。」
我點了點頭,他說完便匆匆走了,我還站在那裡納悶。拉爾夫在倫敦?但他昨天下午確確實實是在金艾博特村。他必定是昨晚或今晨又回倫敦了。但從艾克洛的態度以及說話的口氣看來,他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他仍以為拉爾夫已有幾個月沒回來了。
我沒有時間進一步解開這個謎。甘尼特小姐一見到我,就急切地向我打聽消息。甘尼特小姐與我姐姐卡羅琳的習性完全一樣,但她缺乏卡羅琳那種全面搜索、推演乃至斷然做出結論的本事。甘尼特小姐氣喘吁吁地向我問了些問題。
弗拉爾太太真可憐,許多人都說她多年來一直在吸毒,而且上了癮。說這樣的話可真惡毒,但最糟糕的是,人們說三道四的言語中總有些部分是真的,無風不起浪嘛!她們還說,艾克洛先生也知道了這件事,因此與她中斷婚約─他們之間確實訂過婚喔。她,甘尼特小姐,有確鑿的證據能證明這一點。當然,作為醫生,我一定知道這些事,醫師不都如此……啊,他們從來沒提過這些事?
甘尼特小姐說著那些試探性的話,機警的小眼睛緊緊地盯著我,看我如何反應。幸運的是,與卡羅琳長期相處已使我養成不動聲色的本事,隨時可用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加以應付。
恭喜甘尼特小姐這次沒有參與這些惡意中傷的閒言閒語。我想我很俐落地反譏了回去。她一時摸不著頭腦,當她回過神時,我已經走遠了。
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某些問題,到診所時我才發現,已有好幾個病人在等著我。
看完最後一個病人時──我以為──離吃午飯還有一段時間,我便來到園子裡,摸摸弄弄了一下。然後,我發現還有一個病人在等我。她起身向我走來。我呆呆地站在那裡,心裡難免有點詫異。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感到詫異,可能是因為拉瑟兒小姐臉上那種堅決的表情,裡面飽含某種精神而非肉體上的痛苦。
艾克洛的這位女管家身材高、容貌漂亮,但神情令人生畏,使人望而卻步。她目光嚴厲,嘴唇緊閉。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如果我是她手下的一名女僕或廚傭,那麼一聽見她的腳步聲,我一定會像老鼠見到貓一樣四處奔逃。
「早安,夏波醫生,」拉瑟兒小姐說,「勞駕你幫我看一下膝蓋的毛病。」
我看了。老實說,我瞧不出個所以然來。拉瑟兒小姐所說的不明痛感實在難以輕信,如果她是一個不太誠實的女子,我一定會懷疑她的膝蓋毛病是編造出來的。我在想,拉瑟兒小姐可能是故意藉看病來探聽弗拉爾太太死亡的原因,但我馬上就發覺我的判斷錯了。她只是略略提了一下那件事,其他什麼都沒問,然而看得出她確實很想多待一會,跟我聊聊。
哦,謝謝你給我開了這瓶外用藥,醫生,」她最後說,「雖然我並不相信這瓶藥會產生什麼效用。」
我也不相信。但出於醫生的職責,我駁斥了她的說法。不管怎麼說,擦這種藥不會有什麼害處,而且作為一個醫生,我也必須捍衛自己的謀生用具。
「這些藥我全都不相信,」拉瑟兒小姐一邊說,一邊用眼睛輕蔑地掃視了架上成排的藥瓶。「藥的害處可大了,你只要看看那些古柯鹼成癮者就清楚了。」
「嗯,就這一點來說──」
「在上層社會中倒是非常流行。」
我相信拉瑟兒小姐比我更了解上層社會,所以我並不想跟她多爭辯。
「我想請教你一下,醫生,」拉瑟兒小姐說。「如果你真的染上了毒癮,有沒有什麼藥可治?」
這種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講清楚,我只是跟她做了簡短的講解,她聽得非常認真。我仍然懷疑她是用這問題探聽弗拉爾太太的事。
「還有,比如說佛羅若──」我接著說。
但奇怪的是,她對佛羅若好像一點也不感興趣。她突然改變了話題,問我是否確有某種稀有毒藥,服用後檢驗不出來。
「哈!」我說,「你正在讀偵探小說?」
她承認她以前讀過。
「偵探小說最精采的部分,就是設計一種稀有毒藥。如有可能,最好是從南美洲取得,從未有人聽說過,而且只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野蠻部落用這種毒藥塗擦在弓箭上,人一碰到馬上中毒而死,而西方發達的科學完全無法檢驗出來。這就是你指的那種東西嗎?」
「是的。世上有沒有這種東西呢?」
我很抱歉地搖搖頭。
「恐怕沒有。當然,有一種叫箭毒的毒藥。」
我跟她介紹了許多關於箭毒的特性,但她好像也並不感興趣。她問我,在我的藥品櫃裡是否有這種毒藥,我回答說沒有。我覺得,我因此被她看扁了。
她起身告辭,我送她到診室門口,這時午餐的鑼敲響了。
我絕不懷疑拉瑟兒小姐對偵探小說的愛好。我陶醉地想像她閱讀偵探小說時的情景:她走出女管家的房間,對失職的女僕訓斥一頓,然後回到舒適的房間專心閱讀《第七次死亡之謎》或其他偵探小說。
弗拉爾太太於十六日晚(星期四)離世而去了。十七日(星期五)早晨八點就有人來請我過去。其實我已幫不了什麼忙,因為她已死了好幾個小時。
九點過幾分我就回到家。我取出鑰匙打開前門,故意在大廳裡磨蹭一會,不慌不忙地把帽子和風衣掛好,這些都是我用來抵禦初秋晨寒的東西。老實說,當時我的心情非常沮喪憂愁,並不想假裝自己能夠預料今後幾週將要發生的事。我確實無法預料,但我有一種預感,有段雞犬不寧的時期即將到來。
左邊的餐廳傳來了叮叮噹噹的杯子聲,以及我姐姐卡羅琳的乾咳聲。
「是你嗎,詹姆斯?」她大聲地叫喊著。
這話問得有點多餘,還有可能是誰呢?老實說,就是因為我的姐姐卡羅琳,我才在大廳裡磨蹭了幾分鐘。要說貓鼬這種動物的座右銘,吉卜林先生可是說過了,那就是:「出去挖!」而如果卡羅琳想要選用一種彰顯個人特質的紋章,那我一定極力推薦她採用貓鼬躍立撲擊的圖案;而且對卡羅琳來說,那句座右銘的前兩個字還可省去──卡羅琳只需靜靜地坐在家中就能挖到許多消息。我不知道她是怎麼做到這一點,但事實卻是如此。我猜想,可能是家中的僕人和做買賣的小販都充當了她的智囊團。她外出並不是為了去挖掘消息,而是去傳播消息。就傳播消息這一點來說,她也是一個了不起的專家。
就是因為她的這一特點,才使我感到猶豫不決。如果把弗拉爾太太死亡之事告訴卡羅琳,不出一個半小時,全村的人都會知道。作為一個專業醫務人員,我說話本應特別謹慎,所以久而久之,我便養成了一個習慣──盡可能瞞住消息,不讓姐姐知道。當然,她還是能像平常一樣打聽到這件消息,但至少我自認沒有誤失,對得起良心。
弗拉爾太太的丈夫已去世一年。卡羅琳始終認為他是被妻子毒死的,但她又拿不出什麼確鑿證據。
我跟她說,弗拉爾先生死於習慣性過量飲用含酒精的飲料,導致急性胃炎;而她對我的這一說法總是加以嘲笑。我同意胃炎的症狀與砷中毒有相同之處,但卡羅琳對弗拉爾太太的指控,是基於與此完全不相干的理由。
「你只需要看看她的模樣就知道了。」我曾聽她這麼說過。
弗拉爾太太雖算不上年輕,但丰姿仍然十分迷人。她身上穿的巴黎時裝雖談不上華麗,但看上去非常自然、合適。不管怎麼說,很多婦女都愛去巴黎買衣服,但她們可沒個個都把丈夫給毒死啊!
我躊躇不定地站在大廳裡,腦海裡浮現著所有這一切。這時卡羅琳又叫喊起來,嗓門比前一次還要大。
「詹姆斯,你到底在磨蹭些什麼?為什麼還不來吃早餐?」
「馬上就來,親愛的。」我急急忙忙地應了一聲,「我在掛風衣。」
「這麼長的時間,掛五、六件都可以了。」
她說得一點沒錯。我走進餐廳,習慣性地在她的臉頰上吻了一下,然後坐下來吃雞蛋和鹹肉。鹹肉是冷的。
「你這麼早就去串門?」卡羅琳說。
「是的,我去了金帕達克,到弗拉爾太太家跑了一趟。」
「我知道。」姐姐說。
「你怎麼知道?」
「安妮告訴我的。」
安妮是接待女僕,一個挺可愛的女孩,但她有一個難改的習性,愛多嘴。
沉默了片刻,我繼續吃著雞蛋和鹹肉。這時,姐姐瘦長的鼻子抽動了一下。每當她對某件事感興趣或興奮時,就會出現這個動作。
「然後呢?」她追問道。
「悲劇收場。已經回天乏術了,她大概是昨晚睡覺時死的。」
「我知道。」姐姐又說。
這下可把我惹火了。
「你不可能知道,」我厲聲說道,「我也是到了那裡才知道的,我還沒跟任何人講過這件事。如果安妮連這個都曉得的話,她簡直就是活神仙了。」
「不是安妮,是那個送牛奶的人告訴我的,他是從弗拉爾家的廚師那裡聽來的。」
正如我前面所說,卡羅琳沒有必要出去探聽消息,她只需坐在家中,消息自然會傳到她的耳中。
姐姐繼續問道:「她是怎麼死的?是不是心臟病發作?」
「難道送牛奶的人沒有告訴你嗎?」我譏諷地反問道。
譏諷對卡羅琳不起作用,她還以為我是真的在問她問題。
「他也不知道。」她解釋道。
不管怎樣,卡羅琳遲早會知道的,還不如我告訴她算了。
「她因服用過量安眠藥而死。她最近失眠,一直在服這種藥,大概是吃得太多了。」
「胡說,」卡羅琳馬上反駁說,「她是自殺,你不要為她辯解。」
很奇怪,當一個人心中不願承認的想法被別人揭穿時,他往往會惱羞成怒,竭力否認。我當下感到非常氣憤,衝口說了一番氣話。
「你又跟我來這一套了,」我說,「沒有根據的亂說一通。弗拉爾太太究竟有什麼理由要自殺?她雖是個寡婦,但那麼年輕,那麼有錢,而且身體又棒,每天等著享福就夠了。你的話實在太荒唐了。」
「一點都不荒唐。她最近有點反常,這一點你應該也注意到了。這種情況已有六個月,她一定是被妖魔纏住了。你剛才也說她一直睡不好覺。」
「那你的診斷是什麼呢?」我冷冷地問道,「一場不幸的戀愛,我猜?」
我姐姐搖搖頭。
「自責。」她津津樂道地說。
「自責?」
「是的。我一直跟你說,是她毒死了丈夫,但你就是不信。我現在更確信無疑。」
「你這番話不合情理,」我反駁說,「一個婦道人家如果有膽量殺人,她一定是個冷酷無情的人,絕對會心安理得地享受成果。才不會像意志薄弱的人那樣感到自責。」
卡羅琳搖搖頭。
「可能有些婦女會像你說的那樣,但弗拉爾太太並非如此。她很有膽量,一股無法抑制的衝動驅使她害死丈夫,因為她這個人無法忍受任何形式的痛苦。毫無疑問,身為阿什利.弗拉爾這種男人的妻子,必定飽受不少痛苦……」
我點點頭。
「自從害死丈夫後,她一直在煩憂中過日子。這一點我很同情她。」她說。
弗拉爾太太活著的時候,我可沒見過卡羅琳對她表示同情。現在既然她已遠去那不能再穿巴黎時裝(我猜)的地方,卡羅琳倒準備要盡情發揮她的同情和同理心了。
我堅決地告訴她,她的這個想法純屬無稽。而我之所以格外堅決,是因為我心中其實贊成她某部分──極少部分──的說法。但卡羅琳畢竟只是通過猜測來得到事實真相,這種做法可說是完全錯誤,我絕不能鼓勵這種行為。不然的話,她會走遍整個村子,傳播她對弗拉爾太太死亡的看法。人們必定會認為,那是得自於我所提供的醫學判斷。生活中糾纏不清的事真是太多了。
「胡說八道,」面對我那尖刻的言語,卡羅琳並不示弱,「你等著瞧,十有八九她留有一封懺悔信,把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寫在上面。」
「她什麼信都沒留下。」我嚴厲地駁斥道,不知這麼說會陷自己於何種境地。
「哦!」卡羅琳說,「這麼說你也打聽過信的事情了。我相信,詹姆斯,你內心深處思忖的事,跟我完全一樣。你真是一個可愛的老騙子。」
「當然,我們不能排除自殺的可能性。」我強調道。
「要驗屍嗎?」
「可能會,這要看情況。如果我能絕對有把握地說,她是不小心服用了過量安眠藥,那麼驗屍可能會取消。」
「你有絕對的把握嗎?」姐姐非常奸巧地問道。
我起身離開餐桌,沒有回答她的問題。
02金艾博特村的名流
在我繼續陳述我和卡羅琳的談話內容之前,我不妨先把我們這個村子的地理位置介紹一下。這個村子的名字叫金艾博特,與其他村子沒有什麼明顯的不同。最近的大城鎮是克蘭切斯特,離這兒有九英里。本村有一個規模相當大的火車站,一個小小的郵電所,兩家相互對峙的「百貨商店」。有才幹的男人,大多在年輕時就離開了這裡,留下來的大多是未婚女子和退伍軍官。因此大家的嗜好和娛樂可用一個詞來歸納:「嚼舌根」。
在金艾博特村,像樣的房子只有兩幢。一幢是金帕達克,弗拉爾太太的丈夫留給她的。另一幢是弗恩利莊,主人是羅傑.艾克洛。我對他很感興趣,因為他一點都不像一個鄉紳。一見到他,我就會聯想到老式音樂喜劇中,第一幕就登場的那位紅臉冒險家。這類喜劇大都以鄉村綠野做背景,而這個角色最喜歡哼著上倫敦城的小調。我們現在演出的都是時事諷刺劇,鄉紳已從音樂形式中消失。
其實,艾克洛並不是一位真正的鄉紳,他是一個非常成功的車輪製造商。他年近五十,臉色紅潤,待人和藹。他與教區牧師的關係很密切,常常大把大把的捐獻金錢給教會,作為教區救濟金(儘管外面謠傳,說他在個人花費上非常吝嗇)。他還慷慨地資助板球比賽、少年俱樂部、殘廢軍人療養所。事實上,他是金艾博特這個寧靜村子的靈魂人物。
羅傑.艾克洛二十一歲時,就愛上了一個比他大五、六歲的漂亮少婦,並與她結了婚。她是生有一個孩子的寡婦,亡夫姓佩頓。她與艾克洛的婚姻維持並不長,生活充滿了不幸。直率一點說,艾克洛太太是一個酗酒者,婚後四年因長期酗酒而命歸黃泉。
妻子死後多年,艾克洛一直沒有考慮再娶。妻子與前夫生的孩子拉爾夫.佩頓,七歲就失去了母親,他現在已有二十五歲。艾克洛一直把他當作自己的親生兒子來養育,但這個孩子非常難管教,總是惹事生非,讓繼父為他操心不已。儘管如此,金艾博特這裡的人都喜歡拉爾夫。其中一個原因是,這位小夥子長得英俊瀟灑。
正如前述,在我們這個村子裡,人人喜歡說長道短,因此,艾克洛先生與弗拉爾太太的曖昧關係,一開始就引起了人們的注意。自從弗拉爾太太的丈夫死後,他們之間的親密關係更加明顯。人們總是看見他們倆在一起。有人甚至大膽地猜測,哀悼期一過,弗拉爾太太就會變成羅傑.艾克洛太太。的確,人們都感到事情有點巧合。大家都知道,羅傑.艾克洛的妻子死於酗酒,而阿什利.弗拉爾生前也是一個酒鬼。這兩個嗜酒如命的死者所留下的未亡人,心理上可以相互撫慰對方,彌補死者給他們帶來的痛苦。
弗拉爾來這兒居住的時間並不長,只不過一年多一點,但有關艾克洛的閒言閒語已流傳多年。在拉爾夫.佩頓的成長過程中,先後有好幾位女管家管理過艾克洛的宅邸,而每個人都受過卡羅琳和她的那夥朋友的懷疑。至少有十五年時間,村子裡的人都確信艾克洛會娶某個女管家為妻,這種看法並非全無道理。最後一個女管家叫拉瑟兒小姐,她最引起人們的懷疑。她整整主持了艾克洛家五年的家務,比以前任何一位女管家任職的時間要長上一倍多。人們都認為要不是弗拉爾太太的出現,艾克洛是無法擺脫拉瑟兒小姐的。當然還有另一個意料之外的原因。他那死了丈夫的弟媳,帶著女兒從加拿大回來了。塞西爾.艾克洛太太是艾克洛那個窩囊弟弟的遺孀,她回來後就住在弗恩利莊。據卡羅琳說,她非常成功地讓拉瑟兒小姐知守分寸。
我不知道「知守分寸」的確切含義─聽起來有點令人不寒而慄、不太愉快─我只知道拉瑟兒小姐總是噘著嘴,而我也只能把這看成是一種苦笑。她對可憐的艾克洛太太深表同情,她曾說:「靠大伯的施捨過日子,太可憐了。施捨的麵包是苦澀的,不是嗎?如果我不是自食其力,靠自己的勞動養活自己,那就淒慘了。」
談到弗拉爾太太,我不知道塞西爾.艾克洛太太是怎麼想,如果艾克洛先生不再結婚,這對她無疑是有好處的。但每次遇到弗拉爾太太,她總要向她獻一番殷勤,熱情招呼就更不消說了──但卡羅琳說,她這麼做是沒有用的。
這就是過去幾年金艾博特這個地方的重要大事。我們從各個角度談論了艾克洛以及與他有關的一些事情,當然弗拉爾太太也是談論的中心人物。
現在,萬花筒的角度得重新調整一下了,人們對這樁未來婚禮的討論,已驟然被這件悲劇所取代。
我把所有這一切翻來覆去地想一遍後,按慣例外出巡診。我沒有什麼特別重要的病人需要診斷治療,所以腦海裡一遍又一遍地浮現出弗拉爾太太的猝死之謎。她是自殺嗎?確定無疑。而如果是自殺的話,她必定會留下遺言,告訴人們為何這麼做。按我的經驗,女人一旦下決心要自殺,通常會把自殺的原因講出來。她們一心巴望聚光燈聚焦在她們身上。
我最後一次是何時見到她?還不到一個星期前。那時,她的舉止行為看來還很正常──嗯,有看仔細的話。
這時我突然想起,我昨天還見過她,但沒與她講話。她正和拉爾夫.佩頓走在一起,我感到很吃驚,因為我根本就沒有想到,他會在金艾博特村出現。我一直以為他與他的繼父鬧翻了。他有將近六個月沒在這兒露面了。他們肩並肩地走在一起,頭挨得非常近。她說話時的態度一臉嚴肅。
可以確定地說,就在這時,我的心中產生了不祥之兆。雖然目前還沒發生什麼事,但我有一種模糊的預感。回想起昨天拉爾夫.佩頓和弗拉爾太太兩人熱切交頭接耳的情景,我升起一股厭惡之感。
正想著這件事時,我和羅傑.艾克洛在街上面對面地相遇了。
「夏波!」他大聲喊著,「我正想找你,這實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
「你已經聽說了?」
他點點頭。可以看得出,他經受了沉重的打擊,臉上紅暈消失,往常愉悅、活力十足的精神不再,全然一副失魂落魄的模樣。
「事情比你知道的更糟糕,」他平靜地說,「夏波,我有話要跟你說。你現在能不能跟我一起回家?」
「恐怕不行,我還有三個病人等著出診,而且我必須在十二點以前趕回去診所看診。」
「那麼今天下午─不,晚上一起來吃飯吧。七點半怎麼樣?」
「好吧,我一定準時到。出了什麼事?是不是拉爾夫的事?」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這樣問,可能是因為以前常常都是為了拉爾夫吧。
艾克洛茫然地盯著我,好像什麼也沒聽明白。我開始意識到,一定是出了嚴重的問題。我以前從未見他這麼心煩意亂過。
「拉爾夫?」他含糊不清地說,「哦,不是為了他,拉爾夫在倫敦─見鬼,甘尼特小姐過來了,我可沒興致跟她聊這種可怕的事。晚上見,夏波,七點半。」
我點了點頭,他說完便匆匆走了,我還站在那裡納悶。拉爾夫在倫敦?但他昨天下午確確實實是在金艾博特村。他必定是昨晚或今晨又回倫敦了。但從艾克洛的態度以及說話的口氣看來,他好像什麼都不知道,他仍以為拉爾夫已有幾個月沒回來了。
我沒有時間進一步解開這個謎。甘尼特小姐一見到我,就急切地向我打聽消息。甘尼特小姐與我姐姐卡羅琳的習性完全一樣,但她缺乏卡羅琳那種全面搜索、推演乃至斷然做出結論的本事。甘尼特小姐氣喘吁吁地向我問了些問題。
弗拉爾太太真可憐,許多人都說她多年來一直在吸毒,而且上了癮。說這樣的話可真惡毒,但最糟糕的是,人們說三道四的言語中總有些部分是真的,無風不起浪嘛!她們還說,艾克洛先生也知道了這件事,因此與她中斷婚約─他們之間確實訂過婚喔。她,甘尼特小姐,有確鑿的證據能證明這一點。當然,作為醫生,我一定知道這些事,醫師不都如此……啊,他們從來沒提過這些事?
甘尼特小姐說著那些試探性的話,機警的小眼睛緊緊地盯著我,看我如何反應。幸運的是,與卡羅琳長期相處已使我養成不動聲色的本事,隨時可用一些無關緊要的話加以應付。
恭喜甘尼特小姐這次沒有參與這些惡意中傷的閒言閒語。我想我很俐落地反譏了回去。她一時摸不著頭腦,當她回過神時,我已經走遠了。
回程的路上,我一直在思考某些問題,到診所時我才發現,已有好幾個病人在等著我。
看完最後一個病人時──我以為──離吃午飯還有一段時間,我便來到園子裡,摸摸弄弄了一下。然後,我發現還有一個病人在等我。她起身向我走來。我呆呆地站在那裡,心裡難免有點詫異。
我也不明白為什麼會感到詫異,可能是因為拉瑟兒小姐臉上那種堅決的表情,裡面飽含某種精神而非肉體上的痛苦。
艾克洛的這位女管家身材高、容貌漂亮,但神情令人生畏,使人望而卻步。她目光嚴厲,嘴唇緊閉。我有這樣一種感覺:如果我是她手下的一名女僕或廚傭,那麼一聽見她的腳步聲,我一定會像老鼠見到貓一樣四處奔逃。
「早安,夏波醫生,」拉瑟兒小姐說,「勞駕你幫我看一下膝蓋的毛病。」
我看了。老實說,我瞧不出個所以然來。拉瑟兒小姐所說的不明痛感實在難以輕信,如果她是一個不太誠實的女子,我一定會懷疑她的膝蓋毛病是編造出來的。我在想,拉瑟兒小姐可能是故意藉看病來探聽弗拉爾太太死亡的原因,但我馬上就發覺我的判斷錯了。她只是略略提了一下那件事,其他什麼都沒問,然而看得出她確實很想多待一會,跟我聊聊。
哦,謝謝你給我開了這瓶外用藥,醫生,」她最後說,「雖然我並不相信這瓶藥會產生什麼效用。」
我也不相信。但出於醫生的職責,我駁斥了她的說法。不管怎麼說,擦這種藥不會有什麼害處,而且作為一個醫生,我也必須捍衛自己的謀生用具。
「這些藥我全都不相信,」拉瑟兒小姐一邊說,一邊用眼睛輕蔑地掃視了架上成排的藥瓶。「藥的害處可大了,你只要看看那些古柯鹼成癮者就清楚了。」
「嗯,就這一點來說──」
「在上層社會中倒是非常流行。」
我相信拉瑟兒小姐比我更了解上層社會,所以我並不想跟她多爭辯。
「我想請教你一下,醫生,」拉瑟兒小姐說。「如果你真的染上了毒癮,有沒有什麼藥可治?」
這種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講清楚,我只是跟她做了簡短的講解,她聽得非常認真。我仍然懷疑她是用這問題探聽弗拉爾太太的事。
「還有,比如說佛羅若──」我接著說。
但奇怪的是,她對佛羅若好像一點也不感興趣。她突然改變了話題,問我是否確有某種稀有毒藥,服用後檢驗不出來。
「哈!」我說,「你正在讀偵探小說?」
她承認她以前讀過。
「偵探小說最精采的部分,就是設計一種稀有毒藥。如有可能,最好是從南美洲取得,從未有人聽說過,而且只有一個鮮為人知的野蠻部落用這種毒藥塗擦在弓箭上,人一碰到馬上中毒而死,而西方發達的科學完全無法檢驗出來。這就是你指的那種東西嗎?」
「是的。世上有沒有這種東西呢?」
我很抱歉地搖搖頭。
「恐怕沒有。當然,有一種叫箭毒的毒藥。」
我跟她介紹了許多關於箭毒的特性,但她好像也並不感興趣。她問我,在我的藥品櫃裡是否有這種毒藥,我回答說沒有。我覺得,我因此被她看扁了。
她起身告辭,我送她到診室門口,這時午餐的鑼敲響了。
我絕不懷疑拉瑟兒小姐對偵探小說的愛好。我陶醉地想像她閱讀偵探小說時的情景:她走出女管家的房間,對失職的女僕訓斥一頓,然後回到舒適的房間專心閱讀《第七次死亡之謎》或其他偵探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