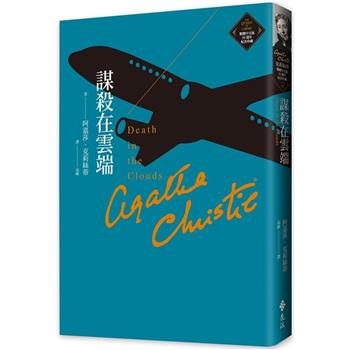01從巴黎到克洛敦
在布爾歇機場上,九月的太陽還很酷烈。旅客們熱得昏頭昏腦,懶洋洋地步入機場,順著舷梯登上「普羅米修斯」號飛機;幾分鐘後,它就要從巴黎飛往克洛敦了。
珍.格雷是最後一批走進客機的乘客,她毫不費力地找到了自己的第十六號座位。有幾個人則繼續穿過隔門、小廚房、兩間盥洗室,朝前艙走去。大多數的人已經就座完畢。通道的另一面,有人在起勁地交談。其中一個聲音刺耳尖銳,而且大都是她在發話,珍稍微皺了皺眉頭,她很熟悉這種類型的聲音。
「親愛的,完全不可思議,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說在哪兒?在鐘拉潘嗎?哦,對了。不,在盧比納……是,就是同一班老人……不,不,當然囉,我們坐在一塊兒吧。難道不行嗎?誰?啊,我明白了……」
然後是一個外國人謙遜、愉快地回答:「噢,很樂意,請坐吧,太太!」
珍偷看了外國人一眼。
這是一個年紀不輕的小個子,蓄著偌大的八字鬍,蛋形腦袋;他把自己隔著走道而鄰接珍的座位恭敬地讓出來。
珍微微扭過頭,瞧見那兩個逼迫這個外國人禮讓座位的婦人。她們提到盧比納激起了珍的好奇;因為她也剛剛去過那兒。她記起最後在哪兒見過其中一位婦人──在賭桌邊見過。當時,這個婦人一會兒握緊拳頭,一會兒又鬆開拳頭;一張精心雕琢、活像尊翠斯騰瓷偶的臉蛋,一會兒發白,一會兒又緋紅。珍一下就想起這個人的姓名。當時,一個女友曾向她提到這個婦人:「她雖然也是個貴夫人,但並不是貨真價實。從前,她是在劇團唱歌的。」女友的口吻中有一種輕蔑和嘲笑。這個女友名叫梅西,她的工作挺不錯─充當按摩女郎,她能「消除」顧客過度肥胖的現象。
「可是另一個婦人,」珍心想,「就是個名副其實的貴夫人。住在郡鄉、習慣騎馬活動的類型。」但旋及她便忘了那兩位婦人,而被窗外機場的景象所吸引。好多飛機都在等待起飛,有一架看來好像是一條金屬蜈蚣。
珍的正對面坐著一位身穿鮮豔淺藍絨線衫的年輕人。為了不跟這年輕人的視線相遇,她打定主意不朝正前方瞧,絕對不!
機師們用法語互相吆喝一陣──引擎隆隆響起─停歇─再響起─障礙物排開─飛機終於起飛了。
珍屏住氣息,這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飛行,她仍舊感到十分興奮。飛機往前疾馳,看來好像要撞上圍牆了……不,眨眼間,他們已經在大地上空了,上升,再上升,盤旋升高,布爾歇機場遠遠落在下面了……
飛機開始了午餐服務,乘客總共有二十一人,十人在前面的客艙,十一人在後艙。機組有兩名駕駛員和兩名空服員,引擎的噪音被高超的技術消音了,甚至耳朵也無需塞上棉花。不過,還是有其他噪音,交談仍然困難,只能胡思亂想。
普羅米修斯號越過法國領土上空朝英吉利海峽飛去,後艙的乘客都在想著自己的心事。
珍.格雷想道:「絕不瞧他!不,絕不,我要望著窗外想心事,我得挑件事情想想,這是最好的辦法。這樣我才不會慌亂。我得從開始想起,好好回溯一番。」
她的思緒回到所謂的「開始」,也就是買下愛爾蘭賽馬會賭票的那天。那的確是個奢侈的行為,卻令人充滿期待……
在珍和其他五個年輕小姐工作的美容院裡,是一片嘻笑聲和嘈雜聲。
「如果你贏了大獎,你要做什麼啊,親愛的?」
「我自有打算。」
接著是計畫,一堆幻想,一堆爭論……
結果她沒得到「大獎」,但贏了整整一百英鎊!
整整一百英鎊。
「花掉一半,另一半存起來,你永遠料不到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要是你,珍,我寧可買一件皮大衣,上好的皮大衣。」
「來趟海上之旅如何?」
一想到海上之旅,珍的心不禁怦怦直跳。但最後,她還是忠於她的第一個選擇:到盧比納去消磨一個星期。她的許多客人都去過盧比納,或者剛從那裡回來……
珍敏捷的巧手正給顧客理好一綹綹頭髮,捲成服服貼貼的鬈髮,嘴裡向顧客提出一些反射性問題:「您多久沒燙頭髮了,太太?」「您的髮色好特別呀,太太。」「今年夏天很棒,不是嗎,太太?」腦中卻想著為什麼就我不能去盧比納?現在,她終於能暢遊一回了。
對她來說,衣著不成問題,珍和大多數在倫敦鬧區工作的女孩一樣,只要花很少一點兒錢,就能把自己打扮得既時髦又漂亮,指甲,化妝,髮型,完全無可挑剔。
於是,珍去了盧比納。
有沒有可能這十天在盧比納的歡樂都在那次付之一炬?
那是在賭輪盤時發生的一件插曲。那幾天的晚上,珍都放任自己小賭一把,但不管怎樣,她都絕不超過某個限額。這天一反迷信傳統的,一開頭她就很不走運。她已經賭了四個晚上,這一次是她今天的最後一筆賭注了,之前珍一直小心地把賭注押在她彩色號碼上。她贏了一點,但多半是輸;此刻,她把錢捏在手裡,屏息等待。
還剩下兩個號碼沒人下,5號和6號。要把最後一把下在其中一個號碼上嗎?可是下在哪個號碼上呢?5還是6?哪個她比較有感覺?
5號就要翻轉過去,小球滾動了。珍伸出手,6,她放在6上。
正巧,她和對面的一個賭客同時下注:她選中了6,他選中了5。
「賭注下定啦。」莊家說。
小球跳了一下就不動了。
「5號,紅的,單數,贏啦。」
珍懊惱得幾乎叫了一聲。莊家掃進賭金,付錢給贏家,坐在珍對面的賭客問道:「你不拿走自己贏得的錢嗎?」
「我贏的錢?」
「是呀。」
「但我下的是6呀!」
「不,下6的是我,你下的是5。」
他笑著說,笑容非常迷人。白白的牙齒,棕黑的臉蛋,藍眼睛,短短的鬈髮。
珍狐疑地拿起贏得的錢。這是不是搞錯了?她有點困惑。或許她是下在5上了。她懷疑地瞅了那陌生人一眼。他又回了一個微笑。
「這就對了,」他說,「如果你把錢留在桌上,別人馬上就會把它拿走!這是一定的。」
說著,他親切地點點頭就走了。這招也很貼心。否則珍可能認為,他僅僅為了跟她結識,而把贏的錢讓給她。不過,他不是那種人,他那麼親切……而此刻,他竟正好坐在她對面!只是一切都結束了──所有的錢已花光了,巴黎的最後兩天也一晃而過(唉,無聊的最後兩天),而現在手中機票上的目的地一欄,印的已是家園的名字。
接下來呢?
「何必去猜測將來如何,」珍阻止自己胡思亂想。「幹嘛瞎操心?」
彼此閒聊的兩個婦人已不作聲了,她望過走道。那位翠斯騰瓷偶夫人氣惱地嘟囔著,瞧了瞧裂掉的指甲。她撳了撳電鈴,當穿著雪白衣服的空服員來到她面前時,她說:「叫我的女傭人到我這兒來一下。她在前艙。」
「是的,夫人。」
空服員周到、敏捷、迅速地走了。接著馬上出現了一個頭髮烏黑的年輕法國女孩。她穿了一件黑色連衣裙,拿來了一個小珠寶箱。霍伯里夫人用法國話吩咐這個女孩。
「馬德琳,去把那個紅色摩洛哥皮的化妝箱拿來給我。」
女傭人朝機尾堆放蓋毯和行李的地方走去。不一會,這女孩就拿了一個小化妝箱回來。西塞莉.霍伯里夫人從女傭手裡接過小箱子,就遣走她了。
「好了,馬德琳,這個就留在我這兒。」
女傭人再度離開。霍伯里夫人揭開箱蓋,從漂亮的箱子裡取出一把指甲銼子。然後,對著一個小鏡子久久地研究自己的面孔,一會兒撲點兒香粉,一會兒又塗塗口紅。
珍輕蔑地撇了撇嘴,眼光落在前面的其他乘客身上。
坐在兩個夫人後面的,是那個和「真貴婦」交換座位的矮小外國人。他脖子上緊緊圍了一條根本用不著的圍巾,似乎睡熟了,但或許是珍凝視的目光驚動了他,他張開眼望望珍後,又闔上眼瞼。
跟他並排而坐的是一個體面而頭髮斑白的男人,膝上放一個打開的橫笛外盒,手裡呵護備至地擦拭著一根橫笛。怪了,珍想到,他看來根本不像個音樂家,而像是律師或醫生。
坐在他們後面的是兩個法國人。一個蓄著落腮鬍;另一個年輕得多,大概是前者的兒子。兩人正比手畫腳地熱烈談論什麼。
至於珍自己這排的視線,則全被那個穿藍色絨線衫的男人給遮住了。也說不出理由,反正珍打定主意不去看他。
「我怎麼會這麼……好像才十七歲似的!」珍懊惱地責怪自己。
對面的這位諾曼.蓋爾則在尋思。「她真漂亮,實在漂亮!她一定記得我。記得她的賭金被掃走時,她有多沮喪啊。但後來看到她得到那筆錢的喜悅,我什麼都值得了!我到底做對了……她的微笑真叫人喜愛:健康的牙齒,堅固的牙床。活見鬼,我怎麼這麼激動!沉住氣,小夥子!」
他向旁邊走過的空服員說:「給我一份冷牛舌。」
霍伯里伯爵夫人則在思忖。「我的天,究竟該怎麼辦呢?這下糟透了。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只要我膽子夠大。這我能夠辦到嗎?我能矇混過去嗎?我的神經快受不了了。全都因為古柯鹼。我幹嘛要碰那東西呢?我的面孔看來好嚇人,太嚇人啦!維妮塔.克爾那爛女人在這兒,就更糟糕了。她老是盯著我瞧,好像我是一個髒東西。她想把斯蒂芬據為己有,可是希望落空了。那張大長臉弄得我好緊張,真的和馬臉沒兩樣。我恨死了這些鄉紳階級的貴族。天哪,我該怎麼辦呀!應當想點什麼辦法!那老妖精可不是說著玩的……」
霍伯里夫人從盒裡取出一根香菸,把它插在長菸嘴裡,她的兩隻手都在顫抖。
維妮塔.克爾女爵嘀咕道:「哼,無恥的婊子!這就是她。或許理論上她貞潔無瑕,但她骨子裡根本是個妓女的料。可憐的斯蒂芬,他要能離開她就好了……」
她也拿出菸盒,就著西塞莉.霍伯里遞上的火柴點了火。
空服員阻止她。「對不起,夫人,這裡禁止吸菸!」
「見鬼!」霍伯里夫人表示不滿。
赫丘勒.白羅想道:「那邊那位小姐真漂亮。她有一個堅毅的下巴,可是什麼使她如此惶惶不安呢?她為什麼一直迴避對面那個英俊男子的目光呢?看來,她是認識他的,他也是認識她的……」
飛機稍稍下降。
「啊,我的肚子。」赫丘勒.白羅哼了一聲,牢牢地閉上了眼睛。
跟他並排的布賴恩醫生小心地撫摸著自己的橫笛,心裡琢磨著:「我無法下定決心,我就是無法下決心。這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捩點啊……」
他從盒子裡小心、愛戀地取出橫笛。音樂……在樂曲聲中可以忘卻人生的一切憂慮。他笑咪咪地把橫笛拿到唇邊,接著又將它放下。蓄著小鬍子的那位矮個子就在旁邊打盹。
飛機突然劇烈地搖晃了一下,晃得人眼睛都發昏了。布賴恩醫生很高興,他從不暈車,也不暈船,坐飛機也不會暈機。
老杜邦先生激動地向小杜邦嚷嚷起來。
「這一點用不著懷疑!他們─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全都錯了!史前陶器發明的日期,他們說得根本不準!比方說,薩邁拉陶器……」
金.杜邦個子很高,彬彬有禮,樣子有點懶洋洋,他溫和地反駁說:「你應當拿出憑據!還有塔爾.哈雷夫和薩基耶.戈茲……」
討論繼續下去。
阿曼德.杜邦先生打開一個飽經滄桑的航空旅行袋。
「你看看這些庫爾德菸斗,簡直像是現代作品。菸斗上的裝飾就像那個西元前五千年的陶器……」
阿曼德.杜邦先生猛然一揮,差點把空服員剛才放在他面前的一個盤子碰掉了。
克蘭西先生是個作家,寫過許多偵探小說;他從諾曼.蓋爾後面的座位上站起來,走到客艙尾部去,並從自己放在那兒的外套口袋裡掏出一份英國布萊蕭火車時刻表,然後拿著它回來,想要為自己的小說構思一個完全的「不在場證明」。
坐在克蘭西先生後面的賴德先生心裡直翻騰:「我一定要堅持到底,只是會很辛苦。我不知道怎麼提高下一筆股息……如果轉讓股份那就嗚呼哀哉了……哦,該死!」
諾曼.蓋爾站起身來,到廁所去。他才離開,珍立即從手提包裡取出小鏡子,不安地看了看自己,搽上一點香粉,再塗上口紅。
空服員把咖啡放在她面前。她望了望窗外,下面是金光閃耀而蔚藍的英吉利海峽。
正當克蘭西先生認真安排晚上七點五十五分在沙里布的故事細節時,一隻黃蜂在他頭頂上討厭地嗡嗡盤旋,克蘭西揮手,沒打到牠,黃蜂於是飛到遠處去糾纏杜邦父子的咖啡杯。
膽大的金.杜邦準確一擊,打死了黃蜂。
客艙恢復平靜。談話聲停止,每個人都專注想著自己的心事。
客艙的深處,在二號座位上,吉塞爾太太的頭忽然向前伸出一點,看起來像是睡著了。但她不是在睡覺,她也沒在說話或思考。
吉塞爾太太已經死了……
02重大發現
資深空服員亨利.米契爾快速地從一個座位走到另一個座位,把帳單送給每個乘客。再過半小時,飛機就要到達克洛敦。米契爾收下鈔票和小銀幣,一面哈腰,一面不住地說:「謝謝,先生。謝謝,夫人。」在那兩個法國人的小桌前面,他不得不等候一兩分鐘,因為他們正在比手畫腳地高談闊論。「在這兒,大概撈不到多少小費了。」米契爾抑鬱地想道。
有兩個乘客正在打盹。一個是蓄著八字鬍的小個子男人;一個是機尾那個上了年紀的夫人,這位夫人給小費都是很慷慨的。米契爾記得她,她搭乘這條航線的飛機已經好幾次了。因此,米契爾並沒有喚醒她。
米契爾剛剛走近,小個子男人馬上醒來,付了一瓶蘇打水和船長牌餅乾的錢──他總共就點了這兩樣東西。
米契爾盡量不去驚動那位女乘客。最後,距離克洛敦約莫只有五分鐘了,他才向她說:「對不起,這是您的帳單,夫人……」
他小心地用手觸碰一下婦人的肩膀。她沒醒來,於是他又加重了一點力氣,搖了搖她。想不到,這位夫人竟從座位上癱了下去。米契爾俯身察看,然後驚惶失色地直起腰來……
空服員艾伯特.戴維斯不大相信地說:「得了吧!你不會是說真的吧?」
「告訴你,是真的!」米契爾直打哆嗦。
「你確定嗎,亨利?」
「十分確定,至少……我猜是突然發病?」
「再幾分鐘就到克洛敦了!」
「如果她只是病了……」
兩個空服員猶豫不決了一兩分鐘才開始行動。米契爾往後艙跑去,從一個座位走到另一個座位,不斷低聲問道:「對不起,先生,請問您是醫生嗎?」
諾曼.蓋爾說:「我是牙科醫生。不過,也許我能幫你忙。」
他從座位上起身。
「我是醫生。」布賴恩醫生說,「發生了什麼事?」
「那頭有個夫人……看起來很不對勁……」
布賴恩醫生站起來,跟隨空服員走過去。那個小個子男人也不動聲色地跟在他們後面。
布賴恩醫生彎腰探看二號座位那個擠成一團的身體。這個婦人歲屆中年,穿了一件深黑色的衣服。
檢查很快結束。他說:「她死了。」
米契爾問道:「您認為她死於……心臟病發作嗎?」
「沒有詳細檢查,不敢斷定。你最後一次看見她是什麼時候?我是說她活著的時候。」
米契爾思索了一下。
「我拿咖啡給她的時候,她還是好好的。」
「多久以前了?」
「大約四十五分鐘前。隨後,我拿帳單去時,還以為她在打盹……」
「她至少死了半個鐘頭。」布賴恩說。
他們的談話引起了注意,乘客們都朝他們這邊望過來,伸著脖子聽著。
「我猜這是突發的,是吧?」米契爾滿懷希望地說。
他執意是心臟命突發,他妻子的姐姐就常突然發病。他個人認為,那是一種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現象。
布賴恩醫生不想涉入太深,只是神情迷惑地搖了搖頭。
有個聲音突然在他旁邊響起,是那個蓄著鬍子的小個子。他說:「她的脖子上有一個小點……」
他說話的態度十分謙卑,像是在向上級報告。
「沒錯。」布賴恩醫生說。
婦人的頭給翻轉過去,是有一個細小的針刺痕跡在喉嚨旁邊。
「對不起,」杜邦父子走過來,他們聽到剛才的討論插嘴說,「你們說有個婦人死了,脖子上有針刺的痕跡?」金.杜邦說得很慢,好像自言自語。
「我能說說自己的想法嗎?不久以前,有一隻黃蜂在這兒飛來飛去。我把牠打死了。」他指了指躺在他咖啡碟裡的黃蜂。「這個不幸的夫人會不會是死於黃蜂的刺螫呢?我聽說過這樣的事。」
「當然有可能,」布賴恩表示同意。「醫學上有過這類的案例,這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如果一個人的心臟衰弱時,更容易造成死亡。」
「現在要怎麼辦?」空服員米契爾問道。「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到達克洛敦了。」
「別緊張,別緊張。」布賴恩醫生站遠一點說,「什麼也不用做,絕對不能碰屍體。」
「是的,先生,我了解。」空服員答道。
布賴恩醫生準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詫異地望了望纏著圍巾的小個子外國人,這個外國人動都沒動一下。
「先生,」布賴恩醫生說,「您最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馬上就到克洛敦了。」
「是呀,先生。」空服員說著提高嗓門。「各位,請回座位坐好!」
「對不起,」矮個子說,「有個東西……」
「有個東西?」
「是呀,有個東西!」
他用鞋尖指了指那樣東西。空服員和布賴恩醫生順著他的動作看去。地上露出一個黑黃色且閃閃發光的小東西,它被死者的黑裙子遮掉一半。
「還有一隻黃蜂嗎?」醫生覺得奇怪。
赫丘勒.白羅跪下,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個小鑷子,細心地夾著,最後他夾著東西直起腰來,說:「沒錯,這很像黃蜂。但它不是黃蜂!」
他把那個東西翻來翻去,讓醫生和空服員看清楚一點。那是一個形狀特別的長針,針尖已受汙染,針頭有黑黃色的軟絲在上面打了結。
「我的天!我的天!」克蘭西先生脫口而出,他剛從座位上走來,正越過空服員米契爾的肩膀在觀望。「太漂亮了!好漂亮的東西,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東西!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你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先生?」空服員問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知不知道?當然知道!」克蘭西先生滿臉驕傲,神氣十足。「先生們,這個東西是某些部落的土著所使用的吹針。這種吹針是從吹管裡吹出去的。現在我無法確切斷定是南美的土人,還是婆羅洲的居民。但是不必懷疑,這正是那種土人的箭,是從吹管射出來的,而且我懷疑針尖……」
「塗了南美印第安人著名的箭毒。」赫丘勒.白羅替他把話說完,並且添了一句:「到底這可不可能呢?」
「當然是很不尋常!」克蘭西先生說得洋洋得意。「簡直是非同凡響!我自己在寫偵探小說,但沒想到竟然在現實生活中真的碰上……」
他不知如何形容。
飛機開始傾斜下滑,仍舊聚在通道上的乘客們顛了一下。接著低空盤旋,準備在克洛敦機場降落。
在布爾歇機場上,九月的太陽還很酷烈。旅客們熱得昏頭昏腦,懶洋洋地步入機場,順著舷梯登上「普羅米修斯」號飛機;幾分鐘後,它就要從巴黎飛往克洛敦了。
珍.格雷是最後一批走進客機的乘客,她毫不費力地找到了自己的第十六號座位。有幾個人則繼續穿過隔門、小廚房、兩間盥洗室,朝前艙走去。大多數的人已經就座完畢。通道的另一面,有人在起勁地交談。其中一個聲音刺耳尖銳,而且大都是她在發話,珍稍微皺了皺眉頭,她很熟悉這種類型的聲音。
「親愛的,完全不可思議,我一點兒也不知道……你說在哪兒?在鐘拉潘嗎?哦,對了。不,在盧比納……是,就是同一班老人……不,不,當然囉,我們坐在一塊兒吧。難道不行嗎?誰?啊,我明白了……」
然後是一個外國人謙遜、愉快地回答:「噢,很樂意,請坐吧,太太!」
珍偷看了外國人一眼。
這是一個年紀不輕的小個子,蓄著偌大的八字鬍,蛋形腦袋;他把自己隔著走道而鄰接珍的座位恭敬地讓出來。
珍微微扭過頭,瞧見那兩個逼迫這個外國人禮讓座位的婦人。她們提到盧比納激起了珍的好奇;因為她也剛剛去過那兒。她記起最後在哪兒見過其中一位婦人──在賭桌邊見過。當時,這個婦人一會兒握緊拳頭,一會兒又鬆開拳頭;一張精心雕琢、活像尊翠斯騰瓷偶的臉蛋,一會兒發白,一會兒又緋紅。珍一下就想起這個人的姓名。當時,一個女友曾向她提到這個婦人:「她雖然也是個貴夫人,但並不是貨真價實。從前,她是在劇團唱歌的。」女友的口吻中有一種輕蔑和嘲笑。這個女友名叫梅西,她的工作挺不錯─充當按摩女郎,她能「消除」顧客過度肥胖的現象。
「可是另一個婦人,」珍心想,「就是個名副其實的貴夫人。住在郡鄉、習慣騎馬活動的類型。」但旋及她便忘了那兩位婦人,而被窗外機場的景象所吸引。好多飛機都在等待起飛,有一架看來好像是一條金屬蜈蚣。
珍的正對面坐著一位身穿鮮豔淺藍絨線衫的年輕人。為了不跟這年輕人的視線相遇,她打定主意不朝正前方瞧,絕對不!
機師們用法語互相吆喝一陣──引擎隆隆響起─停歇─再響起─障礙物排開─飛機終於起飛了。
珍屏住氣息,這是她一生中的第二次飛行,她仍舊感到十分興奮。飛機往前疾馳,看來好像要撞上圍牆了……不,眨眼間,他們已經在大地上空了,上升,再上升,盤旋升高,布爾歇機場遠遠落在下面了……
飛機開始了午餐服務,乘客總共有二十一人,十人在前面的客艙,十一人在後艙。機組有兩名駕駛員和兩名空服員,引擎的噪音被高超的技術消音了,甚至耳朵也無需塞上棉花。不過,還是有其他噪音,交談仍然困難,只能胡思亂想。
普羅米修斯號越過法國領土上空朝英吉利海峽飛去,後艙的乘客都在想著自己的心事。
珍.格雷想道:「絕不瞧他!不,絕不,我要望著窗外想心事,我得挑件事情想想,這是最好的辦法。這樣我才不會慌亂。我得從開始想起,好好回溯一番。」
她的思緒回到所謂的「開始」,也就是買下愛爾蘭賽馬會賭票的那天。那的確是個奢侈的行為,卻令人充滿期待……
在珍和其他五個年輕小姐工作的美容院裡,是一片嘻笑聲和嘈雜聲。
「如果你贏了大獎,你要做什麼啊,親愛的?」
「我自有打算。」
接著是計畫,一堆幻想,一堆爭論……
結果她沒得到「大獎」,但贏了整整一百英鎊!
整整一百英鎊。
「花掉一半,另一半存起來,你永遠料不到將來會發生什麼事。」
「我要是你,珍,我寧可買一件皮大衣,上好的皮大衣。」
「來趟海上之旅如何?」
一想到海上之旅,珍的心不禁怦怦直跳。但最後,她還是忠於她的第一個選擇:到盧比納去消磨一個星期。她的許多客人都去過盧比納,或者剛從那裡回來……
珍敏捷的巧手正給顧客理好一綹綹頭髮,捲成服服貼貼的鬈髮,嘴裡向顧客提出一些反射性問題:「您多久沒燙頭髮了,太太?」「您的髮色好特別呀,太太。」「今年夏天很棒,不是嗎,太太?」腦中卻想著為什麼就我不能去盧比納?現在,她終於能暢遊一回了。
對她來說,衣著不成問題,珍和大多數在倫敦鬧區工作的女孩一樣,只要花很少一點兒錢,就能把自己打扮得既時髦又漂亮,指甲,化妝,髮型,完全無可挑剔。
於是,珍去了盧比納。
有沒有可能這十天在盧比納的歡樂都在那次付之一炬?
那是在賭輪盤時發生的一件插曲。那幾天的晚上,珍都放任自己小賭一把,但不管怎樣,她都絕不超過某個限額。這天一反迷信傳統的,一開頭她就很不走運。她已經賭了四個晚上,這一次是她今天的最後一筆賭注了,之前珍一直小心地把賭注押在她彩色號碼上。她贏了一點,但多半是輸;此刻,她把錢捏在手裡,屏息等待。
還剩下兩個號碼沒人下,5號和6號。要把最後一把下在其中一個號碼上嗎?可是下在哪個號碼上呢?5還是6?哪個她比較有感覺?
5號就要翻轉過去,小球滾動了。珍伸出手,6,她放在6上。
正巧,她和對面的一個賭客同時下注:她選中了6,他選中了5。
「賭注下定啦。」莊家說。
小球跳了一下就不動了。
「5號,紅的,單數,贏啦。」
珍懊惱得幾乎叫了一聲。莊家掃進賭金,付錢給贏家,坐在珍對面的賭客問道:「你不拿走自己贏得的錢嗎?」
「我贏的錢?」
「是呀。」
「但我下的是6呀!」
「不,下6的是我,你下的是5。」
他笑著說,笑容非常迷人。白白的牙齒,棕黑的臉蛋,藍眼睛,短短的鬈髮。
珍狐疑地拿起贏得的錢。這是不是搞錯了?她有點困惑。或許她是下在5上了。她懷疑地瞅了那陌生人一眼。他又回了一個微笑。
「這就對了,」他說,「如果你把錢留在桌上,別人馬上就會把它拿走!這是一定的。」
說著,他親切地點點頭就走了。這招也很貼心。否則珍可能認為,他僅僅為了跟她結識,而把贏的錢讓給她。不過,他不是那種人,他那麼親切……而此刻,他竟正好坐在她對面!只是一切都結束了──所有的錢已花光了,巴黎的最後兩天也一晃而過(唉,無聊的最後兩天),而現在手中機票上的目的地一欄,印的已是家園的名字。
接下來呢?
「何必去猜測將來如何,」珍阻止自己胡思亂想。「幹嘛瞎操心?」
彼此閒聊的兩個婦人已不作聲了,她望過走道。那位翠斯騰瓷偶夫人氣惱地嘟囔著,瞧了瞧裂掉的指甲。她撳了撳電鈴,當穿著雪白衣服的空服員來到她面前時,她說:「叫我的女傭人到我這兒來一下。她在前艙。」
「是的,夫人。」
空服員周到、敏捷、迅速地走了。接著馬上出現了一個頭髮烏黑的年輕法國女孩。她穿了一件黑色連衣裙,拿來了一個小珠寶箱。霍伯里夫人用法國話吩咐這個女孩。
「馬德琳,去把那個紅色摩洛哥皮的化妝箱拿來給我。」
女傭人朝機尾堆放蓋毯和行李的地方走去。不一會,這女孩就拿了一個小化妝箱回來。西塞莉.霍伯里夫人從女傭手裡接過小箱子,就遣走她了。
「好了,馬德琳,這個就留在我這兒。」
女傭人再度離開。霍伯里夫人揭開箱蓋,從漂亮的箱子裡取出一把指甲銼子。然後,對著一個小鏡子久久地研究自己的面孔,一會兒撲點兒香粉,一會兒又塗塗口紅。
珍輕蔑地撇了撇嘴,眼光落在前面的其他乘客身上。
坐在兩個夫人後面的,是那個和「真貴婦」交換座位的矮小外國人。他脖子上緊緊圍了一條根本用不著的圍巾,似乎睡熟了,但或許是珍凝視的目光驚動了他,他張開眼望望珍後,又闔上眼瞼。
跟他並排而坐的是一個體面而頭髮斑白的男人,膝上放一個打開的橫笛外盒,手裡呵護備至地擦拭著一根橫笛。怪了,珍想到,他看來根本不像個音樂家,而像是律師或醫生。
坐在他們後面的是兩個法國人。一個蓄著落腮鬍;另一個年輕得多,大概是前者的兒子。兩人正比手畫腳地熱烈談論什麼。
至於珍自己這排的視線,則全被那個穿藍色絨線衫的男人給遮住了。也說不出理由,反正珍打定主意不去看他。
「我怎麼會這麼……好像才十七歲似的!」珍懊惱地責怪自己。
對面的這位諾曼.蓋爾則在尋思。「她真漂亮,實在漂亮!她一定記得我。記得她的賭金被掃走時,她有多沮喪啊。但後來看到她得到那筆錢的喜悅,我什麼都值得了!我到底做對了……她的微笑真叫人喜愛:健康的牙齒,堅固的牙床。活見鬼,我怎麼這麼激動!沉住氣,小夥子!」
他向旁邊走過的空服員說:「給我一份冷牛舌。」
霍伯里伯爵夫人則在思忖。「我的天,究竟該怎麼辦呢?這下糟透了。我看只有一個辦法,只要我膽子夠大。這我能夠辦到嗎?我能矇混過去嗎?我的神經快受不了了。全都因為古柯鹼。我幹嘛要碰那東西呢?我的面孔看來好嚇人,太嚇人啦!維妮塔.克爾那爛女人在這兒,就更糟糕了。她老是盯著我瞧,好像我是一個髒東西。她想把斯蒂芬據為己有,可是希望落空了。那張大長臉弄得我好緊張,真的和馬臉沒兩樣。我恨死了這些鄉紳階級的貴族。天哪,我該怎麼辦呀!應當想點什麼辦法!那老妖精可不是說著玩的……」
霍伯里夫人從盒裡取出一根香菸,把它插在長菸嘴裡,她的兩隻手都在顫抖。
維妮塔.克爾女爵嘀咕道:「哼,無恥的婊子!這就是她。或許理論上她貞潔無瑕,但她骨子裡根本是個妓女的料。可憐的斯蒂芬,他要能離開她就好了……」
她也拿出菸盒,就著西塞莉.霍伯里遞上的火柴點了火。
空服員阻止她。「對不起,夫人,這裡禁止吸菸!」
「見鬼!」霍伯里夫人表示不滿。
赫丘勒.白羅想道:「那邊那位小姐真漂亮。她有一個堅毅的下巴,可是什麼使她如此惶惶不安呢?她為什麼一直迴避對面那個英俊男子的目光呢?看來,她是認識他的,他也是認識她的……」
飛機稍稍下降。
「啊,我的肚子。」赫丘勒.白羅哼了一聲,牢牢地閉上了眼睛。
跟他並排的布賴恩醫生小心地撫摸著自己的橫笛,心裡琢磨著:「我無法下定決心,我就是無法下決心。這是我職業生涯的一個轉捩點啊……」
他從盒子裡小心、愛戀地取出橫笛。音樂……在樂曲聲中可以忘卻人生的一切憂慮。他笑咪咪地把橫笛拿到唇邊,接著又將它放下。蓄著小鬍子的那位矮個子就在旁邊打盹。
飛機突然劇烈地搖晃了一下,晃得人眼睛都發昏了。布賴恩醫生很高興,他從不暈車,也不暈船,坐飛機也不會暈機。
老杜邦先生激動地向小杜邦嚷嚷起來。
「這一點用不著懷疑!他們─德國人、英國人、美國人,全都錯了!史前陶器發明的日期,他們說得根本不準!比方說,薩邁拉陶器……」
金.杜邦個子很高,彬彬有禮,樣子有點懶洋洋,他溫和地反駁說:「你應當拿出憑據!還有塔爾.哈雷夫和薩基耶.戈茲……」
討論繼續下去。
阿曼德.杜邦先生打開一個飽經滄桑的航空旅行袋。
「你看看這些庫爾德菸斗,簡直像是現代作品。菸斗上的裝飾就像那個西元前五千年的陶器……」
阿曼德.杜邦先生猛然一揮,差點把空服員剛才放在他面前的一個盤子碰掉了。
克蘭西先生是個作家,寫過許多偵探小說;他從諾曼.蓋爾後面的座位上站起來,走到客艙尾部去,並從自己放在那兒的外套口袋裡掏出一份英國布萊蕭火車時刻表,然後拿著它回來,想要為自己的小說構思一個完全的「不在場證明」。
坐在克蘭西先生後面的賴德先生心裡直翻騰:「我一定要堅持到底,只是會很辛苦。我不知道怎麼提高下一筆股息……如果轉讓股份那就嗚呼哀哉了……哦,該死!」
諾曼.蓋爾站起身來,到廁所去。他才離開,珍立即從手提包裡取出小鏡子,不安地看了看自己,搽上一點香粉,再塗上口紅。
空服員把咖啡放在她面前。她望了望窗外,下面是金光閃耀而蔚藍的英吉利海峽。
正當克蘭西先生認真安排晚上七點五十五分在沙里布的故事細節時,一隻黃蜂在他頭頂上討厭地嗡嗡盤旋,克蘭西揮手,沒打到牠,黃蜂於是飛到遠處去糾纏杜邦父子的咖啡杯。
膽大的金.杜邦準確一擊,打死了黃蜂。
客艙恢復平靜。談話聲停止,每個人都專注想著自己的心事。
客艙的深處,在二號座位上,吉塞爾太太的頭忽然向前伸出一點,看起來像是睡著了。但她不是在睡覺,她也沒在說話或思考。
吉塞爾太太已經死了……
02重大發現
資深空服員亨利.米契爾快速地從一個座位走到另一個座位,把帳單送給每個乘客。再過半小時,飛機就要到達克洛敦。米契爾收下鈔票和小銀幣,一面哈腰,一面不住地說:「謝謝,先生。謝謝,夫人。」在那兩個法國人的小桌前面,他不得不等候一兩分鐘,因為他們正在比手畫腳地高談闊論。「在這兒,大概撈不到多少小費了。」米契爾抑鬱地想道。
有兩個乘客正在打盹。一個是蓄著八字鬍的小個子男人;一個是機尾那個上了年紀的夫人,這位夫人給小費都是很慷慨的。米契爾記得她,她搭乘這條航線的飛機已經好幾次了。因此,米契爾並沒有喚醒她。
米契爾剛剛走近,小個子男人馬上醒來,付了一瓶蘇打水和船長牌餅乾的錢──他總共就點了這兩樣東西。
米契爾盡量不去驚動那位女乘客。最後,距離克洛敦約莫只有五分鐘了,他才向她說:「對不起,這是您的帳單,夫人……」
他小心地用手觸碰一下婦人的肩膀。她沒醒來,於是他又加重了一點力氣,搖了搖她。想不到,這位夫人竟從座位上癱了下去。米契爾俯身察看,然後驚惶失色地直起腰來……
空服員艾伯特.戴維斯不大相信地說:「得了吧!你不會是說真的吧?」
「告訴你,是真的!」米契爾直打哆嗦。
「你確定嗎,亨利?」
「十分確定,至少……我猜是突然發病?」
「再幾分鐘就到克洛敦了!」
「如果她只是病了……」
兩個空服員猶豫不決了一兩分鐘才開始行動。米契爾往後艙跑去,從一個座位走到另一個座位,不斷低聲問道:「對不起,先生,請問您是醫生嗎?」
諾曼.蓋爾說:「我是牙科醫生。不過,也許我能幫你忙。」
他從座位上起身。
「我是醫生。」布賴恩醫生說,「發生了什麼事?」
「那頭有個夫人……看起來很不對勁……」
布賴恩醫生站起來,跟隨空服員走過去。那個小個子男人也不動聲色地跟在他們後面。
布賴恩醫生彎腰探看二號座位那個擠成一團的身體。這個婦人歲屆中年,穿了一件深黑色的衣服。
檢查很快結束。他說:「她死了。」
米契爾問道:「您認為她死於……心臟病發作嗎?」
「沒有詳細檢查,不敢斷定。你最後一次看見她是什麼時候?我是說她活著的時候。」
米契爾思索了一下。
「我拿咖啡給她的時候,她還是好好的。」
「多久以前了?」
「大約四十五分鐘前。隨後,我拿帳單去時,還以為她在打盹……」
「她至少死了半個鐘頭。」布賴恩說。
他們的談話引起了注意,乘客們都朝他們這邊望過來,伸著脖子聽著。
「我猜這是突發的,是吧?」米契爾滿懷希望地說。
他執意是心臟命突發,他妻子的姐姐就常突然發病。他個人認為,那是一種人人都能理解的普遍現象。
布賴恩醫生不想涉入太深,只是神情迷惑地搖了搖頭。
有個聲音突然在他旁邊響起,是那個蓄著鬍子的小個子。他說:「她的脖子上有一個小點……」
他說話的態度十分謙卑,像是在向上級報告。
「沒錯。」布賴恩醫生說。
婦人的頭給翻轉過去,是有一個細小的針刺痕跡在喉嚨旁邊。
「對不起,」杜邦父子走過來,他們聽到剛才的討論插嘴說,「你們說有個婦人死了,脖子上有針刺的痕跡?」金.杜邦說得很慢,好像自言自語。
「我能說說自己的想法嗎?不久以前,有一隻黃蜂在這兒飛來飛去。我把牠打死了。」他指了指躺在他咖啡碟裡的黃蜂。「這個不幸的夫人會不會是死於黃蜂的刺螫呢?我聽說過這樣的事。」
「當然有可能,」布賴恩表示同意。「醫學上有過這類的案例,這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如果一個人的心臟衰弱時,更容易造成死亡。」
「現在要怎麼辦?」空服員米契爾問道。「再過幾分鐘,我們就要到達克洛敦了。」
「別緊張,別緊張。」布賴恩醫生站遠一點說,「什麼也不用做,絕對不能碰屍體。」
「是的,先生,我了解。」空服員答道。
布賴恩醫生準備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他詫異地望了望纏著圍巾的小個子外國人,這個外國人動都沒動一下。
「先生,」布賴恩醫生說,「您最好回到自己的位子上。馬上就到克洛敦了。」
「是呀,先生。」空服員說著提高嗓門。「各位,請回座位坐好!」
「對不起,」矮個子說,「有個東西……」
「有個東西?」
「是呀,有個東西!」
他用鞋尖指了指那樣東西。空服員和布賴恩醫生順著他的動作看去。地上露出一個黑黃色且閃閃發光的小東西,它被死者的黑裙子遮掉一半。
「還有一隻黃蜂嗎?」醫生覺得奇怪。
赫丘勒.白羅跪下,從上衣口袋裡取出一個小鑷子,細心地夾著,最後他夾著東西直起腰來,說:「沒錯,這很像黃蜂。但它不是黃蜂!」
他把那個東西翻來翻去,讓醫生和空服員看清楚一點。那是一個形狀特別的長針,針尖已受汙染,針頭有黑黃色的軟絲在上面打了結。
「我的天!我的天!」克蘭西先生脫口而出,他剛從座位上走來,正越過空服員米契爾的肩膀在觀望。「太漂亮了!好漂亮的東西,我這輩子從沒見過這麼漂亮的東西!簡直令人不敢相信!」
「你可不可以說清楚一點,先生?」空服員問道,「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知不知道?當然知道!」克蘭西先生滿臉驕傲,神氣十足。「先生們,這個東西是某些部落的土著所使用的吹針。這種吹針是從吹管裡吹出去的。現在我無法確切斷定是南美的土人,還是婆羅洲的居民。但是不必懷疑,這正是那種土人的箭,是從吹管射出來的,而且我懷疑針尖……」
「塗了南美印第安人著名的箭毒。」赫丘勒.白羅替他把話說完,並且添了一句:「到底這可不可能呢?」
「當然是很不尋常!」克蘭西先生說得洋洋得意。「簡直是非同凡響!我自己在寫偵探小說,但沒想到竟然在現實生活中真的碰上……」
他不知如何形容。
飛機開始傾斜下滑,仍舊聚在通道上的乘客們顛了一下。接著低空盤旋,準備在克洛敦機場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