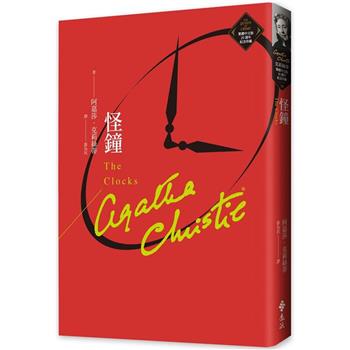序曲
九月九日下午,和其他日子沒什麼兩樣。這天捲入這樁案子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認為這場災難事先有什麼徵兆(住在威布蘭新月社區四十七號寓所的帕克女士例外,她平時的預感特別強,而且事後總會長篇大論地描述她所經歷的特異徵兆和恐懼。可是,帕克夫人住在四十七號,離十九號寓所很遠,那兒發生的一切幾乎和她沒有任何關聯,照理說,是輪不到她出現預感的)。
對卡文迪打字社的經理K.馬丁代小姐來說,九月九日這天枯燥無味一如既往。電話鈴聲不斷,打字機叮咚作響,工作量與平常無異,沒有特別新鮮有趣的事。在兩點三十五分之前,九月九日這天和其他日子沒什麼不同。
兩點三十五分,馬丁代小姐按下對講機,在外間辦公室的艾娜.布蘭答覆時聲音和往常一樣,呼吸沉重而且帶著鼻音,因為她嘴裡正含著一塊太妃糖。
「有什麼吩咐,馬丁代小姐?」
「艾娜……我告訴過你,接電話時不要用這種方式說話,發音要清晰、屏住呼吸壓住喘息聲。」
「對不起,馬丁代小姐。」
「這樣就好多了。如果你注意的話,你是可以做到的。叫希拉.韋布進來一下。」
「她吃午飯還沒回來呢,馬丁代小姐。」
「哦,」馬丁代小姐瞄了一眼桌上的鐘,兩點三十六分,已經遲到六分鐘。最近希拉.韋布總是顯得沒精打采的。「她一回來就叫她進來見我。」
「好的,馬丁代小姐。」
艾娜重新把太妃糖推回舌頭中央,一邊起勁地吮吸著,一邊繼續打亞曼.萊文的小說《赤裸之愛》。儘管萊文先生煞費苦心,小說中的性愛描寫還是非常乏味──大多數讀者讀他的小說時也都這麼覺得。要為「世上最無趣的便是乏味之色情小說」舉例,他便是最佳典範。雖然有俗麗的包裝和挑逗的書名,他的小說銷量仍逐年下降;而且,他上回的打字費已經催了三次都還沒給。
辦公室門開了。希拉.韋布走了進來,看起來有點氣喘吁吁。
「虎斑貓1在找你。」艾娜說。
希拉.韋布做了個鬼臉說:「真倒楣,偏偏在我遲到的時候找我!」
她理一理頭髮,拿起記事本和筆,敲了經理室的門。
馬丁代小姐從辦公桌上抬起頭來。她四十多歲年紀,看起來精明幹練,高高綰起的頭髮髮色泛紅,再加上教名凱瑟琳與貓諧音,使她得到了虎斑貓的綽號。
「你遲到了,韋布小姐。」
「對不起,馬丁代小姐,路上塞車。」
「每天這個時間,路上總是塞車,你應該考慮到這點。」她查看一下記事本,接著說:「有位佩瑪小姐打電話來說,她三點鐘需要一名速記,而且特別指名要你去,你以前為她服務過嗎?」
「我不記得了,馬丁代小姐,至少最近沒有。」
「她的地址是威布蘭新月社區十九號。」
她停了一下,投以詢問的目光,但希拉.韋布搖搖頭說:「我不記得去過那兒。」
馬丁代小姐瞄了一眼桌上的鐘說:「三點鐘,你應該可以準時到達。你下午還有其他差事嗎?哦,對了,」她低頭看了看手邊的記事本。「你得去柯琉飯店的波帝教授那兒,五點鐘。所以你最好五點之前回來,如果回不來,我可以叫珍妮特去。」
她點了點頭表示事情說完了,於是希拉走回外間辦公室。
「有什麼好玩的嗎,希拉?」
「又是無聊的一天。先去威布蘭新月社區一個老小姐那兒,五點鐘還要去波帝教授那兒──都是些老古董的名字!真希望有時也發生一點刺激的事。」
馬丁代小姐辦公室的門開了。
「我想起來我記了一個備要,希拉,就是到了那裡,如果佩瑪小姐還沒回來,你可以直接進屋子裡去,大門不會上鎖。進去後,到門廳右邊的房間等著。你記住了嗎?要不要我寫下來?」
「我記住了,馬丁代小姐。」
馬丁代小姐退回她的密室。
艾娜.布蘭偷偷鑽到椅子下面,拿起一隻俗氣的皮鞋,還有一個從鞋底掉下來的尖錐型鞋跟。
「我這樣怎麼回家呢?」她哀嘆地說。
「唉,別大驚小怪了,到時候就有辦法了。」另外一個女孩邊說邊繼續打她的字。
艾娜嘆了口氣,放上一頁空白紙張,開始打入:「情欲已牢牢控制住他,他用瘋狂的手指撕開她薄軟的胸罩,強迫她躺在肥皂沫上。」
「該死。」艾娜說,伸手去取擦子。
希拉拿起她的手提包,走了出去。
威布蘭新月社區是十九世紀八○年代一位維多利亞建築師的奇幻作品,它的外觀呈半月形,由兩排背靠背的房舍和花園構成。對不熟悉其方位的人來說,這種奇特的結構會造成很多麻煩:走在社區外圈的人不容易發現前段房號的房舍,走在內環的人也會因為找不到後段號碼而摸不著頭腦。這些房子乾淨整潔,陽台設計精巧,看來十分高雅莊嚴,它們幾乎不曾受到現代化潮流的影響,至少就其外觀而言是這樣。廚房和浴室通常是最先感受到現代化氣息的地方。
這裡的十九號寓所沒什麼特別之處,窗簾潔淨,前門的銅製把手光滑潔亮,小路兩旁種著一排薔薇樹,一直延伸到前門。
希拉.韋布推開大門,走到正門處按了門鈴。沒人來應門。等了一兩分鐘後,她照著指示,轉動門把,打開大門走了進去。門廳右邊的門半開半掩著,她輕輕敲了敲門,等了一下,然後就走了進去。
這是間非常普通但十分溫馨的客廳,現代樣式的家具布置得稍嫌擁擠。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各式各樣的鐘──房間角落有一座滴答作響的老爺鐘、壁爐台上有座德勒斯登瓷鐘、書桌上有個銀色的旅行鐘、放在壁爐旁古董架上的是價格昂貴的鍍金小鐘、在靠窗的桌子上,則是一個已褪色的皮革旅行鐘,上面模模糊糊地印著「蘿絲瑪莉」的鍍金字樣。
希拉.韋布有點驚奇地看著書桌上那個鐘。鐘面上顯示的時間是四點十幾分。她把目光轉向壁爐架上那個鐘,上面的時間也一樣。
希拉驀地大吃一驚,因為她頭頂上方突然響起嘰嘰嘎嘎的聲音。一隻布穀鳥從牆上木刻鐘的小門裡蹦了出來,響亮清晰地叫:「布穀,布穀,布穀!」刺耳的聲音彷彿是一種威脅。隨後小門啪地一聲關上,布穀鳥也不見了。
希拉.韋布微微一笑,繞著沙發的一端走過去。接著她戛然停住了腳步,倒抽一口氣。
地板上呈大字形仰躺著一個男人,他的眼睛半開,毫無光彩,在他深灰色西裝上頭有一灘暗色溼痕。希拉幾乎是機械式地彎下身子,摸了一下他的臉頰……涼的,再摸摸他的手,也是涼的……她摸了一下那塊溼痕,又快速地把手抽回,驚恐萬狀地盯著它看。
這時候,她聽到外面有開門的嘎嘎聲。她木然地把頭轉向窗外,看到一位婦女的身影正沿著小路匆匆忙忙走來。希拉遲鈍地嚥了一口唾沫──她的喉嚨非常乾燥。她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動彈不得,也無法叫喊,只直愣愣地盯著前方。
門開了,一個高大年邁的婦人走了進來,手裡提著購物袋。她灰色的鬈髮從前額朝後梳,一雙藍色的眼睛又大又亮。她的眼神瞟過希拉,對她視若不見。
希拉發出了微弱的聲音,僅僅是一聲輕微的喊叫。婦人的藍色大眼轉向她,嚴厲地問:「誰在那兒?」
「我……他……」
希拉突然停住不說了,因為老婦人繞著沙發正迅速地朝她走來。
突然希拉尖叫起來。
「別……別……你就要踩到那個……他身上了……他死了。」
01科林.拉姆的自述
用警察的術語來說,九月九日下午兩點五十九分,我正沿著威布蘭新月社區朝西行走。這是我第一次到威布蘭新月社區,而且老實說,這社區把我搞得暈頭轉向。
儘管我猜測成真的可能性愈來愈小,但我仍日復一日,益加持之以恆地去執行我的猜測。我就是這種個性。
我要找的寓所是六十一號。找得到嗎?不行,我找不到。我從一號寓所仔仔細細地找到三十五號,但走到這裡威布蘭新月社區好像就到盡頭了。路底是一條明確標著艾巴尼路的通道橫在面前。我轉回頭,道路北面沒有任何房屋,只有一堵牆。牆後面有一排排現代公寓聳立而起。這些公寓的入口顯然在另一條馬路上,幫不上忙。
我抬頭查看剛剛經過的宅邸號碼: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黛安娜小屋(應該就是二十號,門柱上一隻黃色的貓正用爪子洗臉),十九……
這時十九號的門開了,一個女孩像枚子彈似地從裡面衝了出來,沿小道飛奔著,她邊跑邊大聲尖叫,使她更像一枚呼嘯而至的飛彈。她叫聲又尖又細,悲慘而淒厲。穿過院門後,這個女孩衝過來,和我撞了個滿懷,衝力之大幾乎把我撞出了人行道。她不只撞我,還緊緊抓住我不放……那種抓法顯得非常瘋狂、絕望。
「冷靜,」我站穩身子,恢復了平衡後說。我輕輕搖了她一下。「冷靜一下。」
女孩安靜了下來。她仍然緊緊抓住我不放,但已不再尖叫,相反地,她大口喘著氣……低沉地嗚咽著。
我不敢說我擅長應付這種情況。我問她有什麼事,但馬上意識到這個問題太軟弱無力,於是改口問道:「發生什麼事了?」
女孩深深吸了一口氣。
「那裡!」她朝身後指了一下。
「怎麼了?」
「有個男的躺在地板上……死了……她就要踩到他身上了。」
「誰要踩到?為什麼?」
「我想……是因為她眼睛看不見。那個男人身上都是血,」她低頭看了看,鬆開緊抓住我不放的手。「我身上也有,我也沾到血了。」
「是有血,」我邊說邊看看我大衣袖子上的血跡。「我身上現在也沾到了,」我指指袖子,嘆了口氣,衡量了一下當前的情勢。「你最好帶我進去看一下。」我說。
聽到這裡,她又開始劇烈抖動起來。
「我不……我不能……我不想再進去了。」
「那好吧。」
我看了看四周,似乎沒有合適的地方來安頓這個處於半暈眩狀態的女孩。我輕輕攙扶她坐在人行道上,靠著鐵圍籬。
「你待在這裡,」我說,「等我回來,我不會去很久。你不會有事的。如果你覺得頭暈,就向前傾,把頭放在兩膝之間。」
「我……我現在覺得好多了。」
她不太確定地說道,但我不想再討論這點。我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一下,然後沿著小徑快步走去。穿過正門進了屋子,我在門廊猶豫了一下,朝左邊的門內望去,那是個空無一人的餐廳。我穿過門廳,走進對面的客廳。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位頭髮灰白的老婦人端坐在椅子上。當我走進房內時,她迅速地轉過頭來問道:「是誰?」
我立刻意識到,這位婦人是個盲人。她那雙直盯著我的眼睛,實際上是集中在我左耳後的某一點。
我馬上答話,並直入正題說:「一位小姐從這裡衝到大街上,說這裡有個男人死了。」
說這些話時我自己都覺得非常荒謬可笑。在這樣整潔乾淨的房間裡,還有一位安詳的老人雙手交握坐在椅子上,看起來不該有這種事。
但她立刻回答我。
「在沙發後面。」她說。
我繞著沙發的一角走過去,接著看到了一雙伸出來的手臂,一雙暗淡無光的眼睛,還有凝固的血漬。
「這是怎麼發生的?」我猛然發問。
「我不知道。」
「可是……好吧,他是誰?」
「我不清楚。」
「我們必須通知警察。」我向四周看了看問道:「電話在哪裡?」
「我沒有電話。」
我更仔細看著她。
「你住在這兒?這是你的房子?」
「是的。」
「可以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
「當然可以。我買東西回來──」我注意到購物袋放在靠門的一把椅子上。「我進了屋子以後,馬上就察覺到有人在房裡。一個人眼睛看不見的時候,感覺會特別靈敏。我問誰在那裡,但沒人回答,只聽見有個人急促的呼吸聲。我朝那個聲音走過去……那時這個人大聲尖叫起來,說什麼有人死了、我就要踩在他身上了,接著這個人又尖叫著從我身邊衝了出去。」
我點了點頭,她們的陳述是吻合的。
「那麼你接下來做了什麼?」
「我小心地朝前走,然後我的腳碰到了一個東西。」
「然後呢?」
「我跪下來,摸到了什麼東西……是一隻男人的手。手都涼了,已經完全沒有脈搏……於是我站了起來,走到這兒坐下,等人來。一定會有人來。那個女孩,不管她是誰,一定會去報警。我認為最好還是不要離開房間。」
這位婦人的鎮靜讓我印象深刻。她沒有大聲喊叫,也沒有嚇得東倒西歪地逃出屋外,她只是平靜地坐下來等待。這是很明智的做法,但得要有很大的能耐。
她問道:「你是誰啊?」
「我叫科林.拉姆,剛才碰巧從這兒路過。」
「那個女孩在哪兒?」
「我把她安頓在門口,她受到很大的驚嚇。離這裡最近的電話亭在哪裡?」
「沿著這條路往前走,大約五十碼遠的轉角處有個電話亭。」
「知道了,我記得曾從那兒經過。我要打個電話給警察,你─」
我猶豫了一下,不知道該說:「你能不能一直待在這裡?」還是說:「你在這裡沒問題吧?」
她解決了我的困境。
「你最好讓那個女孩到屋子裡來。」她果斷地說。
「我不知道她願不願意進來。」我遲疑不決地說。
「當然不要帶她到這個房間,讓她待在另一邊的餐廳裡。告訴她,我正在為她泡茶。」
她站了起來,朝我走來。
「可是,你還可以泡──」
一絲冷笑在她臉上一閃而過。
「年輕人,我搬來住進這所房子是十四年前的事了,每天三餐都是我自己在廚房裡動手做的。眼睛看不見並不表示我毫無用處。」
「對不起,我說傻話了。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名字?」
「蜜莉森.佩瑪……小姐。」
我出了門,沿著小路朝前走。那個女孩抬頭看我,掙扎著要站起來。
「我……我覺得現在稍微好些了。」
我扶她站了起來,愉快地說:「很好。」
「那兒……那兒有個人死了,對不對?」
我說是的。
「是有人死了。我正要到前面那個電話亭,打電話通知警方。如果我是你,我就到屋子裡等著。」接著我提高嗓門,以防她不同意,「你到餐廳去──進屋子後的左邊,佩瑪小姐正在為你準備茶水。」
「她就是佩瑪小姐?她眼睛看不見?」
「對。當然了,這對她一定也是個打擊,但她非常理性。來,我帶你進去。在警察到來之前,喝杯茶對你會有好處。」
我搭著她的肩膀,扶著她沿小徑往前走。我讓她舒適地坐在餐廳的桌子旁,然後匆忙走向電話亭。
一個死板的聲音回答道:「克勞汀警察局。」
「哈凱松警探在嗎?」
那個聲音又小心翼翼地問道:「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你是哪一位?」
「告訴他我是科林.拉姆。」
「請稍等一下。」
我等了一會兒,然後聽到了迪克.哈凱松的聲音。
「科林嗎?沒想到你會這時候找我。你在哪兒?」
「克勞汀,確切地說,是在威布蘭新月社區。這裡的十九號寓所有一個男人躺在地板上,死了,我想是被刺死的,死了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誰發現的?你嗎?」
「不是,我是不相干的路人。是有個女孩像隻地獄來的蝙蝠,突然從屋內飛奔而出,幾乎把我撞倒在地。她說有個男人躺在地板上死了,一個瞎眼太太踩在他身上。」
「你不是在騙我吧?」迪克露出懷疑的口氣。
「聽起來確實讓人難以置信,我承認。可是,事實就是我說的這樣。那個盲眼女士是屋主蜜莉森.佩瑪小姐。」
「她正在踩那位死者嗎?」
「不是你想的那樣。她的眼睛看不見,所以不知道這個人躺在那兒。」
「我們馬上行動,你在那兒等我。那個女孩你怎麼處理?」
「佩瑪小姐正在為她泡茶。」
迪克說,這聽起來還挺溫馨的。
九月九日下午,和其他日子沒什麼兩樣。這天捲入這樁案子的那些人,沒有一個認為這場災難事先有什麼徵兆(住在威布蘭新月社區四十七號寓所的帕克女士例外,她平時的預感特別強,而且事後總會長篇大論地描述她所經歷的特異徵兆和恐懼。可是,帕克夫人住在四十七號,離十九號寓所很遠,那兒發生的一切幾乎和她沒有任何關聯,照理說,是輪不到她出現預感的)。
對卡文迪打字社的經理K.馬丁代小姐來說,九月九日這天枯燥無味一如既往。電話鈴聲不斷,打字機叮咚作響,工作量與平常無異,沒有特別新鮮有趣的事。在兩點三十五分之前,九月九日這天和其他日子沒什麼不同。
兩點三十五分,馬丁代小姐按下對講機,在外間辦公室的艾娜.布蘭答覆時聲音和往常一樣,呼吸沉重而且帶著鼻音,因為她嘴裡正含著一塊太妃糖。
「有什麼吩咐,馬丁代小姐?」
「艾娜……我告訴過你,接電話時不要用這種方式說話,發音要清晰、屏住呼吸壓住喘息聲。」
「對不起,馬丁代小姐。」
「這樣就好多了。如果你注意的話,你是可以做到的。叫希拉.韋布進來一下。」
「她吃午飯還沒回來呢,馬丁代小姐。」
「哦,」馬丁代小姐瞄了一眼桌上的鐘,兩點三十六分,已經遲到六分鐘。最近希拉.韋布總是顯得沒精打采的。「她一回來就叫她進來見我。」
「好的,馬丁代小姐。」
艾娜重新把太妃糖推回舌頭中央,一邊起勁地吮吸著,一邊繼續打亞曼.萊文的小說《赤裸之愛》。儘管萊文先生煞費苦心,小說中的性愛描寫還是非常乏味──大多數讀者讀他的小說時也都這麼覺得。要為「世上最無趣的便是乏味之色情小說」舉例,他便是最佳典範。雖然有俗麗的包裝和挑逗的書名,他的小說銷量仍逐年下降;而且,他上回的打字費已經催了三次都還沒給。
辦公室門開了。希拉.韋布走了進來,看起來有點氣喘吁吁。
「虎斑貓1在找你。」艾娜說。
希拉.韋布做了個鬼臉說:「真倒楣,偏偏在我遲到的時候找我!」
她理一理頭髮,拿起記事本和筆,敲了經理室的門。
馬丁代小姐從辦公桌上抬起頭來。她四十多歲年紀,看起來精明幹練,高高綰起的頭髮髮色泛紅,再加上教名凱瑟琳與貓諧音,使她得到了虎斑貓的綽號。
「你遲到了,韋布小姐。」
「對不起,馬丁代小姐,路上塞車。」
「每天這個時間,路上總是塞車,你應該考慮到這點。」她查看一下記事本,接著說:「有位佩瑪小姐打電話來說,她三點鐘需要一名速記,而且特別指名要你去,你以前為她服務過嗎?」
「我不記得了,馬丁代小姐,至少最近沒有。」
「她的地址是威布蘭新月社區十九號。」
她停了一下,投以詢問的目光,但希拉.韋布搖搖頭說:「我不記得去過那兒。」
馬丁代小姐瞄了一眼桌上的鐘說:「三點鐘,你應該可以準時到達。你下午還有其他差事嗎?哦,對了,」她低頭看了看手邊的記事本。「你得去柯琉飯店的波帝教授那兒,五點鐘。所以你最好五點之前回來,如果回不來,我可以叫珍妮特去。」
她點了點頭表示事情說完了,於是希拉走回外間辦公室。
「有什麼好玩的嗎,希拉?」
「又是無聊的一天。先去威布蘭新月社區一個老小姐那兒,五點鐘還要去波帝教授那兒──都是些老古董的名字!真希望有時也發生一點刺激的事。」
馬丁代小姐辦公室的門開了。
「我想起來我記了一個備要,希拉,就是到了那裡,如果佩瑪小姐還沒回來,你可以直接進屋子裡去,大門不會上鎖。進去後,到門廳右邊的房間等著。你記住了嗎?要不要我寫下來?」
「我記住了,馬丁代小姐。」
馬丁代小姐退回她的密室。
艾娜.布蘭偷偷鑽到椅子下面,拿起一隻俗氣的皮鞋,還有一個從鞋底掉下來的尖錐型鞋跟。
「我這樣怎麼回家呢?」她哀嘆地說。
「唉,別大驚小怪了,到時候就有辦法了。」另外一個女孩邊說邊繼續打她的字。
艾娜嘆了口氣,放上一頁空白紙張,開始打入:「情欲已牢牢控制住他,他用瘋狂的手指撕開她薄軟的胸罩,強迫她躺在肥皂沫上。」
「該死。」艾娜說,伸手去取擦子。
希拉拿起她的手提包,走了出去。
威布蘭新月社區是十九世紀八○年代一位維多利亞建築師的奇幻作品,它的外觀呈半月形,由兩排背靠背的房舍和花園構成。對不熟悉其方位的人來說,這種奇特的結構會造成很多麻煩:走在社區外圈的人不容易發現前段房號的房舍,走在內環的人也會因為找不到後段號碼而摸不著頭腦。這些房子乾淨整潔,陽台設計精巧,看來十分高雅莊嚴,它們幾乎不曾受到現代化潮流的影響,至少就其外觀而言是這樣。廚房和浴室通常是最先感受到現代化氣息的地方。
這裡的十九號寓所沒什麼特別之處,窗簾潔淨,前門的銅製把手光滑潔亮,小路兩旁種著一排薔薇樹,一直延伸到前門。
希拉.韋布推開大門,走到正門處按了門鈴。沒人來應門。等了一兩分鐘後,她照著指示,轉動門把,打開大門走了進去。門廳右邊的門半開半掩著,她輕輕敲了敲門,等了一下,然後就走了進去。
這是間非常普通但十分溫馨的客廳,現代樣式的家具布置得稍嫌擁擠。最引人注目的是其中各式各樣的鐘──房間角落有一座滴答作響的老爺鐘、壁爐台上有座德勒斯登瓷鐘、書桌上有個銀色的旅行鐘、放在壁爐旁古董架上的是價格昂貴的鍍金小鐘、在靠窗的桌子上,則是一個已褪色的皮革旅行鐘,上面模模糊糊地印著「蘿絲瑪莉」的鍍金字樣。
希拉.韋布有點驚奇地看著書桌上那個鐘。鐘面上顯示的時間是四點十幾分。她把目光轉向壁爐架上那個鐘,上面的時間也一樣。
希拉驀地大吃一驚,因為她頭頂上方突然響起嘰嘰嘎嘎的聲音。一隻布穀鳥從牆上木刻鐘的小門裡蹦了出來,響亮清晰地叫:「布穀,布穀,布穀!」刺耳的聲音彷彿是一種威脅。隨後小門啪地一聲關上,布穀鳥也不見了。
希拉.韋布微微一笑,繞著沙發的一端走過去。接著她戛然停住了腳步,倒抽一口氣。
地板上呈大字形仰躺著一個男人,他的眼睛半開,毫無光彩,在他深灰色西裝上頭有一灘暗色溼痕。希拉幾乎是機械式地彎下身子,摸了一下他的臉頰……涼的,再摸摸他的手,也是涼的……她摸了一下那塊溼痕,又快速地把手抽回,驚恐萬狀地盯著它看。
這時候,她聽到外面有開門的嘎嘎聲。她木然地把頭轉向窗外,看到一位婦女的身影正沿著小路匆匆忙忙走來。希拉遲鈍地嚥了一口唾沫──她的喉嚨非常乾燥。她一動不動地站在原地,動彈不得,也無法叫喊,只直愣愣地盯著前方。
門開了,一個高大年邁的婦人走了進來,手裡提著購物袋。她灰色的鬈髮從前額朝後梳,一雙藍色的眼睛又大又亮。她的眼神瞟過希拉,對她視若不見。
希拉發出了微弱的聲音,僅僅是一聲輕微的喊叫。婦人的藍色大眼轉向她,嚴厲地問:「誰在那兒?」
「我……他……」
希拉突然停住不說了,因為老婦人繞著沙發正迅速地朝她走來。
突然希拉尖叫起來。
「別……別……你就要踩到那個……他身上了……他死了。」
01科林.拉姆的自述
用警察的術語來說,九月九日下午兩點五十九分,我正沿著威布蘭新月社區朝西行走。這是我第一次到威布蘭新月社區,而且老實說,這社區把我搞得暈頭轉向。
儘管我猜測成真的可能性愈來愈小,但我仍日復一日,益加持之以恆地去執行我的猜測。我就是這種個性。
我要找的寓所是六十一號。找得到嗎?不行,我找不到。我從一號寓所仔仔細細地找到三十五號,但走到這裡威布蘭新月社區好像就到盡頭了。路底是一條明確標著艾巴尼路的通道橫在面前。我轉回頭,道路北面沒有任何房屋,只有一堵牆。牆後面有一排排現代公寓聳立而起。這些公寓的入口顯然在另一條馬路上,幫不上忙。
我抬頭查看剛剛經過的宅邸號碼:二十四、二十三、二十二、二十一、黛安娜小屋(應該就是二十號,門柱上一隻黃色的貓正用爪子洗臉),十九……
這時十九號的門開了,一個女孩像枚子彈似地從裡面衝了出來,沿小道飛奔著,她邊跑邊大聲尖叫,使她更像一枚呼嘯而至的飛彈。她叫聲又尖又細,悲慘而淒厲。穿過院門後,這個女孩衝過來,和我撞了個滿懷,衝力之大幾乎把我撞出了人行道。她不只撞我,還緊緊抓住我不放……那種抓法顯得非常瘋狂、絕望。
「冷靜,」我站穩身子,恢復了平衡後說。我輕輕搖了她一下。「冷靜一下。」
女孩安靜了下來。她仍然緊緊抓住我不放,但已不再尖叫,相反地,她大口喘著氣……低沉地嗚咽著。
我不敢說我擅長應付這種情況。我問她有什麼事,但馬上意識到這個問題太軟弱無力,於是改口問道:「發生什麼事了?」
女孩深深吸了一口氣。
「那裡!」她朝身後指了一下。
「怎麼了?」
「有個男的躺在地板上……死了……她就要踩到他身上了。」
「誰要踩到?為什麼?」
「我想……是因為她眼睛看不見。那個男人身上都是血,」她低頭看了看,鬆開緊抓住我不放的手。「我身上也有,我也沾到血了。」
「是有血,」我邊說邊看看我大衣袖子上的血跡。「我身上現在也沾到了,」我指指袖子,嘆了口氣,衡量了一下當前的情勢。「你最好帶我進去看一下。」我說。
聽到這裡,她又開始劇烈抖動起來。
「我不……我不能……我不想再進去了。」
「那好吧。」
我看了看四周,似乎沒有合適的地方來安頓這個處於半暈眩狀態的女孩。我輕輕攙扶她坐在人行道上,靠著鐵圍籬。
「你待在這裡,」我說,「等我回來,我不會去很久。你不會有事的。如果你覺得頭暈,就向前傾,把頭放在兩膝之間。」
「我……我現在覺得好多了。」
她不太確定地說道,但我不想再討論這點。我拍拍她的肩膀安慰她一下,然後沿著小徑快步走去。穿過正門進了屋子,我在門廊猶豫了一下,朝左邊的門內望去,那是個空無一人的餐廳。我穿過門廳,走進對面的客廳。
我首先看到的是,一位頭髮灰白的老婦人端坐在椅子上。當我走進房內時,她迅速地轉過頭來問道:「是誰?」
我立刻意識到,這位婦人是個盲人。她那雙直盯著我的眼睛,實際上是集中在我左耳後的某一點。
我馬上答話,並直入正題說:「一位小姐從這裡衝到大街上,說這裡有個男人死了。」
說這些話時我自己都覺得非常荒謬可笑。在這樣整潔乾淨的房間裡,還有一位安詳的老人雙手交握坐在椅子上,看起來不該有這種事。
但她立刻回答我。
「在沙發後面。」她說。
我繞著沙發的一角走過去,接著看到了一雙伸出來的手臂,一雙暗淡無光的眼睛,還有凝固的血漬。
「這是怎麼發生的?」我猛然發問。
「我不知道。」
「可是……好吧,他是誰?」
「我不清楚。」
「我們必須通知警察。」我向四周看了看問道:「電話在哪裡?」
「我沒有電話。」
我更仔細看著她。
「你住在這兒?這是你的房子?」
「是的。」
「可以告訴我這是怎麼回事嗎?」
「當然可以。我買東西回來──」我注意到購物袋放在靠門的一把椅子上。「我進了屋子以後,馬上就察覺到有人在房裡。一個人眼睛看不見的時候,感覺會特別靈敏。我問誰在那裡,但沒人回答,只聽見有個人急促的呼吸聲。我朝那個聲音走過去……那時這個人大聲尖叫起來,說什麼有人死了、我就要踩在他身上了,接著這個人又尖叫著從我身邊衝了出去。」
我點了點頭,她們的陳述是吻合的。
「那麼你接下來做了什麼?」
「我小心地朝前走,然後我的腳碰到了一個東西。」
「然後呢?」
「我跪下來,摸到了什麼東西……是一隻男人的手。手都涼了,已經完全沒有脈搏……於是我站了起來,走到這兒坐下,等人來。一定會有人來。那個女孩,不管她是誰,一定會去報警。我認為最好還是不要離開房間。」
這位婦人的鎮靜讓我印象深刻。她沒有大聲喊叫,也沒有嚇得東倒西歪地逃出屋外,她只是平靜地坐下來等待。這是很明智的做法,但得要有很大的能耐。
她問道:「你是誰啊?」
「我叫科林.拉姆,剛才碰巧從這兒路過。」
「那個女孩在哪兒?」
「我把她安頓在門口,她受到很大的驚嚇。離這裡最近的電話亭在哪裡?」
「沿著這條路往前走,大約五十碼遠的轉角處有個電話亭。」
「知道了,我記得曾從那兒經過。我要打個電話給警察,你─」
我猶豫了一下,不知道該說:「你能不能一直待在這裡?」還是說:「你在這裡沒問題吧?」
她解決了我的困境。
「你最好讓那個女孩到屋子裡來。」她果斷地說。
「我不知道她願不願意進來。」我遲疑不決地說。
「當然不要帶她到這個房間,讓她待在另一邊的餐廳裡。告訴她,我正在為她泡茶。」
她站了起來,朝我走來。
「可是,你還可以泡──」
一絲冷笑在她臉上一閃而過。
「年輕人,我搬來住進這所房子是十四年前的事了,每天三餐都是我自己在廚房裡動手做的。眼睛看不見並不表示我毫無用處。」
「對不起,我說傻話了。能不能告訴我你的名字?」
「蜜莉森.佩瑪……小姐。」
我出了門,沿著小路朝前走。那個女孩抬頭看我,掙扎著要站起來。
「我……我覺得現在稍微好些了。」
我扶她站了起來,愉快地說:「很好。」
「那兒……那兒有個人死了,對不對?」
我說是的。
「是有人死了。我正要到前面那個電話亭,打電話通知警方。如果我是你,我就到屋子裡等著。」接著我提高嗓門,以防她不同意,「你到餐廳去──進屋子後的左邊,佩瑪小姐正在為你準備茶水。」
「她就是佩瑪小姐?她眼睛看不見?」
「對。當然了,這對她一定也是個打擊,但她非常理性。來,我帶你進去。在警察到來之前,喝杯茶對你會有好處。」
我搭著她的肩膀,扶著她沿小徑往前走。我讓她舒適地坐在餐廳的桌子旁,然後匆忙走向電話亭。
一個死板的聲音回答道:「克勞汀警察局。」
「哈凱松警探在嗎?」
那個聲音又小心翼翼地問道:「我不知道他在不在,你是哪一位?」
「告訴他我是科林.拉姆。」
「請稍等一下。」
我等了一會兒,然後聽到了迪克.哈凱松的聲音。
「科林嗎?沒想到你會這時候找我。你在哪兒?」
「克勞汀,確切地說,是在威布蘭新月社區。這裡的十九號寓所有一個男人躺在地板上,死了,我想是被刺死的,死了大約一個半小時左右。」
「誰發現的?你嗎?」
「不是,我是不相干的路人。是有個女孩像隻地獄來的蝙蝠,突然從屋內飛奔而出,幾乎把我撞倒在地。她說有個男人躺在地板上死了,一個瞎眼太太踩在他身上。」
「你不是在騙我吧?」迪克露出懷疑的口氣。
「聽起來確實讓人難以置信,我承認。可是,事實就是我說的這樣。那個盲眼女士是屋主蜜莉森.佩瑪小姐。」
「她正在踩那位死者嗎?」
「不是你想的那樣。她的眼睛看不見,所以不知道這個人躺在那兒。」
「我們馬上行動,你在那兒等我。那個女孩你怎麼處理?」
「佩瑪小姐正在為她泡茶。」
迪克說,這聽起來還挺溫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