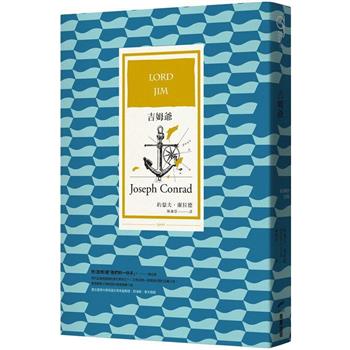第九章
「『當時我自言自語著,「沉下去,該死的東西!沉下去!」』這是他再度開口時說的話。他希望事情結束。他徹底被孤立,在腦海裡用詛咒的口氣對大船說著這些話,在此同時又享受著目擊者的特權,目睹那場在我看來是低俗喜劇的景象。那些人還在對付那根滑栓,船長下令,『鑽到小艇底下,想辦法把小艇抬高。』其他人自然而然退避三舍。你們也知道,萬一大船突然下沉,躺平擠在小艇龍骨下可不是什麼好事。小個子大管輪哀怨地說,『你怎麼不去?……你最強壯。』船長絕望地噴罵,『去你的!我太胖了。』這一幕太可笑,天使看見都會流淚。他們無所適從呆站了一會兒,輪機長突然又衝到吉姆面前。
「『過來幫忙!你想放棄唯一的機會,是不是瘋了?過來幫忙!看那邊……你看!』
「輪機長發狂般堅定地指向船尾,吉姆終於轉過頭去,看見一片無聲的黑色暴風已經吞掉三分之一的天空。你們都知道那個時節在那個區域會出現那種暴風。一開始是海平線慢慢變暗,就這樣。之後不透光的烏雲像一堵牆般升起。雲氣筆直的邊緣鑲著淺白的光芒,從西南方飛上來,將滿天星斗一群群吞沒。它的陰影飛過海面,海天的邊界模糊了,合併成一個晦暗的深淵。一切都靜止了。沒有雷,沒有風,沒有聲響,沒有一絲閃電。緊接著,在那廣大的黑暗中出現一道青灰色的圓弧,一兩道浪濤飛掠過去,像黑暗本身的波動。突然間,強風豪雨同時襲來,氣勢特別狂躁,彷彿剛從某種堅實物體爆發出來。這樣的雲趁他們不注意的時候出現了。他們才剛發現,有充分的理由推測,在絕對的靜止狀態下,大船或許還有機會在海面停留幾分鐘,但大海只要有一分一毫的動盪,她會立刻下沉。暴風開始肆虐之前,大船會第一次對湧來的前浪低頭,卻也是最後一次,因為這次低頭會變成俯衝。過程會拉長,變成漫長的下沉,往下,往下,直達海底。所以那些人才會這麼驚慌失措,才會因為極端排斥死亡,做出更多蠢事。
「『那烏雲黑漆漆的,很黑。』吉姆用穩定的鬱悶口吻說,『從背後悄悄偷襲。可惡的東西!也許我心裡原本還抱有一線希望,我不知道,反正這下子都完了。看著自己陷入這樣的困境,我簡直要發瘋。我很生氣,彷彿中了陷阱。我的確中了陷阱!我記得那天晚上天氣也熱,沒有一絲風。』
「他記得太清楚,坐在椅子上喘氣,在我面前冒著汗,呼吸困難。那暴風當然逼得他發狂,可以說再次將他擊倒。不過,颶風也讓他想起一件被遺忘得一乾二淨的事,也就是他跑來船橋的重要目的。他要砍斷小艇的固定索。他抽出刀子開始猛力揮砍,彷彿他什麼也看不到,什麼也聽不見,彷彿不知道大船上還有其他人。他們覺得他執迷不悟,瘋得無可救藥,卻不敢大聲責罵他做無用功浪費時間。他砍完繩索後重新回到砍固定索的起點。輪機長也在那裡,一把抓住他,湊到他耳邊咬牙切齒地低聲說話,彷彿想咬掉他的耳朵:
「『你這個沒腦子的笨蛋!等那些畜牲都落海,你以為你會有生存機會?哼,他們會敲你腦袋,把你打下小艇。』
「吉姆沒理他,他站在吉姆身旁絞扭雙手。船長緊張不安,拖著腳步原地打轉,喃喃有辭說道,『槌子!槌子!我的天!弄把槌子來!』
「大管輪像個孩子似地抽噎,不過,雖然胳膊斷了,他似乎是那群人之中最有膽量的,竟然真的鼓足勇氣跑進機艙去執行任務。這可不簡單,必須替他說句公道話。吉姆告訴我,大管輪像個走投無路的人,一臉絕望地跑出去,一面低聲哀號。他很快爬了上來,手拿槌子,直接去敲滑栓,動作沒有任何停頓。其他人馬上放棄吉姆,跑過去幫忙。他聽見槌子輕輕地嗒嗒敲著,聽見鬆脫的墊木掉落下來。小艇可以動了。直到這時吉姆才轉頭去看,直到這時。但他依然保持距離。他要我知道他跟那些人保持距離,要我知道他跟那些拿到槌子的人沒有任何共同點。一點都沒有。他想必覺得自己跟那些人之間隔著無法跨越的空間,隔著某種無法克服的障礙,或一道無底深淵。他跟他們保持最遠的距離,船身寬度容許的距離。
「他站得遠遠的,雙腳黏在地板上,眼睛看見那群模糊的人影弓著身子聚在一起,在恐懼的折磨下詭異地擺動。帕特納號船橋有一張小桌子(船的中段沒有海圖室),一盞提燈高掛在小桌旁的柱子上,燈光照亮他們賣力的肩膀和他們向上拱起、時高時低的背脊。他們推著小艇的船頭,推向漆黑的夜色裡。他們推著,不再回頭看他。他們放棄了他,彷彿他離他們確實太遙遠,不可能接觸得到,不值得向他求助,不值得看他一眼或給個手勢。他們沒有閒工夫回頭觀看他消極的英雄作為,也不想受他拒絕同流合污的刺激。小艇頗有重量,他們努力推著船頭,連一句彼此打氣的話都說不出來。只是,他們的沉著在驚恐的亂象中潰散,像風中的穀殼,導致他們急迫的勞動變得有點滑稽,像在鬧劇裡耍寶的丑角。他們用雙手推、用腦袋去頂,為了挽救自己寶貴的生命,用全身的重量去推,用他們的洪荒之力去推。他們剛把船頭推離吊艇架,馬上動作一致地鬆開手,手忙腳亂地爬進去。想當然耳,小艇猛地往迴盪,將他們都送回來,無可奈何地擠成一團。他們困窘地呆站了一會兒,氣急敗壞地壓低聲音把所知的髒話都罵過一遍,重新來過。同樣的情況發生三次。他用憤怒的語氣向我描述那段經過,沒有遺漏那齣鬧劇的任何環節。『我厭惡他們。我痛恨他們,我不得不目睹那一切。』他沒有加重語氣,轉頭用陰沉的目光緊盯著我,『世上有哪個人受過這種可恥的折磨?』
「他雙手抱住腦袋,停頓了片刻,像被某種無法形容的怒氣逼得發狂。這些事他沒辦法在法庭上說明,也沒辦法向我說明。有時我能夠理解他話語之間的停頓,否則我也不適合聽他吐露這些心聲。他的堅忍受到這樣的攻擊,其中少不了復仇之神惡意又卑鄙的嘲弄。他的苦難摻雜了諷刺劇的元素,在死亡或恥辱逼近的時刻,穿插了讓人蒙羞的滑稽怪相。
「我記得他敘述的事實經過,可是時間相隔太久,我想不起他當時的措辭。我只記得他巧妙地在平鋪直敘中傳達滿腹的憤怒。他告訴我,他兩度閉上眼睛,深信那就是最後一刻,卻兩度不得不重新睜開。每一次他都發現死寂的周遭更昏暗了。無聲的烏雲將它的陰影從天頂投下,落在大船上,似乎消除了擠滿生命的大船上的所有聲響。他已經聽不到遮篷下的人聲。他告訴我,每一次他閉上眼睛,腦海就閃過那眾多身軀,躺在那裡等待死亡,那影像清楚得有如白日所見。等他睜開眼睛,看見的卻是四個人在陰暗處奮力搏鬥,像瘋子似地對付一艘頑固的小艇。他垂著眼簾說道:『他們一次一次退回來,站在小艇前方相互咒罵,突然又一湧而上……那情景真能讓人笑到斷氣。』而後又抬起視線看著我,露出淒涼的笑容,說道,『天啊,那原本能帶給我快樂的人生,因為那趣味的畫面可以讓我回味一輩子。』他的視線又向下。『看見也聽見……看見也聽見。』他重複兩次,間隔不短的時間,期間只有空洞的眼神。
「他回過神來。
「『我決定閉上眼睛。』他說,『但我辦不到。我辦不到,也不在乎被誰發現。誰想批評我,就先去經歷那種事。讓他們去經歷,讓他們做得比我更好,就這樣。我第二次睜開眼睛時,嘴巴也張開了。我感覺大船動了:船頭點了一下,又輕柔地抬起。動作很慢,慢得彷彿沒有終點,幾乎難以察覺。她已經幾天沒有動過了。烏雲已經跑到前面去了,這第一道浪彷彿湧過沉重似鉛塊的海水。那波浪沒有生命力,卻擊倒我腦海裡的某種東西。換做是你會怎麼做?你對自己很有把握,對吧?如果現在,此時此刻,你感覺這棟屋子動了,你椅子底下的地板輕輕晃一下。跳啊!我敢說你會從座位上彈起來,落在那邊那叢灌木裡。』
「他伸出手臂,揮向石欄杆外的夜色。我保持冷靜。他牢牢盯著我,眼神嚴厲。錯不了,他在威逼我。而我不能做出任何表示,以免一個手勢或一個字眼就表露出涉及這個事件的致命觀點。我不想冒那樣的風險。別忘了他就在我眼前,而且他太像我們的一份子,不可能不危險。不過如果你們想知道,我不介意告訴你們,我確實匆匆瞄了一眼,估量遊廊前的草坪中央那叢幽暗的灌木跟我距離有多遠。他誇大了。我跳不了那麼遠,落點會差個一兩公尺,而當時只有這件事我可以確定。
「他覺得最後一刻到了,所以動也不動站著。儘管他腦海裡思緒紛飛,雙腳卻依然黏在甲板上。同樣在這個時刻,他看見小艇旁那些人之中有一個突然往後退,舉起雙臂抓向空中,踉蹌幾步後倒下。那動作稱不上摔倒,而是身子慢慢下滑,變成坐姿,整個人蜷縮起來,肩膀抵著機艙的天窗。他說,『那人負責操控輔機,臉色蒼白憔悴,留著雜亂的鬍子,職位是二管輪。』
「『死了。』我說。我們在法庭上約略聽過這件事。
「『據說是這樣。』他語氣肅穆又淡漠。『那時我當然不知道。聽說心臟不好。他抱怨身體不舒服已經一段時間了。情緒激動,用力過度,鬼才知道。哈!哈!哈!不難看出他也不想死。好笑吧?我敢打賭他被騙得丟了小命!被騙了,千真萬確。我的天,被騙了!跟我一樣……唉!他什麼都不做就好了。當初他們把他床上拉起來,告訴他船要沉了,他就該叫他們滾蛋!他就該袖手旁觀,臭罵那些人一頓!』
「他站起來,揮了揮拳頭,凶狠地瞪著我,又坐下。
「『錯失了機會,是吧?』我咕噥說。
「『你為什麼不笑?』他問,『那是在地獄編造出來的笑話。心臟不好!有時候我希望當時我的心臟也不好。』
「這話令我惱火,於是帶著深深的嘲弄問道,『是嗎?』他大聲答,『是!你不明白嗎?』我生氣地說,『我不知道你還奢求什麼?』他投給我一個茫然不解的眼神。這支箭同樣偏離靶心太遠,而他從不理會落空的箭。相信我,他沒有一點戒心,嘲諷他沒有意思。我很慶幸我的箭沒有命中目標,慶幸他連弓弦的砰聲都沒聽見。
「那時候他當然不可能知道那人死了。下一分鐘(也是他在船上的最後一分鐘)有太多亂哄哄的事情和感受衝擊著他,像海水拍打著岩石。我使用這個比喻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因為根據他的敘述,我不得不相信在那一分鐘裡他一直有個古怪的幻覺,認為自己消極被動,彷彿他沒有任何動作,而是被某些邪惡力量牽制住,那些力量選中他做為他們惡作劇的對象。他意識到的第一件事是沉重的吊艇柱終於嘎吱嘎吱地盪了出去,那刺耳的聲響似乎從甲板鑽進他腳底,進入他的身體,沿著脊椎傳向頭頂。當時暴風已經非常接近,另一波比較大的海浪以驚人的力道將靜止的大船往上舉,嚇得他屏住呼吸。在此同時,慌亂的尖叫聲像匕首般刺穿他的大腦和心臟。『放手!放手!放手!她動了。』緊接著小艇吊索被扯離墊木,遮篷底下傳來人們驚恐的說話聲。他說,『那幾個傢伙扯開嗓門大叫,死人都會被吵醒。』等小艇『啪』地一聲落水後,踩踏和翻滾的空洞聲響隨之傳來,夾雜著混亂的喊叫聲:『解開鉤子!解開鉤子!推!想活命就推!暴風來了……』他聽見頭頂上空有微弱的風聲,聽見腳底下有疼痛的吶喊,另外有個模糊的聲音在咒罵旋轉鉤。大船從船頭到船尾開始發出嗡嗡聲,像被驚擾的蜂窩。他說這些事情的時候,神態、面容和聲音都非常平靜。緊接著沒有絲毫預警,用同樣平靜的口吻說,『我絆到他的腿。』
「這是我第一次聽到他動了。我震驚得忍不住咕噥一聲。他終於還是動了,但究竟是在哪一刻,什麼原因將他拉出靜止狀態,他一點都不知道,正如被連根拔起的樹木也不知道是哪陣風將它吹倒。當時那一切同時向他進擊:聲音、景象、死人的腿,天啊!那邪惡的玩笑被強行塞進他喉嚨。然而,你們聽好,他不會承認當時他的咽喉做出任何吞嚥動作。他竟能將他的幻覺投射在別人身上,實在神奇。我覺得自己聽到的是在屍體上施行巫術的故事。
「『他倒向一側,動作很慢,那是我在船上看到的最後一幕。』他接著說,『當時我不在乎他在做什麼,看起來他好像打算站起來。我當然以為他想站起來,以為他會從我身邊衝出去,跳過欄杆,落在小艇上跟其他人會合。我聽得見他們在底下碰碰撞撞,有個吶喊聲像一支箭射了上來:「喬治!」然後三個聲音同時大叫。那些聲音分別傳進我耳朵,一個哀叫,一個尖嘯,一個咆哮。噢!』
「他微微發抖,我看見他慢慢站起來,彷彿上方有一隻穩定的手拉著他的頭髮,將他從椅子上提起來。慢慢地,他整個人站了起來,等到他膝蓋打直,那隻手就放開他,他身體輕輕擺盪幾下。他說到『他們大聲喊』的時候,他的臉、他的動作和他的聲音本身傳達出一份可怕的死寂。我不禁豎起耳朵,等著聽那細微的叫喊聲直接穿透虛幻的寧靜傳過來。『大船上有八百個人,』說著,他用可怕的空洞眼神把我釘在我的椅背上。『八百個活人,而他們在叫喚那唯一的死人,要他跳下去逃生。「跳呀,喬治!跳呀!快跳啊!」我站在那裡,手扶著吊艇柱,文風不動。天色已經墨黑,看不見天空,也看不見大海。我聽見大船側邊的小艇砰砰響,有一段時間底下沒有一點聲音,而我腳下的大船卻有各種交談聲。船長突然大吼,「天啊!暴風!暴風!把小艇推走!」第一陣雨嘶嘶地落下,第一陣強風襲來,他們尖叫,「跳呀,喬治!我們會接住你!跳呀!」大船開始緩緩前傾,暴雨橫掃在她身上,像破碎的海浪。我的帽子飛走了,我呼出的空氣被逼回喉嚨。我彷彿站在高塔頂端聽著另一個瘋狂的尖叫聲,「喬……治!跳呀!」大船在下沉,下沉,船頭往下,就在我腳底下……』
「他緩緩把手舉向臉龐,手指做出挑撿的動作,彷彿臉上沾到蜘蛛絲。之後他看著自己攤開的手掌大約半秒,才衝口而出:
「『我跳了……』他停下來,避開視線。又補了一句,『好像是這樣。』
「他轉過來,清澈的藍色眼珠可憐兮兮地望著我。看著他站在我面前,驚愕又受傷的模樣,我心情沉重,有種無奈的傷感,夾雜著老人家面對孩子惹上災禍時的心情,愛莫能助之餘,啞然失笑又深深憐憫。
「『看起來是。』我喃喃附和。
「『我一點也不知道,直到我抬頭一看。』他匆匆解釋。這也不無可能。聽他說這些事,要把他當成惹出麻煩的小男孩。他自己也不知道,事情不知怎的就發生了,以後不會再犯。他跳下去的時候壓到某個人,而後落在一塊座板上。他覺得左邊的肋骨好像都斷了,之後他翻了個身,隱約看見被他遺棄的大船高聳在眼前,紅色的舷燈在雨中放大了光芒,像穿過霧氣看見山頂峭壁邊緣的火光。『她好像比牆壁更高,像懸崖似地聳立在小艇上方……我真希望我能死掉。』他大叫。『回不去了。我好像跳進了一口井,一個深不見底的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