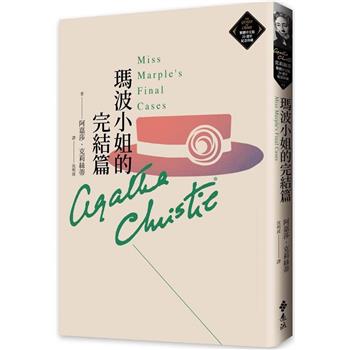01聖堂
牧師娘臂彎裡滿抱著菊花,從住家一角彎了過來。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滿了花園的肥土,連鼻頭都沾著幾塊泥,可是她渾然不覺。
開鐵門的時候,她稍稍費了些力氣。那扇門已經生鏽,半懸半掛地繫在鏈條上。一陣風把她頭上那頂破舊的毛帽吹得更加歪斜。
「煩人!」圓圓罵了一句。
哈蒙太太雖然被樂觀的父母取了個「黛安娜」的教名,不過她自小由於某種顯而易見的原因而被暱稱為「圓圓」,從此以後這個名字就和她如影隨形。她緊緊抱著菊花,蹣跚穿過鐵門和教堂墓地,來到了教堂門口。
十一月的空氣溫涼而溼潤。雲彩在天空裡飛快掠過,留下東一塊西一塊的藍天。教堂裡面則是又暗又冷。它只在做禮拜的時候才會生火取暖。
「哎喲!」圓圓的聲音和表情一樣生動。「我最好趕緊把事情做完。我可不想凍死。」
她以平日訓練來的敏捷,很快就找齊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和花夾。「要是我們有水仙就好了,」圓圓心頭默想。「我已經看膩了這些瘦巴巴的菊花。」她靈巧的手指排了排花器裡的花朵。
這種插花擺設並不需要原創力或藝術感,因為圓圓.哈蒙本人既無原創力也沒有藝術感。可是它會產生一種家的氛圍,令人感到愉快。圓圓小心翼翼地端著花瓶,沿著甬道朝聖壇一步步走去。此時,太陽慢慢升了起來。
東面的窗戶鑲裝的是簡陋的彩繪玻璃,以藍色和紅色為主……這是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常來教堂做禮拜的有錢人捐贈的。陽光透過玻璃直射進來,一瞬間光芒四射,產生了令人震驚的效果。「就像珠寶一樣。」圓圓心想。她驟然停下腳步,兩眼瞪視著前方。聖壇的台階上,有一團黑影縮在那裡。
圓圓小心放下花瓶,走上前去彎下腰來。躺在那兒的是個男人,整個人蜷縮成一團。圓圓在他身旁屈膝跪下,慢慢地、謹慎地將他翻轉過來。她的手指探了探他的脈搏。脈動如此微弱,加上他那蒼白、近乎青綠的臉色,一切已不言而喻。
「毫無疑問,」圓圓想,「這男人快死了。」
那人年約四十五歲,身穿一套寒酸的黑色西裝。她放下那隻軟趴趴的手,查看他的另一隻手。那隻手擱在他胸前,有如握緊的拳頭。她再仔細一看,發現那隻手裡緊握著一大塊軟軟的東西,看起來像是一條手帕。他把它緊緊貼在胸口上,手的周圍布滿了一片乾掉的褐色液體。圓圓猜想,那是乾了的血漬。她一屁股坐在地上,皺起眉頭。
在此之前,那男人的雙眼始終緊閉,這時候突然睜開,定定地盯在圓圓的臉上。那對眼睛既不迷茫恍惚,也非游移不定,看似充滿了活力和機敏。他動了動唇,圓圓彎身向前想聽清楚他的話……更確切地說,是他說的那兩個字。他只說了這兩個字:「聖堂。」
圓圓隱約覺得,在他氣若游絲地說出這兩個字的時候,臉上似乎浮現出淺淺的微笑。她聽得沒錯,因為片刻後他又說了一遍:「聖堂。」
接著,伴著一聲拖得老長的微弱嘆息,他又閉上眼睛。圓圓再度伸手去摸他的脈搏。它仍在跳動,但更加微弱,間隔的時間也更長。她下定決心,站起身來。
「你別動,」她說,「千萬別動。我去找幫手來。」
男人再度張開眼睛,不過他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東面窗戶射進來的彩色光芒上。他低聲說了什麼,可是圓圓沒有完全聽清楚。她心頭一驚,覺得那人好像在說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說,「你是來找朱利安的?」
沒有回答。那人緊閉著雙眼躺在地上,呼吸愈來愈慢,也愈來愈淺。
圓圓轉過身去,快步走出教堂。她看了看錶,滿意地點點頭。葛里斐醫生現在應該還在診所裡。診所離教堂只有幾分鐘的路程。她逕自走了進去,未曾停步敲門或按鈴,便穿過候診室直接進了醫生的診療間。
「你得馬上來,」圓圓說,「教堂裡有個男人快死了。」
幾分鐘後,葛里斐醫生對男人做了一番簡單的檢查,最後站起身來。
「可不可以把他從這裡搬移到你家去?這樣我比較方便照顧他……雖然這不表示他還有救。」
「當然可以,」圓圓說,「我這就去把東西準備好。要不要我把哈勃和瓊斯叫來,好幫忙抬動他?」
「謝謝。我是可以從你家打電話叫救護車來,怕就怕等救護車來的時候……」他沒把話說完。
圓圓問:「是內出血?」
葛里斐醫生點點頭,隨即問道:「他到底是怎麼跑進教堂裡來的?」
「我想他一定在裡面待了一整夜,」圓圓答道,「哈勃每天早上上班前都會到教堂開門,但他通常不會進來。」
五分鐘後,葛里斐醫生放下電話,那個受傷的男人躺在沙發暫時鋪就的毯子上。圓圓正攪動著一盆水,清洗醫生檢查過的傷口。
「噢,就是這樣了,」葛里斐說,「我叫了救護車,也通知警察了。」
他皺著眉頭站在一旁,俯視著雙眼緊閉、躺在沙發上的病人。那人的左手在他身軀旁邊不斷抽搐。
「他是被人射傷,」葛里斐說,「從很近的距離開的槍。他把他的手帕捲成一球,堵住傷口以便止血。」
「他被射傷了還能走那麼遠?」圓圓問。
「噢,可以的,這很有可能。我就知道有個受了致命傷的人自己爬起來走下街道,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可是五分鐘或十分鐘後突然倒下不起。所以,這人不一定是在教堂裡被人射傷的。沒錯,他可能是在遠地受的傷。當然,他也可能是自己打了自己一槍,然後丟下槍,跌跌撞撞地闖到教堂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到教堂來而不去牧師家。」
「噢,這個我知道,」圓圓說。「他說:『聖堂』。」
醫生瞪著她。
「聖堂?」
「朱利安來了,」聽到丈夫在門廳裡的腳步聲,圓圓邊說邊轉過頭去。「朱利安,在這裡。」
朱利安.哈蒙牧師走進房間。他身上流露出一股學者氣質,所以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成得多。
「我的天!」朱利安.哈蒙說,瞪著那些外科手術儀器和蜷縮在沙發上的男人,神情隱隱流露出不解。
圓圓以她一貫的精簡用字解釋道:「這人在教堂裡,快死了。他被人射傷了。你認識他嗎,朱利安?我想他曾經提到你的名字。」
牧師走近沙發,低頭看了看那個即將嚥氣的人。
「可憐的傢伙,」他搖了搖頭。「不,我不認識他。我可以肯定,我從沒見過這個人。」
這時候,那個垂死的人再度睜開眼睛。他的目光從醫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從哈蒙移向他的妻子,接著就停駐在那裡,定定地盯在圓圓的臉上。葛里斐走上前來。
「你能說話嗎?」他焦急地說。
那男人雙眼依然緊盯著圓圓,以微弱的聲音說道:「請……請……」
接著一陣輕顫,就這麼斷了氣。
海斯警佐舔舔鉛筆,把筆記本翻過一頁。
「所以,哈蒙太太,你能告訴我的就這麼多?」
「對,就這麼多,」圓圓說,「這些東西是從他大衣口袋裡拿出來的。」
海斯警佐肘邊的桌子上放著一個錢包、一只刻有「WS」縮寫的破手錶,外加一張去倫敦的車票票根。除了這些,別無他物。
「你們已經查出他是誰了,對吧?」圓圓問。
「一對叫艾柯思的夫婦打電話到警局來。這人是艾柯思太太的兄弟,至少看來是這樣。他的名字是桑伯恩,健康不佳、精神不穩已有好一陣子了。近來他的身體每下愈況,前天出門後就沒再回家。他出門的時候身上帶著一把左輪手槍。」
「然後跑到教堂來朝自己開槍?」圓圓問,「為什麼呢?」
「噢,你知道,他的情緒一直很低落……」
圓圓打斷了他的話。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他為什麼選上這裡?」
海斯警佐顯然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所以他繞了個圈子。
「他是搭乘五點十分的公車到這裡來的。」
「噢,」圓圓又問了一次。「可是為什麼呢?」
「哈蒙太太,這我可就不知道了,」海斯警佐說,「誰又知道。要是一個人的腦筋不正常……」
圓圓替他把話說完。
「他大可在任何地方自殺,可是在我看來,搭車到這樣一個小鄉下來未免多餘。他在此地沒有任何熟人,不是嗎?」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確定。」海斯警佐說。他道歉似地咳嗽一聲,站起身來,口裡說道:「哈蒙太太,艾柯思夫婦可能會來登門拜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當然不介意,」圓圓說,「那是很自然的事。但願我能告訴他們一些事情。」
「那我就告辭了。」海斯警佐說。
「如果這不是一樁謀殺案,」圓圓陪他朝前門走去。「我就謝天謝地了。」
一輛車停在牧師住宅的鐵門前。海斯警佐朝它瞄了一眼,隨口說道:「看來艾柯思夫婦已經上門來了。」
圓圓強打起精神,打算忍受一段想必是痛苦煎熬的經歷。「再怎麼說,」她想,「我可以找朱利安來幫我。人在悲痛的時候,牧師是個很大的安慰。」
雖然圓圓不能確切地描繪出她料想中的艾柯思夫婦是什麼模樣,不過當她趨前招呼的時候,心頭不免感到一絲訝異。艾柯思先生長得粗壯圓胖、紅光滿面,天性應是幽默樂觀;艾柯思太太身上則隱隱有股浮誇之氣,配上一張又薄又小還往上翹的嘴唇,嗓音又尖又細。
「哈蒙太太,你應該想像得到,這真是個天大的打擊。」她說。
「噢,我懂,」圓圓說,「這一定是個天大的打擊。快請坐。要不要我……噢,現在喝茶大概早了點……」
艾柯思先生揮揮他又短又胖的手。
「不用,不用,什麼也不用,」他說,「真是謝謝你了。我只想……呃,可憐的威廉說了什麼,你可知道?」
「他在國外待了很久,」艾柯思太太說,「我想他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事。自從他回家之後,心情就十分低落,也不愛說話。他說這個世界不適合人居住,也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期盼。可憐的比爾,他總是這麼情緒化。」
圓圓盯著這對夫婦看了半晌,一句話也沒說。
「他偷了我丈夫的左輪槍,」艾柯思太太繼續說下去。「我們完全不知情。接著他好像就搭了公車來到這裡。我想他這樣做也算貼心,他不想在我們家裡做這種事。」
「可憐的傢伙,可憐的傢伙,」艾柯思先生嘆了口氣,接著說道:「現在說什麼都無濟於事了。」
又一陣短暫的緘默後,艾柯思先生問:「他可曾留下什麼話?臨終遺言之類的,或者一句也沒有?」
他那對明亮、有如豬仔的眼睛緊緊盯視著圓圓。艾柯思太太的身子也向前傾,彷彿急著想聽到答覆。
「沒有,」圓圓靜靜回答,「他在快死的時候,來到教堂尋求庇護。」
艾柯思太太口氣帶著疑惑地問:「庇護?我想我不大懂……」
艾柯思先生打斷了她。
「親愛的,就是聖所,」他的口氣甚是不耐。「牧師娘的意思是這個。你知道,自殺是一種罪。我想他是想要贖罪。」
「他臨死前是打算說些什麼,」圓圓說,「可是他才說了一個『請』字就嚥氣了。」
艾柯思太太拿手帕蒙住眼睛,鼻子開始抽搐。
「噢,老天,」她說,「這太令人遺憾了,你說是不是?」
「好了好了,潘,」她丈夫說,「別再難過了。這種事誰也沒辦法。可憐的威廉。不管怎麼說,他現在終於安息了。非常謝謝你,哈蒙太太。希望我們沒有打攪你。我知道牧師娘很忙。」
夫婦倆分別和圓圓握了手。臨出門前,艾柯思突然轉過頭來問道:「噢,對了,還有一件事。我想他的大衣在這裡,對吧?」
「他的大衣?」圓圓皺起眉頭。
艾柯思太太接口說道:「你知道,我們希望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就算是追念吧。」
「他留下一只手錶、一個錢包,口袋裡還有一張火車票,」圓圓說,「我全都交給海斯警佐了。」
「那就無所謂了,」艾柯思先生說,「我想海斯警佐會把那些東西轉交給我們。他的私人信件應該在那個錢包裡。」
「錢包裡有一張一英鎊的紙鈔,」圓圓說,「其他什麼也沒有。」
「沒有信件?沒有那一類的東西?」
圓圓搖搖頭。
「噢,再次謝謝你,哈蒙太太。他穿的那件大衣……警方大概也拿走了,對吧?」
圓圓皺著眉頭,極力回想。
「沒有,」她說,「我想是沒有。讓我想想。葛里斐醫生和我把他的大衣脫下來,以便檢查傷口。」她對著房間茫然四顧了一陣。「我一定是把大衣連同毛巾和水盆一起拿到樓上去了。」
「哈蒙太太,如果你不介意,我們想拿回他的大衣。你知道,這是他最後的遺物,我太太對它是很有感情的。」
「當然可以,」圓圓說,「要不要我先找人把它洗乾淨?恐怕那件大衣很……呃,有很多汙漬。」
「噢,不用,不用,那沒關係。」
圓圓蹙起眉頭。
「我得想想我把它放到哪裡去了。失陪一下,我等下就回來。」
她上了樓,過了好幾分鐘才又回到房間。
「真是抱歉,」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的女傭把它和其他衣服包在一起,打算拿去送洗。我花了好一陣子才找到。衣服在這裡,我拿牛皮紙把它包起來了。」
儘管艾柯思夫婦一再推辭,她還是把大衣包了起來。夫婦倆帶著千恩萬謝再次和圓圓道別後雙雙離去。
圓圓慢慢走過門廳,進入書房。朱利安.哈蒙牧師抬頭看了看她,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來。他正在準備一場布道,可是他有點擔心,居魯士國王領下的朱迪亞和波斯間的政治糾葛會讓他分了心。
「有事嗎,親愛的?」他帶著期盼的語氣問道。
「朱利安,」圓圓說,「『聖堂』到底是什麼?」
朱利安.哈蒙帶著感激放下他的布道稿。
「噢,」他說,「在古羅馬和古希臘的廟宇裡,聖堂指的是立有神像的內殿。拉丁文的聖壇叫作『ara』,這個字也有保護的意思,」博學多聞的牧師繼續說道:「到了西元三九
九年,聖堂在基督教教堂裡的地位終於得到確認。在英國,關於聖堂權利的記載,最早見於西元六○○年由艾西伯特所制定的《律法章程》……」
他又繼續解釋了好一陣子,而和往常一樣,妻子對他深入講解的反應讓他一頭霧水。
「親愛的,」她說,「你真好。」
她彎下腰,在他的鼻尖上親了一下。朱利安覺得自己像隻狗,因為耍了個聰明的把戲而受到獎賞。
「艾柯思夫婦剛才來過我們家。」圓圓說。
牧師皺起眉頭。
「艾柯思夫婦?我好像不記得……」
「你是不認識。他們是教堂裡的那個男人的姐姐和姐夫。」
「親愛的,你應該叫我一聲。」
「完全沒必要,」圓圓說,「他們並不需要安慰。我在想,」她皺起眉頭。「朱利安,如果明天我把飯菜放在爐子上,你自己應付得來嗎?我想去倫敦看看這次的拍賣會。」
「去看帆船?」她丈夫茫然地望著她。「你是說遊艇還是小船之類的?」
圓圓笑了。
「不是,親愛的。『布羅和賓特曼』正在大拍賣,你知道,就是賣床單、桌布、毛巾,還有玻璃擦布的那家店。玻璃擦布好容易磨損,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再說,」她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我想我該去看看珍姑媽了。」
牧師娘臂彎裡滿抱著菊花,從住家一角彎了過來。她的厚底皮鞋上沾滿了花園的肥土,連鼻頭都沾著幾塊泥,可是她渾然不覺。
開鐵門的時候,她稍稍費了些力氣。那扇門已經生鏽,半懸半掛地繫在鏈條上。一陣風把她頭上那頂破舊的毛帽吹得更加歪斜。
「煩人!」圓圓罵了一句。
哈蒙太太雖然被樂觀的父母取了個「黛安娜」的教名,不過她自小由於某種顯而易見的原因而被暱稱為「圓圓」,從此以後這個名字就和她如影隨形。她緊緊抱著菊花,蹣跚穿過鐵門和教堂墓地,來到了教堂門口。
十一月的空氣溫涼而溼潤。雲彩在天空裡飛快掠過,留下東一塊西一塊的藍天。教堂裡面則是又暗又冷。它只在做禮拜的時候才會生火取暖。
「哎喲!」圓圓的聲音和表情一樣生動。「我最好趕緊把事情做完。我可不想凍死。」
她以平日訓練來的敏捷,很快就找齊了必要的用具:花瓶、水和花夾。「要是我們有水仙就好了,」圓圓心頭默想。「我已經看膩了這些瘦巴巴的菊花。」她靈巧的手指排了排花器裡的花朵。
這種插花擺設並不需要原創力或藝術感,因為圓圓.哈蒙本人既無原創力也沒有藝術感。可是它會產生一種家的氛圍,令人感到愉快。圓圓小心翼翼地端著花瓶,沿著甬道朝聖壇一步步走去。此時,太陽慢慢升了起來。
東面的窗戶鑲裝的是簡陋的彩繪玻璃,以藍色和紅色為主……這是維多利亞時代一個常來教堂做禮拜的有錢人捐贈的。陽光透過玻璃直射進來,一瞬間光芒四射,產生了令人震驚的效果。「就像珠寶一樣。」圓圓心想。她驟然停下腳步,兩眼瞪視著前方。聖壇的台階上,有一團黑影縮在那裡。
圓圓小心放下花瓶,走上前去彎下腰來。躺在那兒的是個男人,整個人蜷縮成一團。圓圓在他身旁屈膝跪下,慢慢地、謹慎地將他翻轉過來。她的手指探了探他的脈搏。脈動如此微弱,加上他那蒼白、近乎青綠的臉色,一切已不言而喻。
「毫無疑問,」圓圓想,「這男人快死了。」
那人年約四十五歲,身穿一套寒酸的黑色西裝。她放下那隻軟趴趴的手,查看他的另一隻手。那隻手擱在他胸前,有如握緊的拳頭。她再仔細一看,發現那隻手裡緊握著一大塊軟軟的東西,看起來像是一條手帕。他把它緊緊貼在胸口上,手的周圍布滿了一片乾掉的褐色液體。圓圓猜想,那是乾了的血漬。她一屁股坐在地上,皺起眉頭。
在此之前,那男人的雙眼始終緊閉,這時候突然睜開,定定地盯在圓圓的臉上。那對眼睛既不迷茫恍惚,也非游移不定,看似充滿了活力和機敏。他動了動唇,圓圓彎身向前想聽清楚他的話……更確切地說,是他說的那兩個字。他只說了這兩個字:「聖堂。」
圓圓隱約覺得,在他氣若游絲地說出這兩個字的時候,臉上似乎浮現出淺淺的微笑。她聽得沒錯,因為片刻後他又說了一遍:「聖堂。」
接著,伴著一聲拖得老長的微弱嘆息,他又閉上眼睛。圓圓再度伸手去摸他的脈搏。它仍在跳動,但更加微弱,間隔的時間也更長。她下定決心,站起身來。
「你別動,」她說,「千萬別動。我去找幫手來。」
男人再度張開眼睛,不過他的注意力似乎集中在東面窗戶射進來的彩色光芒上。他低聲說了什麼,可是圓圓沒有完全聽清楚。她心頭一驚,覺得那人好像在說她丈夫的名字。
「朱利安?」她說,「你是來找朱利安的?」
沒有回答。那人緊閉著雙眼躺在地上,呼吸愈來愈慢,也愈來愈淺。
圓圓轉過身去,快步走出教堂。她看了看錶,滿意地點點頭。葛里斐醫生現在應該還在診所裡。診所離教堂只有幾分鐘的路程。她逕自走了進去,未曾停步敲門或按鈴,便穿過候診室直接進了醫生的診療間。
「你得馬上來,」圓圓說,「教堂裡有個男人快死了。」
幾分鐘後,葛里斐醫生對男人做了一番簡單的檢查,最後站起身來。
「可不可以把他從這裡搬移到你家去?這樣我比較方便照顧他……雖然這不表示他還有救。」
「當然可以,」圓圓說,「我這就去把東西準備好。要不要我把哈勃和瓊斯叫來,好幫忙抬動他?」
「謝謝。我是可以從你家打電話叫救護車來,怕就怕等救護車來的時候……」他沒把話說完。
圓圓問:「是內出血?」
葛里斐醫生點點頭,隨即問道:「他到底是怎麼跑進教堂裡來的?」
「我想他一定在裡面待了一整夜,」圓圓答道,「哈勃每天早上上班前都會到教堂開門,但他通常不會進來。」
五分鐘後,葛里斐醫生放下電話,那個受傷的男人躺在沙發暫時鋪就的毯子上。圓圓正攪動著一盆水,清洗醫生檢查過的傷口。
「噢,就是這樣了,」葛里斐說,「我叫了救護車,也通知警察了。」
他皺著眉頭站在一旁,俯視著雙眼緊閉、躺在沙發上的病人。那人的左手在他身軀旁邊不斷抽搐。
「他是被人射傷,」葛里斐說,「從很近的距離開的槍。他把他的手帕捲成一球,堵住傷口以便止血。」
「他被射傷了還能走那麼遠?」圓圓問。
「噢,可以的,這很有可能。我就知道有個受了致命傷的人自己爬起來走下街道,就像什麼事也沒發生一樣,可是五分鐘或十分鐘後突然倒下不起。所以,這人不一定是在教堂裡被人射傷的。沒錯,他可能是在遠地受的傷。當然,他也可能是自己打了自己一槍,然後丟下槍,跌跌撞撞地闖到教堂來。我不知道他為什麼到教堂來而不去牧師家。」
「噢,這個我知道,」圓圓說。「他說:『聖堂』。」
醫生瞪著她。
「聖堂?」
「朱利安來了,」聽到丈夫在門廳裡的腳步聲,圓圓邊說邊轉過頭去。「朱利安,在這裡。」
朱利安.哈蒙牧師走進房間。他身上流露出一股學者氣質,所以外表看起來比實際年齡老成得多。
「我的天!」朱利安.哈蒙說,瞪著那些外科手術儀器和蜷縮在沙發上的男人,神情隱隱流露出不解。
圓圓以她一貫的精簡用字解釋道:「這人在教堂裡,快死了。他被人射傷了。你認識他嗎,朱利安?我想他曾經提到你的名字。」
牧師走近沙發,低頭看了看那個即將嚥氣的人。
「可憐的傢伙,」他搖了搖頭。「不,我不認識他。我可以肯定,我從沒見過這個人。」
這時候,那個垂死的人再度睜開眼睛。他的目光從醫生身上移向朱利安.哈蒙,又從哈蒙移向他的妻子,接著就停駐在那裡,定定地盯在圓圓的臉上。葛里斐走上前來。
「你能說話嗎?」他焦急地說。
那男人雙眼依然緊盯著圓圓,以微弱的聲音說道:「請……請……」
接著一陣輕顫,就這麼斷了氣。
海斯警佐舔舔鉛筆,把筆記本翻過一頁。
「所以,哈蒙太太,你能告訴我的就這麼多?」
「對,就這麼多,」圓圓說,「這些東西是從他大衣口袋裡拿出來的。」
海斯警佐肘邊的桌子上放著一個錢包、一只刻有「WS」縮寫的破手錶,外加一張去倫敦的車票票根。除了這些,別無他物。
「你們已經查出他是誰了,對吧?」圓圓問。
「一對叫艾柯思的夫婦打電話到警局來。這人是艾柯思太太的兄弟,至少看來是這樣。他的名字是桑伯恩,健康不佳、精神不穩已有好一陣子了。近來他的身體每下愈況,前天出門後就沒再回家。他出門的時候身上帶著一把左輪手槍。」
「然後跑到教堂來朝自己開槍?」圓圓問,「為什麼呢?」
「噢,你知道,他的情緒一直很低落……」
圓圓打斷了他的話。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是說,他為什麼選上這裡?」
海斯警佐顯然不知道這個問題的答案,所以他繞了個圈子。
「他是搭乘五點十分的公車到這裡來的。」
「噢,」圓圓又問了一次。「可是為什麼呢?」
「哈蒙太太,這我可就不知道了,」海斯警佐說,「誰又知道。要是一個人的腦筋不正常……」
圓圓替他把話說完。
「他大可在任何地方自殺,可是在我看來,搭車到這樣一個小鄉下來未免多餘。他在此地沒有任何熟人,不是嗎?」
「到目前為止我們還不確定。」海斯警佐說。他道歉似地咳嗽一聲,站起身來,口裡說道:「哈蒙太太,艾柯思夫婦可能會來登門拜訪……如果你不介意的話。」
「我當然不介意,」圓圓說,「那是很自然的事。但願我能告訴他們一些事情。」
「那我就告辭了。」海斯警佐說。
「如果這不是一樁謀殺案,」圓圓陪他朝前門走去。「我就謝天謝地了。」
一輛車停在牧師住宅的鐵門前。海斯警佐朝它瞄了一眼,隨口說道:「看來艾柯思夫婦已經上門來了。」
圓圓強打起精神,打算忍受一段想必是痛苦煎熬的經歷。「再怎麼說,」她想,「我可以找朱利安來幫我。人在悲痛的時候,牧師是個很大的安慰。」
雖然圓圓不能確切地描繪出她料想中的艾柯思夫婦是什麼模樣,不過當她趨前招呼的時候,心頭不免感到一絲訝異。艾柯思先生長得粗壯圓胖、紅光滿面,天性應是幽默樂觀;艾柯思太太身上則隱隱有股浮誇之氣,配上一張又薄又小還往上翹的嘴唇,嗓音又尖又細。
「哈蒙太太,你應該想像得到,這真是個天大的打擊。」她說。
「噢,我懂,」圓圓說,「這一定是個天大的打擊。快請坐。要不要我……噢,現在喝茶大概早了點……」
艾柯思先生揮揮他又短又胖的手。
「不用,不用,什麼也不用,」他說,「真是謝謝你了。我只想……呃,可憐的威廉說了什麼,你可知道?」
「他在國外待了很久,」艾柯思太太說,「我想他一定有些不可告人的事。自從他回家之後,心情就十分低落,也不愛說話。他說這個世界不適合人居住,也沒有任何東西值得期盼。可憐的比爾,他總是這麼情緒化。」
圓圓盯著這對夫婦看了半晌,一句話也沒說。
「他偷了我丈夫的左輪槍,」艾柯思太太繼續說下去。「我們完全不知情。接著他好像就搭了公車來到這裡。我想他這樣做也算貼心,他不想在我們家裡做這種事。」
「可憐的傢伙,可憐的傢伙,」艾柯思先生嘆了口氣,接著說道:「現在說什麼都無濟於事了。」
又一陣短暫的緘默後,艾柯思先生問:「他可曾留下什麼話?臨終遺言之類的,或者一句也沒有?」
他那對明亮、有如豬仔的眼睛緊緊盯視著圓圓。艾柯思太太的身子也向前傾,彷彿急著想聽到答覆。
「沒有,」圓圓靜靜回答,「他在快死的時候,來到教堂尋求庇護。」
艾柯思太太口氣帶著疑惑地問:「庇護?我想我不大懂……」
艾柯思先生打斷了她。
「親愛的,就是聖所,」他的口氣甚是不耐。「牧師娘的意思是這個。你知道,自殺是一種罪。我想他是想要贖罪。」
「他臨死前是打算說些什麼,」圓圓說,「可是他才說了一個『請』字就嚥氣了。」
艾柯思太太拿手帕蒙住眼睛,鼻子開始抽搐。
「噢,老天,」她說,「這太令人遺憾了,你說是不是?」
「好了好了,潘,」她丈夫說,「別再難過了。這種事誰也沒辦法。可憐的威廉。不管怎麼說,他現在終於安息了。非常謝謝你,哈蒙太太。希望我們沒有打攪你。我知道牧師娘很忙。」
夫婦倆分別和圓圓握了手。臨出門前,艾柯思突然轉過頭來問道:「噢,對了,還有一件事。我想他的大衣在這裡,對吧?」
「他的大衣?」圓圓皺起眉頭。
艾柯思太太接口說道:「你知道,我們希望把他所有的東西都拿走。就算是追念吧。」
「他留下一只手錶、一個錢包,口袋裡還有一張火車票,」圓圓說,「我全都交給海斯警佐了。」
「那就無所謂了,」艾柯思先生說,「我想海斯警佐會把那些東西轉交給我們。他的私人信件應該在那個錢包裡。」
「錢包裡有一張一英鎊的紙鈔,」圓圓說,「其他什麼也沒有。」
「沒有信件?沒有那一類的東西?」
圓圓搖搖頭。
「噢,再次謝謝你,哈蒙太太。他穿的那件大衣……警方大概也拿走了,對吧?」
圓圓皺著眉頭,極力回想。
「沒有,」她說,「我想是沒有。讓我想想。葛里斐醫生和我把他的大衣脫下來,以便檢查傷口。」她對著房間茫然四顧了一陣。「我一定是把大衣連同毛巾和水盆一起拿到樓上去了。」
「哈蒙太太,如果你不介意,我們想拿回他的大衣。你知道,這是他最後的遺物,我太太對它是很有感情的。」
「當然可以,」圓圓說,「要不要我先找人把它洗乾淨?恐怕那件大衣很……呃,有很多汙漬。」
「噢,不用,不用,那沒關係。」
圓圓蹙起眉頭。
「我得想想我把它放到哪裡去了。失陪一下,我等下就回來。」
她上了樓,過了好幾分鐘才又回到房間。
「真是抱歉,」她上氣不接下氣地說,「我的女傭把它和其他衣服包在一起,打算拿去送洗。我花了好一陣子才找到。衣服在這裡,我拿牛皮紙把它包起來了。」
儘管艾柯思夫婦一再推辭,她還是把大衣包了起來。夫婦倆帶著千恩萬謝再次和圓圓道別後雙雙離去。
圓圓慢慢走過門廳,進入書房。朱利安.哈蒙牧師抬頭看了看她,緊鎖的眉頭舒展開來。他正在準備一場布道,可是他有點擔心,居魯士國王領下的朱迪亞和波斯間的政治糾葛會讓他分了心。
「有事嗎,親愛的?」他帶著期盼的語氣問道。
「朱利安,」圓圓說,「『聖堂』到底是什麼?」
朱利安.哈蒙帶著感激放下他的布道稿。
「噢,」他說,「在古羅馬和古希臘的廟宇裡,聖堂指的是立有神像的內殿。拉丁文的聖壇叫作『ara』,這個字也有保護的意思,」博學多聞的牧師繼續說道:「到了西元三九
九年,聖堂在基督教教堂裡的地位終於得到確認。在英國,關於聖堂權利的記載,最早見於西元六○○年由艾西伯特所制定的《律法章程》……」
他又繼續解釋了好一陣子,而和往常一樣,妻子對他深入講解的反應讓他一頭霧水。
「親愛的,」她說,「你真好。」
她彎下腰,在他的鼻尖上親了一下。朱利安覺得自己像隻狗,因為耍了個聰明的把戲而受到獎賞。
「艾柯思夫婦剛才來過我們家。」圓圓說。
牧師皺起眉頭。
「艾柯思夫婦?我好像不記得……」
「你是不認識。他們是教堂裡的那個男人的姐姐和姐夫。」
「親愛的,你應該叫我一聲。」
「完全沒必要,」圓圓說,「他們並不需要安慰。我在想,」她皺起眉頭。「朱利安,如果明天我把飯菜放在爐子上,你自己應付得來嗎?我想去倫敦看看這次的拍賣會。」
「去看帆船?」她丈夫茫然地望著她。「你是說遊艇還是小船之類的?」
圓圓笑了。
「不是,親愛的。『布羅和賓特曼』正在大拍賣,你知道,就是賣床單、桌布、毛巾,還有玻璃擦布的那家店。玻璃擦布好容易磨損,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再說,」她若有所思地加了一句:「我想我該去看看珍姑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