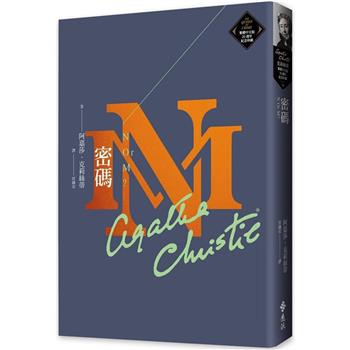01
湯米.貝里福在門廳脫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掛到牆上,又把帽子掛到旁邊的釘子上。
他舒展了一下雙臂,臉上露出一絲微笑,走進客廳。他的妻子正在那兒用卡其色毛線編織巴拉克拉盔帽。
這是一九四○年的春天。
貝里福夫人飛快地瞥了他一眼,又氣咻咻地忙著織她的帽子,過了一兩分鐘才說:「晚報上有什麼消息嗎?」
湯米說:「閃電戰,好,好!法國的情況看起來很糟。」
陶品絲說:「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世界。」
過了一會兒,湯米說:「好了,你幹嘛不問我上哪兒去了呢?沒必要跟我兜圈子。」
「我知道,」陶品絲說,「看別人故意兜圈子是挺氣憤的。不過如果我真的問你,你也不會高興。無論怎麼說,用不著我問。看你的臉色我就知道怎麼回事。」
「我沒覺得我看起來像個受氣包。」
「不,親愛的,」陶品絲說,「你臉上那種彷彿釘上去的微笑,是我看過最讓人心碎的表情。」
湯米咧開嘴笑著說:「不會吧,真的那麼糟?」
「還更糟呢!好了!別想那些煩人的事了。沒什麼差事,對吧?」
「是沒有。他們什麼位子也不給我。陶品絲,我才四十六歲,卻被人家看成顫顫巍巍的老爺爺,真叫人無法忍受!陸軍、空軍、海軍、外交部都眾口一詞地說我太老了……也許以後用得著我。」
陶品絲說:「是啊,我也一樣。他們不要我這個年紀的人當護士。『用不著,謝謝你。』也沒有別的差事可做。他們寧願用那些黃毛丫頭也不用我。雖然我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在不同崗位上整整工作了三年,我在外科病房和手術室當過護士,在商行裡當過司機,後來還給一位將軍開過車。而那些丫頭連個傷兵也沒見過,連給繃帶消毒也沒做過。我還向他們一再保證,我做什麼都很出色,可是沒用。我反正是個可憐的、令人討厭的老太婆,幹嘛不待在家裡老老實實織毛衣,非要由著性子東奔西跑地找工作。」
湯米悶悶不樂地說:「這場戰爭真他媽的討厭。」
「打仗就夠倒楣了,」陶品絲說,「但不能參與其中,才是最悲哀的事。」
湯米安慰妻子,說:「不管怎麼說,黛博拉找到工作了。」
黛博拉的媽媽說:「是呀,她是不錯。我希望她把工作做好。不過,湯米,我還是覺得必須向黛博拉堅持我的立場。」
湯米笑了笑。
「她可不一定這樣想。」
陶品絲說:「女兒有時候也會讓你惱火,尤其當她們對你表現得那樣孝順時。」
湯米喃喃著說:「小德瑞克有時候也對我做出一副寬容的樣子,真讓你沒法忍受。他那雙眼睛彷彿在說:『哦,可憐的老爸。』」
「事實上,」陶品絲說,「我們這對兒女雖然非常可愛,有時候也挺讓人受不了。」
提到這對孿生兒女德瑞克和黛博拉,她的眼裡充滿了柔情。
「我想,」湯米若有所思地說,「人們總是意識不到自己已經步入中年,過了做事的年齡。」
陶品絲不高興地哼了哼鼻子,搖了搖滿頭黑髮,任憑卡其色毛線球從膝蓋上面滾落下來。
「難道我們已經過了做事的年齡了嗎?是這樣嗎?還是別人習慣把我們說老?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再也派不上用場了。」
「很可能就是這樣。」
「也許。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曾經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現在我開始覺得以前什麼也沒發生過。發生過嗎?湯米。你是不是有一次被德國間諜打破腦袋,還被他們劫持?我們是不是有一次跟蹤一個危險的罪犯,最後把他捕獲?你和我是不是救過一個女孩,找到非常重要的祕密文件,受到國家的表彰和感謝?我們,你和我!但我們現在只是被人看扁、沒人稀罕的貝里福先生和貝里福夫人。」
「別說了,親愛的。說這些也沒有用。」
「反正,」陶品絲說,眨著眼睛沒讓眼淚流下。「我對我們的卡特先生完全失望。」
「他給我們寫過一封非常感人的信。」
「他什麼忙也沒幫……甚至連希望也不給我們。」
「他現在也不掌權了。和我們一樣。他已經很老了,住在蘇格蘭,沒事就釣魚。」
陶品絲沉思著說:「或許他們會讓我們在情報部門幫點忙。」
「也許我們幫不了了,」湯米說,「我們現在不像從前那麼機靈了。」
「我可不這麼想,」陶品絲說,「一般人總是這樣想。但就像你說的那樣,碰到關鍵時刻……」她嘆了一口氣,接著又說:「我希望我們能找到一件工作。成天胡思亂想,真是煩透了。」
她的目光落在那個年輕小夥子的照片上。他穿著空軍制服,咧開嘴笑著,那笑容和湯米一模一樣。
湯米說:「男人就更糟了。女人還能織織毛衣,或是到福利社幫人家包包東西。」
陶品絲說:「我二十年後再去包也不遲。我還沒老到那個程度呢。只是我現在剛好不上不下的,真麻煩。」
前門的門鈴響了。陶品絲站起來。這棟房子沒有什麼服務人員。
她打開門,看見一個寬肩圓腰的男人站在門前的踏墊上。他留著漂亮的大鬍子,臉色紅潤,面帶喜色。
「您是貝里福夫人嗎?」
「是的。」
「我是格蘭特。伊森普登勳爵的朋友。他要我來探望你和你的丈夫。」
「哦,太好了!快請進。」
她把他領進客廳。
「這是我的丈夫,嗯,這是格蘭特上尉……」
「格蘭特先生。」
「哦,格蘭特先生是卡特先生……不,是伊森普登勳爵的朋友。」
「卡特先生」是他們的老朋友在情報部當頭頭時的化名,他們叫順口了,總忘了他那顯赫的封號。
三個人興致勃勃地談了一會兒。格蘭特很隨和,是個很迷人的男士。
過了一會兒,陶品絲走了出去,幾分鐘後又回到客廳,手裡拿著雪利酒和幾個杯子。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格蘭特先生對湯米說:「我聽說你在找工作,貝里福。」
湯米眼裡閃爍著急切的光芒。
「是的,我是在找工作。你是不是……」
格蘭特笑著搖了搖頭。
「哦,不是你想的那樣。不是。恐怕那些工作得留給年輕人,或者給那些已經從事好幾年的人。我能給你介紹的只能是些枯燥無味的差事。辦公室的工作。整理文件,把文件分門別類,用紅帶子捆起來。只是這種事。」
湯米的臉沉了下來。
「哦,我明白了!」
格蘭特不無鼓勵地說:「總比沒事幹強吧。不管怎麼說,你哪天到我辦公室來一趟。軍需部二十二號辦公室。我們可以安排一些事情。」
電話鈴響了,陶品絲拿起話筒。
「喂。是的……什麼?」電話那邊傳來一個激動的聲音。陶品絲的臉色大變。「什麼時候?哦,我的天……當然,我馬上過去……」
她放下話筒,對湯米說:「是莫琳。」
「我猜就是她。我從這兒就聽得出她的聲音。」
陶品絲上氣不接下氣地解釋說:「非常抱歉,格蘭特先生。我得馬上到我朋友那兒一趟。她摔了一跤,扭了腳踝。家裡只有她的小女兒。我得馬上去幫她處理一下,找個人照顧她。請原諒。」
「當然,貝里福夫人。我非常理解。」
陶品絲朝他笑了笑,拿起一直放在沙發上的上衣,套在身上急匆匆地走了,前面傳來砰的關門聲。
湯米又給他的客人倒了一杯雪利酒。
「不用急著走。」他說。
「謝謝,」格蘭特接過酒杯,默默地品嘗著。過了一會兒說道:「從某種意義上講,你妻子被人叫走是件好事。我們可以節省時間。」
湯米凝視著他。
「我不明白。」
格蘭特不慌不忙地說:「聽我說,貝里福,你要是早一點到部裡找我,我是有辦法給你安排一份工作。」
湯米那張生著雀斑的臉漸漸露出喜色。他說:「你的意思是……」
格蘭特點了點頭。
「伊森普登推薦了你,」他說,「他對我們說,你正是適合的人選。」
湯米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說吧。」他說。
「當然是一件要絕對保密的事。」
湯米點了點頭。
「連你的妻子也不能知道。你明白嗎?」
「當然明白……如果你這樣要求的話。不過以前我們一直搭檔工作。」
「是的,我知道。可是這回勳爵建議的只有你。」
「我明白了。好吧。」
「表面上你找到一件辦公室的工作──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在我們這個部門的蘇格蘭分部。那地方是個禁區,你的妻子不能與你同行。實際上,你是到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湯米等待著。
格蘭特說:「你從報紙上看過『第五縱隊』嗎?我想,你至少知道……這個組織字面上的含義。」
湯米喃喃著說:「內奸。」
「正是。貝里福,這場戰爭爆發的時候,人們都抱著樂觀的態度。當然了,我不是指那些知道內情的人。我們一直就知道我們面臨著什麼……敵人的精銳部隊、空軍的優勢、拚死獲勝的決心、協調完整的作戰機制、周密的部署。我指的是絕大多數人,我們那些善良、糊塗、信奉民主、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同胞們。他們以為德國人很快就會崩潰,以為他們的武器都是破銅爛鐵,他們的士兵都餓著肚子,一走就要倒在地上。這都是一些異想天開的想法。
「可是戰爭並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樣。它一開始就很糟,現在更糟。我們的士兵沒有什麼不好,不管是在軍艦裡、飛機上或防空洞裡的戰士都優秀精良。但我們缺乏準備,部署也很不得當……也許是我們的素質有問題。我們的人不想打仗,也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件事,更談不上做什麼準備。
「不過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糾正了以往的錯誤,慢慢地選擇合適的人去做合適的工作。我們開始按照正確的辦法去打這場戰爭。我們能贏,這點毫無疑問。但是必須一開始就打好。失敗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不是來自德國人的炸彈,也不是因為中立國家被敵人占領,他們便可以從更有利的地勢襲擊我們。危險來自內部,來自我們城牆內的特洛伊木馬。如果你願意,就叫它第五縱隊。他們就在這兒,在我們內部。這些男男女女有的位高權重,有的只是普通百姓,但他們都相信納粹那一套,妄圖用納粹嚴格的信條取代我們悠閒散漫的民主自由制度。」
格蘭特俯身向前,用他悅耳的聲音繼續從容地說:「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
湯米說:「但是必定……」
格蘭特有點不耐煩地說:「那些小嘍囉我們可以一網打盡,這很容易。重要的是別人。我們知道有幾個傢伙。海軍部至少有兩個高層人物。其中一個一定是G將軍的班底。空軍裡還有三個或者更多,情報部門至少有兩個,他們有管道得知內閣的機密。我們知道這些,因為根據目前的情況分析,必定有敵人打入了我們內部。洩密事件,而且是從高層把情報洩漏給敵人,使我們意識到了這一點。」
湯米和藹可親的臉上露出幾分茫然,他無可奈何地說:「可是,我對你能有什麼用呢?我一點都不了解這些人。」
格蘭特點了點頭。
「是啊,你不知道他們,他們也不知道你呀!」
他停了一下又接著說:「那些人,那些隱藏在上層的人,大都知道我們這些搞地下工作的人,他們不可能不搜集這方面的情報。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便去找伊森普登。他現在已經退出核心了。即使生病了,腦子還是很清楚。他想起了你。你離開情報部門已經二十多年了。你的名字早已從那兒消失,你的面孔也沒人認識。你怎麼想?願不願意接下這個任務?」
湯米喜不自禁,笑得連嘴都合不攏。
「願不願意接下?你當然知道我求之不得。儘管我現在還不知道該從何下手。現在我只是一個『業餘愛好者』。」
「親愛的貝里福,我們需要的正是『業餘愛好者』。『專業』在這裡是障礙重重。你將接替我們一位最優秀的偵探。」
湯米臉上露出疑問的神色。格蘭特點了點頭。
「是的。上星期二他死在聖布里奇醫院,被一輛大卡車撞倒的……只活了幾個小時。車禍……其實根本不是什麼車禍,而是陰謀。」
湯米慢慢地說:「我明白了。」
格蘭特平靜地說:「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法考爾了解到了一些重要情況……他終於掌握了某些線索;他這場絕非偶然的死亡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湯米好像有話要問。
格蘭特繼續說:「遺憾的是,他到底發現了什麼情況,我們一無所知。法考爾追蹤了一條又一條的線索,但是收穫不大。」格蘭特停了一下,繼續說:「法考爾一直昏迷不醒,直到臨死前才清醒了幾分鐘。他想說什麼,但只說出這樣幾個字:N或M,頌舒西。」
「那,」湯米說,「等於什麼都沒說。」
格蘭特臉上露出一絲微笑。
「多少說明了一點問題。你知道,我們以前就聽說過『N或M』這個代號。它代表兩個最重要也最受信任的德國間諜。我們以前截獲過他們在其他國家的活動資料,對他們略有所知。他們的使命就是在外國組織第五縱隊,並且充當該國和德國的聯絡橋梁。我們知道,N是個男人,M是個女人。這兩個人是希特勒非常信任的間諜。戰爭剛開始,我們破譯過這樣的一個密碼︰『建議N或M到英格蘭,委以全權……』」
「我明白了。法考爾……」
「據我分析,法考爾一定發現了某個人的線索。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是哪一個。頌舒西聽起來不知所云。不過法考爾的法語一向不好,口音很重。他身上帶著一張到利漢普敦的回程車票。這個細節充分說明了一點問題︰利漢普敦是南部海岸一座新興的旅遊城市,那兒有許多私人開設的小旅館。其中有一家叫聖守喜……」
湯米說:「頌舒茜……聖守喜……我明白了。」
格蘭特說:「是嗎?」
「你的打算是,」湯米說,「讓我去那兒……搜索?」
「正是。」
湯米臉上又綻出微笑。
「任務不太明確,對吧?」他說,「我甚至連要找什麼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全靠你自己了。」
湯米嘆了一口氣,活動了一下肩膀。
「我可以試試看。不過我不是那種腦子特別靈光的人。」
「你過去不是成績非常好嗎?我聽說過了。」
「哦,那全靠運氣。」湯米連忙說。
「是呀,運氣正是我們需要的。」
湯米想了一會兒,說:「關於聖守喜那個地方……」
格蘭特聳了聳肩膀。
「也許只是白忙一場,我也不知道。法考爾臨死前也許喃喃唸的是:『舒西妹妹給戰士縫衣服。』這只是我們的猜測。」
「利漢普敦呢?」
「和其他地方沒什麼區別。什麼樣的人都有。老太太,老上校,無可懷疑的老處女,可疑的顧客,還有一兩個外國人。一團大雜燴。」
「N或M就隱藏在他們當中?」
「很難說。也許是和N或M接頭的人,也許是N或M本人。那是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海濱度假勝地的一家普通小旅館。」
「你連我要找的是個男人還是女人也不知道?」
格蘭特搖了搖頭。
湯米說:「好吧,我試試看。」
「祝你好運,貝里福。現在關於細節部分……」
半個小時之後,陶品絲闖了進來。她氣喘吁吁,心裡充滿了焦急和好奇。湯米獨自一人坐在一張扶手椅裡,臉上露出一種不無疑惑的表情。
「怎麼樣?」陶品絲意味深長地說。
「哦,」湯米用一種模稜兩可的口氣說,「我找到一件工作。」
「什麼工作?」
湯米做了一個鬼臉。
「到蘇格蘭一個偏遠地區做行政事務。當然也是祕密工作。只是聽起來並不刺激。」
「我們兩個一起去,還是只有你自己?」
「恐怕只有我自己。」
「真該死!我們的卡特先生怎麼這麼不夠朋友?」
「我想也許因為這是個男女有別的工作,而且挺勞心勞力。」
「是發密碼還是破譯密碼?是不是黛博拉那種工作?你可要當心點,湯米,這種差事簡直能把你弄成神經病。半夜三更不睡覺,整晚走來走去,嘴裡不住地背著九七八三四五二八
六,或者什麼玩意兒。最後精神崩潰,住進療養院。」
「我不會的。」
陶品絲悶悶不樂地說:「這只是遲早的事。我能不能不參加你的工作,只是以妻子的身分陪你去?料理你的生活,工作一天之後能讓你吃口熱飯,在壁爐前幫你擺雙拖鞋。」
湯米看起來十分不安。
「真抱歉,老婆。非常抱歉,我也不想離開你……」
「但是你覺得你應該去。」陶品絲喃喃道,言語之中不無留戀。
「不管怎麼說,」湯米有氣無力地說,「你可以在家織毛線。」
「織毛線?」陶品絲說,「織毛線!」
她拿起正在織的那頂巴拉克拉盔帽扔到地上。
「我討厭這種卡其色的毛線,」陶品絲說,「還有海軍藍、空軍藍。我想要織大紅色的東西!」
「火藥味十足,」湯米說,「簡直要來一場閃電戰。」
他心裡非常難受。不過陶品絲是個律己甚嚴的人,她很快就面對現實,鼓勵湯米接受這件工作並且說,自己並不十分在意。她還補充說,她已經打聽到急救中心需要一個擦地板的人,也許這工作很適合自己。
三天後,湯米離開家到蘇格蘭東北部港市阿伯丁。陶品絲到車站為他送行。她的一雙眼睛亮晶晶的,含著淚水。她眨了幾下,沒讓淚水掉下來,努力裝出一副快樂的樣子。
火車開了,湯米看著妻子漸漸遠去、孤零零、瘦癟癟的身影,覺得喉嚨陣陣發緊。雖然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他還是覺得自己背棄了陶品絲。
他振作起精神。命令就是命令。
到達蘇格蘭之後,他又坐上火車,第二天就來到曼徹斯特。第三天火車把他送到利漢普敦。他先在一家大飯店住下,然後去那些私人開的小旅館看房間,打聽看看長住有沒有什麼優惠條件。
聖守喜是一棟紫紅色的維多利亞式別墅,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從樓上的窗戶望過去,美麗的大海盡收眼底。門廳裡散發著一股淡淡的塵土味和煮飯的味道,但是和湯米看過的那幾家小旅館相比,聖守喜環境好得多。他在辦公室裡見到了老闆娘佩倫娜太太。那房間不大,也談不上整潔,一張大桌子上面鋪著幾張報紙。
佩倫娜太太也挺邋遢。她人已中年,微施脂粉,滿頭黑色的鬈髮亂糟糟的,一笑便露出一嘴潔白的牙齒。
湯米喃喃提到他一位年長的堂姐梅多斯小姐。兩年前,她曾在聖守喜住過。佩倫娜太太還清楚地記得梅多斯小姐……一位很可愛的老太太,也許並不是真的很老,很活潑,極富幽默感。
湯米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他知道,確實有一位梅多斯小姐,情報部門告訴過他這些細節。
可愛的梅多斯小姐現在怎麼樣啊?
湯米不無悲傷地表示說,梅多斯小姐已經去世。佩倫娜太太十分同情地咂了咂嘴,又恰如其分地驚叫了一番,臉上現出哀傷的表情。
不一會兒,她便滔滔不絕地介紹起她的旅館。她說,有個房間很適合梅多斯先生住,從那裡看得見大海美麗的景色。她覺得梅多斯先生離開倫敦來這兒度假,真是明智之舉。她知道,現在的局勢讓人高興不起來,特別是經歷了這場流行性感冒之後……
佩倫娜太太邊說邊領他上樓看房間。她還提到每週的住宿費。湯米露出一副大失所望的樣子。佩倫娜太太解釋說,物價飛漲;湯米說,他現在收入不多,還得交稅,諸如此類。
佩倫娜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這場可怕的戰爭……」
湯米表示同意,還說,照他看來,應該把希特勒這個傢伙絞死。瘋子,這傢伙真是一個瘋子!
佩倫娜同意他的觀點,接著又說,政府配給的食物太少,屠夫們也很難弄到肉,而雜碎更是經常不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她這個旅館老闆實在難當。不過考慮到梅多斯先生是梅多斯小姐的親戚,她可以少收半個基尼。
湯米離開聖守喜的時候,表示回去會再考慮一下這件事。佩倫娜太太一直把他送到大門,越發口若懸河起來,那股活潑勁讓湯米大吃一驚。他不得不承認,她雖然有點邋遢,但人挺漂亮的。他在心裡想,她是哪國人呢?一定不是道道地地的英國人。她的名字是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的名字,但那也許是她丈夫的國籍,而不是她的。她說不定是愛爾蘭人,雖然沒有愛爾蘭人的口音。不過她精力旺盛,充滿活力,倒很像愛爾蘭婦女。
最後他們商定,梅多斯先生第二天就搬過來。
湯米說好六點來,佩倫娜太太準時到樓下門廳裡接他。她吩咐一位看起來傻乎乎的女僕把他的行李送到臥室。女僕瞪大一雙眼睛看著湯米,嘴巴也張得老大。佩倫娜太太領著湯米到一個她稱之為休息室的房間。
「我總是介紹客人們相互認識,」佩倫娜太太說。她滿臉堆笑,望著休息室那五個目光充滿疑惑的人。「這是我們新來的客人梅多斯先生。這位是奧羅克太太。」
一位像小山般強壯的女人朝他笑了笑。她一雙眼睛晶亮如珠,嘴唇上還有兩撇唇髭。
「這位是布萊奇利少校。」
少校上下打量了湯米一眼,朝他僵硬地點了一下頭。
「馮戴尼先生。」
一位金髮碧眼的年輕人站起來鞠了一躬。
「明頓小姐。」
一位戴著許多珠子、正在織著卡其色毛線的老婦人朝湯米傻笑著。
「還有班金索夫人。」
那人也在專心織毛線。她黑髮蓬亂的腦袋從織了一半的巴拉克拉盔帽上慢慢抬了起來。
湯米屏住呼吸,整個屋子天旋地轉。
班金索─陶品絲!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陶品絲正坐在聖守喜的休息室裡平心靜氣地織毛線!
她的目光和他相觸。那是種禮貌、漠然的陌生人目光。
他由衷讚嘆。
陶品絲!
湯米.貝里福在門廳脫下外套,小心翼翼地掛到牆上,又把帽子掛到旁邊的釘子上。
他舒展了一下雙臂,臉上露出一絲微笑,走進客廳。他的妻子正在那兒用卡其色毛線編織巴拉克拉盔帽。
這是一九四○年的春天。
貝里福夫人飛快地瞥了他一眼,又氣咻咻地忙著織她的帽子,過了一兩分鐘才說:「晚報上有什麼消息嗎?」
湯米說:「閃電戰,好,好!法國的情況看起來很糟。」
陶品絲說:「真是一個令人沮喪的世界。」
過了一會兒,湯米說:「好了,你幹嘛不問我上哪兒去了呢?沒必要跟我兜圈子。」
「我知道,」陶品絲說,「看別人故意兜圈子是挺氣憤的。不過如果我真的問你,你也不會高興。無論怎麼說,用不著我問。看你的臉色我就知道怎麼回事。」
「我沒覺得我看起來像個受氣包。」
「不,親愛的,」陶品絲說,「你臉上那種彷彿釘上去的微笑,是我看過最讓人心碎的表情。」
湯米咧開嘴笑著說:「不會吧,真的那麼糟?」
「還更糟呢!好了!別想那些煩人的事了。沒什麼差事,對吧?」
「是沒有。他們什麼位子也不給我。陶品絲,我才四十六歲,卻被人家看成顫顫巍巍的老爺爺,真叫人無法忍受!陸軍、空軍、海軍、外交部都眾口一詞地說我太老了……也許以後用得著我。」
陶品絲說:「是啊,我也一樣。他們不要我這個年紀的人當護士。『用不著,謝謝你。』也沒有別的差事可做。他們寧願用那些黃毛丫頭也不用我。雖然我從一九一五到一九一八年在不同崗位上整整工作了三年,我在外科病房和手術室當過護士,在商行裡當過司機,後來還給一位將軍開過車。而那些丫頭連個傷兵也沒見過,連給繃帶消毒也沒做過。我還向他們一再保證,我做什麼都很出色,可是沒用。我反正是個可憐的、令人討厭的老太婆,幹嘛不待在家裡老老實實織毛衣,非要由著性子東奔西跑地找工作。」
湯米悶悶不樂地說:「這場戰爭真他媽的討厭。」
「打仗就夠倒楣了,」陶品絲說,「但不能參與其中,才是最悲哀的事。」
湯米安慰妻子,說:「不管怎麼說,黛博拉找到工作了。」
黛博拉的媽媽說:「是呀,她是不錯。我希望她把工作做好。不過,湯米,我還是覺得必須向黛博拉堅持我的立場。」
湯米笑了笑。
「她可不一定這樣想。」
陶品絲說:「女兒有時候也會讓你惱火,尤其當她們對你表現得那樣孝順時。」
湯米喃喃著說:「小德瑞克有時候也對我做出一副寬容的樣子,真讓你沒法忍受。他那雙眼睛彷彿在說:『哦,可憐的老爸。』」
「事實上,」陶品絲說,「我們這對兒女雖然非常可愛,有時候也挺讓人受不了。」
提到這對孿生兒女德瑞克和黛博拉,她的眼裡充滿了柔情。
「我想,」湯米若有所思地說,「人們總是意識不到自己已經步入中年,過了做事的年齡。」
陶品絲不高興地哼了哼鼻子,搖了搖滿頭黑髮,任憑卡其色毛線球從膝蓋上面滾落下來。
「難道我們已經過了做事的年齡了嗎?是這樣嗎?還是別人習慣把我們說老?有時候我覺得自己再也派不上用場了。」
「很可能就是這樣。」
「也許。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曾經覺得自己很了不起。現在我開始覺得以前什麼也沒發生過。發生過嗎?湯米。你是不是有一次被德國間諜打破腦袋,還被他們劫持?我們是不是有一次跟蹤一個危險的罪犯,最後把他捕獲?你和我是不是救過一個女孩,找到非常重要的祕密文件,受到國家的表彰和感謝?我們,你和我!但我們現在只是被人看扁、沒人稀罕的貝里福先生和貝里福夫人。」
「別說了,親愛的。說這些也沒有用。」
「反正,」陶品絲說,眨著眼睛沒讓眼淚流下。「我對我們的卡特先生完全失望。」
「他給我們寫過一封非常感人的信。」
「他什麼忙也沒幫……甚至連希望也不給我們。」
「他現在也不掌權了。和我們一樣。他已經很老了,住在蘇格蘭,沒事就釣魚。」
陶品絲沉思著說:「或許他們會讓我們在情報部門幫點忙。」
「也許我們幫不了了,」湯米說,「我們現在不像從前那麼機靈了。」
「我可不這麼想,」陶品絲說,「一般人總是這樣想。但就像你說的那樣,碰到關鍵時刻……」她嘆了一口氣,接著又說:「我希望我們能找到一件工作。成天胡思亂想,真是煩透了。」
她的目光落在那個年輕小夥子的照片上。他穿著空軍制服,咧開嘴笑著,那笑容和湯米一模一樣。
湯米說:「男人就更糟了。女人還能織織毛衣,或是到福利社幫人家包包東西。」
陶品絲說:「我二十年後再去包也不遲。我還沒老到那個程度呢。只是我現在剛好不上不下的,真麻煩。」
前門的門鈴響了。陶品絲站起來。這棟房子沒有什麼服務人員。
她打開門,看見一個寬肩圓腰的男人站在門前的踏墊上。他留著漂亮的大鬍子,臉色紅潤,面帶喜色。
「您是貝里福夫人嗎?」
「是的。」
「我是格蘭特。伊森普登勳爵的朋友。他要我來探望你和你的丈夫。」
「哦,太好了!快請進。」
她把他領進客廳。
「這是我的丈夫,嗯,這是格蘭特上尉……」
「格蘭特先生。」
「哦,格蘭特先生是卡特先生……不,是伊森普登勳爵的朋友。」
「卡特先生」是他們的老朋友在情報部當頭頭時的化名,他們叫順口了,總忘了他那顯赫的封號。
三個人興致勃勃地談了一會兒。格蘭特很隨和,是個很迷人的男士。
過了一會兒,陶品絲走了出去,幾分鐘後又回到客廳,手裡拿著雪利酒和幾個杯子。
他們沉默了一會兒,格蘭特先生對湯米說:「我聽說你在找工作,貝里福。」
湯米眼裡閃爍著急切的光芒。
「是的,我是在找工作。你是不是……」
格蘭特笑著搖了搖頭。
「哦,不是你想的那樣。不是。恐怕那些工作得留給年輕人,或者給那些已經從事好幾年的人。我能給你介紹的只能是些枯燥無味的差事。辦公室的工作。整理文件,把文件分門別類,用紅帶子捆起來。只是這種事。」
湯米的臉沉了下來。
「哦,我明白了!」
格蘭特不無鼓勵地說:「總比沒事幹強吧。不管怎麼說,你哪天到我辦公室來一趟。軍需部二十二號辦公室。我們可以安排一些事情。」
電話鈴響了,陶品絲拿起話筒。
「喂。是的……什麼?」電話那邊傳來一個激動的聲音。陶品絲的臉色大變。「什麼時候?哦,我的天……當然,我馬上過去……」
她放下話筒,對湯米說:「是莫琳。」
「我猜就是她。我從這兒就聽得出她的聲音。」
陶品絲上氣不接下氣地解釋說:「非常抱歉,格蘭特先生。我得馬上到我朋友那兒一趟。她摔了一跤,扭了腳踝。家裡只有她的小女兒。我得馬上去幫她處理一下,找個人照顧她。請原諒。」
「當然,貝里福夫人。我非常理解。」
陶品絲朝他笑了笑,拿起一直放在沙發上的上衣,套在身上急匆匆地走了,前面傳來砰的關門聲。
湯米又給他的客人倒了一杯雪利酒。
「不用急著走。」他說。
「謝謝,」格蘭特接過酒杯,默默地品嘗著。過了一會兒說道:「從某種意義上講,你妻子被人叫走是件好事。我們可以節省時間。」
湯米凝視著他。
「我不明白。」
格蘭特不慌不忙地說:「聽我說,貝里福,你要是早一點到部裡找我,我是有辦法給你安排一份工作。」
湯米那張生著雀斑的臉漸漸露出喜色。他說:「你的意思是……」
格蘭特點了點頭。
「伊森普登推薦了你,」他說,「他對我們說,你正是適合的人選。」
湯米長長地舒了一口氣。
「說吧。」他說。
「當然是一件要絕對保密的事。」
湯米點了點頭。
「連你的妻子也不能知道。你明白嗎?」
「當然明白……如果你這樣要求的話。不過以前我們一直搭檔工作。」
「是的,我知道。可是這回勳爵建議的只有你。」
「我明白了。好吧。」
「表面上你找到一件辦公室的工作──就像我剛才說的那樣──在我們這個部門的蘇格蘭分部。那地方是個禁區,你的妻子不能與你同行。實際上,你是到另外一個完全不同的地方。」
湯米等待著。
格蘭特說:「你從報紙上看過『第五縱隊』嗎?我想,你至少知道……這個組織字面上的含義。」
湯米喃喃著說:「內奸。」
「正是。貝里福,這場戰爭爆發的時候,人們都抱著樂觀的態度。當然了,我不是指那些知道內情的人。我們一直就知道我們面臨著什麼……敵人的精銳部隊、空軍的優勢、拚死獲勝的決心、協調完整的作戰機制、周密的部署。我指的是絕大多數人,我們那些善良、糊塗、信奉民主、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的同胞們。他們以為德國人很快就會崩潰,以為他們的武器都是破銅爛鐵,他們的士兵都餓著肚子,一走就要倒在地上。這都是一些異想天開的想法。
「可是戰爭並不像大家所想的那樣。它一開始就很糟,現在更糟。我們的士兵沒有什麼不好,不管是在軍艦裡、飛機上或防空洞裡的戰士都優秀精良。但我們缺乏準備,部署也很不得當……也許是我們的素質有問題。我們的人不想打仗,也沒有認真考慮過這件事,更談不上做什麼準備。
「不過最糟糕的時候已經過去了,我們糾正了以往的錯誤,慢慢地選擇合適的人去做合適的工作。我們開始按照正確的辦法去打這場戰爭。我們能贏,這點毫無疑問。但是必須一開始就打好。失敗的危險不是來自外部,不是來自德國人的炸彈,也不是因為中立國家被敵人占領,他們便可以從更有利的地勢襲擊我們。危險來自內部,來自我們城牆內的特洛伊木馬。如果你願意,就叫它第五縱隊。他們就在這兒,在我們內部。這些男男女女有的位高權重,有的只是普通百姓,但他們都相信納粹那一套,妄圖用納粹嚴格的信條取代我們悠閒散漫的民主自由制度。」
格蘭特俯身向前,用他悅耳的聲音繼續從容地說:「可是我們不知道他們是誰……」
湯米說:「但是必定……」
格蘭特有點不耐煩地說:「那些小嘍囉我們可以一網打盡,這很容易。重要的是別人。我們知道有幾個傢伙。海軍部至少有兩個高層人物。其中一個一定是G將軍的班底。空軍裡還有三個或者更多,情報部門至少有兩個,他們有管道得知內閣的機密。我們知道這些,因為根據目前的情況分析,必定有敵人打入了我們內部。洩密事件,而且是從高層把情報洩漏給敵人,使我們意識到了這一點。」
湯米和藹可親的臉上露出幾分茫然,他無可奈何地說:「可是,我對你能有什麼用呢?我一點都不了解這些人。」
格蘭特點了點頭。
「是啊,你不知道他們,他們也不知道你呀!」
他停了一下又接著說:「那些人,那些隱藏在上層的人,大都知道我們這些搞地下工作的人,他們不可能不搜集這方面的情報。我實在想不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便去找伊森普登。他現在已經退出核心了。即使生病了,腦子還是很清楚。他想起了你。你離開情報部門已經二十多年了。你的名字早已從那兒消失,你的面孔也沒人認識。你怎麼想?願不願意接下這個任務?」
湯米喜不自禁,笑得連嘴都合不攏。
「願不願意接下?你當然知道我求之不得。儘管我現在還不知道該從何下手。現在我只是一個『業餘愛好者』。」
「親愛的貝里福,我們需要的正是『業餘愛好者』。『專業』在這裡是障礙重重。你將接替我們一位最優秀的偵探。」
湯米臉上露出疑問的神色。格蘭特點了點頭。
「是的。上星期二他死在聖布里奇醫院,被一輛大卡車撞倒的……只活了幾個小時。車禍……其實根本不是什麼車禍,而是陰謀。」
湯米慢慢地說:「我明白了。」
格蘭特平靜地說:「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法考爾了解到了一些重要情況……他終於掌握了某些線索;他這場絕非偶然的死亡告訴了我們這一點。」
湯米好像有話要問。
格蘭特繼續說:「遺憾的是,他到底發現了什麼情況,我們一無所知。法考爾追蹤了一條又一條的線索,但是收穫不大。」格蘭特停了一下,繼續說:「法考爾一直昏迷不醒,直到臨死前才清醒了幾分鐘。他想說什麼,但只說出這樣幾個字:N或M,頌舒西。」
「那,」湯米說,「等於什麼都沒說。」
格蘭特臉上露出一絲微笑。
「多少說明了一點問題。你知道,我們以前就聽說過『N或M』這個代號。它代表兩個最重要也最受信任的德國間諜。我們以前截獲過他們在其他國家的活動資料,對他們略有所知。他們的使命就是在外國組織第五縱隊,並且充當該國和德國的聯絡橋梁。我們知道,N是個男人,M是個女人。這兩個人是希特勒非常信任的間諜。戰爭剛開始,我們破譯過這樣的一個密碼︰『建議N或M到英格蘭,委以全權……』」
「我明白了。法考爾……」
「據我分析,法考爾一定發現了某個人的線索。遺憾的是,我們不知道是哪一個。頌舒西聽起來不知所云。不過法考爾的法語一向不好,口音很重。他身上帶著一張到利漢普敦的回程車票。這個細節充分說明了一點問題︰利漢普敦是南部海岸一座新興的旅遊城市,那兒有許多私人開設的小旅館。其中有一家叫聖守喜……」
湯米說:「頌舒茜……聖守喜……我明白了。」
格蘭特說:「是嗎?」
「你的打算是,」湯米說,「讓我去那兒……搜索?」
「正是。」
湯米臉上又綻出微笑。
「任務不太明確,對吧?」他說,「我甚至連要找什麼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全靠你自己了。」
湯米嘆了一口氣,活動了一下肩膀。
「我可以試試看。不過我不是那種腦子特別靈光的人。」
「你過去不是成績非常好嗎?我聽說過了。」
「哦,那全靠運氣。」湯米連忙說。
「是呀,運氣正是我們需要的。」
湯米想了一會兒,說:「關於聖守喜那個地方……」
格蘭特聳了聳肩膀。
「也許只是白忙一場,我也不知道。法考爾臨死前也許喃喃唸的是:『舒西妹妹給戰士縫衣服。』這只是我們的猜測。」
「利漢普敦呢?」
「和其他地方沒什麼區別。什麼樣的人都有。老太太,老上校,無可懷疑的老處女,可疑的顧客,還有一兩個外國人。一團大雜燴。」
「N或M就隱藏在他們當中?」
「很難說。也許是和N或M接頭的人,也許是N或M本人。那是一個不起眼的地方,海濱度假勝地的一家普通小旅館。」
「你連我要找的是個男人還是女人也不知道?」
格蘭特搖了搖頭。
湯米說:「好吧,我試試看。」
「祝你好運,貝里福。現在關於細節部分……」
半個小時之後,陶品絲闖了進來。她氣喘吁吁,心裡充滿了焦急和好奇。湯米獨自一人坐在一張扶手椅裡,臉上露出一種不無疑惑的表情。
「怎麼樣?」陶品絲意味深長地說。
「哦,」湯米用一種模稜兩可的口氣說,「我找到一件工作。」
「什麼工作?」
湯米做了一個鬼臉。
「到蘇格蘭一個偏遠地區做行政事務。當然也是祕密工作。只是聽起來並不刺激。」
「我們兩個一起去,還是只有你自己?」
「恐怕只有我自己。」
「真該死!我們的卡特先生怎麼這麼不夠朋友?」
「我想也許因為這是個男女有別的工作,而且挺勞心勞力。」
「是發密碼還是破譯密碼?是不是黛博拉那種工作?你可要當心點,湯米,這種差事簡直能把你弄成神經病。半夜三更不睡覺,整晚走來走去,嘴裡不住地背著九七八三四五二八
六,或者什麼玩意兒。最後精神崩潰,住進療養院。」
「我不會的。」
陶品絲悶悶不樂地說:「這只是遲早的事。我能不能不參加你的工作,只是以妻子的身分陪你去?料理你的生活,工作一天之後能讓你吃口熱飯,在壁爐前幫你擺雙拖鞋。」
湯米看起來十分不安。
「真抱歉,老婆。非常抱歉,我也不想離開你……」
「但是你覺得你應該去。」陶品絲喃喃道,言語之中不無留戀。
「不管怎麼說,」湯米有氣無力地說,「你可以在家織毛線。」
「織毛線?」陶品絲說,「織毛線!」
她拿起正在織的那頂巴拉克拉盔帽扔到地上。
「我討厭這種卡其色的毛線,」陶品絲說,「還有海軍藍、空軍藍。我想要織大紅色的東西!」
「火藥味十足,」湯米說,「簡直要來一場閃電戰。」
他心裡非常難受。不過陶品絲是個律己甚嚴的人,她很快就面對現實,鼓勵湯米接受這件工作並且說,自己並不十分在意。她還補充說,她已經打聽到急救中心需要一個擦地板的人,也許這工作很適合自己。
三天後,湯米離開家到蘇格蘭東北部港市阿伯丁。陶品絲到車站為他送行。她的一雙眼睛亮晶晶的,含著淚水。她眨了幾下,沒讓淚水掉下來,努力裝出一副快樂的樣子。
火車開了,湯米看著妻子漸漸遠去、孤零零、瘦癟癟的身影,覺得喉嚨陣陣發緊。雖然是為了贏得這場戰爭,他還是覺得自己背棄了陶品絲。
他振作起精神。命令就是命令。
到達蘇格蘭之後,他又坐上火車,第二天就來到曼徹斯特。第三天火車把他送到利漢普敦。他先在一家大飯店住下,然後去那些私人開的小旅館看房間,打聽看看長住有沒有什麼優惠條件。
聖守喜是一棟紫紅色的維多利亞式別墅,坐落在一座小山的山坡上,從樓上的窗戶望過去,美麗的大海盡收眼底。門廳裡散發著一股淡淡的塵土味和煮飯的味道,但是和湯米看過的那幾家小旅館相比,聖守喜環境好得多。他在辦公室裡見到了老闆娘佩倫娜太太。那房間不大,也談不上整潔,一張大桌子上面鋪著幾張報紙。
佩倫娜太太也挺邋遢。她人已中年,微施脂粉,滿頭黑色的鬈髮亂糟糟的,一笑便露出一嘴潔白的牙齒。
湯米喃喃提到他一位年長的堂姐梅多斯小姐。兩年前,她曾在聖守喜住過。佩倫娜太太還清楚地記得梅多斯小姐……一位很可愛的老太太,也許並不是真的很老,很活潑,極富幽默感。
湯米小心翼翼地表示同意。他知道,確實有一位梅多斯小姐,情報部門告訴過他這些細節。
可愛的梅多斯小姐現在怎麼樣啊?
湯米不無悲傷地表示說,梅多斯小姐已經去世。佩倫娜太太十分同情地咂了咂嘴,又恰如其分地驚叫了一番,臉上現出哀傷的表情。
不一會兒,她便滔滔不絕地介紹起她的旅館。她說,有個房間很適合梅多斯先生住,從那裡看得見大海美麗的景色。她覺得梅多斯先生離開倫敦來這兒度假,真是明智之舉。她知道,現在的局勢讓人高興不起來,特別是經歷了這場流行性感冒之後……
佩倫娜太太邊說邊領他上樓看房間。她還提到每週的住宿費。湯米露出一副大失所望的樣子。佩倫娜太太解釋說,物價飛漲;湯米說,他現在收入不多,還得交稅,諸如此類。
佩倫娜太太嘆了一口氣,說:「這場可怕的戰爭……」
湯米表示同意,還說,照他看來,應該把希特勒這個傢伙絞死。瘋子,這傢伙真是一個瘋子!
佩倫娜同意他的觀點,接著又說,政府配給的食物太少,屠夫們也很難弄到肉,而雜碎更是經常不見。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她這個旅館老闆實在難當。不過考慮到梅多斯先生是梅多斯小姐的親戚,她可以少收半個基尼。
湯米離開聖守喜的時候,表示回去會再考慮一下這件事。佩倫娜太太一直把他送到大門,越發口若懸河起來,那股活潑勁讓湯米大吃一驚。他不得不承認,她雖然有點邋遢,但人挺漂亮的。他在心裡想,她是哪國人呢?一定不是道道地地的英國人。她的名字是西班牙或葡萄牙人的名字,但那也許是她丈夫的國籍,而不是她的。她說不定是愛爾蘭人,雖然沒有愛爾蘭人的口音。不過她精力旺盛,充滿活力,倒很像愛爾蘭婦女。
最後他們商定,梅多斯先生第二天就搬過來。
湯米說好六點來,佩倫娜太太準時到樓下門廳裡接他。她吩咐一位看起來傻乎乎的女僕把他的行李送到臥室。女僕瞪大一雙眼睛看著湯米,嘴巴也張得老大。佩倫娜太太領著湯米到一個她稱之為休息室的房間。
「我總是介紹客人們相互認識,」佩倫娜太太說。她滿臉堆笑,望著休息室那五個目光充滿疑惑的人。「這是我們新來的客人梅多斯先生。這位是奧羅克太太。」
一位像小山般強壯的女人朝他笑了笑。她一雙眼睛晶亮如珠,嘴唇上還有兩撇唇髭。
「這位是布萊奇利少校。」
少校上下打量了湯米一眼,朝他僵硬地點了一下頭。
「馮戴尼先生。」
一位金髮碧眼的年輕人站起來鞠了一躬。
「明頓小姐。」
一位戴著許多珠子、正在織著卡其色毛線的老婦人朝湯米傻笑著。
「還有班金索夫人。」
那人也在專心織毛線。她黑髮蓬亂的腦袋從織了一半的巴拉克拉盔帽上慢慢抬了起來。
湯米屏住呼吸,整個屋子天旋地轉。
班金索─陶品絲!
簡直令人難以置信!陶品絲正坐在聖守喜的休息室裡平心靜氣地織毛線!
她的目光和他相觸。那是種禮貌、漠然的陌生人目光。
他由衷讚嘆。
陶品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