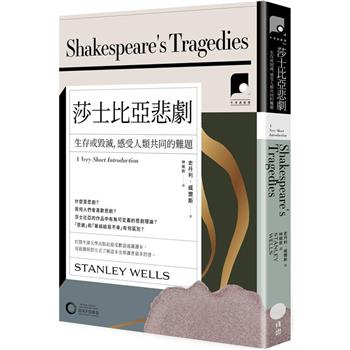第五章:《哈姆雷特》(節錄)
每個人或多或少都讀過《哈姆雷特》,無論在英文或任何語言中,「生存或毀滅,這就是問題」(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是全世界最常被引用的其中一句話。一位長相俊俏、身材健壯的年輕男人,看著一個人類頭骨的空洞眼窩;這分別是哈姆雷特和約里克——活著的年輕王子和死去的小丑,這個關於人類境遇的象徵被無限地重製(見圖四)。「丹麥的情況可能極為惡劣」(something is rotten in the state of Denmark)經常用在與莎士比亞原作出處極為不同的情境。
更甚者,《哈姆雷特》的故事基礎在不同的媒介中,包括:電影、電視、歌劇、芭蕾舞,視覺藝術作品、滑稽模仿(travesty)與戲謔(burlesque)和漫畫等,經過了無數次的改編、重撰,以及重新想像,因而可能已經走入了許多人的內心,即使他們從未讀過,或者看過《哈姆雷特》,甚至可能永遠不會接觸該劇的人,多多少少都聽過「哈姆雷特」這四個字。
但是,究竟什麼是《哈姆雷特》?舉例而言,相較於《凱撒大帝》和《馬克白》這兩部作品只有數種版本,《哈姆雷特》的文字有一種奇特的流動彈性。一六○三年首次付梓的版本——也就是所謂的「劣質四開本」(the bad quarto)中只有大約兩千兩百行,而其很有可能是對於莎士比亞作品的粗製濫造(「生存或是毀滅——沒錯,那就是重點」,哈姆雷特說道);一六○四年的第二個版本則有大約三千八百行,而一六二三年的《第一對開本》則是減少了大約二百三十行,且缺少了哈姆雷特最後的獨白,但增加了大約七十行的新內容,另外在許多地方的口語表達也有所差異。各位在莎士比亞現代書籍讀到的版本,很有可能是採納早期三種版本的綜合文本,並且包含了在舞臺表演中幾乎永遠都會被省略的段落。
一般來說,戲劇的「文本流動性」是戲劇藝術作品靈活度的衡量標準。舉例而言,比起繪畫或雕刻,戲劇通常更有彈性,而《哈姆雷特》比起大多數的戲劇作品,則是更為多變,也因而產生了更廣泛的詮釋空間。《哈姆雷特》每次上演時都是不同的作品,其差異程度不只是如同所有戲劇作品般,是因為演員實際的體型、年齡,以及性格,舞臺和服裝的設計等,還有其他可能會影響從紙本轉變至舞臺的變數,而是「劇情」和「對話」本身都會有所不同。
《哈姆雷特》有許多不同的電影版本,而它們的內容大多是從任何一種印刷版本中「選取」部分的段落進行演繹。例如,義大利導演法蘭高.齊費里尼在一九九○年與梅爾.吉伯遜(Mel Gibson)合作的刪減版本,由吉伯遜飾演王子哈姆雷特,時間長度大約是兩小時又十五分鐘,而齊費里尼和吉伯遜都增加了劇情並重新調整角色的演說內容;而英國演員肯尼斯.布萊納(Kenneth Branagh)在一九九六年推出的作品,則是採用完整內容,時間長達四個小時又二十分鐘(刪減版同時上映,展現了他們擔心完整文本對於某些觀眾來說可能太長)。雖然每個版本的基礎核心故事相同,都是哈姆雷特為了遭到謀殺的父親復仇,但是所有版本必定都會呈現大致上有著些許差異的敘事:有些版本完全省略了哈姆雷特父親被殺害的場景,甚至更動了原著故事中關於福丁布拉斯(Fortinbras)以及入侵丹麥的重要主線,並且在哈姆雷特死亡時倏然結束。這些發展都有助於解釋為什麼《哈姆雷特》與其主要角色會受到如此多元廣泛的詮釋。話雖如此,只要我們閱讀或觀賞任何一部忠於原作的版本,《哈姆雷特》故事之中依然有些事物是恆久不變。
「一個活著的人對著一個骷髏頭沉思」是《哈姆雷特》最令人熟悉的意象,而這個情況並非巧合。如果這部劇有一個最主要的主題,必定是「人如何應對死亡」。在《哈姆雷特》的開場,我們看見「已經死亡的國王鬼魂」──哈姆雷特的父親用恐怖的方式登場,在丹麥一座城堡的城垛中,於一群人面前現身,其中包括哈姆雷特的朋友何瑞修(Horatio);這群人看不出哈姆雷特的父親有何目的,不過他們將所見的情況告訴哈姆雷特,並確信「雖然這個鬼魂不願對我們開口,但他會和哈姆雷特說話」。
隨後,在一個形成鮮明對比的正式宮廷場景中,哈姆雷特首次登場。他刻意穿著表達哀悼的黑色衣物,靜默地站著,而哈姆雷特父親的弟弟克勞迪厄斯(Claudius)談到自己的婚姻──他的結婚對象正是甫過世的兄長留下的遺孀葛楚德(Gertrude)。克勞迪厄斯派出信使處理年輕的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對於丹麥王國造成的威脅,而他同意首席大臣波隆尼厄斯之子雷爾提斯(Laertes)離席時,刻意忽略了哈姆雷特。
當克勞迪厄斯和葛楚德終於開始注意到王子哈姆雷特時,他們責備哈姆雷特用了太久的時間悲悼父親之死,並拒絕讓他回到位於威登堡(Wittenberg)的大學。被獨自留在舞臺上的哈姆雷特,提出了這個角色知名的初次獨白,思考著實現自己的死亡:
哦,但願這個過於堅固的肉身能夠溶解,
融化吧,化為一滴露水,
或者是永恆的神並未設立
禁止屠戮自我的規儀!
(1.2.129-32)
遇見那個鬼魂使哈姆雷特內心的悲傷加劇,鬼魂給了哈姆雷特一個使命,要為「最違逆自然的惡劣謀殺」復仇。哈姆雷特誓言達成使命,而使命的艱鉅讓他瀕臨瘋狂,並且與他的女友奧菲莉亞發生了正面衝突;奧菲利亞將此事告訴她的父親波隆尼厄斯,
一個悲悽深沉的嘆息
似乎完全粉碎了哈姆雷特
並且終結他的生命
(2.1.95-97)
哈姆雷特的精神狀態使宮廷中人和哈姆雷特本人感到驚訝不解:
近來,我已經失去了所有的樂趣——然而,我不知道原因,
遺忘了所有鍛鍊的習慣;這個情況已然嚴重地影響了
我的性格,讓這個美好的世界,這座大地,對我來說
似乎變成了貧瘠的海角
(2.2.297-301)
哈姆雷特如此告訴羅森克朗茲(Rosencrantz)以及古德史騰(Guildenstern),這兩人都受命於國王和皇后,負責監視哈姆雷特。
當一群巡迴演出的劇團成員到訪赫爾辛格(Elsinore)時,哈姆雷特想要知道那個鬼魂的指控是否為事實,而他的方法就是說服劇團成員在向王室表演時插入一段情節──哈姆雷特希望這段情節可以讓克勞迪厄斯坦承自己的罪行。
當劇團的主演開始生動地演繹一種虛構的痛楚時,哈姆雷特用一段獨白文字折磨自己,開場為「哦,我竟是這種無賴與農奴」,責備自己沒有能力將真實的表達痛苦,進一步地轉變為實際的復仇行動。但是,哈姆雷特無法同時遵守鬼魂的命令又忠於自我。對於哈姆雷特來說,殺死國王將會(而且必然會)為自己帶來死亡。作為痛苦的解脫,死亡這個想法縱然吸引他,哈姆雷特依然害怕死亡是「一座人跡罕至之地」,正如我們從哈姆雷特核心的沉思「生存或是毀滅……」所理解的,死亡是一個巨大的問號,而這個問號由「鬼魂」和「哈姆雷特對於死亡的所有質疑」象徵著。
在此之後,裝瘋賣傻的哈姆雷特本人很快就開始遭受「死亡」的攻擊。他殺死波隆尼厄斯只是出乎意料的偶然,甚至可以說是意外,因為當哈姆雷特在母親的房間裡將刀刺進窗簾,意外殺死波隆尼厄斯的時候,哈姆雷特其實陷入了一種對於母親再婚的厭惡,並強烈渴望讓母親可以產生羞愧自知的偏執狀態中。
哈姆雷特的態度經過刻意的描寫,與受害者的子嗣形成強烈的對比。波隆尼厄斯的女兒奧菲莉亞陷入一種真正的瘋狂,最終以幾乎是自殺的方式結束了生命。波隆尼厄斯的兒子雷爾提斯燃起一股復仇的烈火,正如哈姆雷特本人可能會有的感受(雖然這種類比是不完全成立的,因為哈姆雷特的情況不同於雷爾提斯,哈姆雷特並未立刻且直接地知道是誰殺害了他的父親,甚至不知道父親是遭到謀殺)。
在哈姆雷特並未出現在舞臺上的漫長時刻(根據故事的發展,此時的他在英格蘭),死亡及其影響依然持續主導著劇情走向,呈現在奧菲莉亞表面的自殺,以及國王和雷爾提斯計畫殺死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回來時,場景在一座墓園(5.1),結合了該劇最放鬆的喜劇場景還有最令人深刻省思的訊息。該場景經過縝密的設計──觀眾才剛聽見葛楚德解釋奧菲莉亞如何溺斃,所以知道誰會被埋葬至墓園,而觀眾也會聽見和看見兩位工人幽默地用最符合現實的方式討論死亡。在死亡面前,萬物平等,唯有造墓人可以建構持續至世界末日的房子。哈姆雷特與何瑞修進場,一開始是「從遠方」走來,而哈姆雷特不曉得奧菲莉亞的死亡,冷漠地評論造墓人的使命本質與其工作方式之間的差異:「這個人難道對於自己的使命毫無感覺,竟然在造墓時歌唱?」
在該場的第二個舞臺,造墓人拿出了頭骨;在傳統上,頭骨是人類終將死亡的象徵,於是刺激了哈姆雷特,讓他諷刺地深思人類的虛榮浮幻。哈姆雷特不知道的祕密也稍微趨近了真相,掘墓人說他不是為了一個男人,也不是為了一個女人掘墓,而是「一個曾經是女人的人,先生,但願她的靈魂安息,她已經往生了」。造墓人提到哈姆雷特(哈姆雷特正在旁邊偷聽),「哈姆雷特已經瘋了,被送到英格蘭」,那裡不會發現他的瘋狂,因為「那裡的人和他一樣瘋狂」。
掘墓人認出其中一個頭骨是約里克時,我們看見哈姆雷特呈現稍早提到的姿勢。哈姆雷特明白了即使是最偉大的人類也終將如此,而莎士比亞在此也訴諸了曾經偉大的尤利烏斯.凱撒:
皇帝凱撒,死了化為塵土,
或許可以用於填補一個洞,用於阻擋風吹。
(5.1.208-9)
很快的,舞臺上開始進行葬禮。我們曉得被埋葬的是奧菲莉亞,但哈姆雷特至今依然不知道;當牧師透露逝者死於自殺,場上的情緒開始緊繃提高,而雷爾提斯說死者是他的妹妹,並詛咒正在看著他的哈姆雷特,接著他縱身跳入墳墓之中,悲痛的情緒就此爆發。雷爾提斯的悲痛行為有一種不受約束的直率情感,哈姆雷特希望自己聽見父親之死時,也可以有這樣的反應。哈姆雷特也用極具戲劇效果的姿態縱身躍入墳墓之中,他終於能夠用一種承認情感、承認個人身分,以及承認君王身分的方式表達自我:
是誰的悲傷
如此強烈,誰的悲傷言語
喚醒了漫遊的星辰,使其佇立不前
就像漫遊的受傷聽者?是我,
丹麥人哈姆雷特。
(5.1.250-4)
這個場景已經從「掘墓人以事實角度看待死亡的態度」轉變至「一種深刻的表達」,亦即:關於一個人的生命價值和死亡所能造成的沉重痛楚。在這個場景之後,哈姆雷特可以告訴何瑞修,他將會認為自己擁有充分的正當理由殺死克勞迪厄斯,實際上,哈姆雷特甚至認為自己有殺死克勞迪厄斯的道德使命:
——難道最符合良知的行為
不是用這隻手終結他的生命嗎?難道這不應該受到譴責嗎,
如果讓克勞迪厄斯這個人類本質之中的腐敗之物
造就了更多邪惡?
(5.2.68-71)
這段文字明確地表達了,就算不是莎士比亞本人的信念,至少也是哈姆雷特相信為了撥亂反正,凡人可以殺人、哈姆雷特認為他是自己國家的外科醫師。哈姆雷特知道與雷爾提斯決鬥很有可能讓自己喪命,但他用一種明確的斯多葛主義來面對:
即便是麻雀之死,其中依然藏著天命。倘若我的死期是現在
就不會是未來。如果我的死期不是未來,就會是現在。如果不是現在,
我終究會死。萬全的準備就是一切。
(5.2.165-8)
哈姆雷特終究達到了一種精神狀態,他知道自己被雷爾提斯的劍造成了致命傷,因為國王命令雷爾提斯之劍必須上毒,哈姆雷特認為自己可以義無反顧地殺死國王,如此一來,他不只可以替父親之死和母親之死復仇,他的行為也將為自己復仇。哈姆雷特帶著宮廷的優雅死去,並展現了一絲幽默,在他斷氣沉默之前,他談到死亡是一位警官,「冷漠無情的執法者」想要「堅持逮捕他」。
在《哈姆雷特》中想要追尋單一的主題,正如我迄今為止的討論,無法充分地展現這個卓越文本的豐富內容,《哈姆雷特》證明了莎士比亞創作能力的大幅成長。在《哈姆雷特》中我們可以看見許多在維多利亞時代受到歡迎的劇場元素:鬼魂、喜歡說教的父親形象(波隆尼厄斯)、劇中劇、無聲劇(默劇)、對於時事的譏諷、驟死、追逐、用音樂呈現的瘋狂場景、「小丑」的喜劇表演、決鬥,以及最後的混亂死亡。儘管《哈姆雷特》的主要情節是悲劇,但莎士比亞藉由反諷(irony)、諷刺(satire),和譏諷(sarcasm),對於劇情保有了一些喜劇的觀點。這也難怪法國新古典主義評論家伏爾泰(Voltaire)對於《哈姆雷特》並未遵守所有悲劇規則感到震驚,他是如此評論《哈姆雷特》:
一部粗俗野蠻的作品,即使是法國和義大利最粗俗的民眾也無法接受。在這部作品中,哈姆雷特在第二幕陷入瘋狂,他的情人則是在第三幕發瘋;哈姆雷特王子殺了情人的父親,假裝自己只是想要殺一隻老鼠,女主角投河自盡。該劇在舞臺上掘墓,而掘墓人縱情於符合其身分的插科打諢,手中甚至拿著死者的頭骨。哈姆雷特王子用同樣令人厭惡的方式回應掘墓人的可憎低俗。與此同時,劇中的另外一個角色征服了波蘭。
《哈姆雷特》是一部奇特的傑作,而不像《錯中錯》、《羅密歐與茱麗葉》或《凱撒大帝》那樣,是結構縝密的劇作。莎士比亞在《哈姆雷特》中的想像力早已「溢於所有衡量的方式」(o’erflows the measure;引用自《安東尼與克麗奧佩托拉》,莎士比亞在該作中展現了不亞於《哈姆雷特》的不羈)。在目前的舞臺表演慣例中,《哈姆雷特》通常會被刪減八百行左右的內容,而莎士比亞本人也不太可能認為他所撰寫的字字句句都會在一次舞臺表演中完整呈現。有些片段,例如,對於當時男孩劇團的時事譏諷(2.2.339-63)、哈姆雷特對於劇團演員和其劇本內容的建議(3.2)、哈姆雷特在墓園對於律師的諷刺,以及歐斯里克(Osric)的浮誇做作(5.2.112-30)都經常遭到刪減或省略。
莎士比亞以詩文和散文建立角色不同性格的技巧,過去曾經在《羅密歐與茱麗葉》展現最為出色的成果,到了《哈姆雷特》時則是駕輕就熟。這種技巧明確地表現在劇中鬼魂驚人的響亮言詞;表現在克勞迪厄斯於第一個宮廷場景中向哈姆雷特說話時的能言善道;表現在波隆尼厄斯向雷爾提斯的說教;表現在奧菲莉亞發瘋之後的破碎話語;掘墓人與其同伴的粗俗鄉村言語;以及歐斯里克在語言上的浮誇做作。哈姆雷特本人使用了範圍極為廣泛的詩文和散文,而以上的言詞顯然也屬於這個範圍。
哈姆雷特的性格如此敏感易變,任何風吹草動都會讓他產生反應,以致幾乎可以說他毫無自身性格,或者至少能夠認為他的性格處於一種持續的轉變流動,不停地想要尋找自身的身分認同,而或許,直到結局他在奧菲莉亞的屍體面前凜然面對雷爾提斯時,才終於達到了一種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