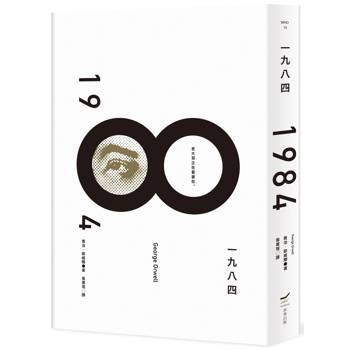第二部第一章(節錄)
上午過了一半,溫斯頓離開他的工作隔間去上廁所。
燈光明亮的長廊另一端,有個單獨的身影向他走來。是那個黑髮女孩。自從他在舊貨鋪外撞見她的那晚,已然過了四天。當她逐漸靠近,他看見她的右手臂用吊腕帶吊著,因為吊帶顏色和她的工作服相同,遠遠地還看不出來。她可能是在推轉一台用來「勾勒」小說情節的大型萬花筒時壓傷了手,虛構局裡常見的事故。
就在他們相距約四公尺遠時,女孩腳下絆了一跤,幾近迎面撲倒在地。她迸出一聲充滿痛楚的尖叫,看來是直接摔在她受傷的手臂上了。溫斯頓登時煞住腳步。女孩已經跪了起來,她的臉色變得慘白泛黃,襯托得嘴唇比平時更加鮮紅。她定定看著他的眼睛,求助的神情中恐懼多於疼痛。
一股異樣的情緒攪動溫斯頓的心。他面前是想置他於死地的敵人,卻也是個受苦的人類,可能還折斷了骨頭。眼下,他本能走上前去幫她。看見她摔在裹著繃帶的手臂上那一刻,他彷彿在自己身體感覺到她的疼痛。
「妳受傷了嗎?」他說。
「沒事,就是我的手。很快就好了。」她顫抖說話的樣子彷彿心跳得厲害,臉色明顯變得非常蒼白。
「沒有摔斷哪裡吧?」
「沒有,我沒事。現在暫時會痛,一下就過了。」
她向他伸出沒受傷的那隻手,他協助她站起身。她的臉上恢復了幾許血色,看起來好很多了。
「真的沒事。」她簡短重複道,「只是手腕稍微撞到而已。謝了,同志!」
說完,她朝著原本的方向繼續走去,步履輕快,像是真的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整起插曲大概不到半分鐘。喜怒不形於色已經從習慣變成本能,況且事情發生時,他們就站在一台電幕的正前方。儘管如此,在幫助她起身的兩三秒間,他還是得相當努力才不致流露出瞬間的驚訝,因為女孩在他手裡塞了某樣東西。她是有意為之的,這無需懷疑。那是一個小小扁扁的東西。他在踏進廁所門的那一刻,順勢把東西送入口袋,並用指尖感覺了一下。那是張摺成方形的紙條。
站在小便斗前的時候,他手指稍微用了點力,設法在口袋裡打開紙條。不用說,上面一定寫有什麼訊息。有那麼一下子,他想到要不要乾脆進到廁所隔間,當下看清紙條內容。不過,他很清楚這想法簡直愚不可及,別的地方還不一定,廁所隔間裡的電幕絕對隨時都有人在盯著。
他回到自己的工作隔間坐下,故作隨意地把紙條塞進桌上的紙堆,戴上眼鏡,將說寫機拉過來。「五分鐘,」他對自己說,「至少要等五分鐘!」他的心臟在胸膛裡撲通跳著,聲音大到令人惶恐。幸運的是他目前在處理的工作只是糾正一份長長的數據列表,純屬例行公事,不需要太專心。
無論紙條上寫了什麼,必定具有某種政治意義。就他看來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機率高很多,正如他所擔心的,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務。他想不透思想警察何以用這種方式傳遞訊息給他,但也許他們自有理由。寫在那張紙條上的,是一個威脅,一次傳喚,一道自殺命令,或者某種圈套。但還有另一種更瘋狂的可能性不斷地出現在他腦海中,他怎麼也揮之不去:訊息根本不是來自思想警察,而是某種地下組織。也許兄弟會真的存在!也許那女孩正是他們的一分子!這無疑是個荒誕的念頭,但在他的手摸到紙片的瞬間,這個念頭就躍入他的腦中。又過了幾分鐘,他才想到另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即便是現在,儘管他的理智告訴他那則訊息多半意味著死亡—但這不是他相信的答案,毫無道理的希望在他腦中固執地不肯離去,他的心狂跳不止,他對說寫機低聲念出數字時,要花很大力氣才能讓聲音不致發顫。
他捲起那份處理完的作業,投進氣動管。已經過了八分鐘。他調正鼻梁上的眼鏡,吐出一口氣,把次一批工作拉過來,那張紙條就躺在最上面。他把紙條攤平。上面是稚拙的筆跡,寫著幾個大字:
我愛你。
他楞了好幾秒,甚至忘了馬上把這張犯罪證據丟進記憶洞。就在他準備丟棄的時候,儘管他明知表現出太多興趣是危險的,還是忍不住再看過一遍,只為了確認上面真的有那些字。
這個上午剩下的時間著實難以定下心工作。相較於集中心思在一連串瑣碎的事務上,更難的是必須在電幕的視線下掩飾他的激動。他感覺肚子裡有團熊熊火焰。午餐時間,待在悶熱、擁擠又吵雜的食堂裡簡直是種折磨。他本希望吃飯時能獨自清靜一下,沒想到就是這麼倒楣,蠢蛋帕森斯一屁股坐在他旁邊,濃烈的汗臭幾乎要壓過燉菜的金屬怪味,他還口若懸河地大談仇恨週的準備工作。他尤其熱中談論他女兒在少年間諜小隊製作的老大哥頭像,是一座用紙漿糊成的模型,有兩公尺寬。最讓人煩躁的是,在一片人聲喧嘩中,溫斯頓幾乎聽不見帕森斯在說什麼,還得不斷請他重述那些白痴言論。就那麼一次,溫斯頓瞥見了女孩,她和另外兩個女生坐在食堂另一頭。她一副沒看見他的樣子,他也未再朝那個方向張望。
下午稍微沒那麼難熬。午餐過後,他馬上接到一項精細困難的工作,需要把其他事先擱在一邊,全神貫注好幾個小時。這項任務是篡改兩年前的一系列生產數據,以便抹黑一名如今處境堪憂的重要核心黨員。這是溫斯頓的拿手好戲,整整兩個多小時的時間,他成功把那女孩拋到腦後。之後,她的面容再次出現,隨之而來的是一股熾烈難忍的、想要獨處的渴望。唯有獨自一人,他才得以把事情的新發展理出頭緒。今晚是他必須去社區中心的日子。他在食堂裡胡亂吞下又一頓淡而無味的餐食,匆匆趕到社區中心,參加一場正經八百且愚蠢的「小組討論會」,打了兩局桌球,乾掉幾杯琴酒,又坐著聽了半小時的演講,主題為〈英社與西洋棋的關係〉。他的靈魂因無聊而痛苦擾動,但這一次,他沒有那股衝動規避掉社區中心的晚間活動。當我愛你三個字映入眼裡,活下去的渴望在他心中汩汩湧現,為小事冒風險突然顯得很笨。一直到了二十三點,當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只要保持靜默,便可以安然避開電幕的監視,他才有辦法不受干擾地好好思考。
有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需要解決:如何和女孩接觸,安排一次會面。他不再去懷疑這有沒有可能是她設下的陷阱。他知道不是,因為她遞給他紙條時的激動不安是千真萬確。她簡直嚇得魂不附體,而這是她該有的反應。他更是未動念拒絕她的表白。
僅僅五天前的晚上,他還考慮過要用鵝卵石砸碎她的頭骨,而這完全不重要了。他想著她年輕赤裸的身體,一如他在夢裡見過的模樣。他曾把她想像得和別人一樣蠢,以為她也是滿腦子謊言和仇恨,一顆心冰冷麻木。一想到可能會失去她,他全身一陣焦灼,那青春雪白的肉體可能會從他身邊溜走!他最害怕的是,若不快點與她聯繫,她可能會就此改變心意。然而,兩人的會面有著巨大的物理障礙,就像在棋局中你已經被喊了將軍,還得想辦法走下一步。無論你轉身朝向哪裡,電幕都正對著你。事實上,在讀了紙條後的五分鐘內,他就想遍了所有和她聯絡的方法;而此刻有了思考的時間,他又再逐一審視每一種方法,猶如把各式工具在桌上一字排開。
顯然,今天上午的那種偶遇不能再重演。如果她也在紀錄局工作,情況會相對簡單,可是他對虛構局的所在位置只有模糊的概念,再說他也沒有過去那裡的藉口。如果他知道她住在哪、她幾點下班,就可以安排在她回家路上巧遇;反之,緊跟著她回家就不妥當了,那表示他得在真相部外頭觀望、徘徊,這必然會引起注意。至於寫信給她,想都不用想。所有信件照例會在郵遞過程中拆開檢查,這甚至已不是祕密。
其實根本沒什麼人寫信。偶爾真的需要傳遞訊息就用明信片,上面已經印好長長的現成詞句列表,任你劃掉不適用的詞句。反正他也不知道那女孩的名字,更別說是地址。最後,他認定食堂是最安全的,如果他能設法和她單獨坐在同一張桌子,在中間那區,不要離電幕太近,加上周圍的交談聲足夠吵雜—一旦這樣的環境條件得以持續,比如三十秒,他們就有可能交換說幾句話。
接下來的一星期,日子就像是一個輾轉反側的夢。收到紙條隔天,她直到他要離開食堂時才出現,午休結束的哨音已響。看來她被換到比較晚的班次。他們擦肩而過時未看彼此一眼。再隔天,她在往常時間出現,可惜身邊有其她三個女孩,而且就坐在電幕下面。而後是度日如年的三天,她完全沒有現身,而他的整副身心像是被一種難以忍受的敏感所折磨,彷彿他變成透明的,每個動作、每絲聲響、每次觸碰、他說出、他聽見的每個字,都成了一種煎熬。即使是睡著的時候,他也無法完全掙脫她的影像。這些天裡他一次也沒去碰日記。如果說有什麼能紓解他的痛苦,那就是他的工作,有時候他可以忘掉自己整整十分鐘。她出了什麼事,他毫無線索,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探聽。她也許被蒸發了,也許自殺了,也許被調派到大洋國遙遠的另一端:最糟糕也最有可能的是,她也許就只是改變了心意,決心避開他。
接下來這天她現身了。手臂不再吊著,只有手腕纏著黏性繃帶。看見她的人影,那巨大的解脫感實在太飄飄然,他忍不住直直看了她幾秒。隔天他差一點就成功和她說到話了。他走進食堂時,她坐在一張離牆很遠的桌子,而且是獨自一人。時間還早,食堂裡的人還不多,領午餐的隊伍緩慢推進,就在溫斯頓快到櫃台之際,又因為前面有個人在抱怨他沒拿到糖精片而多耽擱了兩分鐘。當溫斯頓拿到他的飯菜,準備向女孩的桌子移動,她仍是一個人坐著。他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目光故意搜尋她後頭的座位。她就在大約三公尺的距離內了,再兩秒就到了。這時他背後有人叫道,「史密斯!」他假裝沒聽見。「史密斯!」那人又叫一次,聲音更加響亮。再裝也沒用了,他只好轉身。只見一個金髮、一臉蠢相的年輕人,他名叫威雪,溫斯頓跟他不熟,可是他正笑著邀請溫斯頓過去他那桌的一張空位。拒絕他並不安全。被人認出來以後,他沒辦法再去和一個無人陪伴的女孩坐同一桌,那太顯眼了。於是他露出友好的微笑坐了下來,那張金髮蠢臉則對他報以燦爛的笑容。溫斯頓幻想自己用一把十字鎬把那張臉劈成兩半。女孩那張桌子很快也坐滿了。
但她一定看見了他朝她走過去,或許她接收到了這份暗示。第二天他故意提早到食堂,果然,她就坐在差不多同一區的座位,又是一個人。排在溫斯頓前面的是個那種敏捷矮小的甲蟲型男人,扁平的臉上有雙多疑的小眼睛。當溫斯頓端著托盤離開櫃台,他看見那小矮子直直走向女孩那桌,他心頭的希望再次沉了下去。那方向更遠處還有另一個空位,只是那小矮子從外表看來,是很在意自己坐得舒不舒服的那種人,一定會選擇目前最空的桌子。溫斯頓心中一片冰冷地跟在後面。除非能和女孩獨處,否則一切都是徒勞。未想就在此時,匡啷一聲巨響,小矮子摔得四腳朝天,他的托盤脫手飛出,湯汁和咖啡都流到地板上了。他站起來時狠狠瞪了溫斯頓一眼,顯然懷疑是溫斯頓害他絆倒。但沒關係。五秒鐘以後,溫斯頓內心狂跳不已地在女孩這桌坐下。
上午過了一半,溫斯頓離開他的工作隔間去上廁所。
燈光明亮的長廊另一端,有個單獨的身影向他走來。是那個黑髮女孩。自從他在舊貨鋪外撞見她的那晚,已然過了四天。當她逐漸靠近,他看見她的右手臂用吊腕帶吊著,因為吊帶顏色和她的工作服相同,遠遠地還看不出來。她可能是在推轉一台用來「勾勒」小說情節的大型萬花筒時壓傷了手,虛構局裡常見的事故。
就在他們相距約四公尺遠時,女孩腳下絆了一跤,幾近迎面撲倒在地。她迸出一聲充滿痛楚的尖叫,看來是直接摔在她受傷的手臂上了。溫斯頓登時煞住腳步。女孩已經跪了起來,她的臉色變得慘白泛黃,襯托得嘴唇比平時更加鮮紅。她定定看著他的眼睛,求助的神情中恐懼多於疼痛。
一股異樣的情緒攪動溫斯頓的心。他面前是想置他於死地的敵人,卻也是個受苦的人類,可能還折斷了骨頭。眼下,他本能走上前去幫她。看見她摔在裹著繃帶的手臂上那一刻,他彷彿在自己身體感覺到她的疼痛。
「妳受傷了嗎?」他說。
「沒事,就是我的手。很快就好了。」她顫抖說話的樣子彷彿心跳得厲害,臉色明顯變得非常蒼白。
「沒有摔斷哪裡吧?」
「沒有,我沒事。現在暫時會痛,一下就過了。」
她向他伸出沒受傷的那隻手,他協助她站起身。她的臉上恢復了幾許血色,看起來好很多了。
「真的沒事。」她簡短重複道,「只是手腕稍微撞到而已。謝了,同志!」
說完,她朝著原本的方向繼續走去,步履輕快,像是真的什麼都沒發生一樣。整起插曲大概不到半分鐘。喜怒不形於色已經從習慣變成本能,況且事情發生時,他們就站在一台電幕的正前方。儘管如此,在幫助她起身的兩三秒間,他還是得相當努力才不致流露出瞬間的驚訝,因為女孩在他手裡塞了某樣東西。她是有意為之的,這無需懷疑。那是一個小小扁扁的東西。他在踏進廁所門的那一刻,順勢把東西送入口袋,並用指尖感覺了一下。那是張摺成方形的紙條。
站在小便斗前的時候,他手指稍微用了點力,設法在口袋裡打開紙條。不用說,上面一定寫有什麼訊息。有那麼一下子,他想到要不要乾脆進到廁所隔間,當下看清紙條內容。不過,他很清楚這想法簡直愚不可及,別的地方還不一定,廁所隔間裡的電幕絕對隨時都有人在盯著。
他回到自己的工作隔間坐下,故作隨意地把紙條塞進桌上的紙堆,戴上眼鏡,將說寫機拉過來。「五分鐘,」他對自己說,「至少要等五分鐘!」他的心臟在胸膛裡撲通跳著,聲音大到令人惶恐。幸運的是他目前在處理的工作只是糾正一份長長的數據列表,純屬例行公事,不需要太專心。
無論紙條上寫了什麼,必定具有某種政治意義。就他看來有兩種可能。第一種機率高很多,正如他所擔心的,女孩是思想警察的特務。他想不透思想警察何以用這種方式傳遞訊息給他,但也許他們自有理由。寫在那張紙條上的,是一個威脅,一次傳喚,一道自殺命令,或者某種圈套。但還有另一種更瘋狂的可能性不斷地出現在他腦海中,他怎麼也揮之不去:訊息根本不是來自思想警察,而是某種地下組織。也許兄弟會真的存在!也許那女孩正是他們的一分子!這無疑是個荒誕的念頭,但在他的手摸到紙片的瞬間,這個念頭就躍入他的腦中。又過了幾分鐘,他才想到另一個比較合理的解釋。即便是現在,儘管他的理智告訴他那則訊息多半意味著死亡—但這不是他相信的答案,毫無道理的希望在他腦中固執地不肯離去,他的心狂跳不止,他對說寫機低聲念出數字時,要花很大力氣才能讓聲音不致發顫。
他捲起那份處理完的作業,投進氣動管。已經過了八分鐘。他調正鼻梁上的眼鏡,吐出一口氣,把次一批工作拉過來,那張紙條就躺在最上面。他把紙條攤平。上面是稚拙的筆跡,寫著幾個大字:
我愛你。
他楞了好幾秒,甚至忘了馬上把這張犯罪證據丟進記憶洞。就在他準備丟棄的時候,儘管他明知表現出太多興趣是危險的,還是忍不住再看過一遍,只為了確認上面真的有那些字。
這個上午剩下的時間著實難以定下心工作。相較於集中心思在一連串瑣碎的事務上,更難的是必須在電幕的視線下掩飾他的激動。他感覺肚子裡有團熊熊火焰。午餐時間,待在悶熱、擁擠又吵雜的食堂裡簡直是種折磨。他本希望吃飯時能獨自清靜一下,沒想到就是這麼倒楣,蠢蛋帕森斯一屁股坐在他旁邊,濃烈的汗臭幾乎要壓過燉菜的金屬怪味,他還口若懸河地大談仇恨週的準備工作。他尤其熱中談論他女兒在少年間諜小隊製作的老大哥頭像,是一座用紙漿糊成的模型,有兩公尺寬。最讓人煩躁的是,在一片人聲喧嘩中,溫斯頓幾乎聽不見帕森斯在說什麼,還得不斷請他重述那些白痴言論。就那麼一次,溫斯頓瞥見了女孩,她和另外兩個女生坐在食堂另一頭。她一副沒看見他的樣子,他也未再朝那個方向張望。
下午稍微沒那麼難熬。午餐過後,他馬上接到一項精細困難的工作,需要把其他事先擱在一邊,全神貫注好幾個小時。這項任務是篡改兩年前的一系列生產數據,以便抹黑一名如今處境堪憂的重要核心黨員。這是溫斯頓的拿手好戲,整整兩個多小時的時間,他成功把那女孩拋到腦後。之後,她的面容再次出現,隨之而來的是一股熾烈難忍的、想要獨處的渴望。唯有獨自一人,他才得以把事情的新發展理出頭緒。今晚是他必須去社區中心的日子。他在食堂裡胡亂吞下又一頓淡而無味的餐食,匆匆趕到社區中心,參加一場正經八百且愚蠢的「小組討論會」,打了兩局桌球,乾掉幾杯琴酒,又坐著聽了半小時的演講,主題為〈英社與西洋棋的關係〉。他的靈魂因無聊而痛苦擾動,但這一次,他沒有那股衝動規避掉社區中心的晚間活動。當我愛你三個字映入眼裡,活下去的渴望在他心中汩汩湧現,為小事冒風險突然顯得很笨。一直到了二十三點,當他回到家躺在床上,在黑暗中,只要保持靜默,便可以安然避開電幕的監視,他才有辦法不受干擾地好好思考。
有一個現實層面的問題需要解決:如何和女孩接觸,安排一次會面。他不再去懷疑這有沒有可能是她設下的陷阱。他知道不是,因為她遞給他紙條時的激動不安是千真萬確。她簡直嚇得魂不附體,而這是她該有的反應。他更是未動念拒絕她的表白。
僅僅五天前的晚上,他還考慮過要用鵝卵石砸碎她的頭骨,而這完全不重要了。他想著她年輕赤裸的身體,一如他在夢裡見過的模樣。他曾把她想像得和別人一樣蠢,以為她也是滿腦子謊言和仇恨,一顆心冰冷麻木。一想到可能會失去她,他全身一陣焦灼,那青春雪白的肉體可能會從他身邊溜走!他最害怕的是,若不快點與她聯繫,她可能會就此改變心意。然而,兩人的會面有著巨大的物理障礙,就像在棋局中你已經被喊了將軍,還得想辦法走下一步。無論你轉身朝向哪裡,電幕都正對著你。事實上,在讀了紙條後的五分鐘內,他就想遍了所有和她聯絡的方法;而此刻有了思考的時間,他又再逐一審視每一種方法,猶如把各式工具在桌上一字排開。
顯然,今天上午的那種偶遇不能再重演。如果她也在紀錄局工作,情況會相對簡單,可是他對虛構局的所在位置只有模糊的概念,再說他也沒有過去那裡的藉口。如果他知道她住在哪、她幾點下班,就可以安排在她回家路上巧遇;反之,緊跟著她回家就不妥當了,那表示他得在真相部外頭觀望、徘徊,這必然會引起注意。至於寫信給她,想都不用想。所有信件照例會在郵遞過程中拆開檢查,這甚至已不是祕密。
其實根本沒什麼人寫信。偶爾真的需要傳遞訊息就用明信片,上面已經印好長長的現成詞句列表,任你劃掉不適用的詞句。反正他也不知道那女孩的名字,更別說是地址。最後,他認定食堂是最安全的,如果他能設法和她單獨坐在同一張桌子,在中間那區,不要離電幕太近,加上周圍的交談聲足夠吵雜—一旦這樣的環境條件得以持續,比如三十秒,他們就有可能交換說幾句話。
接下來的一星期,日子就像是一個輾轉反側的夢。收到紙條隔天,她直到他要離開食堂時才出現,午休結束的哨音已響。看來她被換到比較晚的班次。他們擦肩而過時未看彼此一眼。再隔天,她在往常時間出現,可惜身邊有其她三個女孩,而且就坐在電幕下面。而後是度日如年的三天,她完全沒有現身,而他的整副身心像是被一種難以忍受的敏感所折磨,彷彿他變成透明的,每個動作、每絲聲響、每次觸碰、他說出、他聽見的每個字,都成了一種煎熬。即使是睡著的時候,他也無法完全掙脫她的影像。這些天裡他一次也沒去碰日記。如果說有什麼能紓解他的痛苦,那就是他的工作,有時候他可以忘掉自己整整十分鐘。她出了什麼事,他毫無線索,也沒有任何方法可以探聽。她也許被蒸發了,也許自殺了,也許被調派到大洋國遙遠的另一端:最糟糕也最有可能的是,她也許就只是改變了心意,決心避開他。
接下來這天她現身了。手臂不再吊著,只有手腕纏著黏性繃帶。看見她的人影,那巨大的解脫感實在太飄飄然,他忍不住直直看了她幾秒。隔天他差一點就成功和她說到話了。他走進食堂時,她坐在一張離牆很遠的桌子,而且是獨自一人。時間還早,食堂裡的人還不多,領午餐的隊伍緩慢推進,就在溫斯頓快到櫃台之際,又因為前面有個人在抱怨他沒拿到糖精片而多耽擱了兩分鐘。當溫斯頓拿到他的飯菜,準備向女孩的桌子移動,她仍是一個人坐著。他若無其事地走過去,目光故意搜尋她後頭的座位。她就在大約三公尺的距離內了,再兩秒就到了。這時他背後有人叫道,「史密斯!」他假裝沒聽見。「史密斯!」那人又叫一次,聲音更加響亮。再裝也沒用了,他只好轉身。只見一個金髮、一臉蠢相的年輕人,他名叫威雪,溫斯頓跟他不熟,可是他正笑著邀請溫斯頓過去他那桌的一張空位。拒絕他並不安全。被人認出來以後,他沒辦法再去和一個無人陪伴的女孩坐同一桌,那太顯眼了。於是他露出友好的微笑坐了下來,那張金髮蠢臉則對他報以燦爛的笑容。溫斯頓幻想自己用一把十字鎬把那張臉劈成兩半。女孩那張桌子很快也坐滿了。
但她一定看見了他朝她走過去,或許她接收到了這份暗示。第二天他故意提早到食堂,果然,她就坐在差不多同一區的座位,又是一個人。排在溫斯頓前面的是個那種敏捷矮小的甲蟲型男人,扁平的臉上有雙多疑的小眼睛。當溫斯頓端著托盤離開櫃台,他看見那小矮子直直走向女孩那桌,他心頭的希望再次沉了下去。那方向更遠處還有另一個空位,只是那小矮子從外表看來,是很在意自己坐得舒不舒服的那種人,一定會選擇目前最空的桌子。溫斯頓心中一片冰冷地跟在後面。除非能和女孩獨處,否則一切都是徒勞。未想就在此時,匡啷一聲巨響,小矮子摔得四腳朝天,他的托盤脫手飛出,湯汁和咖啡都流到地板上了。他站起來時狠狠瞪了溫斯頓一眼,顯然懷疑是溫斯頓害他絆倒。但沒關係。五秒鐘以後,溫斯頓內心狂跳不已地在女孩這桌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