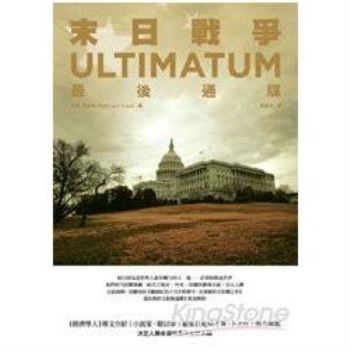二○三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星期三
戰情室,白宮
前夜裡,中國與美國的戰機在南中國海上空發生了一次空中接近。該架美國戰機在接近後發生故障,飛行員被迫彈射逃生。中國媒體將此事描述為一種勝利。一名中國政府發言人聲稱,假如中、美雙方爆發戰鬥衝突,戰爭將不會僅限於東亞。
總統不解這措辭,說:「你們認為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恩德利說:「長官,有可能是指,要攻打我們的關島。那肯定在他們戰機的航程範圍內。」他微笑起來,又說:「放馬過來吧。」
「夏威夷有沒有可能?」
「同上。但,阿拉斯加就不同了,他們攻打阿拉斯加會比較容易。但他們要打什麼目標?炸掉一堆冰山嗎?」
「美國本土呢?」
恩德利搖搖頭,說:「就我們所知,尚無中國海軍活動至射程範圍內。雙方長年以來有個諒解,如果中國把船艦開到具威脅性的位置,我們就會激烈反應。總統先生,他們要打我們本土,只有一個辦法。」V
「他們有沒有可能打掉我們的人造衛星?」
「我們就會打掉他們的。而且我們在軌道上有很多多餘的衛星。自從他們在二○○七年上演發射導彈摧毀衛星的小戲碼,我們就把這個可能考慮在內。他們得打掉五十枚衛星才會產生影響。」
「萬一他們真的打呢?」
恩德利聳聳肩,說:「他們知道蕭克若斯的理論。如果他們打掉太多衛星而使我們無法通訊,我們就會用核彈轟炸中國。」
總統又看了一次中國那份聲明的措辭,說:「所以,他們要打美國本土,就只有一種方式?」
賴瑞•歐森說:「他們若真的那樣搞,下場會一樣悽慘。他們或許很瘋,但不至於瘋成那樣。」
恩德利說:「他們用一枚核彈打我們,會遭受一百枚的回擊。他們很清楚這點。」
「萬一他們打一百枚過來?」
「仍會遭受一百枚的回擊。」
歐森說:「他們是理智的。他們相信他們能承受比我們更多的痛苦,這點固然不錯,但假如那痛苦是全面性毀滅,能否吸收更多痛苦就不重要了,對吧?」
恩德利說:「互相保證會同歸於盡。這一點使我們安然度過冷戰。蘇聯最強盛時,瞄準我們的核彈頭數量是今天中國的五倍。」
埃蘭•玻耳說:「用前一場戰爭的思維來面對新的戰局,這是錯誤的,我們可別犯這種錯。」
「二者有何不同?」
「上將,主角不同了。當冷戰開始,蘇聯便證明了自己的實力。但中國並沒有。他們多年來一直想展示他們是超級軍事強權。他們一直在尋找機會。」
歐森瞪大眼睛說:「你真的認為,試圖以核武攻擊我們,就是他們想要的機會?埃蘭呀,到時候他們那邊有誰能存活下來見證這場軍力展示?」
「他們或許以為我們不會反擊。」
「那他們就搞錯了。」
「當然,他們很可能搞錯。希特勒就把事情搞錯。所以他入侵波蘭。」
恩德利幾乎是帶著優越感地微笑起來,看著他說:「我還以為你都不使用前一場戰爭的思維來思考新戰局呢。」
「我只是要說——」
「總統先生,」歐森說:「他們是理智的,對吧?埃蘭的說法太荒謬了。」
恩德利說:「他們如果打我們,球賽就結束了。這我們清楚,他們也清楚。這份聲明說什麼戰爭不限於東亞,口頭說說罷了。」
歐森說:「全都只是說說。看看這空中接近事件,他們為何對此大聲嚷嚷?總統先生,因為他們不打算有任何實際行動。為何他們還不打台灣?正因為你牢牢站穩立場啊。」
班頓說:「不過,他們終究得有所動作,對吧?他們已盡力動員,卻尚無實際行動。他們已跨過每一條紅線。如果他們退縮,在國內很難不顏面掃地。」
恩德利說:「所以我才建議我們採用先發制人的計劃。」
「我另有建議。」班頓說:「他們需要一個下臺階,我們就給他們一個吧。我們已把事情的重點混淆了。此事無關台灣,而是關於『碳計劃』。還記得嗎?他們已把『碳計劃』忘了,一如各國都把它給忘了。該是提醒他們的時候了。」
埃蘭•玻耳問:「你有何主意?」
「我們宣布台灣問題可公開談判。賴瑞,你先聽我說完再講話。我們就說,我們相信有某種安排是可行的。我們打算與中國政府一起談台灣問題——但,唯有雙方取得『碳計劃』協議之後才談。這就產生關聯了,對吧?你自己說過的。好,我要把這關聯顛倒過來。不從台灣來導向『碳計劃』,而從『碳計劃』導向台灣。」
「你確信這對他們來說能算是一種下臺階?」歐森半信半疑地說。
「為什麼不?他們在國內要怎麼呈現它,就怎麼呈現。他們甚至不必在媒體上提到『碳計劃』是談判的一部分。他們可把事情講得好像是我們退縮。這我倒不在乎。我不介意給他們一點廉價的勝利,如果那是必須給的。」
杰•麥克馬洪搖搖頭,說:「所以我們要背叛台灣?」
「杰,你喜歡的話,就稱之為背叛吧。我會用別的詞來說它。自從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定位一直懸而未決。它是異常的東西,我們好像承認這個次政治實體,又好像沒承認。美國從未保證會承認它。在某個時間點,這事總得有個了結。我們從未承諾台灣建國,這個事實意味著,台灣問題總有一天會以回歸中國作結。如果說,台灣回歸中國是必然的,就讓我們從中換取些東西吧。我會再度跟譚總統通話。我們會盡全力幫忙,使台灣和平回歸。我們可用香港作為範本。」
歐森咕噥著說:「是咧,這還真是行得通呢。總統先生,這是該死的政策轉彎。」
「賴瑞,我們今天的世界不一樣了!今天的世界,跟我就職總統時的世界已經不同了。」
他們陷入沉默。
「呃……總統先生,」是奧利佛•吳在說話:「你所提的方法,唯有在他們能瞭解這整個大局的情況下,才行得通,唯有他們接受你連結這二個議題的方式,才行得通。」
「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我想也是。但,他們不一定會接受。」
「我不確定我是否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他們如果拒絕,那又怎麼樣?有何害處?」
「害處是,情況會變得更糟。你這樣做,等於承認他們有權拿回台灣,而你卻又規定他們何時才能有這權利。假如他們選擇這樣詮釋,就會更凸顯這是西方殖民主義的不合理要求了。這將變成對他們的侮辱。」
「這是個下臺階。」
「也可被視為侮辱。」
總統環顧左右。只見一顆顆的腦袋氣急敗壞而疑惑地搖著。
「總統先生,」歐森說:「我只能說,假如我們這麼做,退縮的人就是我們。打退堂鼓的人就是我們。但我們毋需那樣做啊。我們現在的做法,已經起作用了。」
麥克馬洪說:「長官,他們不會出兵的。這一點我贊同賴瑞。」
玻耳說:「也許他們還在準備。」
恩德利搖搖頭,說:「他們已經就緒。我們清楚他們的底細。」
歐森說:「我們堅持下去就對了。我們的部隊都各就各位,擺出一副準備出戰的樣子。如果我們準備好要出戰,最後就一定不用打。」
班頓說:「要是我們必須出戰,怎麼辦?」
麥克馬洪說:「那就出戰。」
總統點點頭,說:「我已擬好一份聲明。」
班•霍夫曼起身,分發一份份文件。
「這是什麼?」歐森說:「你跟誰商量過?」他讀起拿到的那份,說:「你真的要發布這聲明?」
「他們需要一個下臺階,這樣做可給他們下臺階,用不著流一滴血。」
麥克馬洪說:「如果台灣二千六百萬人民被他們接管時所流的血,不算在內的話。」
「誰說會流血?」
「北京和台北,絕不是什麼好朋友。」
「老實說,我願意冒那個險。無論如何,不管那裡會發生什麼,我都願意用來換取無數美國人的福祉,如果我們無法取得『碳計劃』的協議,那些美國人的生活都將遭到摧毀。」
「如果——」
「我說了,事情就這樣辦!」班頓猛然拍桌,又說:「要講『如果』,會有上千個。我已決定,這就是我要採取的動作。我會打電話給譚總統,讓他知道,然後茱蒂就會發布這聲明。現在,我要你們看看這聲明,如果你們認為哪裡需要改動,就告訴我。」
賴瑞•歐森說:「我認為,我們能犯的錯誤沒有比這更大了。」
「曉得了。」喬•班頓說。他環視左右,看看他們有無意見,又說:「好。我知道你們都會盡全力支持這個策略的。」
三小時後,聲明發布了。夜裡,一架美國F-42戰鬥機在南中國海上空遭到炸毀。中國當局宣稱,該戰機闖入了中國領空,反覆警告後仍不掉頭。他們把這侵犯之舉視同戰爭行為。
沒人知道,這起事件究竟是北京針對班頓的聲明的回應,抑或是中國某位好戰飛行員胡亂開火而幸運命中。
二○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第一家庭寓所,白宮
喬•班頓坐在床緣。他形容憔悴、筋疲力盡,感覺好像一個月沒睡覺了。他盯著地板,看著穿著藍色拖鞋的雙腳。
他感到自己一步步被捲入戰爭。不知為何,事情似乎無可避免。像是場噩夢,進入一封閉而令人窒息的噩夢世界,裡頭有無止盡的簡報、情資、臆測,與中國的衝突事件接踵而來,不斷升高,他卻無法結束這場夢。他們到底要什麼?無論他做什麼,說什麼,他們就是不肯罷手。聯合國秘書長恩列基已提議調解,但中國拒絕接受,認為聯合國無權介入與台灣相關的事件。中國表示,他們將抵制安理會預定於星期五召開的討論會。在美國國內,班頓無論看向何方,國會裡、媒體上、他自己的幕僚之間,盡是分裂和言語相互攻訐的火藥味。國會山莊裡正在討論民主黨所提的促請約束總統的決議案,以及共和黨所提的要求防衛台灣的決議案。有半數媒體似乎被戰爭的欲望所吞噬,彷彿台灣是第五十一州似的。另一半則痛斥他,認為美軍不該出現在那個區域。
他當總統任內不該是這種樣子。他任內應是要設定政策,提出立法,勸說國會議員支持,以及長年來他從賓州大道另一端的國會山莊看見白宮所做的各種事情。他任內應是以文明方式與它國的文明領袖打交道。向中國發動攻擊,不應該是他任內會做的。
他不太能理解自己怎會走到這地步。他難以站到局外來理解它。他哪裡做錯了?他有錯嗎?也許他受賴瑞•歐森的影響太深了。據約翰•艾爾斯的說法,歐森與玻耳除了開會幾乎無法好好說話。其實二人開會時也難以好好說話。他感覺當初若沒延攬歐森入閣,就不會落到今天的田地。他仍會循著京都議定書的預定架構與中國談判、與世界各國談判。而各國也將繼續敷衍、拖延。那麼,到什麼時間點,他才會作出結論,決定非得祭出激進的辦法不可?假如現在事情將演變為衝突,那麼無論如何,事情到了某個時間點都必然演變為衝突。或者,是這樣嗎?換成另一位手法較巧妙的總統,也許能處理得更好,也許能避開他腳下這敞開的深淵。
過去兩天裡,諸多外國領袖紛紛與他通了電話,敦促他撤回東亞地區的美軍,並向他保證,他們也會傳達相同的訊息給中國。這也使他疑惑。也許他們是對的,而他是錯的。也許過去幾週裡,他失去了判斷力,失去了方向感。他甚至開始質疑自己是否能勝任總統職位。有幾次,他納悶自己該不該辭職。如此一來,安琪拉•查維茲便會掌權。安琪拉會不會做得比較好?他找她當副手,主要為了拉丁裔選票,但她確實也精明能幹。然而,這些來找他談話,要他撤回駐軍的外國領袖,正是「碳計劃」公布後拒絕接他電話的同一批人啊。而且當他要求他們承諾簽署,他們依舊滑頭地閃躲。他們說,他們爭執的不是內容,而是班頓提出計劃的態度。好,喬•班頓至少可確定一件事,「碳計劃」本身沒錯。那大概是最後一件他能確切知道的事。當其它一切事情似乎都瘋狂地從他手中盤旋出去,他唯一可牢牢堅持的,就是那一件事。所以,如果得不到任何其他領袖的簽署承諾,他怎能退縮?事情到底要變得多迫切,他們才會瞭解?
但他不得不發動一次攻擊。那是緊接著非做不可的。他心裡有數。
黑瑟兒注視著他,說:「喬?」
他眼神渙散地看看她。
「親愛的,你還好嗎?」
總統聳聳肩。那負荷感覺好沉重。太沉重了。
「有什麼事是你本來可以改採別種做法的?」
太多事了。「真是反諷。以前,大家都以為將發生爭奪資源的戰爭。記得嗎?大家過去都說,石油快用完了,我們終將與中國戰爭以爭奪石油。卻沒人想到,衝突、爭鬥並未因資源而起,而是因碳排放而起。」
「我們要跟他們打仗嗎?」黑瑟兒輕聲問。
班頓無語。
「你要去國會?」
「愛琳認為不需要。還不需要。《戰爭權力法》的文字有模稜兩可之處。反正,行政機關從未接受國會有那權力。本來,伊拉克戰爭之後他們要釐清這案子,記得嗎?但他們從未好好計劃去做那件事。」(譯注:一九七三年民主黨多數的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想藉以限制總統海外用兵的職權。)
「蕭克若斯當年出兵哥倫比亞,是獲得國會同意的,對吧?」
「那不表示我現在也須經國會同意。」
黑瑟兒點點頭,說:「我可以問我們打算怎麼做嗎?」
班頓很為難地長長嘆了一口氣:「某種有限度的行動。不是戰爭。而是一次襲擊,瞄準某個軍事設施的攻擊。跑道或停機棚。我們不尋求造成傷亡。我費好大力氣才拉住麥克馬洪與恩德利,但我們終究得攻擊個什麼。我們的部隊在國際領空遭到攻擊。如今,每過幾小時就有衝突事件。有一個人死,三個人失蹤。我們不能放任情況這樣發展而不去解決。」
「聯合國呢?」
「我們必須用武力解決。這一點,我倒是同意恩德利。」
黑瑟兒點點頭,說:「所以我們會攻擊。那之後會怎樣?」
「我們就打那一次。他們罷手,我們就罷手。」總統說這話時,聲音很沮喪。
黑瑟兒面色凝重,說:「他們不罷手怎麼辦?」
「我們就小規模地跟他們衝突。衝突會漸漸有個收場。他們嚷嚷一些成功保衛了國土的話。我們則嚷嚷一些成功防止了台灣被侵略的話。然後雙方各把事情說成是己方得勝。」
「他們不攻打台灣嗎?」
「看起來不像要打。」喬•班頓皺眉說:「我真不知道他們腦裡在想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他們還在等什麼。他們等那麼多天,等了那麼久,我們的軍隊已盡可能接近,只差沒實際飛到台北市區上空。但看起來他們不像是要入侵台灣。」
「他們卻想惹毛我們?」
班頓聳聳肩,說:「太瘋狂了。」
「要是我們陷入泥淖怎麼辦?像越戰、伊拉克戰爭?」
「對付像中國這種國家,可不能被綁在戰爭裡。你只能小規模衝突。全面戰爭,光用想的,不管對誰來說都太恐怖了。」班頓停頓一下,又說:「黑瑟兒,前線將有更多人命損失。我們對此得有心理準備。但我認為如果我們遭受攻擊,美國人民一定會接受我們反擊。而美軍確實正遭受攻擊。」
黑瑟兒搖搖頭,說:「似乎沒什麼意義。」
「我同意。」班頓深深嘆口氣,又說:「嗯,我猜想,如果小規模衝突一陣子能讓雙方恢復談判,就不會沒有意義。如果我們成功使他們簽署『碳計劃』,也就不枉了。當小衝突結束後,我們會重新提議台灣回歸,以作為他們願達成碳排放協議的回報。希望那個時候,各國領袖眼看事情發展得如此過火,又看到我們如此堅決,足以使他們點頭加入。也許我們就是得走到戰爭邊緣,才能使他們瞭解這點。今晚,我會再次與哥羅丁通話。如果哥羅丁能加入我們,情況就不同了。他一關掉中國的燈火,事情就結束了。他只需瞭解到,對我們來說、對全體人類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事。說不定我們的攻擊行動將使他們所有人領悟到這點。也許小規模衝突是必需的。」
黑瑟兒皺起眉頭,憂心忡忡地說:「所以,你下決定了?」
「我會試著再傳一次訊息給溫。」
「他會接電話?」
班頓搖搖頭,說:「我得用別的管道。你知道的,我一直在思考甘迺迪與赫魯雪夫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的歷史。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但我們現在有一模一樣的問題。溝通。」
黑瑟兒驚慌地看著他說:「現在沒有核戰危機,對吧?」
「對。衝突將是傳統戰爭形式。我們會發動何種報復,他們心知肚明。全面性毀滅。這理論他們是清楚的。」
「真的會發生核戰嗎?」
班頓疲乏地搖搖頭,說:「除非我失去決定能力。我有六十分鐘可以決定我們報復的程度和速度。否則,全面性發射的自動裝置就會啟動。但中國人不曉得這點。他們以為戰略是預先定好的,我們要嘛一枚也不發射,要嘛全都發射。他們以為他們打一發、十發或一百發,我們的反應都一樣是大規模、壓倒性的發射。」
「但我們不會真的那樣打?」黑瑟兒說:「沒必要吧?」
「是沒必要。但不是我們希望怎樣,就會怎樣。你得有賭很大的心理準備。」
二○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橢圓形辦公室,白宮
F•威廉•奈特一副病容。比喬•班頓上次看見的他更瘦了。他很憔悴,眼神看來萬分焦慮。
他聆聽著總統要說的話。班•霍夫曼和約翰•艾爾斯在旁仔細觀察他。奈特很可能拒絕執行這任務。奈特很可能對於似乎是釀成這場危機的總統心懷怨恨。
但他們不知道還有誰比奈特更能接近溫。
「請告訴我,您打不打算走這一趟?」總統說。
「我一直沒見到溫主席,自從……」奈特清了清喉嚨。
「自從他上次拒絕見您?」總統說。
奈特點點頭。
「但是要讓他得知您想見他,對您來說仍是可能的?」
「我想是的。」
「附帶一問,您要如何做到?」
「有個電話號碼。」奈特回答。
班頓注視著他,說:「您就撥那號碼?」
「沒錯。我撥那號碼,並且留言。」
「真的假的呀。」班•霍夫曼說。
奈特清清喉嚨。
「或許我也該試著撥那號碼,」總統說:「來說服班。」
霍夫曼問:「如果他換了號碼,怎麼辦?」
「不會,」奈特說:「極少人知道這隻電話。」
「我猜想這號碼不能給我囉?」總統半開玩笑地問。
奈特清清喉嚨,說:「總統先生,我會試著打打看。我不確知他是否會見我。」
霍夫曼說:「我們會派一架飛機供您使用。」
「我有自己的。」
班頓說:「我來把要傳遞的訊息大意告訴您吧。」
奈特冷冷地看著他,憔悴的面容裡一絲情緒也不露。
「這訊息將對溫主席說,那扇門正對他敞開。目前有關碳排放的協議內容,與丁出現在奧斯陸前,他的人馬所同意的協議一模一樣。假如他撤回軍隊——回歸《馬尼拉諒解備忘錄》的內容——而且假如他宣布中國將接受『碳計劃』,我們也會撤回軍隊,之後,雙方必能以解決台灣問題為目的,坐下來好好協商。」
「總統先先,對不起,」奈特說:「『解決台灣問題』是什麼意思?如果您不介意我知道。」
總統深呼吸一口,說:「意思是我們一定會同意台灣島回歸中國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霍夫曼說。
奈特清清喉嚨,說:「如果他說不呢?」
「您就把他的訊息帶回來給我。」
「我的意思是,您在訊息裡是否會告訴他,如果他拒絕,會發生什麼事?這是不是一種最後通牒?」
總統看了看艾爾斯。
艾爾斯說:「我們希望把焦點放在雙方如何解決危機,而非如果解決不了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要給他一個提議,一個不流血的解決危機的方式。」
總統說:「如果他想拿回台灣,這會是個好辦法。若用侵略的方式,他是得不到台灣的。如果他問了你,你可以這樣轉告他。他會問嗎?」
奈特點點頭。
「那就這樣跟他說。如果他想要台灣,這兒有個辦法,但使用武力是不行的。美國不能讓台灣遭到武力侵犯。」
奈特清清喉嚨,說:「長官,請恕我這麼說,聽起來像是您在勒索他。」
「怎麼說?」
「呃,您說他能夠拿到台灣,但除非他做了某件他不想做的事,他才能拿到台灣。」
「奈特先生,中國非加入『碳計劃』不可。這星球上沒有一個人能夠不加入。這事跟台灣不相干,我就直說吧,無論台灣問題怎麼演變,溫主席都必須簽署。我想說的是,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問題上,確實有其歷史合法性。同時,大家不得不大幅削減碳排放,雖然無比艱難,卻也具有歷史性意義。所以,假如雙方可取得某種協議,讓台灣和平與中國統一,假如那有助於他敦促中國人支持『碳計劃』,沒問題,我們一定幫他這個忙。但『碳計劃』是首要議題。台灣則是枝節議題。」
「對他來說可不是。」
「對我們來說是。因此,我們打算在這件事留下彈性。但『碳計劃』就完全沒彈性的空間。『碳計劃』是核心。」
他們陷入沉默。
「好吧。」奈特說。
「您願意傳遞這訊息?」
「我會試試。」
喬•班頓從辦公桌上拿起一個信封。裡頭有他親筆寫下的短箋。
F•威廉•奈特接過它。有輛車子把他載到雷根機場,他的飛機正在那兒等候。接下來十三個鐘頭裡,他都在飛往北京的航道上。
這十三個鐘頭裡,喬•班頓幾乎是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地開。參謀首長聯席會提出他們的計劃,打算先對廣西省的空軍基地發動有限度的攻擊。二天前擊落美國飛行員的戰機便是自該基地飛出。他們提出若干目標,以及後續的攻擊方案,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在戰情室裡用幾張地圖闡釋三種戰局昇高的層級。他們也一一詳述目前關於防衛台灣的若干方案,如果總統下令採用的話。喬•班頓很想知道,北京的某處是否也召開著一樣的會議。他很想知道北京那邊的螢幕上顯示的是何種地圖。
這十三小時之間,美、中雙方的戰鬥機在國際領空上分別出現十八次不到一百公尺的空中接近。浙江省一家克萊斯勒汽車展售門市遭燒毀。美國銀行若干分行辦事處的窗戶遭人砸毀。在台
戰情室,白宮
前夜裡,中國與美國的戰機在南中國海上空發生了一次空中接近。該架美國戰機在接近後發生故障,飛行員被迫彈射逃生。中國媒體將此事描述為一種勝利。一名中國政府發言人聲稱,假如中、美雙方爆發戰鬥衝突,戰爭將不會僅限於東亞。
總統不解這措辭,說:「你們認為那到底是什麼意思?」
恩德利說:「長官,有可能是指,要攻打我們的關島。那肯定在他們戰機的航程範圍內。」他微笑起來,又說:「放馬過來吧。」
「夏威夷有沒有可能?」
「同上。但,阿拉斯加就不同了,他們攻打阿拉斯加會比較容易。但他們要打什麼目標?炸掉一堆冰山嗎?」
「美國本土呢?」
恩德利搖搖頭,說:「就我們所知,尚無中國海軍活動至射程範圍內。雙方長年以來有個諒解,如果中國把船艦開到具威脅性的位置,我們就會激烈反應。總統先生,他們要打我們本土,只有一個辦法。」V
「他們有沒有可能打掉我們的人造衛星?」
「我們就會打掉他們的。而且我們在軌道上有很多多餘的衛星。自從他們在二○○七年上演發射導彈摧毀衛星的小戲碼,我們就把這個可能考慮在內。他們得打掉五十枚衛星才會產生影響。」
「萬一他們真的打呢?」
恩德利聳聳肩,說:「他們知道蕭克若斯的理論。如果他們打掉太多衛星而使我們無法通訊,我們就會用核彈轟炸中國。」
總統又看了一次中國那份聲明的措辭,說:「所以,他們要打美國本土,就只有一種方式?」
賴瑞•歐森說:「他們若真的那樣搞,下場會一樣悽慘。他們或許很瘋,但不至於瘋成那樣。」
恩德利說:「他們用一枚核彈打我們,會遭受一百枚的回擊。他們很清楚這點。」
「萬一他們打一百枚過來?」
「仍會遭受一百枚的回擊。」
歐森說:「他們是理智的。他們相信他們能承受比我們更多的痛苦,這點固然不錯,但假如那痛苦是全面性毀滅,能否吸收更多痛苦就不重要了,對吧?」
恩德利說:「互相保證會同歸於盡。這一點使我們安然度過冷戰。蘇聯最強盛時,瞄準我們的核彈頭數量是今天中國的五倍。」
埃蘭•玻耳說:「用前一場戰爭的思維來面對新的戰局,這是錯誤的,我們可別犯這種錯。」
「二者有何不同?」
「上將,主角不同了。當冷戰開始,蘇聯便證明了自己的實力。但中國並沒有。他們多年來一直想展示他們是超級軍事強權。他們一直在尋找機會。」
歐森瞪大眼睛說:「你真的認為,試圖以核武攻擊我們,就是他們想要的機會?埃蘭呀,到時候他們那邊有誰能存活下來見證這場軍力展示?」
「他們或許以為我們不會反擊。」
「那他們就搞錯了。」
「當然,他們很可能搞錯。希特勒就把事情搞錯。所以他入侵波蘭。」
恩德利幾乎是帶著優越感地微笑起來,看著他說:「我還以為你都不使用前一場戰爭的思維來思考新戰局呢。」
「我只是要說——」
「總統先生,」歐森說:「他們是理智的,對吧?埃蘭的說法太荒謬了。」
恩德利說:「他們如果打我們,球賽就結束了。這我們清楚,他們也清楚。這份聲明說什麼戰爭不限於東亞,口頭說說罷了。」
歐森說:「全都只是說說。看看這空中接近事件,他們為何對此大聲嚷嚷?總統先生,因為他們不打算有任何實際行動。為何他們還不打台灣?正因為你牢牢站穩立場啊。」
班頓說:「不過,他們終究得有所動作,對吧?他們已盡力動員,卻尚無實際行動。他們已跨過每一條紅線。如果他們退縮,在國內很難不顏面掃地。」
恩德利說:「所以我才建議我們採用先發制人的計劃。」
「我另有建議。」班頓說:「他們需要一個下臺階,我們就給他們一個吧。我們已把事情的重點混淆了。此事無關台灣,而是關於『碳計劃』。還記得嗎?他們已把『碳計劃』忘了,一如各國都把它給忘了。該是提醒他們的時候了。」
埃蘭•玻耳問:「你有何主意?」
「我們宣布台灣問題可公開談判。賴瑞,你先聽我說完再講話。我們就說,我們相信有某種安排是可行的。我們打算與中國政府一起談台灣問題——但,唯有雙方取得『碳計劃』協議之後才談。這就產生關聯了,對吧?你自己說過的。好,我要把這關聯顛倒過來。不從台灣來導向『碳計劃』,而從『碳計劃』導向台灣。」
「你確信這對他們來說能算是一種下臺階?」歐森半信半疑地說。
「為什麼不?他們在國內要怎麼呈現它,就怎麼呈現。他們甚至不必在媒體上提到『碳計劃』是談判的一部分。他們可把事情講得好像是我們退縮。這我倒不在乎。我不介意給他們一點廉價的勝利,如果那是必須給的。」
杰•麥克馬洪搖搖頭,說:「所以我們要背叛台灣?」
「杰,你喜歡的話,就稱之為背叛吧。我會用別的詞來說它。自從一九四九年,台灣的定位一直懸而未決。它是異常的東西,我們好像承認這個次政治實體,又好像沒承認。美國從未保證會承認它。在某個時間點,這事總得有個了結。我們從未承諾台灣建國,這個事實意味著,台灣問題總有一天會以回歸中國作結。如果說,台灣回歸中國是必然的,就讓我們從中換取些東西吧。我會再度跟譚總統通話。我們會盡全力幫忙,使台灣和平回歸。我們可用香港作為範本。」
歐森咕噥著說:「是咧,這還真是行得通呢。總統先生,這是該死的政策轉彎。」
「賴瑞,我們今天的世界不一樣了!今天的世界,跟我就職總統時的世界已經不同了。」
他們陷入沉默。
「呃……總統先生,」是奧利佛•吳在說話:「你所提的方法,唯有在他們能瞭解這整個大局的情況下,才行得通,唯有他們接受你連結這二個議題的方式,才行得通。」
「這就是我要做的事。」
「我想也是。但,他們不一定會接受。」
「我不確定我是否明白你的意思,但是……他們如果拒絕,那又怎麼樣?有何害處?」
「害處是,情況會變得更糟。你這樣做,等於承認他們有權拿回台灣,而你卻又規定他們何時才能有這權利。假如他們選擇這樣詮釋,就會更凸顯這是西方殖民主義的不合理要求了。這將變成對他們的侮辱。」
「這是個下臺階。」
「也可被視為侮辱。」
總統環顧左右。只見一顆顆的腦袋氣急敗壞而疑惑地搖著。
「總統先生,」歐森說:「我只能說,假如我們這麼做,退縮的人就是我們。打退堂鼓的人就是我們。但我們毋需那樣做啊。我們現在的做法,已經起作用了。」
麥克馬洪說:「長官,他們不會出兵的。這一點我贊同賴瑞。」
玻耳說:「也許他們還在準備。」
恩德利搖搖頭,說:「他們已經就緒。我們清楚他們的底細。」
歐森說:「我們堅持下去就對了。我們的部隊都各就各位,擺出一副準備出戰的樣子。如果我們準備好要出戰,最後就一定不用打。」
班頓說:「要是我們必須出戰,怎麼辦?」
麥克馬洪說:「那就出戰。」
總統點點頭,說:「我已擬好一份聲明。」
班•霍夫曼起身,分發一份份文件。
「這是什麼?」歐森說:「你跟誰商量過?」他讀起拿到的那份,說:「你真的要發布這聲明?」
「他們需要一個下臺階,這樣做可給他們下臺階,用不著流一滴血。」
麥克馬洪說:「如果台灣二千六百萬人民被他們接管時所流的血,不算在內的話。」
「誰說會流血?」
「北京和台北,絕不是什麼好朋友。」
「老實說,我願意冒那個險。無論如何,不管那裡會發生什麼,我都願意用來換取無數美國人的福祉,如果我們無法取得『碳計劃』的協議,那些美國人的生活都將遭到摧毀。」
「如果——」
「我說了,事情就這樣辦!」班頓猛然拍桌,又說:「要講『如果』,會有上千個。我已決定,這就是我要採取的動作。我會打電話給譚總統,讓他知道,然後茱蒂就會發布這聲明。現在,我要你們看看這聲明,如果你們認為哪裡需要改動,就告訴我。」
賴瑞•歐森說:「我認為,我們能犯的錯誤沒有比這更大了。」
「曉得了。」喬•班頓說。他環視左右,看看他們有無意見,又說:「好。我知道你們都會盡全力支持這個策略的。」
三小時後,聲明發布了。夜裡,一架美國F-42戰鬥機在南中國海上空遭到炸毀。中國當局宣稱,該戰機闖入了中國領空,反覆警告後仍不掉頭。他們把這侵犯之舉視同戰爭行為。
沒人知道,這起事件究竟是北京針對班頓的聲明的回應,抑或是中國某位好戰飛行員胡亂開火而幸運命中。
二○三三年,十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第一家庭寓所,白宮
喬•班頓坐在床緣。他形容憔悴、筋疲力盡,感覺好像一個月沒睡覺了。他盯著地板,看著穿著藍色拖鞋的雙腳。
他感到自己一步步被捲入戰爭。不知為何,事情似乎無可避免。像是場噩夢,進入一封閉而令人窒息的噩夢世界,裡頭有無止盡的簡報、情資、臆測,與中國的衝突事件接踵而來,不斷升高,他卻無法結束這場夢。他們到底要什麼?無論他做什麼,說什麼,他們就是不肯罷手。聯合國秘書長恩列基已提議調解,但中國拒絕接受,認為聯合國無權介入與台灣相關的事件。中國表示,他們將抵制安理會預定於星期五召開的討論會。在美國國內,班頓無論看向何方,國會裡、媒體上、他自己的幕僚之間,盡是分裂和言語相互攻訐的火藥味。國會山莊裡正在討論民主黨所提的促請約束總統的決議案,以及共和黨所提的要求防衛台灣的決議案。有半數媒體似乎被戰爭的欲望所吞噬,彷彿台灣是第五十一州似的。另一半則痛斥他,認為美軍不該出現在那個區域。
他當總統任內不該是這種樣子。他任內應是要設定政策,提出立法,勸說國會議員支持,以及長年來他從賓州大道另一端的國會山莊看見白宮所做的各種事情。他任內應是以文明方式與它國的文明領袖打交道。向中國發動攻擊,不應該是他任內會做的。
他不太能理解自己怎會走到這地步。他難以站到局外來理解它。他哪裡做錯了?他有錯嗎?也許他受賴瑞•歐森的影響太深了。據約翰•艾爾斯的說法,歐森與玻耳除了開會幾乎無法好好說話。其實二人開會時也難以好好說話。他感覺當初若沒延攬歐森入閣,就不會落到今天的田地。他仍會循著京都議定書的預定架構與中國談判、與世界各國談判。而各國也將繼續敷衍、拖延。那麼,到什麼時間點,他才會作出結論,決定非得祭出激進的辦法不可?假如現在事情將演變為衝突,那麼無論如何,事情到了某個時間點都必然演變為衝突。或者,是這樣嗎?換成另一位手法較巧妙的總統,也許能處理得更好,也許能避開他腳下這敞開的深淵。
過去兩天裡,諸多外國領袖紛紛與他通了電話,敦促他撤回東亞地區的美軍,並向他保證,他們也會傳達相同的訊息給中國。這也使他疑惑。也許他們是對的,而他是錯的。也許過去幾週裡,他失去了判斷力,失去了方向感。他甚至開始質疑自己是否能勝任總統職位。有幾次,他納悶自己該不該辭職。如此一來,安琪拉•查維茲便會掌權。安琪拉會不會做得比較好?他找她當副手,主要為了拉丁裔選票,但她確實也精明能幹。然而,這些來找他談話,要他撤回駐軍的外國領袖,正是「碳計劃」公布後拒絕接他電話的同一批人啊。而且當他要求他們承諾簽署,他們依舊滑頭地閃躲。他們說,他們爭執的不是內容,而是班頓提出計劃的態度。好,喬•班頓至少可確定一件事,「碳計劃」本身沒錯。那大概是最後一件他能確切知道的事。當其它一切事情似乎都瘋狂地從他手中盤旋出去,他唯一可牢牢堅持的,就是那一件事。所以,如果得不到任何其他領袖的簽署承諾,他怎能退縮?事情到底要變得多迫切,他們才會瞭解?
但他不得不發動一次攻擊。那是緊接著非做不可的。他心裡有數。
黑瑟兒注視著他,說:「喬?」
他眼神渙散地看看她。
「親愛的,你還好嗎?」
總統聳聳肩。那負荷感覺好沉重。太沉重了。
「有什麼事是你本來可以改採別種做法的?」
太多事了。「真是反諷。以前,大家都以為將發生爭奪資源的戰爭。記得嗎?大家過去都說,石油快用完了,我們終將與中國戰爭以爭奪石油。卻沒人想到,衝突、爭鬥並未因資源而起,而是因碳排放而起。」
「我們要跟他們打仗嗎?」黑瑟兒輕聲問。
班頓無語。
「你要去國會?」
「愛琳認為不需要。還不需要。《戰爭權力法》的文字有模稜兩可之處。反正,行政機關從未接受國會有那權力。本來,伊拉克戰爭之後他們要釐清這案子,記得嗎?但他們從未好好計劃去做那件事。」(譯注:一九七三年民主黨多數的國會通過了《戰爭權力法》,想藉以限制總統海外用兵的職權。)
「蕭克若斯當年出兵哥倫比亞,是獲得國會同意的,對吧?」
「那不表示我現在也須經國會同意。」
黑瑟兒點點頭,說:「我可以問我們打算怎麼做嗎?」
班頓很為難地長長嘆了一口氣:「某種有限度的行動。不是戰爭。而是一次襲擊,瞄準某個軍事設施的攻擊。跑道或停機棚。我們不尋求造成傷亡。我費好大力氣才拉住麥克馬洪與恩德利,但我們終究得攻擊個什麼。我們的部隊在國際領空遭到攻擊。如今,每過幾小時就有衝突事件。有一個人死,三個人失蹤。我們不能放任情況這樣發展而不去解決。」
「聯合國呢?」
「我們必須用武力解決。這一點,我倒是同意恩德利。」
黑瑟兒點點頭,說:「所以我們會攻擊。那之後會怎樣?」
「我們就打那一次。他們罷手,我們就罷手。」總統說這話時,聲音很沮喪。
黑瑟兒面色凝重,說:「他們不罷手怎麼辦?」
「我們就小規模地跟他們衝突。衝突會漸漸有個收場。他們嚷嚷一些成功保衛了國土的話。我們則嚷嚷一些成功防止了台灣被侵略的話。然後雙方各把事情說成是己方得勝。」
「他們不攻打台灣嗎?」
「看起來不像要打。」喬•班頓皺眉說:「我真不知道他們腦裡在想什麼東西。我不知道他們還在等什麼。他們等那麼多天,等了那麼久,我們的軍隊已盡可能接近,只差沒實際飛到台北市區上空。但看起來他們不像是要入侵台灣。」
「他們卻想惹毛我們?」
班頓聳聳肩,說:「太瘋狂了。」
「要是我們陷入泥淖怎麼辦?像越戰、伊拉克戰爭?」
「對付像中國這種國家,可不能被綁在戰爭裡。你只能小規模衝突。全面戰爭,光用想的,不管對誰來說都太恐怖了。」班頓停頓一下,又說:「黑瑟兒,前線將有更多人命損失。我們對此得有心理準備。但我認為如果我們遭受攻擊,美國人民一定會接受我們反擊。而美軍確實正遭受攻擊。」
黑瑟兒搖搖頭,說:「似乎沒什麼意義。」
「我同意。」班頓深深嘆口氣,又說:「嗯,我猜想,如果小規模衝突一陣子能讓雙方恢復談判,就不會沒有意義。如果我們成功使他們簽署『碳計劃』,也就不枉了。當小衝突結束後,我們會重新提議台灣回歸,以作為他們願達成碳排放協議的回報。希望那個時候,各國領袖眼看事情發展得如此過火,又看到我們如此堅決,足以使他們點頭加入。也許我們就是得走到戰爭邊緣,才能使他們瞭解這點。今晚,我會再次與哥羅丁通話。如果哥羅丁能加入我們,情況就不同了。他一關掉中國的燈火,事情就結束了。他只需瞭解到,對我們來說、對全體人類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事。說不定我們的攻擊行動將使他們所有人領悟到這點。也許小規模衝突是必需的。」
黑瑟兒皺起眉頭,憂心忡忡地說:「所以,你下決定了?」
「我會試著再傳一次訊息給溫。」
「他會接電話?」
班頓搖搖頭,說:「我得用別的管道。你知道的,我一直在思考甘迺迪與赫魯雪夫在古巴飛彈危機期間的歷史。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但我們現在有一模一樣的問題。溝通。」
黑瑟兒驚慌地看著他說:「現在沒有核戰危機,對吧?」
「對。衝突將是傳統戰爭形式。我們會發動何種報復,他們心知肚明。全面性毀滅。這理論他們是清楚的。」
「真的會發生核戰嗎?」
班頓疲乏地搖搖頭,說:「除非我失去決定能力。我有六十分鐘可以決定我們報復的程度和速度。否則,全面性發射的自動裝置就會啟動。但中國人不曉得這點。他們以為戰略是預先定好的,我們要嘛一枚也不發射,要嘛全都發射。他們以為他們打一發、十發或一百發,我們的反應都一樣是大規模、壓倒性的發射。」
「但我們不會真的那樣打?」黑瑟兒說:「沒必要吧?」
「是沒必要。但不是我們希望怎樣,就會怎樣。你得有賭很大的心理準備。」
二○三三年,十月二十八日,星期五
橢圓形辦公室,白宮
F•威廉•奈特一副病容。比喬•班頓上次看見的他更瘦了。他很憔悴,眼神看來萬分焦慮。
他聆聽著總統要說的話。班•霍夫曼和約翰•艾爾斯在旁仔細觀察他。奈特很可能拒絕執行這任務。奈特很可能對於似乎是釀成這場危機的總統心懷怨恨。
但他們不知道還有誰比奈特更能接近溫。
「請告訴我,您打不打算走這一趟?」總統說。
「我一直沒見到溫主席,自從……」奈特清了清喉嚨。
「自從他上次拒絕見您?」總統說。
奈特點點頭。
「但是要讓他得知您想見他,對您來說仍是可能的?」
「我想是的。」
「附帶一問,您要如何做到?」
「有個電話號碼。」奈特回答。
班頓注視著他,說:「您就撥那號碼?」
「沒錯。我撥那號碼,並且留言。」
「真的假的呀。」班•霍夫曼說。
奈特清清喉嚨。
「或許我也該試著撥那號碼,」總統說:「來說服班。」
霍夫曼問:「如果他換了號碼,怎麼辦?」
「不會,」奈特說:「極少人知道這隻電話。」
「我猜想這號碼不能給我囉?」總統半開玩笑地問。
奈特清清喉嚨,說:「總統先生,我會試著打打看。我不確知他是否會見我。」
霍夫曼說:「我們會派一架飛機供您使用。」
「我有自己的。」
班頓說:「我來把要傳遞的訊息大意告訴您吧。」
奈特冷冷地看著他,憔悴的面容裡一絲情緒也不露。
「這訊息將對溫主席說,那扇門正對他敞開。目前有關碳排放的協議內容,與丁出現在奧斯陸前,他的人馬所同意的協議一模一樣。假如他撤回軍隊——回歸《馬尼拉諒解備忘錄》的內容——而且假如他宣布中國將接受『碳計劃』,我們也會撤回軍隊,之後,雙方必能以解決台灣問題為目的,坐下來好好協商。」
「總統先先,對不起,」奈特說:「『解決台灣問題』是什麼意思?如果您不介意我知道。」
總統深呼吸一口,說:「意思是我們一定會同意台灣島回歸中國主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霍夫曼說。
奈特清清喉嚨,說:「如果他說不呢?」
「您就把他的訊息帶回來給我。」
「我的意思是,您在訊息裡是否會告訴他,如果他拒絕,會發生什麼事?這是不是一種最後通牒?」
總統看了看艾爾斯。
艾爾斯說:「我們希望把焦點放在雙方如何解決危機,而非如果解決不了會發生什麼事。我們要給他一個提議,一個不流血的解決危機的方式。」
總統說:「如果他想拿回台灣,這會是個好辦法。若用侵略的方式,他是得不到台灣的。如果他問了你,你可以這樣轉告他。他會問嗎?」
奈特點點頭。
「那就這樣跟他說。如果他想要台灣,這兒有個辦法,但使用武力是不行的。美國不能讓台灣遭到武力侵犯。」
奈特清清喉嚨,說:「長官,請恕我這麼說,聽起來像是您在勒索他。」
「怎麼說?」
「呃,您說他能夠拿到台灣,但除非他做了某件他不想做的事,他才能拿到台灣。」
「奈特先生,中國非加入『碳計劃』不可。這星球上沒有一個人能夠不加入。這事跟台灣不相干,我就直說吧,無論台灣問題怎麼演變,溫主席都必須簽署。我想說的是,好,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台灣問題上,確實有其歷史合法性。同時,大家不得不大幅削減碳排放,雖然無比艱難,卻也具有歷史性意義。所以,假如雙方可取得某種協議,讓台灣和平與中國統一,假如那有助於他敦促中國人支持『碳計劃』,沒問題,我們一定幫他這個忙。但『碳計劃』是首要議題。台灣則是枝節議題。」
「對他來說可不是。」
「對我們來說是。因此,我們打算在這件事留下彈性。但『碳計劃』就完全沒彈性的空間。『碳計劃』是核心。」
他們陷入沉默。
「好吧。」奈特說。
「您願意傳遞這訊息?」
「我會試試。」
喬•班頓從辦公桌上拿起一個信封。裡頭有他親筆寫下的短箋。
F•威廉•奈特接過它。有輛車子把他載到雷根機場,他的飛機正在那兒等候。接下來十三個鐘頭裡,他都在飛往北京的航道上。
這十三個鐘頭裡,喬•班頓幾乎是一個會議接著一個會議地開。參謀首長聯席會提出他們的計劃,打算先對廣西省的空軍基地發動有限度的攻擊。二天前擊落美國飛行員的戰機便是自該基地飛出。他們提出若干目標,以及後續的攻擊方案,如果有必要的話。他們在戰情室裡用幾張地圖闡釋三種戰局昇高的層級。他們也一一詳述目前關於防衛台灣的若干方案,如果總統下令採用的話。喬•班頓很想知道,北京的某處是否也召開著一樣的會議。他很想知道北京那邊的螢幕上顯示的是何種地圖。
這十三小時之間,美、中雙方的戰鬥機在國際領空上分別出現十八次不到一百公尺的空中接近。浙江省一家克萊斯勒汽車展售門市遭燒毀。美國銀行若干分行辦事處的窗戶遭人砸毀。在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