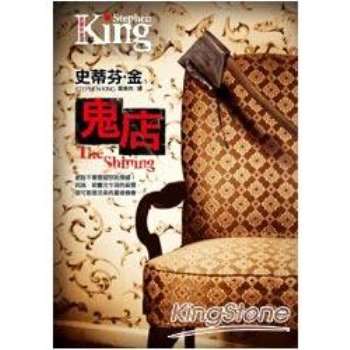◎雪
黃昏。
他們在漸漸微弱的光線下站在門廊,傑克站中間,左手環著丹尼的肩膀,右手摟著溫蒂的腰。他們一同注視著決定權從手中消失。
天空在兩點半之前已佈滿雲層,一小時後開始下雪,這回你不需要氣象預報員來告訴你這場雪非同小可,傍晚風開始呼嘯後,不再有將會融化或吹散的雪花。起先雪以完美的直線落下,逐漸堆起的雪均勻地覆蓋住一切,然而現在,開始下雪後一個鐘頭,風從西北方颳過來,於是雪飄向門廊和「全景」車道的側面。庭園外的公路消失在勻整的白毯之下。樹籬動物也不見了,但是溫蒂和丹尼回到家時,她稱讚他做得很出色。妳這麼覺得嗎?他問,但沒多說什麼。如今樹籬全埋藏在形狀不一的白色斗篷下。
說也奇怪,儘管他們每個人都思考著不同的想法,但都感受到相同的情緒:輕鬆。他們已經渡過橋了。
「春天什麼時候會來呢?」溫蒂喃喃地說。
傑克將她摟得更緊。「很快的。我們進去吃晚餐好不好?外面好冷。」
她微微一笑。整個下午傑克似乎都心不在焉,而且……嗯,怪怪的。現在聽起來比較像平常的他。「我無所謂。丹尼,你呢?」
「好啊!」
於是他們一同進去,留下風低沉的呼嘯聲持續整晚,這聲音他們將會非常熟悉。片片雪花旋舞過門廊。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全景」一直都是如此正面迎接大雪,昏暗的窗戶勇敢地對抗雪花,對飯店如今與世隔絕的事實完全無動於衷。或者也許它樂見這樣的前景。他們三人在它的外殼裡頭忙著傍晚的例行事務,猶如受困在怪獸小腸裡的微生物。◎ 二一七號房內
一週半之後,兩呎深的積雪潔白、均勻地鋪在全景飯店的庭園裡。樹籬小動物園的雪深及動物的腰腿;兔子,凍結在靠後腿站立的姿勢,看起來好像從白色的泳池浮起。有的雪堆超過五呎深。風不停地改變雪堆,將其雕塑成波狀起伏、如沙丘般的模樣。傑克兩度穿著雪鞋笨拙地走到設備倉庫去拿鏟子清理門廊,第三次他聳聳肩,只簡單從門前堆積成塔的雪堆中清出一條小路,讓丹尼在小路左右來回滑雪橇自娛。
真正壯觀的雪堆貼靠在「全景」的西側;有的高達二十呎,而再過去的地面被持續不斷的強風吹颳得連草地都裸露出來。一樓的窗戶蓋滿了雪,從餐廳望出去的景色在休館日曾讓傑克讚嘆不已,如今卻與空白的電影銀幕相差無幾。他們的電話斷訊了八天,歐曼辦公室裡的無線電對講機如今是他們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管道。
現在每天都下雪,有時候只是短暫的飄雪,撒在積雪閃閃發亮的薄硬表面上,有時候則是來真的,風低沉的呼嘯聲拔高成為女人般的尖叫,讓即使深埋在白雪搖籃中的老飯店也令人擔憂地震動呻吟。夜晚的氣溫不超過十度,雖然廚房員工出入口旁的溫度計在下午一、兩點偶爾會到二十五度,但是持續颳著的風堅如刀刃,不戴滑雪面罩外出的話會十分難受。不過陽光照耀的日子,他們一家仍然出門,通常都穿兩套衣服,並在手套外面再戴上連指手套。外出幾乎是種癮頭,丹尼的靈活飛行家雪橇的層疊軌跡環繞在飯店外圍。排列組合幾乎無窮無盡:爸媽拉雪橇,丹尼乘坐;溫蒂和丹尼努力拉,爸爸邊乘邊笑(他們只有在結冰的表面上才可能拉得動他,當細雪覆蓋在表面上時則絕對不可能);丹尼和媽媽一起乘坐;溫蒂獨自一人乘坐,由她的兩個男人負責拉,噴出白色的氣息有如拉貨車的馬匹,假裝她比實際體重來得重。他們乘雪撬繞著屋子巡行時經常歡笑,然而風沒有人性的呼嘯聲卻是如此巨大且虛假,使他們的笑聲顯得渺小而勉強。
他們在雪地上發現了馴鹿的足跡,有一回還看見馴鹿,一群五隻動也不動地站在安全圍籬下方。他們輪流用傑克的蔡司─依康雙筒望遠鏡仔細觀察,注視著牠們讓溫蒂有種古怪、不真實的感覺──牠們站在覆蓋住公路、深及腿部的雪中,她突然想到從現在到春天雪融之前,道路是屬於馴鹿的而不是他們的。此時人類在這兒建構的東西已失效。她相信馴鹿明白這點。她放下雙筒望遠鏡,說些要準備午餐之類的話,然後到廚房哭了一下,試著擺脫心中極為壓抑的感覺,那感覺有時候突然襲來,彷彿一隻巨大的手緊緊壓迫著她的心臟。她想到馴鹿。想起傑克將百麗缽底下的黃蜂,放在員工出入口外面的平台上凍死。
設備倉庫的釘子上掛著許多雙雪鞋,傑克為每個人找到一雙合適的,雖然丹尼的那雙大相當多。傑克用雪鞋走得很順,儘管他只有少年時期在新罕布夏的柏林穿過雪鞋,但他很快又重新學會了。溫蒂不太喜歡雪鞋,光是踩著那雙特大號繫鞋帶的扁平板子,笨重地走動十五分鐘,她的腿和腳踝就劇烈疼痛。不過,丹尼十分感興趣,他認真練習好抓到竅門。他仍時常跌倒,但傑克很滿意他的進步,還說到二月之前,丹尼就能在他們身邊飛快地繞圈圈了。
這天陰沉沉的,不到中午,天空就開始降雪。收音機預報將會再下八到十二吋,並頌讚降雪量──這位科羅拉多滑雪者的大神。溫蒂坐在臥房編織圍巾,自顧自地想著,她完全曉得滑雪者如何能處置那麼多雪。她知道他們到底能把雪放在何處。
傑克在地下室,他下去檢查火爐和鍋爐。自從大雪將他們關閉在屋內後,這種檢查已變成他的例行儀式。確信一切正常之後,他閒蕩過拱門,將燈泡旋上,然後在他找到的老舊、佈滿蜘蛛網的露營椅上坐下,翻閱舊的紀錄和文件,和之前一樣不停地用手帕擦抹嘴唇。長期禁閉使他秋天曬黑的皮膚又白回來,當他拱肩坐著俯視泛黃、帶有裂紋的紙張時,他那紅金色的頭髮凌亂地貼在前額上,看起來有點瘋狂。他發現幾個奇怪的東西塞在發票、提單和收據之間,令人不安的東西:一長條沾有血污的床單;一個看來像是遭到肢解,被砍得支離破碎的玩具熊。還有一張弄縐的紫色女用信紙,在有年代的麝香味底下仍殘留一抹香水味,紙上以褪色的藍墨水寫了一則短箋,但並未完成:「親愛的湯米,我在這上頭沒有辦法如我期望地好好思考,我是指思考我們的事,當然囉,不然還有誰呢?哈哈。一直有事情妨礙我。我作了奇怪的夢,夢到東西在夜裡橫衝直撞,你能相信嗎?還有」就這樣而已。短箋註明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他找到一個看來似乎是女巫或巫師的手偶……總而言之,是留著長牙頭、戴尖頂帽的玩偶,突兀地塞在一疊天然瓦斯的收據及一捆維奇礦泉水的發票中。另外還有看起來像是詩的東西,以深色鉛筆潦草地寫在菜單背面:「梅鐸克/你在嗎?/親愛的,我又夢遊了。/植物在地毯底下移動。」菜單上沒有日期,詩上頭也沒署名,假如這算詩的話。難以理解,卻極為吸引人。對他來說,這些東西宛如拼圖裡的拼圖片,倘若他能找出對的連結拼圖片,所有的東西最後就能組合在一起。因此他繼續尋找,每當身後的火爐轟鳴一聲開始運轉時,就嚇得跳起來並擦拭嘴唇。(待續)丹尼又站在二一七號房門外。
總鑰匙在他的口袋裡。他彷彿吃了興奮劑般渴望地盯著那扇門,穿著法蘭絨襯衫的上半身似乎在抽搐抖動。他不成調地輕輕哼唱著。
他並不想來這裡,尤其是在消防軟管的事情之後。他害怕來這裡。害怕自己又會去拿總鑰匙,違背父親的交代。
他想要來這裡。好奇心
(會害死貓;滿足感會把他帶回來)
無時無刻像根魚鉤在他的腦子裡,又像糾纏不清的誘惑之歌始終無法平息。況且哈洛倫先生不是說過:「我不認為這裡有東西會傷害你?」
(你答應過了。)
(承諾注定是要被打破的。)
他嚇了一跳,彷彿這念頭來自外面,好似昆蟲,發出嗡嗡的聲音,輕柔地誘哄他。
(承諾注定會被打破。我親愛的redrum,被打破。爆裂。粉碎。敲得四分五裂。當心前面!)
他焦躁的哼唱突然轉成低沉、無調的歌曲:「甜心,甜心,奔向我的甜心,奔向我的甜心,我親愛的……」
哈洛倫先生不是對的嗎?這不就是他始終保持沉默,容許這場雪將他們包圍的原因嗎?
只要閉上眼睛,它就會不見。
這間飯店內沒有東西,真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傷害他,假如他走進這間房能向自己證明這一點的話,難道不應該去做嗎?
「甜心,甜心,奔向我的甜心……」
(好奇心會害死貓,我親愛的redrum,redrum我親愛的,滿足感會把他安全無恙地帶回來,從腳趾到頭頂;從頭到尾他都會平安無事。他知道這些景象)
(就像恐怖的圖片,並不會傷害你。可是,噢,我的天啊)
(外婆,妳的牙齒好大啊,那是穿著藍鬍子衣服的狼,還是藍鬍子披著狼的外衣?我真)
(高興你問了,因為好奇心會害死貓,而滿足的希望會帶著他)
走到走廊,輕輕踩在叢林纏繞的藍色地毯上。他在滅火器旁停下腳步,將黃銅噴嘴擺回架上,接著用手指頭反覆戳著滅火器,心臟怦怦跳著,一邊喃喃地說:「來吧,傷害我啊!來吧,傷害我啊!你這摳門的討厭鬼。不敢做吧,你敢嗎?哼?你只不過是個廉價的消防軟管,什麼都不會只會躺在那裡。來啊,來啊!」他覺得自己虛張聲勢得十分愚蠢。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那畢竟只是條軟管,僅僅是帆布和黃銅,你可以將它劈成碎片它也決不會抱怨,不會扭動抽搐,不會流出綠色的黏液,滴得藍色地毯上到處都是,因為它只是管子,既不是鼻子也不是梅子,不是玻璃釦或絲緞帶子,更不是昏睡中的蛇……而他匆匆忙忙,匆匆忙忙的,因為他是
(「遲到了,我遲到了。」白兔說。)
那隻白兔。對了。現在外頭遊戲場邊有隻白兔,原本是綠的,但現在變成白色,彷彿有東西在下雪、颳風的夜晚一再地嚇唬它,把它變老……
丹尼從口袋掏出總鑰匙,插入鎖孔。
「甜心,甜心……」
(白兔正要前往槌球派對,紅皇后的槌球派對上用鸛鳥當球桿,以刺蝟當球。)
他觸摸鑰匙,任手指在鑰匙上徘徊。他的頭感覺疲乏不舒服。他轉動鑰匙,鎖簧平順地彈回。
(砍掉他的頭!砍掉他的頭!砍掉他的頭!)
(儘管球桿很短,但這場比賽不是槌球,這場比賽是)
(敲啊──砰!直接通過三柱門。)
(砍掉他的頭頭頭頭頭頭──)
丹尼把門推開。門滑順地擺盪開來,沒有嘎吱作響。他就站在一大間寢室客廳兩用的組合房間外,雖然雪還沒有積到那麼高──最高的雪堆尚在二樓窗戶底下一呎處──這間房仍昏昏暗暗的,因為爸爸兩個禮拜前將面西的窗戶遮板全關上了。
他站在門口,摸索著右手邊,找到開關面板。頭頂上雕花玻璃燈具裡的兩個燈泡亮了起來。丹尼再往裡跨一步,環顧四周。地毯又厚又軟,是素雅的玫瑰色,令人感到平靜。雙人床上鋪著白色的床罩。一張寫字桌
(請告訴我:為何烏鴉會像寫字桌?)
靠著遮板封起的大窗戶。在飯店的營業季中持續不倦的作家
(享受愉快的時光,希望你害怕)
應該有見識到美麗的山景,可描述給家鄉的親朋好友看。
他再往裡走一些。這裡一無所有,什麼都沒有,只有空蕩蕩的房間,而且寒冷,因為爸爸今天開東側的暖氣。一張書桌;一個衣櫃,門敞開,露出一批飯店的衣架,你無法偷走的那種;一本聖經擱在茶几上。左手邊是浴室的門,一面全身鏡映照著他自己臉色蒼白的影像。那扇門半開著,而且──
他看著自己的替身,緩緩地點頭。
沒錯,無論是什麼東西,它就在此,在那裡面,浴室裡。他的替身往前走,彷彿想要逃離鏡子。替身伸出手來,緊貼住他自己的手。倏地浴室門開了,替身的手因此斜斜地滑開。他往裡瞧。
一個長形而古典的房間,宛如豪華的普爾曼臥車。地板上鋪著細小的白色六角形瓷磚。浴室另一頭有個蓋子打開的馬桶座。右手邊是洗臉台,上方有另一面鏡子,背後藏著藥櫃的那種。左手邊是巨大的白色四爪古典浴缸,浴簾是拉上的。丹尼恍如作夢似地踏入浴室,走向浴缸,彷彿身外有東西推著他向前,彷彿這整件事是東尼帶他去看的夢境之一,當他將浴簾拉開時,或許能看見美妙的東西,也許是爸爸遺忘或是媽媽弄丟的東西,某樣會讓他們兩人感到快樂的東西──
於是他將浴簾唰地一下拉開。
浴缸裡的女人死去很久了。她渾身腫脹青紫,脹氣的腹部浮在寒冷、邊緣結冰的水面上,宛如一座肥肉的小島。她的眼睛凝視著丹尼,又大又呆滯,宛如彈珠。她咧嘴笑著,青紫的嘴角輕蔑地向後拉。她的胸部下垂,陰毛漂浮著。凍僵的雙手有如螃蟹爪,擱在陶瓷浴缸滾著花邊的兩側。
丹尼尖叫,但聲音並沒有從嘴唇逸出,而是不斷地向內再向內,跌落他內心的幽暗處,彷彿石頭掉進井裡。他踉踉蹌蹌地往後退一步,聽見自己腳跟在白色的六角形瓷磚上發出尖銳的聲響,就在這時他失禁了,尿液毫不費勁地溢出。
浴缸裡的女人坐起身。
她仍然咧著嘴笑,大如彈珠的眼睛緊盯著他,一面坐起來,失去彈性的手掌在瓷磚上製造出斷斷續續的雜音,胸部晃盪著宛如年代已久的破損沙袋。她周邊的碎冰破裂時,傳出細微的聲響。她沒有呼吸。她是具屍體,而且已死去多年。
丹尼轉身飛奔,衝過浴室門,他的眼睛嚇得凸出來,毛髮豎直有如刺蝟的毛,嘴巴大張卻發不出任何聲音。他全速奔向二一七號房的外門,如今那扇門已闔上。他奮力地搥門,完全沒注意到門並沒有上鎖,只需要轉動門把就能出去。突然間從他的口中發出震耳欲聾、遠超過人類聽覺範圍的尖叫聲。他只能搥打著門,聽著死去的女人朝他走來,腫脹的腹部、乾枯的頭髮、伸長的雙手──浴缸裡遭殺害也許經年的屍體,奇蹟似地好好保存在那裡。
門打不開,打不開,打不開,打不開。
驀地他想起迪克.哈洛倫的聲音,如此突如其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如此的平靜,於是他閉鎖的聲帶暢通了,開始軟弱地哭泣──不是由於恐懼,而是因為緊張的情緒鬆懈後太過高興。
(我不認為它們會傷害你……它們就像書中的圖片……閉上眼睛,它們就會不見。)
他垂下眼,雙手捲成球狀,肩膀拱起,努力地集中精神:
(那裡沒有東西,那裡沒有東西,那裡沒有東西,那裡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東西也沒有!)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正開始放鬆,正開始注意到門一定沒鎖,他可以出去的時候,那雙經年潮濕、腫脹而有魚腥味的手輕輕地扣住他的喉嚨,執拗地將他轉過身來,直視那張死氣沉沉的青紫色臉龐……
黃昏。
他們在漸漸微弱的光線下站在門廊,傑克站中間,左手環著丹尼的肩膀,右手摟著溫蒂的腰。他們一同注視著決定權從手中消失。
天空在兩點半之前已佈滿雲層,一小時後開始下雪,這回你不需要氣象預報員來告訴你這場雪非同小可,傍晚風開始呼嘯後,不再有將會融化或吹散的雪花。起先雪以完美的直線落下,逐漸堆起的雪均勻地覆蓋住一切,然而現在,開始下雪後一個鐘頭,風從西北方颳過來,於是雪飄向門廊和「全景」車道的側面。庭園外的公路消失在勻整的白毯之下。樹籬動物也不見了,但是溫蒂和丹尼回到家時,她稱讚他做得很出色。妳這麼覺得嗎?他問,但沒多說什麼。如今樹籬全埋藏在形狀不一的白色斗篷下。
說也奇怪,儘管他們每個人都思考著不同的想法,但都感受到相同的情緒:輕鬆。他們已經渡過橋了。
「春天什麼時候會來呢?」溫蒂喃喃地說。
傑克將她摟得更緊。「很快的。我們進去吃晚餐好不好?外面好冷。」
她微微一笑。整個下午傑克似乎都心不在焉,而且……嗯,怪怪的。現在聽起來比較像平常的他。「我無所謂。丹尼,你呢?」
「好啊!」
於是他們一同進去,留下風低沉的呼嘯聲持續整晚,這聲音他們將會非常熟悉。片片雪花旋舞過門廊。將近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全景」一直都是如此正面迎接大雪,昏暗的窗戶勇敢地對抗雪花,對飯店如今與世隔絕的事實完全無動於衷。或者也許它樂見這樣的前景。他們三人在它的外殼裡頭忙著傍晚的例行事務,猶如受困在怪獸小腸裡的微生物。◎ 二一七號房內
一週半之後,兩呎深的積雪潔白、均勻地鋪在全景飯店的庭園裡。樹籬小動物園的雪深及動物的腰腿;兔子,凍結在靠後腿站立的姿勢,看起來好像從白色的泳池浮起。有的雪堆超過五呎深。風不停地改變雪堆,將其雕塑成波狀起伏、如沙丘般的模樣。傑克兩度穿著雪鞋笨拙地走到設備倉庫去拿鏟子清理門廊,第三次他聳聳肩,只簡單從門前堆積成塔的雪堆中清出一條小路,讓丹尼在小路左右來回滑雪橇自娛。
真正壯觀的雪堆貼靠在「全景」的西側;有的高達二十呎,而再過去的地面被持續不斷的強風吹颳得連草地都裸露出來。一樓的窗戶蓋滿了雪,從餐廳望出去的景色在休館日曾讓傑克讚嘆不已,如今卻與空白的電影銀幕相差無幾。他們的電話斷訊了八天,歐曼辦公室裡的無線電對講機如今是他們與外界溝通的唯一管道。
現在每天都下雪,有時候只是短暫的飄雪,撒在積雪閃閃發亮的薄硬表面上,有時候則是來真的,風低沉的呼嘯聲拔高成為女人般的尖叫,讓即使深埋在白雪搖籃中的老飯店也令人擔憂地震動呻吟。夜晚的氣溫不超過十度,雖然廚房員工出入口旁的溫度計在下午一、兩點偶爾會到二十五度,但是持續颳著的風堅如刀刃,不戴滑雪面罩外出的話會十分難受。不過陽光照耀的日子,他們一家仍然出門,通常都穿兩套衣服,並在手套外面再戴上連指手套。外出幾乎是種癮頭,丹尼的靈活飛行家雪橇的層疊軌跡環繞在飯店外圍。排列組合幾乎無窮無盡:爸媽拉雪橇,丹尼乘坐;溫蒂和丹尼努力拉,爸爸邊乘邊笑(他們只有在結冰的表面上才可能拉得動他,當細雪覆蓋在表面上時則絕對不可能);丹尼和媽媽一起乘坐;溫蒂獨自一人乘坐,由她的兩個男人負責拉,噴出白色的氣息有如拉貨車的馬匹,假裝她比實際體重來得重。他們乘雪撬繞著屋子巡行時經常歡笑,然而風沒有人性的呼嘯聲卻是如此巨大且虛假,使他們的笑聲顯得渺小而勉強。
他們在雪地上發現了馴鹿的足跡,有一回還看見馴鹿,一群五隻動也不動地站在安全圍籬下方。他們輪流用傑克的蔡司─依康雙筒望遠鏡仔細觀察,注視著牠們讓溫蒂有種古怪、不真實的感覺──牠們站在覆蓋住公路、深及腿部的雪中,她突然想到從現在到春天雪融之前,道路是屬於馴鹿的而不是他們的。此時人類在這兒建構的東西已失效。她相信馴鹿明白這點。她放下雙筒望遠鏡,說些要準備午餐之類的話,然後到廚房哭了一下,試著擺脫心中極為壓抑的感覺,那感覺有時候突然襲來,彷彿一隻巨大的手緊緊壓迫著她的心臟。她想到馴鹿。想起傑克將百麗缽底下的黃蜂,放在員工出入口外面的平台上凍死。
設備倉庫的釘子上掛著許多雙雪鞋,傑克為每個人找到一雙合適的,雖然丹尼的那雙大相當多。傑克用雪鞋走得很順,儘管他只有少年時期在新罕布夏的柏林穿過雪鞋,但他很快又重新學會了。溫蒂不太喜歡雪鞋,光是踩著那雙特大號繫鞋帶的扁平板子,笨重地走動十五分鐘,她的腿和腳踝就劇烈疼痛。不過,丹尼十分感興趣,他認真練習好抓到竅門。他仍時常跌倒,但傑克很滿意他的進步,還說到二月之前,丹尼就能在他們身邊飛快地繞圈圈了。
這天陰沉沉的,不到中午,天空就開始降雪。收音機預報將會再下八到十二吋,並頌讚降雪量──這位科羅拉多滑雪者的大神。溫蒂坐在臥房編織圍巾,自顧自地想著,她完全曉得滑雪者如何能處置那麼多雪。她知道他們到底能把雪放在何處。
傑克在地下室,他下去檢查火爐和鍋爐。自從大雪將他們關閉在屋內後,這種檢查已變成他的例行儀式。確信一切正常之後,他閒蕩過拱門,將燈泡旋上,然後在他找到的老舊、佈滿蜘蛛網的露營椅上坐下,翻閱舊的紀錄和文件,和之前一樣不停地用手帕擦抹嘴唇。長期禁閉使他秋天曬黑的皮膚又白回來,當他拱肩坐著俯視泛黃、帶有裂紋的紙張時,他那紅金色的頭髮凌亂地貼在前額上,看起來有點瘋狂。他發現幾個奇怪的東西塞在發票、提單和收據之間,令人不安的東西:一長條沾有血污的床單;一個看來像是遭到肢解,被砍得支離破碎的玩具熊。還有一張弄縐的紫色女用信紙,在有年代的麝香味底下仍殘留一抹香水味,紙上以褪色的藍墨水寫了一則短箋,但並未完成:「親愛的湯米,我在這上頭沒有辦法如我期望地好好思考,我是指思考我們的事,當然囉,不然還有誰呢?哈哈。一直有事情妨礙我。我作了奇怪的夢,夢到東西在夜裡橫衝直撞,你能相信嗎?還有」就這樣而已。短箋註明的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六月二十七日。他找到一個看來似乎是女巫或巫師的手偶……總而言之,是留著長牙頭、戴尖頂帽的玩偶,突兀地塞在一疊天然瓦斯的收據及一捆維奇礦泉水的發票中。另外還有看起來像是詩的東西,以深色鉛筆潦草地寫在菜單背面:「梅鐸克/你在嗎?/親愛的,我又夢遊了。/植物在地毯底下移動。」菜單上沒有日期,詩上頭也沒署名,假如這算詩的話。難以理解,卻極為吸引人。對他來說,這些東西宛如拼圖裡的拼圖片,倘若他能找出對的連結拼圖片,所有的東西最後就能組合在一起。因此他繼續尋找,每當身後的火爐轟鳴一聲開始運轉時,就嚇得跳起來並擦拭嘴唇。(待續)丹尼又站在二一七號房門外。
總鑰匙在他的口袋裡。他彷彿吃了興奮劑般渴望地盯著那扇門,穿著法蘭絨襯衫的上半身似乎在抽搐抖動。他不成調地輕輕哼唱著。
他並不想來這裡,尤其是在消防軟管的事情之後。他害怕來這裡。害怕自己又會去拿總鑰匙,違背父親的交代。
他想要來這裡。好奇心
(會害死貓;滿足感會把他帶回來)
無時無刻像根魚鉤在他的腦子裡,又像糾纏不清的誘惑之歌始終無法平息。況且哈洛倫先生不是說過:「我不認為這裡有東西會傷害你?」
(你答應過了。)
(承諾注定是要被打破的。)
他嚇了一跳,彷彿這念頭來自外面,好似昆蟲,發出嗡嗡的聲音,輕柔地誘哄他。
(承諾注定會被打破。我親愛的redrum,被打破。爆裂。粉碎。敲得四分五裂。當心前面!)
他焦躁的哼唱突然轉成低沉、無調的歌曲:「甜心,甜心,奔向我的甜心,奔向我的甜心,我親愛的……」
哈洛倫先生不是對的嗎?這不就是他始終保持沉默,容許這場雪將他們包圍的原因嗎?
只要閉上眼睛,它就會不見。
這間飯店內沒有東西,真的沒有任何東西能傷害他,假如他走進這間房能向自己證明這一點的話,難道不應該去做嗎?
「甜心,甜心,奔向我的甜心……」
(好奇心會害死貓,我親愛的redrum,redrum我親愛的,滿足感會把他安全無恙地帶回來,從腳趾到頭頂;從頭到尾他都會平安無事。他知道這些景象)
(就像恐怖的圖片,並不會傷害你。可是,噢,我的天啊)
(外婆,妳的牙齒好大啊,那是穿著藍鬍子衣服的狼,還是藍鬍子披著狼的外衣?我真)
(高興你問了,因為好奇心會害死貓,而滿足的希望會帶著他)
走到走廊,輕輕踩在叢林纏繞的藍色地毯上。他在滅火器旁停下腳步,將黃銅噴嘴擺回架上,接著用手指頭反覆戳著滅火器,心臟怦怦跳著,一邊喃喃地說:「來吧,傷害我啊!來吧,傷害我啊!你這摳門的討厭鬼。不敢做吧,你敢嗎?哼?你只不過是個廉價的消防軟管,什麼都不會只會躺在那裡。來啊,來啊!」他覺得自己虛張聲勢得十分愚蠢。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那畢竟只是條軟管,僅僅是帆布和黃銅,你可以將它劈成碎片它也決不會抱怨,不會扭動抽搐,不會流出綠色的黏液,滴得藍色地毯上到處都是,因為它只是管子,既不是鼻子也不是梅子,不是玻璃釦或絲緞帶子,更不是昏睡中的蛇……而他匆匆忙忙,匆匆忙忙的,因為他是
(「遲到了,我遲到了。」白兔說。)
那隻白兔。對了。現在外頭遊戲場邊有隻白兔,原本是綠的,但現在變成白色,彷彿有東西在下雪、颳風的夜晚一再地嚇唬它,把它變老……
丹尼從口袋掏出總鑰匙,插入鎖孔。
「甜心,甜心……」
(白兔正要前往槌球派對,紅皇后的槌球派對上用鸛鳥當球桿,以刺蝟當球。)
他觸摸鑰匙,任手指在鑰匙上徘徊。他的頭感覺疲乏不舒服。他轉動鑰匙,鎖簧平順地彈回。
(砍掉他的頭!砍掉他的頭!砍掉他的頭!)
(儘管球桿很短,但這場比賽不是槌球,這場比賽是)
(敲啊──砰!直接通過三柱門。)
(砍掉他的頭頭頭頭頭頭──)
丹尼把門推開。門滑順地擺盪開來,沒有嘎吱作響。他就站在一大間寢室客廳兩用的組合房間外,雖然雪還沒有積到那麼高──最高的雪堆尚在二樓窗戶底下一呎處──這間房仍昏昏暗暗的,因為爸爸兩個禮拜前將面西的窗戶遮板全關上了。
他站在門口,摸索著右手邊,找到開關面板。頭頂上雕花玻璃燈具裡的兩個燈泡亮了起來。丹尼再往裡跨一步,環顧四周。地毯又厚又軟,是素雅的玫瑰色,令人感到平靜。雙人床上鋪著白色的床罩。一張寫字桌
(請告訴我:為何烏鴉會像寫字桌?)
靠著遮板封起的大窗戶。在飯店的營業季中持續不倦的作家
(享受愉快的時光,希望你害怕)
應該有見識到美麗的山景,可描述給家鄉的親朋好友看。
他再往裡走一些。這裡一無所有,什麼都沒有,只有空蕩蕩的房間,而且寒冷,因為爸爸今天開東側的暖氣。一張書桌;一個衣櫃,門敞開,露出一批飯店的衣架,你無法偷走的那種;一本聖經擱在茶几上。左手邊是浴室的門,一面全身鏡映照著他自己臉色蒼白的影像。那扇門半開著,而且──
他看著自己的替身,緩緩地點頭。
沒錯,無論是什麼東西,它就在此,在那裡面,浴室裡。他的替身往前走,彷彿想要逃離鏡子。替身伸出手來,緊貼住他自己的手。倏地浴室門開了,替身的手因此斜斜地滑開。他往裡瞧。
一個長形而古典的房間,宛如豪華的普爾曼臥車。地板上鋪著細小的白色六角形瓷磚。浴室另一頭有個蓋子打開的馬桶座。右手邊是洗臉台,上方有另一面鏡子,背後藏著藥櫃的那種。左手邊是巨大的白色四爪古典浴缸,浴簾是拉上的。丹尼恍如作夢似地踏入浴室,走向浴缸,彷彿身外有東西推著他向前,彷彿這整件事是東尼帶他去看的夢境之一,當他將浴簾拉開時,或許能看見美妙的東西,也許是爸爸遺忘或是媽媽弄丟的東西,某樣會讓他們兩人感到快樂的東西──
於是他將浴簾唰地一下拉開。
浴缸裡的女人死去很久了。她渾身腫脹青紫,脹氣的腹部浮在寒冷、邊緣結冰的水面上,宛如一座肥肉的小島。她的眼睛凝視著丹尼,又大又呆滯,宛如彈珠。她咧嘴笑著,青紫的嘴角輕蔑地向後拉。她的胸部下垂,陰毛漂浮著。凍僵的雙手有如螃蟹爪,擱在陶瓷浴缸滾著花邊的兩側。
丹尼尖叫,但聲音並沒有從嘴唇逸出,而是不斷地向內再向內,跌落他內心的幽暗處,彷彿石頭掉進井裡。他踉踉蹌蹌地往後退一步,聽見自己腳跟在白色的六角形瓷磚上發出尖銳的聲響,就在這時他失禁了,尿液毫不費勁地溢出。
浴缸裡的女人坐起身。
她仍然咧著嘴笑,大如彈珠的眼睛緊盯著他,一面坐起來,失去彈性的手掌在瓷磚上製造出斷斷續續的雜音,胸部晃盪著宛如年代已久的破損沙袋。她周邊的碎冰破裂時,傳出細微的聲響。她沒有呼吸。她是具屍體,而且已死去多年。
丹尼轉身飛奔,衝過浴室門,他的眼睛嚇得凸出來,毛髮豎直有如刺蝟的毛,嘴巴大張卻發不出任何聲音。他全速奔向二一七號房的外門,如今那扇門已闔上。他奮力地搥門,完全沒注意到門並沒有上鎖,只需要轉動門把就能出去。突然間從他的口中發出震耳欲聾、遠超過人類聽覺範圍的尖叫聲。他只能搥打著門,聽著死去的女人朝他走來,腫脹的腹部、乾枯的頭髮、伸長的雙手──浴缸裡遭殺害也許經年的屍體,奇蹟似地好好保存在那裡。
門打不開,打不開,打不開,打不開。
驀地他想起迪克.哈洛倫的聲音,如此突如其來、完全出乎意料之外,如此的平靜,於是他閉鎖的聲帶暢通了,開始軟弱地哭泣──不是由於恐懼,而是因為緊張的情緒鬆懈後太過高興。
(我不認為它們會傷害你……它們就像書中的圖片……閉上眼睛,它們就會不見。)
他垂下眼,雙手捲成球狀,肩膀拱起,努力地集中精神:
(那裡沒有東西,那裡沒有東西,那裡沒有東西,那裡什麼東西也沒有,什麼東西也沒有!)
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他正開始放鬆,正開始注意到門一定沒鎖,他可以出去的時候,那雙經年潮濕、腫脹而有魚腥味的手輕輕地扣住他的喉嚨,執拗地將他轉過身來,直視那張死氣沉沉的青紫色臉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