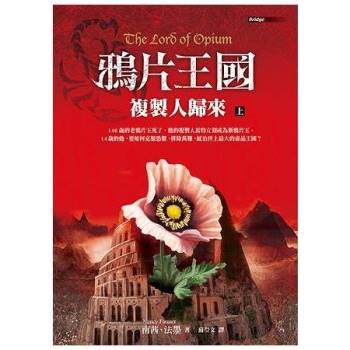第二章 新任鴉片王
前一天晚上,馬特把一匹安全馬留在峭壁下。馬兒遵照他昨晚的指示還在等待,但頭低低下垂,四條腿也在發抖。「喔,不會吧!我怎麼會這麼笨?」馬特大喊一聲,連忙跑向飲水槽。水槽裡還有半滿的水,但是馬沒經過許可不能喝水。他這時也想起馬兒前一晚也沒喝水。明明水槽就在旁邊,但牠會這樣站到渴死。「喝水!」馬特命令馬兒。
馬兒往前走,大口大口喝了起來。馬特拉動唧筒的把手打水,清水先淋到馬頭才流進水槽裡。牠喝個不停,馬特又想起安全馬沒聽到指令也不能停。「停!」他說。
馬兒往後退,鬃毛一邊滴著水。牠喝夠了嗎?會不會喝太多?馬特也搞不清楚。植入馬匹腦中的晶片壓制了這些動物的本能。馬特等了幾分鐘,然後再度命令馬兒繼續喝一些水。
他踩著大石塊坐到馬鞍上。馬特只騎過安全馬,而且馬術不怎麼好,還不會縱身跳上馬鞍。他在大家眼中過於珍貴,不能冒險騎著沒有植入晶片的真馬。「回家。」他下了指令,馬兒服從的沿著小徑緩緩往前走。
太陽升起後空氣便溫暖多了,馬特脫下身上的夾克,騎著馬慢慢行進,他不急著回莊園;因為他有太多事要思考,太多決定要做。幾個月前,馬特還只是個複製人。齷齪的複製人,他修正自己的措辭,因為「複製人」這個字眼本身就有侮辱的意味,而且地位比禽獸還不如。他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供給真人肢體器官,和養來吃的牛一樣,只不過牛還是自然產物,可以得到應有的尊重,甚至有人愛。
複製人比較像是沒人看顧時溜進湯碗裡的蟑螂。然而蟑螂雖然讓人作噁,卻仍是上帝的創造,不像複製人那樣會招來毫無理性的仇恨。馬特在幾個月前的身分便是如此,然後──然後──
鴉片王死了。
馬提奧.阿拉克蘭本尊和所有子孫一起躺在墳墓裡,壓在山下。聯合國代表埃絲帕蘭莎.門杜沙向馬特解釋過,就國際法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有兩個版本,若是如此,法律會宣告其中一人「不是真人」。然而「真人」本尊死後,「複製人」這個說法也無法成立。
馬特告訴埃絲帕蘭莎:我不懂。
這表示你恢復了「真人」地位。你是鴉片王。你具備他的身體、身分,以及相同的DNA,擁有他名下的一切,統御他所有的產業。也就是說,你成了新的鴉片王。「我是真人。」馬特告訴慢慢往前走的安全馬,可惜牠聽不懂也不在乎。這時候他們已經進入了罌粟田,農場裡一年四季都種植作物,而且分別處於不同的生長期,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剛冒出的綠芽、燦白奪目的花朵和飽滿的種子莢。一排排身穿褐色制服頭戴軟帽的呆瓜工人正在照料老植株。他們動作一致,彎腰拿著剃刀劃開種子莢,讓汁液流出來;而負責採收的呆瓜則是要將乾燥的膠汁刮進金屬容器裡。
罌粟田四處都有農場巡邏隊員騎在真馬上監工。巡邏隊員可以決定工人什麼時候休息,什麼時候喝水,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呆瓜工人和安全馬一樣沒有思考能力。他們的腦子同樣植入了晶片,因此才會對勞役般的苦工毫無怨言。傍晚時,農場巡邏隊會將他們趕回長排形的建築內,監獄般的宿舍只有陰暗的小窗戶,天花板低到連站都站不直,但這都不重要,因為呆瓜沒有社交生活。
他們的晚餐是大桶分裝的顆粒食物,吃完後,巡邏隊員會命令他們回宿舍睡覺。馬特不知道他們是睡在乾草上還是直接躺在泥巴地上。他從來沒有走進呆瓜的監獄。
馬特看到成長中期的罌粟田裡有好幾排兒童在拔草除蟲。比起成人的大手,孩子的小手更容易照顧新長出來的細嫩作物。這些童工的年紀從六歲到十歲左右,但由於長期營養不良,他們的真實年齡很可能要大一點。
馬特很震驚。在親眼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前,他不覺得呆瓜兒童比成人可憐。但在看過了正常小孩後,現在他簡直沒辦法忍受孩子受到如此野蠻的對待。馬特不禁開始想像,不知道活潑聰明的小搗蛋菲德里托穿上褐色制服、戴上小軟帽,會是什麼模樣。
「停。」馬特命令安全馬停下腳步,坐在馬背上凝視這群小童工,思索該怎麼幫他們的忙。他可以把這些孩子帶回莊園,讓他們好好吃點東西、睡在真正的床上。但接下來該怎麼辦?難道說聲「玩」,他們就會服從?他能命令他們笑嗎?問題在他們的腦子,而馬特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修復。
他要安全馬繼續走。來到馬廄後,一名年輕男子出來接過韁繩。年輕男人有一雙深褐色眼睛和黑色的頭髮,農場巡邏隊抓到的偷渡者外貌大多是這樣。馬特以前沒看過這個人。「羅薩呢?」他問道。羅薩是馬特小時候的看護人,就因為馬特是複製人,所以一直以殘忍暴虐的方式對待他。鴉片王得知消息後,叫人在羅薩的大腦裡植入晶片,讓她以呆瓜的身分在馬廄裡工作。只要馬特開口,眼神呆滯的羅薩便會慢吞吞的牽出安全馬供他騎乘。
起初,馬特樂得看到羅薩受到懲罰,但越來越覺得不舒服。她過去對他的確不好,但眼見從前的看護人變成沒有靈魂的影子,馬特更加難過。他經常和羅薩說話,希望藉此喚醒她內心深處的感情,但她從來沒有回應。「羅薩呢?」馬特又問了一次。
「你希望換一匹馬嗎,主人?」新來的馬廄工人問道。
「不必了。原來在馬廄工作的女人到哪裡去了?」
「你希望換一匹馬嗎,主人?」年輕男人回答。他不過是另一個無法提供其他答案的呆瓜罷了。馬特轉身離開,朝莊園走去。
鴉片王的大莊園好比沙漠中的綠寶石,周邊有廣闊的花園,噴泉在陽光下潑灑水花,孔雀在通道上漫步,大理石台階上方的陽台種了一圈橙樹。花園裡有幾名真人花匠,他們謙恭的向馬特鞠躬問候。這幾名花匠負責監督一排安安靜靜、拿著花剪修整草坪的呆瓜。
馬特很驚訝,過去這些花匠不曾向他鞠躬,他們當然服從他的指示,但那是出自對鴉片王的恐懼,他知道他們在背後都看不起他。哪裡變了呢?他還沒說出自己的新身分,連對塞麗亞也沒講。無論他是不是真人,塞麗亞對他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他的腳步聲在大廳裡敲出回音,走廊的地板擦得光可鑑人,踩在上面,就像在水面上行走。馬特沒走進阿拉克蘭家族專用的包廂。他一向不屬於那裡,那些成員只留給他心酸的回憶。馬特走向傭人區和塞麗亞掌管的大廚房。
塞麗亞和音樂老師奧疊戈先生、唯一倖存的保鏢達夫特.唐納德,以及帶馬特回鴉片王國的飛行員一起坐在桌邊。這張大木桌用了很多年,桌面布滿歲月留下的痕跡。他叫什麼名字?對,是貝特航少校。他們正在喝咖啡,塞麗亞準備了一盤玉米餅和酪梨沾醬。看到馬特進來,塞麗亞突然起身,差點打翻自己的咖啡杯。
「喔,天哪,天哪。」她反射性的拉起圍裙擦乾潑出來的咖啡。「看看你,我的小心肝。但是我不能再這樣叫你了。喔,天哪。」其他人也站了起來。
「妳高興怎麼喊我都可以。」馬特說。
「不,不可以。你太重要了。但是我喊不出來,沒辦法稱呼你鴉片王。」「當然不要!妳瘋了嗎!你們到底怎麼了?」馬特只想擁抱塞麗亞,但她似乎有些敬畏他。達夫特.唐納德、奧疊戈先生也戰戰兢兢的站著,只有貝特航少校輕鬆的直視他。
「你告訴他們了,是嗎?」馬特指責這名飛行員。
「那又不是祕密。」貝特航少校好像很開心。「埃絲帕蘭莎夫人要我找出阿拉克蘭家族位階最高的人談條件。問題是這個人不存在,他們全死了。」
「你說的談條件是什麼意思?」馬特問道。
飛行員聳聳肩。貝特航少校一頭發亮的黑髮往後梳,臉孔和電影明星一樣英俊。看到他整潔的外表,馬特驚覺自己的衣服散發出一股馬臊味,而且臉上還長滿疹子。「我們要開放邊境。」貝特航少校說:「我載你飛進來的時候你也看到了,鴉片王封鎖了這片土地,只有他的繼承人能夠開放邊境。在來這裡之前,我還不知道該找誰。」
「那個人就是我。埃絲帕蘭莎夫人說我就是繼承人。」
飛行員再度聳聳肩。「你還小,而且你的說法有待查證。這個地方應該由鴉片王的曾孫或玄孫接管。不過──沒錯,現在只剩下你。」
馬特發現貝特航少校不喜歡他,奇怪了,他從前怎麼從來沒注意到呢?他臉上奉承的笑容沒有任何意義,嘲笑的眼光像是要說:三個月前你還是個齷齪的複製人,在我眼裡,你現在還是一樣。不過沒關係,在找到更適合的人選之前,我會將就一點。
光看到這個眼光,馬特便決心採取不合作政策。「我是鴉片王。」他平靜的說。他聽到身後的塞麗亞倒抽了一口氣。「我會直接和埃絲帕蘭莎談判。如果我的傭人還沒幫你安排房間,貝特航少校,我會請他們準備。在我開放邊境後你才能飛回家。」馬特不停的發抖,但竭盡全力不表現出來。他還不習慣命令大人。
貝特航少校嚥了嚥口水,眼神變得冰冷又疏遠。「我們走著瞧。」說完話,他便離開廚房。
馬特癱坐在椅子上。他不敢開口,免得大家聽出他有多緊張,但塞麗亞、奧疊戈先生和達夫特.唐納德的目光只有尊敬。
「太棒了!你讓他退回自己應有的位置了。」奧疊戈先生說話時和聾人一樣缺少高低起伏。達夫特.唐納德則是拍著高舉過頭的雙手表示慶祝。「他一走進莊園就對大家頤指氣使的,」塞麗亞說:「像在他自己家裡一樣發號施令。他說,依據國際法,鴉片王死後你就恢復了真人身分──這我可從來沒懷疑過。跟據他的說法,在法律上你是鴉片王沒錯,但是你太笨,不知道該怎麼做。怎麼可能!我才不那麼想!」她張開雙臂熊抱住馬特,但立刻就放開。「我再也不能這樣抱你了。」
「妳當然可以。」馬特說完話,也回抱塞麗亞。
她嚴肅的拉著馬特的雙手放回他身邊。「不行,小心肝。不管你心裡怎麼想,你現在是鴉片王了,得學會忍下這些動作。」她叫來一名傭人,帶馬特到鴉片王的私人房間去。「你看起來好累,小寶貝。去洗個澡然後小睡一下。我等一下拿乾淨衣服讓你換。」
前一天晚上,馬特把一匹安全馬留在峭壁下。馬兒遵照他昨晚的指示還在等待,但頭低低下垂,四條腿也在發抖。「喔,不會吧!我怎麼會這麼笨?」馬特大喊一聲,連忙跑向飲水槽。水槽裡還有半滿的水,但是馬沒經過許可不能喝水。他這時也想起馬兒前一晚也沒喝水。明明水槽就在旁邊,但牠會這樣站到渴死。「喝水!」馬特命令馬兒。
馬兒往前走,大口大口喝了起來。馬特拉動唧筒的把手打水,清水先淋到馬頭才流進水槽裡。牠喝個不停,馬特又想起安全馬沒聽到指令也不能停。「停!」他說。
馬兒往後退,鬃毛一邊滴著水。牠喝夠了嗎?會不會喝太多?馬特也搞不清楚。植入馬匹腦中的晶片壓制了這些動物的本能。馬特等了幾分鐘,然後再度命令馬兒繼續喝一些水。
他踩著大石塊坐到馬鞍上。馬特只騎過安全馬,而且馬術不怎麼好,還不會縱身跳上馬鞍。他在大家眼中過於珍貴,不能冒險騎著沒有植入晶片的真馬。「回家。」他下了指令,馬兒服從的沿著小徑緩緩往前走。
太陽升起後空氣便溫暖多了,馬特脫下身上的夾克,騎著馬慢慢行進,他不急著回莊園;因為他有太多事要思考,太多決定要做。幾個月前,馬特還只是個複製人。齷齪的複製人,他修正自己的措辭,因為「複製人」這個字眼本身就有侮辱的意味,而且地位比禽獸還不如。他們之所以存在,是為了供給真人肢體器官,和養來吃的牛一樣,只不過牛還是自然產物,可以得到應有的尊重,甚至有人愛。
複製人比較像是沒人看顧時溜進湯碗裡的蟑螂。然而蟑螂雖然讓人作噁,卻仍是上帝的創造,不像複製人那樣會招來毫無理性的仇恨。馬特在幾個月前的身分便是如此,然後──然後──
鴉片王死了。
馬提奧.阿拉克蘭本尊和所有子孫一起躺在墳墓裡,壓在山下。聯合國代表埃絲帕蘭莎.門杜沙向馬特解釋過,就國際法而言,一個人不可能同時有兩個版本,若是如此,法律會宣告其中一人「不是真人」。然而「真人」本尊死後,「複製人」這個說法也無法成立。
馬特告訴埃絲帕蘭莎:我不懂。
這表示你恢復了「真人」地位。你是鴉片王。你具備他的身體、身分,以及相同的DNA,擁有他名下的一切,統御他所有的產業。也就是說,你成了新的鴉片王。「我是真人。」馬特告訴慢慢往前走的安全馬,可惜牠聽不懂也不在乎。這時候他們已經進入了罌粟田,農場裡一年四季都種植作物,而且分別處於不同的生長期,一眼望去,可以看到剛冒出的綠芽、燦白奪目的花朵和飽滿的種子莢。一排排身穿褐色制服頭戴軟帽的呆瓜工人正在照料老植株。他們動作一致,彎腰拿著剃刀劃開種子莢,讓汁液流出來;而負責採收的呆瓜則是要將乾燥的膠汁刮進金屬容器裡。
罌粟田四處都有農場巡邏隊員騎在真馬上監工。巡邏隊員可以決定工人什麼時候休息,什麼時候喝水,什麼時候開始工作。呆瓜工人和安全馬一樣沒有思考能力。他們的腦子同樣植入了晶片,因此才會對勞役般的苦工毫無怨言。傍晚時,農場巡邏隊會將他們趕回長排形的建築內,監獄般的宿舍只有陰暗的小窗戶,天花板低到連站都站不直,但這都不重要,因為呆瓜沒有社交生活。
他們的晚餐是大桶分裝的顆粒食物,吃完後,巡邏隊員會命令他們回宿舍睡覺。馬特不知道他們是睡在乾草上還是直接躺在泥巴地上。他從來沒有走進呆瓜的監獄。
馬特看到成長中期的罌粟田裡有好幾排兒童在拔草除蟲。比起成人的大手,孩子的小手更容易照顧新長出來的細嫩作物。這些童工的年紀從六歲到十歲左右,但由於長期營養不良,他們的真實年齡很可能要大一點。
馬特很震驚。在親眼看到外面的世界以前,他不覺得呆瓜兒童比成人可憐。但在看過了正常小孩後,現在他簡直沒辦法忍受孩子受到如此野蠻的對待。馬特不禁開始想像,不知道活潑聰明的小搗蛋菲德里托穿上褐色制服、戴上小軟帽,會是什麼模樣。
「停。」馬特命令安全馬停下腳步,坐在馬背上凝視這群小童工,思索該怎麼幫他們的忙。他可以把這些孩子帶回莊園,讓他們好好吃點東西、睡在真正的床上。但接下來該怎麼辦?難道說聲「玩」,他們就會服從?他能命令他們笑嗎?問題在他們的腦子,而馬特還不知道該怎麼處理修復。
他要安全馬繼續走。來到馬廄後,一名年輕男子出來接過韁繩。年輕男人有一雙深褐色眼睛和黑色的頭髮,農場巡邏隊抓到的偷渡者外貌大多是這樣。馬特以前沒看過這個人。「羅薩呢?」他問道。羅薩是馬特小時候的看護人,就因為馬特是複製人,所以一直以殘忍暴虐的方式對待他。鴉片王得知消息後,叫人在羅薩的大腦裡植入晶片,讓她以呆瓜的身分在馬廄裡工作。只要馬特開口,眼神呆滯的羅薩便會慢吞吞的牽出安全馬供他騎乘。
起初,馬特樂得看到羅薩受到懲罰,但越來越覺得不舒服。她過去對他的確不好,但眼見從前的看護人變成沒有靈魂的影子,馬特更加難過。他經常和羅薩說話,希望藉此喚醒她內心深處的感情,但她從來沒有回應。「羅薩呢?」馬特又問了一次。
「你希望換一匹馬嗎,主人?」新來的馬廄工人問道。
「不必了。原來在馬廄工作的女人到哪裡去了?」
「你希望換一匹馬嗎,主人?」年輕男人回答。他不過是另一個無法提供其他答案的呆瓜罷了。馬特轉身離開,朝莊園走去。
鴉片王的大莊園好比沙漠中的綠寶石,周邊有廣闊的花園,噴泉在陽光下潑灑水花,孔雀在通道上漫步,大理石台階上方的陽台種了一圈橙樹。花園裡有幾名真人花匠,他們謙恭的向馬特鞠躬問候。這幾名花匠負責監督一排安安靜靜、拿著花剪修整草坪的呆瓜。
馬特很驚訝,過去這些花匠不曾向他鞠躬,他們當然服從他的指示,但那是出自對鴉片王的恐懼,他知道他們在背後都看不起他。哪裡變了呢?他還沒說出自己的新身分,連對塞麗亞也沒講。無論他是不是真人,塞麗亞對他的愛永遠不會改變。
他的腳步聲在大廳裡敲出回音,走廊的地板擦得光可鑑人,踩在上面,就像在水面上行走。馬特沒走進阿拉克蘭家族專用的包廂。他一向不屬於那裡,那些成員只留給他心酸的回憶。馬特走向傭人區和塞麗亞掌管的大廚房。
塞麗亞和音樂老師奧疊戈先生、唯一倖存的保鏢達夫特.唐納德,以及帶馬特回鴉片王國的飛行員一起坐在桌邊。這張大木桌用了很多年,桌面布滿歲月留下的痕跡。他叫什麼名字?對,是貝特航少校。他們正在喝咖啡,塞麗亞準備了一盤玉米餅和酪梨沾醬。看到馬特進來,塞麗亞突然起身,差點打翻自己的咖啡杯。
「喔,天哪,天哪。」她反射性的拉起圍裙擦乾潑出來的咖啡。「看看你,我的小心肝。但是我不能再這樣叫你了。喔,天哪。」其他人也站了起來。
「妳高興怎麼喊我都可以。」馬特說。
「不,不可以。你太重要了。但是我喊不出來,沒辦法稱呼你鴉片王。」「當然不要!妳瘋了嗎!你們到底怎麼了?」馬特只想擁抱塞麗亞,但她似乎有些敬畏他。達夫特.唐納德、奧疊戈先生也戰戰兢兢的站著,只有貝特航少校輕鬆的直視他。
「你告訴他們了,是嗎?」馬特指責這名飛行員。
「那又不是祕密。」貝特航少校好像很開心。「埃絲帕蘭莎夫人要我找出阿拉克蘭家族位階最高的人談條件。問題是這個人不存在,他們全死了。」
「你說的談條件是什麼意思?」馬特問道。
飛行員聳聳肩。貝特航少校一頭發亮的黑髮往後梳,臉孔和電影明星一樣英俊。看到他整潔的外表,馬特驚覺自己的衣服散發出一股馬臊味,而且臉上還長滿疹子。「我們要開放邊境。」貝特航少校說:「我載你飛進來的時候你也看到了,鴉片王封鎖了這片土地,只有他的繼承人能夠開放邊境。在來這裡之前,我還不知道該找誰。」
「那個人就是我。埃絲帕蘭莎夫人說我就是繼承人。」
飛行員再度聳聳肩。「你還小,而且你的說法有待查證。這個地方應該由鴉片王的曾孫或玄孫接管。不過──沒錯,現在只剩下你。」
馬特發現貝特航少校不喜歡他,奇怪了,他從前怎麼從來沒注意到呢?他臉上奉承的笑容沒有任何意義,嘲笑的眼光像是要說:三個月前你還是個齷齪的複製人,在我眼裡,你現在還是一樣。不過沒關係,在找到更適合的人選之前,我會將就一點。
光看到這個眼光,馬特便決心採取不合作政策。「我是鴉片王。」他平靜的說。他聽到身後的塞麗亞倒抽了一口氣。「我會直接和埃絲帕蘭莎談判。如果我的傭人還沒幫你安排房間,貝特航少校,我會請他們準備。在我開放邊境後你才能飛回家。」馬特不停的發抖,但竭盡全力不表現出來。他還不習慣命令大人。
貝特航少校嚥了嚥口水,眼神變得冰冷又疏遠。「我們走著瞧。」說完話,他便離開廚房。
馬特癱坐在椅子上。他不敢開口,免得大家聽出他有多緊張,但塞麗亞、奧疊戈先生和達夫特.唐納德的目光只有尊敬。
「太棒了!你讓他退回自己應有的位置了。」奧疊戈先生說話時和聾人一樣缺少高低起伏。達夫特.唐納德則是拍著高舉過頭的雙手表示慶祝。「他一走進莊園就對大家頤指氣使的,」塞麗亞說:「像在他自己家裡一樣發號施令。他說,依據國際法,鴉片王死後你就恢復了真人身分──這我可從來沒懷疑過。跟據他的說法,在法律上你是鴉片王沒錯,但是你太笨,不知道該怎麼做。怎麼可能!我才不那麼想!」她張開雙臂熊抱住馬特,但立刻就放開。「我再也不能這樣抱你了。」
「妳當然可以。」馬特說完話,也回抱塞麗亞。
她嚴肅的拉著馬特的雙手放回他身邊。「不行,小心肝。不管你心裡怎麼想,你現在是鴉片王了,得學會忍下這些動作。」她叫來一名傭人,帶馬特到鴉片王的私人房間去。「你看起來好累,小寶貝。去洗個澡然後小睡一下。我等一下拿乾淨衣服讓你換。」